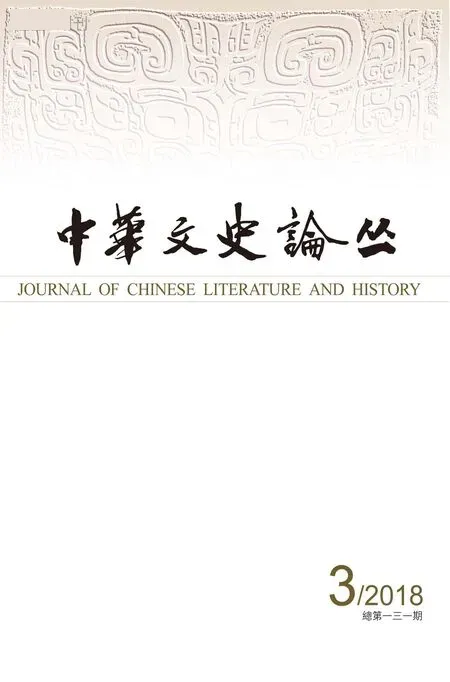清朝西進與17—18世紀士人的地理知識世界❋
馬子木
提要: 17—18世紀士人地理知識世界中有關西域、中亞認知的擴充,與清代政治史進程密切相關。康熙年間考訂河源成爲朝廷與士人雙方共同的興趣,隨着西北經略的推進,河源成爲彰顯盛治的符號,聖祖並試圖利用經學傳統化新土爲舊疆。動機各異的士人逐漸熟悉原被視作異域的西域,其地理知識亦較明人大爲增長。乾隆朝底定新疆後,朝廷對“同文”理念的構築、文臣紀功詩文的創作都構築起西域與中土、漢唐與本朝的連續性,成爲盛清時期大一統論述的基礎邏輯之一,部分士人的治學興趣也開始轉向西域史地、宗教。士林與朝廷對西域的興趣最初淵源各異、旨趣不同,卻最終匯爲一流,改變了明代四夷書寫想象與事實並存的局面,也徹底更新了士林對西域的認知,構成西北史地學興起所必須憑藉的知識基礎。
關鍵詞:西北輿地學 河源 三危 同文之治 大一統
王國維論清學三變,邊疆輿地學的盛衰爲其表徵之一,所謂“道咸以降,塗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注]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載《王國維遺書》(2),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2011年,頁583。梁啓超的表述更爲透徹,“康乾兩朝,用兵西陲,辟地萬里。幅員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頻繁,復覺研求之有藉”。[注]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380。歸結言之,盛清時期大一統國家疆域的形成促使學者開始關注邊裔,道咸以降邊疆史地學的研究則在“世變”的刺激下達到了空前盛況。晚近學者多持此論,以爲西北輿地之學於嘉慶朝正式形成,道咸以降乃至全盛,其中既有經世思潮之影響,又有外侮邊患之刺激。[注]趙儷生《論晚清西北之學的興起》,《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郭雙林《論清嘉道年間的西北輿地學》,《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徐松巍《關於十九世紀邊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侯德仁《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北京,羣言出版社,2006年。無可否認,西北輿地之爲“學”,確肇始於嘉慶,然而其作爲一種“知識”,則淵源有自,且非中土士人所陌生。“學風”之生成,必待與學人生活世界、知識世界的交錯。本文所關注的是西北輿地學的“周邊”: 其興起以前時代的士人,他們有關“西域”、“新疆”的知識爲何,又是藉助何種資源來形塑的。先行研究於清初至嘉慶初之“發端期”多有貶抑,如謂其成績僅集中於官書,零散而不成氣候,[注]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1—22,38。惟黃愛平於乾隆朝西北邊疆著作的評價殊爲公允,認爲其關乎治道,是十九世紀邊疆史地學興起的基礎。[注]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文化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275—276。本文則欲嘗試,能否在脈絡化的學術史敍事之外,在士人知識世界與政治文化的交互之中,尋找西北輿地學興起的另一種可能。
一 明清西域形象的製作與傳遞
討論十八世紀士人地理知識世界的“變”與“新”,必須首先檢視在此之前,士人如何認知與想象西域。有關西徼的知識來源固有多種,加之士人羣體的複雜性,事實上不可能全面評估其知識圖景。本節僅選取作爲讀者與作者的士人,考察其一面如何由業已寫定的文本中獲得四裔的知識,一面又如何整合而創造新的文本。
對於明代士人而言,“西域”是一個並不陌生的概念。[注]今人所論“西域”,多指天山南北路,不出蔥嶺以西,與“中亞”爲對稱。但帝制時期的“西域”概念則甚爲寬泛,凡中央政府郡縣統治極西之外,以至波斯地區,皆可視爲“西域”,如明人便謂“嘉峪關外並稱西域”,參見萬曆《大明會典》卷一百七,《續修四庫全書》(791),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頁92下。爲敍述之便,本文仍從時人之界定。歷代正史大抵皆有敍述西域之專篇。中古以後,西行歸來的使者、僧侶亦留下許多記述。就政治實踐言之,明代承元之後,對蒙元的政治遺產多有繼承,如成祖便自視爲忽必烈之繼承者。[注]David Robinson:“The Ming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the Yuan Mongols”, in idem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367-369, 401-402, 407-409.來自所謂“西域三十八國”[注]《大明會典》卷一〇七,頁94下。的貢使絡繹往來於京師,《會典》中亦詳細開列了撒馬爾罕等“西戎朝貢國”之名。
由歷代正史構成的較爲連續的文本傳統,雖然在理論上成爲明人獲知西域史地知識最權威的來源,但明人所面對的西域格局,經由伊斯蘭化與蒙古統治,已非復故貌。而在與西域進行朝貢貿易、外交往來的過程中,朝廷勢必對各國情勢有所知曉,然而這些情報並非明朝主動蒐集,不過是朝貢體系的副產品之一而已。各國之“貢使”資格亦多售予商人,[注]C. Wessels: Early Jesuits Trav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2, p.25.此輩所呈述的信息,其可信程度頗堪懷疑。其實明人早已認識到“其番文方物大率相同,雖間有慕義而至者,然亦難辨其真僞也”。[注]張天復《皇輿考》卷一八《萬集·四夷考》,明天啓刻本,葉20b。
事實上真正影響到明人西域圖景的是明初西使諸臣所撰寫的行記或報告,其中尤以陳誠的《西域番國志》與《西域行程記》最著。陳氏於永樂間奉使哈烈,歸朝後作有是書。是時雖去元未遠,但元朝橫貫歐亞的地理學知識卻未被完整繼承,在明初士人的知識世界中,撒馬爾罕已是極邊。[注]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外篇卷一胡《送陳員外使西域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6),濟南,齊魯書社影印,1997年,頁359上—下。因此,陳誠留下的基於耳聞目擊的第一手記述,自然成爲明人西域與中亞知識最重要的來源。兩書雖在明代未單獨刻印,但並不難看到,《太宗實錄》便附有題爲《西使記》之節略本;正統間梓行的《陳竹山先生文集》,亦錄有《番國志》全文。[注]王繼光《陳誠及其西使記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75—179。官修地理志書亦不免受到陳誠的影響。天順間修成的《大明一統志》,記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等處風俗,即多取陳氏之書爲之。[注]李賢等纂《大明一統志》卷八九,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1990年,頁1375上—1376下。
陳誠之書亦以鈔本形式在士大夫間流通,傅增湘藏有寫本《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乃“明海鹽鄭端簡曉家寫本”。[注]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2)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53。鄭曉爲浙江海鹽人,除曾短暫擔任鳳陽巡撫外,一生仕宦皆在兩京,不過卻成爲明中葉以降首位系統對邊疆四裔展開探究的學者。鄭氏素以淹博稱,任兵部主事時,“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注]焦竑《國朝獻徵錄》卷四五,《刑部尚書端簡公曉傳》,《明代傳記叢刊》(111),臺北,明文書局影印,1991年,頁197。並纂輯《九邊圖志》,取閱文牘檔案的同時,亦向邊吏咨詢,頗得邊塞故實。鄭氏遺著有《吾學編》,其稿創始甚早,其中《皇明四夷考》與《皇明北虜考》專述邊徼史事,後者取材於舊檔、案牘、奏議與《實錄》,考證尚稱精詳。[注]唐豐姣《淺論〈皇明北虜考〉的史源與史料價值》,載《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23—232。相較於《北虜考》,《四夷考》的撰述則較爲簡單,亦嫌粗疏,很大程度上當由於鄭氏所讀到的西域記述甚少。筆者曾以巴達克山爲例,討論過《吾學編》書寫的特徵與疏漏。大致言之,鄭曉所撰述的是一個時間上斷裂的西域史,先代典故與本朝故實都有所缺失;就前者論,鄭氏幾乎未能上溯西域諸城的歷史,在蔥嶺以東者如于闐、哈密等雖間有上溯至漢唐者,但蔥嶺以外則鮮溯其源流,文本中呈現的是一幅共時性的西域圖景。[注]參見拙稿《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 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頁351—355。
因同時代材料所限,鄭曉對各國的書寫是不均等的。大抵陳誠書中敍及者,鄭氏則節略其文而述之,反之則但據傳聞而已,故造成了一種真僞雜陳的西域圖景。即以伊斯蘭化爲例,陳誠已注意到若干表徵,[注]陳誠《西域番國志·哈烈》,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8—69。雖未指出其教爲何,但絶非佛教可知。鄭曉的改寫甚爲有趣,凡述其祭祀、宗教禮俗之文悉被删落,而地處哈烈與葉爾羌之間的巴達克山(八答黑商),則仍被視作佛教國家,“人俗樸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宫”,唐代佛教西域的印象依然影響到明代士人的異域想象。[注]鄭曉《吾學編》卷六八《皇明四夷考》下,《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46),頁48下。另一方面,鄭曉的書寫也體現出想象與事實間的張力,如謂撒馬兒罕有世傳之國寶“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哈烈“人多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注]鄭曉《吾學編》卷六八《皇明四夷考》下,頁40上,43上。云云,皆不見陳誠書,當另有來源,其事近小説家言,殊屬不經,卻成爲中土士人想象西域的重要意象。
米華健認爲,清初士人西域知識的來源大致有漢唐舊史、筆記、僧侶遊記、詩賦乃至通俗小説等。[注]Jame A. 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2), Dec., 1999, p.66.若置於晚明,亦大體成立。由於缺少明中葉的私人藏書目錄,很難判斷有明士大夫平日可能接觸到何種與西域有關的書籍。目前可見較早的材料已遲至嘉、隆之際。據高儒、晁瑮之藏書目錄,二人所藏有關西邊之書甚少,高氏僅有《異域志》一部;晁氏有《異域志》二卷及《咸賓錄》《玉門重譯》兩種。[注]高儒《百川書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71;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91。《異域志》係元人周致中撰,與當時流行之《異域圖志》相類,大抵“摭拾諸史及諸小説而成,頗多疏舛”,四庫館臣便譏其“無足采錄”。[注]《四庫全書總目》(1)卷七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2年,頁678下。
常熟錢氏與山陰祁氏爲晚明江南大族,頗富藏書,並編製有詳細的藏書目錄,由其書目可見是時核心圈知識精英有關西域知識的來源。限於篇幅,此處僅列出專記西域的書籍,《實錄》、政書、地理總志及明人所撰之本朝史書概不列入。
士大夫的藏書目錄往往經過精心編撰,且所藏未必即等於所讀,難以據之完全還原其閱讀情況。不過上表已可説明,晚明精英士人事實上可以接觸到涉及西域的不同文類的著述。除未列入的官修史籍外,還有關注邊疆的學者、官員如張雨、馬文昇、嚴從簡等人的著作,亦有抄撮而成的雜纂之書。
隆慶、萬曆間,九邊擾攘,邊政逐漸引起士人的興趣,湧現出大量關於邊疆與異域的著作。而《實錄》鈔本亦在此前後流傳於士人間,加之出版業的繁榮,編纂本朝史與本朝地理總志蔚然成風,四夷大抵皆有專篇。甚至邊緣的士人亦參與其中。歸安人慎懋賞由監生任保定安州吏目,其父曾任漳浦知縣,慎懋賞或因此對域外頗有興趣,輯有篇幅不短的《四夷記》,雖抄撮諸書、不知辨别,幾無體例可言,但亦可見一時風氣之好尚。[注]道光《武康縣志》卷十,《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年,頁1280;萬曆《保定府志》卷八,《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1992年,頁212上。必須説明的是,由於邊患所在,諸書之關注點多在北部邊疆與西北哈密一線,義的西域諸國本非重點,其敍述大抵節鈔鄭曉之文,多不足觀。鄭曉遂成爲此一風潮的早期創始者,而其《吾學編》則成爲明後期各類“四夷文本”的來源。不過與《吾學編》相似,這些文本所呈現出的則是斷裂的西域圖景,又雜入奇幻的異域想象,不免出現小説家言。當事實與傳説、陳迹與今世的區隔固化成爲明代四夷志書的文類特徵,因有舊文可襲,作者本身並不需對西域有足夠的認知,便可遵循格式化的書寫策略編竣全卷。[注]如慎懋賞纂《四夷記》,內尚有“回紇”、“西夏”等條目,此書有《玄覽堂叢書續集》影印本。晚明四夷志書多出,而價值不宜高估,蓋由於此。
二 經世學術、河源考訂與西北經略
明清易代並造成明代四夷文本傳遞的斷裂,如明人關於撒馬爾罕出產“照世杯”之想象,在清初由士人繼承,並最後進入《明史》。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清朝亦在與準噶爾、俄羅斯的不斷交往中構築其西域圖景,朝廷的西北史地知識大爲擴展,康熙朝之修《皇輿全覽圖》、雍正朝之修《十排圖》,皆是明證。不過此類輿圖深藏秘府,即使是供職朝廷的士人亦難得一見原本,對士人影響甚微。本節關注的重點並不在官方的測繪工作,而是“西北”在康熙年間如何成爲朝廷與士人、官員與遺民間共同的學術話題,學術與政治的交錯,在此宛然可見。
明代士人撰述四夷志書者,率未親至其地,但不乏有異例存在。明中期以降,逐漸產生一篇記述自嘉峪關至西魯迷城(今伊斯坦布爾)沿途路程、山川、城池、風俗的《西域土地人物略》。[注]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趙永復《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亞、西亞地名考釋》,《歷史地理》第21輯。因係親身經行者的記述,較之士人僅知依憑文本經驗,自不可同日而語。其文最早收錄於嘉靖《陝西通志》,[注]嘉靖《陝西通志》卷十《土地六·西域》,《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5年,頁28—66。但在明代影響有限,晚明邊政書層出不窮,而曾引用其文者僅有張雨《邊政考》,且變易爲表格形式。[注]張雨《邊政考》卷八,《續修四庫全書》(738),頁148上—155上。明清易代後,此份文本的際遇也隨着士人對西徼認知的漸進而發生變化。顧炎武最先注意及此,並全文收入《天下郡國利病書》。康熙前期梁份纂輯《秦邊紀略》,亦以此文錄於書末。梁份曾從學於彭士望,素有經世之志,好遊歷四方,“燕趙秦晉吴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迹之所及矣”。[注]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十三《梁質人文集序》,《清代詩文集彙編》(174),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0年,頁116下。其人“留心邊事已久”,於西陲尤所關心,與邊將相熟,“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遊牧,暨其强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注]劉獻廷《陽雜記》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65。
二人的學術興趣並非個例,實與清初的社會風潮有關。明清易代使北虜、套虜之患不復存在,九邊的戰略地位亦開始下降。不過“西北”仍然頻繁出現於士人的經世文字之中,在明遺民或對勝朝抱有好感的士人看來,“西北”代表一種“土厚水深、風俗剛厲、人鮮驕惰、國易富强”的風俗,“爲可畏而可愛也”。[注]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關中王子詩集序》,載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62。遺民中若顧炎武、屈大均皆曾親至關中塞上,傅山則自署“西北之西北老人”,莫不有一種“西北情結”在焉。[注]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94—98。流風所及,無論心念勝朝的士人抑或興朝新貴,多有開始關注西北者。如劉獻廷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注]劉獻廷《陽雜記》卷四,頁197。必須説明的是,遺民所謂的“西北”大抵指關中一帶而言,雖然尚未涉及嘉峪關外,但反復的論説至少已將部分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西北。這種士人社羣中自覺自發的行爲,其影響力雖較有限,然而已爲後來朝廷主導的知識工程導夫先路。
康熙、雍正兩朝是清代大一統國家的形成期,隨着朝廷針對西陲不斷的軍事行動與使者往來,朝廷的地理知識亦持續擴展。在討論朝廷與士人的互動前,有必要檢視的是,域外地理知識的傳播是否在滿漢之間有所區隔。馬世嘉(Matthew Mosca)以清初對奧斯曼帝國的認識爲例,認爲是時邊疆地理知識在滿—蒙與漢人間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場域,多語言的邊疆情報在前者間流通,後者則一直沿用明人的材料。[注]Matthew W. Mosca:“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 p.152.作者發現1850年代前漢文史料中對奧斯曼帝國(控噶爾)的記述寥寥無幾,如揆敍《隙光亭雜識》、錢良擇《出塞紀略》與圖理琛《異域錄》。揆敍、圖理琛之書分别代表了時人對奧斯曼帝國的兩種觀點,然而是否因其作者是滿洲人,便由此認爲滿、漢地理知識世界間的區隔,實頗成問題。圖理琛之知識來源爲俄人,乃出使時所聞,而揆敍則號稱聞自蒙古、西洋人,[注]揆敍《隙光亭雜識》卷二,《續修四庫全書》(1146),頁47下。要之揆敍之書以漢文撰述,而《異域錄》亦同時有漢文版。馬世嘉謂私撰地志與邊疆行記本爲文學精英(writing elite)之專屬,清初滿洲人多因其教育背景之缺乏而難於下筆,圖理琛、揆敍二人受到良好的漢文化教育,故屬例外。[注]Matthew W. Mosca:“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pp.158-159.事實上,圖理琛、揆敍的撰述皆遵循來自中原文化傳統的書寫範式,如《隙光亭雜識》,“全書所著,皆爲經史之學,蓋平日讀書見得所識,隨筆而記”,[注]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2),濟南,齊魯書社影印,1996年,頁526下。與康熙朝顯宦如王士禛等喜爲説部之書以粉飾太平者,蓋同出一脈。[注]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頁157—158。此一淵源既明,則二書自然不可代表彼時地理學中的“滿洲傳統”,後者之存在也無法得到足夠的文獻證據。易言之,較之“滿”與“漢”,“朝廷”與“士人”之對舉毋寧説更能代表十八世紀初期地理知識世界的區隔。
然而此種區隔卻非截然的斷裂。清代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從“異域”到“舊疆”的轉換,並非僅得益於軍事行動與設官分職,更有待於意識形態與知識體系的整合,特别是歷史學與輿地學傳統的應用。朝廷對統治合法性的論證、經世學者對實學的講求,在此匯聚爲一。康雍兩朝關於河源的考述、關於西藏源流的辨説,雖皆屬輿地考證的範疇,卻有皇權隱然的宰制,由是構成大一統國家形成前期政治與學術相互交錯的場景。
河源素爲歷代史家聚訟所在。明正德、嘉靖以降,因河患頻仍,河臣始自黃河水性的角度探討治河之策,河源遂成爲不可回避的問題。嘉靖中,河南按察司僉事車璽作《治河總考》,自《河南總志》中抄出黃河“源出星宿海”一段,附於書末,此似爲今可見之河臣關注河源之始。[注]車璽《治河總考》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21),頁242下。後河南巡撫吴山病其疏漏,遂命重訂爲《治河通考》,特列“河源考”一卷,摘錄《禹貢》以至《元史》的記述,但無所論斷。[注]吴山《治河通考》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21),頁517下—524下。車璽、吴山等皆因職任所繫,故用心於河源問題,然其抄撮舊史,不可視之爲謹嚴的考據,而同時之士林中也未出現相應的響應。
直至康熙中葉前後,考訂河源方成爲京中部分士人社羣中的風尚。《明史》與《一統志》陸續開館纂修,使一批素有經世之志的精英士人雲集京師,並與朝中文臣交遊,因之形成的不僅是占有大量文化資源的士人社羣,更是一個新的、具有話語權與影響力的學術論辯場域。[注]期間以《明史》館爲中心的士人往還與學術討論,參見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萬斯同作爲此一社羣的核心,最富盛名,延續浙東學術的傳統,在京師組織了講會,聽者甚衆。據曾躬逢康熙三十四年講會盛況的陳正心回憶:
時苕上温子鄰翼亦在都,與先生爲講會,士大夫聚者常數十人。先生據高座,凡禮樂源流、典章沿革、圖書曆象、河渠邊務,惟所欲奮袖抗談,問難蜂起,應之如響。[注]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卷首陳序,揚州,江蘇陵古籍刊行社影印,1990年,頁13—14。
“河渠邊務”成爲講會的主題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既是甬上證人社講求名物制度與文獻精確性學風的延續,又是清初數十年間經世學者注意力向邊陲、向西北轉移的體現。遺憾的是,《講會錄》早已散佚,講會中所討論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河源考訂無疑是萬斯同頗感興趣的問題。京師修史期間,萬氏撰有《崑侖河源考》一卷,大旨以元代潘昂霄所志與《史記》《漢書》不合,《水經》所述亦有謬誤,故歷引《禹貢》、諸子及正史之文以證之。根據林佶的序文,萬斯同撰此書“馳騁絶域”,旨在爲治河提供資鑑。[注]萬斯同《崑侖河源考》卷首林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79册,頁319下。誠如李慈銘所評論,“書闕難稽,事非目驗,終亦不得而詳也”,[注]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536。萬氏考訂河源,未必對本朝河工或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有何助益,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建立一種新的學術話題或典範,將河源與西北地理引入京師學人的討論場域之中。
對河源感興趣的不僅有學者,亦有朝廷。早在萬斯同入京修史的六年前,聖祖便已在試策中有所表露。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聖祖考試詞臣,題目之一便是“河源考”。[注]葉方藹《葉文敏公集》,《御試河源考》,《清代詩文集彙編》(113),頁12上;張廷玉《澄懷園文存》卷十五《先考敦復府君行述》,《清代詩文集彙編》(229),頁502上。參與考試的共有46人,[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1),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九日,頁87。部分應答文字因收入文集而倖存,筆者並未系統蒐集,僅就檢覽所及共找到葉方藹、徐乾學、張玉書的三份答卷。與萬斯同不同,這三篇文字較少有考辨的意味,詞臣應制作文,本不能爬梳舊籍、進行精細的文本考證,惟就正史縷述漢以降河源異説而已。在詞臣看來,河源方位的爭辯至潘昂霄已大抵告終,無再辨之必要。其旨趣乃是通過河脈了解水性,以爲朝廷治河提供某種資鑑,如徐乾學提醒治河者“自周以來,無代不有河患,竭人力以捍之,而僅乃得安”;[注]徐乾學《憺園文集》卷十八《河源考》,《清代詩文集彙編》(124),頁482下。張玉書則關注到河、淮治理的問題,“今日之患不在河强淮弱,而在河淮分流、悍不相顧,而河不爲我用”;[注]張玉書《張文貞公集》卷三《河源考》,《清代詩文集彙編》(159),頁419上。葉方藹以爲既藉黃河以利漕,必“必防其北行”,同時參酌明人治河舊法,舉述邱濬興西北水利以紓東南之策。[注]葉方藹《葉文敏公集》,《御試河源考》,頁12上—13下。治河是貫穿康熙朝始終的重要政治議題,聖祖“自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厪念,曾書而懸之宫中柱上”,[注]《清聖祖實錄》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清實錄》(5),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5年,頁701下。加之此時淮揚“連年饑饉,民不聊生”,[注]《康熙起居注》(1),康熙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頁42。故以此題考試詞臣。
不過河源之於朝廷,不僅僅有治河資鑑之效,更成爲朝廷聖德與國家大一統的符號,尤具深厚的政治文化意涵。在士人看來,無論河源於崑侖抑或于闐,都是渺遠的絶域,是前此王朝所難以企及的地域,不過這一印象卻隨着康熙中葉以降朝廷治權向西擴展而改變,“河源”逐漸成爲一個可以感知且探索的地區。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三十六年,聖祖三度親征噶爾丹,班師告捷後,便有士人在“西師”與“河源”間建立隱然的關聯。如曾扈從親征朔漠的陳元龍,於康熙三十七年作《神武北平詩》十六首,其十二云:
振旅狼山度翠旛,龍舟天外溯河源。大荒自古無人渡,斷岸從今有棹痕。
斗象南看皆奉朔,流沙西去亦稱藩。穹廬悚息同編戶,不用黃雲塞上屯。[注]陳元龍《愛日堂詩》卷十《環召集四》,《清代詩文集彙編》(183),頁204下。
漢之張騫、唐之蔡元鼎,所訪河源,皆不過玉門關外,紀載寥寥;元之都實,遠履發源之地,紀其分流伏脈,歷歷可指,較之往代,相去懸絶。論者乃以爲無益,何也?[注]玄燁《御製文集第二集》卷三九《閱史緒論》,《清代詩文集彙編》(192),頁482上。
此篇筆記當寫於康熙三十六年前,是時聖祖即有探索河源之意,而政局未定,亦不可得。親征平準戰爭勝利後,聖祖明確將“河源”與國家之治世相關聯。第二次親征班師途中,聖祖臨流興嘆,作有《黃河》詩,其詩序略云:
河源發於塞外,流經萬里餘,始由中土入海。曩曾遣使探流窮源,河之爲利爲害,莫不洞悉。……明弘治間,(河套)淪於外彝地逼秦境。……國家威德所布,龍荒大漠與河套盡入版圖,諸蒙古歲修賮貢,奉職惟謹,非務德意綏柔,詎兵力之所可致耶?[注]玄燁《御製文集第二集》卷四七《黃河(并序)》,頁565下—566上。
河套地區在明代久受蒙古諸部之擾,而清朝則“咸施沐浴恩”,內外一體、並無分别,亦得廓清並納入“版圖”。同時,東南河工也因河源的廓清而受益,“東南”與“西北”在此連爲一體,成爲清朝“大一統”國家構造的明確體現,即如聖祖詩尾所云“期令歸化意,來者如河源;晝夜入滄海,包括彌乾坤”。[注]玄燁《御製文集第二集》卷四七《黃河(并序)》,頁566下。
青海地處準噶爾、西藏與內地交通之要衝,成爲三方角力中的重要因素。在平準戰爭中,聖祖已開始綏撫青海和碩特蒙古各部。雖然朝廷尚無法完全掌控青海地方,然而這並無礙於朝廷在此展開勘測活動。四十三年三月,遷侍衛拉錫、內閣侍讀舒蘭探查河源,諭曰“爾等務直窮其源,察視河流,從何處入雪山邊內,凡經流諸處,宜詳閱之”。[注]《清史列傳》卷十二《舒蘭》,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829。二人於九月復命,並繪製《星宿海河源圖》進呈。根據二人的勘查,河源爲星宿海山中三支河: 噶爾瑪塘、噶爾瑪楚木朗與噶爾瑪沁尼,匯入扎稜諾爾,後者之一支入鄂稜諾爾,是爲黃河所出。是年,戴名世入京,“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注]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卷十《窮河源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85。是時戴氏尚未登第,以布衣之身而獲知此事,説明朝廷雖未立即公佈,但勘查結果事實上已在京師士人中有所流傳。
聖祖正式以上諭形式昭示河源位置在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同時提出的還有本節所關注的另一問題即西藏源流。是月十八日,聖祖向大學士、九卿等頒示長諭,逐一縷述黃河、岷江、長江等江水源流,兹節引如下:
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注]《清聖祖實錄》卷二九〇,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清實錄》(6),頁819下—821下。
聖祖在此時公佈此諭,用意甚深。是年二月,大將軍王胤禎護送新封六世達賴喇嘛入藏;八月,大軍收復拉薩,驅準保藏之局至是告成。康熙朝晚期的政治景況,於內於外,均不容樂觀,聖祖甚至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亦有所顧慮,故有五十六年面諭之頒布,於“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反復申説。驅準保藏的成功,無疑爲緊張已久的政局帶來了緩和的可能,“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也使得清朝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得以彰顯。聖祖在上諭中歷述江河源流,强調“中國諸大水”的西南/西北起源,一方面欲以説明疆域之超越前代,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自然地理的一體性、臣屬部族的多元性以闡揚清代“大一統”的政治構造。此份上諭首次向士林展現了大量西北、西南的地理知識,不過“大一統”並非通過這樣的簡單勾連即可證實,尚有待於回到經學論域、對經義作出新的詮解,因此聖祖方提出西藏源流的新説——三藏即三危。
《尚書·舜典》述虞舜之施政用刑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注]《尚書·舜典》,《十三經注疏》(1),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89年,頁40下。流放四凶,意不僅在懲罰,更欲以化導夷狄,如張守節謂“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爲中國之風俗也”,[注]《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2013年,頁35。皮錫瑞亦據《大戴禮記》證“蓋用夏變夷”。[注]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69。《禹貢》中亦有關於“三危”的記述,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敍”,又導水章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尚書·禹貢》,頁86下,88下。在經學世界中,屬於西戎之地的“三危”是《禹貢》九州的邊界,且自虞舜時代便受到中土的感化,此種雙重意涵正可滿足聖祖的論證需求,如西藏即是三危,清朝經略青藏的軍事行動便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聖祖藉此回到了三代盛治、實現了“遠近大小若一”的大一統局面。
關於“三危”地望的考證,歷來是古史研究的聚訟所在。蓋三危本爲神話傳説之山,自難徵實,歷代經師亦較審慎。[注]《尚書·舜典》,頁40下,42上。地理書中反留下了更多的記載,大抵將三危地望定於敦煌之三危山。所謂“三危”者,蓋指有山有三峰,因此附會極多、異説迭出。[注]“三危”地望異説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1),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79—183。與三危地望密切相關的是《禹貢》“黑水”之方位,聖祖在上諭中將怒江上游哈拉烏蘇河比定爲黑水。“三危”與“黑水”的考訂,以今日視之,無疑毫無根據,且在經注傳統中也並無承受。不過在皇權的宰制之下,這一新説很快擴散開來,並至少被部分精英學者所接受。
學者在此問題上與官方欽定論述的互動較爲複雜,贊同者有之,商榷者亦有之,雖態度有異,但事實上促使學者聚焦於西藏,以新的地理知識審視經學傳統。筆者所見最早附和者有全祖望,其有《皇輿圖賦》云:
三危苗裔,諸説紛綸;昆明居延,人各有云。不知出乎甘肅,直接滇雲,瓜沙西峙,緬甸南分;當年吐番之建節,鐵橋所屯;三藏鼎足,以相爲鄰;斯即三危,得所未聞。(三危即今西域之三藏,番僧實苗民之裔,聖諭兼取證于佛經,其博也。)[注]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皇輿圖賦》,載《全祖望集彙校集注》(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61。
此篇屬應制之作,分敍長白、西藏、俄羅斯,於康熙朝重要的地理勘測活動皆有涉及,大體可見乾隆初年東南士人地理知識世界的擴展。全祖望將聖祖的論述置於經學史脈絡中,强調三危西藏説對舊説的廓清作用。至乾隆十四、十五年前後,全氏時方居鄉主講書院,再度申述三危西藏説的意義,作《二西詩》述西藏歷史與宗教,首聯即云“三危舊是中原地,分比苗民尚有存”,[注]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卷八《二西詩》,載《全祖望集彙校集注》(3),頁2253—2254。遵循上諭的邏輯,將清朝之平定西藏視爲對《禹貢》九州的回歸。與之類似的尚有阮葵生,其在《茶餘客話》中節引了聖祖上諭,但均未給出任何學理上的論證。[注]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三,《續修四庫全書》,1138册,頁108上。三危西藏説在經學傳統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九州是否如此闊、可以達到渺遠的邊徼之地,因此學者又在聖祖上諭的基礎上有所彌合,這方面較具代表性者有齊召南與戴震。乾隆初,翰林院侍講鄭江與齊召南曾就黑水、三危地望往復討論,齊召南首先承認黑水即怒江,並於蒙古名中找到對應的證據,怒江上游有喀喇池,“華言黑湖也”,“地百里,從南流出曰喀喇烏蘇,華言黑水也”。在此前提下,三危即不可能在敦煌,因“敦煌並無有水南流能越雪山而逕沙海者”。[注]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七《(鄭問)然則黑水不可考乎》,《清代詩文集彙編》(300),頁267下—268上。齊召南在三危地望的考訂上則頗顯謹慎,破除經注三危敦煌之舊説後,齊氏未遵聖祖上諭將三危徑行比定爲西藏,而稱“三危自古原無確證,爲地、爲山、爲水,俱不可知”,有可能即是江畔流經之一山,亦未可知。[注]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七《(鄭問)然則黑水不可考乎》,頁268上。戴震的觀點與齊召南略同,亦認定黑水爲怒江,怒江之上游“水色深黑,故西番名是水曰哈喇烏蘇,番語謂黑‘哈喇’,謂水‘烏蘇’”。至於三危之地,戴震仍模糊地推斷其在怒江沿岸,“蓋其所經之地,歲久名湮,無從證實耳。”[注]戴震《水地記》,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4),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頁409。
康熙朝是士人關注西域史地之“風”初起之時。遺民志存恢復者闡揚“西北”風土之可堪大用,强調興西北水利爲“聖人”治理天下之首要。在“華—夷”、“文—質”的對舉之下,“西北”風土被符號化爲一種“質樸”的象徵,開始逐漸受到士人的關注。不過這仍是極少數士人社羣自發自覺的行爲,至康熙中期,士人興趣的選擇逐漸受到朝廷行政的影響。一方面,聖祖重視河工,欲探明河源,以期明瞭水性;另一方面,遵循經世傳統的士人,如萬斯同等,亦將河渠水利視爲講會討論的重點,在此學術與政治的交錯中,考訂河源逐漸成爲朝廷與士人雙方共同的興趣,士人亦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西北。康熙三十年以降,隨着對準部戰爭的勝利、對青海台吉的籠絡以及驅準保藏的成功,由朝廷主持的實地勘測乃成爲可能,拉錫、舒蘭實測河源使爭論千年的河源問題得到確解。疆域的拓展也爲“大一統”國家提供了足夠的論説資源,河源遂成爲彰顯盛治的符號,聖祖提出“三危西藏説”、“黑水怒江説”,試圖利用經學傳統化新土爲舊疆,由是也引發考據學者持續數十年的討論。正是在此過程中,動機各異的中土士人逐漸熟悉原被視作異域的西域,其地理知識亦較明人大爲增長,而這又與康熙朝政治史的進展有不可分割的關聯。
三 同文之治與乾隆朝西北輿地研究的展開
袁枚爲蕭騰麟《西藏見聞錄》作序,借《文獻通考》中的吐蕃敍述譏評南宋輿地學之疏陋,並稱輿地之學“必詳于大一統之朝也”。[注]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蕭十洲西征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399。袁枚生當盛清大一統之時,不啻自道時況,且完全道出了邊徼輿地學興衰之樞機所在。此之所謂大一統,非僅就地域統一而言,更指意識形態、知識譜系的“統”於一,更確切言之則是政治文化上的“同”與“通”。乾隆朝西師告捷使天山南北路被納入清廷的直接統治之中,而外藩諸國的漸次來歸,亦使“亙古不同中國之地,悉爲我大清臣僕”。[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3),北京,檔案出版社影印,1991年,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頁362上。西師告捷、疆土展拓,都極大擴充了士大夫地理知識世界中對西域的認知,正如全祖望所言,“蓋自西師告捷,使節嘽嘽,古所未至,盡於極邊,而後探討,罔不了然”。[注]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皇輿圖賦》,頁61。
如前所述,清廷面對新納入統治的疆域,亟需完成的不僅僅是設官與駐兵,更重要的則是在意識形態與知識譜系中創造新舊之間的連續性,將之與內地同置於“大一統”的王朝體制與文化傳統中,輿地學則是此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平定準部、回部後,高宗除進行行政制度建置與軍事部署外,旋即派出官員進行測繪,並繪製地圖、編纂史籍。[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49),桂林,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2012年,頁110上—111上。此類地圖藏之秘府,難得一見,這與康熙朝所繪《皇輿全覽圖》景況相近。不過在此基礎上修成的各類欽定圖籍,如《平定準噶爾方略》、《皇輿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等則成爲士人獲取西土知識最權威的渠道。
作爲由朝廷推動的文化工程,官書纂修需大量詞臣參與,在此過程中,纂修官的學術取向往往會受到影響,如祁韻士的西北輿地研究得益於其與修《王公表傳》的經驗即是顯例。乾隆朝大量纂修有關西域的官書,也促使部分學者將關注點轉向西北史地,甚至開始使用“殊族之文”以研究“塞外之史”。這方面可舉褚廷璋與汪師韓爲例。
褚廷璋(1728—1797)係江蘇長洲人,字左峩,號筠心,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試,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二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遞遷侍講、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後以不附和珅,降主事罷歸。[注]褚廷璋生平參見錢思元《吴門補乘》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46;《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18),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1997年,頁594下—595上。就早年經歷來看,褚廷璋與邊徼之學並無直接淵源,其早歲入紫陽書院,從學於沈德潛,詩法頗得其心傳,“旨遠詞文,卓然大雅”,[注]王昶《湖海詩傳》卷二九《褚廷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3年,頁334上。其後亦因文詞見知於高宗。入都後,褚氏被派充《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纂修官,由是開始接觸西北史地。褚廷璋的主要工作是根據最新繪製的輿圖,逐一考訂各地的地理沿革,在此之前必先對《漢書·西域傳》與《水經注》以降的地理書瞭然於心,褚氏有詩記其事:
溯從漢唐來,古迹煩考究。因思地理書,孟堅實領袖。山水界形勢,都城延袤。懸圖盈尺幅,高下象奔湊。參以道元經,脈絡了無瞀。維時守土臣,萬里繪方就。郵函上史館,展按粲如宿。印證漢西域,一一同發覆。某部即某國,位置儼仍舊。因緣得推暨,唐及宋元後。
並有自注云:“先據《漢書》所載西域三十六國及山北烏孫國道里方位,參以《水經注》,合山川形勢,懸繪一圖,與軍營所送現在準、回諸部圖若合符節,唐宋以下皆由此類推。”[注]褚廷璋《筠心書屋詩鈔》卷三《承纂西域圖志書成進御蒙恩敬述》,《清代詩文集彙編》(363),頁211下。其在館先後七年,“於準夷、回部山川風土最爲諳悉”,[注]王昶《湖海詩傳》卷二九《褚廷璋》,頁334上。至二十七年書成,大學士傅恆薦之於朝,特旨嘉獎,隨即又奉旨與修《同文志》。遺憾的是,褚廷璋並没有留下任何專論西北史地的文字,僅有《西域詩》一組十二首,是其修書之餘興,希望用以“補史乘之未備者”,兹引其中《喀什噶爾》一首爲例:
往代羈縻迹漸更,渾河西望莽縱橫。(喀什噶爾河下流入塔里木河,于古亦名思渾河。)鎮傳疏勒唐貞觀(貞觀中,疏勒內附,置都督府,今喀什噶爾地也。),人去兜題漢永平。(永平中,疏勒王兜題爲漢吏田慮所執。)飲馬雪深尋舊井(耿恭拜井處),晾鷹風勁上高城。陽春萬里吹還到,散作天方畫角聲。(回部亦名天方。)[注]褚廷璋《筠心書屋詩鈔》卷三《西域詩·喀什噶爾》,頁217上。括號內爲作者自注。
《西域詩》寫成後,曾以寫本的形式在師友間流通,[注]翁方綱《復初齋集外文》卷一《宋雲亭太守新疆詩草序》,《清代詩文集彙編》(382),頁634上。此雖非嚴謹的著述之體,其融地理沿革與掌故舊聞於自注中,較之卷帙浩繁的《西域圖志》,士人更易從此中獲得關於西域各城的可信的歷史地理知識,法式善便譽之爲“詩史”。[注]法式善著,張寅彭等編校《梧門詩話合校》卷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306。Laura Newby討論清中葉以降形成的新疆行記,認爲其共同特徵是對新疆本土文化的忽視,以及對今古地名的勘同,其效果則是將新疆與內地在歷史與地理上構築了一種連貫性,證明了邊緣與中心、過去與現在的聯繫。[注]Laura J. Newby:“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Morden China, 25(4), Oct., 1999, pp.454-455.事實上,此種策略淵源有自,自乾隆朝纂修《西域圖志》以降,地理沿革、漢唐經略舊事逐漸成爲士人對西域關注的重點,明人所樂道的近於小説家言的想象,在清人的書寫中已明顯淡化。其直接後果即是,在明人筆下呈斷裂性的西域圖景,至乾隆年間學者的精審考據中已漸次形成其連續性,此種連續性是雙重的,通過在時間上對漢唐以來西域歷史地理的釐清與疏通,以在地緣上彰顯西域與內地的關聯性,即在輿地學的視域中化“新定之疆”爲“漢唐舊土”,在中土的文化傳統中“發現”並再熟悉西域。
另一例爲汪師韓(1707—1774)。汪師韓字抒懷,號韓門、上湖,浙江杭州人,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乾隆初年,以張照薦,入武英殿校勘經史。後落職,直隸總督方觀承延之主持保定蓮池書院。[注]《清史列傳》卷七一《汪師韓》,頁5852—5853;《清儒學案》(3)卷六八《息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637—2638。限於史料,其人早年的交遊與問學背景仍較模糊,僅知其曾受學於方苞,得古文之義法,中年後的治學興趣則相當泛,潛心經學,於詞章之學亦用心頗多。值得注意的是,汪師韓係清書庶吉士,應具有相當的滿語文水平。汪師韓於館選之年賦有《龍書五十韻》,述歷代文字因革,尤詳於北族文字之創製,如謂“有元班彌怛,新字奉敕製;四十一母音,語韻韻關備;仿佛婆羅門,二七貫一切;同時畏兀兒,橫行似勃泥”。[注]汪師韓《上湖紀歲詩編》卷一《龍書五十韻示同館諸君》,《清代詩文集彙編》(308),頁502下。此詩寫成後,大爲李紱激賞,汪氏因李紱之薦在八旗志書館行走,隨即進入國史館,並由此接觸到部分舊檔。[注]汪師韓《上湖紀歲詩編》卷一《史局》,頁505上。汪師韓對西北史地的關注散見於《韓門綴學》及其詩集中。《韓門綴學》係其平日讀書遇疑,“博引旁搜,以求其通其故”,[注]汪師韓《韓門綴學》卷首題辭,《續修四庫全書》,1147册,頁443下。日久積爲一帙。除同時士大夫留心的經史字義考據外,汪氏對遼金元三代史事、北族官稱、部族源流皆有論述,如譏拓跋土后説爲“無稽之談,不足據也”;考突厥、回鶻、蒙古可汗稱號,“汗者,君也、主也,可乃語辭”;考遼金元部族姓氏分野與賜姓;述北族政權雙軌政制之源流等。[注]分見汪師韓《韓門綴學》卷二《拓跋二解》、《可汗台吉》、《三史姓氏》各條,頁460下,462上—463下;同書卷三《達魯花赤》,頁486下。西北歷史與地理的考據主要分佈於卷四,包括青海、伊犁、哈薩克、回部與鄂罕(浩罕),大抵於正史中勾稽舊史、連綴而成,同樣旨在構築“古今”、“內外”間的連續性。汪氏雖亦承認“荒遠之區,臆度豈能有當”,[注]汪師韓《韓門綴學》卷四《鄂罕》,頁512下—513上。然而較之明代士人想象與事實雜陳的四夷文本,已屬準確。
褚廷璋、汪師韓並非特例,同時學人之關注邊徼四裔者實非鮮見,雖然所使用的文獻仍很難脫出中土文本的局限、結論亦不盡如人意,但看待文本、尋找問題的“眼光”已大有不同。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自天啓年間出土後,李之藻、徐光啓、錢謙益均進行過初步的研究,然而其後即歸沉寂。至乾隆年間,景教與景教碑再次成爲學者討論的熱點,杭世駿、錢大昕、畢沅、王昶等均對此有所論述。此外,如錢大昕之究心蒙元氏族、制度,於《道藏》中鈔出《長春真人西遊記》;[注]錢大昕《潛研堂集》(1)卷二九《跋長春真人西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28。裘曰修之考證西域古今地名,錢維城之考訂天竺方位,王昶之考訂安西、陽關地望,皆屬此類。[注]裘曰修《裘文達公文集》補遺《西行古今地輿考略》,《清代詩文集彙編》(332),頁445上—449上;錢維城《茶山文鈔》卷十《御製天竺五印度考訛恭跋》,《清代詩文集彙編》(346),頁692下—693下;王昶《春融堂集》卷四三《書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後》,《清代詩文集彙編》(358),頁442上。錢大昕、王昶與上文提及的褚廷璋是蘇州紫陽書院的同學,[注]錢大昕著,錢慶曾校注《錢辛楣先生年譜》,載《嘉定錢大昕全集》(1),頁9。裘曰修爲乾隆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錢維城則爲乾隆十年一甲第一名進士,均屬盛清時期頗負盛名的學者與官員,而對西域地理、歷史、宗教各有所用心。處於地方的士人也逐漸產生對西域的興趣,如王初桐在乾嘉之際便纂有一部《西域爾雅》,仿《西域同文志》體例,抄撮《同文志》、《西域圖志》、《西域聞見錄》諸書而成。王初桐(1730—1821)本爲嘉定縣諸生,曾充四庫館謄錄,其書並無學術價值可言,然而可見一時世風之好尚與學風之下滲。[注]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五《西域爾雅》,《續修四庫全書》(927),頁218下;光緒《嘉定縣志》卷十九,《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8),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2010年,頁412下—413上。
康乾兩朝西陲經略的成功使青海、西藏與新疆漸次納入朝廷的直接統治之中,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的,版圖的擴大無疑會促使士人關注西北。另一方面,隨着考據學逐漸成爲彼時學術的主流,音韻、文字、金石、輿地方面積累有年,已形成較爲成熟的治學路徑與成果,用之於四裔邊徼的研究,亦屬進路之必然。這兩方面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仍是前提性與技術性的原因,特别是前者,不過敷衍地將政治史視作解釋背景,在疆域擴展與學術轉向間很難構建起直接的聯繫,因此有必要回到乾隆朝政治史與政治文化史中尋找新的解釋。
西師告捷使“西被流沙,極於二萬餘里,皆入版圖,皇威丕振,超軼前古”,[注]《皇清文穎續編》(7)卷五三《皇太后七旬萬壽新樂府九篇》,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2000年,頁157下。而真正使之在士人社羣中產生影響的是告捷後朝廷主導的一系列的政治慶典活動,特别是樹立紀功碑以及大量頌美詩賦的創作,正是通過這些慶典活動,西北的軍事勝利、疆域擴張的消息方在士人乃至基層社會中泛傳佈開,參與慶典的士人乃產生了一種自覺的“盛世”意識: 即通過平定西域,清朝之疆域遠逾三代,形成了“盛治”的局面。關於紀功碑的問題,近來已有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在此不贅。[注]朱玉麒《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 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載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编《高田時雄教授退職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中文分册)》,東京,臨川書店,2014年,頁399—410。如果認爲遍佈各州縣的紀功碑是武功與盛治的視覺性表達,相較而言,士人所創作的紀功詩文則顯得較爲私密,除非收入文集刻印,否則僅在少數友朋、同僚間傳播。這種以詩文稱賀大捷的傳統並非清朝所發明,然而卻被清朝發揚至極致,乾隆朝歷次重大戰爭基本皆有文臣詩文稱賀,筆者並未統計此類紀功詩文存世的具體篇目,但其數量之多則不難想見,若檢覽平定西域前後在京詞臣之詩文集,幾乎皆有此類作品,體裁則涵括詩、賦、頌、表等。《皇清文穎續編》曾選錄了一批紀功詩文,筆者初步統計有68篇(首)。這只是當時寫作的紀功詩文中的一部分,全面檢視這些詩文的書寫邏輯及其意涵並非本文所能完成,在此僅對其內容特質略作提示。其一是對先代的回溯,强調清朝之功業超乎漢唐之上,較之三代亦不遑多讓。如竇光鼐稱西域之地“自三代聖王,罔不懷惠顧”,漢雖開闢西域,然亦耗竭財力,“唐屬國少於漢,旋淪吐蕃,宋乃不能盡有中土,唯元威制最遠,而德薄弗能敵也”;[注]《皇清文穎續編》(5)卷二二《平定回部頌(謹序)》,頁220上。與追溯史事相隨的是對地理的勘同,是時《西域圖志》尚未編纂,而士人已用心於此,如紀昀述準噶爾之形勢云“其境東巴爾坤,西哈薩克,抵鄂羅斯之南,縈烏斯藏之北,內瞰則伊吾、柳城、高昌舊國,卻背則月氏、罽賓、大宛、安息,出五郡之故疆,渺河源於絶塞”,[注]《皇清文穎續編》(6)卷三九《平定準噶爾頌(謹序)》,頁223上。雖敍述較爲含混,然大致方位不誤。其二則是對“同文”的稱頌,此可舉葉觀國之詩證之。葉氏首先揄揚平準有五善:“伐暴救民,至仁也;底定絶域,至武也;上合列聖之志,至孝也;斷自宸衷,至明也;啓佑後人,爲萬世福,至慈也”,由此“帝王之事備矣、天人之應允協”,“北燮南諧,東漸西被,有文同文,有軌同軌”。[注]《皇清文穎續編》(7)卷五九《平定準噶爾詩(謹序)》,頁382下。“同文”不僅出現於紀功詩文中,而且是乾隆朝士人經常用以形容“國家之盛”的概念,如錢樾爲高宗七旬萬壽作頌文云:“聖武既揚,戢戈櫜矢,梯霄架極,同文並軌,井絡氛清,于闐玉采,屯牧豐藩,商民遄喜”。[注]《皇清文穎續編》(5)卷二九《皇上七旬萬壽頌(謹序)》,頁363下。
事實上,“同文”正是乾隆朝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高宗君臣念兹在兹的“盛治”景象。關於“同文”的意涵及其政治實踐,先行研究已有所討論。[注]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頁97—99;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頁345—367。大致言之,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同文”意味着强制性的統合與畫一,面對四裔文字時則有强烈的“用夏變夷”式的同化隱喻。得益於非漢族王朝特别是元朝的統治,同文的意涵開始向多元的結構轉變。元代士人稱頌八思巴字之頒行爲“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注]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六《南安路帝師殿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85年,頁459上。並非是以八思巴字取代漢文,而是“字雖重百譯,而文義如出一口”,[注]程鉅夫《程雪樓集》(3)卷十一《同文堂記》,北京,中國書店影印,2011年,頁11a。文字僅是符號,漢蒙文字雖異,然其承載的義理卻是一致的。清人所理解的“同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接續元人的認識。在高宗看來,語言僅是外在之“名”,雖有分殊,亦無關乎天理,各語言所表現之“理”或“實”是一致的,易言之,不同語言皆具有“載道”的資格與能力。[注]關於高宗對“同文”的敍述參見《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卷首,御製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34册,頁7上—8上;《欽定西域同文志》,御製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35册,頁1下—2上。就表面觀之,諸凡合璧體例的碑刻、圖籍等皆可視爲“同文”之表徵;而就本質言之,“同文”事實上是“大一統”的另外一種表述。高宗內禪後,曾就“同文”做過系統性的總結歸納,可謂晚年定論,歷來學者皆未措意,兹節引如次:
國家威德覃敷,無遠弗届,外藩屬國,歲時進至,表章率用其國文字,譯書以獻。各國之書,體不必同,而同我聲教,斯誠一統無外之規也。……夫疆域既殊,風土亦異,各國常用之書,相沿已久,各從其便,正如五方言語嗜欲之不同,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偶題和闐玉筆筒,因及回疆文字,復思今日溥天率土各國之書繁夥,而統於一尊,視古所稱書同文者,不啻過之。[注]弘曆《御製文餘集》卷二《題和闐玉筆筒詩識語》,《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1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影印,1993年,頁1011下—1012上。
高宗在此展現出一幅盛清治下多族羣、多語文、多文化的圖景,各國、各部族風俗各異,卻“統於一尊”,即在清朝統治的多元結構之中相調適,而共奉清朝之聲教、尊高宗所定之“道”,即“一統無外之規”。有學者指出,由於疆域的空前展拓,高宗君臣早已放棄了用《禹貢》九州作爲朝廷疆土與統治合法性的論説依據,在地理志的書寫上采用“本朝之制”取代九州之制,“大一統”的標尺由此不再是經典劃定的疆界範圍。[注]趙剛《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國的大一統話語重構》,載楊念羣主編《新史學(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3—34。而在論述邏輯上,高宗精心闡述的“同文”概念無疑成爲最合適的替代,“本朝之制”之所以能成立,端在“同文”之維持,“同文”亦因之成爲盛清時期大一統論述的基礎邏輯之一。
乾隆朝若干重要的政治舉措,如多語文辭書與地理志的編纂、漢籍與佛典的譯介、翻譯科舉的定制化等等,皆因同文而起。生活於乾隆中葉的士人不免受其漸染,將多族羣、多文化與多語言在王朝體制之下的融匯共存視爲常事,因而方能脫出明人對西域的漠然以及明代四夷文本中如小説家言的異域想象,以較爲平實的眼光審視天山南北的“新定之疆”及新近建立外交聯繫的中亞鄰國,並重新審視漢唐舊史中的西域記載,藉助較爲成熟的考據學方法,逐漸在“古—今”、“內—外”構建連續性,西域史地的一個初步輪廓由是形成。
四 餘 論
萬曆八年(1580),時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的王宗載“搜輯往牒,參稽國朝故實”[注]王宗載《四夷館考》卷首自序,引自向達《記巴黎藏本王宗載〈四夷館考〉》,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頁656。按通行東方學會校印本《四夷館考》缺此序。作《四夷館考》,康熙三十四年(1695),太常寺少卿江蘩又在此基礎上纂輯《四譯館考》。這些在明人四夷志書中反復出現的知識,至乾隆朝被四庫館臣譏爲“多不確實”、“不足以資掌故”,[注]《四庫全書總目》(1)卷八三《四譯館考》,頁720中—下。評價的變化事實上映射出二百年間士人對西域認知的拓展,以及與之相關的一整套地理知識體系與價值的更新。馬世嘉討論清朝對奧斯曼帝國認知的變化,認爲1800年是一個轉捩,由於高宗駕崩,士人減少了對文禍的顧忌,大量與邊疆地理、政治有關的文獻在此後陸續刊布,滿、漢分别所具有的邊疆知識被整合入同一網絡之內。[注]Matthew W. Mosca:“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 p.151, p.200.如前文所述,西域地理知識在滿、漢間的傳佈並無截然之分;而士人對西域產生興趣並形諸文字,亦不必遲至高宗駕崩之後。乾隆中葉以降,士人之流放新疆者以耳聞目見之資寫下筆記、詩文,成爲此前“遙觀西域”的文本式考據研究之補充,祁韻士、徐松等人由此因緣際會而開始其西北史地的研究。
本文討論17—18世紀士人地理知識世界的變遷,只是一個極爲粗疏的勾勒。事實上,無論相關史料之多寡,試圖全面理解一人或一羣體的知識世界以及其來源都是無法實現的。另一方面,書寫成爲今人理解古代士人知識構成的近乎唯一的途徑,然而兩者未必即能完全對等,士人完全可以並可能通過書寫策略隱匿或規範其知識及來源,實現一種自我審查或自我的正統化。本文所討論的,事實上只是此類或可稱爲“知識精英”的士人的地理知識世界,而行文論述亦需基於一種預設,即今日所見詩文或筆記大致可以反映其作者所掌握的地理知識,特别是其對西域的認知,此亦係不得不然耳。
就總體趨勢而言,17—18世紀士人地理知識世界中有關西域、中亞的認知是不斷擴充的,士人的注意力亦逐漸轉向西北。其原因是多元的,如在“華—夷”、“文—質”的對舉之下,“西北”風土被明遺民符號化爲一種可資利用的“質樸”的象徵;講求經世的士人如萬斯同等,則將河渠、邊務作爲講會討論的重點,“西北”由此受到一部分士人的重視,不過這仍是極少數士人社羣自發自覺的行爲。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地理知識世界的擴充,事實上與清代政治史進程密不可分,其中處處可見政治與學術的交錯。最初關注“西北”的士人大多心念故明,在政治上絶非滿洲統治者的合作者,然而這一趨勢卻最終被朝廷所利用、成爲論述統治合法性的工具。在康熙朝關於河源的爭論中,此一借用與合流的趨向清晰可見,聖祖重視河工,欲探明河源,以期明了水性,考訂河源逐漸成爲朝廷與士人雙方共同的興趣。隨着對準部戰爭的勝利、對青海台吉的籠絡以及驅準保藏的成功,由朝廷主持的實地勘測乃成爲可能,拉錫、舒蘭實測河源使爭論千年的河源問題得到確解。疆域的拓展也爲“大一統”國家提供了足夠的論説資源,河源遂成爲彰顯盛治的符號,聖祖提出“三危西藏説”、“黑水怒江説”,試圖利用經學傳統化新土爲舊疆,由是也引發考據學者持續數十年的討論。正是在此過程中,動機各異的中土士人逐漸熟悉原被視作異域的西域,其地理知識亦較明人大爲增長。至乾隆朝,準部、回部的底定以及與中亞各國外交、藩屬關係的漸次確立,西域的歷史與地理再度成爲朝廷與士人共同關注的熱點。一方面,褚廷璋、汪師韓等學者開始利用歷代正史中的西域記述,對西域歷史、地理、部族乃至宗教作出相對精審的考證。另一方面,在高宗君臣試圖構築“同文盛治”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西域地理志、多語種辭書的編纂,漢籍、佛經的翻譯等均成爲朝廷專意經營的文化工程;此外,西域平定後盛大的慶典儀式、文臣間持續不斷的詩文唱和,都逐漸構築起西域與中土、漢唐與本朝的連續性,成爲清朝平定新疆正統性論説與盛清時期大一統論述的基礎邏輯之一。多族羣、多語文、多文化在“大一統”國家框架內融匯共存且共奉大清聲教,在乾隆朝士人看來正是“盛治”的表徵,此種來源於政治環境的認知正如一種“空氣”瀰漫於乾隆朝的士人社羣,於不覺中對士人的治學興趣與取向產生影響,甚至也輻射到遠離中心的地方士人。[注]趙儷生編次嘉道以降西北學者的生卒年,第一代所謂西北史地學者如祁韻士(1751—1815)、俞正燮(1775—1840)、張澍(1776—1847)、徐松(1781—1848)、王筠(1784—1854)等(參見趙儷生《論晚清西北之學的興起》,《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均出生於乾隆朝的巔峰時期,對“同文盛治”、“大一統”之觀念自不陌生,且幼年對清廷的西域戰功亦當多有聽聞。
“知識”之所以爲“學”、成爲一時學風之所尚,必有待於學人社羣的形成、專門著述的大量刊印與學術討論“話題”的產生,就此意義而言,西北史地之爲“學”,確始於嘉慶朝。然而一時學風的生成,亦有待於“知識”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的傳佈與沉積。自明遺民在清初對“西北”產生興趣,至嘉慶朝西北輿地學之初興,其間一百五十餘年,正是清代大一統國家逐漸形成、清朝疆域不斷擴展的時期。士林與朝廷對西北的興趣最初淵源各異、旨趣不同,卻最終匯爲一流,改變了明代四夷書寫想象與事實混雜的局面,也徹底更新了士林對西域的認知,構成西北史地學所必須憑藉的知識基礎。政治與學術的關係是朝廷借用士人對西北的興趣以實現正統性的論述,抑或士人因應功令而轉移好尚,殊不易判斷,亦無須截然劃分,事實上政治與學術本來即處於相互交錯纏繞的狀態中。一代學人本來即生活於一代的政治史籠罩之下,“雖有智者,亦逃不出”,[注]此處及前文“空氣”之譬喻俱引自王汎森《執拗的低音》,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頁175。政治史、學術史與生活史往往難以分開審視,重此薄彼,未免失當。西北史地學之“風”,至遲在康熙朝已初興微瀾,而在乾隆朝則已遍拂朝廷與士林,風氣瀰漫之下,西北輿地研究之爲“學”由是成爲可能。邊患與“世變”固然是刺激士人從事西北輿地學的重要因素,然而若僅强調邊患,未免陷入“衝擊—回應”的模式中,自清初以降關於西北的知識積累、朝廷對於大一統國家的論述,都成爲西北輿地學之“潛流”與“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