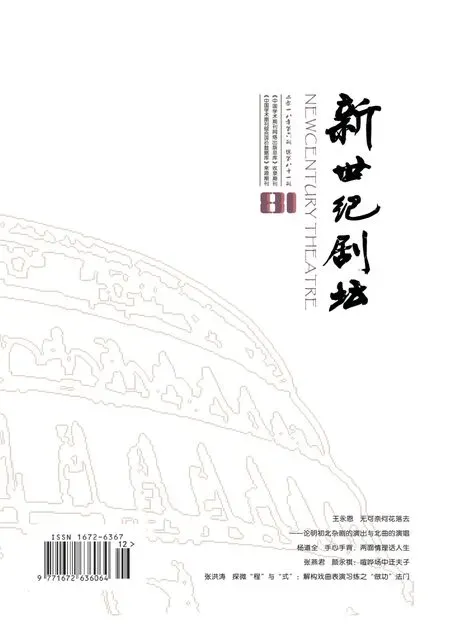《血胆玛瑙》好在哪里?
2018年9月,在唐山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评剧节”剧目展演中,阜新歌舞剧院将此前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的京剧《血胆玛瑙》移植为评剧,使这出戏再次呈现于舞台。《血》剧能够以相同文本和不同的剧种形式来表现而再次获得成功,这并不是因为这部作品获过多少奖的背景,也不是因为这部戏是因为由谁来表演而得以支撑,而是这部戏从文本到舞台都在结构和情节设置上体现出一种难得的匠心独运。
中国戏曲向来将“以角儿为中心”和“以表演为中心”这些特点当做不可更改的优点来看待,而其实这极有可能恰是对戏剧艺术本身最大的伤害。梅兰芳时代,那些以梅兰芳个人表演魅力为主要审美对象的戏在情节上都非常虚弱,《天女散花》和《嫦娥奔月》等等很多仅仅就是一个故事的雏形——如果把“故事”放在戏剧意义上考量,甚至梅派名剧《贵妃醉酒》等也谈不上有多少情节的丰富性。情节的设置是戏剧展开一切冲突的核心,这一点具有的重要性完全不应该是中西戏剧的区别,而是剧作成熟优秀和平庸幼稚的分野和标志。传统戏曲并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元杂剧时代的《救风尘》和《窦娥冤》都有非常好的叙事经验,但经过了地方戏黄金时代而进入当下的戏曲创作,却越来越将“看戏看角儿”“以表演为中心”“抒情本质”当成了忽略叙事性的免死金牌。中国戏曲具有抒情性本质或者说以抒情为中心,这一点不错,但不错不等于完全正确,不成其为一个拒绝改变的理由,不应该以此为由排斥叙事的技巧。没有漂亮的叙事,没有讲故事的能力,那些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抒情又怎么能感人?所以,加强对戏曲叙事能力的认识,尤其是新创剧目,这是一个应该被整个行业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血胆玛瑙》这部戏具有的特点值得关注,对这部戏的评价也具有了超越单纯的剧作来探讨的意义。《血》剧的情节设置环环相扣而又环环相生,体现了剧作家的功力、智慧和对舞台的理解,这些完全应该成为一个样本为创作和理论提供思考。
那么,从这些角度看,这部戏到底好在哪里?
(一)
《血》的故事体现的是传统传奇创作的思维,也就是传奇者,非奇不传。观众和评论者完全不必要去操心这个故事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从来不是一回事,不管多少意料之外,只要最后在情理之中即可。这个戏的情节设置非常巧妙,剧作家把人物关系拧成麻花的能力、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设置、次要人物的有头有尾和推进剧情的作用都见功力。由于真正的剧评并不是演出剧情说明书,剧评不需要复述剧情,也避免不必要的剧透给读者和潜在观众带来过度信息,所以此处不必要通过复述剧情的方式来论述《血》剧在情节设置上这种环环相扣感。
全剧围绕一块神秘化了的也意象化了的贯穿道具——血胆玛瑙来展开全部故事,把家国情怀和男女之情交接在一起。在故事的讲述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做到了让观众看到开头无法知道结尾,看到中场不知结尾,甚至看到结尾也还是不知道结尾,这种峰回路转、奇峰迭起的写法也许不仅体现的是传统戏曲“非奇不传”的创作传统,更多地体现的则是剧作家非凡的想象力和情节架构能力。想象力和文采是剧作家最重要的两样本事,文采很多时候是功,而想象力其实是天赋。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出能让观众坐得住的戏,不仅能坐得住,而且能始终处于悬念和期待之中。
《血》剧能抓住观众注意力这一点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是创作观。戏剧,不是一个事件的记录,也绝不是单纯地讲故事。戏剧讲故事和文学讲故事的不同在于,戏剧的讲述要呈现一个因果链,一件事发生了,另一件事也要跟着发生,两件事之间不能没有联系,也就是说一台戏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因果结构,这里面的因果折射出人物的性情。但是当下的太多舞台作品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创作的。很多劳模戏,用一条线的方式来展现一个劳模的一生,演完这段演那段,一段一段演,最后以死亡或者一段抒情的核心唱段收尾。就以同样是此次参加第十一届评剧节的剧目为例,表现天津司法干部模范事迹的《王武强》、表现内蒙古乌兰牧骑防风治沙事迹的《大漠绿魂》、以追随李大钊革命而牺牲的早期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李昆为讴歌对象的《李昆》都是这样按照“纪实”手法来写的戏。完完整整、老老实实把王武强、李刚和李昆的人生故事一段一段地放在舞台上,开始做了什么,中间做了什么,并没有故事,没有将整台的人物拧在故事的讲述中,很多次要人物有头无尾……这种“纪实”貌似是文学化的,其实什么都不是。退而言之,文学的确是戏剧的灵魂,但有时也是戏剧的敌人,因为文学的表达方式、歌颂或者批判的方式,尤其是口号式的,不依托故事的讲述而存在的抒情等等都是舞台呈现最大的障碍,是舞台的敌人。劳模和英雄人物理当为人钦敬,他们真实的人生也确实是中国的脊梁,但把他们的人生变成戏,必须使用戏的写法,不能是流水一样讲述一个故事,必须重视结构。王武强也好,李昆也罢,其实都是极好的题材选择,但创作者只着意表现丰功伟绩的伟大和英雄事迹的感人,往往忽略去讲述一个为什么,忽略这个剧中人是为了表现性格而去行动,还是根本这个宏大的戏剧行动需要人物性格的支撑。所以,在众多平庸的作品中,更显出《血》剧的可贵。
如果说奇峰迭起和非奇不传体现出的是《血》架屋构梁的能力和颇值得关注的核心优势,那此剧第二个值得探讨之处还在于在这样紧张密集的故事中展现人物性情的能力,毕竟情节的构筑除了事件,核心更有人物。
(二)
《血》在具有情节含义的戏剧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人物性情同样动人。《血》剧的主题毋庸置疑,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交织叠加,最终个体的生命选择让位于民族大义。用一块玛瑙贯穿始终串起故事,同时这块神秘的石头也是一个高度意象化的隐喻——以一石做江山的隐喻——祖先留下的片石寸土不能拱手予人。“血胆”二字,也是红心之意,家国大义面前纵然是风流浪子和梨园优伶,皆有亦有赤子之心。
男主是位“一掷千金买欢笑”的浪荡公子,但风流不羁却又心性单纯,这样的人设多少有点类型化的嫌疑,但容易出戏。剧中没有过多渲染他面对外辱时的激愤之情,而是把浓墨重彩都放在他对女主情感的痴诚之上——他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寻心中所爱,不仅有诚,更有人性中的可爱和合理。相比较男主,女主角的性格设置似乎更贴近“抗日”的主题。女主的身份是一个“戏子”,戏子自古多情无义,多情者言其情感丰富却善变,而无义,却是长久以来让人费解的一个身份总结。从汉代营妓到元代的“唤官身”再到明代的教坊制度、乐户制度,传统戏曲自古以来有倡优一体的传统。台上卖艺、台下卖身的屈辱想必使得这些色艺双绝的优伶为了生存的需要更懂得保护自己,无情无义、自先凉薄可能也就使自己能免受更多的伤害。吃戏饭的,只要站在舞台中央,有利益就有一切,所以必须见利忘义。戏子无义,天经地义,可偏偏《血胆玛瑙》中这位欢喜花旦却有多少须眉男子和文人士夫都没有的家国大义。浪荡公子+风尘女子,这种组合并不新鲜,甚至多见,为何多见,因为容易出故事,出人物出性情,放在爱情的大背景里就是《杜十娘》,放在时代变迁中,就类似《霸王别姬》,《血胆》把这种组合放在“抗日”这个大主题下,容易突出主题,同时也好看。
具体到舞台而言, “跳崖”一场戏是人物性情转变的节点,她本来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而盗取玛瑙,但得知玛瑙蕴含的秘密,决定以身守宝,其实更是以身殉国。这种转变对于无义的戏子,也突然,也不突然。更多的关键要看这个节点,也就是情感的高潮时表演如何处理,如何把高潮推上去。从评剧这一版的呈现来说,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无论是表演还是文本,如果能有更多的铺陈来突出女主的决意向死,而非因偶然爬上悬崖,也许会更感人一些。这场戏以外,整出戏而言,在表导演处理上还有推进的空间,“盗宝”一场戏,现在的处理是让女主举起玛瑙砸昏汉奸队长,这当然显示出动作性,但假如处理为“色诱”而盗,通过暗示性强的表演会不会更具有观赏性呢?这些细节希望在以后的演出版本中能再精细打磨。
最后一场“冥婚”,这是一场出乎意料的戏,也是采用唯美悲情的浪漫主义手法的戏。大悲即是大喜,喜悦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情,死别不能阻隔生聚,有情人定要终成眷属。这样的结尾是非常戏曲化的,参透了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的手法,但又不是真的团圆和真的“光明的尾巴”,而是梦幻的,想象的,壮烈的,悲剧的美感在冥婚的喜乐中呼之而出。
最后一点是关于这个戏的核心唱段的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戏曲的创作而言,核心唱段的有无和是否能流传,一般被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出戏的成功与否。《血》剧的唱段不少,旋律动人,但似乎没有大段独白式的抒情段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回到了我们论述的起点,剧作如果叙事线弱则必会给抒情留出足够的空间,但如果情节紧凑,故事性强,则长段抒情会妨碍整体节奏。从评剧的老戏来看,是非常重视故事的剧种,《花为媒》《杨三姐》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时事公案,都非常重视故事的可视性和曲折感,根本没有走梅兰芳时代京剧那种重视技艺而不重视故事的路子。剧种发展是不均衡的,走的路也不是唯一的,不能用从京剧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来框定其他剧种的创作。也就是说让剧本为表演留出空间没有错,但更要考虑剧种特性,京剧可以的,评剧未必必须,至少不能过。好的旋律和出色的音乐形象自然会得到流传,《血》在这一点上体现出的用力均匀,我认为并不是缺陷。
总之,《血胆玛瑙》是一出值得关注的好戏,它体现出的很多优点是当下创作需要借鉴和思考的。这一切的一切,首先需要我们要看到戏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