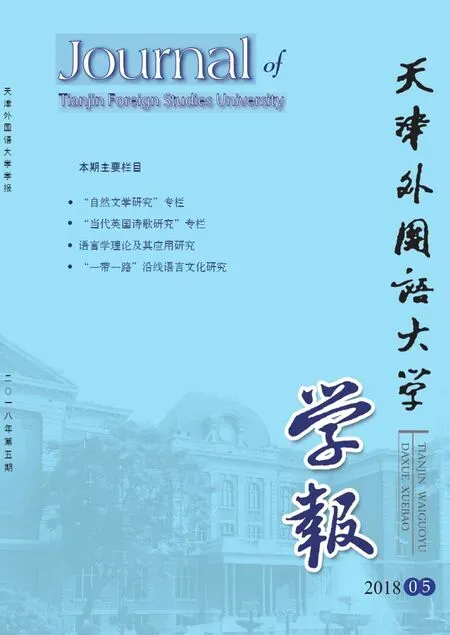英国当代底层叙事探源——华兹华斯底层诗歌探析
李琳瑛
英国当代底层叙事探源——华兹华斯底层诗歌探析
李琳瑛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一位执着于苦难书写和底层关照的诗人,底层人的悲苦生活成为其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主题。凭借诗意的叙述方式,他的底层诗歌超越了悲苦和困顿的表象,创造出了新的审美境界。在华兹华斯看来,与自然的亲密相交使底层人的灵魂更趋于净化,他们身上蕴含着完美的永恒天性。他的底层诗歌充满了对底层人美好品德和高贵人性的赞美和敬意。
华兹华斯;苦难书写;底层诗歌
一、引言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经历着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独立宣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民族民主运动浪潮汹涌,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原有的现实生活秩序,社会各阶层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在新的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持续被边缘化。他们身份低微,社会资源匮乏,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面临着双重困境。面对那些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的底层人,心怀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主义信念的诗人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怅惘和悲悯。他从民主和人道主义出发,以满腔的同情和敬意创作出了大量以平民百姓为题材的诗歌。英国底层人的生活成为华兹华斯创造力及想象力的最牢靠的立足点。
二、底层的苦难书写
所谓底层叙事,指的是“以一种鲜明的民间立场,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审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书写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观,再现他们在那种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怀、血泪痛苦、挣扎与无奈,揭示他们生存的困境和在这种生存困境面前的、精神的坚守与人格的裂变”(何志钧、单永军,2004:62)。这种以展示苦难为主的叙事模式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在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缺乏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贫瘠使得他们在现实中屡屡遭遇挫折、失败、不幸甚至死亡,底层生活的困苦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任何时代的文坛上都有一批身负道德感和使命感的文学家,他们心怀悲悯,情牵草根,以书写苦难的表达方式来呼吁民主、平等,传递人文关怀,苦难叙述成为底层文学的叙事主线。在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华兹华斯就是这样一位执着于苦难书写和底层关照的诗人。
提起华兹华斯人们往往想起的是他笔下旖旎神秘的自然风光。的确华兹华斯正是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到了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但这种自然决不是人迹罕至的原野荒地,而是居住有无数艰难度日的底层大众的乡村地区。在大半生栖居乡野的生活中华兹华斯比其他任何浪漫派诗人都更接近和关切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那些社会底层大众。那些过着乡村生活的底层人距离自然更近,他们身上有着更加本性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才应是文学书写的主题。
在华兹华斯所生活的时代,他所热爱的自然和乡村正遭受着空前的灾难。一方面,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现代化生产方式进入乡村,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了乡村往昔的宁静,彻底摧毁了本已衰弱的田园经济;另一方面,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镇,为资本主义工厂出卖劳力,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家园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感,最终沦落为漂泊无依的无根阶层。曾经平和怡人的田园景象变得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日夜劳作却得不到温饱的破产农民以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面对那些流离失所的农民,诗人心中充满了无限惆怅和同情,便“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以满腔的同情与敬意,描写贫贱农民、牧民、雇工、破产者、流浪者直至乞丐的困苦生活、纯良品德和坚忍的意志”(杨德豫,1996:2)。在他笔下既有衣衫褴褛的流浪者、绝望的母亲、被遗弃者,又有十足的傻瓜、杀婴者、囚犯,人物主体与身份呈现出一种苦涩的底层意味。正如布拉德利(Andrew Bradley,1999:124)所言,如果暂时抛开诗人处理这些主题的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
英国底层人的悲苦生活成为华兹华斯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主题,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迈克尔》。作为《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最后一首诗作,它一直是华兹华斯最重要的叙事诗之一。诗人以一个贫穷老村夫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底层人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悲惨命运。迈克尔是一位年迈的牧羊人,但他节俭勤快,“心灵手巧,干什么活计都在行”(45),他于垂暮之年喜获爱子路克,心境更好似转世重生,“是这个孩子给了他柔情和活力,/好比太阳的光辉,天风的音乐”(200-201)。在偏僻的高地上,老迈克一家三口相依相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忙碌却又不失温暖的田园生活。老迈克辛勤劳作,付出毕生心血,终于在有生之年挣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家产。
咱们这块地刚到我手里的时候,
租子重着呢;到我四十岁那年,
这一份产业还有一半不属我。
我拼死拼活地苦干;靠着上帝的恩典,
三个星期以前,它全是我的啦(374-378)
正如英格兰大多数农民一样,老迈克热爱他脚下的每寸土地,对土地的挚爱之情超越了一切。当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他无法面对失去土地的现实。为了保住土地,渡过难关,老迈克只得送自己心爱的独子到城里去谋取出路,“眼下他留在家里,又能干什么?/这地方人人都穷,上哪儿挣钱去?”(354-355)他和妻子依依不舍送走路克,期盼他“很快能攒下钱,补上这一笔亏空”(352)。然而,“在那座荒淫浪荡的城市里”(444),抵挡不住诱惑的路克“终于陷进了泥坑;丑事和耻辱/弄得他没脸见人,最后他只得/逃到海外去,找一个藏身之所”(445-447)。迈克尔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也最终失去了自己视作生命的土地。妻子去世之时“他们家那份产业/已经卖出去了,落到了外人手里。/那座小屋——‘晚上的金星’,也没了”(474-476)。华兹华斯用无韵诗的手法、简朴的语言书写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英国底层人,特别是农民阶层所遭遇的冲击和迫害。在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中,底层农民即便终日辛苦劳作也难逃家破人亡的厄运。诗人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底层农民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
诗歌《露西·格瑞》则讲述了穷苦人家的小女孩在暴风雪之夜毙命于荒野的悲惨故事。诗人毫不掩饰地赞美了这位名叫露西的乡下女孩,“人世间千家万户的孩子里/就数她甜蜜温柔”(7-8)。但命运却并没有善待这个天使般的孩子。傍晚时分,暴风雪将至,忙于砍柴的父亲差遣小露西去接她在城里干活的母亲。善良、孝顺的小露西愉快地提着灯上路,但“大风暴提前来到了荒原,/荒原上走着露西;/她上坡下坡,越岭翻山,/却没有走到城里”(29-32)。柔弱无助的孩子最终迷失在茫茫的荒野之中,只留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他们哭起来,往回走,哭叫:/‘在天国再见吧,亲人!’”(41-42)露西的悲剧表面上是由大自然的狂暴力量而致,但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圈地运动后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外出谋生,露西的母亲正是其中的一员。为了生存她走进城里的工厂,遭受资本家的剥削,最终换来的却是骨肉离散的悲惨结局。正如约翰·伯吉斯(John Purkis,2005:49)所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削弱了原本稳固的家庭纽带,父母与孩子不得不为忙碌生计而相互离散,工业革命夺走了农家孩子。小露西的悲剧正是时代大背景下无数穷人孩子命运的真实写照。
华兹华斯生活的时代恰是英国乃至欧洲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伴随着工业文明进程的加快,社会也发生着深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财富、阶级以及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都使得底层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和无奈。华兹华斯从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出发,将这一时期底层人的平凡生活、生存境遇和精神痛苦凝聚在他的诗行里。他感受民间疾苦,触摸底层伤痛,对时代变迁进程中底层人所遭受的无助、孤独、悲苦给予了真切的关怀,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同时期的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947:117)所言,华兹华斯的天才就在于最好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他的诗歌是时代的革新之一,展现了我们时代的革新运动,也与我们时代的革新运动一起被传颂。
三、穿越苦难的阴霾
虽然底层人物生活的贫苦与艰难是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是底层文学最鲜明的表现符号,但它并不是底层生活的全部。底层人虽然经济和文化贫瘠,但他们却是一个鲜活、丰富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浓缩着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整体经验,是苦难与欢愉的并存、黑暗与光明的同在。因此,底层叙事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苦难叙事。底层文学家可以书写苦难,但不应该沉浸于苦难。而底层文学的不少作品却冲破了人们正常情感的承受力,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间间毫无光亮的黑屋中,而这正是一种苦难焦虑症的表现(洪治纲,2007:40)。这些弥漫着黑暗、悲惨、哀怨、斥责等情绪的底层书写是对底层生活经验的单极化处理,必将带给读者极度压抑和沉重的感觉,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美感和艺术性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因此,为了超越现实生活的苦难,底层文学家必须寻找有效的缓冲措施。
华兹华斯书写悲剧,却并不渲染悲剧,他的言说始终是冷静客观的,很少流于说教或沉湎于悲伤的情结不可自拔。他从人类生活的普遍性出发,用简朴、克制的语言和充满诗意的叙述使底层书写穿越了苦难的阴霾,保留了文学本身的美好意蕴。正如托马斯·迈克法伦(Thomas McFarland,1992:17)所言,华氏的文学思维有一种尊严和高尚气度,这是由于他“能将人类个体的不幸提升到人间生活普遍状况这一高度”。在他的诗意叙述下,那些看似琐碎、平凡、悲哀的底层景象也散发出高贵气质。
在诗歌《可怜的苏珊在梦想》中,女主角苏珊原本是生活在乡下的穷苦女孩,后来迫于生计进城来当使女。清晨街角一只画眉鸟的歌声让她回想起了自己的故乡。苏珊在清晨的曙光中陷入一片幻象,记忆里故乡的山川、树木、白雾、河流和牧场令她飘飘欲仙。尽管那时候的她常常提着桶四处奔忙,住在“鸽窝一样的孤零零小屋”里(11),可在她看来“那是世上她唯一热爱的住处”(12)。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苏珊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现实束缚的她唯有默默忍受,在画眉的歌声中悄悄缅怀着故土,独自陷入悲伤的回忆。在整首诗中苏珊只是静静聆听着画眉的歌声,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言语。诗人同情孤苦无助的苏珊,但却选择用轻柔、淡然的笔调去诉说她的哀愁。他以舒缓诗意的语气娓娓道来,于平静自然中表现出了一位底层少女对故乡和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眷恋。
这歌声真迷人;可她为什么痛苦?
她眼前浮起了山峦,出现了树木;
大团的洁白云气飘过洛斯伯里,
一条河淌过了契普赛德的谷地。(5-8)
华兹华斯在同样是书写底层少女的诗歌《她住在人迹罕到的路边》中描写了一位独自居住在荒野之地的姑娘。这首诗是华兹华斯的著名组诗《露西》中的第一首,描写的是一位平凡的苏格兰民间少女。少女美好得像含苞待放的紫罗兰,但只因她住在人迹罕到的路边,她的美和高贵就仿若被禁锢在了一个孤寂的世界中。远离人群的她既得不到人们的赞美,也得不到人们的怜爱。她悄无声息地死去,仿若流星划过夜空。诗人用浅吟低唱的语调和淡淡的笔墨将姑娘情态里的孤独与忧伤娓娓道出。这种孤独和忧伤也是底层人基本情感的常态。它疏离如那长满青苔的石旁一棵孤零零的紫罗兰,又寂寥如那远在天边、清辉闪闪的星。少女露西的生命从来都不是恢宏的存在,她只是万千孤弱的底层少女中的其中一位,微贱到活着默默无闻,离世亦无人知晓。而诗人却对这微弱卑贱的生命倾注了无限的关怀和同情。诗歌最后听闻少女的逝去,诗人突然感觉到世界变了。诗人将觉醒的个性意识与超凡脱俗的神圣情感融合在一起,流露出对生命流逝的哀婉和叹惜之情。
她住在人迹罕到的路边,
住在野鸽泉的近旁;
这姑娘生前没有谁夸赞,
很少人曾把她爱上。
一朵半遮半掩的紫罗兰,
开在长青苔的石旁!
美好得像颗星孤孤单单,
在天上闪闪地放光。
活着时谁知道她在人间,
更有谁知道她夭亡;
但露西已在坟墓里长眠!
对我呀世界变了样!(1-12)
华兹华斯笔下底层人的生活或许悲情,但却不失美好。他以诗歌艺术本身的魅力表明悲剧的成就并不需要刻意的渲染。在《坎伯兰的老乞丐》中诗人描写了一位身处社会最底层、朽迈不堪的老乞丐。诗人以画面感来暗示诗意的内涵,一位衰弱老迈的流浪者独自坐在山间的石阶上,周围是渺无人烟的野岭荒山,陪伴他的唯一活物只有脚下那一只只前来觅食的小山雀。他小心翼翼地取出讨来的残糕剩饼,却在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中散落一地碎屑。整幅画面寂静苍茫,但并不悲惨凄凉。行乞的老人虽然佝腰曲背,但并未做出怨天乞怜之态。诗人也没有使用类似“可怜”、“凄惨”、“悲哀”之类的词来形容他,没有给予他世俗意义上的同情,而是从更深层次上表现了人类处于天地之间的状态。卑微低贱的老乞丐变成了一种庄严而超然的存在,显示出了气魄恢弘的生命之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2005:19)曾评价道:“(《坎伯兰的老乞丐》等三首诗)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深刻性,华兹华斯的其他作品都难以企及……当我步入老年时,这些诗在表现个人痛苦时精心控制的悲情与审美尊严让我比阅读任何一首诗都更受到感动。”
漫步中,我曾看到一位老乞丐;
他坐在大路旁边一个不高的
石礅上;这石礅做工颇为粗糙,
位于一大座上的脚旁,为的是
便于牵着马走下陡峭而崎岖
山道的人们在此重新骑上马。
石礅顶部是宽阔光洁的石板,
老乞丐把拐棍往这上面一放,
拿起被村姑乡妇施舍的面粉
染白的袋子,一一取出里面的
残糕剩饼;他谨慎专注的目光
慢慢盘算似地把东西看一遍。
阳光下,他坐在那个小石礅的
第二级上,独自吃着他的粮食——
周围是渺无人烟的野岭荒山。
他风瘫的手虽尽力避免浪费,
但是却毫无办法,食物的碎屑
依然像是小阵雨洒落在地上;
一只只小小的山雀不敢过来
啄食注定归它们享用的吃食,
只是来到距他半拐棍的地方。(1-21)
对于悲苦题材的书写,华兹华斯展示出了卓尔不群的掌控能力。虽然他的底层诗歌内容是悲剧性的,但情感表达却并不情绪化。面对底层人的生活苦难,华兹华斯既怀有怜恤之心,又不失理性的克制。他以较为平静的心态呈现底层苦难,做到了情绪的有效节制和情感的普遍升华。凭借其沉静又富有诗意的叙述方式,华兹华斯的底层诗歌没有成为简单的苦难叠加和悲情泛滥,而是超越了悲苦和困顿的表象,创造了新的审美境界,表达了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四、卑贱中的伟大
底层文学是面多棱镜,反映纷繁复杂的底层生活。虽然底层生活困苦是不争的事实,但底层叙事绝不等同于苦难叙事,它不应该停留在苦难的表层,而是要有更高层次的思考。华兹华斯底层叙事中最伟大之处便是对卑微人物心灵世界的刻画。在《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第十三卷中华兹华斯(1999:336)就曾明确指出自己的创作中心:“人心是我惟一的主题,它存在于与大自然相处的人中那些最杰出的胸膛。”正是通过这些与自然相处的平凡、普通的人和事诗人感悟到了更高精神的存在。他认为,与自然的亲密相交使这些底层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灵魂趋于净化,他们身上蕴含着完美的永恒天性,即朴实、善良、仁慈、坚强等,是真正拥有“心志的力量”和德行的人(华兹华斯,1999:330)。他的诗歌从不缺乏对底层人美好品德和高贵人性的赞美和敬意。
在《迈克尔》一诗中,不安分守己的路克最终经受不住荒淫浪荡的城市诱惑,在丑事和耻辱中陷入了命运的泥潭。而面对独子的堕落和流放,老迈克却并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念,而是表现出了底层人对勤劳和朴实精神的坚守。
他照样上山去,
仰望太阳和云彩,听风的呼唤;
照样干各种活计,侍弄那群羊,
侍弄那块地—他那份小小产业。
也时常走向那一片空旷山谷,
给他的羊群砌那座新的羊栏。(456-461)
面对灾难和逆境,卑贱的老农夫表现出了强大的精神意志,因为他相信“在爱的强大力量中有一种安慰/它能使祸事变得可以忍受”(448-449)。痛失爱子的他选择独自疗伤,在隐忍和坚韧中承受着生活的苦痛。
那儿,挨着那没有砌好的羊栏,
有时候可以看见他独自坐着,
要么,还有他那条忠心的看羊狗,
也老了,陪着他,蜷伏在他的脚旁。(467-470)
生活对老迈克来说无疑是不公的,而他却从未流露出任何的怨恨和悲愤,更没有因此丧失对土地和生命的热爱。尽管老迈克最终在日夜操劳中死去,但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他强大的生命力及对未来生活的懂憬,而他于苦难中激发出的博大之爱折射出的正是底层人的美好人性之光。
写于1802年的《决心与自立》同样表现出了华兹华斯对底层人高贵人性和强大生命力精神的赞赏。他描写了一位年老体衰却要为了维持生计而四处奔波劳作的捞水蛭人。
看来这人就如此;他不活不死,
也没有睡着,只因他年事太高;
他已勾腰曲背,在生活旅途里
他的头已渐渐靠近他的双脚;
似乎在久远的以往,他曾受到
极度痛楚或剧烈疼痛的折磨,
似有人所不支的重量把他压迫。(64-70)
这是一位靠打捞水蛭为生的老者,他迎着呼啸的狂风走过一口口池塘、一片片荒野。他步履艰难,动作迟缓,疾病和苦难的摧残使得他几乎直不起腰来。诗人以十分同情的语气描写了老人的外貌和生存境遇。这一具看上去毫无生命活力的躯壳让人顿生悲凉之感。而当诗中的“我”忍不住向老人流露出同情之意时,老人的反应和话语却使人肃然起敬。
我接着又向他说了这样的话:
“你待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干?
对于你来说,这是个荒凉地点。”
他答话之前,微微惊讶的神色
在他仍很灵活的黑黑眼珠里闪烁。
无力的胸膛吐出无力的话语,
但字儿一个接一个次序井然;
话里还带有某些崇高的东西——
……
他告诉我说,因为他又穷又老,
所以就来到池沼边捉些蚂蟥。
这活既要碰运气又叫人疲劳!
有许许多多艰难困苦要碰上:
从这里到别处,从池沼到水塘,
凭上帝的恩典,住处时无时有——
这样他总算用正当的办法糊了口。(88-105)
一个自力更生、自强自立、诚恳朴实的底层劳动者形象跃然纸上。在他身上诗人也仿佛找到了生命个体与生命力意志的伟大结合。面对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老人言谈举止中表现出的淡定和从容透露出灵魂的坚毅与崇高,使他有了一种庄严的气派。老人遭受的苦难正是底层劳动人民苦难的缩影。在悲苦的人生境遇下他们贫苦却不贫乏,与社会变迁和工业文明带给人的生存压力和痛苦相比,他们心中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仿佛更加热烈。他们内心的坚毅与自立散发着伟大的人性光辉,也是强大生命意志力的体现。
华兹华斯不是单纯的自然诗人,也不是农村命运的客观记录者,而是一位关注人类心灵世界的诗人。他的底层诗歌揭示了底层大众在遭遇生活苦难时所折射出的内在人性和心灵追求。他从生命个体内部出发探讨如何突破外在和自身的局限性,充分享有生命尊严的严肃命题。他构建了底层叙事的现代精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呈现出了底层叙事的深度以及时代精神。
五、结语
华兹华斯通过诗歌描写了英国社会底层生活中的人和事。他以众多悲伤、哀愁、凄苦、凝重的意象构建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底层诗歌世界,既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又传递了人文主义精神。他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审视现代工业社会里底层人的生存境遇,书写普通人的苦难生活与美好情感,更关注工业文明和社会变革给底层人所带来的心灵创伤。饱含感伤情绪及悲剧意蕴的叙事风格具有直面现实和净化灵魂的教育意义。华兹华斯对底层人的悲苦表现出既持久不衰又不大肆声张的关注。他对底层人怀有深切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却又不失理性。他有伤而不言伤,努力将诗歌带回到至真至纯的形态。他用悲悯却不失克制的语声与沉静又富有诗意化的叙述创造出了全新的审美境界。他从人类灵魂深处出发努力探索现代工业社会里底层人所遭遇的情感变化、内心世界冲突以及他们在苦难中所折射出的内在人性和心灵追求。华兹华斯对底层人物所表现出的悲悯情怀及精神敬畏拓宽了底层诗歌悲剧性的构成范围,令读者感悟到了更高精神的存在。
[1] Bradley, A. 1999.[M].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 Hazlitt, W. 1947.[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McFarland, T. 1992.[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 Purkis, J. 2005.[M].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5] 哈罗德·布鲁姆. 2005.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 江康宁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6] 何志钧, 单永军. 2004. 荆棘上的生命——检视近期小说的底层书写[J].理论与创作, (5): 62-66.
[7] 洪治纲. 2007.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J].文艺争鸣, (10): 39-45.
[8] 威廉·华兹华斯. 1999.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M]. 丁宏为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A Source Study of British Contemporary Bottom Narration: An Analysis of William Wordsworth’s Poetry for the Subaltern
LI Lin-ying
William Wordsworth is a poet intent on the suffering writing and concerns of the subaltern. The bitterness and sufferings of the subaltern is the main theme in many of his poems. With poetic narration, his poetry for the subaltern, far beyond the bitterness and sufferings creates a new aesthetic realm. He thinks the intimacy with nature can purify the souls of the subaltern to obtain eternal humanity. His poetry shows great respect and praise for the virtues and nobility of the subaltern.
William Wordsworth; suffering writing; poetry for the subaltern
2018-07-03;
2018-08-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国诗歌的底层叙事研究”(14BWW053);河南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当代英国诗歌的底层叙事研究”(2015-YXXZ-13)
李琳瑛,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2
A
1008-665X(2018)5-005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