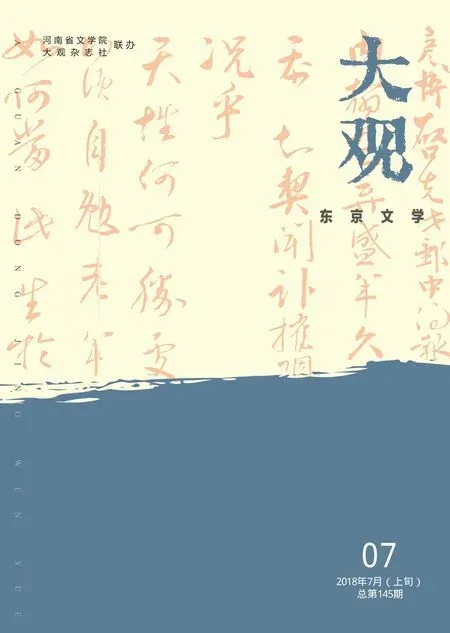老兵传奇
静谧的午后,一缕阳光照进客厅,把家刷成了明亮的暖色。父亲安详地坐在雕刻古朴的红木沙发上,微驼的背,依旧保持着老兵的姿势。背景墙上悬挂着一幅六尺整张的国色天香的牡丹画,笔力遒劲,色调自然……望着父亲的满头银发,我仿佛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烟云,透过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那些尘封的记忆慢慢被打捞起来。
一
父亲傅云吉,祖籍山东省平度市马戈庄乡埠口村。档案生年是193年9月16日,祖母说他实际属羊。祖母虽然大字不识,却深明大义、干净利落,她不认可“十羊九不全”的俗语,还说,属羊的人命好,羊代表吉祥。若按照祖母所说属相推算,父亲应该是1931年出生。我们小字辈给父亲庆生做寿,询问其具体寿辰,他总是含混地说:“不记得了。”被逼急了,便勉为其难地说:“大概九九重阳节就是我的生日吧。”难得糊涂!老人节做寿,既吉祥如意,又皆大欢喜。
父亲在贫困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童年是凄苦的。小孩子做不了重活,也不能闲着玩耍,父亲便做烧火、拾草、放猪这些他能干的轻快活儿,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手脚勤快的习惯。为了吃饱穿暖,父亲自五六岁懂事起,便当了一名小小的乡村放猪倌,给富裕人家喂猪放猪,挣口饭吃。
回忆起那段放猪生涯,父亲饱含深情地说,做猪倌,是乡下娃常做的一项农活。那时的猪与现在的猪养法不同。现在圈养的猪养着无趣,吃着不香,它们吃的是饲料,饲料里面放置的是添加剂,生长速度也快,半年就能出栏,猪一辈子都没有出圈溜达的机会。那时的猪基本是散养的,活得自由快活,它们可以在田野撒欢奔跑,随意觅食喝水,猪肉自然是香喷喷的。每天清早天蒙蒙亮,父亲就报到上工了。他提着半桶残汤剩饭,来到猪圈,猪好像听到了集合的哨响,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更多的时候,父亲刚把猪圈门打开,饿了一夜的五六头猪便急吼吼地冲出栅栏,直奔熟悉的地里、河滩、田埂……长了一夜的嫩草肥菜,看上去干净而新鲜,大小不一的猪贪婪地吃着,咀嚼着,一副满足而享受的样子。此时的父亲会暂时忘记饥饿与贫穷,仰望蓝天白云,甚至闭上眼,幻想着自己的未来。
大约半个时辰,猪吃饱了,大猪四处逛逛,小猪甩蹄撒欢,它们互相追闹着,发出欢快的叫声。有的猪崽成群地挤在一起,你挤我,我挤你,热闹极了。父亲说,最有趣的是看小猪打架:彼此拉开架势,低着头,噘着嘴,冲向对方,攒足劲,拱对方的头、肚子,相持,转圈,想把对方掀倒。到了秋天,父亲就把这些猪赶到收完庄稼的地里,随意它们去拱地瓜地,找落花生,吃些收割后遗漏的庄稼。父亲也捡花生吃,那花生脆甜脆甜的,仿佛人间美味。
一头头猪,在父亲的悉心照顾下,茁壮成长,膘肥体壮,猪毛发亮。逢年过节宰猪杀羊的时候,也是他最难过的时刻,他会悄悄地躲避在一个小小的角落,流着泪看朝夕相处的猪,成为人们的口中珍馐。常年没有沾过荤、吃过肉的人们,吃得嘴里冒油,好像比吃了唐僧肉还过瘾,他们还竖起大拇指,夸赞父亲是个好猪倌,喂养猪不偷懒。
在村东南角,有一所私塾学校,父亲非常羡慕那里读书的孩子,看着他们每天背着小书包,有说有笑地去读书,他便伸长脖子,目送一个个远去的背影。读书,在当时是富人家拥有的特权。偶尔,父亲在放完猪,做完农活之余,一个人偷偷地跑到教室门口,紧盯着教书先生在黑板上书写的优雅姿势,聆听着教室里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他觉得,那是世界上的天籁之音,也会情不自禁地嘴里念念有词,手拿一根枯树枝,在黄土地上涂抹写画。教书先生偶尔也会教父亲读书识字。多少年过去了,我看见父亲如醉如痴地聆听京剧《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的经典片段,透过那满头如银的白发,眼前依稀幻化出一幅图画: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教室外,赤脚细腿上沾满了黄泥巴,如饥似渴的乌黑眼睛,盼望春风细雨滋润心灵……这个特写镜头,珍藏于心,出现于梦,时刻警醒我别懈怠、不偷懒、赶紧做、马上干。
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狼烟四起,兵荒马乱。山东大地自然灾害频发,饿殍遍野。祖父母再三商量,觉得与其在家被困饿死,不如投亲靠友,逃荒东北。全家人收拾行李,大门一锁,离乡背井,加入闯关东大军的澎湃洪流。跋涉数千里,历尽万般苦,来到了东北沈阳。10岁的父亲依旧给人喂猪放羊,有时候也挖野菜、拾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贴补家用。遇到不听指挥的任性猪,父亲就与它斗智斗勇,在田埂里追逐狂奔,虽累得气喘吁吁,却锻炼了体能,让他成了“飞毛腿”,为以后上战场去打仗,打下了良好的体力基础。
有一次,天色已近傍晚,一头调皮淘气的任性猪,执意不回猪圈,瘦弱的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与它巧妙周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赶进了猪圈。就在转身关栅栏门的一瞬间,父亲脚底一滑,身体摔在一侧,栅栏上一颗锈迹斑斑的铁钉划破大腿,又深深地扎进腿里。四周昏暗,阒寂无人,父亲使劲把铁钉从腿上拔出,伤口很深,鲜血直流,他从破裤子上撕下一块脏兮兮的布条,简单地把伤口包扎一下,一瘸一拐往家里走去。
拥挤贫寒的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闲钱抓药医伤?祖母从邻居家讨来一杯白酒,用棉花蘸着给父亲涂抹处理伤口。不久,父亲的腿严重感染,红肿发炎,以至化脓腐烂,晚上时常疼痛难忍,父亲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唯恐再给祖父母添烦增愁。很长时间里,父亲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去喂猪放猪,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痛,心情十分郁闷。凭着身体强大的修复能力,一个多月后,父亲逃过一劫,伤口竟不治自愈。至今,他的左腿依旧隐约可见当年留下的伤疤——成为山村放猪倌的岁月印迹。
二
沈阳大街上,随处可见来回巡逻的日本鬼子,还有只准日本人出入的戒备森严的日军机构。当时有日本人抓中国劳工修桥建路,为了躲避被抓,大伯离开沈阳,跑到马家沟农村(现辽宁沈阳法库县三面船镇南),在一家织布厂学徒做工。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1946年前后,祖父母举家前往吉林长春,租住在一位远房亲戚闲置的旧屋里。那时的父亲已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白天在长春街巷背着小木箱卖烟卖报,晚上回家学习手工织布。
1947年,一场神秘的瘟疫笼罩着长春上空,疫情四处蔓延。一天清早,祖父如往常一样起床干活,到了晚上,突然开始高烧不退,病魔没有放过这位一辈子与苦难生活抗争的山东汉子。第二天中午,祖父便带着满腹未了的心事,以及对故乡的无限思念,永远告别了这个悲苦的世界。祖母扑倒在地,哭得死去活来,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年幼的姑妈撕扯着祖父的衣袖,不让街坊四邻把他拉走。父亲看着这个风雨里摇摇欲坠的家,一个人默默地跑到无人角落,痛哭一场。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瘟疫造成的伤亡特别严重。窗外的梧桐树上,传来一声声乌鸦聒噪的叫声,更平添了几分忧愁与凄苦。
祖父病逝,家里的顶梁柱倒塌了,没有了生计来源。16岁的父亲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祖母既经历了丧夫之痛,又因思儿心切,每天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双眼。深夜里,父亲劝慰祖母说:“娘,别哭了,您还有哥哥、妹妹和我,将来,我给您养老送终!”倔强的祖母默默点头,变卖了养家糊口的织布机以及所有值钱的家当,领着我父亲和姑妈,直奔沈阳马家沟,想与大伯团聚后,一家人再回平度老家,安放祖父的骨灰。
孤儿寡母三人推着一辆独轮小车上路了。父亲吃力推着的车子上,一半是锅碗瓢盆的生活物品,一半坐着9岁的姑妈,她紧紧地怀抱祖父的骨灰盒。祖母用刚毅的眼神凝望远方,准备用一双三寸金莲一步步丈量着走出长春,走回故乡。恰逢乱世,旷日持久的长春围困战,使这座城市几乎成了凄惨的死亡之城。城门戒备森严,禁止通行,只准进不准出,祖母三人在城门口排队苦等了三天三夜……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低三下四地鞠了多少回躬,经过了多少道审问和检查,终于挨到了出城之日,他们与饥民们一起走出了长春城门,迎来了生命的新天地。
逃荒路上,饥一顿饱一顿,一路颠簸,风雨兼程。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从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加之祖父刚刚病逝,痛苦萦绕于心,前途未卜。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一路上,推车走路,一言不发。有了心事也喜欢埋藏在心里,闷着不愿张扬。结果,郁结成疾,父亲生了一场大病,类似现在的急性痢疾。
祖母三人行走到一个叫“拳头站”的地方,父亲浑身上下已像面条一样软软绵绵,有气无力,生命危在旦夕。旅店老板可怜他们孤儿寡母,善意收留,安排在客栈旅馆住下,只收祖母一人的住宿费。祖母拿出身上仅有的5元钱,这是一家人的全部积蓄,恳求旅馆老板找当地郎中为父亲看病抓药。旅馆老板是个热心的中年男人,一直跑前跑后,直到第七天,父亲的病情才稍微有点起色,他从死亡线上颤巍巍地站起来了。
时隔近70年,定居黑龙江的姑妈,依稀还记得,当地郎中用了一个白酒泡鸡蛋的祖传秘方,把父亲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80岁的她深情地回忆道:
我二哥从小性格倔强,沉默寡言,躺在小客栈的炕上,缩成了一团,一边发着烫手的高烧,一边不断说着吓人的梦话:“别拦我,让我去找俺爹!别拦我,让我去找俺爹!”经白酒泡制后的鸡蛋,有一股很难闻的臭味,他赌气似的坚决不吃。娘一遍遍唤他的小名,乞求道:“儿啊,快喝了吧,你喝了,咱的病就好了!”
二哥依旧背着身子,就是不喝,娘急得“啪嗒啪嗒”地直掉眼泪,气得直跺脚,狠狠地说:“你这头小犟驴!怎么跟你死去的爹一模一样!”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客栈热心的老板见此情形,也前来帮忙劝说:“孩子,快喝了吧,你想把你娘急疯啊!”
最后,在大家的劝说逼迫下,二哥喝下了这碗救命的鸡蛋汤。娘和我整夜守护在二哥身边,娘流露着疼惜的眼神,一刻不停地给他一遍遍揉肚子。次日,二哥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天,腹中空空了,好像还阳了一样,脸色渐渐有了血色,也开始喝水吃东西了,终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很多年后,我还开玩笑地对他说:“二哥,你喝的那碗汤不叫救命汤,简直就是还阳水嘛!”
救急不救穷。小本生意的旅店老板生意惨淡,面露难色,祖母已身无分文,不好意思再麻烦萍水相逢的好心人,千恩万谢后,她带着父亲和姑妈继续赶路,向大伯所在的马家沟靠拢。
孤儿寡母风餐露宿,徒步行走,一想到家人的团圆,娘仨又脚下生风,继续赶路。第三天,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暴雨冲刷着泥泞的道路。正在不知所措之时,父亲抬眼看见前面有一座破寺庙,年久失修,无人居住,他们便临时有了个落脚处,在庙里住下来……
就这样,历尽艰辛,大约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祖母三人终于抵达马家沟。一家四口相见,抱头大哭,为不幸病逝的祖父,为颠沛流离时的险些丧命,为来之不易的亲人团聚,更为硝烟弥漫的动荡时代。
家里一贫如洗,没有回故乡的盘缠,他们不得不在马家沟临时住下。白天,父亲跟随大伯一起到织布厂织布做工,赚得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晚上,守着家里那台手摇织布机,再继续轮流织布。那“吱扭吱扭”的织布声,不知疲倦,与满天的星光相连接,它仿佛命运的叹息,伴随着朦胧的月光,编织着全家人回归故乡的梦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那个响彻世界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久久回荡耳边,举国上下喜气洋洋。中国犹如旭日东升的太阳,闪耀着万丈光芒。
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即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进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全国各地大规模征兵,每家都有参军名额。大伯当兵的名额已定。长兄如父,大伯已到结婚年龄,祖母舍不得家里这个主心骨、主劳力,左右为难。父亲对祖母说:“娘,我年龄小,顶不起家,还是让我替哥哥去当兵吧!”祖母沉默不语,眼里含泪,既不肯答应,也不愿摇头。“娘,俺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命硬,咱一点也不亏!”此时此刻,祖母抱着父亲的头,涕泗滂沱:“儿啊,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呀!”
1950年9月30日,父亲带着祖母的叮嘱,光荣参军,用19岁的肩膀扛起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重担。当时,父亲个子矮小,一脸稚嫩,白净柔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填写报名表的人误认为他谎报年龄,也可能是听错了,擅自填写成17岁,比实际年龄小了两岁。
父亲当兵后,首站分配到辽宁锦州骑兵五师一连任通信员。他第一次去照相馆照相,把身穿军装的照片寄回马家沟,给家人报平安。但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后来,父亲与一位老乡谈话得知,他参军的第二年,祖母、大伯和姑妈便回了山东平度老家,寄到原住址的信件,以及身穿军装的照片,他们都没有收到。
儿行千里母担忧。回到久违的平度老家,安放好祖父的骨灰,祖母整天提心吊胆,时常念叨起父亲,他成了祖母放不下的“心病”。村里每每有人关心询问:“他婶,老二来信了吗?”50岁的祖母便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自言自语:“我找回了大儿子,结果,又把小儿子弄丢了……”
“他大娘,别站在村头等了,老二什么时候回家,一定会提前告诉你的!”每天黄昏时分,祖母像掉了魂似的,习惯性地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手遮额头,遥望远方,幻想着,有一天,父亲飒爽英姿地突然出现在眼前……
四
1951年3月,由于父亲虚心好学,勤奋能干,被选调到高射炮兵第62师任警卫员。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白热化。在朝鲜战场上,前方没停止过枪炮声,后方没停止过美军飞机轰炸声和机枪扫射声。父亲看到,朝鲜的许多城市被炸成废墟,百姓死伤无数,不断听到朝鲜妇女儿童的悲泣,他内心升腾起对敌人的愤怒,对祖国的责任感。父亲时常仰望朝鲜阴霾密布的黝黑山峰,又扭转头,面朝祖国的方向,默默祝福。
父亲当时是警卫员,但他坚决请战,首长批准他跟随领导参加一线作战。据他回忆,部队在保护永楼机场战斗中打过一场漂亮仗,击落了两架敌机,击伤一架敌机。他亲眼看到敌机冒着黑烟爆炸落地,指战员们胜利欢呼,战旗飞扬,一片欢腾。
子弹不长眼,有战争必有伤亡。值得庆幸的是,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父亲与死亡擦肩而过,侥幸躲过了子弹的袭击。有一次,敌机来犯,全师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对来犯之敌瞄准射击。突然,父亲觉得头上的军帽动了一下,险些被打飞,他本能地一躲,抓下帽子一看,一颗子弹将帽子打了一个窟窿。事后,惊魂未定的战友们看到父亲毫发未损,连连称奇。多年之后,他的一位战友还逢人便说:“傅云吉这小子真是命大,呼啸而过的子弹都抬高一厘米,绕着他飞呢!”另一位战友则补充说明:“幸亏他个子矮,若再长高点,这百十来斤,早让美国佬给报销了!”的确,经历了贫穷的时代和饥饿的童年,没有及时汲取丰富营养的父亲,身高最终定格在1.66米。这既是成长的遗憾,又是矮个子的造化。
除了残酷的战斗,父亲还要面对行军、饥饿、疲困、惊恐等重重困难,以及各种让人胆战心惊的战争场面。父亲咬紧牙关,默默地承受着,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与坚韧毅力啊!
经历了抗美援朝洗礼,经受了战争的生死考验,父亲永远不忘那炮火纷飞的岁月,他曾自豪神气地告诉我,在部队里,一传十,十传百,最终战友们把他传得更神,更邪乎了,说他的军帽被子弹打穿,上面的弹眼还冒着烟花,父亲却镇定自如,继续瞄准打美军飞机……
1953年7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父亲唱着《志愿军战歌》胜利归来。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亲人的身边。因在朝鲜战场上机智勇敢,表现突出,父亲于1954年9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以后,父亲被选调给团长李忠仁当警卫员。年轻的父亲少言寡语,恪守职责,聪明能干,颇得首长的赏识。他的倒水技巧在全师有口皆碑,为了把暖瓶里的水准确无误、一滴不露地倒入杯中,他曾反复地用不同的茶杯进行强化练习。标准之高,要求之严,令全团战士肃然起敬。
一次,李团长在宽敞的会客厅随手丢下20元钱,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去。父亲清扫卫生时发现了地上的钞票。20元,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不小的数目,相当于父亲近一年的津贴。但他毫不犹豫地如实上交了。原来,这是李团长为了考验父亲,故意做的一个诱饵。父亲的行为得到了首长的颔首称赞。李团长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鬼,人之初,你便上交了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当即修书一封,推荐父亲去辽宁营口第八预备学校学习。
经过严格筛选审查,1955年,父亲走进了辽宁营口市第八预备学校。走进学校的父亲,不再是一名无钱读书、在学堂外偷听的放猪倌,实现了萦绕于心的读书梦。三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沈阳高炮学校,继续进修深造,连年被评为“学习竞赛优胜者”。
父亲在军营这所大学校里如鱼得水,并继承发扬了李忠仁团长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刚正不阿的秉性,一直到自己也成了战士眼里和蔼可亲的首长。1959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调入高炮67师626团任指导员。
五
我的母亲董秀兰,是革命烈士的女儿。1947年,时任妇女主任的外婆不幸牺牲,当时,风华正茂的她已有五个月的身孕……10岁的母亲和5岁的姨妈只好相依为命,度过了最艰难的烽火岁月。1957年,激情燃烧的岁月,经人介绍,拥有“英雄情结”的母亲与父亲结为红色革命伴侣。1960年,我的姐姐出生。而立之年的父亲非常高兴,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相聚的日子总是很短,离别的日子总是很长。母亲与父亲婚后一直两地分居,分别最长的一次时间是一年半。那时,母亲已身怀6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她领着5岁的姐姐,与父亲依依惜别。母亲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嫂就意味着奉献。”面对生死离别,母亲强作欢颜,背着父亲,独自哭得如泪人一般。母亲支持父亲的工作,无声地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1966年10月金秋,父亲回山东老家探亲。踏上这片生他养他的广袤土地,他激动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炕上炕下,挤满了父老乡亲,父亲带来的过滤嘴香烟和花花绿绿的糖块,更增添了喜庆团圆的浓烈气氛。一群小孩子你推我搡地嬉笑着抢糖吃,男女老少围绕着父亲,听他讲述战场上的故事,分享抗美援朝的传奇经历,他是大家眼里的大英雄,是“最可爱的人”!
已满周岁的哥哥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蹒跚学步的他歪歪扭扭地扑向父亲的怀抱。父亲离家一年多,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父亲眼含热泪,紧紧地抱着哥哥,亲了又亲,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我相信,那一刻,父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为了永恒地纪念这一刻,他专门到照相馆,给姐弟俩照了一张黑白合影照。第一次面对镜头的姐姐表情严肃,拘谨紧张,站立着手握《毛主席语录》。调皮的哥哥则站在椅子上,手扶椅背,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
祖母更是喜极而泣,所有的牵挂与相思,都化成了喜悦的泪水,她张罗着让大伯一家杀鸡宰鱼,炒菜煮蛋。母亲则收拾着屋里屋外,铺上了崭新的被褥……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父亲任北京顺义公安局军代表,后调入河北滦县52979部队626团任教导员,亲历唐山大地震。1979年,48岁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山东潍坊,与母亲同时被分配到了一所职业学校,开始了从头再来的事业。1993年,父亲正式退休。
我时常想起诗人桑恒昌的一首诗:“六十岁,是一篇文章;七十岁,是一部专著;八十岁,是一部文集;九十岁,是一部辞海,只有天年,才是自己的万里江山。”若一生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分,父亲刚过完金秋,步入初冬。用这首诗里的比喻,父亲的文集刚刚开始续写。能点亮“万里江山”的人,才是堪称智者人生最后的金秋。我希望,父亲能拥有自己的“万里江山”,福寿平安。
——给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