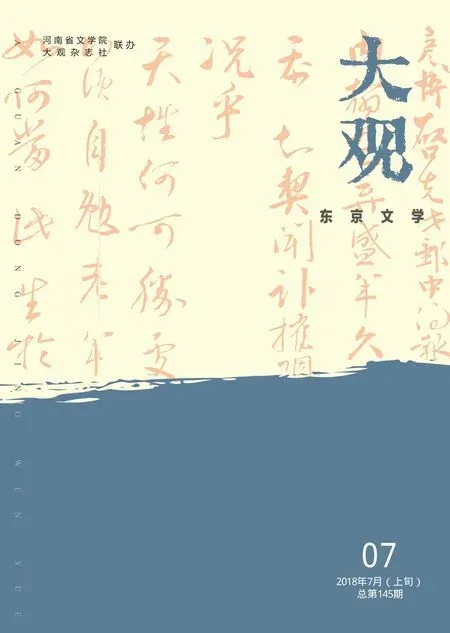最后的忏悔(短篇小说)
婶已病入膏肓,在镇医院治疗了七天,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就坚决要求丈夫潘有福把她弄回家,静待天命。主治大夫也无力回春,就同意让婶出院。
婶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嫁给丈夫后也没能为他生个一男半女,她就让丈夫的子女、儿媳和女婿管她叫“婶”,但不带“子”字,绝不允许他们叫自己“娘”或“妈”;当然,丈夫的孙子辈、外孙辈、重孙辈、重外孙辈依然管她叫“奶奶”“姥姥”或“老太”。
回家后,婶每天只能喝几小勺面水或开水,至第三天开始昏迷,但昏迷过后却很清醒。这天上午,婶从昏迷中醒来,清醒的目光把病床前的家人扫了几遍,显出遗憾的神色。丈夫走到婶跟前弯下腰,问她是想说啥。婶说,我……想……想见个人。见个人?见谁个?你要见哪个?丈夫连问三遍,婶就艰难地伸出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个手指头。你想见三个人?丈夫又问。婶又把中指弯了弯。丈夫明白了她想见的人,说,你想见任老三?能见他吗?人家会来吗?婶的眼角就溢出了一滴泪,丈夫就说,好,他婶,晚上我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吧。听到这句话,婶的脸上似有了隐隐约约的期待。
任老三在大潘庄西边的小任庄住,大集体时大潘庄和小任庄是一个生产队。有福搞不明白,都这个时候这个样子了,老伴为啥要提出来见任老三。
解放前,又高又胖、壮硕有力的婶是任老三的结发妻。虽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亲的,但婚后两人还是很恩爱的。怎奈结婚三年,婶的肚子一直不见膨胀。而老三的两个哥哥先前都被抓了壮丁,杳无音信。给任家传宗接代的责任就落在老三一人身上。在那个时代,不能延续香火的婚姻是很难继续下去的。老三的父母就到处张罗着给老三纳妾。婶当然不情愿;老三也不乐意,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三胳膊也拗不过大腿,就又娶了一个听力有障碍的姑娘做了二房。婶就搬到偏房里住。为了传宗接代,老三到婶房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等到妾为老三生了个儿子后,老三基本上就不再到婶房里去睡了。但之后,妾也没能再生出第二个孩子。不过,后来任老三还是有了三个孙子两个孙女、几个重孙子孙女和重外孙外孙女。
解放后,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度。妻和妾只能留一个。老三就离了妻留下妾。婶还在老三院子里住,只是在偏房里垒了锅灶,另立门户,吃自己的饭,种自己的地。后来工作队员就把婶介绍给东边潘庄的潘有福。潘有福前几年死了老婆,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娘,日子过得十分凄惶。冬天里,一床破被子盖几个人,两边掖不住。怕冻着孩子,有福就用麻绳把被子两边缝在下面铺的草席上。开始,婶不同意,虽不能做老三的妻子了,但老三还在她心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啊。工作队员反复做她的思想工作,又找了几个跟她关系好且能说会道的妇女劝她,最终劝醒了她,她就改嫁给了潘有福。婶虽说不能生育,但却很喜欢孩子,疼爱孩子,视有福的几个孩子如同己出,几个孩子对她亦如亲娘,但她只许孩子们叫她“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再也不同老三家任何人来往。大集体时出工或赶集上店偶遇了,也如同陌路,一低头便错了过去。
都这个时候这个样子了,她为啥要提出见任老三?有福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能不能见?有福担心的是村里人会不会说三道四,会不会影响名声。夜里就把几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叫到家里商量。晚辈们大多说:“这是您自己的事,您的事儿您做主。”有福就一声声哀叹。一个高中毕业的孙子说:“爷,我看我奶也撑不了几天了,你就满足她这个心愿吧,可别让她带着遗憾走。”有福就对这个孙子说:“那你明天就去请你任爷爷来。”这个孙子的父亲开口了:“你叫他去请,我也不反对。可人家会来吗?人家要是不来,咱多没面子呀?闹得沸沸扬扬,村里人怎么看咱?”“二啦,”——说话的这个儿子排行老二,有福一直这样称呼他,“你是担心因为那事儿人家还在记恨咱吗?都二十年了。当年,虽然任老三受了伤,可咱也赔了他医药费和误工费,你还为这事儿坐了几年牢,也算两清了。来不来是他的事儿,咱总得把话给传过去吧?”于是,高中毕业的孙子就踩着月光往小任庄去了。
他家真还在记恨这件事儿吗?孙子出门后,当年的事儿犹如大雨后碧水河的波浪一样在有福的胸中翻滚起来。
大潘庄和小任庄在碧水河北边一字儿排开,正对着碧水河的一个弧形大湾。这个河湾犹如一张巨型的弓,弓的“弦”正对着这两个庄。庄的北面都是旱地,南面都是水田。水田地势由北向南渐次低下去,呈梯形。上世纪七十年代,公社组织生产队长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队长就带领社员苦干一个冬春,把庄南一二百亩水田改造成了整整齐齐、十分壮观的梯田。第二年,县里又举全县之力修碧水河,庄南的河道被取直了,还在新河的东头留了一道小小的滚水坝,蓄水浇田。队长又领着社员挑土在坝西侧河边往北筑起一条抽水灌溉渠。
联产承包的第二年,水稻正扬花时。农谚:小麦扬花要火烧,稻子杨花要水浇。可当时烈日如火天天烧,田里水都晒干了,有的田块出现了裂缝,急需抽河水浇灌。家家户户心急如焚。可怎么个浇法,大家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大集体时,生产队是按地势由高到低的顺序浇水的。可田地包到户后就不一样了,都想先浇。一是早浇一天,庄稼就少受一天损失,二是田在下边的担心浇晚了河里的水不够用。有几家就放出狠话:要是生产队拿不出公平合理的办法,河里的水谁也别想动一滴,宁可全村的水稻都干死,也不能光干死哪一家的!
后来有人建议,先把全村的田每块都测量一下,看总共需要多少方水,再把河里的水测量一下有多少方。若河里的水够用,就还按大集体时的顺序浇水;如果水不够,那就都干着,老天爷叫吃多少就吃多少。能亏一群不亏一人,要穷大家一起穷。结果,这个建议大家都赞成。队长和会计就带着两个上过初中的小青年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测量任务。测量数据表明:水不仅够用,还略有剩余。这才开始往田里抽水。但事先有些因素还是被忽视了。一是浇水时,各家各户都把自己田里的水蓄得比测量的多,才让往下放水;二是天太热,河里的水蒸发得太快。因此,到河里的水实在抽不出来时,最后一块九亩大田就无水可浇了。
这块田是任老三的。面对干蔫了的稻秧,老三在田埂上蹲了整整一天,太阳落下好大会儿他才扛着铁锨垂头丧气地往家里回。老伴和孩子们也火烧火燎无计可施。可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却发现老三的田里也有了半田水。稻秧的花也精神起来。而它上边的那块田有的地方露出了泥巴,田埂上有一处挖开的豁口。这块露泥巴的秧田正是有福家的。
于是爆发矛盾,两家人大吵起来。 有福说是任老三偷着把他的田埂挖开放了他田里的水,任老三就说他绝对没挖。有福就说:“肯定是你挖的,因为有人看见天黑透了,田里都没人了,你才扛着铁锨往庄里回。”任老三就说:“我绝对没挖,天再黑,老天爷能看得见!”说着就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捶胸指天发誓:“要是我挖的,天雷劈我;谁要是诬赖我,天雷劈谁!”
这时,有福的二儿子掂着一把铁锨蹦到老三跟前,额上青筋暴突,眼睛血红,一把拽起任老三吼道:“你真是半门媳妇子嘴头硬,提上裤子不认承!你敢做就不敢当吗?真是贱骨头!”“你骂谁?”老三挣脱了“二”的手。“二”说:“我看你这贱骨头就是欠揍!”老三说:“谁不知道你是牛血(方言:指极不讲理、脾气暴躁、缠住人不放、不计后果、谁也惹不起的人)?我就叫你揍!谁要是不敢揍谁就是孬种!”“二”说:“你说我牛血我就牛血,今儿就叫你尝尝牛血是啥味!”说着就挥起铁锨朝老三头上砍去。老三本能地一个趔趄闪了过去。“二”又一铁锨朝老三左腿砍去。这下砍到了老三脚脖子上,小腿骨被砍断了,老三当场昏了过去……
后来,老三在县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又在家躺了三个月;再往后拄了三年拐杖。“二”被抓起来,判了三年刑。
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上午九点刚过,任老三老两口还是带着儿子儿媳、孙子孙媳、重孙等大大小小八九口子,第一次走进了潘有福的家门。一番寒暄客套自不必说。这时,婶的精神比前几日好了许多,几欲挣扎着坐起来。有福就过去让她继续躺好。婶的眼神碰到了任老三的眼神,就抬起右手往里摇了两下,示意叫老三到她跟前来,老三就抬步站到床边;婶又用右手指了指墙边的一个木凳,那个高中毕业的孙子明白了奶奶的意思,就走过去把木凳搬到奶奶床边,让任爷爷坐下。老三坐下后,有福的一个儿媳提议大家先出去回避一下,好让两位老人无拘无束地说会儿话。婶见有人开始往外走,嘴里就传出微弱但清晰的话:“都别走哇……”右手又往里摇了两下,叫大家都站到她床边。于是大家就围着她站了一圈。婶示意要拉老三的手,老三于是把左手伸了过去,婶就轻轻摇了下头,老三就换了右手。婶要侧过身子躺,一个儿媳就帮她向右侧过了身子。婶就把左手掌放到老三右手上摩挲,两个眼角都有泪水溢出。老三的右手是残疾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跟小拇指一般长,而且没有指甲盖。两个庄上的人都知道,那三个手指缺的部分是被人砍掉的。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一个集日,老三到碧水河南岸的瓦盆镇赶集,逛到一个猪肉摊前。一个买肉的老头正在跟卖肉的屠夫争执,说肉没给够秤。屠夫说:“我一年到头凡是逢集都站在这儿卖,卖的就是秤头,就是门头。买家就是我们一家老小的衣食父母,我怎敢缺斤短两自毁生意呢?”屠夫姓赖,叫赖海,人都叫他赖孩或老赖。任老三跟他很熟,就想从中斡旋一下,免得起大事端,就说:“够不够斤两,再称一下不就妥啦?”还没等老赖同意,老三就抓起秤杆秤砣,把那块猪肉挂在秤钩子上,把秤砣绳子放到刚才屠夫称的斤两位置上,老三感觉秤砣起不来,就把秤砣绳子往里连挪了几次才放平秤杆,一看星星,三斤肉竟短了半斤。
屠夫的脸红了,老三赶紧打圆场说:“人一天三迷,都有看走眼的时候,老板肯定不是故意的。”因为周围人多,老赖双手抱拳朝买肉的老头连摇了三下,赶紧又割了一块超过半斤重的肉塞给那个老头。上午老三没有回,夜里又到一个朋友家里喝酒,正好朋友也请了老赖作陪。酒都喝高了,老三就劝老赖做生意要讲诚信,偶尔错一次好说,次数多了就难说了……老赖就骂他故意给自己难堪,砸他牌子。吵着吵着就要动手。众人就起来劝。朋友就对老三说:“任兄,你回吧,我也不留你啦,酒以后咱还有的喝。”老三就起身返家。
刚过碧水河,老赖就掂着一把砍刀追了上来,还疯狂地叫着:“好你个任老三,狗咬耗子,看我今儿晚上不砍死你!”月光下,老三见老赖真的酒疯劲上来了,就撒开腿跑起来,把老赖越撇越远。到了院门前,推不开,就拍门,拍了一阵也没人出来开。家里只有妻和小妾母子——老三的父母都已故去——小妾耳朵背,又住在后面的堂屋里,妻住在偏房里,可能睡熟了。老三又猛拍了一阵子门,仍没人出来开门。这时老赖已掂着砍刀来到跟前,举起刀。老三就拼命反抗。老赖比老三个子大,又长年杀猪,手劲特大。老赖左手一下子捏住了老三的右手腕,使劲按在门上,右手一挥,砍断了三根手指头,老三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惊得老赖酒醒了,后怕了,猛转身就往回跑……
婶摸着老三的那三个残指说:“老三,老三……我、我……这辈子……对不住你……我都瞒了你……一辈子……我该走了,我得跟你说实话,你的手指头被人家剁掉……都怨我……”“咋能怨你呢?又不是你剁的。”老三以为她糊涂了,赶紧说。“是怨我呀……你还没敲门时,我听见脚步声和喘气声就听出是你回来了……可我使了奸心……我想,我就是给你开了门,你也不会到我房里跟我睡……我就装着没听见……我想……我听见没听见你也不会知道的……其实,咱家的铡刀就在我房里门后边放着,你也知道,我那时力气是很大的……我要是拿着铡刀出来,咱俩还拼不过他吗?……”满屋子静得如混沌初开之前一样,大家听得都默默流泪。婶又说了一句:“你还能原谅我吗?”老三点头,老泪纵横 。
次日早饭后,老三一家人正准备去有福家时,有福的那个高中毕业的孙子又过来了,说:“我奶快走了。”
老三一家人来到有福家,有福家的人面容都很沉重,屋内的气氛仿佛凝固了。 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微弱的气息正一点点散去。须臾,合上的眼皮似乎睁开一道小缝,停了一会儿,便紧紧合上了。婶平静安详地走了,脸上浮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两家人大放悲声。哭了半小时,有福把大家劝住,郑重地说:“昨夜里,他婶说还有一个事儿,没敢当着大家说,就给我说了,叫我等她走后再替她跟大伙说说,跟大伙说了,她到那边心里才会愧得轻一点儿……”众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等有福往下说。有福接着说:“她说,二十年前,我家田埂上的豁口是她夜里去挖开的,放点水给老三的田,别叫秧干死了。老三家也有八九张嘴等着吃饭呀。”顿了下,有福又接着说,“他婶说,年轻的时候能帮老三却没帮,结果他手被人砍伤了;年老了能帮他时帮了他,结果他腿被砍伤了。当年放水的事儿她没出来说话,是她怕村里人戳她脊梁骨,说她跟老三婚都离几十年了,心里还在想着人家,作风不好;也怕自己家里人说她胳膊肘子往外拐……”
有福把话说完,那个高中毕业的孙子就领着两家人给婶的遗体连鞠了三个躬。
安葬婶时,两家后人都披麻戴孝。八十多岁的有福和老三拉着手颤颤巍巍地来到婶的墓穴前哭泣,还互相劝着安慰着对方别再伤心了。
从此,两家人尽弃前嫌,主动往来交好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