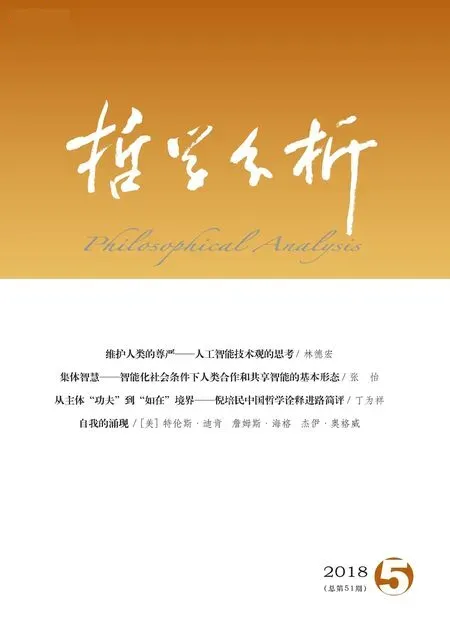“超真实”概念探析
马小茹
伴随着后现代的加速推进,人类告别确定的生存秩序,开始步入符号空前激增的超饱和拟真秩序,迎来了新的拟像真理(超真实)时代。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眩晕”图景,人类社会整体上进入不可回溯的加速“失重”状态。大部分人还没有足够准备,就几乎别无选择地被卷入这一漩涡。本文从符号哲学的角度出发,尝试描述、概括、梳理分析这一新的生存世界图式,并作出一种前瞻性的批判回应。
一、“超真实”问题缘起
“超真实” (Hyper-reality)概念是由鲍德里亚提出的。作为一个时代主词,“超真实”是鲍德里亚在对现代性真实观念的符号学反思批判基础上,对大众消费社会症候的“确诊”。同时,其具体生成与现当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主要是在超现实主义到超级写实主义的艺术蜕变中直接催生出来的。①Richard G. Smith, 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5—97.本文对“超真实”的研究缘起基于以下理由。
(一) 人类生存世界图式的根本转变
当前,随着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人类生存方式普遍受制于大众媒介的符码操控,人类以往长期构建的实体性存在样式都被不断数字化,连同人类周遭世界也在被不断符号化。这就意味着人类根本上告别“原型”真实的生存处境,进入“超真实”生存状态。这样,原来占主导的现代性“真实”话语体系及其一系列思想观念也普遍面临一场根本变革。
1.“能指符”/“真实”指涉物的翻转
从人类现实生存秩序来看,符号从“原型”真实的“代理者”,晋级到第一性真实——符号的真实,“原型”真实就下降到“质料”而被吸收进符号系统本身,符号(拟像)的真实成为必然。在大众媒介操持的时代,“真实”的指涉物被清除、密封,导致“能指符”完全脱离与外界真实世界的关联,符号获得了绝对的飘逸自由,人类进入“符号狂欢”的时代。这样,“真实的指涉物”与对应的作为其“代理者”的“符号” (能指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翻转:曾经作为真理依据的固态指涉物被不断地转化为“液气化”的符号(能指符)真实形态。正如波兹曼所断言:“在语言文字的‘诠释时代’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间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②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章艳、吴燕莛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如今几乎是全人类开始步入图像嬉戏的魔幻世界。
2. 大众文化消费时代需要新的真实范式支撑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推进,早期关于什么是真实的观念构建已经被抛弃,甚至被看作科学的幻觉。尤其是量子力学的提出,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形成的居于至尊地位的“确定性”原则。同时,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现代性文化领域出现了这样一种回归趋势,即对于这种真实原则的多次质疑和抛弃,同时导致不存在真实的指涉物这样的观念趋势。
首先,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在物质生产领域,社会总体上对人的基本需要满足达到饱和以后,资本价值逻辑促使生产的重心转向以最大限度开发大众文化(符号)消费“欲望”为目的的再生产。对于一个文化符号受大众媒介操持的现代国家来讲,其逐步占据“生产”主导地位的将是“符号产品”。这样,文化性娱乐工厂会因自身的发展而不断设定新的真实理论基础。因为,从根本上讲,大众媒介的全面操持秘诀在于对大众“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全面控制,而这种集中在大众娱乐层面,并且遵循“娱乐至死”原则的消费文化符号再生产,就需要新的符号真理性的学理支撑。
其次,大众在这种数字化消费时代,普遍性的陷入符号化消费和被消费的双重境地。随着拟像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图像真理原则的潜在“完美”构形,人们越来越不能承受人(事物)固有缺陷的“真实”,在拟真媒介技术的多重模型操作中,真实的缺陷肉身在穿越这些媒介之后,经过媒介符码化,就能遮蔽所有的“残缺”,剩下一个被媒介不断任意性复制加工的“美丽”能指符,而真实却被符号堆积成的“坟头”活埋。小到个体的极端事件,大到国际灾难性事件,在拟像媒介不断复制传播中,我们无法知道真相,而只能在不同版本的超强度“拟像”视觉暴力威慑下生存。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悲剧”性拟像的消费者,而我们却和事件本身并没有关系。
在“拟像”时代,任何意义上的“真实事件”,本质上都是一个拟像事件,我们只在拟像光滑的表明滑行。媒介拟像竟成了我们避免真实“创伤”的有效保护隔离带,就像“防弹玻璃”一样;而真实事件就像“真枪实弹”打在媒介拟像层,我们得到的就是媒介拟像分泌物的真实——我们是真实灾难的幸存者,消费成了救赎我们的唯一真理。人们对“真实”事件的唯一真实反应就是对媒介拟像化的“真实”冷漠。在此,冷漠与消费形成共构,真实就变得“无所谓”。这意味着所有关于“真实”本身的存在意义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仅仅是再生产链条上符合“价值”原则的拟像真实。
3.“代替者/代理者” (物/人)的翻转
数字化时代人类的普遍生存图式的集中体现就是人的符号化生存维度。随着“全能式的”消费者及其世界整体上呈现“比特”水平上的符号化趋势,人陷入符号产品的海洋,同时也沦为一种数字化存在,成为各种符号装置下的功能性产品。人因此成为一部欲望再生产机器,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翻转。科技理性宰制下,万能的物化功能符从人的“代理者”转变为人的“代替者”,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式的翻转:“物”升级为人,人沦为物。物从“它”变成“他” (她),人从“他” (她)变成“它”,人彻底地从“役物”转变为“役于物”。①这里“代理”与“代替”区别极大,前者是以人为主体的,服从于人的,后者是人成为一个“傀儡”,变成人服从于“代替者”。参见李河:《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126页。人最终趋向消失,人类已经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这根本上源于人类自由的悖论:“人是个从不满足的动物,他总是要追求自由的最大值。这个最大值就像人们用铁丝系在猫尾巴上的老鼠模型,引逗他不断追逐奔跑。”①李河:《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作为代理者的符号产品在使用中完美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使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满足。然而,“工具代理者的出现恰恰是对人自身的否定:随着庞大工具世界的日益进步和完善,我们日益发现人的天然身体和头脑简直原始得让人不可容忍”②同上书,第128—129页。。
人类在完美的符号代理者面前终于变得“自惭形秽”,再也无法承受自身真实的残缺。一句话,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决定了,人必须“勇敢”地迈出完全“否定自我”的最危险一步——消除真实的人,即用机器改造和加工人这种产品,完全用“替代者”来代替人的一切,人作为真实的剩余物趋向过时而不断消失。人从“自由”出发,最终却完全消失在“物”的自由之中,这就是人类的“自由”宿命:“从克服自己天然器官的若干缺陷开始,直到把自己当作全部缺陷加以克服结束;从对世界的有限虚拟化活动开始,直到人生的全部虚拟化境界结束。”③同上书,第129页。这就是人类自由的“终结”道路,也是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最终,人把人本身超越了,人什么都不是了,进入了所谓“后人” (post-human being)时代。在高度自动化的智能人面前,人变得无所事事,纯粹是一种多余和累赘,而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和精灵般的“索菲娅”做游戏。这不能不说是人的又一种不可思议性。本文正是针对这一人类普遍面临的“超真实”现实处境,本着对“人”的何去何从终极关怀,展开对“超真实”的理论探 究。
(二) 从超现实主义到超级写实主义的艺术蜕变
艺术④本文的“艺术”是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的“艺术”概念,不是广义上的经验世界艺术。正如丹托所言:“我的观点是艺术,作为艺术,作为与现实(reality)相对应的事物,是与哲学一起出现的,为什么艺术是哲学所必须关心的某种东西,与这一问题部分匹配的是,为什么哲学没有历史地出现在每种文化中,而只是出现在某些文化中,尤其是在希腊和印度出现。” (Danto,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Criticism,Vol.33, No.2, 1974, pp.77—78.)作为特定时代的观念性符号产物,其最感性直观的叙事特质对哲学的推进往往具有预演效应。本文涉及“真实”原则的动摇及颠覆,从艺术角度来诠释,则是当代艺术危机的必然结果。鲍德里亚的“超真实”思想正是从批判超现实主义的主体性“幻象”解放,到吸收超级写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对当代“艺术终结”的哲学回应。故本文将关涉符号“狂欢”的艺术符号贯彻其中。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超真实”与“艺术的终结”状态有一种共构锁合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1. 超现实主义对“真实”的双重指向
正如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开创者布勒东所宣称:“我相信在表面上被认为是矛盾的两个状态,将来是有办法解决的,那便是梦与现实的统一。那可以说是绝对现实的一种,也可以说是超现实的一种。”①1924年布勒东公开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标志着超现实主义运动正式开始了。尽管《宣言》是一种立场的声明,它肯定了布勒东和其他同事挪用并重新定义了阿波利奈尔的术语——超现实主义。目前关于超现实主义运动及其后来的理论思想等特征的辨识依据主要还是依据《宣言》的定义:超现实主义——纯心理自动主义,人们借此以口头、书面甚至或其他方法表达思想的真正活动,它受思想的支配但又不受理智的控制,超越一切美学或道德的成见。参见金·格兰特:《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王升才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2页。在这里,超现实主义者天才般地预言了今天的“超真实”现实存在。可以说今天的“超真实”正是超现实主义的“现实版”,而超现实主义则是对“超真实”的一种理论预演,其充满幻觉的奇思妙想对于拟真时代的到来意义深远。
现代伊始,在真实原则主宰下,整个生活世界不断趋向“物化”,超现实主义正是在20世纪先锋艺术领域展开的,是对这种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深度怀疑和精神抗争。超现实主义试图构建一个与现实对抗的、幻想的他性真实世界,这是一个全新的真实世界在艺术中的呈现,主要依据就是非理性的梦想、幻象荒诞、潜意识等领域。其艺术价值发挥了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和人文担当,同时,也悲剧性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理性神话破灭时刻的到来。当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宣布“我和疯子的唯一区别就是我知道我不是疯子”的时候,现实世界已经疯狂。
概而言之,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挑战主流真实规则的非理性真实图式,其整体上遵循的仍然是哲学层面的“真实”原则,是一种“异质性”真实原则,内在蕴含着对真实的双重性指向:一方面是超现实主义坚决反对的真实,一方面又是超现实主义始终开辟和坚守的可能性真实空间。其深刻的哲学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更在于其对真实的复数性指向(真实图式的变奏),其中孕育着“超真实”的现实蓝图。
2. 超现实主义向功能“物”的蜕变
超现实主义是在与功能主义主导的物化现实世界相对抗,其批判的立场和态度是鲜明的,是捍卫“真实原则”的艺术思潮。但是,它最终难逃政治经济学对艺术的殖民统治,以及艺术之物与功能之物的耦合,超现实主义最终沦为一个艺术批判的真实“神话”。
随着现代性功能设计的包豪斯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介入(反之亦然),交换价值原则发展到符号—价值阶段。而符号的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进入交换领域,其关键在于作为能指符的物的功能性任意发挥和使用。符号“任意性”必然浸染、操持所有可能具有价值的功能符号领域,这就必然导致艺术作为美学功能—审美价值的符号被首先征服和全面虏获,并最终导致真实原则下“艺术之为艺术”的边界完全崩溃。艺术的“贞操”必然殖民于功能主义的合理性操作算计和媚俗的艺术淫秽游戏之中。这要归结于功能主义的霸权本质,“即作为一种‘统治的理性’强制性地把自己嵌入它的秩序当中(就像在其秩序中的政治经济学),(嗅觉)灵敏地探测每一个事物并驾驭着全过程”①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1981, p.192.。超现实主义引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反过来却被符号政治经济学入侵,最终,也作为艺术符号的“另类”而被功能性符号体系全部吸收,消解在超现实主义的神话遗迹中。
超现实主义之物作为一种对功能物的嘲弄和超越,是伴随功能之物而出现的。尽管它们总是宣称反功能或超功能,事实上,超现实主义之物被功能之物的边界重重包围,超现实主义之物并不能超过艺术家的最自由想象——无意识的极限幻象,但是,功能主义的任意性决定了功能之物的边界就是没有任何边界限制,能够以复制的方式生产出无限的花样繁多的功能之物。对于做梦也想不到的物的世界,功能之物不仅可以完全覆盖,而且多于超现实主义之物。
与此同时,超现实主义自身也滑向对立面——功能物系统。如果说超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功能秩序”与“象征秩序”的临时性短路②Ibid., p.194.,那么,随着物(符号之物)的诞生以及其功能性(和语义学的)算计的不断延伸,整体性拓展到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超现实主义走向对立面,或者说催生出其自身的对立物,这也是一种必然。超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的幻想之物,通过否定的方式达到了对现实的被任意切割的物的世界的嘲讽,但是,超现实主义仅仅是嘲弄,并没有走出功能的边界,没有走向艺术的象征性维度。超现实主义被无所不能的控制体系完全吸收,没有存在的动力,超现实主义逐渐衰败没落,现代先锋艺术也接近尾声。
3. 超级写实主义是大众消费时代“超真实”艺术症候
(1) 超级写实主义是“真实”复本的“重言式”表征
如果说超现实主义的功能“物化”蜕变预示着“超真实”时代即将到来,那么,超级写实主义③超级写实主义(Hyperrealism,也写作Super-Realism,彼此意思相近,通常互用,又称高度写实主义),是绘画和雕塑的一个流派,其风格类似高分辨率的照片。超级写实主义可以看作照相写实主义(Photorealism)的发展。则是艺术领域的“超真实”实现。超级写实主义是对外在真实对象物的一种逼真的“比真实本身呈现得还真实”的技术操作的艺术再现。它采用的是技术上的顺势夸张延伸方法,就如“显微镜”“放大镜”的作用,甚至利用一些特殊的视错觉技术对真实对象的一些细节做了加强版处理,从而达到一种“超真实”的视觉震撼效果。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拟真的世界一定不存在真实”,与传统写实主义相比,超级写实主义是对照片的再现,又千方百计避开个人主观情感,试图用一种客观甚至冷漠的心态来复写照片中的现实世界。
从哲学角度讲,超级写实主义仍然坚持“真实原则”,在技术手法上是一种对真实的过度夸张机械性再现,以达到“恶心”的震撼效果,是走向艺术技术化的趋势。就深层意蕴来讲,它是对冷漠的物化机械现实世界的一种“重言式”批判与揭示。相比超现实主义的对抗性真实批判风格,超级写实主义是对真实的一种加强版的同一性再现,达到“愈演愈烈”的崩溃效应,这是一种艺术对现实的“同归于尽”式的摧毁。从现代艺术的一贯批判风格来看,超级写实主义无疑是一种艺术“自杀”式的表征现实世界的“死亡”征兆——无限完美的“真的不能再真”的世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超真实”在艺术领域的成功预演,预示着“超真实”的普遍性来临。
(2) 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与真实的关系比较
作为现代艺术流派,超现实主义与超级写实主义虽然都和真实有关,都是针对物化现实世界的一种艺术表征,但是,两者角度恰恰相反。超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理性世界的非理性批判抗争,而超级写实主义则是纯粹客观地对复本进行冷漠、夸张的复制性再现,不掺杂任何批判态度,只客观呈现过度的真实,它是一种艺术“犬儒”样式。
超现实主义与超级写实主义的区别关键在于,其艺术对真实的呈现方式和批判态度截然不同,但是又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超现实主义是在与真实的对抗中呈现出一种他性的真实艺术世界,是以A的真实对抗B的真实,彼此是一种差异性真实的横向并置与比较关系,是一种“反俄狄浦斯”式的叛逆。它最终却被功能主义吸收,彻底物化为一种融入现实世界的真实。超级写实主义则以加强版的同一性级层叠加方式呈现,其呈现样式是一种比真实A更加真实的A’,视觉效果上出现虚幻的真假倒置——真的和假的一样,假的比真的还真,是一种同一性的真实的自身纵向“比较级”关系(比什么还什么)。但其主题是鲜明的,比如克洛斯的人物绘画尽管真实程度不同,绘画的人物比照片或真人还真实,但是共同展现的就是“比冷漠还冷漠”的加强版。在这种看似平庸的艺术形式中,同质的比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反讽”效果,呈现出没有人性的机械物化世界。这种艺术上对“真实”的“升级”处理,正是鲍德里亚“超真实”问题提出的直接理论资源。
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三种现代艺术风格对于真实的再现关系,可依次简单概括为:逼真的再现真实(A→A);超越否定性呈现他性真实(A→-A);比真实还真实的过度再现(A→A’)。在绘画中可以参考的典型例子分别是:库尔贝的写实主义作品《采矿工》、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克洛斯的自画像。
从以上三种现代艺术对真实的差异性再现形式的比较分析来看,所谓“真实”并不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原则,而是一个不断转换形式、地位的哲学范畴。
首先,写实主义的画作是以“原型”真实为其创作再现的依据,并且,从艺术作为“能指符”形式看,它是以最大限度地逼真再现真实对象为作品标准。而且,这种再现不仅仅是一种采用理性形式,以“能指符”表层的相似性逼近真实的指涉物,而且是在作为艺术符号的所指层面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是作者内心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照。比如,库尔贝作为一位写实主义画家,采用“矿工”作为题材,来进行逼真的诠释,而没有选择后来超级写实主义的那种颓废的“自画像” (比如克洛斯)。这也反映了真实原则的真理性地位,它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再现,蕴含着艺术家对底层劳动者命运的关注。可以说,指涉物在此是神圣的、具有唯一性的真实。
其次,超现实主义者对真实就不再坚持“原型”真实原则,而是对抗性地提出新的真实——非理性真实原则。“原型”真实原则受到挑战,开始丧失真理地位。这不过是真实的形式的对抗性变革,是从理性真实向非理性的真实形态转变,其原则还是真实本身,遵循的仍然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理路。超现实主义与“原型”真实原则是一种对抗性分裂关系。
最后,超级写实主义创作风格与前两类截然不同,它既不颠覆,也不忠诚,而是冷漠地复制和再现。相比前两者,这种再现也是坚持真实原则,是真实的、任意的某个事物的图片(照片)复本,几乎对再现物没有深层的正向关照,而是一种反讽式的再现。从艺术的所指意义来讲,它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冷漠的物的再现;从作为能指符的再现形式来讲,其所选择的对象真假不再是关注的重点,符号的所指以及指涉物真实与否都无所谓。它通过最新科技手法、材料机械地呈现大众生活的周遭平庸之物的面相,甚至比对象更加真实逼真,是一种溢出的过度真实。根本而言,它要表达的就是“无意义”本身,是一种艺术的深层绝望。“原型”真实在这一阶段已经被解构,沦为不存在,通过这种溢出“逼真性”的比较级手法,揭示现实与艺术一样的无意义感,而且艺术比现实还无意义,是无意义的意义。这样,“原型”真实在后现代超级写实主义为代表的艺术思潮中“寿终正寝”。
(3) 超级写实主义的“超真实”蜕变
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承担严肃批判使命的先锋艺术逐渐消退、衰落,紧接着在艺术领域出现的就是反语式的类似超级写实主义的新媒介艺术。对于这种艺术来说,最主要的是,艺术不再表达什么了。比如,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沃霍尔的那些现成品——罐头盒、玛丽莲·梦露的若干张复制图片组合图形,此类“庸物”,没有任何创造性、艺术性可言,除了宣称它就是艺术之外,什么都不是,反而有一种丑的效果,机械地重复着艺术的堕落之美。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艺术通过“反艺术”的极端方式,与现实的物化符号世界产生图像同构效应——生活世界就是艺术本身,艺术就是现实本身,从而达到对现实的怀疑、否定、反思,并陷入一种整体性艺术层面的“犬儒”效应中。艺术不再对真实有什么持守,没有任何禁忌界线,艺术已经和真实完全重合,甚至比真实世界还堕落。鲍德里亚正是在对这一艺术领域最新发展趋向极其敏锐地洞察中,发现并作出了极具原创的理论概括——“超真实”,从而引领了思想界新的方向。同样,鲍德里亚的“超真实”思想对后现代艺术景观乃至其他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正如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艺术家彼得·哈雷(Peter Halley)所解释的:“是鲍德里亚使我认识到我用我一直所使用的日常颜色(day-glo colors)在做什么。突然间我开始把那些真实的颜色超真实化了,而且我认为,没有鲍德里亚我不可能把这一过程上升到概念化高度。”Cone Michèle, “Peter Halley”, Flash Art,Vol.126, pp.36—38.可以说,是鲍德里亚开创了拟真艺术的新时代,并且与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总之,艺术蜕变到今天,超现实主义的东西成了真实本身,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已为现实的审美光晕所笼罩。②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p.148.我们的真实生活世界也同步进入艺术审美“极乐”的拟真享受域。
(三) 哲学层面“真实原则”遇到新挑战
在对超真实问题的探究中,本文最终要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真实”问题。“真实”一直是哲学界,尤其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系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它也是一切认知理论、实践活动的一个本原性基点,是确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或者说人类构建世界图式框架的基本前提。在不同时代中,真实的哲学图式总体上是复数的存在。所以,哲学之真,始终是一个不断建构、不断解构的流变过程。人们何以对“真实”如此“当真”呢?只因为人是一种有自我意识、能够并且需要区别他物的存在,人是一种需要且能够展开自我确定并确定外在世界的存在。真实是人的精神依托、生存生活的凭证,尤其是传统形而上学智慧的集中体现。
1.“超真实”的真实问题域
“超真实”根本上属于真实谱系,“超真实”产生于关于真实的现实与观念的土壤之中。“超真实”的产生同时伴随着真实的消失。但是,真实的被遮蔽区别于不存在“真实”本身。现代哲学伊始,尤其是尼采以来,传统形而上学遭遇到轮番的颠覆行动,但是,对作为现代性核心语词的“真实”的最激进否定和超越,则非鲍德里亚莫属。鲍德里亚对西方文化中关于真实性观念问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和理论诠释。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既然宣称真实性是普遍的,那么认为存在一些并不能遭遇真实的社会就是一个悖论。然而,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真实的观念和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结构,这种构造是与科学技术的诞生相关联的。鲍德里亚的真实观念受拉康的影响,他始终认为,原初象征性阶段没有人的主体性介入、没有人的意识参与的独立自存的“原初物”才是真实的。事实上,这样的真实只能是一种观念的假设,并不存在与人类无关的不被意识到的真实。鲍德里亚企图通过前现代社会的象征秩序反对现代的真实观念和后现代的超真实观念。在鲍德里亚“超真实”语境中真实的秩序经过三个阶段:象征秩序下的真实、生产秩序下的概念真实、拟真时代的超真实。真实的消失与死亡是从真实到超真实的必然宿命。
鲍德里亚坚决批判的就是第二阶段的真实形态——概念的真实。因为,“真实一旦被命名,它就消失在概念中,失去了自身的能量,即‘通过把事物再现给我们自身,通过为它们命名和使它们概念化,人类借助称谓使它们存在,同时促使它们死亡,隐蔽地把它们与它们的原初真实分离开来’”①Richard G. Smith, 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2011, p. 94.。对于鲍德里亚来讲,抽象的理论语言凝固了具体化的活生生的世界,真实消失在“结晶体”式的概念中。由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变成知识史的一个碎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变成一种陈词滥调以及精神分析的知识和商业工具;全球化变成一个市场化口号或攻击对手的新的恶言形式。②瑞安·毕晓普、道格拉斯·凯尔纳等:《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戴阿宝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总的来讲,鲍德里亚推崇的真实是亦彼亦此的原初象征性存在。
2. 鲍德里亚对索绪尔符号语系“真实”理路的承接
现代性的概念真实诞生以后,引起一场复杂而深刻的文化模式转变:原初的象征性文化符号转变为现代性文化符号模式。这种符号被索绪尔理论化为三项构成形式:能指符(signifier——语词)、所指符(signified——概念)、指涉物(referent,在此暗示着思想的外部——真实的世界)。然而,“最终在这种模式里存在一个永久性问题,即这种真实的存在是蕴含在符号内部并且由此指向一个再现物(表征),还是这种真实仅仅是在符号之外的某种呈现?”③Richard G. Smith, 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p. 95.鲍德里亚在这里暗示了三种真实观:概念逻辑的真实、外在世界的感官意义上的真实,以及符号本身的真实。鲍德里亚并没有按照形而上学一贯的路子追问索绪尔符号语境所关涉的“真实”问题,而是抓住其对“真实”的“悬置”处理,顺势沿着“能指符”真实结构模型指向,构造其“超真实”符号语系。同时,利用索绪尔留下的关于“真实”的理论裂缝,转而以“真实”为靶心,发起对现代性的全方位批判,瓦解真实概念的形而上学合法性依据。这一点充分暴露了鲍德里亚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态度。从符号学角度讲,鲍德里亚属于索绪尔谱系。
3. 现代性“真实”问题的提出
超真实理论的提出源于现代性哲学关于真实再现的危机——符号对真实的再现之不可能性,导致了一场符号与真实或指涉物的分离运动。鲍德里亚从符号自身的演进来展开批判,并提出解决真实问题的出路:“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①Jean Baudrillard, Forget Foucault, New York: Semiotext(e), 1987.
随着大众媒介时代的到来,这场现代文化模式的大转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场文化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拟真时代的到来。“当前符号再一次呈现出独立自存状态,但是这并非说我们退回到第一阶段。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符号被假设为我已经提出来的‘超真实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现实就是真实的指涉物消失,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的无所不在。”②Mike Gane,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1982—1993),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42.这就意味着,从科技进步的动力因来看,符号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自主”,是由于数字信息媒介技术的出现,符号的模式化再生产有了物质保障。“根据第一阶段的幻象逻辑,符号指涉物的消失不算有争议的问题,而是本来就不存在指涉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返回一种原初状态——不过很显然,彼此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③Ibid., p. 142.
二、“超真实”概念界定
(一)“超真实”词源学与翻译
1.“超真实”词源学
“超真实”的英文词为“hyperreality”,其前缀“hyper-”主要指高于、超过、之上、过度等意思,它根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许珀里翁。“许珀里翁”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穿越高空者,从高空往下俯视者”,从他的名字(Hyperion)中产生了词根hyper-,表示“超过、太多”。④这里不同于“Sur-”词根,尽管后者也表示“超越、超过”,前者是在纵向的同一性意义上的“过度”,越出事物本真的边界达到“虚假”的程度,或者说比本真还真的程度;而后者是指横向的与事物本真相对立的相反的一面,比如相对理性现实的“超现实主义” (surealism)其实就是一种非理性的真实。前文也有涉及,不再详解。“真实” (reality)则是“表示实际存在的属性” (quality of being real),即现实、实际事实。中世纪拉丁语中有“realitatem”(nominative realitas),表示“真实的存在、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reality”一词在哲学层面则渊源悠久,通常被翻译为“实在”。从巴门尼德对“实在性”的哲学追问就开始,它就是关涉“存在” (being)的真理性概念,并一直是哲学家关注的主题,与形而上学终极真理“确定性”问题息息相关。本文主要涉及的是哲学范畴的真实,不同哲学语境其指涉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这也说明“真实”本身就是一个复数概念。
作为后现代语词,“超真实”是鲍德里亚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为了深入解读“超真实”概念,必须首先了解关于鲍德里亚文本中的词语前缀“hyper-”。在鲍德里亚文本中,尤其是其中后期的成熟思想表述中,该词缀的整合性使用相当频繁。鲍德里亚的这种概念用法,除了依据一些相关的学科前沿,比如病理学上的疑难杂症,最主要的是对美国这个“超真实”现实版本的概括,从而形成了关于社会结构的普遍性轮廓,描绘出迷狂的、双曲线式的、千丝万缕的“超级态”。美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符号化产品,它也是炮制超真实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对于每一个难判词(hyponyme)——这种词总是有讽刺性的前缀构成‘超-’——总有一种对应的超真实的晦涩类型:对于鲍德里亚和艾柯来说,这种疑难杂症就是超真实;他们预想的超难化包括超图像化(hypericons)、超程式化(hyperbolic formulae)、增生(hyperplasia)、过速进化(hypertelia)、超空间(hyperspace)等。从每一种难判词的延伸源头的范围中,根据给定的一系列难判词,都可以构建一个美国的形象:光学透视可以对应梦幻、虚拟、全息图式的;病理学角度可以对应类似肥大的、癌症的、病毒的等术语。这就是一个人可以用符号学的方式生产美国的超真实图景的一些运作方法。”①G. Genosko, Baudrillard and Signs: Signification Ablaz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156—158.
2.“超真实”的语词翻译与流传
“超真实”语词在中国的翻译、流传主要是伴随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传播开的,尤其是在对鲍德里亚的文本翻译、解读。“hyperriality”除了译为“超真实”,还有“超级现实”“极度现实”“超现实”等译法。例如,在车槿山翻译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Hyperrealism”被译为“超级现实主义”,“hyperreality”被译为“超级现实”,“hyperreal”被译为“超真实”;“极度现实”则是艾柯的《在极度现实中旅行》中文版中的译法;艾尔伯特·鲍尔格曼的《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中文版中将“hyperreality”译为“超现实”。本文选择“超真实”,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出于对“真实”的文里文外的内在概念一致性需要。鲍德里亚此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现代性“真实原则”,而真实与虚假是关联的、对应的,有强烈的反指涉效果。其实,鲍德里亚对“超真实”概念的运用,所针对的就是现实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过度的拟像虚假。其次,“真实”一词与“现实”还是有区别的,真实的不一定现实,现实的不一定真实。现实与历史、未来相对应,也与理论相对应(往往是强调实践性的时候),而且往往是和历史、理论问题关联在一起,所以,使用“现实”很容易混淆鲍德里亚“原初真实”的本意。
最后,“超现实”与“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超级写实主义”也很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解。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明显,最基本的就是:“超现实”是真实的加强版;超现实主义则是一个现代艺术流派,其产生恰恰是为了与现实的理性真实相对抗,通过艺术途径追求潜意识的梦幻境界,通过艺术来表述一种新的非理性真实,其实是极不现实的。鲍德里亚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象征交换与死亡》明确使用了“超真实”,本文承接了这一表述。
随着鲍德里亚文本的翻译与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展开,尤其是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超真实”逐渐从陌生术语变成了学界关注的“主词”,“超真实”必将会不断深入现实的角角落落,成为人们的“常识”。
(二)“超真实”文本生成分析——鲍德里亚与艾柯
1. 鲍德里亚“超真实”概念的文本梳理
“超真实”概念是从鲍德里亚早期的《物体系》 《消费社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生产之镜》这四部作品展开的。“超真实”最早是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作为“语词”出现。①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p. 194.随后其在承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进路中,不断呈现出现实世界告别“真实”步入“超真实”。
从“超真实”核心观点的提出、初步构建到发展,最后达到理论的成熟阶段,主要可以依据的三个文本是《象征交换与死亡》 《拟像和拟真》及《拟真》。正如鲍德里亚是一个“复制”论者,其原创性“拟像”思想也是通过“复制”性论述不断深入人心的。紧接着在《拟像与拟真》中对“超真实”的全面论述,鲍德里亚在《拟真》中主要是将前两个文本中的从拟像到拟真的两部分整合在一起。关于“超真实”的这三个核心文本可以概括为“三部曲”。
从“三部曲”中标题的明显变化就可以看出,鲍德里亚的三个文本尽管都有部分重复内容,但不同侧重点体现出对“超真实”主题的不断接近。第一部里“拟像”仅仅是整个文本的一部分,“超真实”才是初步提出;第二部“拟像”“拟真”成为并列的标题主词;第三部则是以“拟真”为题,而“超真实”就是拟真的效果、状态,也就是“超真实”阶段。
本文以《拟真》为范本展开追溯。鲍德里亚在文本开头就引用“拟像从来不是隐藏真理(truth)的事物,而是隐藏什么都不存在的真理,拟像就是真相(true)”,从而提出拟像的真理这一核心命题。这篇文章首先采用魔幻作家博尔赫斯的一个故事,以隐喻的方式呈现拟真秩序的“超真实”图像轮廓①这个隐喻就是“地图与帝国”。讲的是一个地图绘制家,制作了一个足够详细的关于帝国的地图,详细到可以覆盖整个帝国版图。帝国衰败的时候这张地图已经磨损了,只留下一些依稀可辨的地图残片遗留在沙漠废墟中。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一寓言的现实版已经环绕着我们,现在我们拥有的就只是属于第二拟像阶段的断裂式的魅力,或者说就是属于第二拟像的残骸。鲍德里亚把这个地图比喻为形而上学模式下抽象性“再现”衰败的美丽已经结束。“拟真”不再以“真实”的“原本”为依据从而“再现”真实本身,拟真是真实事物的“代替物”。,以此来说明对真实“再现”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拟真时代已经到来。拟真秩序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1)作为真实本身的沙漠。在拟真模型“帝国主义”统治下,所有的真实及其想象都逐渐消失,被“超真实”遮蔽掉,只剩下模型复活轨道和拟真产生的差异。(2)神圣的非指涉物图像。这就是“自我指涉”的能指符式的拟像,拟像就是真实本身,拟像之外无真实。(3)拉美西斯(Rameses)或玫瑰色式的复活(Rose-Coloured Resurrection),即拟真模型对历史真实的复活(复制)。(4)“超真实”与“想象”。想象的真实、虚拟的真实,拟真秩序下的生活。(5)政治的符咒(Incantation);拟真的政治模式(政治的超真实)。(6)莫比乌斯带(Moebius-Sprialling)的负效应(Negativity)。最典型的就是通过类似一系列“水门事件” (以政治人物的各类丑闻为佐料)的媒介“真实”,一方面维护政治真实性,一方面保证了一种完全的控制(无论什么样的新闻都可以利用作为操控的利器)。(7)真实的策略(Strategy of the Real)。拟真秩序对“真实”的消解(谋杀),悖论性地导致拟真的不可能。因为阴谋已经被揭穿,所以拟真受到“真实”的报复性回应。同时拟真秩序体现的正是真实的资本操控,所呈现的是拟真与真实的交互关系。(8)全景图像的终结(The end of Panopticon)。在日常生活的影像化拟真之后,生活的真实逐渐丧失、意义丧失,这也是拟真的代价。(9)全景系统的终结(The end of panoptic system)。这说的是媒介模型的真实,在媒体的类似真人秀的操作中与模型混淆在一起。(10)轨道和核能(Orbtal and Nuclear)的拟真威慑的真实,永远分泌出一种剩余物的真实效果。核武器“威胁”就是军事拟真表现,既遮蔽了战争,也消除了和平。而且,拟真核武成为军事领域唯一的真实,产生一种真实的安全效应。
所谓“超真实”,“就是一种没有原型和真实性的真实,由一种真实的模塑制造的真实”②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它“比真实还真实”,“真实不再是那个可以再现的东西,而是永远都是已经再现的东西,即超真实的东西”③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1993, p. 73.。在鲍德里亚看来,“超真实”是一个普遍性的现实处境,在这一状态中,再现和真实都被拟像取代,成为没有本原的复制。其主要表征就是符码拟真的不断复制、永远再现。文化的内爆导致保证真实存在的差异性界线消解,真实消失了,超真实就出现了;自然的真实与制造的真实的界线被抹平。鲍德里亚认为,作为一个后现代概念,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的本质概况,超真实不是对真实的背叛,而是指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级真实状况。这一超真实状况在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再生产替代生产,在认识论中拟真替代再现,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模型先在的思维理路。由此,鲍德里亚在某种意义上瓦解了现代性所追求的真观念,为他的后现代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2. 艾柯“超真实”文本描述
(1) 艾柯“超真实”的基本含义
艾柯对“超真实”的关注,很显然是对鲍德里亚提出的“超真实”概念的一个积极回应。艾柯主要是通过“超真实”概念来应对那些文化意义上的特定情境——即复制在先(复制先于真实的原本)。艾柯并没有像鲍德里亚那么激进地强调原本真实的消失,而是主张“超真实”仅仅属于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真实依然存在。艾柯进一步从符号学解释了“超真实”:超真实行为就是对真实的欲望,为了满足那种欲望(对某真实的事物)从而伪造(fabricate)一种可以当作真实来消费的“虚假真实” (a false reality)。①Umberto Eco,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Sand Diego a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86, p. 4.这其实就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变形的对真实的过度欲望。
艾柯的“超真实”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文集《极度现实中的旅行》,他以美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来展开符号学意义上的解读。所谓“超真实”就是美国人想象的实现,从而人为地制造出一种“虚假真实”,即“源于美国人的想象力对真实事物的需要,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为了得到‘真实’,不得不伪造(fabricate)绝对的造假(fake)”②Ibid., p. 8.。
(2) 美国作为“超真实”模板
在进入“疯狂的美国式的超真实”世界后,艾柯发现了一个压缩版的符号(semisis),那是一个类似全息图(hologram)的像似符,已经丧失了指向它们特定对象的所指能力——其实就是没有了指涉物存在。艾柯同鲍德里亚一样,使用全息式的图像计算——这种技术在虚拟真实系统之前是最具有理论弹性的、最合适的——预示了一个梦幻般的三维空间中的美国。艾柯所说的全息图技术(服从于三维视觉领域的一种虚拟图像的透析程序),“仅仅在美国这样一个迷恋于现实主义的国度才可以兴盛发达,在那里如果说重建是可信赖的,那么它必须是完美的图标、一种完美的逼真性、一个被活生生表征的真实性的‘真实’复制(a ‘real’ copy of the reality being represented)”③Ibid., p. 4.。
(3)“超真实”的虚假本质
艾柯强调,他的超真实旅行就是探寻“造假的信仰” (faith in fakes)的秘密。在这个“旅行”中,他发现:美国人想象力所及的地方就是他们对特定真实事物的渴求,即“编造绝对的虚假”;并且,美国“对过去的保存和纪念一定是通过完全的真正复制来实现的”,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造假的天堂。艾柯对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加以发展和推进,他并不认为真实被取代或消除,他关注的是仿真的赝品(imitations)。由于相比那古老而无用的原本,仿制品更新、更完整,因此人们更偏爱它。在某种意义上艾柯的批判性比鲍德里亚更强,他洞见了“绝对的造假” (the Absolute Fake)源于事物那种“没有深度的呈现”真空。在他看来,迪士尼乐园就是“消费意识形态的完美典范” (quintessence of consumer ideology)。艾柯还发现了一种异质的、更现代的文化和态度:“真实的历史仍然存在而且可以触及”,其中就包括“历史的意义就允诺其逃离超真实的诱惑”这一点。
3. 鲍德里亚与艾柯的“超真实”概念比较
二者的“超真实”解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点在于他们都结合了当代西方文化批判背景,以对美国的“超真实”状况为“范例”展开,并且都抓住了“超真实”是绝对“虚假的真实”这一根本。但是,由于彼此视角不同,他们的解读不完全一 样。
第一,“超真实”与“真实”关系的差异性理解定位。鲍德里亚选择的是一种悖论性批判角度,是以象征秩序为真理性参照预设语境,所以是在批判“真实原则”基础上提出“超真实”概念,从数字媒介技术发展角度肯定了“超真实”取代“真实”的必然性。在鲍德里亚看来,“超真实”是一种模型复制的真实(A real without origin or reality),是一种新的真实样态,具有本体论意义;同时,“超真实”系统的同一性决定了其“死亡”的根本特征,它最终将被象征秩序取代。艾柯则不然,他从“大符号”视野的真实维度出发,或者说从生活世界的真实出发,以历史真实为参照系来审视“超真实”,发现“超真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本真的造假” (The authentic fake)①Umberto Eco,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p. 43, p. 44, p. 48.。而且,艾柯注意到超真实对真实的正向互补关系:技术上越来越系统的“超真实”,或者说效果功能上越来越逼真的“制假”,正是源于对应的真实事物的缺失,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对真实的缝合。
艾柯不承认“超真实”对真实的“屏蔽”效果,而将其定位为退一步求其次的“次真实”。艾柯注意到真实与“超真实”之间的良性互补共存性,而不像鲍德里亚的二分思维模型下的“超真实”,不仅遮蔽真实,而且消解、吸收真实,过度夸大了媒介技术的力量,从而产生双重理论煽动效果。第二,两人对“超真实”问题的解决思路不同。艾柯认为“超真实”的暂时的、令人眩晕的虚假效果毕竟不能替代真实本身,一旦真实成为可能,超真实就“黯然失色”。鲍德里亚对“超真实”的解决方案则是,提出高于拟真秩序的“超逻辑”的象征秩序来超越“超真实”。从历史角度看,象征秩序就是前现代社会的缩影;从现实资本价值系统来看,就是超越资本系统的非价值系统。这两方面都具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
第三,两人对“超真实”的解读立场不同。鲍德里亚是从激进批判立场,展开“连环式的”双重批判。首先,鲍德里亚是在级层划界分析中构建“超真实”构架来实现对“真实”的批判,其次,他是对“超真实”本身的象征语境批判,从而构造了纵向上的“超真实”对“真实”的彻底谋杀。相对鲍德里亚这种激进的拟真模型构造,艾柯的“超真实”主要以现实的美国作为文本范式,展开符号学真实语境中的分析批判,揭示了这种“复制的真实”的绝对虚假性,即虚假的极限——过度真实的效果。“超真实”的发展趋势指向真实的历史维度,表明了“超真实”的过度泛滥、淫秽效果,最终导致人们对真实的渴望与真实的回归。
(三)“超真实”概念的界定
1. 关联真实的“超真实”基本内涵
“超真实”与“真实”并不是像鲍德里亚宣称的那样毫无干系。可以说,“超真实”正是针对“原型”真实的消失与不可能性而提出来的。两者的关系是呈“复数”性展开的,这就表明“超真实”不仅是拟真秩序对“真实”完全遮蔽的“全息式”图式,而且,作为“复制的真实”,“超真实”并没有完全脱离“原型”的真实,只不过克服了“真实”的缺陷。比如,最近获得公民权的智能人“索菲娅” (Sophia)虽然能说会道,但是其原型恰恰是好莱坞女星奥黛丽·赫本。为什么不是随便某个人都可以被复制呢?
第一,“超真实”之所以取代真实,主要通过数字化模型的再生产,到处都是“超真实”的存在,真实沦为缺场性存在。超真实在无限再生产性能、数字媒介传播的“时空同步性”超速度以及产品“超功效”的完美无缺等方面以压倒性的优势取代了真实。这种关系是单向关系,也是一场“拟像”符号作为“虚假的代替物”对“真实”的胜利,也就是“完美的谋杀”。“超真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数字技术拟真模型中“制造的真实”取代自然的“生成性真实”,它在功能的完美程度上超过了“真实”,从而达到“比真实还真实”。①“完美的复制改变了原本(复制独特的东西,独特的东西就不再独特,因为这个实体有两个样本;同样,复制的每一个副本的性质也发生变化,虽然变化的程度比较低)。在这个意义上,完美、完全的复制同样是难以实现的、自我拆台的。复制的意图是要捕捉原本的一切品质,包括其独特性;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使原本和复制品两实体都失去了独特性。”引自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参见注释8。
第二,利用数字媒介复制模型,拟像达到“超真实”,产生“隐喻”的比较效应,从而形成模型之外的世界是“真实”的假。隐瞒了整体的“超真实”性,也就意味着“超真实”能够隐秘地产生附加性的“真实”感受。这种符号化模型“真实”隐性置换了自然的、实际的“真实”。
第三,“超真实”中“超”的含义就是“僭越真理性地位”。物质层面功能符号的真实优于“原型”真实本身。“超真实”并不是一般常识所理解的遮蔽了“真实”,而是取代了后者的“中心”真理位置,而把所有的“真实”当作次级的从属性质料进行加工、吸收、改造。就算“真实”语境中的“虚假”也会一样被吸收利用。总之,在拟真阶段,拟像的真假区分已经没有多少意义,既没有区分的可能性,也没有区分的必要性,剩下的是符号的价值与符号的功能。
第四,“超真实”以数量无限性、功能完美性的“重复”繁殖增生淹没了“真实”。面对相同的无数个事物,人们马上陷入“真实”的困境。最终,“超真实”回归“真实”世界本身,就是在那些充满魔力的智能机器被卸载为一堆垃圾的时候,或者说,走到系统之外的时候。①具体事例和分析参见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6—109页。
2. 对“超真实”概念的初步界定
(1) 数字媒介技术实然层面
“超真实”是伴随着视觉图像时代、物质主义统摄下的消费时代、人类欲望能量的无节制释放时代的一种真实的图像“症候”,其本质是数字模型操控的真实。“超真实”是一种愈演愈烈的普遍性既成事实,其中包含着本体意义上技术决定论的哲学态度。“超真实”就是一种“升级”改造版的“真实”,是最新拟真模型的真实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无限的无缝隙数字模型复制性再生产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的真实。
(2) 文化符号学批判应然层面
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化悖论性批判主词,“超真实”是一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状况,而不能不加辨别地任其蔓延。有必要用最新理论的雄辩揭穿“超真实”的幻象性欺骗本质。在此,作为“拟像”最新阶段的“超真实”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媒介真实。随着“拟真”秩序的不断推进,“超真实”的论域不断扩展。一方面,它是生活消费层面符号—物的视觉功能效果的一种特殊的过度状态;另一方面,它是人的精神观念、心理层面的眩晕失重状态。从语言结构符号学谱系来讲,“超真实”就是作为代替物替换原对象(被代替者)的真实,是作为再现者(符号)对被再现物(真实的对象原型)的遮蔽替换以后的真实。“超真实”就是结构符号对真实的僭越,以及能指符对所指的僭越,或者说是一种消解了“指涉物”的脱离真实的真实。
(3) 哲学反思层面
“超真实”属于古老的“真实”家族谱系。“超真实”并不是“真实”的绝对“反对者”,而是一种新的真实——模型复制的真实,是一种以各种真实形态作为基质的对“真实”概念的超越,是一种哲学环节上的升级版真实,是对后现代资本主义操控的现实世界图景的最新概括。“超真实”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批判现代性真实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去真实”“去真理”,是关于“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拟像的真实(拟像真理),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真实,是“谎言重复上千次就成为真理”古语的“兑现”。其之所以升级为真实,就在于完美的媒介复制技术可以任意重复再生产任何符号—物。以上述艾柯的观点看,这种复制的真实就是“造假的真实”。
3.“超真实”的真实谜底
作为复制的“超真实”也只有在“真实”的语境下才是有意义的,没有“真实”的依托,“超真实”只能是局部性的对“真实”“缺失性存在”的一种替补,而不仅仅是一种“恶”的增补。一种人工“拟真模型”产品,必须遵循价值最大化原则,最终仍然从属于“真实”原则,拟真和真实在此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性关系。比如,近期人工智能人的话题喧嚣一时,人类似乎成了“过时产品”。但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惯用的“控制术”,在消费社会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超真实”震慑——人不是人,现在进入“后人时代”,出现了比人还像人的存在——人工智能人或超人类。其背后的隐喻就是:仅仅有人类是不够的,我们的欲望需要人工智能来满足,于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将是一个新的物种——比如“索菲娅”。
三、结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本文面临重要的理论问题是:究竟何为真实?真实与超真实是怎样的关系?鲍德里亚在继承其前辈尤其是尼采等人的基础上提出:真实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构造,甚至是假设——科学理性的神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当下的拟真时代,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的二分逐渐被真实的新形态所取代。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超真实的现实处境?
拟真时代符码媒介数字精心制造出来的“超真实”也是一个超级版神话。因为无论打开哪个“超真实”存在的门——其实里面已经空空如也(void),超真实都不过是一个超级版的幻象而已。人不可能永远待在“迪士尼乐园”,他必须走出模型。①当下网瘾严重的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真实的破坏性后果,就是高度依赖于模型真实的一种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有无真实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真实。不能孤注一掷地“执著于”形而上学的概念或实体性真实,要纠正的是真实的过度,而不是消除真实,某种意义上后现代话语中的“超真实”正是为了拯救真 实。
鲍德里亚构建的符号学解构话语得出真实原则似乎已经过时,我们已经进入比真实更高的级层——拟真时代的超真实状态。但是,在本文看来,这仅仅是一种“顺势疗法”式的解决,“超真实”原则可能最终也难逃被最新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收编的宿命。“超真实”对“真实”的侵染、遮蔽的暴力能量,在激进的“超真实”批判话语的不断拟像化播撒中,变得“超”钝化,大众对“超真实”的过度也习以为常。鲍德里亚作为一个少有的体系之外的边缘性跨界思想家,之所以在媒介时代产生超真实的“鲍德里亚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源于拟真秩序。比如,他竟然成为影视界、艺术界的“教父”,《黑客帝国》的产生以及影片开始的视频图像就是鲍德里亚的著作《拟像与拟真》。鲍德里亚深刻地回答了时代的最新状况,但是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药方。真正的现代性危机、学理上的“真实”再现危机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得到了一种理论上的暂时性遮蔽。任何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并不会因为被宣布过时就自动消失。
总之,“真实”是一个绝对的他性问题,也是一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永恒哲学主题。在高度不确定的本真生存域中,人类无法承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痛苦,我们总是需要设定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作为“真实”的确定性幻象支撑。①参见尚杰:《确定性的丧失——20世纪新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第1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