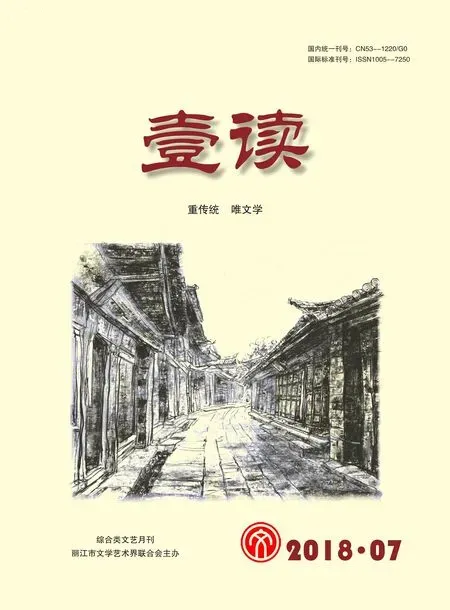那时雨天
杨艳川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在等待一场雨。
一场瘦雨,亲切悠然,润物无声。
一场肥雨,轰轰烈烈,酣畅淋漓。
我总能躲在一个角落里,品味一场瘦雨的温柔,记住一场肥雨的凶煞。有雨的时光是曼妙的,有雨的日子是美好的,有雨的故乡更加美好。
故乡的雨,因为稀少,所以弥足珍贵。大家太需要一场让庄稼茁壮成长的雨。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盼望着,雨,在六七月份终于来了。
雨来了,大家也不会整天窝在家里,除了小孩,大人照例忙碌,他们戴上斗笠,披上油布,扛上锄头,匆匆走出家门,像一名出征的战士,一头扎进雨中,他们迫不及待地赶在前头,生怕积在河里沟里的雨水,被别人抢先占去。他们希望把更多的雨水引到自家的田地了,他们生怕雨脾气大,说走就走。干渴的田地太需要雨水的浸泡了,干渴的庄稼太需要雨水的滋养了。所以他们要亲眼看着田地被泡透,才安心。
季节的深处,雨成了家常便饭。一连下几天雨,父母又开始担心围墙被淹、猪圈被淹。墙基矮,土酥,如果雨水大一些,排不走,就可能漫上来。雨一直下,他们就睡不着,有时半夜冒着大雨,出来清理路边的沟道,淤堵的地方通畅了,他们才回来,然后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
另一个揪心的地方是田。我家有一块田,就在河道拐弯处,是河水改道后,生产队平整出来的。一连几天的雨,此时再没有人去围水泡田。滚滚的河水咆哮着,在河道里横冲直闯,发泄着所有的不满,我家的田刚好挡住了它直行的脚步,深一口浅一口,肆意撕咬着。好几年,差一点就将河岸冲毁,危及田地。如若大水从我家的田地里漫进去,在我家里面的一大片田地,必将一起被毁坏吞噬。所以父母只好扛去包谷杆,一层层培上土,压上沙袋,他们经常在半腰深的河水里,垒河埂。以至于在多年后的今天,天气稍微变化,他们风湿病便复发,疼得难以走路。是父母用他们渺小的身躯,一次次、一年年阻止了河水的阴谋,换来每年两三千斤粮食的收成,让全家人不至于挨饿。
也许是河水被父母的坚持镇住了,妥协了,也许是上天被父母的精神打动了,改主意了,河水一年比一年小,无可奈何地慢慢从另一处流去。
父亲曾跟我讲过,为了引水泡地,双方发生争执,亲朋好友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杀人,都出现过。因为老天不下雨,大旱的年成,关键的那几天泡不上水,包谷开不了花,谷子结不了穗,就影响一季的收成。地少人多,微薄的收成关系到一家人的生计,温饱尚未解决的时候,谁也不可能让谁。退让就是懦弱的表现,与善良与否,与道德无关。
而我,从小是喜欢雨的,我喜欢在细雨里奔跑,或是漫步,或是穿着拖鞋在水洼踩水玩。可是父母总担心我被雨水淋病,每一次出门都非得让我带上雨具不可,家里没有伞,就让我戴上斗笠,或是披上油布,我坚决不肯,还在母亲反复叮咛的时候,一溜烟跑向学校了。虚荣心占领上风,我总是觉得我家的东西太土,会被同学们笑话,因为好多同学打着雨伞,穿着雨鞋上学,而我戴一顶斗笠,披油布,想着这样的场景就扎心。
故乡人常叮嘱孩子说“晴带雨伞,饱带干粮”,每次还未等母亲唠叨完,便被我毫不留情地剪断,不耐烦地离去。孩子与大人的世界,永远隔着一道沟,当你懂得父母那番苦心的时候,你已经长大,不再是孩子了。
遇上大雨,母亲就会把雨具送到学校,她站在教室窗子下面,等着我下课,然后把一把大伞塞在我的手里。之后顶着一块油布走了,我远远地听到雨滴落在油布上的脆响。其实我打心里不喜欢母亲给我送大黑伞。那时大部分同学已在用折叠伞,我用大黑伞,依旧还是土,还是会被笑话。
雨,带给我屈辱、倔强和叛逆。
雨年复一年,遵守时节,按部就班地下着。到外求学找工作,我离家越来越远。头顶的蓝天,与故乡的天空,已经不同。每一场雨,都落在思乡的土壤上;每一滴雨,都打在我柔软的心坎。
多年后的今天,到了子欲孝的年龄,我却不能守候在他们身边,不能时常陪伴父母,白天陪他们晒晒太阳,看看电视,晚上在他们熟睡时掖一掖被子,生病的时候端上一碗汤药。阴雨来时,我想象着落在头顶上的那滴雨,是来自故乡母亲的问候和诉说,父亲的牵挂和期盼。
总是怀念丽江,怀念丽江的雨。丽江的雨,是惊醒的孩子,是复活的阳光,是琴弦上的余音,袅袅回旋,轻起慢落,跌进脚步里,跌进人的心里,柔情而暧昧。
总盼望着自己的伞下,多出一个曼妙的女子。
一场带着故事的雨,剪不断理还乱。
而我,打着一把蓝色的伞,在石板路上,走得很慢很慢,我想尽力去倾听雨水的声响,尽力去倾听雨水的每一句抒情,然后标注,整理成诗。
走过古城,走过龙潭,又走过清溪水库,雨穷处,彩虹升起。
唯美的年华,守候唯美;恰当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两个情投意合的人,转角相遇,一起走,一起爬山,一起看花,一起赏月,一起过桥,一起听雨。不分彼此,一起走过一段路,转角又匆匆离开。幸或不幸。
丽江,因雨而多情,因多情而难舍,因难舍而怀念。
最初工作的地方,是一所山村小学,位于崇山峻岭之中。
一下雨,漫山遍野都是雾,花草树木,鸡猪牛羊,房屋院子,宛如浸泡在柔软的牛奶里,朦朦胧胧,舒畅而惬意。
雨一下,便是好几天,不紧不慢地从空中落下来,然后又不紧不慢地滴在山坡上,渗到土壤里。老师和学生都被困在学校,难以出校门,外面全是土路,一走便弄得全是泥,万一滑倒,更惨。
长时间的雨,让人坐立不安。孩子们找不到柴生火做饭。他们大多离家很远,平日里回不了家。也许很多人无法想象,二三年级的孩子,带着念学前班的弟弟妹妹,住校,自己做饭吃,每顿就吃荞粑粑和洋芋。
我无法用语言来定义雨的美好,同样无法用语言来定义人生的得失。不经意间,我想到的是困境、苦难、磨砺、坚强、勇敢等词汇。
不可否认,边远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就是山里人勇于走出大山的拼搏奋斗史。雨水喂养的山川河流、高山土地,从来就不缺苦难,苦难不是让人强大,就是让人消亡。
几年后,走出万格梁子的我,当听说通了电,能看电视,我彻夜未眠,写下了一篇《山村的眼睛亮了》的通讯;当听说有学生考入县城学校读书,我由衷的高兴;当听说有学生高考考出全市最高分,我激动了好一阵,与一群老师举杯庆贺。在千里彝山,实属不易。逆境出人才,逆境出的人才更为难能可贵。
我想,恶劣的自然环境,终究是囚困不住人的,山里人的骨子里,天生就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和品格。有人的存在,希望之灯就不灭。
雨,是长在时光长绳上的一个结,轻易无法解开。
在一个暴雨如注的黄昏,父亲骤然离我而去,没能最后说上一句话。当我冒雨赶回家时,已是深夜,父亲已入殓,静静地如熟睡一般。一场苦雨,让我刻骨铭心,让我的心生疼,让我想了很多很多。先前的恐惧和担忧,在那个平凡的傍晚得以应验。我反复在脑海中,书写父亲的履历,在我们三十年的交集里,各种喜怒哀乐,点点滴滴,印在我的心里。父亲全身心地教育我,培养我,我是他的传记,我是他精心塑造的版本。
夜雨戚戚,下到深处,肝肠寸断。
父亲这个词汇,搁在心里,硬如石头。三十年的光阴,三十年的陪伴,无法言表。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竟无法写下只言片语,多少个清晨,心潮澎湃,当铺开白纸,提笔后,脑海却骤然变得如纸一样空白。我的身体被掏空,空如皮囊,我为自己稀松的陪伴羞愧不已。我不知道,他坟前的那块石头,是不是整天守候陪伴;他坟旁的那株橄榄树,是否长大,是否在寂寥的时候跟他说说话。如果我是一滴雨,我会落在父亲干裂的唇上,去滋润他嘴里的每一句话。
我一直不敢换掉号码,不敢关机,生怕父亲想到我,梦到我的时候,电话接不通。关于父亲的一切,都是沉甸甸的,梦乡成了我们唯一的通道,枕边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我不知道父亲在那个世界有没有悲欢离合,有没有病痛和苦难纠缠,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跟我说,千万不要独自承担,说出来便会好一些。
因为想念,我一次次地往回走,去亲近故乡,亲近父亲。
走在父亲千百次带我走的田埂上,看村庄,看水井,看庄稼地,看一株谷穗,看一只蜜蜂忙碌和飞舞……
田畴无言,却又千言万语,深邃浑厚。这里有父亲的烙印,他的灵魂以另一种姿态存活于大地。
雨,有时可以给心灵慰藉。内心阴霾的时候,在阳光里也能看到雨;内心晴朗的时候,在雨里也能看到阳光弥漫。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静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会了听雨。
静夜听雨,又是一番滋味,那是一支奇妙的曲子,时而舔食心灵,时而激发诗意。时光的藤蔓爬着光阴的故事,讲述、聆听,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境地。
每一次雨的洗礼,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重塑。
也许明天醒来,阳光明媚,万物笑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