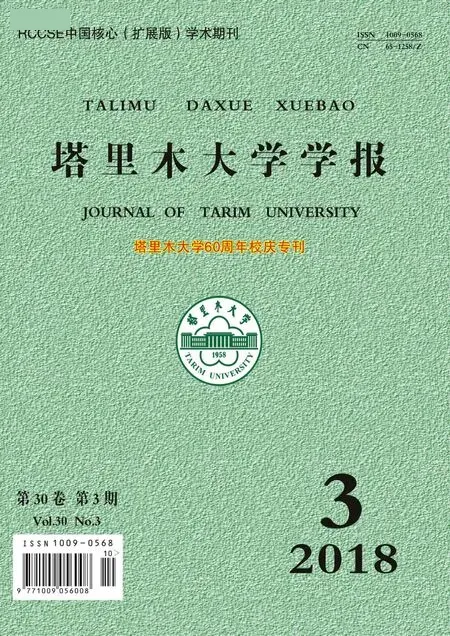汉兴三《论》原始考异
胡 鸣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汉兴三《古》、《齐》、《鲁》的差异,是横亘在《论语》溯源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此问题是否得以合理解决,则关系今本《论语》之定性,以及汉兴之前《论语》基本面貌的确立。此是《论语》溯源研究的难题,又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1 汉兴三《论》说缘起
汉兴三《论》说始见于班固《汉书》,《汉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6页。其中班固自注云,“《古论》,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论》,多《问王》、《知道》。”由此可知,言三《论》者,并非始自班固,班固只是注者。
康有为认为,《汉志》三《论》说可追溯至刘向。其理据是,《汉书》全用刘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就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3页。。此说固可异议,但《汉志》本之刘歆《七略》,而《七略》本之刘向《别录》,《汉志》却有所叙及。[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因而,三《论》说本之于刘向应有其根据。
刘向一生主要贡献在于校中秘书,其生活在《齐》、《鲁》名家辈出的宣、元、成时期,尤其历经石渠阁会议评议五经及《论语》异同,熟知《论语》状况,故其对汉兴《论语》分为三类,并非毫无根据。况且,其不象张禹那样整合文本,而只是从目录学意义上“条其篇目”,分门别类,记录早期《论语》诸本区别,尤为客观可信。因而,从校雠意义上而言,以汉兴三《论》说源自刘向,尽情合理。此分类,出自刘向于中秘所编《别录》。而刘向入主中秘,在成帝河平四年(前25)。故以此为追溯汉兴三《论》之起点,往前追溯三《论》形成于何时,及汉兴之时《论语》究竟有几家。
刘向之前,未见三《论》之说,并不意味三《论》不存在。据《汉志》可知,在刘向入主中秘之前,三《论》俱已形成。传《鲁论》者,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六家。依此,《鲁论》形成,可由张禹溯至夏侯胜。夏侯胜奉诏作《论语说》,在宣帝元康二年(前64),此为开汉太子习《鲁》传统的奠基之作。再往前则为龚奋,史书无传,未知其详。传《齐论》者,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五家,惟王吉名家,其成名于宣帝年代。皇侃以琅琊王卿为传《齐论》先行者,然未云其传授年代。惟《古论》出自孔壁,有年代记载。而最初今读《古论》的孔安国,其献孔壁古文则元光五年(前130)。由此可知,三《论》出,年代不一,似以《古论》为最早。至于《齐》、《鲁》,虽然分别有王卿、龚奋传授之说,终因龚奋、王卿传授年代不明而难定。但从《论语》之名形成看,则可断其大致年代。
今所知早期《论语》之名有六例,金德建以为,《史记》中“论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两例,即《论语》之名[注]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05页。,《韩诗外传》引文冠以《论语》之名者三例,《礼记·坊记》一例。《坊记》一例,尽管周予同认为“具有史料价值”[注]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但毕竟是孤证。明朱睦《五经稽疑》因其与句首“孔子曰”相矛盾,以其为汉注孱入,故存疑。而《史记》征引《论语》章节一百三十九例,或书随人名,尊之以“孔子曰”、“仲尼曰”、“圣人曰”,或冠之以“传曰”,以示其书性质,是解经之传,但未见一例冠之以《论语》之名。《韩诗外传》亦多如此。引例称谓或为“孔子曰”,或为“传曰”,可见,至司马迁之时,《论语》之名并未定说。但可确定,已有《论语》之名,此为《韩诗外传》三例可证。
问题在于,韩婴所引据《论语》属性难定。从引例有“不知命”章看,此章本属《古论》,文献未载今文《论语》有此章。而韩婴三传至王吉,王吉为《齐论》名家,此是否意味《齐论》可追溯至韩婴。若如此,韩婴生活年代早于王卿,王卿为御史大夫尚在孔安国献书后三十年的天汉元年(前100),此是否意味《齐论》形成年代尚可提前。巧合的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与韩婴论争的董仲舒,于天人对策中亦引“不知命”章,董仲舒作为汉兴齐学的先驱人物,是否可佐证此时《齐论》已形成。若如此,则出现“不知命”章属《齐》抑或属《古》之疑问。若二书皆有此章,则意味《齐》、《古》二者在二十篇之外存在一致性之可能。若二书相沿袭,《齐论》乃汉兴后以今文面目复出,而《古论》则保留汉前古文面貌,以此而言,《齐》相沿《古》的可能性大。若依王充所言推之,《齐论》晚至昭帝后,出自今读二十一篇之《古》。若如此,从孔壁发现《古论》至刘向定名,三《论》形成,历经由一而三的漫长过程。
2 汉兴三《论》的分类依据
若三《论》形成是由一而三,那么,以何为据界分三《论》。《汉志》以《论语》为总名,以《论》为简称,分别在《论》前冠以不同称谓,作为判别标志。以此表明《论语》类分为三,但未说明分类依据。
对此分类,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云:“寻当昔撰录之时,岂有三本之别,将是编简缺落、口传不同耳。故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壁所得,谓之《古论》。”[注]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依此可知,三《论》划分,依据有二:一是今、古文,另一是地域学派。
以今、古文为依据划分,看似明晰,实则存在难辨今、古《论》之分。因为,在孔安国今读《古论》之后,《古论》实是以今文形态传承,此从鲁扶卿为《鲁》名家推之,其所传孔安国《古论》当为今读本。更为显明的是,汉至许慎,已不辨古文,甚至不知古文为战国东方六国文字。而郑玄本,名为《古论》,实非古文所书,此从其以《古》校“周之本”,二者异文仅“五十事”,此意味今、古《论》文字,几无差别。可见,以今、古文为分类依据,只适用于分辨汉兴复出时文本,不适于分辨其后流传中的文本,否则出现同一《古论》,有今、古文之分。为以别于其他今文学派,刘向故以“合壁所得”特指,谓之《古论》。刘向如是界定,实质在于表明《古论》仅指孔壁一家学派,而不论其今古文书写形态。同样,以地域学派为分类依据,实质亦不是以地域分类,而是以学派划分。以地域冠名,仅仅标示学派初兴地及流行地,而不论传者籍贯,否则,难以解释同一学派有不同地域籍贯的名家。以此观之,三《论》分类,遵循一个原则,即以学派分类为依据。
从汉代其他诸经分类看,同样如此。既有经本复出属地之分,如《诗》有齐、鲁、韩;亦有传承系统之分,如《书》有大、小夏侯、欧阳,此实质同《论语》,皆以学派分类。而诸经学派分类诸多,汉兴《论语》仅为三,是否穷尽其派别分类。翟灏则以为,《论语》尚有别本存在,而未列全,其《四书考异》云:“按汉时通谓《论语》为《传》,《燕传》犹言《燕论语》,故刘氏录《论语》类也。”[注]翟灏:《四书考异》,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3页。王充《论衡》则从《论语》形成过程,否定汉兴复出时有三《论》。其云:“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二篇。至昭帝始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少或多,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谶纬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注]王充:《论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9页。王充此说,比之翟灏说,更为直接否定汉兴三《论》说。其要有三:一是初始《论语》数十百篇,只是汉兴失亡;二是汉兴《论语》复出,非一处,而是多处;三是至昭帝始读二十一篇,而后隶写以传诵。依此可知,王充是就《论语》形成过程中的分合而言,故以为汉兴《论语》不囿于三《论》。刘向则就《论语》传本归属分类而言,并未抹去同类中各家差异。如,盍、毛、包、周诸本,同属《张侯论》,但各有异,此为熹平石经所确证。由此可知,刘向分类,最根本的是以学派为依据,循其所出师法家法而分类。因而,其分类不致不穷尽,至少对主流学派的分类,不致不穷尽。
由此可见,王充与刘向观点并不矛盾,甚至可互补。若依王充观点,《齐》、《鲁》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至昭帝,始读二十一篇,及宣帝,更隶写以传诵。若如此,不仅王吉、夏侯胜是《齐》、《鲁》形成的标志,而且王吉、夏侯胜传本皆出昭帝始读的二十一篇。从“书难晓”而“隶写以传诵”推之,此书无疑是《古论》。那么,《古论》形成早于《齐论》、《鲁论》形成。
3 汉兴三《论》的起始年代
在未能实证《齐》、《鲁》形成早于《古论》之前,姑以《古论》为汉兴《论语》复出的起始年代。问题在于,《汉书》记载孔壁《古论》复出年代有误,以致出现质疑是否真有孔壁古文之事。
《汉志》记载复得孔壁古文有二处,其一:
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注]见《汉书》,第1706页。
其二,《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
至孝武帝 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於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壊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閔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於全经,固已逺矣。及鲁恭王壊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注]见《汉书》,第1969页。
同时代的王充,[注]王充(27—约97),会稽上虞人。《汉书》王充本传云:“充好论説,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絶庆弔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以此观之,他著《论衡》当于罢州还家之后,《论衡·自纪篇》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絶,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齿落,日月踰迈,儔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厯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但《讲瑞篇》却云:“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也即王充三十岁左右,二者相差三十余年。据此,钟肇鹏《王充年谱》认为:“《论衡》大部分成于建初之年,然最后定稿,直至章和之时,全书创作将近三十年”。而班固接续其父之业,在建武末,完成《汉书》于章帝建初七年(82)可见,王充《论衡》与班固《汉书》著述年代相差不远,其所载资料可相互印证。据《汉书》本传,王充曾“师事班彪”因而,其学与班固同源。其《论衡》记载亦有二。其《案书篇》年代记载同《汉书》。而《正说篇》则云:
孝景帝时,鲁共王壊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见。[注]见王充《论衡》,第1125页。
从两书记载上看,《汉书》记载有二说。一说在“武帝末”。另一说未明言,但从其行文推之,若孔壁古文发现在汉武帝诏书感叹“书缺简脱”之后,则亦为“武帝末”。而王充《论衡》对此发现年代亦不确定,故或在武帝,或在景帝。此表明,班固、王充时代,乃至刘氏父子时代已不知发现孔壁古文的确切时间。康有为正是从否定发现年代着手,达到否定孔壁古文事件,从而认定其事为刘歆伪造。
康有为认为,鲁恭王发现孔壁古文年代为“武帝末”与鲁恭王卒年的记载相矛盾。《汉书》景十三王本传与武帝纪皆记载鲁恭王卒年在武帝初,因而,发现孔壁古文不可能发生武帝末年。即使“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确有其事,但未见得与发现孔壁古文有关。因为发现古文是经学上重大事件,并且其事发生在景帝末,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记载。况且此年代记载的严重冲突,实际上关涉到事件本身的有无及古经真伪诸重大问题。故康有为以此为起始证据,以振聋发聩的十伪之证,步步推论刘歆以编造孔壁古文“伪撰古经”系统。[注]如,《汉书》记载鲁恭王发现孔壁古文在“武帝末”与鲁恭王在位二十八年而死的“武帝初”相矛盾,孔安国献书在“巫盅事件”之后与孔安国蚤卒相矛盾,《汉书》记载与《史记》未载相矛盾等诸如此类二难问题。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570页。
如果转换视角,不是从事件年代记载,而是从事件本身记载上看,则有可能推出孔壁古文发现的确切年代。不论《汉书》还是《论衡》,对事件本身的记载却是完全一致,均认为是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诸经。那么,从鲁恭王卒年记载可推算出发现孔壁古文的大致年代。如康有为所论证,《汉书》武帝纪记载“鲁王馀、长沙王皆薨”的年代,与《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年代相合。据此,鲁恭王立于景帝前二年(前156),卒于在位二十八年,即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纪传记载完全相合。而《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与《史记》五宗世家记载亦大致相合。《五宗世家》云:“鲁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辨,为人吃,二十六年卒。”[注]《史记》,第3125页。若将鲁恭王卒年定位在元朔之年,按《汉书》在位二十八年计,即其鲁恭王立于景帝征继位的第二年,按《史记》在位二十六年计,则立位于景帝前三年。可见,鲁恭王卒于汉武帝继位后十余年可确定。故他发现孔壁古文的年代不是武帝末,而应提前至武帝初至景帝初期间。以《史记》记载,事件发生在“孝景前三年”较为切实。王充《正说篇》记载合乎此年代,故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王充《正说篇》为是。
再则,从事件本身上看,不可能出于刘歆的伪作。比较《汉书》与《史记》可知,《汉书》将鲁恭王好治宫室与发现孔壁古文合为一事,《史记》则分为二事。有关《史记》古文说的记载,王国维分疏十分详细。如,其认为,《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即为“其家室有此种旧籍也”;撰史记依据之古文,有秦石室金匮之书,有汉中秘非当时写本,有孔氏所传旧籍,但对本传司马迁得古文经之事,王氏避而未答。从《汉书》上看,来源主要有河间献王与鲁恭王,但《史记》却无河间献王得书,鲁恭王坏壁之记载,唯有同样含混的孔安国得书之记载。《史记》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此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注]王国维认为,此数语,自来读者多失其解。王念孙《读书杂志》用其子伯申氏之说,认为当读“因此起其家”为句,意在古文家法自孔氏兴起。康有为认为:“因以起其家《逸书》”为句,意在孔安国因之得逸书之事。二者强调重心不同,却都言及孔氏得书之事,此逸书显然指新发现之书,可作为《汉书》发现孔壁古文的旁证。如果将此逸书视为《汉书》所载鲁恭王坏孔宅所发现之书,那么,孔安国及司马迁所得之书就有出处了。因为司马迁曾一度师事孔安国,所选择的自然是孔氏所长的古文经籍。况且,刘向《别录》已明确指出“孔壁所出,谓之《古论》”。由此而言。王念孙认为古文家法自孔氏兴起不无道理。
实际上,王充所叙宣帝之前的《论语》演变状况,尤其对《古论》溯源具有重要意义的“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的记载,与《汉志》传《鲁论》名家“鲁人扶卿”的相接,使《古论》流传脉络得以畅通。因为从孔安国、鲁扶卿、刘氏父子、班氏父子直至马融,他们生活年代环环相扣,他们都是《古论》的见证人,使《古论》从发现到东汉末一百五十年间的存在变得真实可信。因而,相对《论语》其它传本而言,《古论》真实地再现了原本的基本面貌。
4 汉兴三《论》主体的一致性
汉兴三《论》从《古论》发现后,终汉之际却未出现三家鼎立的局面。但却呈现清晰的演变轨迹,即从《古论》始,一而三《论》,至《鲁论》终,三《论》而一,实现此一转变的节点无疑是《张侯论》,但促使此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何在?
以往多归因于张禹糅合《齐》、《鲁》所致。在实证并立于熹平石经中《张侯论》与《鲁论》几无差异且篇章完全一致后,则发现根本原因不在于认为糅合,而在于汉兴三《论》主体内在一致性的驱动。理据有二:
其一,张禹的崛起,不在其一人之力,而在于诸家合力。因为,糅合三《论》,不始于张禹,而始于《古论》学者。孔安国今读《古论》后,分殊为二:入门弟子鲁扶卿与再传弟子庸谭分别以《古论》糅合《鲁》、《齐》,皆成名家。从而,《鲁论》中流淌着鲁扶卿《古论》,《齐论》中流淌着庸谭《古论》。而孔安国原本则在宫中默默无闻,被何晏认为“世所不传”。直至马融在发现而重新面世,最后由郑玄以之与“周之本”合。再则,《齐论》内部出现二次糅合,先是张禹糅合庸谭本与王吉本,后为王骏糅合王吉本与《鲁论》。最后,方是张禹糅合《齐》、《鲁》。在诸多糅合中,最为重要的是,《鲁论》的先期糅合。萧望之于石渠阁会议平议大、小夏侯异同,确立了大夏侯本的根本地位,此成为张禹最后糅合诸家的根本依据
其二,张禹的成功,不在于其糅合,而在其以《鲁论》为本,存同去异。实际上,三《论》分别糅合,在张禹之前,业已完成。张禹所实施,与其说是糅合,不如说是取舍。如在《鲁》、《齐》中凡有鲁扶卿、庸谭《古论》经文的,凡同大夏侯本,皆存之。同样,《齐论》四次糅合,尤其后二次糅合,《鲁论》成为存同的集聚点,《齐论》溢出篇章,即使不为张禹所裁减,亦会为王骏所裁减。王骏《论语》二十篇之事实,证明这一推测的成立。可见,张禹之糅合,只是将诸家整合之精华内聚在《鲁论》上。故而至张禹出,一家独尊,风行于汉世,《齐》、《鲁》诸家皆式微。[注]见《汉书》,第3 352页。
可见,三《论》归《鲁》,并非张禹主观意愿所为,而是汉兴三《论》本体一致的内在规定性所致。如果撇开三《论》门户之洞见,就文本而论,三《论》差别只是在篇章、篇次及异文上。而此异文不过是文的增损和字的假借及今古不同,并未影响到文本的整体一致性。从根本上说,此差异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由于长达二、三十年的“挟书律”造成《论语》传承的中断,另一方面由于统一文字带来的六国文字的亡佚,拉开了今、古文的差距。在汉兴后,还原先汉《论语》面貌,仅就隶写再现古文《论语》,就存在着不同书写文字系统转换的技术性难题,何况凭着口耳相传的追记,难免诸家间差异,惟凭三《论》本体一致性的内在要求,促使诸家合力整合,方能存同去异,张禹的整合只是顺应了这种内在要求的趋势,以致《鲁论》有如此强盛永久的生命力。
汉兴《论语》正是以《古论》为内在尺度,以《鲁论》为表现形式下获得相对的统一。此统一文本既成为此后二千余年《论语》传本的宗本,也成为追溯先秦结集初本可靠的起点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