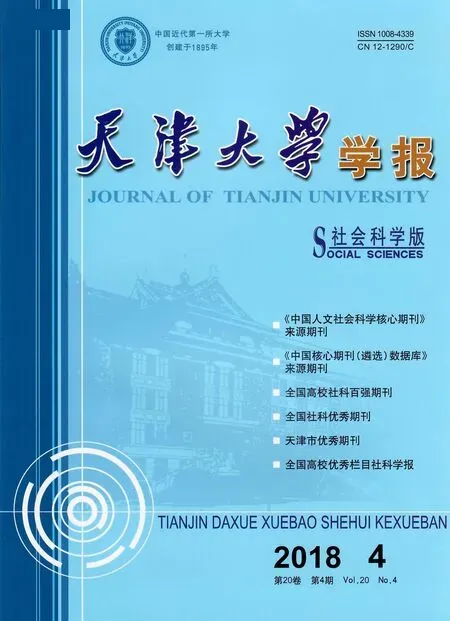日本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及其启示
张建伟, 赵向华
(1. 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72;2. 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安阳455000)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写进政治报告以来,生态文明一词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由此可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必将成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在稳步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惑和问题。从过去成功经验的角度来讲,通过适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省去一些本来并不必要的试错环节,因而可大大节约改革的成本。就我国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而言,日本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经验应该是值得借鉴的,因为毕竟日本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内走出公害的阴霾、甩掉公害大国的帽子[2],其科学且高效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功不可没。
一、 日本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概述
1. 日本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日本国家层面的环境行政机关发端于1970年内阁府设立的公害对策本部[3]。1971年,内阁在公害对策本部的基础上设立了环境厅(2001年,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此后该机构一直在国家层面承担着生态环境监管的核心职能。如今,环境省除单独就废弃物对策、公害管理、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等进行监管外,还与内阁其他省府一同,在地球温暖化对策、臭氧层保护、循环利用和防止海洋污染等领域采取监管措施[4]。
环境省在日本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的功能。根据《环境省设置法》,环境省的主管事务主要涉及与下列事项相关的全国性政策、标准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环境保护基本政策;与环境保护基本政策相关的全国性国土利用规划;以防止公害为目的的管理活动;特定有害废弃物等的输入、输出、搬运、处理等相关事项;保护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保存、野生鸟兽的保护和管理以及适当狩猎和确保生物多样性;控制废弃物的排放、废弃物的适当处理以及清扫等。
除了环境省外,在日本国家层面的环境行政中,还有农林水产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以及国土交通省等多达十几个内阁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生态环境进行监管。例如农林水产省不仅承担着制定和监督执行环境保护型农业政策的职责,而且对与畜牧生产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及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等进行监管;外务省则负责制定并执行与全球环境相关的外交政策[5]。
2. 日本地方层面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1) 地方自治体的生态环境监管职能。实践表明,相对于国家而言,日本地方自治体一直走在公害治理的最前线[6]。这样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日本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地方自治体在生态环境监管实践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地方自治法》规定,地方自治体的主管事务分为自治事务和法定受托事务。具体到生态环境领域,哪些事务属于地方自治体的自治事务,哪些事务属于其法定受托事务,是由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例如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地方自治体的法定受托事务限于总量管理标准的制定、常态化的监视以及制定监测计划这3项,而自治事务则涉及制定总量削减计划和总量管理标准的公示等26项。
(2) 地方自治体与环境省的关系。日本地方自治体都设有专门的环保行政机构,承担着生态环境执法和监管职能。由于在《地方自治法》之下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所以地方自治体在生态环境监管领域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环境省才可依据《地方自治法》对地方自治体的生态环境监管行为进行干预。具体而言,对于环境省和地方自治体均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事务,如果环境大臣认为地方自治体对该事务的处理违反法令,或者其处理明显不当且明显侵害公共利益,则可对地方自治体的处理进行干预。具体干预措施包括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提供资料、要求改正、进行协商、代替执行等。根据《地方自治法》规定,地方自治体应当遵守环境大臣的合法干预。例如,在环境大臣要求地方自治体改正违法行为或者采取必要的改善措施的情形下,后者有服从的义务。《地方自治法》规定了环境大臣的诉权,以司法介入的形式来保障上述干预措施效果的落实。具体来说,对于地方自治体在生态环境领域内的违法行为(包括怠于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的行为),环境大臣可要求或进而命令其改正,在该命令未得到服从的情形下,环境大臣可以向有管辖权的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地方自治体执行相关命令。
(3) 地方自治体对污染企业的监管。地方自治体生态环境监管实践中的一大特色是与排污企业签订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公害防治协定的实践始于1964年时任横滨市长与电源开发公司之间围绕防治公害事项而进行的书面交涉。其交涉的成果是,后者对于前者提出的一系列与防治公害相关的要求(如烟囱的高度、燃料的选择、现场检查等)予以明确接受。此后,这种在协商的基础上约定排污企业防治公害具体义务的做法获得广泛运用,并成为地方自治体对排污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监管的直接依据[7]。
二、 日本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特征评析
1. 环境省的综合协调能力获得有力保障
从性质上看,日本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环境省统一规划、统一协调下的多部门合作监管体制。在这一体制中,环境省相对于内阁其他部门而言居于“优越地位”。环境省的这种“优越地位”,获得了《环境省设置法》的有力保障。一方面,该法规定:在环境大臣认为为推进环境保护基本政策的实施而有特殊必要的情形下,可就环境保护基本政策相关事项向内阁相关部门的长官提出建议,并可要求其就根据该建议所采取的措施进行汇报。另一方面,环境省负责协调内阁相关部门的环境保护事务,有权调整相关部门在地球环境保护、防止公害、保护和建设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经费预算,有权调整与这些事务相关的内阁各相关部门所属试验研究机关的经费分配,以及调整内阁相关部门的试验研究委托经费的分配。
在以环境省为核心的多部门合作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下,环境省相对于内阁其他部门的“优越地位”保证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下的综合性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推行全国性的环境政策和标准。在《环境省设置法》建立的建议、报告、调整经费预算和调整经费分配等制度下,环境省获得了一根具有魔力的指挥棒,可及时调整内阁相关部门在其管辖的生态环境事务上的前进方向,使其不致因部门利益驱使而过度偏离全国性的环境规划、政策和标准。
2. 有效的干预机制促使地方自治体积极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
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与地方政府或其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呈正相关的关系。日本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成效就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自治体的积极行动。日本地方自治体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性既得益于长期以来的公害治理传统,更离不开《地方自治法》建立的干预制度这一制度根源。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地方自治体可以清楚地预见在何种情况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不作为会受到环境省的干预并深知此种干预的法律后果,可以说,正是这种依法构建起来的具有可预见性的干预制度成为地方自治体在生态环境监管方面发挥积极性的重要外部动力之一。
3. 基于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的灵活监管
在日本的生态环境监管实践中,公害防治条例/环境保护条例和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代表了不同的监管模式。由地方自治体单方制定的公害防治条例/环境保护条例体现了一种垂直的关系,其以条例规定为载体向排污企业直接施加义务,其内容统一适用于所有排污企业这一普通主体。相对而言,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则构建了一种仅适用于特定排污企业的义务关系。它以地方自治体和排污企业之间的合意为前提,具有行政契约的性质和效力,其强制执行力也已被诸多判例所承认[8]。作为一种个别调整手段,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能够从作为协定主体的排污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有针对性的公害防治/环境保护措施,并以其强制执行力作为措施实效性的担保。从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都包含了以下主要内容,即排污企业公害防治/环境保护信息的公开、地方自治体对排污企业的现场检查、企业应当采取的公害防治/环境保护措施、公害或环境损害发生后的处理措施、企业开发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考量、开发之后的自然环境修复等。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所具有的灵活性、针对性及可诉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地方自治体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重要模式。
三、 日本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1. 确保中央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的综合协调能力
从本质上说,长期以来我国中央层面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与日本类似,也属于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协调下的多部门合作的监管体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0条规定了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而根据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国务院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有对特定的环境保护事项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例如,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但是,如果着眼于具体内容的话,就会发现我国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与日本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具体而言,在日本的体制下,环境省的综合协调职能不仅有专门法的明确规定,而且其协调能力也获得了法律的强力保障。如前所述,在《环境省设置法》规定之下,建议、汇报、预算调整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环境省的综合协调不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层面,而是能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实践,从而使日本多部门合作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能够高效运转[9]。反观我国,虽然环保部的统一监管职能能够从《环境保护法》和环保部门法中获得法律依据,但遗憾的是,这些法律中有关环保部统一监管职能的规定过于原则化[10],既没有像日本《环境省设置法》那样明确规定中央环保部门在哪些具体事务上发挥统一监管职能,更没有明确规定确保这一职能得以切实发挥的有效保障措施。这样一来,实践中就难免会遇到以下问题:在环保部的统一监管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来解决这种冲突?实际上,因为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在这种权力对抗的构造下往往导致两种遗憾的结果。第一,相关部门各自为政,分别行使监管权力,从而导致监管权的积极冲突。特别是当行使监管权将为本部门带来具体利益时,监管权的积极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利益驱动型的监管权行使不仅导致监管成本的成倍增加,而且出自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往往使被监管者无所适从。从长远来看,在缺乏明确规制的背景下,利益驱动型的监管权行使具有形成先例的示范作用,最终必将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陷入混乱低效的恶性循环。第二,监管权者均采取坐视的态势,从而形成监管权的消极冲突。监管权的消极冲突往往产生于监管权的行使不会为监管权者带来利益的情形下。监管权的消极冲突极易形成监管的空白地带,从而使环境违法行为难以得到及时制止,久而久之甚至会成为纵容环境违法行为的推手[11]。
在刚刚开启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长期以来面临的上述难题出现了转机。随着生态环境部的组建,生态环境监管领域由于多头管理、“九龙治水”而导致的职责交叉重叠、权责不清晰、部分领域权责缺失等问题有望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实际上,在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之间仍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牵扯面甚广、远非一个部门所能独自完成,因此可以预见,生态环境部仍然要在具体工作中面临如何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对此,日本实践所提供的启示,在于通过立法为生态环境部综合协调能力的切实发挥提供保障。可供选择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规定生态环境部具有就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事务对国务院其他部门进行指导的权力;规定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接受上述指导的义务;由生态环境部对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经费进行统一预算,并在此预算下对国务院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相关的各种事务的经费预算进行调整。
2. 建立促使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的长效机制
生态环境部的组建极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层面生态环境监管权力的集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政府不再承担本地区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实际上,即便是在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当下,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监管积极性仍然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责,建立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但是,近年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和频繁发生的生态环境灾害表明,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并没有有效履行监管职责[12]。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非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政策的短视,而在人力和财政上完全依赖于本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最终也往往沦为政府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追随者和践行者,抛弃了法律赋予其的生态环境监管职责。
如何让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在生态环境监管方面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应对为主动出击?这是事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全局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日本相关实践的考察而得出的可供参考的经验是在缺少基于传统实践而产生的内在动因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构建有效的监督制度,并通过这一制度功能的发挥从外部促进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积极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
当前,我国在实践层面上存在通过外部监督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环保监管职责的机制。其一是2014年之后以“督政”为核心的环保综合督察,其二是2016年以后体现“党政同责”的中央环保督察。虽然这两种环保督察制度确实对于督促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二者在法律依据方面均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若以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衡量,不得不说均存在着制度上的瑕疵。首先,就环保综合督察来说,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环境保护法》建立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但是其所规定的仅是由本级政府对本级政府中负有环保监管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或者由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其负责人进行环保目标考核评价,该法并没有规定由环保部对地方政府进行环保目标考核评价。其次,就中央环保督察而言,虽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可视为其法律依据,但是该文件在性质上仅属于“党内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严格意义上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国家立法和党内立法存在重大差别。基于以上两点似乎可以认为,当前的环保督察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带有浓厚的“运动型治理”特征的监督行为[13]。因此,为了使当前的环保督察上升为一种具有严肃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法律制度,从而形成促使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的长效机制,就必须以《环境保护法》和《立法法》等相关法律为依据,通过制定专门法的方式来消除环保督察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的瑕疵。同时,为了保证环保督察的规范性和权威性,还应在专门立法中明确规定与环保督察相关的各项程序性和实体性内容,包括:环保督察的启动、督察机构的组成与权限、督察的方式、督察结果的通知和公示、督察意见的效力以及不遵守督察意见的救济措施等。
3. 试点推行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签订环境保护协定
日本地方自治体的生态环境监管既包括公害防治条例/环境保护条例的垂直监管,也包括以公害防治协定/环境保护协定为依据的水平监管,后者因具有针对各排污企业的不同特点进行管理的弹性而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在我国,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的环境监管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垂直监管。在这种监管体制下,排污企业的环保义务主要是由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所界定的。就积极意义而言,这种通过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来规定企业环保义务的方式具有整齐划一、便于管理的优越性;但同时,其弊端也是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整齐划一的环境标准和环境义务严重忽视了不同企业环保承载力的差异,容易导致具有较强环保承载力的排污企业怠于采取进一步的环保措施,从而出现“搭制度便车”的不利后果。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推行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签订环境保护协定不失为克服这种弊端的有益尝试。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已经获得承认,而且以排污企业环保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环保协定也不会对国家事权产生影响,因此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签订环保协定既不存在制度阻碍,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是可行的。就环保协定的具体内容这一微观层面而言,日本相关实践的以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借鉴:一是环保协定的内容应根据排污企业环保承载力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虽然在签订之初,环保协定具有为企业“量身定制”的特点,但是,如果其内容不能因应企业环保承载力的变化而适当调整,则不仅难以发挥推动企业不断提高环保水平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为企业的“合法排污”提供依据;二是在以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为当事方的环境保护协定中,可以通过为第三方创设权利的方式,规定当地居民在排污企业不履行环境保护协定义务情况下的诉权。日本判例法承认了环境保护协定为当地居民创设诉权的正当性,并就当地居民依此权利提起的请求作出了判决,判令作为环境保护协定当事方的排污企业履行相关义务。这一实践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在当前我国不承认个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背景下,当地居民可依据环境保护协定创设的诉权,针对排污企业提起诉讼,从客观上实现对环境公益侵害的救济;二是环境保护协定通过为当地居民创设诉权,预示了当地居民以排污企业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潜在可能性,而这种潜在可能性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可在无形中推动排污企业在履行环保协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 人民论坛网.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创新[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06/c40531-29688522.html,2017-12-15.
[2] 胡王云.日本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析[J].日本研究,2015(4): 66-78.
[3] [日]伊藤昭男.環境行政機関の改革に関する日中比較[J].中国21,2009(32):221-236.
[4] [日]環境省.環境省のご案内[EB/OL].http://www.env.go.jp/annai/,2017-12-15.
[5] 姜 雅,姜 舰.日本环境污染防治经验与启示浅析[J].国土资源情报,2014(2):46-52.
[6] 王 丰,张纯厚.日本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其启示[J].日本研究,2013(2):28-34.
[7] 胡云红.日本自愿式环境协议实施评析及对我国环境保护管理的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146-152.
[8] [日]岡山公法判例研究会.公害防止協定と公序良俗違反:福津市最終処分場事件差戻控訴審[J].岡山大学法学会雑誌,2012(3): 467-475.
[9] 殷培红.日本环境管理机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环境,2016(2):27-29.
[10] 王 曦,邓 旸.从“统一监督管理”到“综合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7条评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6):85-92.
[11] 李爱年.论我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D].长沙:湖南大学法学院,2012.
[12] 陈泉生,马 波.论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的法治保障[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2):73-77.
[13] 陈海嵩.环保督察制度法治化:定位、困境及其出路[J].法学评论:双月刊, 2017(3):17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