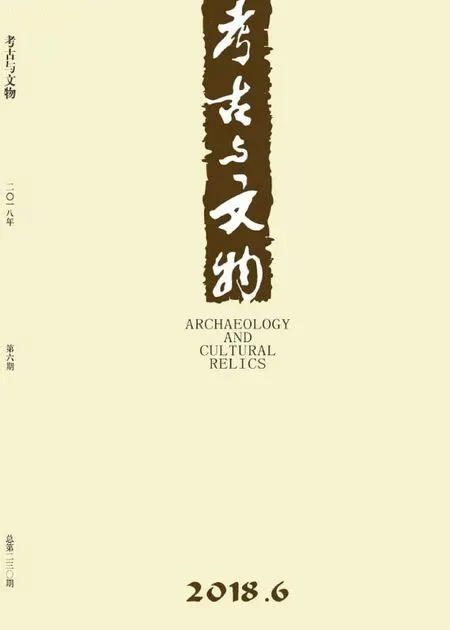西辛战国墓银器铭文释读议*
禤健聪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西辛战国墓是2004年度国家重大考古发现,发掘简报近期已发表[1]。该墓所出器物中有银器5件,皆刻有内容相近的铭文。发掘简报对铭文已有初步释读,李零则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以下简称“李文”)[2]。我们对银器铭文的释读有不同看法,写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按我们的理解,铭文可释写如下:
发掘简报和李文均释为“又卅”合文。按,战国文字“又”字或“又”旁常见,此字右旁最后一笔有折笔,与之不类,而与“丑”字写法略近,试比较战国齐系文字的“又”和“丑”:
古文字“卅”绝大多数情况下皆作三竖笔下端连接的写法,齐系文字作(《陶文图录》3.240.4)、(私之十耳杯,《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047),作平行三竖的写法仅见于货币文,作[4],但这类写法竖笔上不会加任何点或横画,皆与银器之字的左旁判然有别。
从文义看,若按照李文的解释,“一又卅分”义为一镒三十分之一镒,则铭文独缺最关键的记重单位,颇为怪异。而李文所举两件齐国耳杯的记重铭文,皆作数词加记重单位的格式,亦与此西辛银器铭文格式完全不同[5]。凡此可见,所谓“又卅”合文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战国齐系文字中有一个量器名的用字作:
退一步说,金文中“斗”“升”作为偏旁时有见讹误成“又”之例,如伯子父盨(《集成》4442—4445)诸铭中“盨”字写法有以下两种:
第1类从“斗”或“升”;第2类从“又”。但“又”旁于“盨”无义可取,实为第1类第二例“升”旁省去表示升柄的笔画上的饰笔而来。
补记:本文写成于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公布之初,在此前后,有不同学者提出过或详或简的铭文释读意见,读者宜参看。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4(9):4-32.
[2]李零.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J].文物,2014(9):58-70.
[3]原器照片不甚清晰,见:文物,2014(9):26。
[4]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40-243.
[5]同[2]:61-62.
[6]施谢捷.古玺汇考[D].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7]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J].考古学报,1980(3):290.
[8]吴振武.试说齐国陶文中的“锺”与“镒”[J].考古与文物,1991(1):67-70.
[9]魏成敏、朱玉德.山东临淄新发现的战国齐量[J].考古,1996(4):24-28.
[10]同[2]:64-65.
[11]同[8]:289-290.
[13]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铜器[J].文物,1975(6):70、74-75.
[14]黄盛璋.论出土魏国铜器之秦墓与墓主及遗物[J].人文杂志,199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