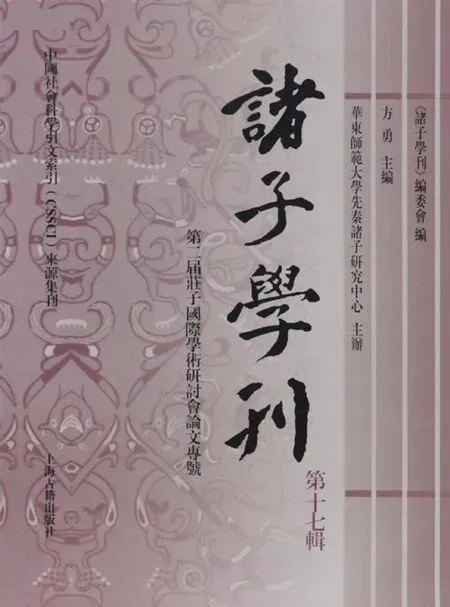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莊子》身體技藝中的天理與物性*
(臺灣) 賴錫三
内容提要 本文探討《莊子》技進於道的經驗中之天理與物性。除了技藝經驗中的身體感之外,本文特别着重身體與物性遭遇的雙重轉化過程,尤其細部描述身體主體的内在之天與物性天理的外在之天,進入到主客相互中介與彼此轉化的以天合天之過程。此一因循天理的過程,不僅讓人可以養生達生,也讓殊異萬物保有其自然天性。本文也檢討這種官止神行、以天合天的經驗,不宜用純粹的精神超越的合一論去理解,應調整爲人與物的雙重轉化,其中物性的陌異與阻力並不完全被消除,反而一直是促成身體不斷因循順任的他者化力量,只是此時的物性他者,已成爲身體活動的内在他者性之一環。最後,本文檢討了法國《莊子》學者畢來德的天人機制轉化和本文的差異,希望將跨文化的莊學對話帶入漢語學界,也期許將《莊子》帶入跨文化語境。
[關鍵詞] 莊子 物 天理 養生 身體 主體轉化 跨文化
一、 禮文雅層與庶民勞動的不同身體模態
筆者過去對《莊子》身體觀的研究,經常發現一種雅俗顛覆現象。所謂雅俗顛覆,是將禮教階層與俗民階層的上/下位階,給予顛倒式解構,從而産生脱冕高雅禮教,加冕勞動俗民的價值重估活動(1)賴錫三《論〈莊子〉的雅俗顛覆與文化更新——以流動身體和流動話語爲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7期,第73—113頁。。例如《養生主》的文惠君和庖丁,《莊子》讓兩人主客易位,使原本卑賤無名的屠夫成爲舞台主角,位高權重的文惠君反倒成了配角,重新聆聽庖丁所體現的“養生”福音。文惠君與庖丁的主客易位,雅俗顛覆的叙事反轉現象充斥《莊子》,顯示這是莊書自覺采取的書寫策略,藉此批判舊價值,解放新福音。如果説,周文以來所建構的禮樂教化是以“名人”爲中心的雅層來體現,那麽《莊子》透過一系列“無名人”即邊緣俗民之日常生活實踐,以“地方包圍中央”的顛覆方式,將價值中心給予解構,將價值之光挪移到邊緣地方、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從而揭露雅層過度規訓之貧乏,重新發現俗民勞動之豐饒。這一雅俗顛覆,意不在全盤否定貴族禮教,也不在全然歌揚庶民野性。當貴族雅層長期執政於禮文階層的集體馴化過程中,《莊子》顯然洞見了其價值觀僵化與生命力消弱的危機。所謂“禮失求諸野”,《莊子》意不在化外之地看到禮文風貌的保存,而是在禮文較少全面性控制的百姓日常生活中,注意到活活潑潑、生機暢然的生命力。它反映出類似主奴辯證的弔詭現象,當雅層階級掌握大量政治社會文化的象徵資本後,長期養尊處優於名利繁榮之權力機制,其價值觀和生命力,終於逐漸走向“周文疲弊”的僵硬弱化。筆者過去曾花費較多篇幅談論《莊子》對意識形態之解構治療與價值重估,本文則想從技藝實踐的力量美學這一角度,觀察《莊子》雅俗顛覆策略的另一向度,亦即《莊子》如何透過日常性生活的身體勞動之實踐,彰顯主體轉化與物性天理的交往密切性,從而揭露《莊子》的技藝實踐與力量美學對生命活力的通達(達生)與培養(養生)之啓發性。
二、 技進於道的人與天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2)郭慶藩《莊子集釋·養生主》,(臺灣)華正書局1985年版,第117頁。
《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是《莊子》對技藝通達之人,如何“技進於道”,最細緻、最豐富的一則有關技藝修養、主體轉化、養生達生的寓言叙述。所謂“道也,進乎技矣”,表明促使庖丁生手從“技”之操控層次,轉化爲庖丁達人的“道”之超乎技術,其中關鍵正在於——(身體)主體狀態從“官知”轉化爲“神行”。或者説,從“官知止”到“神欲行”,“一止”、“一行”之間,發生一種從“技”向“道”的質性變化。我們一再看到《莊子》記録一系列的技藝達人,他們對自己“出神入化”的關鍵性描述,必然都超出純粹方法性操作:“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庖丁解牛);未敢耗氣、齋以静心、以天合天、器以凝神(梓慶爲鐻);“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痀僂承蜩);“操舟若神”、“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津人操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吕梁蹈水);“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忘適之適”(工倕旋規矩)。
《莊子》並不把技術操控的具體細節,當做成熟性技藝美學的真正重點,反而當主體從“刻意”(如“心稽”的操控狀態)轉化爲“非刻意”(如“忘適”的非操控狀態),才真正是“凝神”以“入化”的關鍵所在。可以説,只有當行動者的“官知”之意向性有爲行動“止”(被懸擱或被轉化)的時候,另一種非刻意、非目的性的無爲行動(神)才被打開釋放(解心釋神)而流行起來(神行)。從上述基本描述,首先可給出暫時性的區分架構。例如“技”和“道”,“官知”和“神行”,“刻意”和“非刻意”,“有爲”和“無爲”,“心稽”和“忘適”,“意志操控”和“自然運作”等等異質行動的差異區分。這裏的暫時性區分,並非意指“技”與“道”完全斷裂或兩不相關,更不在於全盤否認技術積累的實踐意義。本文想要説明並探討的是,技與道之間的“非同一性”之質變經驗,到底發生什麽樣的主體轉化現象,而這種經由技藝實踐的主體變化又如何帶給我們對於新型態主體性的再思考;技進於道所發生的“神行”主體之力量狀態,對於“官知”主體的解放意義何在。《莊子》將這類技藝達人的生命活力現象,歸屬於可“養生”、可“達生”,似乎也透露這種活力的“生命身體”(3)尼采曾區分“個體身體(Körper)”和“生命身體(Leib)”。據劉滄龍分析,尼采的“生命身體”超越了笛卡兒、康德脈絡的我思、理性主體,歸屬於完整生命卻多元力量交匯的身體主體,其内涵大不同於個體性、對象化的“個體身體”。劉滄龍甚至進一步將尼采的“生命身體”和《莊子》的“氣化身體”給予對話會通。參見氏著《身體、隱喻與轉化的力量: 論莊子的兩種身體、兩種思維》,《清華學報》新44卷第2期2014年6月,第187—188頁。另外,法蘭克福學派孟柯繼續發揮尼采觀點而有力量美學之提出,其與《莊子》技進於道的主體轉化之對話可行性,可參見賴錫三《〈莊子〉的美學工夫、哲學修養與倫理政治的轉化——與孟柯(Christoph Menke)的跨文化對話》,《文與哲》第28期2016年6月,第347—396頁。,對人的存在狀態具有激活的存養、通達能耐。
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4)《莊子集釋·養生主》,第119頁。
《莊子》對技藝實踐中主體轉化的技與道,官知與神行,有爲與無爲等作出區分。如果我們再擴大觀察範圍,或細察相關文獻的叙述脈絡,還會發現一對更爲核心的區分概念,也就是“人”與“天”的區分。例如,當《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從官知轉爲神行的流動狀態時,同時也被描述爲能够“依乎天理”。簡言之,轉化爲神行而遊刃有餘的新主體流動狀態,它必須同時能够因循“天理”、依偎“天理”。若不急於解釋這裏所謂的“天理”(5)任博克(Brook Ziporyn)在英文譯本中,對《養生主》脈絡的天理,做了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注解,正和本文“物論”觀點相呼應:“Heaven’s unwrought perforations”are tianli, which also could be translated as “Natural Perforations”, “Spontaneous Perforations”, or “kylike Perforations”. This is the only occurrence of the character li (See Glossary) in the Inner Chapters, and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at the binome tianli is used. This term would later come to stand for a crucial category in Neo-Confucian metaphysics, in which context it is sometimes translated as the “Principle of Heaven” or “Heavenly Pattern”. The meaning here is much more literal. The term li can refer to the optimal way of dividing up and organizing a raw material to suit human purposes or to the nodes in the material along which such division can most easily be done. In this context, it remains closely connected to a still more literal meaning, the pattern of lines on skin. 參見“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Cambridge,2009, p.30.任博克的注解重要在於指出,天理這一重要概念首次出現在《莊子》,後來轉而成爲了新儒家形上學的重要概念,並提醒我們注意兩者脈絡的細微差别,尤其要注意《莊子》在技藝實踐中的物之文理脈絡。换言之,它並非抽象之理,也非形上理則。,至少得先注意《莊子》在描述這類經驗時,運用了“人”轉向“天”的回應模式。問題在於,技藝中人對於天理的因循回應,或者人向天的自我轉化狀態,該如何來理解?《達生》篇有關梓慶“技進於道”的身體實踐描述,可以讓我們看得更加清楚,人向天的回應與轉化過程: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6)《莊子集釋·達生》,第658—659頁。
不管是削木爲鐻,或者庖丁解牛,技藝通達之人都不會停留在“術”或“技”,他們一樣體驗到建立在技術層次,最終又溢出技術之上的體驗。這種美妙體驗,庖丁將其描述爲“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而梓慶則再進一解,首先他描述了“官知”的主體轉化過程,牽涉到“齋以静心”、“未嘗敢以耗氣”的心、氣工夫。例如透過“不敢懷慶賞爵禄”、“不敢懷非譽巧拙”等等消除名聞利養、技術框架對心神的干擾(齋以静心),保持自己的生命能量處於最精純、最專注、最飽滿的力量狀態(未敢耗氣),然後才能够進入技進於道的手作創造歷程(然後加手焉)。更重要的是,梓慶將他自己技進於道的創作,描述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凝)神者”。引發筆者特别關注的是,神凝(創作者之主體狀態)與器成(作品之客體狀態)之間的主客交涉,被描述爲“以天合天”的關係。仔細推敲,這裏至少碰到了兩個意義脈絡的天。我暫且將其權稱爲: 一是有關主體之天,二是有關客體之天。而且在技進於道的主客、物我交往轉化過程中,這種主客關係遠不是一般知識論思辨意義下的主體宰制客體,或主體同一化客體的主客關係。問題是,這種技藝實踐透過物我交涉的兩相轉化狀態,到底發生了什麽樣的關係質變或力量辯證,讓梓慶使用了“以天合天”來描述這種體驗。
在筆者看來,第一是有關“人”轉化之後的“人之天”,亦即從官知主體解放出神行主體的“神”之力量狀態。第二則是有關於“物”轉化後的“物之天”,亦即人的神行主體能善加回應而非壓抑物之天性。而“以天合天”的主客交涉、物我往來的轉化意義就在於,只有當人的“神行之天”,亦即人的官知主體内部原先被壓抑的自然力量解放出來,並與主體外部的“物性之天”之自然力量相互轉化,而不是單方面的官知控制或意向强迫時,我與物、物與我“之間”,才能引發既非“以我役物”也非“我役於物”,而是“客體轉化了主體”、“主體參贊了客體”的兩相質變與轉化。亦即梓慶的主體性轉化(人之天)和物的客體性轉化(物之天)同時發生,兩相成全,從而創造出“人之天”和“物之天”的“以天合天”之兩行交换與互轉。
呼應於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所隱含的技、道區分,官知、神行區分,梓慶的描述又補充了一項: 人和天的區分。如此一來,我們便可先簡單歸納出: 技、官知、人,三者屬於同一層次,且三者可互文補充來描述一般生手還停留在“技術”的主體狀態。而道、神行、天,這三者屬於另一層次,也可互文補充來描述熟手“技進於道”的新主體狀態。而從生到熟(甚而至於從熟到忘)的主體轉化過程,則分别可被描述爲: 技進於道、人轉化爲天、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質變過程。而這個新形態的主客交涉,物我交往的質變演化狀態,先前被庖丁描述爲“依乎天理”,現在則進一步被梓慶描述爲“以天合天”。
三、 技進於道的天理與物性
然而“依乎天理”的“天理”何在?“以天合天”的前後兩個“天”該做何理解?如上所述,這裏至少碰到了兩個不同意義脈絡的天。首先是有關人轉化後的“人而天”,亦即從官知解放出“神行”或“凝神”狀態。其次則是關於山林木植的“物之天”,亦即梓慶能因循回應而非强行宰制的物之天性。而“以天合天”的主客轉化意義就在於,只有當人的“内在之天”,能從官知主體的過分規訓中解放出來,並與主體外部的“物之天性”相互轉化,而不是單方面的控制與强迫,最美妙的物我關係才得以發生。亦即梓慶的主體轉化(人之天),以及物性生命的轉化(物之天)同時成就,從而創造出“神行主體”與“凝神妙器”的雙重實現。根據筆者這樣的理解,“以天合天”的第一個“天”,也可被理解爲“意識主體(官知)”從有爲操作狀態(人)轉化爲“身體主體(神行)”的無爲潛能狀態(人之天),於是身體便從意識官能的同一性控制底下,解放出一種身體活力之潛能,以通達於人之主體内部的自然之天。這種自然而然的身體活力,過去被過分的技巧所規訓(如非譽巧拙),被過多的意識目的所干擾(慶賞爵禄),如今透過“齋以静心”、“未嘗敢以耗氣”的心性收斂與身氣轉化,又在與物遭遇的力量遊戲過程中,才逐漸被釋放出來(7)换言之,官知止而神欲行,首先涉及意識主體向身體主體的落實與轉化。對於技藝的凝神入化和身體潛力的關係,畢來德、楊儒賓、宋灝都有與筆者類似的身體主體之描述。而本文要强調的是,從官知到神行的主體轉化,雖涉及從意識到身體的肉身化體現過程,但這種活力身體所體現的神行狀態,既不適合再以主體形上學的身心二元論方式來理解,也不適合再用心性形上學的心之優位性來理解,本文打算重新透過類似阿多諾的身心相互中介、主客相互中介、物我相互中介,或類似孟柯的官能與力量的弔詭運動,來重新加以描述,希望增添差異新義。。這種依循身體活力的“人而天”狀態,也就是在技藝過程中解放遺忘在主體内部,那未被人的官知規訓所徹底馴服的“非同一性”之自然力量。然而純粹從“人之天”這一向度來描述技藝,在技進於道的技藝實踐過程中,顯然並不完整。因爲技藝不能單憑主體自我的“人而天”之單向轉化,它必然還要進入“以天合天”的“合天”脈絡。或者説,“依乎天理”的具體化情境。甚至可以反過來説,只有在依乎天理的依循、交往的具體性辯證脈絡,主體原本自我封閉的官知狀態,才能被帶向“人而天”的自我轉化。由此可見,技藝實踐中的主體轉化並非單獨依靠人的身體自我來完成,而是在一個“依乎天理”的處身情境之中,才得以具體發生。
問題是,在技藝活動中,人合乎天理的處身情境,要如何理解?順着技藝實踐、身體運作的現象,這個答案必須扣緊着“物”之遭遇來理解。更完整的説法是,必須扣着物之天性、物之天理、物之情境,來加以具體化把握。如以庖丁的處身情境來説,整個天理所在,主要就是屠宰境遇中,牛之身體的内在空間和肌理内勢。若以梓慶的處身情境來説,合乎天理則是呼應於山林境遇中的木植本性與自然紋理。一言以蔽之,不同的存在物各有其風格殊異的自然情性與自然處境,牛有牛的天理,樹也自有樹的天性,千差萬别的存在物都各自擁有風格殊異的自然天理與天性。而技藝實踐者都必須學會尊重不同生命情境的物之天理,體會不同自然存在的物之天性,才能够與差異於我、陌異於我的萬物生命力,找到一種“以天合天”的微妙交往、力量律動。要避免獨我論地以人類“自我觀之”的同一性標准尺度,强硬套加在風情萬種的物之天性上。《莊子》顯然高度自覺人類經常犯了“以人欲滅天理”的同一性暴力: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无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8)《莊子集釋·齊物論》,第91—93頁。
不只在觀念上,反省知性的同一性暴力,更要在技藝實踐過程中,身體學習被陌異於我的物性力量給轉化(9)此觀點令人聯想起卡夫卡曾對Gustav Janouch説的話:“世上没有什麽比那些單純、具體、普遍地有用的行業更美的了。除了木工,我也做做農事和園藝,比起强迫性的辦公室工作,要好得多而且有價值多。坐在辦公室裏工作的人似乎比較高級,但那只是表面而已。……智力勞動硬生生把人和人的社會撕離,然而手藝使人更像一個人。”又説:“我一直夢想到巴勒斯坦務農或作個木匠。”參見古斯塔夫·亞努赫《與卡夫卡對話》,(臺灣)商周出版2014年版。令人驚喜的是,卡夫卡也是個《莊子》愛好者。。技進乎道的整個“人而天”的主體轉化過程,還要落實到物、我之間的力量交往過程。不管是身體潛力(内在之天)的解放,還是對天理物性(外在之天)的參贊,整個技藝過程的技進之道、天理之道,都不是抽象的觀念之道或者形上超越之道,而是落實在“即物而道”、“物化天性”的具體經驗中來“以身體知”(embodyment)。由此,才可能實現物與我之間相互中介、彼此轉化的力量質變之躍進。正是這種異於主體的物性力量之牽引,才同時啓動並質變了主體内在的非同一性力量,讓身體的原始天真之潛力給引發出來。如此也可説,物之天引動了人之天,人之天又參贊了物之天。
筆者將“依乎天理”、“以天合天”,落實到差異、陌異的物性力量來加以具體化、動態性描述,也直接在《達生》篇底下案例得到印證:“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10)《莊子集釋·達生》,第662頁。在這個技藝的例子裏,“依乎天理”、“以天合天”,被直接表達爲“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當一個生手能將官知控制習慣的成心(慶賞爵禄之心、非譽巧拙之心),給轉化爲“神欲行”的熟巧之指時,此時“由生而熟”的身體活動,甚至“由熟而忘”的物我關係,就能進入“以天合天”的“忘適”狀態,“自然而然”地表現出“指與物化”之美妙活動。可見,技進於道的技藝一定要透過“手做”(身體參與轉化),而手做的身體活動一定會“遇物”,而“遇物”的主客辯證,通常又會從不適到適、從不忘到忘的轉變過程。而能否技進於道的關鍵,就在於“指”與“物”的遭遇,手做與遇物的力量交往,到底是停留在主體單方向的意識强迫、有爲操控(不適),還是能進入到順任無爲的“被轉化”狀態(能適)。或者更完整地説,能不能進入到物我之間“相拒又相迎”的力量共振之遊戲狀態。這是一個又主動又被動的弔詭來回運動,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被化約或消除的辯證律動,如此才能成就“以天合天”的力量美學。
相對於上述那種“忘適之適”、“以天合天”的技藝化境、力量美學,《達生》篇曾以東野稷敗馬的相反案例,反映出: 一旦物我之間的力量,非但不能相轉化、互加乘,反而呈現兩衝突、相抵消,那麽其結果必將猶如生手庖丁切割牛體大骨,硬碰硬地落入相刃相靡的兩敗俱傷: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钩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11)《莊子集釋·達生》,第660—661頁。
故事中的顔闔,之所以能一眼看出東野稷將會敗馬,原因就在於他觀察東野稷和馬性的關係,乃是一種“人”强行規訓、單方主控的力量操作狀態,表現在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的控御行爲。這首先使得馬的天性活力不斷遭受抑制,再則使得人和馬之間的力量交往,墮化爲機械式的克制操縱。如此一來,東野稷本身的身體活力,根本不能在與馬力的交手過程中被啓發出來,而馬之爲馬的天真活力,也因爲過分受到規矩繩墨的斵喪而難以發揮。其結果不僅馬力竭矣,東野稷必然也是身疲力竭,如此人馬衝突的力量耗損,遠於“以天合天”的力量美學甚矣,自然必敗。這也是《莊子》批評伯樂治馬不給“馬之真性”留有任何餘地,其近乎工具性的治馬、御馬之高壓控制,除了犧牲了更多馬匹之外,根本無法將馬之天真原成的自然生命力(天理與天性)給予較好的引導與發揮: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12)《莊子集釋·馬蹄》,第330頁。
上述以天合天、物我忘適的力量來回之身體技藝,很適合用馬師騎馬的例子來觀察。因爲馬的野性力量(馬之天),正是馬之爲馬的天理與天性,而技進於道的好騎師,不宜一味地想要徹底馴服馬性,想以馬術規矩來單邊强御,而是要去體會馬之天、馬之真,從而在引導與因循之間,回應不同馬性的生命律動,並且不斷調整並引發騎師自己的身體律動,以便讓彼此的力量交往,從“我與它”的强行對抗與彼此消耗,轉化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力量舞蹈。這種我與馬之間的力量律動之美妙節奏,才能呼應於庖丁解牛所謂“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這是一種在順逆之間、迎拒之間,力與美結合的美妙韻律,人與馬共同完成的人馬共舞。此時,馬師的身體潛力(人之天),被馬之野性活力(馬之天)給引動並激發出來,而馬的天生活力也能在人的回應與因循中,自然而然地盡情發揮。如此便成就了物我之間“以天合天”的力量美學之體現。换言之,“不以人滅天”,甚至强調人可以“反以相天”的解讀,並非强調“人”單邊自以爲參贊了天地萬物之化育,應該同時强調人被萬物給參贊給轉化。人並非不能用物,但要以依乎天理、觀乎天性爲“度”,而不是純粹以實效利益爲“度”,並將其合理化爲參贊天地之化育。總之,人不能因爲人類私我利用厚生之需求太過,從而裁抑萬物情性而濫用無度,更不宜將“以人滅天”之人病合理化爲“反以相天”之參贊,以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13)最明顯的弔詭案例,便是郭象。他强調:“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騖驥之力,適遲速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表面看來郭象好像頗能善得人“反以相天”之妙旨,然而再仔細看,郭象實有爲既得利益者服務,給予權力層級者合理化辯護的毛病:“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爲哉?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莊子集釋》,第333、58頁。。
四、 以天合天的主客與物我
對於上述,官知止而“神”行,指與物“化”,以天“合”天,其中的“化”“合”情狀,内涵該如何理解?過去筆者多少傾向於直接使用“主客合一”、“物我交融”——亦即指向身與物、物與我的超越主客與融合無間(14)參見拙文《〈莊子〉身體觀的三維辯證: 符號解構、技藝融入、氣化交换》,《清華學報》42卷1期2012年3月,第1—43頁。,來陳述這種依乎天理的“神行”化境。但目前筆者愈來愈意識到,所謂“物我無礙”、“物我合一”的描述,並不那麽精准、甚至過於美化。因爲在身體感的技藝運動過程中,人的身心再怎麽與物遇合、融合,都不可能完全取消阻力之觸覺與澀感。筆者近來經由與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的跨文化對話之後,認爲有必要加强從“唯物”與“微觀”的“辯證角度”,來描述其中所發生的力量牽引狀態(15)這呼應了阿多諾的形上學之唯物轉化,從而進入到微觀形上學的主體轉化、物性轉化來理解生命力量的辯證與超越。對此,筆者將以另文透過與阿多諾和孟柯的對話來加以呈現。。所謂主客合一般的行雲流水之描述,比較傾向於突顯“自然無礙”的身體感,但這樣的“無礙”並不意指物之天性的非同一性力量,完全被人之身體主體的力量消融或化解。倘若如此,便有單獨突顯“人之天”的片面化傾向。同樣,“無礙”也可能被理解完全消解身體自我,以能融入物之天理與天性,此種描述也會有單獨突顯“物之天”的片面化傾向。换言之,物我合一、主客無礙的境界式畫面,很容易將物我之間雙向來回的“非同一性力量”、“差異性力量”,給簡化爲静態綜合的同一性力量之純粹整合狀態。不管是用“人之天”來綜合“物之天”,還是用“物之天”來綜合“人之天”,兩種綜合似乎都很難免於將差異性力量給予“融合”,甚至“合一”的片面化傾向。
對于這種主客融合、物我合一的描述,是否能將技進於道的整個動態歷程、力量辯證,給予微觀考察,筆者愈來愈持保留態度。目前更傾向將技進於道中的力量豐富與複雜狀態,尤其將“礙與無礙”之間的“弔詭”關係考慮進來,亦即對“礙”的正視與肯認,顯示出主客之間,有不可完全被克服的“非同一性”力量正在發生作用。而技進於道的狀態,並非意指完全消除“礙”所暗示的非同一性力量,而是在礙與無礙“之間”尋獲一條弔詭運動的力量曲線。微觀而言,線條舞動的力度,乃是因爲它辯證遊動於物我之間、迎拒之間、順逆之間,在曲曲折折之間,不斷發現力量的迂迴通道。而非全然順暢、完全無礙的同一性力量之直線通行。因此,物性與情境的非同一性力量,雖能被納受與轉化,但是做爲它者的差異性力量,並不因此完全被均一化、齊平化。
歷程性來看,技進於道的官知轉化爲神行,乃是從“不化”到“化”的轉進。亦即庖丁手刃如何與牛體紋理的力量交涉運動,如何從直接的主/客對抗(所見無非牛),漸漸在身體感的運動摸索與調適過程中,讓主體逐漸能回應客體的物性天理(未嘗見全牛)。可見“所見無非(全)牛”的階段,代表着主體與物性的力量互動太過粗糙表淺,主體停留在自我主宰的意識操控狀態,封閉在自我主體的同一性力量循環中,不能因循物之天理,尊重物之天性。到了三年後的“未嘗見全牛”狀態,庖丁主體已經逐漸在身心之間、物我之間,體會更爲細微的力量來往之回蕩經驗,因此能够從較爲表面的物我關係,進入到“未嘗見全牛”的相對内層之身體感受狀態,只是這種身體與牛體的力量交往,還未完全脱開主體有爲的意志操控習性,因此仍然殘留“以主攝客”、“攝客歸主”的徼向。雖然相對於“所見無非(全)牛”的主體同一性强制暴力,“未嘗見全牛”已逐漸在揣摩主客之間、物我之間的非同一性力量關係的可能性。但是只有來到“神遇而不以目視”,才真能顯示技進於道的質性蜕變,庖丁終能進入主客之間、物我之間,感受來去回蕩、彼此轉化的力量遊戲之活力。而這種神依乎天理、指與物化的力量質感,很明顯落實在因循牛體内部的自然理路而迂迴運動——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亦即,神庖的身體感能在“與物相化”之精微運動節奏中,彈性協調地因循已啓動的物我交往之力量通道。而這種持續在時間性變化中的力量狀態與迂迴通道,並不是單獨由主體意志所化身的刀刃可强行決定,反而必需藉由與物性力量相互合作的交往磨合,才能讓物我協作動勢中的力量通道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也因爲這種回應物性力量、因循物性情境的“指與物化”,庖丁才能通達一種“不耗氣”的“遇物之道”。也因爲他能順應於物之天理(萬物差異的内在生命力),並在物我之間的力量來回,發現力量的辯證理路(間隙),最後才能遊刃有餘地回應“礙與不礙之間”的非同一性力量。也就是上文一再提及的,主體的内在之天(原先被抑制的身體自然性力量)和主體的外在之天(原先被宰割的自然物性力量),現在終能進入深度的辯證交往。一方面主體轉化而解放出内在自然的非同一性力量,另一方面和外在自然萬物的非同一性力量進行一種雙向來回的力量舞蹈、彈性韻律。如此一整個活動的兩行轉化,才成就了依乎天理、以天合天。
指與物化、人與牛忘、以天合天的主客狀態,應該要如何理解?東方學者自然很習慣用主客合一、主客泯合、無主無客這些概念,來加以描述。一言以蔽之,這種技進於道的境界似乎是一種純粹精神主體(如徐復觀、牟宗三的理解方式(16)牟宗三“主觀境界形上學”和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的詮釋進路,都偏向心靈的純粹性,他們認爲老莊的人格之美在超越主客、物我對立後呈現出玄冥心境,一種不著於物、自由自在的心靈狀態。龔卓軍曾分析徐復觀所理解的莊子美學帶有濃厚的觀念論/現象學式的主體論,缺陷便在身體向度的不介入(《庖丁手藝與生命政治: 評介葛浩南〈莊子的哲學虚構〉》,第80—86頁);而我亦曾分析牟宗三所理解的道家美學傾向於静態式的觀照,無法揭露道家那充滿活力、差異的物化美學向度(參見拙文《論先秦道家的自然觀: 重建一門具體、活力、差異的物化美學》)。),而這種純粹精神則近乎處於完全與物無礙的化境。這樣的理解,看似一目瞭然且似有文獻根據,因爲從修辭來説,“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看來近乎是毫無阻礙的神行遊化境界,似乎任何物性阻力皆已被消融化解,神之精神主體從此收納了物之天理天性於自身,盡情從容、自在無礙地遊於物化之中。這種理解方式,顯然將物性的力量(物之天理天性)給收編到超越性的精神主體來理解,這仍然是一種“以心統物”、“以主攝客”的同一性思維方式,只是將認知性的意識主體,改由超越性的精神主體來代替。但就本文的理解角度,依乎天理、回應物性力量的神行狀態,雖然轉化了意識主體的主客對立,但卻不是以精神主體來收編物性力量的主客合一;而是主體的非同一性力量(人之天),與客體的非同一性力量(物之天),彼此進行兩行交换、雙向質變的力量辯證運動。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會轉介到對方去,並且也被對方的力量給周轉。换言之,在雙向過渡與相互轉介的過程中,自身既被改變,卻也變化了對方。但是雙方的差異性力量,並没有完全融合爲一種同質性的同一力量,反而是在運動狀態中持續維持着——既迎且拒、既順且逆的弔詭兩行。因此宣稱主客合一的絶對精神主體,反而可能使得千差萬别的物之理、物之力,原本陌異於主體的他者性,不再成爲轉化主體的非同一性力量之契機,因爲它近乎已被全能的精神主體給吸收殆盡。
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17)《莊子集釋·養生主》,第119頁。
以上這段文獻所描述,表明了就算已有十九年功力的神庖,在他的解牛過程中,也絶非一直處在毫無阻力的順刃暢通狀態。尤其每當遭遇某些特殊結構的錯綜情境(“每至於族”),刀刃便立即顯出特别礙澀的力量張力(見其難爲),因而庖丁也就要特别慬慎(怵然爲戒)與精微調度(動刀甚微),來和緩力動的時間性節奏(視爲止、行爲遲)。换言之,當刀刃與牛體的互動來到某些特殊的力量交涉場所時,原來較爲順暢的物我交往之力量空間,會轉换到較爲阻澀的力量空間,此時細敏的身體運動之時間性韻律,也要跟着轉换力量速度。這是因爲此時的物性阻力,會反過來要求庖丁要能被牛體天理給再度調適轉化,以便進入到另一節奏的“以天合天”之力量辯證。由此可見,“以天合天”或“依乎天理”,是一個不斷回應、不斷調整的力量來回之變化過程(活動中天理、變化中天理),而不是一個相對簡單静態的主客合一可以完全描述。這表明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力量過程,是一個不斷回應精微物化脈絡的力量交涉過程。因此與其使用相對簡化的主客合一、物我消融來概括,不如從人牛之間、主客之間,不斷互相調整的力量辯證交往過程,來加以微觀深描。用時間性來描述,整個過程正是一個順逆之間、快慢之間,不斷彈性來回的“非同一性”之時間流。而這樣的“非同一性”之時間流變,與其説是由人刀(主體)所自主決定的,不如説牛體的物性理路(客體)要求神行主體回應它,因而轉化了主體的運動狀態以及時間節奏。由此可説,神庖之所以爲神庖,在於他能鬆開主體“同一性”的主宰意志,能够在指與物化、隨物婉轉的交涉過程中,被“非同一性”的物化處境給不斷打開與更新。從而讓整個主體與客體的來往交涉,充滿差異又新鮮的持續性之動態活力。
類似梓慶透過“齋以静心”、“未嘗敢以耗氣”來鬆解主體的同一思維與宰制意志之後,才能真正進入物的整體情境(然後入山林),讓物的自然天性(觀天性)顯示自身(形軀至矣),彷彿植物内裏自然有一股力量會自發湧現形式(然後成鐻)。由於梓慶能够對物之天理天性敞開,讓物之差異殊性、非同一性力量顯現自身,由此轉化了梓慶主體的同一性,然後使他進入“指與物化”(加手焉)的物我交涉之力量實踐。倘若梓慶感受到自己還不能進入那種“與物婉轉”、“被物所化”的“交往”狀態,自己也就還不到進行成熟創作的力量實踐(不然則已)。因爲强行宰物只會重複了主體控物的同一性衝動,而不能領受主體被物之天性所轉化之契機,因而也就錯過了技進於道所能促發的主體轉化之養生、達生之效。也只有透過與物婉轉、被物所化,主體才能從人轉化出“人之天”,而這種“人之天”的狀態,也才能與“物之天”進行互相轉化的交涉。這個過程方可謂之“以天合天”,而人之天與物之天雙向交往的創造性結果,才足以成就“凝神之器”。行動者也才能在整個技藝的實踐轉化過程,通達其天真活力而達性養生。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和专业英语的文章有点类似,首先是让学生熟悉文章内容,然后解释里面的句子含义,最后翻译文章和讲解里面的专业知识点,但到最后主要知识点讲解时所剩时间无几。
上述所述,對物之情境脈絡敞開,並在隨物婉轉中被物轉化。我們可以從《達生》篇中,分别再擇取一偏静、一偏動的例子,來説明實踐主體在技進於道的物我交往過程中,如何被不同的物化情境給轉化,以便進入非同一性的時間節奏、變化之流: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18)《莊子集釋·達生》,第640頁。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9)同上,第657—658頁。
上述兩例,雖然痀僂承蜩的處身情境偏向於静(捕捉樹林静蟬),而吕梁游水的處身情境偏向於動(泳於瀑水激流),但就促成兩個出神入化的技藝達人,關鍵處都超出了技術層面。對於技進於道的關鍵内涵,筆者想延續上述以天合天、依乎天理、察乎天性的理路,尤其將天理天性落實在每一當下的具體、差異之物化處境,來總結物我交往的婉轉過程,亦即主體我(如承蜩者、游泳者)如何“隨物所化”。
從痀僂承蜩的例子來看,平常的手藝訓練(累二丸、三丸、五丸的技術訓練),雖是必要但並不充分,甚至不是最關鍵處。原因在於,捕蟬的具體活動是在一個自然物化的生態系統當中,例如各種植物昆蟲交織而成的密樹深林。當捕蟬者(主體)帶着强烈的主體意向性(捕蟬動機),任意趟入這片充滿物化生命的密林之中,一不小心極容易犯上外來者的粗暴躁進,進而干擾原本在其自己的萬物生態與力量韻律。换言之,當捕蟬者的主體還未和這個自然情境相接觸時,原本各種萬物交織而成的自然生態,就有它屬己的特殊時間性韻律。一旦捕蟬者的處身情境進入這個自然物化情境時,倘若只以外來者的强行干預來介入原本的時間性韻律,必將造成萬物驚動而四散走飛(蟬也必將受驚嚇而飛逝),那麽痀僂老人平常再好的手藝訓練,都將無用武之地。可見關鍵處並不在於單獨手臂與工具之間的協調訓練,更重要的是,實踐者必需對他的處身情境有高度的覺知性,並且有參與情境、融入情境的“模擬”能力(20)本文采阿多諾的模擬(Mimesis)意含:“如果下一個定義的話,阿多諾的所謂模仿能力並不是向已知事還原同一化,而是能够體驗、認識未知事物的能力。它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現抵抗主體的同一性概念的‘非同一性事物’的主體的能力。”詳見和之著,謝海静、李浩原譯《阿多諾: 非同一性哲學》,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50頁。。此即痀僂捕蟬者的身體轉化體會——“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因爲這時的蟬正停留在相對静定的樹木上,倘若捕蟬者不讓自己模擬於這個相對静定的樹木氛圍,他(主體)便無法與蟬(客體)處身在接近的時間性節奏中,一舉一動必將打草驚蛇(主體强擾客體),從而徒勞無功。只有當人的處身情境能被原本蟬的處身情境給轉化,那麽人才能因爲“隨物婉轉”而與蟬共在於同一物化世界、同一時間之流。也正是這種被物轉化的身體模擬能力,讓主客從兩相對立,轉化爲彼此共在。由於這種共在與交往,讓蟬的生態和人的生態進入了相近的時間流速,因此蟬便難以知覺到人的捕捉活動,捕蟬者便自然而然地容易上手。這裏“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乃意指捕蟬者能全神貫注地模擬己身,以進入蟬的處身情境(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並在隨物婉轉的共振頻律中,以樹林的世界爲世界、以蟬的時間爲時間(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如此與蟬處身於契近的物化脈動中,自然而然能“指與物化”地百發百中(何爲而不得)。
相對林中捕蟬,痀僂老人模擬己身來轉入静寧深林,吕梁游水的例子則是擬身於激水瀑流的高速湧動之水世界。這除了吕梁泳者因爲從小就生長在流水環伺的大自然情境中,使得身子裏早有了親水生態的適水性(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亦即骨子裏早就浸習於自然風土而内化爲身體親水性。更重要的是,每當他進入到變化莫測的激流韻律時,泳者這個主體必須放空自己的主宰欲和抗水性,反而要學會將身體交付給不斷變化流動的水流力量。一旦主體意志與水流韻律完全相抗,那麽人很快就會精疲力竭而終將滅頂,這都是因爲主體自“私”(自私其心)的原故。因此好的泳者,必須放開私心私意的自我主控力,要學會無私地隨物婉轉,才能與水流一直處於變化莫測的運動節奏,此即所謂“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順物之化、從水之流,才能安於水的運動時間性,獲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自在從容。一言蔽之,這也是主體婉轉於水之天理、天性,從而獲得被自然情境、被自然物性給轉化更新的活力經驗。而所謂“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是指人的主體從來不是獨我孤存,他總是生活在一個“自然風土”而“與物共在”的處身情境中(生於陵,長於水),如此而能適身共活於其中(安於陵,安於水)。在處身情境而潛移默化地適應、模擬物化風土(吾不知其然),如此才促使物我之間有了最自然又必然(命)的親密性交往。
結論: 畢來德的人天機制、主客融合的再檢討
筆者上述的問題意識以及討論脈絡,可和法國《莊子》學者畢來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以及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孟柯(Christoph Menke)兩人觀點,産生有意味的跨文化對話(21)畢來德著、宋剛譯《莊子四講》,(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7—57頁。Christoph Menke, Kraft: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hropologi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8).英文譯本: Christoph Menke, Force: A Fundamental Concept of Aesthetic, trans. Gerrit Jacks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81-82.。技進於道的關鍵,用畢來德的“機制”(régime)概念來説,涉及如何從“人的機制”轉化爲“天的機制”。若用孟柯的概念説,則涉及如何從“官能”到“力量”的習練,或者從“規訓習練”蜕變爲“力量習練”,又或者從“規訓工夫”到“美學工夫”的轉變。對於孟柯而言,美學實踐的根本重點也不在有爲的技術層次,而是涉及主體如何從“官能”到“力量”(相應於《莊子》的“官知止”到“神欲行”)的遊戲轉化過程:“美學毋寧是美學化的過程,感性認識的實踐官能將在此過程中轉化並提升,遊戲於焉開始。感性認識的操練(praxis)展現於力量的美感遊戲當中……因爲幽黯力量的美感遊戲透過其美學化以對反於實踐官能的方式展現自身,我們據此也經驗了一種全然不同的實踐能力。力量遊戲的美感經驗媒介了轉化中的自我經驗,一種自身實踐官能的轉化經驗。”(22)Menke, Force, p.70.而畢來德對《莊子》技藝達人的研究,則直接使用人的機制到天的機制之“人而天”轉换過程,來描繪技進於道的忘與覺。並且透過這種自發活動的身體潛能發用狀態,重新提出一種“虚而能化”的嶄新主體:“一言以蔽之,《莊子》當中凸顯了一種嶄新的主體以及主體性的概念範式……我們所謂的‘主體’和‘主體性’,在其中呈現爲一種在虚空與萬物之間來回往復的過程。而在二者之間,是前者——虚空或是混沌——居於根本的位置。我們是憑藉這一虚空才具備了變化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使得我們能够在必要的時候重新定義我們與自我、他人及事物的關係;我們也是從那裏萃取了賦予意義的根本能力。……我相信,進一步研究這些文本,就會證明,莊子論述到虚空與萬物之間來回往復的過程時,描寫的是我們主體的運作。……這一概念範式還有一種含意: 莊子所説的‘虚’或是‘混沌’之所在,不是别的,而是身體。”(23)《莊子四講》,第109—111頁。
筆者過去曾經撰文,分别與畢來德及孟柯兩人觀點做過較爲完整的對話(24)參見拙文《身體、氣化、政治批判: 畢來德〈莊子四講〉與〈莊子九札〉的身體觀與主體論》,《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卷3期2013年9月,“畢來德與跨文化視野中的莊子研究專輯(上)”,第59—102頁;《〈莊子〉的美學工夫、哲學修養與倫理政治的轉化——與孟柯(Christoph Menke)的跨文化對話》,《文與哲》第28期2016年6月,第347—396頁。,現在則透過結論,嘗試再以畢來德做爲反省對象,來暫時總結本文的討論焦點。在討論梓慶削木爲鐻的主體轉化工夫時,最後將來到“以天合天”的狀態,用畢來德的“機制”概念,“以天合天”是指實踐者能從“人的機制”轉化爲“天的機制”,並在“天人轉换”之際,虚化了主體意識的有爲操控,轉化成融入整個活動脈絡的回應狀態(25)《莊子四講》,第二講《天人》,第27—57頁。。若以孟柯的話説,此時主體的“控制失能”正好開啓了“回應之能”,而藝術家的實踐轉化契機,正在於“能於不能”。只有從目的性“控制”轉换爲對力量的任隨與回應,才可能發生“以天合天”那樣既自然又自由的美好活動。對於如何開啓回應力量的“天”之機制,上述《達生》篇曾透過游泳案例,給出了深刻的描述。當吕梁丈夫融入溪流中時,似乎已卸下泳者的主體意向,純粹忘我地因循水流而任運浮沉,正所謂“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换言之,這完全在於主體能否去己忘私、渾然無我,投身於水流力量的流變脈絡之内勢中。吕梁丈夫的蹈水之道,最後所以能“技進於道”,完全就在於“不爲私”。正是這種私我控制的“失能”,他才能成就“不知所以然”(無爲),又通達於“自然而必然”的完美回應活動(無不爲)。有趣的是,畢來德在面對泳者“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的關鍵體驗時,就將其理解爲,始於本然,發展出自然,終而達至必然:
游水男子已經能够與激流漩渦完全融合,他的動作是完全自發的,無意的,不由他主體意識來支配,换句話説,對他來説是‘必然’的了……而要達到高超的境界,游水男子對孔子解釋説,就要將本然的現實作爲基礎,下工夫發展出一種自然,從而可以回應水流的激蕩與翻滾,以一種可以説是必然的方式來行動,而且因爲這種必然而自由。很顯然,這裏的激流漩渦指的不只是水,而是指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當中,所有外在和内在於我們的一同運作的所有力量。(26)《莊子四講》,第18—20頁。
畢來德根據《莊子》的天人觀點,清楚指出這種自然與必然合而爲一的“自由”,乃建立在泳者能從“人”的機制(意識主體)轉向“天”的機制(身體主體),而且在“人而天”的機制轉换下,超越意識的有爲控制,轉入必然而自發的活動狀態。只有身處必然而自發的身體主體之活動機制,才能將已知和未知的潛力發揮到淋漓盡致。由於畢來德熟悉《莊子》文獻並對它頗有領會,因此清楚指出: 不管是“技進於道”的轉换關鍵,還是“人而天”的轉化關鍵,亦或“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身體潛能之開發,轉换的中間環節都必然要觸及“忘”的工夫。《莊子》的“忘”或“虚”,都是針對主體轉化的無爲工夫,以便重新整合出更爲完整的活動機制,對此《莊子》以“神”或“天”稱之。也就是説,當“人”失能之後,“天”的機能卻被開啓。此即《大宗師》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27)《莊子集釋·大宗師》,第273頁。天大而人小,當人放下私我的主體計執,他更有了機會重獲大我的天之機能。對於《莊子》的技藝實踐脈絡,“神”和“天”並非意指任何超絶的形上本體或終極真理,神與天也並不指向任何的超越彼岸,反而是在主客之間、物我之間、人和周遭情境之間的融合爲一、渾然一體的“忘我”狀態下,所開發出來的“既自然又必然”的活力狀態。值得提出討論的是,畢來德描述技進於道的“神行”、“忘我”狀態,大體停留在物我合一、主客消融的大塊式描述,以至於物之天理、物之天性對於主體的阻力(其實也是轉化之力),則幾乎完全可以被整合。用筆者上述的概念來説,在畢來德的理解裏,物性的“非同一性”力量,似乎可被整合成同一性力量的狀態。於是畢來德主張“克服物之慣性”,以能達至主體客體的徹底融合,甚至主體和客體的共同消失。例如他在解讀庖丁解牛的主客關係之變化歷程時,便采取這種融合論觀點:
“所見無非牛者”,滿眼都是那一整頭牛。面對那樣一個龐然大物,他只會感到自己有多麽無能爲力。之後,最初這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狀態發生了變化。經過三年的練習,他就“未嘗見全牛也”,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部分了,也就是那些在切割的時候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庖丁已經靈活了,開始戰勝客體對他的對抗了,他所意識到的已經不再是客體對象,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活動了。最後,這一關係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庖丁對文惠君説:“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他練出來的靈巧,現在已經高明到了牛對他不再構成任何阻力,因此也就不再是他的一個客體對象的程度了。而客體的消失,自然也伴隨着主體的消失……“神”不是外在於庖丁的某種力量,也不是在他身上行動的某種殊異力量。這個“神”只能是行動着本身那種完全整合的動能狀態……先從戰勝物的慣性開始……最後,我們完成這些動作可以是毫不費力,完全不受物的限制。有時候,我們甚至也能够達到那種渾整的狀態。(28)《莊子四講》,第6—8頁。
從上述畢來德對吕梁泳水與庖丁解牛的描述,他傾向將“神”朝向身/心/物整合之後所發揮出的最大潛能,來説明技進於道的自由與必然。换言之,神既整合了人的身心於合一,也整合了物我於合一,甚至讓“外在和内在於我們的一同運作的所有力量”都能進入渾然整合狀態。也就是這種渾然整合的純粹力量狀態,讓畢來德主張物的慣性阻力可被戰勝,客體可以完全被超克而消失,而主體從此不再受物之限制,甚至進入了主體與客體皆消失的“自然又必然”之“自由”境界(29)何乏筆最早指出畢來德具有融合論傾向,參見其著《氣化主體與民主政治: 關於〈莊子〉跨文化潛力的思想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卷4期,“畢來德與跨文化視野中的莊子研究專輯(下)”,第41—73頁。。對筆者而言,這種傾向從融合論對技進於道的描述,從合一論對“官知止而神欲行”的描述,屬於“宏大叙事”而不及於“微觀叙事”。由於技藝實踐必然涉及身體與物性的力量辯證,因此我們有必要進到更爲微細而複雜的内部力量之辯證狀態,來呈現物與我的雙向轉化、平等辯證之弔詭複雜性。雖然就庖丁的身體感而言,由於他已從“所見無非牛者”的物我衝突,進化到“未嘗見全牛”的交涉狀態,甚至進入“官知止而神欲行”的遊刃有餘,但技藝狀態中的“神”與“遊”,是否真能完全消除物之他性,徹底整合物性的差異性力量呢?
經由本文先前之論述,“虚而能遊”的新主體狀態之“神行”運動,並非從此以往就一味暢遊於全然無礙、徹底無阻之境界。那種融合論、合一論的描述似乎不免於美學烏托邦的宏大叙事,甚至導致將主客之間、物我之間、順逆之間的“非同一性”力量,給予同一化與静態化。因爲物之天理、天性對於主體的限制和阻力,同時帶來了主體調整與轉化契機,嚴格講,它並非只是消極性的限制原則,它也是引發主體轉變的他異性力量。而當主體能“依乎天理”並且“以天合天”時,此時的官知主體轉化爲“人而天”的神行主體,並與“物之天”産生了“合作”關係。然而這種“合作”而非“對抗”的力量關係,與其被簡單描述爲同一性力量的融然爲一,不如進到力量的微細又微妙之辯證關係來加以微觀。亦即,“以天合天”的合,並非意指人之力量與物之力量的單純合一,反而是要描述物我之間持續性的雙向轉化之“兩行”運動。换言之,物我之間的力量協調合作(此時,物之阻力被轉化爲主體之内部動力),並没有完全取消我與物之間的頡頏作用(亦即物之阻力並没有完全被主體給同一化),甚至唯有保護物之非同一性力量的持續運作,主體的持續(被)轉化才能長葆新鮮。由上觀之,技進於道的融合論屬於宏觀叙事,忽略了主客之間、物我之間,唯有持續保有“非同一性”之弔詭關係與兩行運動,才能帶領我們走向微觀力量辯證之兩行描述。
此外畢來德將《莊子》帶有形上超越意味的概念,天、道、神、虚、渾沌、氣,全部還原回技藝達人身體經驗的潛力發揮來理解。筆者雖認同這一類概念所藴含的超越性不宜透過西方形上學的外部超越來理解,也認同這種力量經驗可還原到身心與事物的協調運作之具體脈絡(物化之天理天性)來理解,可在“物化之道”的身體感知中被重新描述。但筆者並不贊同畢來德對《莊子》氣化力量的狹窄化理解,尤其質疑他對《莊子》氣論潛力的化約甚至取消,可能導致《莊子》思想廣度與深度的簡化。這是由於畢來德擔憂東方氣論傳統被過度神秘化、形上學化,尤其强烈質疑它被濫用來爲大一統集權政治秩序提供一種同一性形上學的世界觀。就此而言,自有他身爲歐洲知識人旁觀者清的批判性觀察。
但就《莊子》文獻所反應的氣化多元論,卻不必掉入畢來德所憂慮的同一性暴力。況且《莊子》對身心的轉化描述,從來就没有隔離於氣體驗,而氣之體驗本來就流通於身内身外。氣之流動性、流通性,使得身心之間、物我之間、天人之間、自然與人文之間,具有不斷交通的辯證性格。氣涉及身中之氣(自體内部的自然力量),也涉及身外之氣(身體外部的自然力量)。《達生》篇技藝達人梓慶的“未嘗敢以耗氣”以便能“以天合天”,《人間世》透過心齋的“聽之以氣”以便能“虚而待物”,身心潛能的發揮都在於向萬物、向世界敞開。正如畢來德自己曾强調的: 調合已知和未知的身體潛能,在於身體是一種没有確鑿可辨邊界的世界。這種没有確鑿可辨邊界的描述,在《莊子》脈絡裏,正和氣通内外的力量體驗密切相關。其實當畢來德將轉化後的“人而天”之身體經驗理解爲“没有確鑿可辨邊界的世界”時,幾乎已觸及氣化領地,只因爲過份擔憂同一性形上學的幽靈復活,所以堅持把“氣”之世界性體驗向度給消除。也由於窄化了真人氣化身體的描述,使得畢來德所描述的身體經驗仍然被封限住,使得“力量”的體驗被狹隘化爲身體主體内部,而未能徹底充盡“没有確鑿可辨邊界之身體世界”的天地浩瀚性格,即他對《莊子》身體經驗之描述,僅停留在“内通(身中之氣)”,而無法“外通(身外之氣)”(30)以何乏筆的觀察來説,畢來德最多僅能肯定個我身體之(内)氣,卻無能從“身體主體”通向域外之氣的“氣化主體”,參見何乏筆《氣化主體與民主政治: 關於〈莊子〉跨文化潛力的思想實驗》,第59頁。而以宋灝的“身體現象學”觀察角度來看,孟柯的力量偏陷於主體個人的内在而發,忽略了力量乃是在身體與世界的共在境遇之間來感應發生,由此批評孟柯的力量無法呈現“雙重發生”與“開啓世界”,參見宋灝《美學工夫與時間之成其爲時間》。而從筆者看來,何乏筆對畢來德的批判,宋灝對孟柯的批判,應該都可連結到《莊子》的氣化身體與氣化世界複雜交織來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孟柯在最近的回應文中已逐漸調整其觀點,有關身體與自然、氣化的關係,他已經有更複雜的辯證思考與調整回應。。
《莊子》之氣,同時也是扮演通達物化、通達天地的關鍵性概念。因爲氣通達於身體内外,才使身體和週遭世界産生無分而分、分而無分的力量交换運動。這一通向域外而使得無内無外的氣化主體之敞開,才能真正完成《莊子》真人身體經驗的十字打開。而氣化主體所通向的天地氣化世界,並不一定會掉入畢來德所擔憂的形上虚玄,因爲《莊子》的天地之氣化世界,其實並不曾脱離“物化”的多元差異之自然世界。换言之,當技藝達人與物遭遇時所唤起的身體力量,若能再通向真人氣化主體的十方敞開,這同時也就意味着,將身體體驗再通達於浩瀚的自然體驗。這也是筆者一再强調的,《莊子》技藝達人的力量身體,還可再擴大擴深爲真人的氣化身體。而此一氣化身體將連綿於自然氣化,從而使藝術家的沖創性身體力量,因通達於自然力量而受到平淡調節。筆者認爲這一自然力量的帶入,正可使藝術家帶有狂迷性格的力量身體,被自然的氣化力量調整爲“迷而不迷”的弔詭狀態。對於這個身體主體與氣化主體的弔詭關係,以後筆者將再透過與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孟柯的跨文化對話,來進一步釐清與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