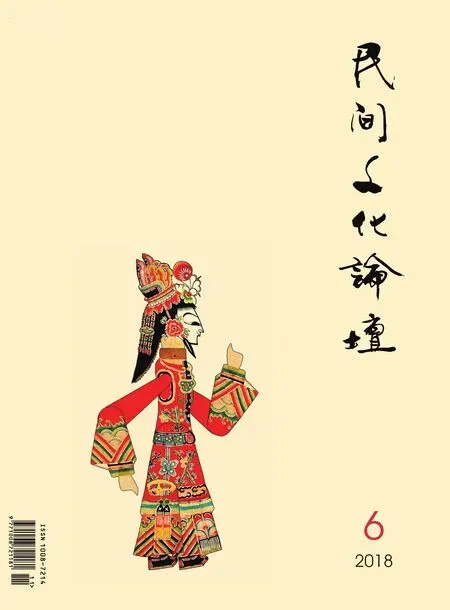影视人类学成果评价体系的理论构想和方案设计
吴..乔.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传统上是以文本(含静态图表、图像)的形式呈现的。例如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但近年来,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载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数据库成果、新开发的学术软件、学术影音成果等。而在人类学领域,典型的例子就是影视人类学作品,即:人类学纪录片/民族志电影①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y film)和人类学纪录片(anthropology documentary)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在国际学界通常等同使用。。下文即以人类学纪录片为例,探讨建立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构想。
一、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影响
在国际学术界,人类学是一级学科,拥有众多分支。目前公认发展最兴盛的两个分支是医学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于20世纪70年代即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学术合法性,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国际学术共同体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的专业委员会之一。影片与文本同等重要成为国内及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共识②影视人类学在IUAES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为IUAES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现任主席鲍江研究员所述。。国外一些名校,如曼彻斯特大学、南加州大学等,授予影视人类学博士学位已有十多年。西方某些国家(如法国)电视台建立了专门的纪录片频道和网络平台,大量播映人类学纪录片和其他类型的真实电影,并将这些作品运用于大学教育。每年世界各国有许多重要的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活动,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美国米德民族志电影节、法国让·鲁什电影节、北欧人类学电影节、荷兰人类学电影节、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等。这些活动每届都收到来自世界各国人类学者的数百、上千部的影片投稿,从中筛选出二三十部播映。电影节上聚集数以千计的学界同行及大量社会各界观众。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力之广,与文本作品的任何学术年会相比都有过之无不及。最近一些年来,随着视频网络、多媒体和VR(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影视人类学作品不但受到学界重视,在公共领域和普通社会民众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加。早些年如法国的《夏日纪事》《我,一个黑人》①《我,一个黑人》和《夏日纪事》均为法国影视人类学名家让·鲁什的作品。前者1958年,后者1961年出品。这两部作品常常被看作“真实电影”的开创性代表作。,近年如英国的《56up》②《56up》是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的名作。他从1964年开始,为英国BBC电视台拍摄了记录片《7 Up》,采访和拍摄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七岁的小孩子。以后跟踪他们的人生,每隔7年拍摄一次。最近的一次是《56up》,2013年出品。这部系列片仍在继续拍摄中。一般认为这部影片用前所未有的巨大时间跨度,反映了现代英国阶级固化、社会上升通道狭窄的现实。,美国的《杀戮演绎》③《杀戮演绎》是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执导的一部纪录片,于2012上映。该片通过刽子手的叙述和扮演,揭露了1965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场至今未受到反思的大屠杀。此片多次荣获影视大奖。其在我国放映后,在第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也获纪录佳片提名。等,都以真实记录的震撼性力量,在学界和社会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所以说,影视人类学是一个与新兴技术紧密结合的朝阳学科,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势头之中。其学术影像的传播更是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有效地推广中国文化。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和现状
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时期起,在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前辈学者就开始在从东北到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中摄制黑白胶片的民族志纪录片。迄今,这批影像素材已经成为反映许多民族半个多世纪以前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社会面貌的珍贵资料。这批影片被公认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奠基之作④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奠基之作,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分会秘书长庞涛所述。。“文革”之后的1977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本领域全国第一个实体学术机构民族学研究所电影摄制组。改革开放后,云南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学人类学影视实践活动,组建影视人类学团队。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于1995年成立影视人类学研究室,成为全国第一个成立影视人类学专业学术部门的单位。同年,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与世界同行接轨。近年来,我国影视人类学界表现更加活跃。全国建立的两个“国”字头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均下辖影视人类学分会。前者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分会”,后者为“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在昆明举办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大会组织了专门的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有6部人类学影片被评为本届大会的优秀影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庞涛的《祖先留下的规矩》和贾丁导演的《家族》这2部中国影片获此大奖。2015年,中国社科院吴乔副研究员的人类学纪录片《难产的社头》获得 “首届北京民族电影展·首届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银奖,并入选第8届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节;2017年,该片又入选皇家(英国)人类学会电影节Festival Film Library单元;同时入选的还有中山大学熊迅副教授的《the last lineage opera in zhouguan village》;以及后来在国内院线上映,声誉票房双丰收的郭柯导演的《二十二》。2018年7月在巴西举行的第18届大会上,中国社科院鲍江研究员当选为新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IUAES)”的“影视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VISUAL ANTHROPOLOGY)”主席。同年,中国社科院再开先例,在正高级研究员的职称评审中将影视作品也纳入学术成果计量,有学者因此成功获评正高职称。这正顺应学科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潮流,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全局眼光的举措。以上种种情况表明,影视人类学在我们国内呈现繁荣活跃的态势;而且中国影视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也日益显著。
影视人类学的独立“学术人格”
文本是传统的学术成果载体,其合法性已经为历史所确立。影片这种新兴体裁与文本相比,在抽象程度和理论概括能力方面确有不如。实际上,行业内均知,影片不擅长(但并非不能)表达抽象观念;而文本则擅长于此。学术影片在某些只产出文本作品的传统学者那里评价甚低,其最主要的一个批评也就在于它“非抽象,不理论”。理论性曾是社会科学的传统基石和最高诉求。但是随着现代学术的进步,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追求目标也有新的发展。今天国际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学的价值不应局限于抽象理论和普适性的规律,更在于对特定“人类生活模式(life style)”的深度呈现①这一观点,参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走访》(The Visit),载于美国《纽约图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年10月18日。笔者将其译为中文,载于《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尤其是民族志作品。为此,需要对“细节(details)”加以强调。而文本无论如何“深描②这里的“深描”指的是格尔茨意义上的概念。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提出深描(deep description)这个术语,指民族志描写不仅限于现象,更要深入描绘当地人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观念。”,仍然是符号性的、抽象的信息传递,挂一而漏万;生活本身是复杂多态,难以系统化、符号化描述的。文本的民族志,只是一个主体(研究者)对另外一些主体(研究对象)的观点的反映,即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③“主体间性”概念源自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哲学,被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所借用,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进行批评,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观念是一种交互反映。。但在这方面,影视有着远超文本的先天优势。影视的动态画面和声音,是迄今为止人类表达手段中唯一的可以称为 “准全息性”的方式。镜头传达了几乎一切细节,几乎一切可观测到的信息,基本达到了对“社会语境(context)”的完整呈现。其丰富程度,甚至超出作者的原初主旨;其真实呈现的客观性(所谓“镜头不会说谎”),也超越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区隔。因此,影视人类学具有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和学理特色。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学术影片在某些具体应用领域(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学术作品的大众传播、各级学校教育),有着文本载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另外,影片作为载体,相对于文本还有三项公认的优势:第一、活动影像的场景性和沉浸性。和文字的抽象概括不同,影像通过海量的具体信息为受众构建一个有利于传递信息的场域,从而使得受众经由通感达成对对象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对信息的了解④这两句话是中山大学熊迅教授提出的,作者赞同并引用他的观点。。第二、对运动状态(人体动作)的呈现⑤文本无法精确地传递和呈现动作,镜头语言是表达人类动作的目前唯一的手段。这一观点,笔者得自与蔡华教授的交谈。。无论是成熟系统的语言文字如英语汉语,还是较为简单的前工业社会的语言文字,都无法精确地描述动态行为,例如舞蹈、武术、手工艺等。这是语言文字先天能力的短板。而影视对此则极为专擅。第三、人类情感的直观呈现。镜头语言在传递“共情性(empathy)”的能力方面也远超语言文字。这是由视觉的预设算法决定的。一秒钟面部表情的特写,对受众的感染胜过千言万语。再有,在现代人类学方法论所强调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知识共建”⑥“知识共建”是近年来人类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卷入式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对这个概念使用多。即人类学知识的获得和产生,并不仅仅是研究者的思想劳动的成果,而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合谋”互动共同产生出来的。方面,影视也是非常适合的实现途径。
综上所述,总体上看,从学理上讲,影视与文本并非谁是谁的补充或附属的关系;它们各具独立的“学术人格”①“独立学术人格”的概念提出者为罗红光研究员。笔者在与他的交谈中接受了这一观点。,互相不可替代。而在现今的“视觉时代”,影像几乎成为社会性的文本被制作和传播,对影像制作和研究的强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职责所在。
影视人类学的工作量和影响力
生产高质量影视作品需要投入的时间和工作量不亚于文本作品,而在社会影响力上则更胜一筹。笔者及所访谈的多位学者,都是既产出文本作品,又产出学术电影的“双栖”研究人员。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个学者全身心投入,先做前期田野,再进行中期拍摄,最后后期制作,产出一部质量较好的人类学纪录片,通常需要不少于一年的时间。其比一篇论文的调研和写作的生产周期,只长不短。在所需的资金量、技能、田野劳动量和团队协同能力方面,更是远超论文。而如果是一个主题系列学术影片,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数年专注于一个族群/社区/社会问题才能完成。这样的例子在国际和国内都不罕见。其比一部学术专著所需投入的工作量通常更多,周期也更长。另一方面,从作品的影响力来看,人类学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往往仅在本学科同行中有人阅读,很少形成社会效应;而一部优秀的影视人类学作品,其影响和传播不仅在本专业,更遍及社会各界,甚至能形成改变社会观念的力量。所以从生产作品所需的工作量,以及作品产出之后的影响两方面论,影视人类学成果都值得与文本成果同等重视。
二、人类学纪录片纳入学术成果考量的难点和理论参照
目前,在我国倡导人类学影片纳入学术成果考量,其难点在于建立一个能获得同行认可,取信于学界,同时又具备较为清晰的量化标准、具备可操作性的考核体系。此前国内其他高校的从业者虽有倡议,均未成事,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尚无现成的这种体系。我们认为,既然主张学术影片与文本成果同样考量,要建立这样的体系也应将文本作为参照。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本成果的评价,虽不常采用自然科学成果的“重复试验”②“重复试验”是自然科学成果的同行检验方式。即:如果某位研究者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宣称做出了某个试验成果,其有责任在论文中写明试验条件和步骤。看到这篇论文的全球同行都可在各自的实验室里按照同样的条件步骤重复这个试验。如果做不出同样的结果,这篇论文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但仍遵循“同行公议”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学术期刊论文。原则上讲,每家学术期刊都应建立自己的分类学者库。在收到一篇投稿后,最重要的一轮评审是“匿名外审”。即编辑部将论文随机发给库中与该文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几位学者,由他们对这篇论文的学术性、创新性、严谨性等价值进行评判,并决定是否刊用。因此,一篇论文如果在专业期刊上获得登载,就意味着它至少已经得到了学界同行对其学术质量的某种程度的承认;而责编和主编的审核,又对其格式规范性和政治正确性进行了认可。同时,期刊的发行,又让这篇论文在人群中传播,并继续受到同行的检验。所以,核心期刊论文作为学术成果,具有较大的说服力。目前我国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无论是在中国社科院还是北大、南大的期刊目录中,都有从一般期刊到核心期刊再到权威期刊、顶级期刊(北大、南大分为A刊、B刊和C刊)的详细划分。相比之下,专著在事先获取同行认可这方面就要弱一些。出版社是一个掌握书号的企业,其通常只对出版物的政治正确性和文字通顺承担审查责任,并不负责学术考评。因此,专著的“硬条件”是作品的学术“体量(专著的字数一般远多于论文)”,而非质量。当然,这并不妨碍负责任的学者在专著中倾注同样甚至更多的精力和心智,以产出高学术水准的专著。以上就是我们影视评价体系的参照。
此前已有的某些提案,将学术影片的正式出版(DVD或闪存格式)或在省级以上电视台的公开播映,当作影视成果的门槛。比照文本成果的评价机制可知,这个标准在学理上有不足。如前理,由于出版社的企业性质,一件作品的出版并不体现同行公议的学术考核,只是起到了政治上把关的作用以及提供了传播的合法途径。而在某个级别以上的电视台播出,电视台固然不仅政治把关,也有自己的一套考量标准。但由于电视台的大众性质,其标准更偏重传播能力,即影片的可观赏性,而非学术价值。另外,电视台播出节目通常只是一次性的:如出版光盘,出版社也通常不负责发行。因此这两种方式对影视作品的传播,在受众的“可获得性”方面,仍然明显不如期刊(无论纸质还是电子版)对论文的加持。
还有一种方案,是将学术影片的评价权给予立项方。即将一部人类学纪录片经正式立项(有立项书和项目编号),并正式结项,且结项评价为“良”以上(有结项书为证),作为影片算作等同文本学术成果的门槛。这一做法的优点在于省事和可操作性强,作者的所在单位不必专门设立评价机制。但也有明显的缺陷:项目出资方未必具备评价一部人类学纪录片的学术水准的资质。即使项目出资方在学术质量上高度负责,每设立一个项目都召集国内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委会来评议,不足也仍然存在:这样的评议会是一事一议的临时组织,难以发育形成系统的、成熟的评审标准和制度流程。长久来看,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避免上述不足,形成长效发展机制,我们认为,与文本成果一样,影视成果的考核也应该遵循“同行公议”这一原则,比照核心期刊而不是出版社或电视台来划定学术门槛。但是这么做的难处在于:期刊无疑是论文的传播与交流平台;而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的影视人类学播映平台(前文提到,某些西方国家有比较成熟的专门的学术纪录片频道)。出于我国国情和影视审查制度的考虑,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建立这样的播映平台。故一直以来,人类学影片没有专门的发行机构,也就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建评审专家库。
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情况正在改善,条件正日趋成熟。随着学科的发展,目前国内的影视人类学从业队伍已经不小,也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知名学者。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红光、庞涛,北京大学蔡华、朱晓阳,清华大学张小军,人民大学(现浙大)庄孔韶,中央民族大学朱靖江,中山大学邓启耀,云南大学张跃等。这些人不但以影视人类学著称,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是高产和有声望的文本作者。而随着拍摄制作技术的普及,青年一辈的人类学者中,具有影视能力、产出影视作品的人更是所在多有。再如,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和实施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09@ZH013)和《中国史诗百部工程》(09@ZH014)。两大项目已持续进行10年。规划中均设立以影视人类学方法为主要手段的独立版块,通过公开招标、邀标和自行研究的方式,已在全国各地立项200余项子课题,结项70余项。其中许多成果影片已经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奖,也造就了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一大批学者投身到影视人类学的行业①这些数据为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和马秋晨提供。。因此,我国目前已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学者来组建外审专家库;也有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的影视作品来支撑年度影展,形成发表所需的规模。
另一方面,诸如“中国影视人类学会”等本学科的组织也日渐成熟。这个学会已经举办过多届影评、影展和年会,也已经形成了覆盖国内几乎所有影视人类学重镇的学术委员会,囊括大多数代表性学者,乃至纳入了媒体界、独立制片人等其他领域的评委,故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和认可度。又如“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经过近年的年会和影展,以及发行电子期刊《视觉人类学论坛》,其学术认可度也正在迅速提升。
因此目前可行的原则就是:依托现有的两家“国”字头影视人类学协会,利用他们的评审专家库进行学术把关。同时鼓励多渠道的播映和传播。下面是我们的具体建议。
三、人类学纪录片纳入学术成果考量的具体设计
设计方案
具体来说,我们有以下操作化规则可供探讨:
一、影视作品入选全国性学术影展/电影节(例如“中国影视人类学会”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影展”;以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和中国民族博物馆合办的“中国民族志电影学术展”),有入选证书;并由正规的音像出版社出版(有书号或音像制品号),或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为门槛标准。一部影片入选此类影展并有此等级的出版或播映,即等同于一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二、以影视作品入选国际性、全球性学术影展/电影节(例如每两年一届的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美国米德民族志电影节、法国让·鲁什电影节、北欧人类学电影节、荷兰人类学电影节、意大利撒丁岛民族志电影节、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等),有入围证书或邀请函,并由国家级音像出版社出版,或国家级电视台播出为更高标准。一部影片入选此类影展并有此等级的出版或播映,即等同于一篇论文在权威期刊(即北大体系中的A刊)发表。
三、以单部影片对应单篇论文,以学术专题系列影片(三部集及以上)对应学术专著。
四、允许乃至鼓励一个学者既产出文本作品又产出影视作品,尤其是对于一个研究主题产出既有文本又有影视的“配套”作品。在计算成果时,同一学者的这两类作品可以等价交换。例如“二篇论文加一部影片”等于“三篇论文”;“一部专著加一部系列影片”等于“两部专著”。
扩展和未来规划
以上标准,均具备以下可扩展性:
1. 全国性的影视人类学学会目前只有两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 ;二是国家民委管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前者每两年举办一届全国影展。不仅评选入围影片,还从入围影片中评出“学会奖”的一、二、三等奖(未来可作为对应论文获奖的“加分”考量)。其已建立了较为稳定和完备的学术委员会,如现任专家委员会的9名成员为:方勇、罗红光、庄孔韶、蔡华、张小军、张跃、邓启耀、孙增田和李松。这样的平台有清晰的学术边界和专业的影像追求。又由于已举办多届全国性影展,其影响力有历史积淀。在这样的学会年会上,我们可以组织评审专家团,采用与论文同样的“双盲”方式对影视作品进行评审①中国影视人类学会正在草拟匿名评审单并征求意见。其采用与核心期刊类似的表格,要求外审专家从7个方面,用五等排序的方式评价一部影片,并给出三选一的评审意见(入选、落选、再议)。评价内容如下:1.选题与人类学主题相关度;2.是否呈现解释性结构;3.是否具备人类学的问题意识/研究问题;4.影片的视觉语言表达;5.材料的真实和扎实;6.拍摄和制作是否符合人类学学术伦理;7.专家建议的其他加分项(请用文字说明)。,得出同行公允的结论。目前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影展,间隔较长。但正如前文所述,影视作品的生产周期也长于文本,国内影视人类学界的成果总产量尚明显低于论文,故影展已敷当下使用。将来随着学科的繁荣,影展举办的频率也应相应增加。而“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虽然成立才三年,但由于频繁的学术活动和电子期刊的出版,也使得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该专委会已经出版的《影视人类学论坛》电子期刊,为未来影视成果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今后可尝试将入围作品放到此期刊的服务器上。请主管部门审查后,在期刊主页提供链接,在线观影。为保护拍摄对象的个人信息,可设立身份认证的会员观影制度。这种方式,比出版社出版光盘和电视台一次节目播出,作品有更强的“永续性”,对观众来说“可获得性”也更好,更类似于期刊对论文的传播和交流作用。而且,这种方式运行成本也低。
因此,今后随着学科的发展壮大,影视人类学的“期刊目录”还可逐年更新和增加,类似于核心期刊目录的更新增补。
2. 国际性/全球性的学术电影节/影展,在国际学界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名录。其虽有增减消长,但长期历史积淀造成的几大影展的“影响因子”是比较公认和确定的,类似于SSCI期刊目录。这个名单,除前文提到的几家外,我们也可根据学科的发展及时更新、定期调整。另外国际上泛纪录片类型的影展/电影节数量非常多。为强调作品的学术性,我们只考虑那些“人类学纪录片/民族志电影”的专门的学术影展。
3. 如前所述,与核刊论文不同,专著成果体现的是体量和政治把关。其并无事先的同行评审。同理,与专著对等的专题系列影片,也应相应降低同行评审门槛,以正式出版或省级以上电视台播映为最低标准,不必要求入围影展或获奖。当然,如果在出版的同时又入围影展还获奖,在计算学术成果时可予以加分考量,例如等同于“优秀专著”。
结 论
影视作品入选影展/电影节,体现的是同行评议对学术质量的把关;同时要求正式出版或电视台播映,即兼顾了影片的政治把关,又在尚无专门频道的情况下考虑了影片的发行、传播和社会影响。做到这三点,影片与核心期刊论文的审核和发表已经等同,且同样符合“学术为重”的原则。这是我们建立影视人类学成果考评体系的基础。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具体设计,我们相信:影视人类学具备独立的学术人格和普遍的学术价值,应该且能够建立起以“同行公议”为基础的、可操作的评价机制。当然这需要学界同行共同的努力和长期的发展完善。但这个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对于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