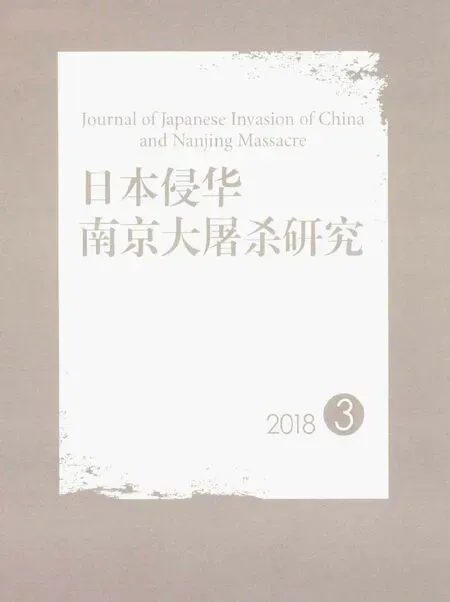拒敌·内斗·生存: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考察*
刘志鹏
抗战时期,山东沦陷后,在日伪控制的重要城市及通衢要冲外,还有面积广大的日伪、国共及地方势力多方杂处拉锯的灰色地带。相持阶段到来后,战事稍事缓和,国民党即开始着手从组织机构调整、干部选任与领导效能的发挥上,重建和整理沦陷区党务。本文从山东省党部切入,尝试通过对省党部委员群体的任用与流动、工作效能、内部关系及日常生活等问题的梳理,揭示战时沦陷区环境下国民党基层党务干部的生存状态,以此希望为我们认识国民党因应沦陷局势在地方党务调试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提供一个视角。①国内对抗战时期山东国民党组织进行梳理的主要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近代中国》1994年第104期),初步宏观扫描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山东的组织概况及党务活动,而针对党务干部群体及其党务运作情形并未详细考证。
一、任用与流动——国民党中央对山东党务的配置和督导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对山东党务的配置主要体现于省党部委员群体的任用方面,其沿革大体可以分为韩复榘、沈鸿烈、范予遂和何思源四个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前,国民党中央规定山东省党部实行执监委员会制,执行委员有韩复榘、李文斋、秦启荣、张瑞璜、蒋伯诚、梁醒黄、刘心沃等7人,其中常委为韩复榘和李文斋,胡庭樑为书记长。②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3年版,第101页。1938年,为加强省党部在地方政府中的领导,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对于省党部采用主任委员制。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国民党中央依照此原则于7月改组山东省党部,派沈鸿烈为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文斋、秦启荣、梁醒黄、刘心沃、林鸣九、李子虔、牟希禹、赵季勋、王立亭、张维中、李先良为执行委员,并以李文斋兼书记长。及至1938年9月,山东省党部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今属山东阳谷县)重新成立。②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关于此时期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的基本概况,首先从年龄上看(以1938年任职计算),除主任委员沈鸿烈56岁、委员李子虔42岁外,余均出生于1900年代,在35岁上下,正值青年血气方刚之时。由于沈鸿烈身兼省主席及省保安司令,而李子虔又久未到职,可以说抗战时期山东国民党党务掌握在这批35岁左右的年轻党部委员手中,他们成为山东沦陷区开展党务活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其次,以籍贯分布而言,除沈鸿烈为湖北籍、李先良为江苏籍外,其余省党部委员皆为山东籍,显示出地方党务由本土人发展的优势。再次,从学历背景分析。除沈鸿烈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牟希禹毕业于坊子铁路警察所外,其他均毕业于国内大学及省立师范,侧面反映这一时期党务领导者皆为较高学历,有相当的教育素养。
受战时环境影响,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更替频繁,人员流动很大。1941年8月,沈鸿烈赴重庆述职后,国民党中央改派组织部秘书范予遂接掌。迨至范予遂派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后,党部委员群体已经变化泰半,其中阎实甫、宋从颐、牟尚斋、刘道元、陈惕庐、李子虔(开缺后复任)等人均系新任,原党部委员仅留有秦启荣、牟希禹、赵季勋、林鸣九、李先良5人。③张俊华:《国民党山东地方组织的活动》,朱铭、王宗廉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事件:北洋政府时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范予遂任职期间,党部委员先后增派周从政、孔祥哲、裴鸣宇、潘维芳、赵士伟、李汉三、李廷俊等7人,牟希禹、阎实甫、潘维芳先后兼任书记长,变化幅度不可谓不大。④范予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1944年底,国民党中央令何思源以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山东省实行战时体制——党政一元化,省党部委员牟尚斋(兼书记长)、林鸣九、赵季勋、李汉三、裴鸣宇、刘道元、李郁廷、田谊民、许星园、刘汝浩、臧元骏、裴昌会(未到任,由李延年接替)等全体任省府委员。⑤《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版,第628页。其中新派委员即有李延年、臧元骏、许星园、李郁廷、刘汝浩、田谊民等6人。这一时期的党部委员已与抗战初期完全变更,但这些委员成长于敌后沦陷区,年龄大都在40—50岁之间,具有战时工作经验。同时连主任委员何思源在内,省党部委员均为山东籍,更加表现出本地人掌控本地党务的特点。
至于国民党中央对于省党部委员的管理与督导,虽然明文规定省党部委员奉委后,“应即遵照中央规定程限,到达各该党部所在地参加工作”;就职后“应不避难险,努力工作,不得敷衍懈怠,或畏缩不前”;“非因职务关系并经中央或主任委员之核准,不得离开工作地区”;“除中央认为必要时明令更调外,不得托故请辞”,⑥《各省市党部委员服务简则》,《中央党务公报》1939年第2期,第213页。但是因敌后情形复杂,多数情况下难以做到令行禁止。如1939年王立哉受国民党中央任命党部委员后,长达两年才到职。接替沈鸿烈任职的范予遂,于沈离职6个月后始于1942年2月自重庆动身抵达安徽阜阳,迟至5月才进入鲁南山区省党部驻地。仅年余,范再回重庆无意返任,经朱家骅劝慰并由蒋介石召见嘉勉后,乃回返阜阳。⑦1943年初,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省政府被迫东移,经安丘、莒县,至日照和诸城边境。7月,鲁苏战区总部和省政府南迁安徽阜阳后,党务大受影响。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范予遂赴大后方,省党部则暂留省内,机关由日照、诸城边境移驻昌乐。为了与省政府取得联系,省党部在阜阳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参见张俊华《国民党山东地方组织的活动》,朱铭、王宗廉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事件:北洋政府时期》,第181页。范见阜阳政治环境更复杂,又再三请辞,终于1944年底获准请辞,省党部由牟尚斋代理主任委员会。⑧《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第623页。尽管国民党中央明令省党部委员违反规定者,“应予撤职,并酌量情节,予以停止任用之处分(停止任用期间为一年至三年)”;擅自放弃职守者,“除撤职外,并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①《各省市党部委员服务简则》,《中央党务公报》1939年第2期,第213页。,但实际执行中却绵弱无力。抗战初期,省党部委员李子虔就因久未到职为中央开缺,然1940年9月李子虔又复任党部委员。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同样,国民党中央还规定,对于受停止任用或开除党籍之处分的省党部委员,“由中央通知政府转行所属各机关一律不得任用”。③《各省市党部委员服务简则》,《中央党务公报》1939年第2期,第213页。然而1942年3月周从政受国民党中央委任后,因8个月内久未到职被免,却于1943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以上系列违反规定情形,虽缘于战时种种因素,但鲜有受处罚警戒者。此外,国民党中央通告“凡党部委员营私舞弊者以后应交军法机关办理,不得以撤职或交普遍司法机关了事”。⑤《通知党部委员营私舞弊者应交军法办理》,《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5期,第475页。这些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基本没有付诸实施,对党部委员很难有约束力。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山东省党部形同虚设,与中央党务的联系,多靠王立哉、李文斋等人,王大部时间在中央所在地,李大部时间则在山东。⑥《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5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版,第3052页。山东省党部恢复后,国民党中央着即策划省党部委员实行分区督导,重建鲁中区、鲁东区、鲁南区、鲁西区、鲁北区、鲁东北区、鲁西北区、青岛区、胶济铁路9个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分别由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牟希禹、朱永宝、刘心沃、赵季勋、林鸣九、梁醒黄、李先良、宋从颐任党务指导专员,以实现对全省党务指导工作。⑦张玉法:《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近代中国》1994年第104期。1940年,国民党中央鉴于敌后党务活动隐秘、范围狭小,又把山东划分为24个党务督导区,指派党务督导员进行督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极其重视加强北方党务,对于“冀鲁二省增加经费,添派干员为督导员,分区发展党务”。⑧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53页。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王子壮曾谈及敌后精干党务人员的缺乏,“目前回省为一较危险之工作,因此人不易得”,“山东需用干员十六人,余现虽多方探求,完全合格认为满意,究为少见”。⑨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53页。由于省党部委员不敷分配,国民党中央有意在全省设立办事处以分别统领各地党务工作,再加上范予遂初到鲁南时,亦颇欲有所作为,乃决定设立鲁东、鲁西、鲁北三个办事处,分别由省党部委员牟尚斋、赵季勋、刘道元为办事处主任。后鲁西办事处主任改由委员李汉三代理。鲁东办事处主任由中央组织部核派林毓祥担任。⑩《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第623页。1945年4月山东省党部又成立6个区办事处,由省党部委员李郁庭、田谊民、李汉三、刘汝浩、赵季勋、林鸣九分任办事处主任,管理17个行政督察区所辖各县,至11月撤销。⑪⑪《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一九四五年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档案,山东省档案馆藏,J001—01—0058。可见,国民党中央对山东党务尤其是省党部委员群体的配置和督导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
二、工作效能——省党部委员群体的敌后抗战
抗战伊始,除韩复榘为保存实力逃避西南外,省党部委员大多分散组织游击抗日。尽管受到战争阻隔及经费无着等影响,此时省党部委员“李文斋、刘心沃等人,在曹县发动武装民众纷起抗敌,约有三千余人;张瑞璜等在阳谷、寿张、范县、郓城一带约有七八千人;秦启荣、黄华堂于邹县、滕县、峄县、新泰一带约有四五千人”。①《山东省党务状况》,朱家骅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301—01—06—056。迨至沈鸿烈到任后转退为进,“由徐州进入鲁西,推动省政。这位六十高龄的主席,算是全国以主席身份进入沦陷区发动抗战的第一人,其艰苦卓绝的精神,真令人钦佩。后来山东方面,能够在敌人所占点线之外,掌握住沦陷区的全面,不同平津、河北的弃守,这种功劳,实不容忽视”。②李先良:《抗战回忆录》,乾坤出版社1948年版,第16页。与沈鸿烈身兼党部主任委员不同,范予遂唯掌党务,所能指挥者,仅有阎实甫、潘维芳,“曾先后派遣二人到李仙洲处敦促积极入鲁,终究未达到目的”。③范子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72页。虽然在日伪密布的艰苦环境中,附逆叛国者多有所在,然而以拓展党务为责任的省党部委员群体鲜有投敌者。同时,应当看到在国难当头,省党部委员响应“抗战建国”,挺身而出积极领导敌后抗战者不乏其人。在山东各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党部委员即有鲁南的张维中、秦启荣,鲁北的何思源,鲁西的李文斋、梁醒黄、刘心沃,鲁东的李先良、赵季勋等。
抗战中期,鲁南山区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的活动中心,亦即省会区。坚守鲁南的省党部委员有张维中、秦启荣等人。王子壮在日记中谈到张维中“七七战起,回鲁适值沈主席注意民众工作。与之谈,深为器重,大加擢用,……沈主席依为左右手,凡国家民众之工作悉委之,是彼之一生出处,无不以民众工作奠革命基础为其努力之核心”,称赞其“绝对忠于理想,一生不移不惑,宁忍痛忍饿以赴之者,余现在之朋友中维中一人而已”,然1939年日军扫荡东里店时“竟历尽卒劳,为敌机轰炸以去”。④《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4页。孤悬鲁北抗战的为何思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进入天津意租界逮捕了时任省政府教育厅长兼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的夫人及4个孩子作为人质,迫其投降。当时何思源在鲁北垦区经常食宿无着,与部属一起喝苦水,吃豆粒。⑤石金生:《何思源在鲁北》,《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何思源不顾个人与家庭安危,拒不接受日方的威胁利诱,并当众撕碎了日军的劝降信。⑥丁岚生:《何思源在山东的活动》,《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⑦ 宋振春:《何思源与山东抗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同时,何思源利用所谓的“反人质”事件,扣押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70余人作为“反人质”,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和日军施加压力,成功解救家人。⑦1942年3月8日,日伪军扫荡鲁北惠民一带时,党部委员许星园(时任鲁北行署秘书处处长)被俘,后设法脱险。⑧丁龙嘉编:《黄河咆哮: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民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鲁西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党部委员先后有李文斋、梁醒黄、刘心沃、李汉三等。1938年李文斋出席国民党中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受到蒋介石召见,“以鲁南为重要基地,嘱其早归”,李文斋“明知路经敌伪地区,异常艰险,仍服从总裁命令毅然成行。……卒能安抵鲁西展开工作,予省政极大助力。”⑨《李故立法委员文斋先生事略》,《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第62页。
鲁东地区则以党部委员李先良为旗帜进行抗日斗争。沈鸿烈与李先良本同为青岛市党部常委,在抗战初期青岛实行“焦土撤退”,采取迫日撤侨,破坏青岛日厂财产等措施。国民党中央称之为“是开战以来,撤退各城市最光辉的一次”,并对担任市长的沈鸿烈特予嘉奖,李先良亦因负党务责任,受到各方赞誉。⑩李先良:《抗战回忆录》,第15页。及至沈鸿烈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青岛特别市党部被并入山东省党部,李先良亦被任命为省党部委员兼青岛区党务专员。初随沈主席奔走于鲁西、鲁北工作,后因省府及省党部即将转入鲁南地区,李先良乃往鲁东地区主持抗战工作。1939年间,鲁东地区尤控制栖霞、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等完整县,自1940年起各县城相继沦入敌手,李先良则以鲁东行署主任指挥军政,在乡间发挥游击战的力量,以维系人心,推行政令。为了要矫正游击部队因利害关系所发生的摩擦、冲突,保持正规的体系和优良的军风纪,李先良对之“施以党的训练,使其了解主义的政策和抗敌的意义”。①李先良:《抗战回忆录》,第23页。李先良为发展青岛游击武装,专门成立隶属鲁东行署的崂山独立营,并调一百余名干部到行署所在地莱阳受训。因李先良兼任鲁东区及青岛区党务指导专员,即从中“挑选五十人,举办党务训练班,施以一个月的训练,使之接受党的智识,提起革命的精神。毕业后就编成四个连,以两个连保卫行署,以两个连回崂山打游击”。②李先良:《抗战回忆录》,第65页。这批游击干部的训练,为日后在青岛坚持游击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42年以前李先良仍能在鲁东坚持抗战打击敌人,撑持这一艰难的局面。及至鲁东行署撤销,抗战局面顿趋恶化,李先良乃奉中央任命代理青岛市长,遂由莱阳率部转入青岛郊区进驻崂山,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华严寺作为我们的战时市政府,以太清宫作为军事干部及保甲长训练的基地,以白云洞为修械所,以太平宫为军需品粮秣库”,作为对抗日寇发号施令领导军民抗战的中枢,期间对敌进行大小战役78次之多。③李先良:《李先良回忆录: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国民党中央为顾全“抗战建国”大局,督促省党部委员坚持敌后抗战,除抗战伊始就正法擅自逃离战场的韩复榘外,嘉奖工作努力的党部委员,如李文斋、何思源等均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和嘉勉,其中对于战时遇难的党部委员更是优待有加。
抚恤金是衡量国民党中央对省党部委员群体抚恤程度的重要标志。1939年6月,因敌机轰炸东里店,重伤殉难的张维中即得到国民党中央三种抚恤金,一部分为先拨治丧费1000元,一部分为一次恤金1000元,另给一等年恤金600元,直至其子女成年。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这一抚恤金后来也水涨船高,至1943年国民党中央发给秦启荣的一次恤金增加到5万元,另给一等年恤金也涨至900元。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7册,第226页。除此之外,国民党中央还明令褒扬,对其事迹大加宣传。王子壮曾撰张维中传略,并将张维中和秦启荣的事迹送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尽管战时省党部委员牺牲者所受抚恤较为优厚,但是真正能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毕竟为少数。
三、内部纷争——省党部委员群体间的派系冲突
派系是组织内部成员因主张或利益等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一般而言,派系的规模不大,其组成大多依靠与派系领导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同乡、同学、血缘、亲缘等相结合,但是结构松散,领导人对于成员没有约束,部分成员在各个派系中游走。⑥刘维开:《〈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受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的影响,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间亦派系林立。韩复榘作为地方实力派在战前即与省党部委员矛盾重重,以致发生“张苇村事件”⑦关于此案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张苇村为韩复榘秘密派人所杀,另一说为张苇村因倾向韩而被国民党中央派人刺杀。,韩与省党部人员交恶,借机处死省党部调统室主任谌峻岑,党部委员李文斋亦受牵连被韩扣押,“后查无佐证,始释放”⑧《李故立法委员文斋先生事略》,《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第62页。。蒋介石始终对韩复榘放心不下,派心腹蒋伯城作为省党部委员秘密监察韩复榘,并在韩因弃职逃跑受处决后整顿山东党政公务。
抗战之前韩复榘作为地方实力派仍能自恃武力与蒋介石派驻山东的党部委员相抗衡,抗战进入第二年之后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及全国的领袖地位的正式确立,反蒋派系则相继隐退。山东境内党部委员间派系之争亦不再是反蒋派系与拥蒋派系之争,而主要表现为拥蒋派系内部的彼此冲突。尽管蒋介石于1938年春夏之间同时宣布取消力行社和CC系的“青白团”两大派系,但两派又以“党方”与“团方”(三青团)的对抗形式延续下来,更以所属中统与军统的特务活动针锋相对。①王奇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再加上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派、国民党中央的政学系及抗战时期新兴的朱家骅系,致使战时国民党在山东的派系之争日趋激烈。1939年5月18日,王子壮直言国民党组织缺陷,“上级对下级干部从未予以绝对之信任,则努力者又或以小团体之关系彼此能力为之抵消,民众工作为之迟怠”。②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188页。
山东省党部重建后,沈鸿烈总揽党政军大权并安插亲近之人,由其旧属李先良坐镇鲁东主管党务。同时又派卢斌为鲁东行辕主任,据李先良称“卢氏原先为胶济路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在中央调查局工作有年,人极干练。抗战军兴,卢衔中央之命往胶东发动民众抗日,因卢做事泼辣而多谋,又与沈主席同为湖北同乡,不久即为沈主席拉任鲁东行辕主任,付以大权。”③李先良:《李先良回忆录: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第5页。然不久即遭到厉文礼等国民党军统系派人袭击殒命,是为“鲁东行辕事件”。李先良事后言及“行辕袭击事件发生之日,幸本人已往海阳边境之发城授课,否则住在行辕之招待所,或遭意外”。尽管前往鲁东视察军事的沈鸿烈内侄亦在行辕被执杀害,但限于党派之纠纷,权责之干涉,沈对于八区专员厉文礼仅以“口头之申斥而已”,后鲁东行辕主任由李先良接替。④李先良:《李先良回忆录: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第5页。同时,沈鸿烈作为党部主任委员与书记长李文斋本“有私交”⑤《李故立法委员文斋先生事略》,《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第62页。,旋“因撤换县长事,及李怀疑沈与共产党有来往,二人发生矛盾”⑥郭崞:《鲁西名士李文斋》,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上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导致李文斋调回重庆,沈鸿烈“以二千元赠行,先生以滥支公款拒不受”⑦《李故立法委员文斋先生事略》,《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第62页。,由此显现党部两负责人亦非团结。作为东北军出身的沈鸿烈并非蒋介石的嫡系,然而其能在山东掌握大权并能与国民党省党部李文斋以及军统的人物,还有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等相抗衡的因素,据他的副官朱子明透露,主要缘于“后台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机要秘书陈布雷”。⑧张希周:《我所知道的沈鸿烈》,沂水县政协文史委编:《沂水县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第103—104页。以此可知战时国民党中央派系之争已经延展至山东省内。1940年9月10日,王子壮根据杨沛如所谈山东党务情况,慨叹“我在鲁省之政府沈主席不了解新式作风,故不能有丝毫之建树。至党部方面人才太少,学识又差,更不足以言领导民众也。以故与日伪、共党奋斗二年,处处失败。如不觉悟,彻底更张,则山东必将成河北之续,我党政人员绝难插足其间也”。⑨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254页。
原与二陈关系较为亲密的朱家骅自从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及组织部长后,就开始自树一帜与CC系分庭抗礼。据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⑩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133页。李文斋出席国民党中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欲返鲁南,“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先生对先生期望甚殷,认此行任务艰巨,请自珍重,中央当鼎力支持”,⑪⑪《李故立法委员文斋先生事略》,《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第62页。可谓朱在山东地方培植个人势力之始。范予遂作为朱家骅所派人员,离鲁返渝后遭到CC派分子“到北平勾结汉奸”的攻击,决心辞职,但受到朱家骅和丁惟汾的劝阻,称“你辞职正是中了诬告你的人的诡计,他们不是专为攻击你个人,而是想赶走朱家骅夺回组织部”。1944年初,范予遂经西安洛阳而达省府所在地阜阳,却坚决拒绝朱家骅再三催促回鲁的要求,以致其“在阜阳的多半年期间,比较清闲,无事可做”。①范予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第76页。6月,得知组织部长由朱家骅换为陈果夫,又复电朱家骅、丁惟汾辞职,陈果夫即派何思源继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②范予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第78页。
至于何思源就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子壮认为“系果夫一手制成”,其曾长期工作于山东并形成“曹州系”。③1944年8月23日,王子壮以《曹家庄之作风》为题指出,“此一系人以曹州为中心”,“抗战发生,一部分投敌伪,组织山东省市政府,美其名掩护,以何思源为中心则与重庆政府之二陈系相接纳,复得本省之党政大权”。参见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337页。先后就职省党部委员的刘道元、许星园即皆曾任何思源秘书,以招致原属三民主义大同盟等丁惟汾系人员范予遂、王立哉、王子壮等人产生嫌隙。王子壮认为何思源得以独应其选,“果夫固然推荐,而彼之欺骗亦实有力于其中”,并指出其欺骗总裁“对地下军最有研究”,“总裁信以为真,遂决定以全省党政军责任畀彼一人”。④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454页。最后竟尖锐批评其,“素善作官,不惜以种种方法达成其目的,现当国家最危险之时,犹复以猎官之手段作此欺罔之行,吾真不知彼将何以善其后!果夫以为曹州系人物为忠实,不惜以大多数人曹州人居此次省政府省党部之要津,而殊不知彼等固有狡兔三窟之技,与敌伪亦非并无往还,以何在鲁抗战数年,颇有人以彼与敌伪通声气者,万一中央形势不利,彼等或有投敌之可能。目前在中央固可以增高地位,月领数百万元,胜利亦可作独霸鲁省之贤也”。⑤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455页。然王立哉“在鲁倍极辛劳,而以人事之复杂,又致诽谤造谣无所不至”,最后仅得一中央秘书处专门委员。⑥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337页。战后何思源“因其仍本一贯作风,以曹州系统为中心,专以位置已系,致引起若干人之不满”。⑦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10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334页。可以看出,在省党部人员任用上呈现出山东籍人士内部的矛盾,大有丁惟汾系与所谓曹州系分庭抗礼之势。
四、日常生活——沦陷区省党部委员的吃穿用度
抗战时期,由于生活经费来源困难,造成深处敌后的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的日常生活不同于往日。抗战初期,省党部委员经费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拨付,进入鲁南山区之后“不复再能陆运,就改为空投,其任务系经由第一战区来执行”。1939年秋,空投最初约2、3月一次,翌年因法币贬值,所需经费增加,遂改为1或2个月空投一次,此间“经费从未感到拮据,空投亦从未发生过意外”。⑧刘道元:《抗战期间山东省会区》(上),《山东文献》第11卷第2期,第21页。自在东里店及吕匣店子建立省会区时期,“不分官阶高低,职位大小,……一律法币30元”。“另每人发给草绿色夏冬服各一套。除个人衣食之外,没有任何消费开支”。尽管“法币在后方各省,1939年下半年开始贬值”,但“在省会区迟了一年方有此一现象”。以致“30元的法币维持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而且1940年起改依国民党中央标准发给,“山区里的物价上涨迟,后方待遇提高快”。⑨刘道元:《抗战期间山东省会区》(下),《山东文献》第11卷第3期,第53页。到抗战中后期,生活情形渐有转变,由于物价暴涨,生活奇缺,再加上国民党中央通令省党部委员“已由中央发给办公费各一百元,自五月份起,除薪俸外,凡在省市党部预算内,支领之一切补助津贴等费,无论已否列入预算,一律不得支领,以减少地方负担。”⑩《令知省市各党部委员除薪俸外不得支领一切补助津贴等费》,《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6期,第106页。这使得处于山东敌后的省党部委员生活益加艰难。
在鲁南省会区战事稳定情况下,党部委员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当充裕的。以沈鸿烈在沂蒙山区的日常生活为例,“沈鸿烈自奉俭朴,经常吃小米煎饼、馍馍、农村做的小豆腐,或者吃点鸡蛋、萝卜、咸菜,大米很少见到。如果宴请客人,菜馔非常丰满,虽无山珍海味,但鸡、鱼、肉等是满盘盈碗,入门大嚼,达到宾主欢欣。”沈鸿烈所谓处事之道为“对己要俭,对人要奢,万勿寒酸,使人不快”①章棣:《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但是一遇到日伪扫荡,省党部委员则四处躲藏,寝食难安。如1939年夏东里店突围时,省党政人员大部安全转移,“唯沈鸿烈被敌冲散与警卫部队及卫士脱离,只有随身副官一人冲到广合峪山上的一个羊圈里潜伏。敌人走后,由附近村民送给他一套农民服装穿上,每天送给饮食,就这样在羊圈里呆了多日”。②沈尹:《敌后游击四年》,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抗战中后期,据刘道元描述省党部办公地址在青崖南庄,“委员除牟希禹、秦启荣、刘道元、田谊民、刘汝浩外,余多不在省会区”。③刘道元:《抗战期间山东省会区》(上),《山东文献》第11卷第2期,第23页。总之,省会区的党部委员同其他党政人员一样,“如与抗战前后来比,算是苦。如与大后方各省来比,不能说是苦。以抗战前后期言,前期不算苦,后期是较苦了。省府迁皖之后,员工不算苦,敌后人民则较苦。处于这一大时代的人,在信心支持与行动斗争之下是不会感觉痛苦的,若由当前人看起来,将是苦不堪言的”。④刘道元:《抗战期间山东省会区》(下),《山东文献》第11卷第3期,第58页。
山东作为沦陷区,在日伪占据交通干线及城市要点的情况下,日常交通变得非常困难,省党部委员进出省部与发展党务均须相当之勇气与智慧。韩复榘为保存实力逃避日军之后,沈鸿烈乃用“蘑菇战术”由鲁西、鲁北、鲁东,而后在鲁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范予遂进入山东境内则颇费周折,首先化装用樊世昌为代名编造敌伪区的通行证——“良民证”,并由省政府派职员祝廷林引路,“于1942年5月间自阜阳动身,从宿县乘火车到济南,换胶济路车到张店,再换火车到博山,然后由伪军护送到新四师吴化文的防区,再由吴化文派人送到省府所在地临朐辖境的”。⑤范予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第72页。因为“刺于案”,沈鸿烈于1941年秋返回重庆。原计划由吴化文派一个团兵力护送,“据说吴不同意,只答应派一个营送到阜阳。沈一跺脚,当面辞退了,改由沈尹的教导团护送的。沈鸿烈由永城过陇海路时受到日伪袭击,损失很大。他的电务总负责人沈士祥和一个姓赵的被打死了,最后总算回到重庆,不久担任农林部部长”。⑥张希周:《我所知道的沈鸿烈》,沂水县政协文史委编:《沂水县文史资料》第6辑,第102页。就连省党部主任委员行动都如此不便,普通省党部委员的活动方式及范围就可想而知了。
处于敌后艰苦环境当中,日常生活已属困难,如若出现伤病则更为危险致命。省党部主任委员范予遂就因从阜阳来鲁途中跌下马伤了左手,在“省会区”无法医治,以致1943年春节之后范“一个人到北平去治病”,并特意到胶县车站“由一个伪军队长派他的弟弟”送其上车。⑦范予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第72页。同时,生活于敌后的省党部委员如遇有紧急家事也难以从速处理,如李先良于1942年往鲁南省府所在地临朐办理交代返途经寿光期间,接到内眷自上海来信,“母亲忽患重病,人事不省,经延医打针后稍痊,但病势仍重……”,两星期后又忽接得友人电“伯母于七月十四日逝世,望节哀顺变”,这对于幼年丧父,“既无伯父,终鲜兄弟”,长期远离亲人居于敌后抗战的李先良来说有丧难奔,犹如晴天霹雳。而李先良自称“从前母亲在的时候,不敢轻言牺牲,抗战的过程中,终是抱着幸存的心理,期望母子团圆,重叙天伦的怀念;如今便没有牵挂了,准备随时可以牺牲了”。⑧李先良:《李先良回忆录: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第52页。停驻在寿光居丧五六个月期间,李先良由初期的心灰意冷,不欲问世,到最后以“为抗战救国而牺牲”成为继续抗战的精神支撑,促其重回鲁东莱阳,更由莱阳率部众往敌寇基地青岛崂山腹地长期游击抗战。
在山东敌后物质匮乏的情形中,也有党部委员利用读书、著文等精神方式充实自我。沈鸿烈在沂蒙山区稍有时间就抓紧读书,曾阅读《曾文正公全集》、《管子》等书籍。在读后与人交流,谈及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名将,特别崇拜曾国藩的“步步为营”的办法和做人做事的方法,却把太平天国说成是“叛逆集团”。①章棣:《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67页。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办的纪念会历来是虚应故事,但沈鸿烈在1941年纪念七七事变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作报告时流了眼泪,甚至触景生情撰写挽联:“成仁曰仁成义曰义夙怀壮心报祖国;要枪无枪要人无人空洒老泪奠忠魂”,可见其精神上的压抑。②章棣:《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67页。李先良在寿光居丧期间曾写《思母记》,把孝经、礼记中的精理加以引证阐发,书成约5万言,为其痛苦中的真情记载,然这一著述不幸在日伪大扫荡中遗失了。③李先良:《李先良回忆录: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第54页。李先良亦认识到抗战不能没有理论,一方面要与敌寇的“大东亚主义”理论相对抗;另一方面需要用理论号召民众,控制人心,防止抗战部队变成土匪部队。李先良在鲁东讲演了不少的抗战理论,写了不少的文章,自称最发挥效力的,就是一本自著《总理遗教概述》,约5万余字,“以抗战到底来阐述民族主义,以真正民权主义来阐述民生主义的真谛,批驳敌伪开发大东亚的经济理论。这一部书在鲁东各县、各学校,无不采用为教本,甚至鲁南亦多采用,确实发生了极大的作用”。④李先良:《李先良回忆录: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第50页。这些都体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沦陷区的精神生活状态。
由上观之,抗战时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构成变动较大,在国民党中央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发展党务,领导“抗战建国”工作,为敌后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抗战时期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但在恶劣环境、自身素质及内部纷争等因素的影响下,于国民党党务的推进相当缓慢和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日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