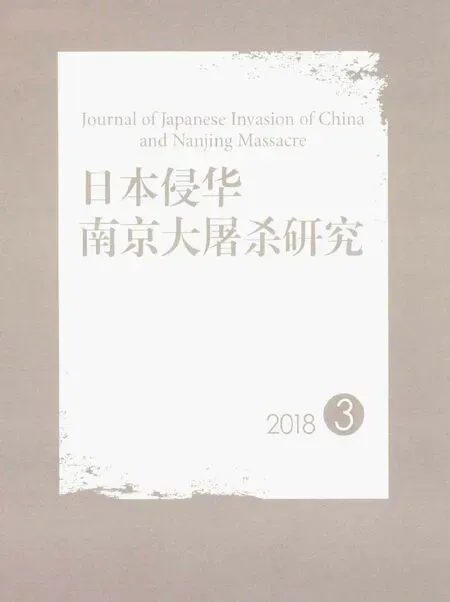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兵要支那语》探究*
寇振锋
随着甲午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及一般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出现了大量增长的趋势。自1894年8月开战至年末的四个月时间里,日本出版发行的纯军用汉语教科书至少有8部,准军用汉语教科书有6部,也就是说与军事扩张及侵略密切相关的汉语教科书至少发行了14部之多。平均每个月出版3.5部,其增速可想而知。①寇振锋:《甲午战争与日本军用汉语热探究: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
《兵要支那语》就是其中一部颇具代表性的日本纯军用汉语教科书。该教科书初版发行于1894年8月7日,正值甲午战争开战6天后。该教科书也是甲午战争开战后的第一部军用汉语教科书,而且编者为日本的中坚部队,即日本近卫军中的劲旅——近卫步兵第一旅团。
日本学者认为,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联的、真正的汉语会话书籍始于《兵要支那语》的刊行。②鱒澤彰夫┍日本陸軍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の形成┘、『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别冊第18集、1992年、130頁。可见该教科书的前瞻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学者李无未在《日本汉语教科书会汇刊(江户明治编)》一书中也收录了《兵要支那语》,并对其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概述,③李无未等:《日本汉语教科书会汇刊(江户明治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可见学者们开始关注该教科书。然而,目前学界尚未对该教科书予以详细考证,尚无学者言及增订再版《兵要支那语》。
那么《兵要支那语》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汉语教科书,其编者、校对者、版本以及内容等情况究竟如何?这尚需详细考证。对于该教科书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日本军方对汉语的重视程度,同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汉语教科书编写方面的诸多问题,而且对掌握日本在战争期间发行军用汉语教科书的脉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编者及校对者
所谓“兵要”是指有关战争的战术或战略上的系统知识,是军事之根本。从《兵要支那语》这一书名可知,日本军方充分认识到汉语在军事战略及战术上的重要地位。换而言之,编者无疑设想该教科书将在甲午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兵要支那语》的编者署名为“近卫步兵第一旅团”。近卫步兵第一旅团的母体近卫师团为拱卫京城的卫戍部队,该部队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其司令部设在东京,战时可作为野战军出征。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下设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其官兵是从全国优秀青年中选拔出来的。当时日本青年均以在近卫师团从军为荣。该师团参加过甲午战争、平定台湾、日俄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资助广部精于1879年出版汉语教科书《亚细亚言语集》的12名军官中就有8人来自近卫步兵第一旅团,①鱒澤彰夫┍日本陸軍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の形成┘、『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别冊第18集、1992年、125頁。而且当时由数十名军人组成的著名汉语学习组织“汉语会”的主要成员也来自近卫步兵第一旅团。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如此看重汉语教科书的出版是可想而知的。可见这样一支“热衷”于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及汉语学习的部队,编写属于自己的军用汉语教科书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近卫步兵第一旅团还在甲午战争开战前编写了《兵要支那语》的姊妹篇《兵要朝鲜语》。《兵要朝鲜语》在早于《兵要支那语》一个月的1894年7月8日由明法堂出版。《兵要朝鲜语》同样也是一部小型口袋书,该教科书的出版无疑为《兵要支那语》提供了借鉴。
《兵要支那语》的校对者为平岩道知,书中标注为“陆军参谋本部属平岩道知校正”。平岩道知时为陆军参谋本部的汉语翻译兼教员,是1879年日军参谋本部第一次派遣来北京留学的16人中的一员。这些人有的一边学习汉语,一边从事情报收集等间谍活动,有的甚至只是以留学生的身份为掩护,纯粹进行谍报工作。两年后这批人陆续回国,在日本各地镇台②日本陆军于1871—1888年间常设的最大的军事单位。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
1898年,平岩道知还与金国璞共同编写了一本汉语教科书《北京官话:谈论新编》,至1918年10月,该书已发行至第12版。该教科书还成为在华英美人学习汉语用书。另外,平岩道知还于1905年编有汉语教科书《日华会话筌要》,由中国人张廷彦校阅,至1918年,已发行增补第11版。
综上,编者虽署名为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但显然是出自当时对汉语较为娴熟的军人之手。校对者平岩道知具有扎实的汉语基础,还是参谋本部的汉语翻译及教员,有着丰富的汉语知识和翻译经验,作为校阅者极为合适。
二、出版背景及再版情况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中日两国爆发了丰岛海战,紧接着又爆发了牙山战役。牙山之战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交锋,最后牙山失守。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1894年8月7日,即战争全面爆发的第6天,《兵要支那语》由东邦书院初版发行,增订再版于8月25日发行,此时正值战事正酣之际。
增订再版发行38天后的1894年10月3日,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司令部称已经完全做好了出征中国的准备工作。③┍近衛歩兵第1旅団司令部┘、『各部隊経歴書』(明治27、28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C06061720400。所谓“准备工作”显然包括其编纂出版的《兵要支那语》。可见在战争中与中国人沟通交流的汉语教科书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该教科书并非从汉语拼音开始学习,但由于编者在汉字旁用日语标明了汉语发音,即使是初学者也能模仿出汉语的发音。出于应急之用,日本军人手持该教科书,基本能够达到与中国人沟通交流的目的。
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当时虽然并未立即出征,而是在第二年的1895年4月9日方从广岛出发,4月13日抵达大连湾,4月21日在柳树屯登陆,同日抵达北三十里堡,并在此驻扎至5月15日;5月17日到达曹家屯,停留至5月22日;同日,脱离第二军战斗序列,准备赴台湾基隆;5月23日离开旅顺口。①┍近衛歩兵第1旅団司令部┘、『各部隊経歴書』(明治27、28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C06061720400。可见,该部队在中国仅停留40天。由于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已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就此结束。在40天的停留及行军过程中,与中国人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而后又开赴台湾驻守基隆,由此完全可以判断,这部军用汉语教科书必有用武之地。
如前所述,初版《兵要支那语》由近卫步兵第一旅团编纂,平岩道知审校,于1894年8月3日印刷,8月7日由东邦书院出版发行,是一部仅有72页的小型口袋书。然而,在该教科书出版发行18天后,又发行了増订再版《兵要支那语》,编者、校对者及发行者均无变化。再版《兵要支那语》将1894年7月出版的《兵要朝鲜语》予以修订附于其后。再版《兵要支那语》同为口袋书,共107页。
那么,为何在短短的18天后该教科书就再版发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如前所述,日本近卫步兵第一旅团的官兵汉语学习热情异常高涨,对汉语学习予以高度重视,并充分认识到该教科书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扩大化,该教科书发行量未能满足需要,因此再版发行。
第二,由于编纂时间仓促,发现教科书中存在一些不妥之处,亟待修订。这也是为了保障教科书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达到最佳。
第三,由于甲午战争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导火索,朝鲜语必然也是日本军人所要掌握的语言之一。将《兵要朝鲜语》与《兵要支那语》合为一册,便于军人使用。可以说一册在手,既可与中国人交流,又能与朝鲜人沟通,起到一举两得的功效。
三、两个版本的对照
通过对初版和再版《兵要支那语》进行比照研读,可以发现两个版本的如下差异。
首先,再版时对原文内容的增加部分。经比照,该教科书再版时,主要增加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篇首增加了由松本纪山所作的一首用汉语写的汉诗:
海外堂堂劳六师
牙山丰岛望风披
谙将此语臻城下
说下穷兵亦一奇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盛赞日军的赞美诗,赞扬日军六个师团在牙山战役以及丰岛海战中的优异战绩。附加这首诗无疑是为了增加日本军人学习汉语的信心,并试图提升日军的斗志。
第二,增加的单词并不多,仅为6个词语:“矛”“火药”“暗号”“不许”“不能饶”“不准”。这几个词语都与军事密切相关,显然使该教科书更符合军用特征。
第三,增加了“我国与清国通货及度量衡之比较”,其中包括“货币、尺度、量地尺、衡量、斗量”五个部分。这有利于军人明确掌握两国间通货及度量衡的区别和换算。
第四,增加分量最大的部分为《兵要朝鲜语》。编者将修订后的67页的《兵要朝鲜语》,作为附录附于《兵要支那语》之后,使姊妹篇合二为一,便于军人灵活运用。
其次,再版时的删除情况。再版时删除的内容较多。经比照,删除的单词有51个,删除的句子有61个。关于删除的内容及其原因等,可归纳为几点:
第一,删除了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零”这样的数字,显然这是由于附录中已列有相关数字,因此正文中予以删除。
第二,删除了与军用关系并不密切的词汇和句子。如“倒茶”“恳切”“景色”“造化”“右翼”“古时候”“好吃的么”“乐么”“有病人么”“放下帘子”等。
第三,删除了模糊不清、语句不通的句子。如“被人砍”“这几天你竟管说撒谎”“改打”“别糊”“他那个东西彼奴”等。
第四,删除了无关紧要的关联词语。如“虽然”“然而”“要是”“总”“就是”等。
第五,删除了当时中文中没有的词语。如“转后头”(标注“中国无”)、“大将”(标注“该国无大中少将之名”)、“担架”(标注“中国无此名称”)等。
第六,删除了重复的词语和句子。如“挑选”“你说实话罢,你不说实话就杀你”等。
第七,删除了部分错误。删除了“責める(责罚说)”中的“说”,因与其对应的日语无“说”之意。
第八,删除了已过时的词语。如“郡长在家”中的“郡长”等。
再次,再版时对初版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主要对初版中的如下两种情况进行了修正:
第一,对初版中日语错误的修正。如“取て往け(取去)”修正为“取に往け(取去)”;“渡舟”修正为“渡船”;“買て来れ”修正为“買て来い(买来罢)”;“すてつき机”修正为“ステツキ机”。
第二,对初版中汉语错误的修正。如“悄悄儿的”修正为“密密儿的”;“积上”修正为“堆上”;“到低”修正为“到底”;“猫儿”修正为“猫子”;“甚广”修正为“甚么”;“两口了”修正为“两口子”;“暂旦”修正为“暂且”;“我侮的兵”修正为“我们的兵”;“日去吧”修正为“回去吧”。
最后,再版时对初版错误的忽略。再版时对初版中的8处错误并未及时修正。试举其中6例:1.“砍石头”未修正,应为“扔石头”;2.“卓子”未修正,应为“桌子”;3.“剩下的吾在那儿”中的“吾”未修正,应为“兵”;4.“别动这块儿”中的“别动”未修正,应为“别离开这块儿”;5.“你的大夫在家里么”中的“大夫”未修正,应为“丈夫”;6.“间工儿”中的“间”未修正,应为“闲”。
通过以上比照研读发现,再版时除了8处错误未修正之外,修订后的内容基本上趋于完善,语句变得更加通顺自然,词语使用已较为得体。更重要的是,该教科书不仅更具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而且从军用角度来看,也更加便捷、更贴近实用。
四、《兵要支那语》的特点
《兵要支那语》,如闻其名,具有明显的军用特性。然而,该教科书同时具有一般汉语教科书的特征。以下将从军用特性及一般汉语教科书语言特征的角度,分别对其特点予以探讨。
如前所述,该教科书是完全出于军用目的而编写的,其功利性极其明显。如下几类用语便把该教科书的纯军用特性及侵略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大量使用军用词语。犹如书名一样,其军用特性在军用词语大量使用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与其编写目的完全吻合。如“步兵”“炮兵”“营房”“兵器”“陆军”“海军”“水师”“枪弹子儿”“搜查”“枪筒”“阵亡”“军营”“军医”“军队”“押送”“救兵”“看守”“进攻”“号令”“打仗”“攻打”“探马”“水兵”“打死”等等。
第二,频繁使用命令用语。对于入侵中国的日本军人来说,对中国人的命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书中充斥着命令用语。如“一步儿也别动”“听我的话”“别跑了”“拿下兵器吧”“在道路上你看见中国兵么”“你被拿的时候有甚么差使”“跟我一块来”“投降么”“夜里攻打”“别胡说”“动了就打你”“别动这块儿”“别放声”“打水来”“别动”等等。
第三,大量使用恐吓用语。除了命令以外,更为甚者是恐吓。在以侵略为目的的前提下,恐吓更是必不可少的。对中国人的恐吓,主要用语如“杀死”“砍你”“烧死”“扎死”“打死”“若在路上要跑就打死你”“你不肯说实话就打死你”“动了就打你”“砍你”“把你烧死”“扎死你”“若说撒谎就杀你”“你不说实话就杀你”等等。
第四,频繁出现行军用语。行军用语是出征部队在陌生的中国行军时必然使用的语言,因此该教科书此类句子较多。如“有过河的船么”“这个河可以走过去么”“容易通过么”“可以去得么”“车可以过去么”“一直的走罢”“把船聚在一块儿”“叫船工来”“开船罢”“把船摇到这岸上来”“离这儿有多远”“这条河有个桥么”“这左近有甜水没有”“敌兵所在的地方”“有上那屯里的道路么”“给我向导”等等。
第五,侦察用语大量出现。对于作战部队来说,侦察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侦察就必然要与当地中国人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就应该标准,否则难以沟通。如“探听敌兵的动静来”“你说暗号”“你说你从本营里出来的时候的光景”“离京有多少里地”“号令官的姓名叫甚么”“水师提督是谁呀”“你是哪儿的人”“你营里有多少人”“你是哪队的人说出营名来”“有马队么”“号令官的姓名叫甚么”“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在前面的那村庄叫甚么”“你的头目是谁”“你是队长么”等等。
综上,这些词语和句子包括战时方方面面的术语,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来说,应该是必须掌握的。换言之,该教科书的军用特性及其蕴含的侵略属性正是通过上述内容表现出来的。这对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兵要支那语》虽然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军用汉语教科书,但同时还具有普通汉语教科书的语言特征。
首先,从循序渐进的编写原则来看。初版的单词首先是从极其简单的数字开始,接着是单音节词,然后是双音节及多音节词,最后为句子。句子一般也是按照从短句到长句的形式循序渐进。如“ヒ部”首先出现“东”“人”“火”等单音节词语,然后是“左边”“粮饷”“火绳子”等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接着是“东方是那边儿”“粮食很多么”“往左边儿是那个”等句子。又如像“慢”“来的慢”“回来的慢”,“跳”“跳上”“跳下去吧”等。编者通篇采用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编写原则。
其次,从语言贴近现实的角度来看,一是表现在方言的大量使用上。如“左近”“快快儿”“昨儿”“昨儿晚”“鸡子”“多咱儿”“明儿”“后儿”“末末了儿”等;二是表现在口语词汇的大量使用上。如“起初”“起头儿”“对过儿”“一块儿”“这块儿”“这儿”“挠头的事”“那边儿”“左边儿”“前头”“放声”“一点儿”“那么着”“背阴儿”等。
再次,从注重相关词语重现的角度来看。单词首先出现,后面的句子大都是围绕单词编排的。如“イ部”的单词中出现“石头”,短句中是“砍石头”;单词“房子”,句子是“烧你的房子”;单词“一个人”,句子是“有几个人”。这种编写方式,也是现今汉语教材编写采用的形式。
从次,从注重运用语义场的角度看。一个日语单词对应复数的汉语表达形式,无疑是为了让学习者能够应付多变的交流场合,而且还注重口语与书面语表达形式的并列表述。如“見る”:“看见”“瞧见”;“痛いか”:“痛不痛”“疼不疼”;“昨日”:“昨天”“昨儿”“昨日”;“許さん”:“不许”“不能饶”“不准”;“左樣なら”:“改日见”“明儿见”“回头见”等等。
该教科书在注重同义词语义场的同时,有时还同时出现反义词,编者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强学习者的记忆力。如“给我看”“别看”“看得见”“看不见”“看看来”“看得见么”;“拿有”“拿着”“拿来罢”“拿去罢”;“要快的”“快快儿的去”“快快儿的做”“快来”;“取”“取去”“取来”等。
最后,从注重时事用语的角度看。教科书中适度采用时事用语,如“大日本帝国”“俄国”“高丽兵”“清国”“中国皇上”等相关时事词语频繁出现,这也是一般汉语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经常采用的形式。
综上,《兵要支那语》虽然是一部军用汉语教科书,但其仍然离不开教科书的本质特性。可以说,该教科书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编写水准,这种由生词到句子、由易到难、注重词语的重现、注重语义场及联系实际等编写形式,仍然值得我们在编写汉语教科书时借鉴。
五、结论
《兵要支那语》虽为语言类汉语教科书,但其出版发行上的军事背景、内容上的军用特性及其表现出来的侵略属性不容忽视。该教科书的出版,无疑表明了日军对战争的精心策划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环节。归根结底,《兵要支那语》就是为甲午战争服务的。
虽然战争也是语言传播的一种方式,但这种传播方式是畸形的、极端的。畸形的语言传播方式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广汉语,但这种方式具有侵略性也是不容否认的。正因为该教科书以侵略扩张为目的,语言才成为日本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重要工具。
《兵要支那语》这样的纯军用汉语教科书无疑成为日本畸形传播汉语的一个有力佐证。在日本,为侵略扩张服务的汉语教科书的大量出版,这在世界汉语教科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总之,《兵要支那语》这种“异类”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不容小觑,因为它是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发行的一面“旗帜”,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甚至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大量出版发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示范效应。时至今日,此类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仍然值得人们予以关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