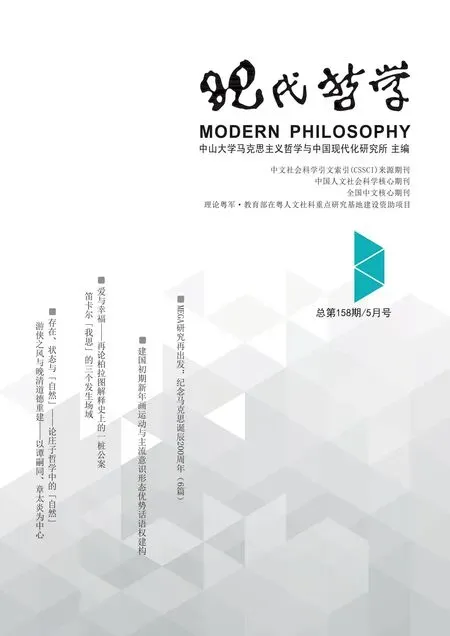论韩非对“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李国斌
以“申韩之法”代表去道德化的并且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治理技术,是先秦法思想研究的通见。*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2001年,第216页;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2页;[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梁治平:《“法”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杨一凡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6—104页。但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对“法”之道德基础的探寻与重构,表明法治不仅是治理实践中用以计算成本效益的技术方案,法家对自身的期待也不仅限于“统治工具”的设计者和操作者(即“法术之士”),还有树立自身学说之正统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诉求。而这,正是韩非思想中最具时代性与原创性的部分,其核心则是将对“法”的观察从“律令”转向“人”,尤其是人的“德性”。由此,“法”的道德向度就初步显露出来。当然,从韩非思想的复杂性看,他对“德性”的理解始终在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之间摇摆。某种意义上,这恰恰呈现了韩非思考“法”之道德基础的曲折努力。
一、人性无善恶
韩非的哲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将人从各式各样的伦理结构中解脱出来,并还原为他的自然性之后,人的生活境况陷入一种彻底的危机和绝望中。这种焦虑是整体性的,上至君主,下至臣民,无不面临因政治、社会和文化急剧变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幻灭感。焦虑的发生,是由剧烈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人的定义从政治人演变为自然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基于“德性”的伦理关系转变为基于“欲求”的自然关联。在韩非看来,自然人如何直面政治生活,是他所生活时代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他对时代困境给出的答案。
韩非完全放弃依靠人性本身实现通往伦理生活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性就是人的生性,本无所谓善恶,人的第一属性是他的“自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是自然的。人性不是其它,就是人和物因生而获得的“德性”。早期观念和思想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天地合德”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和态度,集中体现在“德者得也”(《管子·心术上》)的表述中。韩非基本延续了这种观念,并将其作为人性论的立足点。《解老》言:“德者,所以建生也。”人性就是其自然本性,不应该包含任何意义上的道德预设。第二,人的自然决定了人的平等。天的荡然公平,使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平等关系,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人性都是自私的,体现为各式各样的“人情”。“人情”的“私人性”恰恰构成了“法治”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参见冯国超:《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论〈韩非子〉的内在逻辑》,《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王中江明确指出:“人情论”和“因循论”在黄老学中的重要地位,构成了法律统治的“自然法”基础,并以人情的合目的性为基本的诉求。参见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9—455页。“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诡使》)第四,自然人的“社会”生活所描绘的是一种基于“人情”的激烈争斗的状态,它是一种“悲惨”的状态。*参见李猛:《自然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78—188页。所有人都被卷入冷冰冰的权力争夺和利益算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基本伦理关系丧失了它们应有的约束力,人缺乏一个安全而稳定的生存环境。第五,种种抽象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基于“力量”和“利益”的分配与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如此。第六,统治秩序的造成,是通过“力量”的等级化而实现的,集中表达为君主所处之“势”。“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难势》)第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统一与延续,这个力量就是国家。荀子已经明确国家的世俗权力架构,并认为国家是礼乐教化能够成为现实的基本保障,但他依然坚持儒家对于“王道”的诉求,“王道”的实质是人能够依靠自身德性“自然地”造成有德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在人的自然性之上添加了人的伦理性,认为“王制”才是国家的最高道德目标所在。韩非则完全放弃了这种情怀,强调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和利益结构,完全以功用为目的。
就韩非之前的整个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而言,“自然性”不仅是对传统治道的挑战,也是传统在新时代所面临困境的表达。一方面,人的“自然性”消除了人性本身种种道德属性的天然根基,否定了人类社会可以自然地实现某种良善秩序和道德的可能性,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权力和利益算计。君臣之间如此,“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父母子女之间也不例外,“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外储说左上》)。五伦关系中,最重要的君臣和夫子关系尚且如此,夫妇、兄弟、朋友也可推而见之。韩非对人社会生活境况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关于“自然状态”的解释,因此有学者将韩非的思想焦虑解释为一种超前的“现代性”,并认为这种焦虑的核心是道德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冲突。*参见白彤东:《韩非子与现代性——一个纲要性的论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另一方面,人需要在规则和规范之下方能有序地生活,人的“自然性”极大地彰显了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的迫切性。在礼崩乐坏的现实促逼下,儒家尝试以“复古”的方式重建“周礼”,然而这种努力被证明是失败的。在韩非看来,儒家之所以失败,并非情感上的偏颇或方法上的失误,而是因为他们回避了政治和社会剧变背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个体德性与政治道德之间如何实现统一?或者说,能否直接通过政治方式塑造人的德性,使得个体德性从属于整个秩序的伦理,从而保证整个政治秩序是“有德”的?
在儒家的经典表述中,政治秩序的发生,是以“圣人”创制立业,从而确立人间秩序即“人道”为标志。在这一思想路径中,人的政治生活开始于某种已有的、由圣人所创立的政治秩序和道德,通过“教化”方式被纳入政治秩序中,因此人的“德性”与政治道德之间是高度统一的。政治的权威及其合法性源于政治秩序自身的历史性与道德性的统一,它有效避免了“自然状态”下的人如何造成良善政治秩序的难题*[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88页;李猛:《自然社会》,前揭书,第90页。。在这样一种观念和制度的主导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中介,政治是直接的、切身的,政治生活对人而言是基础的、本原的。对政治生活中的个体而言,“政治”的直接形象就是君主及其领导下的官吏,他们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政治道德的践行者,还是百姓学习和效法的对象。那么,君主和官吏的“德性”便成为一个政治秩序好坏的评判标准。
这种观念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人的“德性”从属于主导的政治道德,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儒家“政治”定义直接的推论:贤能之所以能够治理百姓,是因为他们的德性更加接近圣人之德,并且优于百姓。因此,“统治”的本质,是以德性的优劣高下为基础构造的等级序列。人间秩序为圣王“制作”,本就已经蕴含了“德性”与“政治”之间天然的矛盾,体现为官吏和君主必然面临自身的意志及德性与整个统治秩序的道德和伦理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使得“政治”自身就面临“德性”与“技艺”的统一性难题。就其身份和角色而言,政治结构中的官吏显然带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在总体上,“为政”是一门“技艺”。由此,如何协调“为政者”身上“技艺”和“德性”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古典政治哲学最为基础的课题之一。儒家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试图将“修身”与“为政”完美结合起来,以“教化”方式达成善治的目标。但“身教”的最大弊病是非常容易走向“空疏化”,从而演变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宋洪兵:《论先秦身教政治的演变》,《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德性”与“技艺”之间的矛盾是根源性的,根植于“政治”自身的属性,因此根本无法消除。在韩非那里,“技艺”与“德性”之间的矛盾被彻底激发出来,由此走向分裂。最终的结果是二者被完全对立起来,并且围绕各自的观念、逻辑和历史,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对置身政治生活核心的君主和官吏而言,这种矛盾和冲突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带入一个十足的困境中:“技艺”和“德性”各自都能造成一种“合理的”统治秩序,并且它们在道德上是相互背离的。从“技艺”出发,功用、效用、有用性、可行性及精密性等,成为现实统治秩序最直接的诉求,代表性的是商鞅的“法治”思想;而从“德性”出发,自私、权术、算计、戒心及阴谋心等,被认为是维系君主权威,从而保障统治稳定的根本,代表性的是申不害的“术治”理路。它们之间的矛盾被导向如康德所说“二律背反”境地。
导致社会生活呈现“二律背反”现象的根源是“德性”,它的实质在于:政治秩序自身是否存在儒家意义上的“政德”,从而使个体德性与政治共同体道德之间达成统一?如果从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出发,这样的共同体道德是不存在的。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和个人,永远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并且国家相比个人并不具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性。另一方面,将人纳入某种秩序整体中,削弱甚至于消除人与人之间因权力和利益争夺所造成的困苦状态,使重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成为一个非常复杂却又十分紧要的难题。
二、心志的“渊薮”
由“德性”所导致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是人的“心志”的复杂性,体现为个体意志和情感的多变性,从而造成“我”的动机对于“他者”而言难以捉摸,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心志”与他的“行动”之间,并不具备天然的统一,我们无从知晓某一行为背后的动机,自然也无法通过外在经验窥测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狂者东走,逐者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说林上》)人类存在一些稳定的行为模式,比如对美食、美色、美味、音乐、权力、财富、知识、爱、荣誉、成就等的追求,又比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韩非称之为“人情”。但这些行为模式不仅没能弥合上述矛盾,反而彻底撕裂人的身心。在韩非看来,人类稳定的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基于历史经验的生活样式,这些经验在冷峻而理性的权力和利益算计面前,造成人情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之间的分离。最终的结果是个体身心之间、社会道义与个人私心之间、政治共同体道德与自然人情之间,都走向分裂和对立。人类社会的有序,仅限于对“人情”的节制和引导,它根本无法触及人的内在的意志和情感。
在《说难》篇中,通过剖析行为、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韩非深刻展现了“德性”的个体取向与社会取向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说的是语言、逻辑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故,所得而然也。”(《墨子·经下》)“说”本为“达意”,“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其过程是两个意志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困境的发生,恰恰就是因为彼此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在动机、意志和道德等方面面临冲突和矛盾。“心”在整个困境中占据核心地位。在荀子那里,“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认识活动的中心,也是道德实践的发起者,更是道德生活的主导者。“心”的最大难题是“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除“蔽”的办法就是心术修炼,“通过精神修炼建立起道德自我和道德理性”“化‘客观之道’为‘道德自我’,并通过道德自我来调节人的性情,以建立起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理想”*王中江:《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3、58页。。这一观念同样面临巨大困难: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建立,需要以“道德德性”的养成为基础,以认识心和智性来解释“心”,那么人的道德根基应该落在哪里?*牟宗三:《名家与荀子》,《牟宗三全集》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集团,2003年,第192—198页。韩非干脆放弃从人性自身寻求道德根基的努力,将人还原为自然个体,进而将道德理解为完全外在于人性的规则和规范系统。在他看来,通过心术修炼实现“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呈现方式就是“心志”,是人发起一项行动的动机和意志,这些动机和意志复杂多样,毫无规律可言,就像是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渊薮”。
君主“势”重,“心志”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矛盾和压力,便因此显得更为突出。《喻老》言:“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主抱法处势,不仅独占势位以显权威,“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还要以“虚静”“静退”“不可见”(《主道》)的方式示人;更要牢牢掌握驾驭臣民的“术”,使其与“渊深”的势位一样深不可测、无从揣摩,是谓“术不欲见”“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定法》)。“术”隐秘性的另一面,是其无序性和随意性。换句话说,君主对刑、德“二柄”的使用,没有一套客观的标准,它在提升君主权威的同时,也使君主处于一个更加孤立的地位。
在多变且无序的“心志”面前,因“德性”而来的秩序和道德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心志的“渊薮”,使得对恒定“德性”的追求成为遥不可及的目标,至于作为最终道德目标的“人的生活样式”则根本无法企及。人的内在世界是一个完全无法捉摸,故而毫无规律可循的“渊薮”。那么,“法”的范围便局限于人的外在行为,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经验世界的流变性,使得法、律、令沦为应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工具,却不能解决如下问题:如果“法”只是“治术”,那么如何才能为人寻得一种合理良善的生活方式?法治国家的基本形态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它意味着“法”不能仅仅作为惩恶扬善的工具,还要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价值引导;与之相应,“吏”的角色并非简单按章办事,还要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将“明法”“循法”“奉法”的良好形象展现出来,作为百姓效法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治术”的“法”,远远不能满足秩序和道重建对“法”所提出的要求,与功用、功效和功利为主的“治术”相比,重建“法”的道德根基成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难题。
韩非深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它作为法家思想的原生性难题,渗入到与“法治”相关的所有问题。因而,韩非需要总结和批判之前的法家思想,在此基础上为“法”寻求全新的道德根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定法》篇中,韩非分别批评了申不害和商鞅,认为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商鞅“徒法而无术”,“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申不害将“法”等同于“治术”,进而将“治术”等同于君主的“心术”,以君主的智能和好恶作为法令依据,“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利在新故相反,前后相悖”,朝令夕改成为“常态”。最终的结果是以君主的一己之智能讦奸,不仅不胜其能,而且使奸邪之徒愈发纵恣。商鞅重法,但其所重之“法”,是一套客观化、标准化的规则和规范,其施行过程被简化为简单的“数值计量”,将战场杀敌斩首的数量作为晋爵封官的唯一依据,“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然而斩首凭借的是勇力,治官则需要依靠智能,商鞅的做法最终导致“官不当其能”的严重后果。
在韩非看来,“法”和“术”都是“帝王之具”,二者缺一不可,它们的含义及形式都属于“治术”层面,并没有触及“治术”背后的道德。慎到的观念触及了“法”的根本问题,即恒定秩序的来源及维系,认为“法”根源于自然的秩序和分理,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最好的治国方式便是“法”,“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任法”的具体方式是“因循”,因天之道,因人之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慎子·因循》)。在慎到看来,法令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道”,它构成“法”的道德基础,这也是《威德》篇所说“势位足以为治”的依据。慎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仍然是“德性”的私人性,“法”与“人”是完全的对立关系,“法”作为秩序和规范力量的提供者,“法治”的意义只是强力和规范,而非法律共同体的建立。
韩非对人之社会心理的描述和反思,开启重新理解“法”的新视野。如果说此前关于“法”的使用和理解,都与“律”“令”混杂在一起的话,那么到了韩非这里,“法”获得独立且尊崇的地位。通过利用来自申不害、商鞅和慎到的思想资源,韩非重建“法”的道德基础:对自然秩序的关切只是“法”的本义,在法治国家中,“法”最重要的意义是“治人”,既包括对人的外在行为的引导和规范,也包括对人的内在意志、动机及情绪的节制和规约。在法治国家,人的内在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而应成为“法”所可能的范围,通过塑造一种良善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身心、内外之间的和谐。
三、“法”之道德基础的建立
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各式各样的“复古”被证明是失败的,集权国家被证明是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而“法治”是集权国家能够建立并长久维系的唯一有效手段。
韩非之前的法家,基本将君主作为“法”的根源,认为“法”就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管子·君臣上》言:“有道之君,善命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君据法出令,有司奉法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任法》言:“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商君书·君臣》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简言之,“法”的来源是“圣人”制作,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及相应的道德正当性。通过叠加“法”之历史与当下的情势之后获得的“法律令”,即《商君书》开篇所说的“更法”“变法”。既然“法”可变,那么“变法”的实质,其实就是君主本人意志的表达。因此,在商鞅那里,“法”毫无疑问以君主的意志为准绳,“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商君书·权修》),意思就是指君出令而臣奉法。这样,“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君主意志和智力的直接表达,它不仅缺乏公共性,而且很容易演变为实现君主个人意志的工具,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法律的朝令夕改。《管子·法法》言:“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慎子看到这种危机:“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言下之意,“法”应该具有超越君主个人意志和智力的独立性。
韩非将“术”和“法”分开,并且将“术”的含义及使用范围限定于君主本人,本质上是为了重新安排君主与“法”之间的关系。抬高“术”的地位,可以有效保障君主权威和地位的稳定性,因为就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君主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韩非看来,君主无时无刻不处于危机中,“人主者,利害之軺毂也”(《外储说右上》),“主上不神,下将有因”(《扬权》),《八奸》《十过》《奸劫弑臣》《亡徵》等篇目所列君主所面临的危机,可谓是不胜枚举。因此,君主必须“主道”,而实现“主道”的方式便是“执术”。君主所执之“术”,韩非将其简化为“刑”、“德”所谓“二柄”,“明主之所治其臣者,二柄而已矣”,“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韩非的说法是当时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看法。《尹文子·大道上》言:“庆赏刑罚,君事也。”《管子·君臣上》言:“是故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戮死之刑,而民不疾也。”《商君书·君臣》言:“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禁使》言:“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另一方面,君主“执术”构成对“主道”之现实性的“外在化”,而“道”构成“法”在总体上保持一个统一的目标和道德的根本所在。表面上看,韩非似乎将“术”的地位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使其与“法”绝对地悬绝开来,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庆赏爵禄生杀予夺的权柄,却不直接作为“法”的制定者和发布者,所谓“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外储说右下》)。君主“执术”而不擅改法令,理想的君主更是将“道”作为最高的“术”,“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扬权》)。这就给“法”留下非常广阔的空间,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法”不是君主根据个人智力和意志所发布的“法令”,而是有着一个更为深远的起源,这一起源构成了“法”的道德基础所在。
关于“法”的起源,《管子》一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管子·侈靡》言:“故法有常守,尊礼而俗变,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驵,此谓成国之法也。”言下之意,“法治”的主要目标在于维系一种基于“习俗”的良善的生活方式,因此“法”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也”。因此,在更多场合使用的不是“法”的抽象含义,而是具体的“法令”。《管子·任法》言:“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也就是说,“法令”有非常明显的目标性和现实性,是君主实现治国目标的手段,“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管子·法法》)。但“法令”之本,不能由某些具体的功利性目标构成,而必须有一个更为基础的来源。“法古之法”,是指“法令”只能作为应变之方,“古之法”则构成“法令”直接取法的依据。至于“古之法”究竟为何,《管子》书并没有给出更多说明。将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在《管子》书中,“法”的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效法天道的“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它们代表的是某种恒定不变的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是“法”字的本义。《管子·正》言:“如四时之不贷,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其二,是由“道”而来的针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法”。《管子·枢言》言:“法出于礼,礼出于知,法、礼,道也。”《心术上》言:“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礼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礼,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乎不得不然者也。”《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因此,“法”不是一些教条化的律令,而应该是带有很强时效性和功能性的礼法,它需要兼顾人情和义理,却能在总体上合于“道”的要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关于“礼”、“法”和“理”、“义”的观念,带有很强的儒家思想烙印,只不过将其含义限定在“法治”的框架之下,故而沾染了几分法家的色彩。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管子》一书,杂糅了“道”“理”“义”“礼”“法”等观念,却没能非常清晰地呈现“道”与“法”之间的关系。
这一难题通过黄老道家获得非常好的解决。《黄帝四经·经法》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的形态是“虚无形”,由“道”直接产生的“法”,所体现的是“道”的特征,具体而言,“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蓄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道”囊括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秩序所有恒定性的规律、规范、法度和道德。“法”的含义是“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言下之意,“法”是衡量事物成败的标准所在,然而它仍然是抽象,必须具体化为“刑(形)名”,才能如规矩准绳一般直接衡量和评价事物。“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则白黑之分已”,“刑(形)名已定,物自为正”(《黄帝四经·经法》)。“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尹文子·大道上》)“形名”不仅标示着事物的客观性,而且表明该事物在经验层面具有现实性。曹峰强调,“形名”是“道”的体现,本质是“名分系统”和“规则系统”。在《黄帝四经》中,“名”的重要性超过“法”,只有在“名”确立之后,“法”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这是黄老道家比法家更为深刻的地方。*曹峰:《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然而“形名”毕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困境,简单地说,就是其自身的正当性并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结果。尽管研究者强调“道”之于“形名”的根源性,但仍然没能有效解决这一困难。《管子·心术上》言:“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者也。”《经法》强调:“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顺逆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但“名”的正当性,最终来还是源于君主本人。毫无疑问,在“形名”观念中,“名”具有非常高的客观性和规范性,与“理”甚至是可以互换的。《法经·名理》言:“循名厩(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诸如“审查名理”、“见正道循理”、“循名究理”、“得名理之诚”,其要义无外乎“主执度,臣循理”,说的都是人事之理,是作为治术的名分和刑名。“主执度”强调君主在最终的意义上构成“名”和“理”的正当性的来源;它从另一层面表明,“道生法”的表达仍然存在一个潜在的危机,即“法”可能最终只是获得它的形式,其正当性必须由君主来给予,正如“形”之于“名”的关系一样。我们所期望的“法”具备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客观性和道德正当性的目标,并没有在这里实现。
也就是说,“法”无论如何都存在着两个层面的根源:一个是它的“自然”基础。简单地说,“法”来自“天道”。《管子·形势》言:“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韩非子·大体》也有类似表述:“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另一个则是它的“道德”基础。既然用于国家治理的“法”必须由人来制定,那么立法者就必须是“圣人”,因为“圣人”的本义就是“聪明人”*参见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王元化主编:《释中国》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15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立之法不仅合于“天道”,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且能很好地用于国家治理,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具有公共性和正当性。简言之,这就是《黄帝四经》所说“道生法”与“主执道”的统一。在韩非看来,无论是“法”的公共性、客观性还是普遍性、道德性,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突破个体的“私欲”和“私心”,如《诡使》言“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可见“圣人”除了“主道”、“执术”和“无为”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私”。而这正是“法”的道德基础所在,也是法治国家整体的道德诉求所在。
不可否认,这种道德诉求与君主操持权术的非道德性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从逻辑上讲,作为“法”之道德基础的君主,本应该是道德上的圣人,然而韩非消解了“德”本身的道德性,使君主成为表面上“无为无思”、实际上深谙权术并操持生杀赏罚大权的“术士”。另一方面,韩非强调“法治”的本意是希望以一种客观统一的规则来治理国家,使整个统治秩序能在总体上保持其秩序性和规范性。基于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尽可能将“法”客观化,使它成为能被直接把握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越是强调“法”的客观性和公共性,就越需要去除“法”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道德诉求,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道家,将“法”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客观秩序,却同步消除了“德”对人的基础性,因为“德”字的含义和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必然导向某种“特殊性”,即通常所说的“德性”无法化约为一个客观统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