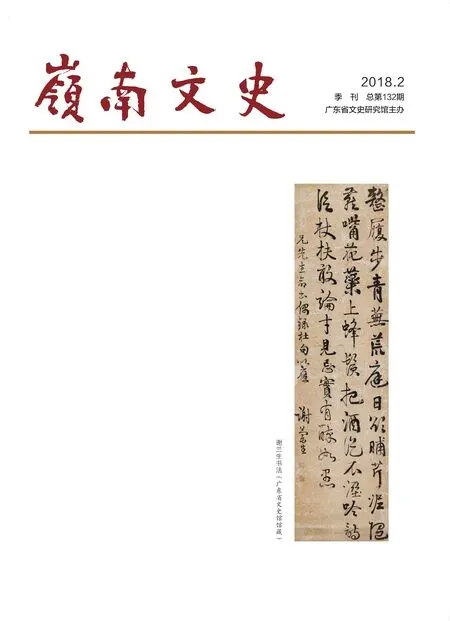四川客家文化历史与现状探寻
郭一丹
一、四川客家人的前世今生
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对四川客家作了如下描述:“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等十县。巴县即旧重庆府首县,涪陵即旧涪州本州,泸县即旧泸州本州,资中即旧资州本州。这些地方的客人,都是清初自粤赣二省迁去的,亦与湘赣系人杂居。”[1]罗香林先生强调客家人与各省移民 “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成都客家话研究成果最受瞩目的是董同龢先生于民国35年(1946)所作《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这一成果的研究范围也主要限于成都“临近好几个县份”。钟禄元先生的研究也主要限于成都东山地区。鉴于学术前辈的研究条件,只能根据得到的族谱资料或有限的田野调查作出初步的描述。其实,清代四川客家人远远不止这些地区。语言学者崔荣昌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发现,至1993年底,四川境内的客家方言点已达47个,另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17个,两者合计为64个;至2001年又增加了8个方言分布点,总数达72个。[2]崔荣昌先生的研究刷新了早年罗香林先生对四川客家分布的推断,他还承认这都仍是一个保守数据,认为如果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这一数据还会扩大。据学者刘正刚研究,四川客家分布几乎遍及全川(包括今天的重庆),清代四川府州县厅的90%左右均有闽粤客家人入籍定居。清前期近百万的闽粤客家人移民入川,几乎遍布四川省所有的府州县。[3]而且,刘正刚先生的研究还少有涉及赣南迁川的客家人。总之,清代西进入蜀的客家人遍布巴山蜀水间。而成都东山是至今保存相对集中的客家聚落,也是相对最容易观察的客家文化“基地”。
二、西部客家第一镇——洛带
洛带镇,俗名甄子场,总人口3万多人,客家人占总人口的85%以上。洛带镇及村落有很多保存至今的客家文化遗产,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有会馆,宗祠、古庙、古树(红豆、古榕)、古村、字库、客家公园、传统民居、青石板街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客家方言、族谱、广东小儿歌、客家山歌、清代碑刻、客家民俗、文化认同、原籍记忆等,这座“西部客家第一镇”承载着很多四川客家的历史文化信息。
会馆是洛带规模最大的建筑文化遗存,为广东同乡、同行集会、寄寓的公共空间。各省移民初来乍到之时,各从其俗,自为风气,彼此融为一体商尚需要一个过程,移民最初大都以同籍老乡为“凑聚之道”,建立同乡组织,以凝聚人心,守望相助,抱团发展。这种文化认同需要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符号——原乡神祇,于会馆中“迎神庥、聚嘉会、襄义举、笃乡谊”、“坚团结而通情谊”。洛带各省移民也争相修建会馆,联谊同乡。古镇现存清代会馆四座,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为近年成都市区川北会馆原貌迁建)。会馆群建筑精巧、华丽、独特,是古镇最为厚重、靓丽的文化景观。广东会馆(南华宫)主要神祇为禅宗六祖慧能。各省会馆设客长一人,首事若干,负责主持会馆事务,组织管理系统的建立、完善,以会馆为主体,开展社会活动,联络乡谊,维护共同利益.反映了移民前期不同原籍移民在地缘、文化、方音、习俗等方面的文化认同或族群认同,蕴藏着移民以原乡地缘为纽带、缘于同省“乡党”“里党”情谊生存策略的社会内涵。
洛带广东会馆,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建筑达三千多平方米,为“三殿二天井”,除广场前戏楼外,前殿为“单檐卷棚式”,中殿为单檐硬山式,后殿为三层重檐歇山式,下檐硬山式,上檐歇山式阁楼,屋檐四角高翘,恢宏庄重。山墙以实墙围合,上部开高三面半圆形水形封火墙,圆润流畅,错落有致,远处就看见会馆恢弘的殿顶与独特的封火墙,看见一条耀眼亮丽的天际线。意味深长的是,广东会馆的大门朝向,不是沿用中国建筑“坐北朝南”的传统,而是径直朝向东南方向,表达了对祖地的无限向往思念之情。[4]而面临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街道,会馆只是开了一道便于进出的很小的后门,这是广东客家人不忘先祖,传承历史记忆的特有方式,情感表达朴实无言,却早已下自成蹊。会馆大门有副楹联为“系衍曹溪恩流洛水,宗传梅岭泽荫巴山”。反映移民从中原到岭南,再从岭南到巴蜀的迁徙辙迹与历史记忆。广东会馆曾在清光绪五年(1879)遭遇大火,大殿被烧毁,经过广东乡亲的再次醵金公建,于四年后原样恢复,并增加了“香园祠”和粤王楼左侧附属建筑。民国20年(1931)以后,广东会馆基本改由和尚管理经营,出租部分房屋,收取租金作为会馆开支。[5]大殿几幅楹联蕴藏着会馆的前世今生,也蕴含着客家移民浓郁的乡愁:“此间故人今何在?只剩得乐楼与耳楼,想见当年缔造;以外能手究属谁?惟重新佛殿诸神殿,合观后世经营。”“云水苍茫,异地久棲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庙堂经遇劫灰年,宝相依然,重振曹溪钟鼓;华简俱成桑梓地,乡音无改,新增天府冠裳。”这些楹联透露出当年洛带客家人对原乡桑梓广东与新家乡四川之间的历史联系与文化追忆,思乡、缅怀之情,溢于言表。会馆后殿一楼供奉禅宗六祖慧能,二楼供奉妈祖,三楼供奉南越王赵佗。从这些现存的楹联看,人们心目中的原乡神祇为禅宗六祖慧能、南越王赵佗和海神妈祖。但是,据学者刘正刚研究,四川的广东会馆中大多数供奉“南华六祖”,也有少部分广东会馆供奉的是南华真人“庄子”。[6]据洛带当地文史资料记载,镇上的“南华宫”曾经供奉过庄子,洛带广东会馆也有曾供奉“南华真人”一说。当地人也认为自己的原乡是来自庄子泛指的遥远蛮荒的“南溟”之地。[7]因此广东移民以庄子的“南溟”来寓意自己曾经来自遥远的南方。1986年商务印书馆《词源》上“南华经”条认为,魏晋时的《南华经》只称《庄子》,《隋书·经籍志》三著录中有梁旷所撰的《南华论》、《南华论音》,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得明经典释文虽然尊《庄子》为经典,但那时还未出现“南华”这一名称。直到唐天宝元年二月(743)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才开始也被称为《南华真经》。但是,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证明庄子与“南华”的联系其实更早,认为实际上唐玄宗以前就有“南华”指庄子之说,梁代就有《南华论》,敦煌写本中也有《南华论》。“南华”之号当出自南朝道教徒所为,庄子在东晋道教徒心中是为仙人,主要以南华一词来形容庄子及其著作有如日光一样璀璨夺目,足可照耀八方。他最后下的结论说:“‘南华’一词亦当由南朝道教徒最先赋予了其特殊含义。总之,庄子及其著作早在南朝时已与‘南华’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唐玄宗天宝元年(472)仅是依旧号而诏庄子及其著作为‘南华真人’和‘《南华真经》’而已。”[8]而到了民间信仰的“多神大河”(杨庆堃)中,对于乡民来讲,训诂考据是专门家的事业,他们只需要更加注重“生活世界”本身,只要能从中提炼出凝聚原籍同乡的文化认同符号就可以“拿来主义”了。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洛带广东会馆正殿楼堂供奉粤王宝相,他兴戴冕旒、身着龙袍,而外馆堂供庄周、老君、炳灵、南极寿星和八仙,三清九皇等神像。每年在广东会馆要举办粤王会,还会附带举办南华、九皇、炳灵等小会,皆称“社会”。[9]一般来说,取名“宫”、“观”等,应主要为道教信仰,但同时将当地乡民的记忆、民间举办的各种“社会”以及与留存的楹联结合起来看,这一“南华宫”里应该是佛道并存,共济一堂的,这在民间信仰中本也常见。移民会馆与寺庙、道观有所不同,并不是宗教场所,而是一个集信仰与世俗生活于一体的“混血儿”。神祇崇拜主要是凝聚人心的文化符号,人们来参加会馆活动是在“努力缔造神庥共保千秋”,以慰漂泊孤零之叹的。不管过去供奉的到底何方神圣,但“通过在会馆举办庄严的祭祀活动,使人们在追思神灵和祖先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的归属感,从而更加律己、齐心,珍惜同籍人之间的情谊。”[10]在这里,佛道兼容,不分畛域,反而体现了民间文化的放达、率真与自然勃发的创造力与精神活力。此外,单单从建筑装修来讲,会馆的瓦当上有蝙蝠、铜钱等,是前人们对“福在眼前”的一种美好愿望的期待。墙上石雕还有将蝙蝠、官帽、银钱、长穗等融为一体的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福、禄、寿、财的祈福心理。目前,洛带广东会馆正在进行全面维修,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会以更加厚重而清丽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
洛带镇 “客家公园”建于民国17年(1928),人们早在那时是否已经意识到“客家”的称谓了?还没有更多证据表明,他们眼中的“客家”是四川“土广东”这一特指,还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视野下的“客家”。对当时提倡修建客家公园的“团总”刘惠安推测,他既是族群意义上的“广东人”,又是洛带这一五方杂处场镇的实际管理者,他要管理的人群中有客家人,有湖广人,也有来来往往的各地商贾,加之从清初到民国,经过近二百年融汇,外来移民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因此,镇里建造于九十年前的“客家公园”或许是外来移民这一广义上的客家,而非文化意义上的“客家”。人们也可以大胆推测另一种可能性,在洛带广东会馆里,“广东会馆”的匾额为清代广东人所赠。至民国时期,这里的客家人与广东来往仍然密切,与原乡信息畅通,知晓“广东人”的族群标签是“客家”也是可能的。因为民国时期客家人的族谱中偶尔已经能看到“客家”一词的身影。如民国33年(1944)成都《陈氏族谱》。《陈氏族谱》记载,陈氏先祖于清乾隆二年(1737)从广东嘉应州长乐县迁入四川,始祖置业于成都西门外。陈氏在追溯广东祖先之时,提到先人“散处广东长乐县城乡及河源等地方(后人称长乐语言为客家语言)”。[11]可见,修谱者在当时已经接触到“客家”这一称谓了。因此,洛带客家人民国时期已经知道“客家”这一称谓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洛带古镇至今保存较好的客家祠堂主要有“巫氏大夫第”及宝胜村的“刘氏祠堂”。客家人西进入川时,主要以少数人口组成的“家”的形式佃耕或小置田地房产,经过数年发展壮大,渐又成“族”,逐渐人丁兴旺,财力渐丰,买田置业,聚族而居,醵金建祠。巫氏大夫第是洛带镇保存最为完好的客家宗祠,里面承载着巫氏家族入川,创业兴家的历史记忆,是诸多入蜀客家人兴家、建祠、敬宗、收族的一个鲜活样本。入川始祖巫锡伟的父亲巫象嶷在广东兴宁时就有四方之志,其子巫锡伟不失先父播迁之志,后携家入川发展,十五岁起就“货殖重庆”,贸易为业,于洛带安家,并“以经商而昌盛”,遂有现在的“巫氏大夫第”。洛带宝胜村六组的“刘家祠堂”虽然没有“巫氏大夫第”保存完好,但祠堂的清代碑文仍清晰可见,承载着丰富的家族式管理的内涵。刘氏原籍江西赣州府安远县,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入川,佃种数载,置地建祠。如今刘氏族人大都在祖堂周边各建房屋,但刘氏祖堂保留至今,不敢稍动,以妥先灵。尽管供桌等祭祖器物大多不存,但清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六日实贴刘氏祖堂的两通示喻碑完好镶嵌祠堂左墙。碑文中共刻有十九条族规,包括家族管理制度、用水、农事、祭祖、舞龙、账目管理、处置族内不肖等生产、生活具体细节及相关规定,有条不紊,宽严相济,颇有法度。
凉粉是“尚滋味,好辛辣”的四川人喜爱的一道小吃。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它的身影。清傅崇矩《成都通览》就记载:“凉粉,有漩子,有荞凉粉,有煮凉粉。有摆摊者,有肩挑者。”清末民初邢锦生《锦城竹枝词》也描述:“豆花凉粉妙调和,日日担从市上过。生小女儿偏嗜辣,红油满碗不嫌多。” 虽为一道小吃,却十分美味开胃,招人喜爱。对此,客家人杨明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和认知,深知祖先上川打拼的艰辛与不易,联想到自己一家在洛带广东会馆里创业起步的艰辛曲折,便给凉粉取名“客家伤心粉”。他说这样就会“让人联想到生活的艰辛,联想到背井离乡的客家人,思念家乡的伤心,在伤心中迁徙,在伤心中起步创业。”籍由“客家”迁徙流离、艰辛打拼、思念故乡的意象,“客家”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客家伤心粉”也成为洛带一个主要的小吃品牌,成为一个新的可以大快朵颐的文化符号。品牌是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的集合,“客家伤心粉”依靠文化力量,成功将功能性利益与情感性利益合二为一,最终融注为古镇一碗“舌尖上的客家”。
三、清水沟范家祠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清水沟威灵六组的范家老祠堂是市区内保存至今的客家祠堂,1998年被公布为成都市成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老祠堂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范氏族谱》中有《清水沟对扬公祠图说》记载老祠堂概况:“祠在华邑东关外二十余里,地名清水沟。其龙由迴龙寺起祖,磊磊落落,奔至马鞍山……以之立祠,虽未尽美,亦庶乎可矣!”《图说》从风水角度对清代老祠堂选址因由作出说明,反映了人们的风水崇信与实践。天人合一、天道人道相通、反气入骨等观念正是人们崇信风水的思想根基。家族成员因之凝聚成一个血缘上、心灵上的生命共同体,族人由此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祠内保留清代木制碑刻,为“大清光绪九年(1883)岁次癸未末孟秋月”订立之族约,共三通。数条族约主要为奖勤罚懒的具体规定,尤其是针对子弟读书科举等奖励事宜,为研究家风建设的良好素材。范氏家族对后世子孙的教导管理可谓严谨不苟,有条不紊。祠堂虽已有倾圮,陈旧空寂,但雕梁画栋,历历在目,清晰可辨,镂空饰图,保存较好,风采依然。内堂屋檐上一对“和合二仙”清晰可辨,因室内暗淡,高悬房梁,未及仔细辨认,但仍能遥想当年的秩序井然与兴旺发达。祠堂正堂房梁有各种祈福图案,如“爵禄封侯”、“丹凤朝阳”“三阳开泰”、“龙凤呈祥”等为烫金饰纹,尤其以精美烫金“五福”木饰最为珍贵,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尚书·洪范》有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些文化元素在范家祠堂都有符号的艺术性呈现。祠堂屋顶、墙体、天花、梁、柱、檐、门扇、窗扇、栏杆、吉祥饰物等都经过一番考究,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这里,民间社会的“五福”信仰,人间美好情感的积淀、凝结与传承能使人有深切的现场体认。
那些被自己内在目标驱动的人比较不容易损耗自控力,而认为自己是被迫进行自我控制的人以及那些出于讨好和满足他人需求去行动的人更容易耗尽自控力。
四、新都石板滩客家文化
成都“东山五场”之首——石板滩镇,历史上为小川北古道的重要驿站,也是成都东山客家聚落的重要节点,镇上曾有清乾隆年间所建的南华宫。此外,这里曾经还有玉皇观、观音庙、土地庙、川主庙、药王庙、上南海庙等,颇有旧时“九宫十八庙”古风古韵,也反映出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庞杂、包容与博大。现在尚存的文昌宫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殿宇为东南朝向,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宫殿式。以前这里每年农历二月二举行文昌会,文人墨客、善男信女纷纷赴此祝文昌君诞辰,祈求庇佑子弟金榜题名,学业有成。惜现仅存大殿,作为当地老年活动馆。附近还有关帝庙,主奉关帝,附祀炎帝、火神祝融,因此乡人也称“火神庙”,其秀美绝伦的八角形钟楼和琉璃筒瓦卷棚拱顶格局别致,婉约不失气派。
石板滩廖氏宗祠“廖氏实蕃宗祠”(实蕃公即花公,为廖氏福建杭永始祖)与“廖氏体用祖祠”的合二为一,为当代川渝两地廖氏宗亲齐集一堂,共叙亲情的一方乐土。室内一尊“廖氏历代始高曾祖考妣神位”为传统木质,雕花镂空,底座精美,是较为罕见的传统神主牌。这支廖氏迁蜀前居广东兴宁,因“连岁荒旱”及入川始祖廖明达(体用)阻挠家族恶人擅卖祖茔、“不忍亡此血食”,不愿同流合污而惹祸上身,遂于清雍正四年(1726)避难入蜀。
石板滩土城村位于东山客家聚集区内的中心地带,95%为客家人,一走进客家新村,全然一片客家话语境。在客家新村前建有一座“客家风情园”,雕塑为一双大手轻轻托起一个婴孩,为新时代、新发展中,祖先精神遗产代代传承的艺术表达。广场处处彰显客家文化传播的用意,如介绍客家围龙屋的渊源、功能、寓意等,“客家风情廊”里有主要当地文化元素浮雕:“客家入川”、“占地兴宅”、“耕播劳作”、“东山首场”,“巾帼英雄”(廖观音)等,为村民营造一个新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客家新村为现代客家综合减灾文化大院,共301户,入住1100多人,院内面积1.8万平方米。据介绍,修建之前,有关部门专程赴广东梅州考察客家围龙屋,借鉴梅州客家民居减灾抗灾的文化理念,充分发挥防火、防水、防盗等功能新建而成,新村也是成都市近期的一个减灾样板工程。
五、龙王镇“刘氏宗祠”
在成都青白江区龙王镇梁湾村12组,有一座“刘氏宗祠”,当地人称之为“刘家老屋”。清康熙五十年(1711),刘氏留下父亲及次子在广东老家,其余四兄弟一起“同赴西川”而来,渐渐发展壮大,聚族而居。如今刘氏子孙散居附近各地。刘家祠堂是龙王镇仅存的老祠堂,神主牌、祖宗画像、神龛尚存,与广东常见的客家祠堂大致相同,为家族礼治的核心区域。祠堂共有三进,间以两个鹅卵石铺就精致图案的天井。祠堂排水系统较为考究,天井漏引在中堂呈龙形,中有沉沙池,便于清掏,即使大雨季节也不会积水。二进中厅悬挂清光绪六年(1880)的“坤维正气”烫金匾额。上堂(祖堂)正中上墙挂“禄阁长辉”,下为祖先神榜,最下为本宅福德正神即土地菩萨神位。据介绍,祠堂较为独特的是墙体,为版筑墙,用造墙木版固定地基,以竹条穿插,以黏土填充,以木杵夯实,层层上累而成。祠堂主要架构为传统穿榫结构,至今非常坚固。屋顶为小青瓦。祠内木质窗棂,镂空雕花,朴实精细。中堂外侧还留有一块木质“旌表节孝”牌坊,为“刘府古老太太立”。客家民居,既解决了族人生存居住问题,又是对族人心灵需求润物无声的默默形塑,反映入蜀客家人在川言川,对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这些文化遗产反映了传统社会中的天道人伦、秩序法则与儒家的礼制精神。另一方面,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也构筑起彼此文化认同与“他者”的文化边界。但总体上,这种五方杂处是相对和平祥宁的,也展开了一幅丰富厚重、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画卷。文化多样性的实际存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四川客家文化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价值感受。
注释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第97页,1992。
[2]参见崔荣昌:《四川境内的客方言》(上)。巴蜀书社,第39页,2011。
[3][10]参见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第125、237、243页,1997。
[4]参见姚云书:《进洛带 看古迹 说客家》。载《龙泉驿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2000。
[5]参见姚云书:《保存最好的广东会馆》。载《龙泉驿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2001。
[6]参见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0、237页。
[7]参见梁佐证:《洛带古镇的历史文化与客家文化》,2006。
[8]方达:《庄子何时始称南华?》。《文史知识》,2008年,第4期。
[9]参见李泽良:《洛带古镇及会馆本事》。载《龙泉驿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11]成都《陈氏族谱》,民国33年(1944)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