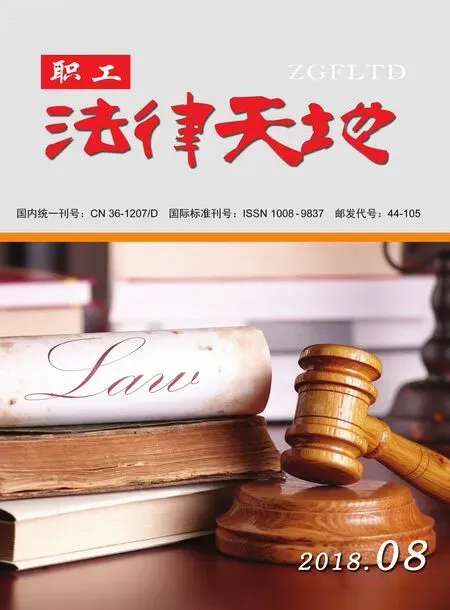从新旧过失论的比较分析达标排污致损入刑问题可能性
陈微雯
(710063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一、新旧过失论的比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为适应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理论上先后出现了旧过失论、新过失论、超新过失论三种过失理论。超新过失论起源于日本,其主张对危险结果预见的标是抽象、模糊的而非明确、具体的。可以想象,如果采用这种理论,在高危作业和风险创新如此普遍的今天,医生在进行手术时,企业在开发新药时,诸如此类的活动将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由于超新过失论容易“使责任主义空洞化、形骸化”,且在具体实践中基本不会被使用,因此在此不做展开讨论。
新旧过失论的核心区别在于对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侧重不同。旧过失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那种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对一种危险行为结果的预见应是非常容易的,因此旧过失论认为,过失的本质在于由于违反了预见结果的注意义务,即有预见可能性,但因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从而酿成大祸。同理,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只要排污企业因为过于自信的过失或疏忽大意的过失而造成成环境污染事故,排污行为是否违反环境资源法规不影响过失犯罪的成立。由此可见,根据旧过失论的原理,侵权行为造成实害结果的情况基本都具有违法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中难以避免法益侵害危险性的行为(如科研探索、医疗行为、不断提速的交通运输、建筑工程施工等)不断增多。而这些事业又是现代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人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受危险的发生。基于此种背景,一律适用以有无结果预见可能性为核心的旧过失论便有失妥当,因为在这些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从业者不可能没有预见可能性。若适用旧过失论,未免处罚过于宽泛。为了弥补旧过失论对这些社会必要高风险行业之要求近乎结果责任的不足,新过失论由此产生。新过失论顺应了现代危险事业对危险预见的必然性,转变了注意义务的侧重点,认为即使对危害结果有预见可能性,但如果行为人采取了避免结果发生的合理措施,就不会构成过失犯罪。根据新过失理论,排污企业只要没有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即达标排放),不管其主观上是否预见到了污染结果的可能性,都会因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结果回避义务而对环境污染事故不承担过失的刑事责任。
二、新旧过失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如何使用
目前污染环境罪在我国属于过失犯罪。“违反注意义务”作为这种过失犯罪的前提,对该义务的定性,会通向截然相反的结论。在达标排污致损的问题上,适用新过失论的入罪门槛较高,只要采取措施预防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就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相比之下,适用旧过失论入罪门槛较低,即使达标排放也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应当适用旧过失论。首先,两种过失理论产生的时间先后并不是衡量其适用价值的标准。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庞大复杂、缓慢稳定的过程,新诞生的事物或理论并不必然会得到广泛的适用,旧的理论依据也不会因个别新事物的产生而迅速且明显地失去价值。以我国刑法为例,现行刑法虽然在一些具体罪名中规定了许多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的情形,但仍规定了第233、235条的普通过失致人死亡、重伤伤罪,而其适用旧过失论。大量事实表明,旧过失论并没有过时。其次,新过失论的重要依据是“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如前文所述,虽然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必然伴随着合理的风险,但在具体案件中,与危险所威胁或侵害的法益相比,仍需再三斟酌。一方面,发展固然重要,但人权才是根本,不能一味追求科技的发展而牺性了公众的生命健康。另一方面,允许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和那些根本没有应注意之风险的案件之间,也不完全是泾渭分明的。再次,虽然新过失论是近代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企业的排污问题上不宜适用新过失论。事实上,从事业务之人反而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对业务的熟知和专业使他们对该业务行为潜在的危险性具有比一般人更为明确的认识,由此导致的过失也当然比一般的过失罪责严重。同时,考虑到刑事立法政策,相比于普通行为,业务过失行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险性更高。最后,即便适用新过失论,要判断排污企业是否真的履行了结果回避义务也是相当困难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公诉机关必须承担被告人怠于履行法定义务的证明责任,否则法院便会因证据不足而作出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判决。而在实践中,污染结果的潜伏性、排污行为对人身或财产法益侵害的间接性、污染涉及的科学部门的广泛性与复杂性,以及排污企业较强的反侦查性,往往使侦査机关在熟悉行业情况的排污企业面前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结语
“只要不超标,管它污染谁”,面对高举“达标排放”挡箭牌的污染企业日益肆意妄为,污染环境罪无异于一纸空文,何况“排污费”后的黑幕普遍存在,苦了百姓,害了万代。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与结果回避义务相比,要更加强调排污企业的结果预见义务,“应预见、能预见而不预见,应避免、能避免而不避免,就是追究达标排污致损刑事责任的理由。”明面对现今如此频频发生的严重环境公害行为,为避免污染环境罪“设而不用”,立法者可以考虑将“违反国家规定”变为该罪的法定加重情节,即将其从定罪标准转变为量刑依据,从立法上严格要求,对国家、人民和民族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