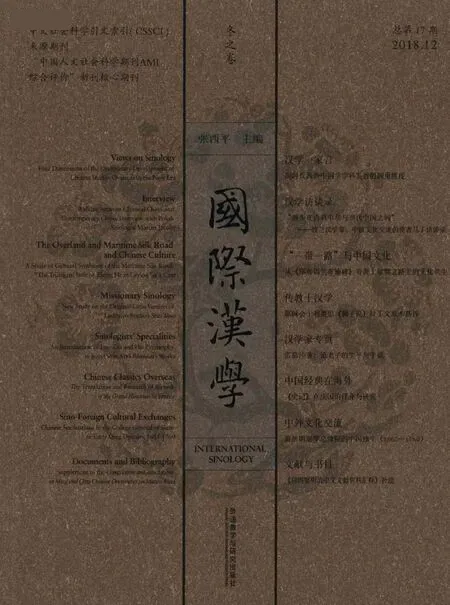论丁韪良对中国科举制的评介*
丁韪良(W.A.P.Martin, 1827—1916)是晚清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也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最为重要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在华近六十年,长期广泛地参与中国各级机构的教育事业,①其在中国的主要教育活动包括:1851年,在宁波开设两所学校(见R.R.Covell, W.A.P.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Washington, D.C.: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0);1864年,在北京开办崇实馆(见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92—94页);1865年,出任同文馆英文教习(见W.A.P.Martin: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p.152),并于1869—1895年间担任该馆总教习(见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 1896, pp.293-327);1898—1902年间,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见陈平原:《不被承认的校长——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载《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5—113页);1902—1905年间,在张之洞拟创建的武昌大学担任校长(见W.A.P.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ork: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7, pp.229-238)。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并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并以汉学家身份,通过英文著述演讲等方式向西方进行系统介绍,成为中国科举制西渐史上的重要人物。
本文梳理丁韪良评介中国科举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强调他对科举制所持的异于同时代其他西方人士的理性褒扬态度。在此基础上,将丁韪良的评介活动回置于近代中西方权力关系背景下,以19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在国际法框架内所制定的世界“文明等级”秩序为参照,分析丁韪良持这一态度的潜在动机,并探索丁韪良对科举制的评介在中美两方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一、评介的途径和主要内容
丁韪良对中国科举制的评介集中体现为他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向美国提交的两篇英文报告。1869年,丁韪良在美国东方学会宣读《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制度》,②会议提要见 W.A.P.Martin, “On the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ystem in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869, pp.liv-lv.全文于1870年以《中国的竞争考试》为题刊载于《北美评论》,③W.A.P.Martin,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in China,”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XI, no.CCXXVIII, 1870, pp.62-77.并于1880年和1881年先后收录于《翰林集》和《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两部个人英文文集。①分别见W.A.P.Martin, Hanlin Papers.London: Trubner & Co, 1880, pp.51-74; W.A.P.Martin, 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Philosophy and Letters.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1, pp.39-56。1901年,稍加修改补充后,以《论科举考试》为题收录于另一部英文文集《中国的学问》。②W.A.P.Mart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The Lore of Cathay,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 1901, pp.308-328.此三部文集分别在伦敦、纽约、芝加哥等地出版。
另一篇是丁韪良于1875年向美国教育部提交的调查报告。原文于1877年由美国教育部发行,后以《论中国的教育》(“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in China”)为题收录于《翰林集》和《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③分别见Hanlin Papers, pp.75-110.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 pp.57-84。经修改补充后以《论学校和家庭教育》为题收录于《中国的学问》。④W.A.P.Martin, “School and Family Training,” in The Lore of Cathay, pp.281-307.除两篇专题报告外,丁韪良在1896年《中国六十年记》(A Cycle of Cathay)、1900年《北京被围记》(The Siege in Peking)以及1907年《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等三部个人后期英文传记和回忆录中,也多次对科举制进行介绍,⑤分别见A Cycle of Cathay, pp.42-43, 318-319, 455; W.A.P.Martin, The Siege in Peking.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0, p.40; The Awakening of China, pp.109-111, 121-125, 234-235。并在纽约、芝加哥、多伦多等地出版。
这些报告和著述的主要内容涉及:(1)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2)民间教育在中国的普及情况;(3)中国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接受教育的具体情况;(4)历代中国政府在教育事业中发挥的作用;(5)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和演变;(6)科举制各级考试的选拔机制;(7)科举制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8)科举制的主要弊端;(9)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改革意见;(10)科举制对美国文官选拔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丁韪良所谈及的许多内容,对于19世纪的西方并非全新的知识。在此之前,从16世纪起,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等群体就曾有所介绍。⑥关于16世纪以来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介绍和影响,有如下主要研究成果:Y.Z.Chang, “China and English Civil Service Refor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42 (3), pp.539-544; S.Y.T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3 (4), pp.267-312; 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88—202页。但是,这些群体要么处于中西交流初期,与中国并无深入接触,对科举制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听途说加异域想象的产物;要么过度注重商业、政治或宗教利益,对中国教育事业并无亲身参与,其介绍往往只触及皮毛,且零星武断。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真正以教育家和汉学家的视角,在深入接触和了解的基础上,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科举制者,丁韪良可谓第一人。
二、异于同时代的理性褒扬态度
与涉及的内容相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丁韪良对科举制所持的态度。总的说来,丁韪良在介绍过程中持一种辩证、客观的态度,既有褒扬,也有批判。不过,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在有限的论及科举制弊端之处,丁韪良往往话锋一转,随即展开正面的辩护,⑦例如,(1)虽然中国女性受到教育歧视,但其中不仅能够涌现出女诗人、女学者,还有不少人成为优秀的母亲,培养出优秀的后代(The Lore of Cathay, p.285, 299-300);(2)虽然科举制影响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但中国人的智慧潜力并不亚于世界上最好的民族(The Lore of Cathay, p.284);(3)虽然科举考试内容陈旧单一,注重文学而忽略实际,注重儒家伦理道德而忽视自然科学,束缚了个人和社会发展,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任何时期,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都并不落后于西方(The Lore of Cathay, p.321);(4)虽然中国政府把科举考试当作选拔官员以维持国家运作的工具,并不真正关心公众教育事业,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知识的普及(The Lore of Cathay, pp.301-302);(5)虽然科举考试存在徇私舞弊、买官卖官等现象,但也有严厉的处罚机制相制约(The Lore of Cathay, p.326)等。并最终落脚于理性的褒扬,认为科举制是“中华帝国最令人羡慕的制度”。⑧The Lore of Cathay, p.309.
要理解这一态度有何耐人寻味之处,需将它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在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文明水平领先西方,中西交往并不深入。要么出于浪漫的异域想象,要么出于为本国变革提供理想之参照,西方对中国的文明形象常常是极端美化。以汉学家、启蒙思想家和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对科举制往往也表现出一味褒扬的态度。①如门多萨(Juan de Mendoza, 1545—1618)、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和伏尔泰(François Voltaire, 1694—1778)等人对科举制的赞扬和推崇。具体参见“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pp.276-300.《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第190—193页。而自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欧美工业革命以来,中西方文明水平此消彼长。加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正面冲突,使得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整体上急转直下。在此背景下,与丁韪良同时期来华的19世纪西方汉学家和新教传教士等西方群体对科举制虽然不乏理性之辞,但绝大多数人在向西方进行介绍时都落脚于否定和批判。②如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 1812—1884)、林乐知(Young J.Allen, 1836—1907)、狄考文(Calvin W.Mateer, 1836—1908)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等人对科举制的集中批判。具体参见孙邦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判》,《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第47—53页。杨齐福:《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与批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5—19页。
对于上述背景,丁韪良是清楚的。他在《论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就曾提到:“西方公众对科举考试并非不曾听闻,但却未能获得恰当的了解。因为,有人认为其价值受到过度高估,且这一观点还在蔓延。他们认为是科举考试造成了中国人精神文明的所有弊端,事实却正好相反。”③The Lore of Cathay, p.303.显然,丁韪良所谓“有人认为其价值受到过度高估”,主要是指19世纪以来的新教传教士一反18世纪以前耶稣会士的赞美,对科举制体现出贬抑的态度。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则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丁韪良本人对科举制所持的、与同时代其他新教传教士针锋相对的积极判断。
三、隐晦而深刻的宣传动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带着相同的传教使命而来,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较之其他新教传教士,丁韪良为何会对科举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认知和评判?个中缘由,自然包括他在华时间长,④丁韪良1850年来华,1916年在北京去世。66年间,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共计8年左右。所以,他在华活动的确切时间为将近60 年,比绝大多数其他新教传教士长。有着更深的中国情结,也包括他更加广泛地参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对中国教育考试制度有着更为“同情”的理解。但是,如果结合19世纪中西方之间特定的权力关系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之下丁韪良所具有的特殊的个人身份,则可以做出一个推测:丁韪良之所以逆反19世纪西方传教士群体的主流观点,以理性褒扬的态度向西方介绍科举制,其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潜在的动机。这与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在国际法框架下对中国的“文明等级”定位相关,也与丁韪良本人的国际法学家、美国外交官以及西方传教士等多重身份相关。
1.19世纪西方国际法对中国的“文明等级”定位
在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有将异族贬低为“野蛮”,将自我标榜为“文明”的传统。15世纪末以降,随着全球地理大发现和东方新航路开辟,各大洲不同种族相继进入欧洲视野。18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西方人自我优越意识进一步上升以及对外殖民扩张所需,西方殖民主义学者以种族肤色为界,将全世界不同民族以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为序排列为高低等级,建立起“文明(civilized)——野蛮(barbarian)——蒙昧(savage)”的“文明等级”秩序,⑤B.Mazlish,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9-60.作为黄色人种的中国人被定位于“野蛮”行列。
18至19世纪之交,关于中国的“野蛮”话语由小范围的殖民学术圈向西方社会诸多领域蔓延。自启蒙时期以来,中国在西方社会的正面印象崩溃瓦解,“野蛮”形象取而代之。中国之“野蛮”无疑为西方强权在“文明使命”之下的武力征服提供了必要理据。19世纪,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法美等西方“文明”国家以武力打开“野蛮”中国的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到开放通商、治外法权和传教自由等诸多利益。
“野蛮”可以凭借武力相征服,而征服之后的既得利益,还需要相关国家之间的法律条约,才能合理化巩固,并长期维系。不过,一方面,在19世纪,源于西欧内部的国际法被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等西方主流法学家明确界定为“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s)之间的法律。①H.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6th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5, p.22.因此,不论是为了使中西方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国际法体系内的严格合法性,还是促使清政府遵守和履行不平等条约,都有必要赋予中国“文明”国家的身份象征。但另一方面,在19世纪西方列强看来,中国并不符合启蒙以来由西方国家所确立的诸多“文明”标准,②详见 G.W.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14-15。且西方殖民势力并不愿真正给予中国平等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
两相权衡之下,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国际法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权宜性质的“半文明”(halfcivilized)话语,18世纪以来西方所建立的“文明等级”秩序被细化扩充为“文明——半文明——野蛮——蒙昧”四个等级。吴尔玺(Theodore D.Woolsey, 1801—1889)等权威法学家都将中国在法理上划归为“半文明国家”(half-civilized nations)之列,③T.D.Wools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2nd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864, p.232.企图依靠这种“文明”与“野蛮”之间模棱两可的文明等级定位,将中国置于西方近代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一方面,以向“文明”靠拢的名义,促使中国遵守国际法律条约,以便维持西方在华所取得的殖民利益;另一方面,以尚未脱离“野蛮”为借口,拒绝中国享有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权利。2.丁韪良的国际法学家和美国外交官身份
一方面,丁韪良对近代西方国际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早在1864年,他就因为将惠顿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为《万国公法》而名声大振,④丁韪良:《万国公法》,北京:京都崇实馆存板,同治三年。成为西方在中国的国际法权威,并于随后出任同文馆国际法教习。在正式接任该职务前,丁韪良还于1867年专门返回美国,师从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吴尔玺学习国际法,并且在此期间阅读了吴尔玺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⑤1877年,丁韪良将吴尔玺这部国际法著作译为汉语,以《公法便览》为题在中国出版。在该汉译本的“凡例”中,丁韪良曾提到:“余于丁卯年(即1867年)请假回国,曾在雅礼学院(即今美国耶鲁大学)得识吴君,观其教法,心甚羡之。复读是书(即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复令译以汉文,俾得公诸同好。”(见丁韪良:《公法便览》,“凡例”,北京:同文馆聚珍版,光绪三年。)因此,在1869年和1875年分别向美国国内提交关于中国科举制的两篇调查报告之前,丁韪良就已经知晓国际法属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法律这一性质,也知晓西方国际法学界据此对中国做出的“半文明”等级定位。
另一方面,丁韪良与西方殖民势力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858年来华初期,他就以美国外交官身份参加过《中美天津条约》谈判,并利用自己的汉语能力为美国谋取到诸多利益。⑥详见W.A.P.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pp.90-98。即便后来就任清政府官职,仍大力鼓吹美国对中国进行领土侵占。⑦详见The Siege in Peking, pp.155-157。作为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丁韪良自然也懂得,只有当中国的“半文明”身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才能够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具备合理的法律效应。因此,“半文明”的国际形象对于巩固和维护西方在华殖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19世纪的西方,有关中国“半文明”的话语主要存在于国际法学界。在西方社会的其他领域,18世纪下半叶以来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的“野蛮”形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负面印象仍根深蒂固。如丁韪良1868年在美国东方学会演讲中指出:
没有哪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多的误解。他们被抨击为麻木呆板,因为我们没有足够透明的媒介向他们传递我们的思想,或向我们传递他们的思想;他们被诬蔑为原始野蛮,因为我们缺乏胸怀去了解一个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他们被描述成卑屈的模仿者,尽管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少挪用他人成果;他们被描述为缺乏创造能力,尽管全世界都曾受惠于一长串最为有用的发明;他们被描述为死守传统遗产不放,尽管在历史上他们经历了众多深刻的变迁。①见 Hanlin Papers, p.297.The Lore of Cathay, p.8。(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为了消减中国在西方社会中的“野蛮”印象,使之契合于国际法对中国的“半文明”定位,丁韪良一生曾利用自己汉学家的身份,通过一系列英文演讲、著述和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诸多层面中的“文明”要素进行了诸多积极肯定的介绍。②物质层面包括茶叶、瓷器、丝绸以及古代四大发明等,制度层面包括古代公法和外交制度等,精神层面包括儒家哲学、宗教信仰以及文学诗歌等。丁韪良认为,中国社会在以上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高度“文明”的要素。由于科举制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笔者看来,丁韪良以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西方人士的理性褒扬态度对之进行介绍,一个重要的潜在动机即在于,以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为例,向西方社会展示中国所具有的“文明”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野蛮”偏见,从而将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定位于19世纪国际法所规定的“半文明”之列,使得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具备国际法框架下的法律效应,维护西方在华所取得的殖民利益。3.丁韪良的西方传教士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自古希腊以来,宗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督教兴起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基督信仰一直是欧洲“文明”的核心标志。③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pp.23-24.说到“文明”,西方公众往往联想到其中的基督教因素。因此,作为来华传教士,丁韪良以理性褒扬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在宣扬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明”元素的同时,也在向西方暗示中国社会具备接受基督教的基础,进而争取西方教会和公众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④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曾指出,18世纪欧洲耶稣会士通过西文著述来美化中国形象,原因之一是为了“便于为教会的中国活动募捐”(见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丁韪良以褒扬的态度向西方介绍科举制,就促进传教而言,其动机与此有类似之处。
四、“文明”元素在科举制中的具体体现
具体而言,丁韪良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宣传科举制中所包含的“文明”元素,从而消减西方公众对中国的“野蛮”印象,最终将中国的文明等级向“半文明”提升的呢?细读其两篇报告文章,不难发现,其做法是挖掘并展示科举制与近代西方“文明标准”契合之处。
首先,由于工业革命以来新型生产力所造就的物质繁荣奠定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础,因此在整个19世纪,西方文明标准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源发之活力”(agency),即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社会发展的能力,包括在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精神等各方面的发明能力和创造能力。⑤J.M.Hobson,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 34.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世界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民族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源发之活力”,所以只有在西方“文明使命”的帮助之下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丁韪良将科举制的雏形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舜的时代,明确表示它产生于“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早时期”,强调中国人是这一制度“源头上的发明者”,⑥The Lore of Cathay, p.309, 311.正是为了纠正西方关于中国人“原始野蛮”和“缺乏创造”的印象,说明中国人并非“卑屈的模仿者”,而能够以自身“源发之活力”贡献出值得西方人学习的制度发明。
第二,较之古代和中世纪,工业革命给近代西方社会带来巨大变化,因此,在19世纪西方文明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①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p.52.较之西方,“野蛮”的东方往往被视为“停滞”不前。为了纠正西方关于中国人“死守传统”的印象,丁韪良多次强调科举制中所体现出的“进步”元素。一方面,中国人自幼年开始读书,经历各个阶段,向秀才、举人、进士等更高层次不断努力的过程,体现了个人对“进步”的追求;②The Lore of Cathay, p.317.另一方面,科举制经历远古、周汉、唐宋、明清等不同历史时代,其考试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完善,体现了该制度本身的“进步”。③Ibid., p.313.更为重要的是,除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器物之外,科举制也在制度层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④Ibid., p.308.
第三,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得人权大于神权、民权大于君权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标准中,“民主”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点。⑤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p.14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则往往以“专制”“暴虐”和“野蛮”的他者形象出现在西方的“民主”叙事之中。为了扭转西方社会的这一负面印象,丁韪良特别强调突出了科举制的“民主”性质。他指出,在中国,任何人均有权利参加科举考试,且唯一的选材标准就是个人能力,除此以外,任何世袭爵位、君主旨意、帮派推选或个人财富都无助于应试者中榜。这体现了“真正的公平”,并且说“这种真正的民主,全世界的国家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⑥The Lore of Cathay, pp.310-311.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1901年的英文文集《中国的学问》中,丁韪良专门介绍了《论学校和家庭教育》一文诞生的历史背景。他指出,该文是应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邀请,向美国教育部提交的调查报告。美国教育部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是为了弄清科举制“如何导致了中国文明的衰败”,⑦Ibid., p.281.可见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集体偏见。作为回应,丁韪良在文末添加了一段此前版本没有的后记。在这段后记中,丁韪良描述了美国议会选举的混乱,将之与科举选拔进行对比,最后反问道:“可见,在选拔官员方面,哪种方式更加文明?”⑧Ibid., p.328.
五、对中美双方的历史影响
文明形象的建立和传播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因此很难说丁韪良凭借两篇调查报告,就能够实现中国形象由“野蛮”向“半文明”的提升。不过,丁韪良的介绍促进了西方对科举制的了解,并且对中美两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奠定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对美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影响
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文职官员的任用主要实行政党分肥制。党派利益的争夺使得政府在任用官员方面徇私枉法,效率低下。1866年,众议院进行改革,开始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官员。到1883年,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文官考试制度在美国初步确立。在此期间,丁韪良于1869年在美国东方学会宣读第一篇专题报告《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制度》,于1877年在美国教育部出版第二篇调查报告《论中国的教育》。在两篇报告中,丁韪良把科举制的优越性跟美国政党分肥制,乃至整个西方中世纪以来贵族政治的弊端进行了鲜明对比,并呼吁美国加以借鉴。⑨他表示,在科举体制中,“财富无法使其拥有者获得职权,统治者也无法凭借其意志将职位授予毫无教养的宠徒,大众也无法根据其偏好将国家的荣誉授予无能的政客”(The Lore of Cathay, p.311)。并呼吁,“难道在我们自己的共和国体制中不应该移植一些类似的品质吗?科举制与我们自由政体的精神更为契合,可以预见,在我们国家将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The Lore of Cathay, p.326)。
不可否认的是,在美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之前,英法德等国已经开始实行该制度。作为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西方国家,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在渊源上必然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不过,如丁韪良所强调,文官考试制度“在这些国家采用只是近来之事,且适用不广。要看清该制度如何在足够广阔的范围发挥作用,如何在足够长期的范围充分展示其利弊,还得将目光放到更远的东方”。①The Lore of Cathay, p.308.丁韪良的两篇报告问世于美国文官考试制度由萌芽到确立的关键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丁韪良以权威汉学家和职业教育家身份,对中国科举制所做的系统客观而又理性褒扬的介绍,使美国政府对文官考试制度的内在价值产生了积极的认同,进而在操作层面引进了英法德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简而言之,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直接借鉴了英法德等国在考试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近代元素,其根本理念却植根于中国科举制的精神理念。对于丁韪良在美国文官考试制度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学者刘海峰表示:“丁韪良是主张美国借鉴中国科举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的人中最为积极且最典型的一个。”②《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第199页。而美籍华人学者邓嗣禹(Ssu-yu Teng)则更加决断地表示,正是丁韪良对科举制的推崇和呼吁,使得美国政府引入了文官考试制度。③“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p.308.
2.对中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影响
丁韪良对科举制的褒扬性介绍,不仅促进了美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还以某种迂回的方式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由孙中山创立。1906年,孙中山在首次公开宣传《五权宪法》时,提出考试权独立,且所有政府官员均需参加资格考试。1924年,该制度被写进《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游历欧美,对西方社会制度多有认可,因此很容易使人认为其文官考试制度借鉴自近代欧美。不过,他本人曾提到,“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④《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第188—189页。显然,孙中山所谓“中国的考试制度”即科举制。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科举制1905年已遭废除,那么孙中山这样一位资产阶级西化派人士对科举制这一中国传统制度的信心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近代西方人士对科举制的褒扬和赞赏。如前文所述,在整个19世纪来华西方人士中,对科举制持理性褒扬态度者,除丁韪良之外寥寥可数。而据民国学者吴经熊(John C.H.Wu, 1899—1986)和当代海外学者汪一驹(Y.C.Wang)分别考证,孙中山在一系列呼吁设立文官考试制度的演说中,多次引用丁韪良在两篇报告中对科举制的正面评价。⑤见J.C.H.Wu, Sun Yat-sen: The Man and His Ideas.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71, p.341.Y.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33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丁韪良以权威汉学家和职业教育家的身份向西方社会发出的声音,坚定了孙中山对科举制的信心,使得科举制以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吸收了近代西方合理元素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在中国确立起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
结语
考察丁韪良的中英文著述,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其中文著述中,存在大量对中国的批判;而在其英文著述中,又存在大量对中国的赞扬。在笔者看来,这种看似矛盾之处可以从丁韪良特殊的个人身份中得到解释:丁韪良是精通西方国际法和中西方外交实践的传教士,他深谙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殖民强权对中国的“文明等级”定位。在中国,要打破中国人在传统华夷秩序中所形成的“文明”自我优越感;在西方,则要纠正公众自18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的“野蛮”印象,从而在近代国际社会中将中国置于“半文明”的地位,以便在国际法框架内维护西方已经取得的殖民利益和传教利益。
丁韪良以异于同时代绝大多数其他西方传教士的理性褒扬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一个潜在动机正是为了以传统教育考试制度为例,突出宣扬其中所蕴含的“文明”元素,以消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野蛮”偏见,最终将中国的“文明等级”定位于国际法所规定的“半文明”之列,使得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具备国际法框架下的法律效应,为西方在华的殖民利益和宗教利益服务。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和中国文化的本位,这无疑值得批判。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历史事件的动因往往纷繁复杂,某一具体人物具体行为背后的动机更是千头万绪,很难做出唯一的归结。本文从丁韪良的个人身份入手,挖掘线索,旨在为丁韪良评介科举制的潜在动机提供一个视角、一种解读,以期对理解这位重要汉学家该方面的汉学研究行为有所增益。
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就客观的历史效果而言,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真正以教育家的专业视角,在亲身接触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以权威汉学家的身份向西方系统理性介绍中国科举制的先驱,丁韪良不仅促进了西方对科举制,乃至该制度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内在精神价值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确立,其历史贡献无疑也值得客观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