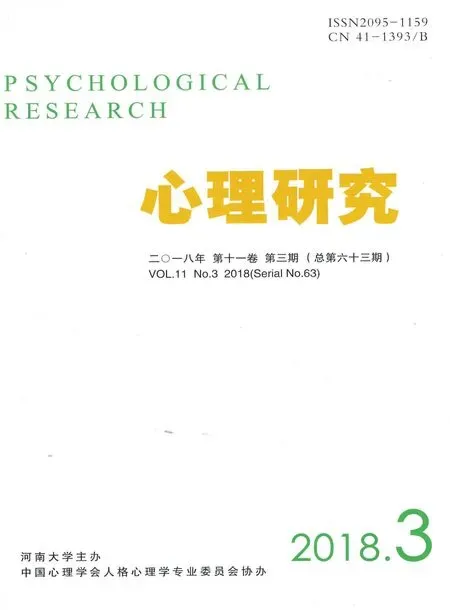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类型、机制与影响因素
刘建一 吴建平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83)
近年来,随着环境不断恶化,全球各地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环境灾害。解决污染,改善环境,已经成为公众的共同愿望。而亲环境行为 (pro-environment behavior,PEB)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Carrico et al.,2010)。Dietz,Gardner,Gilligan,Stern和Vandenbergh(2009)的研究指出,如果美国全民采取亲环境的生活方式,将减少美国20%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往的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和人格、情感、认知、价值观等心理因素能够有效地预测亲环境行为(Gifford&Nilsson,2010;余真真,田浩,2017)。在近年的研究中,亲环境行为之间的溢出效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研究者们认为合理的行为干预不仅仅能改变特定的亲环境行为,也可能会对公众其他类型的亲环境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也开始主张在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行为干预的手段(Allcott&Mullainathan,2010;Thφgersen&Noblet,2012)。因此,本文将对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参考。
1 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
“溢出”(spillover)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的情绪、态度、行为向其他领域发生转移 (Dionisi&Barling,2015),例如消极情绪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传递(严瑜,王轶鸣,2016)。在亲环境行为领域,一些研究者认为,溢出是指对特定亲环境行为的干预能够影响其他非特定亲环境行为。这里的干预意义比较广泛,包括鼓励、要求、宣传、教育、政策等(Thφgersen,1999;Thomas,Poortinga,&Sautkina,2016)。但有研究者指出,提醒人们过去做过的亲环境行为或者想象完成了亲环境行为任务,也能改变后续亲环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不需要对特定行为进行干预使其发生变化 (Van der Werf,Steg,&Keizer,2014b)。而且溢出是指已经发生的亲环境行为对未发生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综上所述,把溢出定义为过去的亲环境行为增加或者减少后续亲环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合适。
关于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研究是多样的,一些是通过调查的方式来探讨多种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相关性(Berger,1997;Ha&Kwon,2016)。 这些研究虽然不能证明溢出效应的因果关系,但是也为溢出效应提供了证据。更直接的因果证据来自实验研究 (Baca-Motes,Brown,Gneezy,Keenan,&Nelson,2013)。研究者们一般通过几种实验操作来研究溢出效应:一是让被试完成一项亲环境行为任务,例如回收塑料瓶 (Truelove,Yeung,Carrico,Gillis,&Raimi,2016)或者绿色消费 (Lanzini&Thφgersen,2014);二是让被试回想之前做过的亲环境行为,例如让被试写出之前做过的亲环境行为或者让被试阅读亲环境行为条目(Lacasse,2016);三是让被试想象参与了一项环保行动,例如想象自己购买了一辆电动汽车来上下班(Van der Werff et al.,2014b);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更困难的方法,通过现场实验研究来检验溢出效应(Lanzini&Thφgersen,2014)。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发现了混合的结果,一些研究证明了积极溢出效应的存在,但是部分的研究发现了消极溢出效应。
1.1 亲环境行为积极溢出效应
人们渴望行为是一致的,当个体行为不一致时,他们就有可能接收到外界的压力。比如被他人认为是虚伪和两面派的,这导致了人们期望保持行为的一 致 性(Abrahamse,Vlek,&Rothengatter,2005)。 Freedman 和 Fraser(1966)指出,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effect,FITD)就是行为一致性的表现,诱发个体答应一个小要求之后,个体更容易同意一个更大的要求。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自我感知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对积极溢出的过程进行解释。自我感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对自身亲环境行为的判断和发生背景形成亲环境的态度和认同(Bem,1967)。认知失调理论则认为,为了避免心理紧张出现,个体会维持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Festinger,1957)。当过去的亲环境行为使个体形成了亲环境态度或认同,为了避免心理紧张的出现,个体仍旧会以亲环境的方式行事。此外,目标理论(goal theory)也可以对积极溢出效应做出解释,亲环境行为可以激活亲环境目标,而亲环境目标可以促进随后的亲环境行为(Dhar&Simonson,1999)。
实证研究也发现了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效应。研究指出,回收行为和包装袋的使用(Thφgersen,1999)、能源保护、节约用水、使用环保购物袋 (Berger,1997)、 绿色消费 (Ha&Kwon,2016)均呈正相关。类似的,研究也发现了其他亲环境行为之间的正相关,例如省油驾驶风格与减少肉的购买 (Van der Werff,Steg,&Keizer,2014a),多种亲环境行为与环境政策支持(Tobler&Siegrist,2012)。一些研究者也通过实验研究为积极溢出提供了证据。 Evans,Maio 和 Corner(2013)发现将汽车与他人共享的被试组更倾向于把纸扔进可回收型的垃圾箱。Baca-Motes等人(2013)在酒店进行了一个现场研究,允许被试以匿名的方式承诺减少毛巾使用,且不告知对被试的行为进行记录。结果表明,承诺减少毛巾使用,不仅仅会减少毛巾的使用,也会减少电灯的使用。Van der Werff等人(2014b)发现,让被试回想过去做过的亲环境行为能够显著增加被试选择可持续产品的可能性。此外,为了评估积极溢出的长期性,研究者采用了纵向研究的设计,Lauren,Fielding,Smith 和 Louis(2016)对居民节水行为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结果发现,简单的节水行为能够显著预测困难的节水行为,比如安装节水设备。
1.2 亲环境行为消极溢出效应
虽然研究者们期望出现积极溢出效应,但是少量研究也发现了消极溢出的结果,并且能对这些消极的溢出效应做出合理的解释。认知失调理论解释了积极溢出效应,但如果过去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被迫采取的行为,行为一致性的结果就不会出现(Collins&Hoyt,1972),或者过去的亲环境行为比较简单,唤起水平达不到目标激活的阈限值(Van der Werff et al.,2014b),积极溢出也不会发生,甚至由于道德执照(moral licensing)等效应的存在而出现消极的溢出。
一项关于假期旅游计划的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环保倾向最高的参与者往往会选择碳密集型的交通 方 式 出 行(Barr,Shaw,Coles,&Prillwitz,2010)。与这个结果相类似,Miller,Rathouse,Scarles,Holmes和Tribe(2010)的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在家里做了很多亲环境行为,他们就认为不需要采用环保的方式来选择旅游方式。这表明参与一项环保行动可能会减少参与其他环保行动的道德义务感,从而不再参与其他环保行动。另外,实验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证据。在一个节约用水的实验中,将相同公寓的居民分为两组,实验组居民收到了自来水使用量的反馈,而控制组不做任何的干预,结果发现反馈确实能够减少实验组居民自来水的使用量,但是实验组的居民会使用更多其他种类的能源(Tiefenbeck,Staake,Roth,&Sachs,2013)。Lin 和 Chang(2017)在探索浪费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比较反对浪费发生,过去做过的亲环境行为也会让他们产生亲环境行为凭证,从而降低对自我消费行为的约束性,最终导致浪费行为。
2 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中介机制
那么溢出效应为什么会发生呢?研究者们对其中介机制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索,通常认为包含两种相反的路径:环境自我认同、自我效能感、个人规范等可以用来解释积极溢出效应;道德自我形象、内疚感等可以用来解释消极溢出效应。这些中介变量同时存在形成了竞争性中介,而积极溢出和消极溢出就是在不同情况下不同变量发挥作用大小不同所导致的。
2.1 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作用
环境自我认同 (environmental self-identity)指的是个体将自己看作是环保人士的程度(Whitmarsh&O'Neill,2010)。 Poortinga,Whitmarsh 和 Suffolk(2013)通过对比实施一次性口袋收费政策的威尔士和没有实施任何政策的英格兰发现,威尔士居民会有更强的环境自我认同。而且环境自我认同比较强的人更有可能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去生态型的商店(Whitmarsh&O’Neill,2010),回收物品,避免通过飞机去旅行,选择可持续的产品,减少纸的使用(Van der Werff et al.,2014a)。 此外,研究发现环境自我认同可以作为亲环境行为积极溢出的中介变量。Van der Werff等人(2014b)的研究指出,通过提醒人们过去的亲环境行为能够加强个体的环境自我认同,然后又促进了后续亲环境行为的发生。Lacasse(2016)的研究发现,使人们回想起过去的亲环境行为虽然增强了人们的环境自我认同,但同时降低了人们的内疚感,两个作用相互抵消,积极溢出效应没有出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使人们回想起过去的亲环境行为之后,给予一个环保反馈,环境自我认同进一步增强,出现了积极溢出效应。
2.2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强调我们可以通过边做边学的过程发展相关的技能、意识、知识和自我效能感(Bandura,1986)。所以当人们做了亲环境行为之后,可以获得知识和技能,增强了自我效能感,从而更容易做更多的亲环境行为(Thφgersen,Haugaard,&Olesen,2010)。 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亲环境行为的发生,例如回收行为(Tabernero,Hernández,Cuadrado,Luque,&Pereira,2015)。 此外,自我效能感是亲环境行为积极溢出的中介机制已经得到了证明。 Steinhorst,Klöckne 和 Matthies(2015)通过框架效应对被试进行干预,结果发现,相比于金钱框架,环境框架能够显著增加被试的自我效能感与个人规范,从而加强了被试的气候友好倾向。Lauren等人(2016)发现,简单的节水行为能够预测复杂的节水行为,而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3 个人规范的中介作用
在传统的规范激活模型中,个人规范(personal norms)被定义为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特定行为的自我期望,体现为道德义务感(Schwartz,1977)。目标理论指出,当被试出于环保的原因去从事亲环境行为或者参与环保运动,就会激起环保目标,这些目标就会反映在相关的心理结构上,例如激活的亲环境行为个人规范(Thφgersen&Ölander,2003)。而相关研究已经重复证明了个人规范对于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例如回收倾向 (Wan,Shen,&Choi,2017),交通工具的选择 (Klöckner&Blöbaum,2010)。 此外,Steinhorst等人(2015)的研究直接证明了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受到个人规范的中介作用。
2.4 道德自我形象的中介作用
当人们成功完成了一个道德行为,道德执照效应就可能会出现。道德执照效用指的是,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做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接下来的行为更可能是非道德的,这是因为以道德的方式行事能够提高个体的道德自我形象(moral self-image),从而降低他们道德义务感与参与道德行为的意愿,甚至做一些非道德的行为 (Blanken,Van,&Zeelenberg,2015)。也有研究者认为道德执照效应是为了维持道德自我形象的平衡(Thφgersen&Crompton,2009)。 Cornelissen,Bashshur,Rode 和 Le(2013)的研究发现道德自我形象在最初的道德行为与欺骗之间起中介作用。亲环境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道德行为,也会受到道德自我形象的影响。当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如果人们感觉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部分,他们可能会放弃执行后续与环保相关的行为(Lin&Chang,2017;Van der Werff et al.,2014b)。
2.5 内疚感的中介作用
情绪反应可以源于对亲环境行为的感知并且可以激发未来的亲环境行为和态度。具体来讲,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没有采取环保行动,就会觉得内疚(guilt),而内疚感就会成为人们决定从事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Lacasse,2016)。Harth,Leach 和Kessler(2013)通过提醒被试所在的小团体带来的环境污染成功引发了他们的内疚感,结果发现他们更愿意为环境破坏承担后果,比如节约能源,甚至支付环保税。实证研究已经发现了内疚感在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中起中介作用。Lacasse(2016)发现,使人们回想起过去做过的亲环境行为能够降低他们的内疚感,从而减少他们之后的环境政策支持。
3 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前人已经发现溢出效应的混合结果,而为了促进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抑制亲环境行为的消极溢出效应,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探索。综合以往研究,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种:反馈框架、行为特征和行为归因。
3.1 反馈框架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指的是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描述会使决策者产生不同的选择 (张凤华,邱江,邱桂凤,张庆林,2007)。具体而言,对亲环境行为给予不同的反馈会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决策。研究已经表明,提供反馈可以有效地促进能源节约,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Fischer,2008)。针对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研究者主要探讨环境框架和金钱框架两种决策框架的影响。
根据营销手段和传统观点,人类的上进心主要是由于利己的本质(Miller,1999)。所以当亲环境行为能给人们带来更多利益时,比如低碳驾驶能够节约燃料,人们更可能继续从事这些亲环境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金钱框架可能比环境框架更有效。但是研究者也提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反馈内容会使个体产生不同的动机,环境框架会激发人们利他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亲环境行为带来的效益很小,人们还是很愿意为环保做努力。而金钱框架会激发人们的利己动机,只有行为带来足够好处才会促使人们继续执行下去,而且这种效果往往不会扩散到其他类型的亲环境行为上,所以环境框架可能比金钱框架更有效 (Dogan,Bolderdijk,&Steg,2014)。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第二种观点。Dogan等人(2014)通过对环保驾驶行为的研究发现,相比金钱框架,环保框架下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环保驾驶倾向。Steinhorst等人(2015)对省电技巧提供两个不同的反馈框架,结果发现相比于控制组,环境框架和金钱框架组具有较高的省电倾向,但是只有环境框架组能够正向溢出到其他类型的亲环境行为倾向上。这表明了环境框架能够更好地促进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而金钱框架可能只能促进同类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甚至是没有溢出效应。
3.2 行为特征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亲环境行为本身的特征能够影响溢出效应的方向。Gneezy,Imas,Brown,Nelson和Norton(2012)指出道德执照效应的大部分证据来源于那些初始行为相对简单或成本较低的研究,当最初的行为代价较高时,积极溢出效应才会出现。Van der Werff等人(2014b)指出亲环境行为数量越多,类别越多,难度越高,和他人相似性越低,亲环境行为的信号强度越强。结果发现,提醒被试多个不同类型的亲环境行为能够更好地提升他们的环境自我认同,选择更多的可持续产品。此外,他们的研究也同样发现,相比其他条件,让被试想象完成困难且惟一的亲环境行为任务能够使被试选择更多可持续的产品。溢出效应不仅仅会受到最初亲环境行为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之后亲环境行为特征的影响。Truelove等人(2014)指出,如果之后的亲环境行为比较困难,人们就很可能把最初的亲环境行为作为借口,不再做其他的亲环境行为。而且有研究发现,积极溢出效应只出现在了之后亲环境行为比较简单的情况下,而对那些困难的行为,积极溢出效应并没有出现(Lanzini&Thφgersen,2014)。
此外,相似性也会影响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认知失调理论已经指出了个体有维持行为一致性的期望。Margetts和Kashima(2014)指出,同一类型的亲环境行为的不一致会加重个体的心理紧张,这就使个体更不愿意这种不一致性发生。Steinhorst等人(2015)对被试的省电行为进行了干预,结果发现相比于不同类型亲环境行为,相同类型的亲环境行为更容易产生溢出效应。
3.3 行为归因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de theory)将动机分为两种: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当我们将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行为本身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内部动机就会被激活,但是如果将行为归因于获得外在奖励或者避免外界惩罚,外部动机则会被激活,而内部动机的激活会让我们更容易重复之前的行为(Deci&Ryan,2000)。 Maiteny(2002)指出,直接经验与持久和泛化的亲环境行为变化相关,而通过激励或法规手段推动的转变更为肤浅,必然会退化回老习惯。Van der Werff等人(2014b)认为,相比于被强制要求,如果我们自由地选择我们的行为,那么行为更可能被归因到内部因素,因此环境自我认同能够被加强,积极溢出就容易出现。Truelove等人(2014)也认为行为归因会影响溢出的结果,最初行为的外部归因会导致消极溢出的结果,而最初行为的内部归因导致积极溢出的结果。他们同时指出了一些基于价格的措施或者命令性和要求性的政策最终的实际效果可能会比较差。一项基于一次性口袋收费政策的调查发现,政策实施后虽然能够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但是会使其它的亲环境行为显著地变少(Thomas et al.,2016)。 出于成本的考虑,人们会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但是政策实施损害了人们的内部动机,从而出现了消极溢出。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基于省钱 (Evans et al.,2013)或者获得地位(Griskevicius,Tybur,&Van,2010) 而做出的亲环境行为,不能增加后续亲环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4 总结与展望
研究已经指出了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结果是混合的,过去的亲环境行为能够促进或者抑制之后亲环境行为的发生。对于两种溢出效应的解释也是不同的。过去的亲环境行为能够通过提升环境自我认同,加强自我效能感,激活个人规范来增加之后亲环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相反,过去的亲环境行为也会由于道德自我形象、内疚感而对后续的亲环境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包括三种:反馈框架、行为特征和环境归因。但是目前关于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研究仍然比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深入探讨其发生机制与影响因素。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未来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深化。
首先,进行更多的实验研究,尤其是现场实验研究来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往对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研究主要采用相关研究的方法,少部分采用实验研究的也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缺少现场实验研究的方法。而相比之下,现场实验研究有更好的外部效度,能够检测到真实生活条件下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结果,为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更好的参考。此外,有研究者指出,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会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对我们而言,亲环境行为的复杂性、熟悉度和重要性不同,之后亲环境行为的出现时间可能会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在实验研究中一些实际存在的溢出效应由于时间因素没有被检测到(Lanzini&Thφgersen,2014)。 因此在实验研究中应该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划分不同时间段进行测量。
其次,从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入手,验证并挖掘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中介变量。竞争性中介能够为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不一致的结果提供很好解释,很多研究已经对这些中介变量进行了验证,但是一些不支持的结果也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Truelove等人(2016)的研究并没有发现道德自我价值感、内疚感在溢出效应中发挥作用,相反的是回收条件下的环境自我认同显著低于控制条件下的环境自我认同。Truelove等人(2014)也指出只有基于负面情绪决策的亲环境行为才会导致这些负性情绪下降,从而降低之后亲环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表现为消极溢出效应。此外,应该深入挖掘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中介变量。例如,环境风险认知,以亲环境行为的方式行事会让人们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会让他们降低对环境风险的感知。Ha和Kwon(2016)也指出,回收行为可能会增加人们的环境关心,从而促进了他们的绿色消费。但基于此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环境风险感知和环境关心在亲环境行为溢出中的中介作用。
第三,建议未来研究探讨更多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文献中不一致的发现表明,需要更深入了解积极或消极溢出效应,探讨其他的影响因素来增加或减少其发生的可能性。Van der Werff等人(2014a)指出,环境自我认同不仅会受到过去行为的影响,也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而且价值观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价值观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此外,社会规范也可能影响溢出效应,个体的行为会受到他人和群体的制约,如果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感知很低,那么积极溢出效应可能就很难出现。
第四,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进行扩展,不仅仅局限于问卷测量的方式。目前的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方式对亲环境行为倾向而并非行为本身进行测量 (张庆鹏,康凯,2016)。这一局限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外部效度较差,一方面是由于行为倾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真实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存在,测量结果与真实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方式进行扩展,对被试的亲环境行为进行直接测量。例如让被试记录每天与环保有关的行为,也可以设置场景观察被试的亲环境行为。
最后,未来的研究应该以政策制定为出发点,对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实际效益进行考量,有两点研究者要注意。一是溢出效应的净效益。消极溢出虽然必定会给环境带来一些损害,但如果干预对目标行为改变很大,能带来很大的环境效益,即使出现了消极溢出效应,总体利大于弊,这种干预手段仍然是有效的。二是积极溢出效应的持续时间。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希望看到亲环境行为积极溢出效应,但积极溢出效应的持续时间往往会被研究者所忽略。类似于人们追求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一样,如果积极溢出效应的实现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但是溢出效应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带来很小的环境效益,这种“投资”就不是最佳的选择。因此,研究者应该考虑溢出效应的实际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