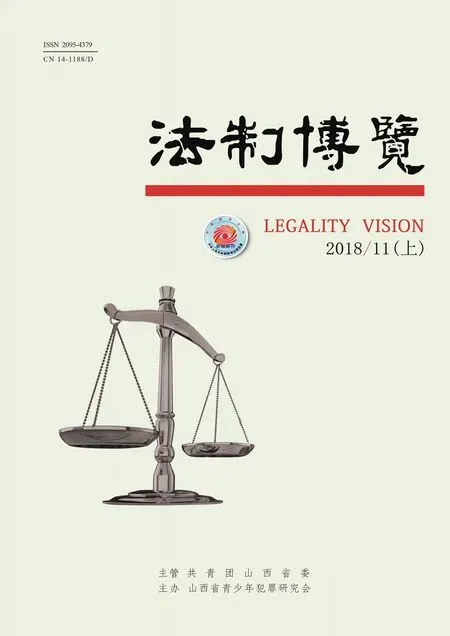浅析自然法与实在法的辩证关系
——基于方孔先生理论的一些反思
刘小稚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对方孔先生理论起点的质疑
(一)自然法概念存在局限
在方孔先生看来:“自然法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影响的,是一种类似于科学定理、自然规律的在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未经人的认识的规律。”[1]对于人作为生物这点,笔者并不否认,但是人绝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与其他生物一样的自然界存在,而应该被区分看待,因为人除了具有一般生物的属性,还具有精神性和社会性。我们不能忽略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对人进行定义的方法,不能无视人所具备的特性以及人丰富的外延和内涵。虽然方孔先生极力论证了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主观特性的客观性,但是就算是出于同一环境下的人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认识,而且其所处的环境对其是否有影响,该影响有多大都难以具体衡量,正如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可以打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理论一样,方先生以实践中一般的情况作为说明并不足以论证没有特例的出现,而这一点将是致命的。
(二)科学思维方式的绝对化倾向不妥
科学的发展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欧法学的思维方式的一种热潮,但笔者认为将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完全运用于对法律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实验为标志,其认识对象是十分具象化和稳定的,但法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研究对象,其认识的社会本身与自然科学就存在较大的差异,法学的客观性和具象性都远远弱于自然科学,如果直接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法学的研究,必然会导致诸多的不适应和排斥。韦伯赞同法学的科学化却认为这种科学化不可能是绝对的、纯粹的科学化,并不是韦伯思维的局限和不彻底,而恰恰是其基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所得出的恰当结论。
二、法律适用的相对性
(一)所谓“物化过程”其实掺杂法官主观因素
“立法者通过自己的认识活动,获得对自然法的个人认识并最终把它表达为实在法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物化。”[2]在先生看来,物化在自然法转化为实体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实在法与自然法之间的偏离是由于物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偶然性因素所致,例如人的主观认识和意志因素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但是先生没有看到除了立法层面偏离,实体法在司法运用方面的异化也值得我们关注,司法层面的运用绝不是仅仅局限于机械的公式套用,而是掺杂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司法人员本人所在的社会层级、教育背景、社会经历以及现实生活中群众的舆论和民意等等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弗兰克曾经说过:“在法律运用的过程中,判决结果将碰巧依审理案件的法官的个性而定”。先生看到了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主观要素作用,却忽略了法官本身在司法过程中的主观性,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二)没有看到法官自由裁量的积极意义
如果认为法官仅仅扮演着套用公式的作用,实际上就否定了法官能对案件所起到的自由裁量作用。众所周知,自由裁量不仅可以克服实践中法律规定过于宽泛所导致的适用困难,也能够克服规定过于严格所造成的适用僵化,此外还起着能够提高司法过程中的效率和弥补规则空缺等重要作用。完全将主观的要素和判断隔离出去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对自由裁量的否认可能会导致某些酌定的情形和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况且,从先生常常提到的“实用”角度出发,这种不具有自由裁量权且只能发现法律的法官,也很难解决实践中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案件,并不“实用”。
三、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为双向互动关系
自然法是实在法的本体和重要来源,但是自然法不能独立于实在法而存在,两者不能够被割裂开来,而应是一种息息相关的关系。方孔先生强调自然法通过物化的过程成为实在法,这其实是过度重视自然法的单方作用,而忽视了实体法等其他因素对自然法所能够起到的促进效果。
(一)立法者主观因素可以对自然法产生影响
虽然立法者的主观因素不能直接被看作是实在法的组成部分,但该主观因素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实在法的具体规则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立法者和司法者本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被认识的对象,自然法是会受到立法者等的主观要素影响的。正如有学者曾提到过:“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理性的,有理性便可发现那些先在的客观真理。然而人不可能做到物我两忘,人与客观世界是纠缠在一起的,客观世界为人经验的世界,人也是客观世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主客体二分,彼此外在,彼此限制。”[3]由此可见,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多样的角色,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立法者认识法律的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所需要认识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虽然从表层看来,立法者的立法行为似乎是一种客观而又中立的活动,但仔细探究下去就不难发现,这其中早已参杂了许多立法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加之人与客观世界有着难舍难分的纠缠关系,这种主观因素实际早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人类社会的根源之中,因此自然法就不可避免地将会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自然法虽然作为物化前的存在,但其本身早已蕴含了一些主观因素,而这一推论并不会影响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应然”与“实然”差别的存在。因为在自然法的范畴内主观因素所占的比例和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而在实在法中主观要素往往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所以相较于实在法而言,自然法仍然具有更强的客观性,仍然是一种应当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自然法作为实在法的重要来源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动摇的。
(二)物化的偶然性既影响着制定出的实在法,也作用于存在着的自然法
物化因作为连接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关键一环,对于实在法和自然法都意义非凡,同时,这种在物化偶然性背景下形成的实在法和相关的司法架构其实又在无形中改变着现实社会,也改变着自然法。正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陪审制度上的异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从历史上看,在神示证据之后,英美法系国家采用陪审团制度来进行庭审,以随机抽选的方式从登记的选民中选取陪审员并对其是否具有担任陪审员的能力进行审核,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则多采法定证据制度,缺乏陪审团的存在,法官的职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这一客观现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夹杂着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物化偶然结果——两种不同的实在法。就两大法系的审判形式看来,英美法系控辩双方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表现地更加激烈,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性和纠问主义则体现地更佳明显。英美法系中审判的对抗性要求庭审过程中原、被告的权利都得到充分、平等地保障,否则陪审团将极有可能认为该次审判是不公正的,同时反对法官在庭审中积极干预案件和找寻案件事实,但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则恰好相反。我们不难看出,陪审团的出现实际上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人民对于审判所持的理念和判断标准,即对于双方,特别是被告方诉讼权利保障的高度重视;影响了诉讼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诉讼中平等的诉讼地位的维护;影响了庭审的具体开展流程,即整个审判程序以及内设环节开展的先后次序,而以上三者均为我们所需要认识的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作为自然法的客观重要来源,人类社会自身内涵因素的变化会导致自然法本身的变化。由此可见,具有物化偶然性的实在法会影响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客观因素,基于此的人类社会变化又会产生影响自然法的效果,从而验证了实在法对自然法所起到反向促进作用。
(三)实在法对自然法的影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
对于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者都看到“虽然自然法始终处于与国家正式颁布并以一定的制裁来强制执行的实在法的相对一面,但它重视实在法的存在,追求在实在法中更多地反映、实现或者接近永恒正义并以其自许的崇高效力深刻地影响实在法的存在和发展。”[4]但是正如方孔先生一样,大家都忽略了实在法对自然法的影响作用。笔者想进一步从一般意义上论证实在法在自然法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以及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实在法作为对目前所有法律体系的统称,这一定义虽然不太精准,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在法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虽然以传统的视角来看,实在法相较于自然法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但这并不能否认实在法在整个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实在法作为一种代表着极大权威性的社会规划,相较于自然法而言,能够对社会中的道德冲突和矛盾作出更加明确地选择与规定,从而促使相关问题的解决。实在法能够具像化地将人们的行动和相关的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掌控在一个不存在过多的道德冲突的合理范围之内,并更加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一方面,实在法将现实社会的事实作为进行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实在法的运用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事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何况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也已经证明了实在法会对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实在法对于自然法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实在法自身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性的,其并非一味地依赖于自然法并仅仅以自然法的附属品的身份存在。由此可见,片面地否定实在法,或者以一种轻蔑而又傲慢的态度对待实在法都是极其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实在法,去探析实在法与自然法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并试图在一种精妙地平衡中使两者共生共存地更好。
四、结语
作为法理学与法制史读物中经常出现的“自然法”概念,虽然其对过去欧美法治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历史局限性也较为突出。笔者认为方孔先生其理论在立论依据方面,存在概念局限以及对科学思维的绝对化偏信等方面问题,其次对法律的所谓“物化过程”观察与分析不全面,并没有把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积极意义,所以对其论著存在的思想与历史局限,应该全面客观理性看待。正因为立法者主观因素对自然法能够产生影响,“物化”的偶然性既影响制定出的实在法,也作用于存在着的自然法,所以实在法对自然法的影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