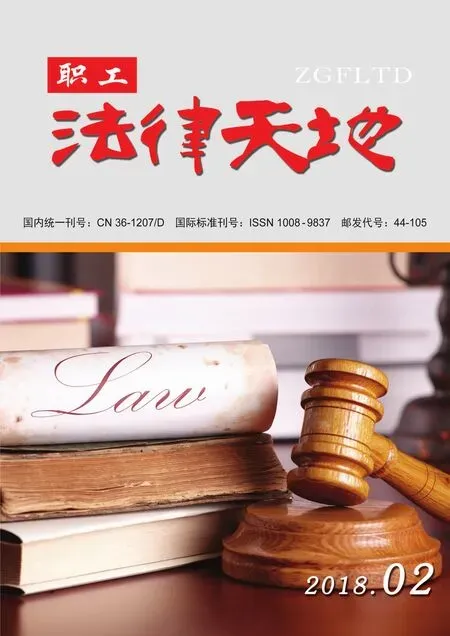结果型准中止犯初论
孙梦真
(361000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 厦门)
一、结果已发生能否成立准中止犯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成立犯罪中止必须要求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未达既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按通说理论则会在中止犯与其他犯罪停止形态间产生理论空白,使得其他停止形态的处罚范围膨胀,同时限缩了中止犯的存在空间。如,行为人已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做出了足以阻止结果的真挚努力,但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并非由于其努力,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据通说理论,会将其归属于犯罪未遂进行刑法归责。这不仅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更为犯罪人搭建的回归合法世界的“金桥”设置了阻碍,也不利于鼓励犯罪人弃恶从善。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立法上针对此设立了准中止犯,我国也有学者探讨准中止犯问题,在其成立的空间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很多学者对于犯罪结果已经发生能否成立准中止犯持否定态度,此观点将准中止犯的概念限制在未发生犯罪结果的情况中,将犯罪未达既遂状态作为成立准中止犯的前提,认为一旦发生了犯罪结果就无法成立准中止犯[1]。即使行为人为防止结果的发生采取了积极的预防措施,做出了真挚努力,也认为是既遂。若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足以防止既遂结果发生的努力,但由于其他异常因素介入,阻断了防止行为,该异常介入因素独立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据此也应当成立既遂犯。这明显限缩了中止犯的范围,导致在处罚上主客观不一致,无法准确的进行刑法归责。
袁彬教授提出,准中止犯是指行为人在着手实行犯罪后自愿做出了防止犯罪既遂的真挚努力,但因其他因素的作用阻断了其防止行为与犯罪既遂与否之间的因果关系,对行为人予以与中止犯同等评价的法律制度[2]。即使发生了既遂结果,仍可成立准中止犯。
在我国准中止犯研究中存在的基本分歧是,在发生了犯罪结果的情况下是否还能成立准中止。行为人虽为防止既遂结果的发生作出真挚努力,但结果仍然发生,可分为两种表现[3]:第一,行为人虽然为防止既遂结果作出真挚努力,但因果关系的自然进程致使犯罪结果仍然发生;第二,在行为人为防止既遂结果作出真挚努力后,由于其他异常介入因素阻断了防止行为的进程,独立的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第一种情况争议不大,行为人的行为应当以犯罪既遂评价,因为该既遂结果是由行为人先前的犯罪行为合乎规律地引起,该犯罪结果应当归属于行为人。也体现出行为人未做出足以防止犯罪结果的真挚努力,应作为犯罪既遂处理。争议主要在第二种情形,即其他因素的出现阻断了行为人的防止行为,应如何处理,有三种观点:
第一是犯罪既遂说。按照通说观点,既遂结果发生后,犯罪形态已完成,犯罪已在既遂状态定格,应当成立犯罪既遂结果。此观点认为,以犯罪既遂论处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可以将行为人自动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作为量刑情节从轻处罚,不会导致处罚过于严厉,又不违背中止犯成立的有效性条件[4]。第二种观点认为成立犯罪中止。该观点认为其完全符合中止犯的主客观要件和有效性要件[5]。第三为准中止说,认为此情况与中止犯的成立条件有所不同,应归入准中止犯。
笔者支持准中止说。首先,这种情况不能归属犯罪既遂,犯罪既遂中的“犯罪结果”与此情况中的“犯罪结果”不同。犯罪既遂,即“遂愿”,要求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符合所有该犯罪成立的条件且引起犯罪结果的发生,简单说,就是要求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引起了犯罪结果。而此情况中,由于其他介入因素,中断了行为人先前的犯罪行为,独立地导致结果发生,这里的“结果”并非行为人的先前行为造成的“犯罪结果”。因此,不能将最后的“结果”归属于已经做出真挚努力进行防止行为的行为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发生既遂结果,不能成立犯罪既遂。其次,将其定性为犯罪中止也不准确,中止犯的成立要求有效性条件,而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防止行为显然在结果上是无效的,同样欠缺防止行为与犯罪结果未发生之间的现实的因果关系,不符合中止犯的有效性要件,但却符合准中止犯制度的设计初衷,即减少中止犯对于有效性的要求,对有效性条件进行扩张,在行为人做出了原本足以防止结果发生的真挚努力,可能成立准中止犯。若以此观点推理,准中止制度就失去了价值,因为依此观点,准中止犯的情况当然也符合中止犯的有效性要件,不仅曲解了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也完全抹杀了准中止制度的存在意义。因此,在提倡准中止制度的同时却将此种情况归于中止犯的观点是矛盾的,应当将其作为准中止犯的一种类型进行评价更为合理,即结果型准中止犯。
二、结果型准中止犯的认定
结果型准中止犯即行为人实行犯罪后,为防止犯罪既遂结果的发生做出了真挚努力,但由于异常因素介入而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准中止犯。认定结果型准中止犯应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做出的“真挚努力”是判定的关键,在不具备中止犯的有效性要件时,以真挚性来补强其减免处罚根据。但何为真挚努力,需要达到何种程度,需要进一步探讨。真挚性应采取客观标准加以判断,而完全从行为人主观角度判断其努力的真挚性,会使得准中止犯的成立过于宽泛,易使真挚性内容虚化,有主观归罪之嫌。
在客观标准说中也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真挚性的程度需要达到“足以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不同观点认为,此标准对于行为人要求过高,过于侧重中止行为的实效性而非防止行为本身,应采取“尽力”标准,即根据一般人标准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行为人尽一切可能采取了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就表明行为人已经“尽力”,具备真挚性条件。两观点在多数情况下所得结论是一致的,仅在一种条件下会得出不同结论:即,行为人虽努力防止结果的发生,但其先前危害行为的性质使得其无论采取何种真挚努力都无法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介入了异常介入因素,最后独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是否还能够成立结果型准中止犯。如,甲意图杀死乙,在荒无人烟的深山中将其砍伤,行为人心生悔悟,想尽办法对被害人施救,但因地处深山,尽管甲用尽一切手段仍无法使得乙得到有效救助,最后乙意外被雷击中身亡。根据“尽力”标准,仍应当认定为结果型准中止犯。根据“足以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标准,显然此行为无法成立准中止犯。笔者认为,“足以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一标准更为合理。首先,“尽力”标准更倾向于主观标准说,过于模糊,同样会产生主观归罪之嫌;其次,准中止制度是对于中止犯有效性条件的放宽,并非完全抛弃,“尽力”标准完全不考虑防止行为的有效性;最后,“尽力”标准过于扩大了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无疑是鼓励犯罪人实行犯罪行为时使用更加无法挽回的极端方式。在这种情况中,犯罪结果的发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不可避免性则是行为人先前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他应当对该行为的不可挽回性承担责任。
第二,介入因素的判断是结果型准中止犯的一个关键。在结果型准中止犯中,犯罪结果已经发生,但该结果并非行为人先前的犯罪行为所致,这是结果型准中止犯的特殊之处,这需要考虑导致结果发生的介入因素的判断问题。该介入因素的认定需要考虑几个条件:①外界因素的介入必须发生在行为人做出防止行为之后,犯罪停止形态固定下来之前,否则无法成立准中止犯。介入因素的中断是将该因素出现之前的行为与最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切断,使得行为人仅对介入因素之前的行为负责,若行为人的防果行为发生在介入因素中断后,行为人的防止行为已不可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该防止行为为时过晚。②介入因素必须具有异常性,若介入因素具有通常性则无法切断先前行为与最后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应当肯定结果归属,这一点与因果关系的判断一致。若该介入因素具有通常性,则说明行为人先前的加害行为已经为结果的发生设置了一个潜在的危险,无法阻断其行为与结果发生的因果链。③介入因素还必须独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若虽介入了一个异常的介入因素,但异常介入行为仅对结果的发生起轻微作用,这说明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所创设的危险更大,在结果的发生中起主导作用,那么同样也无法切断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先前的加害行为,而行为人的防止行为至多可作为量刑情节交法官自由裁量。
三、结果型准中止犯的理论意义
(一)符合准中止制度的设计初衷
准中止制度是对犯罪中止的“有效性”条件的扩张,由于我国在不同犯罪停止形态之间采用不同立场和双重标准,才需要准中止制度来填补其他犯罪停止形态与中止犯之间的缝隙,而结果型准中止恰恰属于其中的空白。我国的预备犯、未遂犯实行普遍可罚原则,其受到刑罚处罚范围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皆因意志以外的因素而停止,主观恶性与既遂犯并无差别,这是基于主观主义立场来考虑刑事可罚性的[7]。我国刑法不仅给中止犯设置了主观自动性、真挚性这种主观条件,且强调了有效性条件,这就缩小了中止犯成立的范围。对于一般的准中止犯,行为人符合了中止犯的主观条件,但欠缺防止行为的有效性,不成立中止犯,但同时主观上也不同于预备犯、未遂犯的“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可以说,一般的准中止犯就存在于这二者的夹缝中。结果型准中止犯亦是如此,由于发生了犯罪结果,不符合中止犯的有效性条件,但犯罪既遂的成立要求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其所希望发生的犯罪结果,而在这一类型中,由于异常因素的介入,使得行为人行为的因果链中断,认定为犯罪既遂也并不合理,那么结果型准中止犯的提出就解决了这二者间的空白,是对中止犯“有效性”的扩张,这就回归了准中止制度的设计初衷,更多的考虑行为人主观层面,符合其激励行为人及时回归正途的目的。
(二)符合刑法科学归责的要求
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既遂结果的发生有过错,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型准中止犯行为人的防果行为本可以合乎规律地使得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只是因为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中断了这一因果进程,并且独立导致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应当适用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中断论”,行为人仅对发生中断事由前的行为负责,即若其中断前努力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符合准中止犯,那么该行为人成立准中止犯,而无需为介入因素之后发生的独立后果承担不利的评价责任。若将其以既遂犯论处,则明显有客观结果归罪之嫌,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科学归责原则。
(三)符合“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
我国目前正致力于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8],提倡结果型准中止犯符合这一趋势,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刑法的谦抑性可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处罚的范围,二是处罚的程度,即定罪和量刑。从近几次对刑法的修正即可看出,我国犯罪圈在不断扩大,刑事法网趋于严密,但并未违反谦抑性原则。这是因为虽然罪名在增多,却在刑罚上的修改变得更加轻缓,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体现在量刑层面上。相比于过去刑事法网疏漏、刑罚苛责的“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向“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的转变给刑法更增添了温度,更加人道化,不易激化社会矛盾以及个人对法律的对抗情绪,增加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感。而结果型准中止犯的提倡,有限地扩张了准中止犯成立的条件,更多的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由恶转善,符合目前刑法发展的这一理念。将结果型准中止犯纳入到准中止犯的范畴中,不仅是准中止制度本身的完善,也是现代刑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1]赵秉志.海峡两岸犯罪中止形态比较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5).
[2]袁彬.准中止犯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29.
[3]张平,韩艳芳.准中止犯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
[4]赵秉志.海峡两岸犯罪中止形态比较研究[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7,5.
[5]张平.中止犯论[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9(1):245.
[6]袁彬.论中止的真挚性及其立法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7]汪东升.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基于主观主义立场的思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
[8]储槐植,何群.刑法谦抑性实践理性辨析[J].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