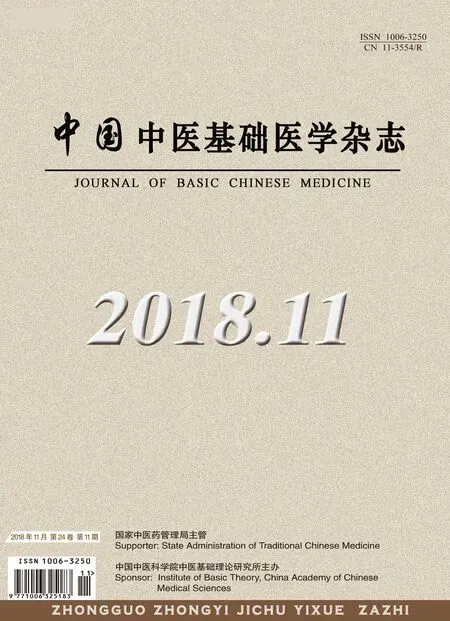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证候与体质分布情况及两者 相关性多中心研究❋
, ,,,,△
(1.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 210028; 2. 兴化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兴化 225700; 3. 如皋中医院,江苏 如皋 226500; 4. 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苏州 215100)
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AM)是指子宫内膜侵入子宫肌层形成的良性病变[1]。近年来,其发病呈现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临床主要表现为痛经、经量过多、子宫体积增大及不孕等[2]。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西医主要通过药物(口服、皮下注射)、手术切除等方式来治疗本病,但其存在易复发、副作用明显等让大部分患者难以接受。中医从整体出发,将病、证、体三者综合考虑[3]。其在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提高妊娠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体现了治疗本病的巨大优势[4]。
中医认为证候与体质的准确判断是治疗疾病的前提。然而临床关于多中心、大样本的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证候与体质相关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在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BE2015729)的支持下,通过多中心联合进行了子宫腺肌病患者流行病学调查,现报道如下。
1 病例及标准
1.1 病例来源
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233例)、如皋中医院(7例)、兴化市妇幼保健院(4例)、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6例)就诊的250例子宫腺肌病患者。
1.2 诊断、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5],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医妇科学》[6]《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7]中中药新药治疗痛经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1.2.2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知情同意,自愿参与该调查,并能如实回答调查者的问题。上述2个标准全部符合方可纳入。
1.2.3 排除标准 不符合纳入标准者;妊娠期、哺乳期及绝经期妇女;不能对自身状况进行评价者;合并有其他严重的原发性疾病者。上述3个标准有任何1个或以上符合即可排除。
2 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获得一般资料、中医诊断获得四诊信息以及根据相关量表判定中医证候及体质类型,最后统计分析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证候、体质分布情况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2.1 实施问卷调查
请患者如实填写调查表,调查问卷主要分为2个部分。
2.1.1 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证候研究调查表 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职业、平素情绪、饮食习惯、运动情况、孕产史)、既往病史(手术史、上取环、诊刮、宫腔镜等)、痛经史(痛经评分量表)、月经情况(经量、经色、经期、周期)和其他临床症状(如月经前后头痛、乳房胀痛、急躁易怒、善太息、平素怕冷、四末发凉,神疲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多痰、体倦、纳差、失眠健忘等)。
2.1.2 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体质调查表 主要包括面色、眼神、肤色、唇色、口味、腰酸痛、夜尿、大小便、睡眠、月经(量、色、质),痛经、带下(量、色、质)及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工作强度等。
2.2 四诊信息采集
由各合作中心两位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联合诊断,主要通过望闻问切来收集患者月经干净后(1周内)四诊信息,包括患者的外形、精神状态、平素性格、记忆力、饮食喜好、睡眠情况、二便情况、经带情况、舌面脉象、过敏史等作出综合中医诊断。
2.3 中医证候及体质类型判定标准
2.3.1 中医证候评定标准 根据《中医妇科学》中子宫腺肌病的中医证候分型以及对近20年有关中医治疗子宫腺肌病的现代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8],初步将该病分为气滞血瘀型、寒凝血瘀型、湿热瘀结型、痰瘀互结型、肾虚血瘀型、气虚血瘀型等。但在临床辨证时调查者可按中医临床辨证标准,如实辨证分型并注明具体的辨证分型。
2.3.2 中医体质判定标准 参照200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并通过调查者与患者一问一答的模式,将患者所回答的问题进行评分,每个问题按5级评分并计算原始分数和转化分数[9]。
2.4 统计学方法
整理汇总所有调查资料,将资料导入Exce数据库,转入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线性分析、卡方检验等方法进行分析与归纳。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分析
本次研究共收集子宫腺肌病患者250例,经手术确诊的有121例占48.4%。
3.1.1 子宫腺肌病患者年龄分布 该研究中年龄最小24岁,年龄最大56岁,平均年龄(44±0.28)岁,其中年龄在30~50岁患者共216例占85.20%。
3.1.2 主要临床症状 月经量偏多137例,偏少5例;痛经轻度71例,中度61例,重度29例。
3.1.3 合并其他妇科疾病史 合并有子宫肌瘤为主104例占41.60%,其次为单纯卵巢囊肿27例,巧囊21例,子宫内膜息肉19例。
3.1.4 相关妇科手术史 有人工流产史216例占82.40%,其中有2次及2次以上共109人占总人数的43.60%;其次为上/取环60例,剖宫产37例,宫腔镜13例。250例子宫腺肌病患者中曾有过相关手术史者219例占87.60%。
3.2 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证候分布情况
全部250例子宫腺肌病患者中,以气滞血瘀型为主的有92例占36.80%。按证候类型所占百分比大小排序为气滞血瘀型(36.80%)>肾虚血瘀型(19.60%)>寒凝血瘀型(16.40%)>气虚血瘀型(10.80%)>痰瘀互结型(8.40%)>湿热瘀结型(8.00%)。
3.3 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体质分布情况
全部250例子宫腺肌病患者中,以气郁质最为常见有79例占31.60%。按体质类型所占百分比大小排序为气郁质(31.60%)>平和质(16.80%)>阳虚质(16.00%)>阴虚质(10.80%)>气虚质(8.40%)>痰湿质(8.00%)>湿热质(5.60%)>瘀血质(2.40%)>特禀质(0.40%)。
3.4 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体质与证候的相关性
3.4.1 特定证候类型患者体质类型分布(每项按体质类型所占百分比大小排序) 气滞血瘀型:气郁质(69.57%)>平和质(14.13%)>痰湿质(5.43%)>瘀血质(4.35%)>气虚质(3.26%)>湿热质(2.17%)>阴虚质(1.09%); 寒凝血瘀型:阳虚质(68.29 %)>平和质(14.63%)>气郁质、气虚质(各4.88%)>阴虚质、湿热质、痰湿质(各2.44%); 痰瘀互结型:痰湿质(42.86%)>平和质(33.33%)>阳虚质、湿热质(各9.52%)>瘀血质(4.77%); 湿热瘀结型:湿热质(45.00%)>平和质(20.00%)>痰湿质(15.00%)>阳虚质(10.00%)>气郁质、气虚质(各5.00%); 气虚血瘀型:气虚质(51.85%)>气郁质(18.52%)>阴虚质(14.82%)>平和质(11.11%)>痰湿质(3.70%); 肾虚血瘀型:阴虚质(42.86%)>平和质(18.37%)>阳虚(16.33%)>气郁质(14.28%)>气虚质、瘀血质、痰湿质、特禀质(各2.04%)。
3.4.2 特定体质类型患者证候类型分布(每项按体质类型所占百分比大小排序) 平和质:气滞血瘀型(30.95%)>肾虚血瘀型(21.43%)>痰瘀互结型(16.67%)>寒凝血瘀型(14.29%)>湿热瘀结型(9.52%)>气虚血瘀型(7.14%); 气郁质:气滞血瘀型(81.01%)>肾虚血瘀型(8.86%)>气虚血瘀型(6.33%)>寒凝血瘀型(2.53%)>湿热瘀结型(1.27%); 阳虚质:寒凝血瘀型(70.00%)>肾虚血瘀型(20.00%)>痰瘀互结、湿热瘀结型(各5.00%); 阴虚质:肾虚血瘀型(77.78%)>气虚血瘀型(14.82%);气滞血瘀型、寒凝血瘀型(各3.70%); 气虚质:气虚血瘀型(66.67%)>气滞血瘀型(14.29%)>寒凝血瘀型(9.52%)>湿热瘀结、肾虚血瘀型(4.76%); 湿热质:湿热瘀结型(64.28%)>气滞血瘀型、痰瘀互结型(各14.29%)>寒凝血瘀(7.14%); 瘀血质:气滞血瘀型(66.66%)>痰瘀互结、肾虚血瘀型(各16.67%); 痰湿质:痰瘀互结型(45.00%)>气滞血瘀型(25.00%)>湿热瘀结型(15.00%)>寒凝血瘀、气虚血瘀、肾虚血瘀型(各5.00%); 特禀质:仅有肾虚血瘀型1例占100%。
4 讨论
子宫腺肌病为妇科疑难病症,近年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妇科常见疾病。本次研究发现,该病多发生于30~50岁的妇女,临床上妇女多次妊娠分娩、人工流产等宫腔手术是引起该病的主要原因。中医在诊治过程中强调“审证求因,审因论治”,而体质作为中医辨证的基础,若体质不同即使同一病因,其病证却有悬殊,故证候与体质的准确判定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10]。然而子宫腺肌病临床证候分类各医家观点不一。如彭霞[11]等研究发现,气滞型、血瘀型、肾虚型为其常见类型。谌海燕[12]等研究发现,子宫腺疾病的常见证型为肝郁气滞、肾阳不足。本研究发现,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证候以气滞血瘀型为主,中医体质以气郁质为主,笔者认为因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在当代社会中女性需承受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容易引起情志抑郁不舒,气血运行不畅,从而使得积血滞于胞宫、胞脉,久而久之而发为本病。
本次调查发现,病-证-体三者之间存在趋同性和矛盾性。一是趋同性。气郁质与非气郁质比较,气滞血瘀型患者较多,湿热质与非湿热质比较,湿热瘀结型患者较多等,说明体质与证候的趋同性。中医认为体质决定着证候的产生,证候又在体质的基础上演变;二是矛盾性。阳虚质患者可以出现胸闷纳呆、脘腹胀满、舌苔白腻等痰瘀互结型等症状,甚至可以出现带下量多、色黄质稠等湿热瘀结型特点;气虚质患者可以出现下腹胀痛、胸闷不舒等气滞血瘀型症状,亦可出现四肢冰凉、下腹冷痛等寒凝血瘀型症状。这是因为常态下患者处于阴平阳秘的状态,即所谓的平和质,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阴阳失衡,则会出现偏颇体质。它可以是机体整体上的,也可以是个体脏腑的阴阳偏盛或偏衰。若影响较大则会受制于机体本身的阴阳状态,产生与其阴阳属性相同的证候类型,如痰湿质以痰瘀互结型为主,阳虚质以寒凝血瘀型为主;若影响较小、受限于局部脏腑,则其不会改变机体本身的阴阳属性,故临床就有阳虚质患者出现湿热瘀结型临床症状。偏颇体质的存在未必是病态,而证候的产生是在病的前提下,有时二者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难以区分,故在临床施治时应在调体中寓有治证,治证中含有调体。
本次研究因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还不能完全反映子宫腺肌病中医证候、体质的分布规律和相关性。今后还需进行更大样本量、多中心、系统性、规范性的研究,从而使结论更具说服力,为子宫腺肌病中医个体化临床诊疗规范的制定奠定基础,为子宫腺肌病的预防治疗提供参考依据,以期达到“未病先防”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