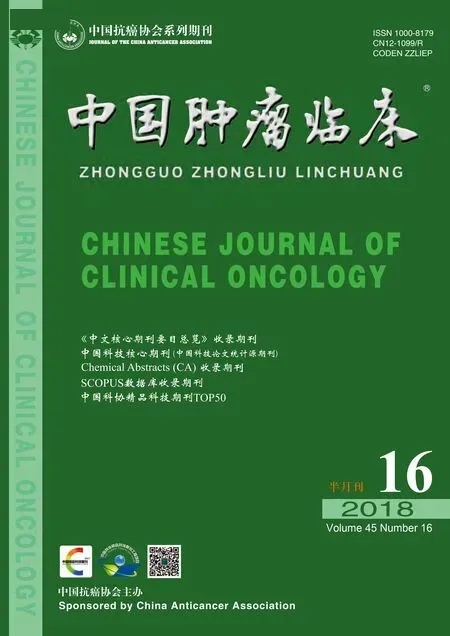癌因性疲乏最新进展—NCCN(2018版)癌因性疲乏指南解读
谢晓冬 张潇宇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发布的2017年癌症进展报告[1]预测,至2035年全球每年癌症新发病例数可能由现在的1 520万例增加至2 400万例。同样,在全球范围内肿瘤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也在逐年提高[2-3],因此关注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显得越发重要。癌因性疲乏(cancer-related fatigue,CRF)有发生快、持续时间长、程度重和不可预知等特点[4-5],降低患者CRF水平,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6]。2000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发布了CRF指南(第1版),并指定专家小组定期对指南内容进行更新。2018年1月17日NCCN再次推出(2018版)CRF指南[7]。为使广大医务工作者对CRF更为了解,现对CRF的研究进展和NCCN(2018版)CRF指南的更新要点进行解读。
1 CRF研究发展历程
1979年Haylock和Hart最早报道了有关癌症患者CRF的研究[8]。1986年Piper[9]首次从护理学的角度将CRF定义为:一种受生物节律影响的主观疲倦感,其强度、持续时间、引起的主观不愉快感常会发生变化。1996年Ream和Richardson[10]以护理为目标对疲乏的定义为:疲乏是一种主观的、不悦的症状,包括从疲倦至精疲力竭的各种感受,其产生的全身症状可干扰个人的日常生活。1998年Schwartz[11]将其定义为:一种包括生理、情感、认知、时间性在内的自我知觉体验,一种动态的、多维的自我感知状态。1999年陈克能[12]发表了CRF的综述。最新的NCCN CRF指南(2018版)将CRF定义为:一种痛苦的、持续的、主观的、有关躯体、情感或认知方面的疲乏感或疲惫感,与近期的活动量不符,与癌症或癌症的治疗有关,并且妨碍日常生活。CRF逐渐引起国内外医护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到的结果显示,2008年有关CRF的中文文献仅34篇,2017年为198篇,数量增长近6倍。然而,中文文献数量远低于外文文献数量,仅Lancet刊发的文献2008年为66篇,2017年为247篇。可见中国CRF相关研究虽然发展迅速,但仍需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提高。
CRF为多因素相互作用所致的肿瘤常见症状,贯穿于肿瘤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等全过程[13]。有研究显示,年龄、性别和焦虑情绪是CRF的危险因素,家庭月收入、血红蛋白水平和白细胞计数为保护性因素[14-15]。有研究显示,肾上腺皮质的功能状态在CRF的发病机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16]。有研究提示,有氧运动能够有效缓解化疗导致CRF加重的情况[17]。
2009年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癌症和营养专题研讨会上,PC.Stone针对CRF作了名为《癌症治疗期间疲乏管理:药物与营养和运动》的报告[18]。201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中的《癌症患者疲乏的筛查、评估和管理指南》[19]在JCO上发表。2018年ASCO年会分别报道了乳腺癌患者化疗体质量指数增高对CRF影响的纵向评估[20];关于被批准用于改善标准姑息治疗下晚期癌症患者的CRF一种新的植物药物PG2注射液的双盲、多中心、随机Ⅳ期研究[21];癌症患者血清生长素、抑胃肽、胰岛素和瘦素水平与睡眠质量和CRF的关系,表明了代谢标志物与CRF的潜在联系[22]。
2 NCCN(2018版)CRF指南更新解读
NCCN(2018版)CRF指南将诊疗分为4个阶段,即筛查、初步评估、干预和再评估,并将CRF的一般策略单独进行了归纳。
2.1 CRF的筛查
指南在附录中列举了可用于测量儿童、青少年和成人CRF程度的方法及仪器,对于年龄>12岁的患者采用0~10量表(0为无疲乏,10为能想像的最为严重的CRF),7~12岁的患儿采用1~5量表,5~6岁的患儿表达“累”或“不累”来筛查。指南建议定期开展重新检查和评估。2018版指南更新强调,对从无到轻度的CRF患者仍要进行持续监测。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筛查常常无法系统且有效地进行。如患者可能不想打扰为他们服务的医务人员,担心如果报告的CRF程度较高,会影响到正常的治疗;部分患者不想被认为是抱怨而回避CRF;还有的患者认为他们必须忍受CRF,默认无治疗CRF的方法。由此可见,临床工作中科学宣教和人文关怀非常必要,可以避免或减少影响诊疗的因素。
2.2 CRF的初步评估
对筛查发现的中重度CRF患者需采取初步评估,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以及伴随症状和可干预影响因素的评估等。指南提出,应确定CRF是否与被治愈的癌症患者复发或与其潜在的恶性肿瘤恶化有关,这通常是导致CRF患者寻求进一步评估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CRF与疾病复发无关,明确告知将有效降低患者和家属的焦虑水平。新版指南在初步评估营养不良部分,补充了对维生素缺乏的监测,进一步丰富了CRF的初步评估标准。
2.3 CRF的干预
CRF的干预措施分为非药物性干预和药物性干预。抗肿瘤治疗过程中CRF患者的非药物性干预主要包括体力活动、按摩治疗、心理社会干预、营养辅导和睡眠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以及明亮白光疗法(bright white light therapy,BWLT)。CBT是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的整合,临床上多用于抑郁、焦虑、失眠、强迫障碍等疾病的治疗,常用的有认知重建、暴露和放松训练等[23]。BWLT采用高亮度(10 000 lx)的家用荧光灯刺激调节昼夜节律的下丘脑视交叉上核,治疗情绪和睡眠障碍。终末期CRF患者的非药物性干预主要包括体力活动和心理社会干预。
药物性干预,排除其他可导致CRF的情况(如癌痛、贫血等),可使用中枢兴奋剂(哌醋甲酯),终末期患者可考虑使用皮质类固醇(强的松或地塞米松)。考虑到长期使用的不良反应,类固醇仅限于晚期CRF和厌食症患者,以及与脑或骨转移相关的疼痛患者。针对睡眠障碍、营养缺乏以及并发症,可以根据患者和家属的具体需要,随着疾病的进展优化方案。新版NCCN指南更新专家小组强调,饮食和营养应该根据患者的舒适程度进行调整。
2.4 CRF的再评估
由于CRF可在整个疾病过程和抗肿瘤治疗的任何阶段发生,因此定期进行CRF的再评估是为患者提供有效CRF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2.5 CRF的一般策略
新版指南在CRF的一般策略部分整合了上一版抗肿瘤治疗过程中、抗肿瘤治疗结束后以及终末期患者的科学宣教和一般性干预原则,如自我监测CRF的水平、节约体能、分散注意力等。终末期患者须避免不必要的活动(保留体力给有价值的活动)。在296例接受CRF治疗的患者中,一项多地点的能量守恒临床试验报告显示,接受试验干预的患者CRF程度明显降低。分散注意力的活动,如游戏、音乐、阅读和社交等有助于缓解CRF,机制尚不明确。日间小睡可以补充能量,但最好限制在1 h以内,以避免打扰夜间睡眠。节省体能的技巧,如洗澡后穿浴袍代替用毛巾擦干;也可使用辅助工具,如助行架、抓取工具、床头柜等。指南强调要关注有意义的互动,提升患者的尊严。
近些年CRF指南各版本更新要点,如2014年指南开始强调有意义的互动,提升患者的尊严;2015年指南更新删除了药物干预中对莫达非尼的推荐,同时建议必要时考虑转诊给相应的专家或支持治疗机构。自我知觉体验中情感、认知,即心理方面同样是CRF的重要表现。2014年指南提到“关注有意义的互动、提升患者尊严”就是对心理方面的体现,专家小组逐渐重视患者的人文关怀。专家小组在2014年指南中对“莫达非尼在小型试验中对CRF治疗后患者的管理前景”达成共识,在排除其他疲劳原因后,可以考虑使用甲基苯酯或莫达非尼。2015年指南更新为“由于莫达非尼对患者CRF的治疗研究有限且改善并不明显,因此不予推荐”,可见指南随研究的进展而不断更新完善。
3 CRF的国内研究现状
姑息治疗不仅可以缓解患者的病痛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更是一种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20世纪80年代,李同度教授发起了“肿瘤康复与姑息治疗”的号召;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康复医院在蚌埠市建立;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癌痛三阶梯治疗方案在全国推行;1994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成立,先后举办14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参会人数逐年增多。此外,2018年6月“第一届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学术年会暨第十四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上成立了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在中国抗癌协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和北京CSCO基金会的支持下,CRPC组织相关学术活动,开展CRF培训班,为患者提供科普宣传。
4 小结
2003年 Ahlberg等[24]回顾性分析发现,65%~100%的化疗患者、82%~96%的放疗患者和70%~100%接受干扰素治疗的患者会经历CRF。由此可见,CRF的发病率较高,对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较大。CRF指南(2018版)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意见,体现了对患者的关爱,更加人文化,符合舒缓医学理念,较为直观,易于医患阅读、理解和参考。CRF不仅是躯体上的疲惫感,在心理、精神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目前,国内对于CRF的研究尚少,缺乏充足证据支持相关临床实践。要合理运用指南,由多学科小组完成CRF的治疗和管理,根据患者的需要个体化制定干预措施,从而为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提供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