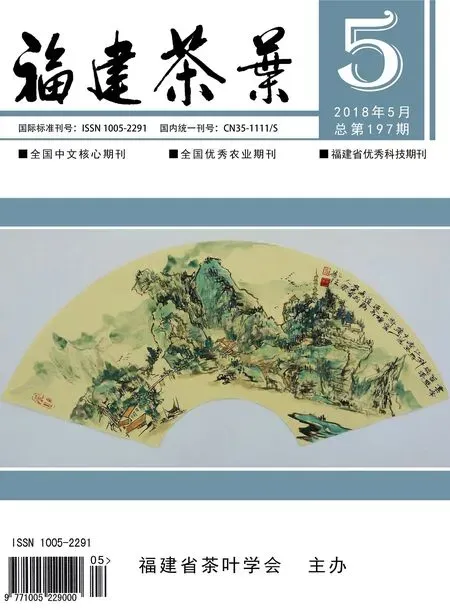跨文化视域下中国典籍英译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
——以《红楼梦》饮茶对白为例
杨月秋
(齐齐哈尔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本文以现有的对《红楼梦》中饮茶对白里的茶文化的译文为基本点,通过分析来解读英译文化内涵丰富的内容时候常常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对于常用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本文也对比了二者在传承文化过程中的意义,继而深入探索英译文化内容时的相关问题。
1 归化与异化
早在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霍尔首次在其作品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概念。自此,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正式确立。在近些年,翻译的文化交际作用被翻译领域愈来愈看重,并逐渐成型了跨文化交际相关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差异的相关问题。然而,如何应对这些文化差异呢?就目前来说,主要是应用两种翻译策略: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
在异化策略看来,当翻译者翻译过程中遇到文化内涵丰富的翻译文本且源语言文化与目标语言文化悬殊时,翻译者应当以源语言为中心与归宿。而当面临同种情况的时候,归化则是主张要以目标语言为中心与归宿。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详细阐述了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他认为,翻译者在翻译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时要尽可能地保留源语言的相关文化,能不改变则不加改变地引到目的语中。译者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译文让目的语的读者更为直观地感知源语言文化。也即是:译文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其原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表达方式以更为准确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而这,将有助于译者通过译文让译文读者准确地解读源语言文本的意思,继而助力源语言国家的文化与国际接轨,这是国际间不同文化的碰撞与流通。诚然,异化常常也会带来一些弊端。譬如,如果源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悬殊过大,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译出的文本常常会给译文的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障碍。还有时候,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地域特色浓烈的或经典的文化典故,如果译者使用异化策略进行翻译而译文的读者的理解能力不够强大,将很难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在韦努蒂看来,如果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使用归化的策略,那么译者就会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对源语言翻译内容的语言结构或文化意象作改动,这样让译文所展现出的文化价值观更加符合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真正实现文化上的交流。这也即是说,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事先了解目的语国家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意象,而后在自己的翻译中利用目的语文化中的一些意象来替代源语言中的一些意象。这样的翻译对于译文读者来说是通俗易懂的,可读性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拉近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2 《红楼梦》中的茶文化内容解读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茶文化的发源地。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737年的时候我国的炎帝神农氏发现了茶树,自此也便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茶树、茶叶利用的记录。中国人民最早发现茶,茶的历史迄今已有逾四千年了。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又被戏称为百科全书,它勾勒了中国十八世纪的民俗全景。在这本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中国茶文化的内容。据相关学者统计,在这本著作中有一百二十回涉及到了茶相关的内容。在整个著作中,“茶”字总共出现了近三百次。其中,关于茶的描述也是极其细致且涉及范围广泛,堪称文学作品之最。具体地,在这本著作中涉及到的茶相关的内容有茶具、茶名、茶俗、茶诗、茶联、茶祭、茶礼,几乎涉及到了茶的所有方面。其中,该著作中多次谈及到的“茶祭”是其他文学作品中鲜少会涉及的。对于作品当中的诸些茶文化的内容,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的时候应该如何予以处理,应当应用何种翻译策略,这不仅关乎到翻译作品的质量,更关乎到中国茶文化走向国际的力度与强度。
3 《红楼梦》中饮茶对白英译策略
从研究价值来看,《红楼梦》中的饮茶对白是具有很好的研究意义的。塑造饮茶的对白情境,不仅有助于向世人展现我们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助于作者塑造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自然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在众多的《红楼梦》一本中,属杨宪益夫妇和牛津大学汉学家霍克斯的一本最为经典(后续统一简称为“杨译本”、“霍译本)。在这两个译本中,译者们都非常关注著作中的茶文化内容,但他们在对这些茶文化内容进行翻译的时候,采用的是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1:凤姐与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喝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
这是《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中在林黛玉喝了王熙凤递的贡茶后对她说的话。这个对话涉及到的是中国茶相关的婚俗文化。在中国古代,男女双方在下订婚聘礼的时候会将茶叶作为其中的聘礼之一,俗称为“定茶”、“下茶”,寓意为男女双方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对于这句话的翻译,杨译本中的译文为“drinking our family tea,a daughter-in-law to be!”但在霍译文中,该句被翻译为“You know the rule:drink the family's tea,a bride-to-be”。由此可见,杨和霍在翻译该句的时候都将“茶”与“妻子”的意义对接,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都是异化。二者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因为异化翻译后能够让译文的读者非常直白地感知到在中国文化中、中国茶婚俗的内容,有助于提升译文读者对中国茶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例2袭人晴雯二人忙笑说:“沏了一缸子女儿茶,已经吃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这句对话截取自《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在这句对话中涉及到女儿茶,这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个茶名。在杨译文中,“女儿茶”被翻译为“nuerh tea”,加脚注“...tender wutong leaves...”。而在霍的译文中,“女儿茶”则被翻译为“herbal tea-wutong tip”。由此可见,杨在翻译这个茶名的时候,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他没有改变翻译文本的语境。而运用脚注,则让译文读者感知到这种茶是有特色的中国茶中的一种,又能够清晰地了解到这是用嫩嫩的梧桐叶尖做成的茶。而从霍的译文我们可以看出,霍在翻译“女儿茶”这一茶名的时候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他没有保留原文本的文化情境,直接将女儿茶的实质展现在译文读者的面前。这样的翻译非常直截了当地让译文读者了解了中国人用梧桐嫩叶泡水喝的事实,这也即是女儿茶的实质。尽管通过这样的译文,译文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女儿茶的实质,但“女儿茶”中“女儿”所指向的中国茶文化内涵却没有被很好地解读出来。经过对比我们看到,相较于霍译本,杨译本中对“女儿茶”的翻译处理更为妥善,它更能助力中西方的茶文化交流。
此外,该著作中还多处涉及茶名。譬如,在著作的第五回中仙姑提到名为“千红一窟”。于作者的初衷来说,他是在预示女子命运不济。而在翻译“千红一窟”的时候,杨和霍也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杨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为“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字面上的意思即为“洞中的千朵红花”,这样的翻译很直接地沿用了原翻译文本中的意义,给译文读者带来的是直观的画面。诚然,这样的翻译并没有揭示出文本作者所要传达的寓意,对于译文读者全面认知作品的主题是有所欠缺的。而在霍的译本中,他将“千红一窟”译为“Maiden's fears”(少女的眼泪),他摒弃了原文字面上将女子喻为花朵的意思,却准确地揭示出了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寓意,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的深层含义,从而理解这段对白对于全文的作用。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翻译文化因素的时候,归化和异化是译者常常使用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二者常常对立又互补。纵观各类翻译,没有纯粹的归化策略的使用也没有纯粹的异化策略的使用。在翻译文化内涵丰富的翻译文本时,翻译者要多方位地考量作者、读者的情况,也要考量文化冲突的因素,继而妥善地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也即是说,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来选择多使用归化翻译策略还是异化翻译策略。而这需要译者在长期的翻译经验中不断实践与积累经验,方能良性把握、妥善应用。
[1]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96-208.
[2]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胡文彬.茶香四溢满红楼——《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J].红楼梦学刊,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