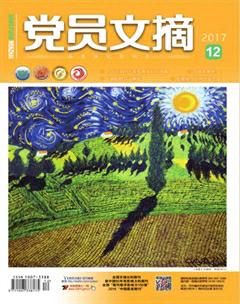知识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民族的未来
刘震云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这里涌现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蔡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贡献了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就牵扯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都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另外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民族最缺什么。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就挖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很多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缺远见。
大家开始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的时候,有两句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一句是“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不成立,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投机分子走近路,因此成功的人很多。但他们得到的利益只属于他们自己。希望你们牢记:要做“笨人”。这个民族不缺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有两个特别好的人生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个子只有一米五六。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田里,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我问她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我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得比别人更快一点。”
还有一个是我的舅舅。他是一个木匠,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40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地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问他:“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說:“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
接着他又说:“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的木匠,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的刨子花的味道。但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也当不好木匠,有时候我看到一棵树,如果它是松木、柏木或楠木,我会想:这要是给哪家出嫁的姑娘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我想只能打个小板凳。”
我觉得刘麻子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是他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生的水平。
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一句是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