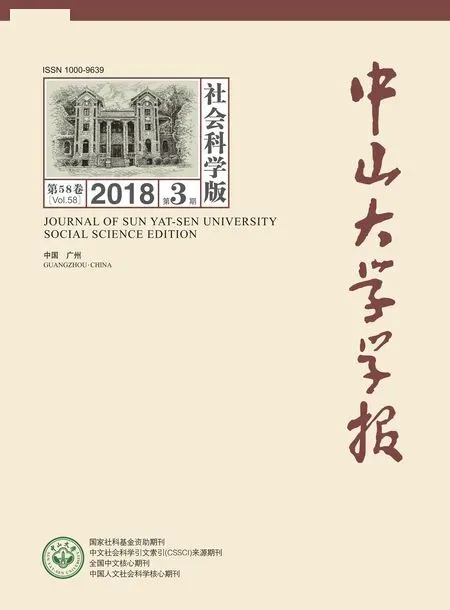《礼记·经解》写作年代考*
陈 桐 生
《礼记·经解》记载孔子论述六种典籍之教,文中所列《诗》《书》《乐》《易》《礼》《春秋》正是儒家后学所说的六经,只是六种典籍排列顺序与后人所说六经有所不同。《经解》作于何时,不仅仅关系到该文的写作年代,还涉及更多的学术疑案。如果《经解》所记载的是孔子本人真言论,那就意味着六经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形成,中国经学史上“孔子作六经说”或“孔子删述六经说”也就有了铁的文献证据——实际上今文经学家就是以《经解》作为“孔子作六经”的一个重要文献依据。前修时贤虽然对《经解》写作年代做过种种考证,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还存在不小分歧,需要继续深入探讨。
一、前修时贤关于《经解》写作年代的观点
梳理前修时贤关于《礼记·经解》写作年代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认为《经解》所记载的是孔子真言论。唐人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以为:“《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经解》所载既是孔子之言,这就意味着《经解》作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以《经解》作为“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页。的文献证据。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一书中以为:“此篇论《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治,各有得失。六艺称经,此为最早矣。”*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吕思勉以为《经解》是六艺称经的最早文献,从语意推测,他是把《经解》看作是孔子时代的作品。只不过《经解》之“经”字,并不是出现在“孔子曰”之下,而是出现在文章题目之中,而先秦文章的某些题目可能是后人在传播过程中加上去的,因此以《经解》作为六艺称经的最早文献,存在明显的漏洞。
二是认为《经解》中《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教是孔子说的,但“经”字以及“经解”题目出于孔门七十子后学之徒。清人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说:“孔子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因举六者而言其教之得失,然其时犹未有‘经’之名。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尊孔子之所删定者,名之为‘经’,因谓孔子所语六者之教为‘经解’尔。”*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54页。孙氏一方面沿袭传统的孔子删述六经之说,另一方面又认为孔子时代还没有“经”的名称,因此他提出上述调停之说。
三是认为《经解》所载是孔子真言论,但《经解》应当成书于战国中期。王锷在《〈礼记〉成书考》一书中提出《经解》是孔子真言论的三条论据:第一,《经解》引用孔子论述六经言论,这些言论又见于先秦其他文献,并非虚妄之言。第二,《荀子·王霸》曾引用《经解》文字。第三,《大戴礼记·礼察》曾引用《经解》文字。此外,《经解》所论与《孝经》及上博简有相通者。综合以上三点因素,他认为《经解》应当成书于战国中期*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4—209页。。
四是认为《经解》出于汉代治《荀子》之学者之手,篇首托名“孔子曰”。杨天宇在《礼记译注》中说:“将儒家典籍尊奉为经,并用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教材,是到了汉代才有的事。而将上述六种儒家典籍称作‘六艺’(即‘六经’,若不数《乐》则称‘五经’),最早而又最可靠的记载,则见于贾谊《新书》卷八之《六术》篇。可见《经解》之作,出于汉人之手无疑,而于篇首托名‘孔子曰’。又本篇中所用篇幅最多而又着重谈论的,还是‘隆礼’的重要意义,颇疑此篇乃汉初治荀子之学者所为。”*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49页。杨天宇将贾谊《新书·六术》视为“六经”最早而又最可靠的记载,不知他对《庄子·天地》中的“六经”如何解释。
以上四种观点,分别将《经解》写作年代系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战国前期七十子后学、战国中期和汉代,各种说法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四百年。前两种观点是通过经验直观而得出的结论,后两种则是运用文献旁证方法——一种考证文献真伪及其写作年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得出的认识。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本文拟在前修时贤基础之上,继续运用文献旁证方法,从分析《经解》两组关键词入手,来考察它的写作年代。
二、 第一组关键词的考察
《经解》第一组关键词,是孔子用来形容所入诸侯国民众“其为人也”状态的六个词语:“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68,1368页。。其中“恭俭庄敬”一词产生时代甚早,《尚书·尧典》载帝尧“允恭克让”“敬授人时”*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8,430页。。此处的“恭”意为“谦恭”,“敬”包含“恭敬”“严肃”“谨慎”诸义。《无逸》称殷中宗“严恭寅畏天命”*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8,430页。,“严”意为“庄重”。可见“恭俭庄敬”思想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产生,在判断《经解》写作年代方面没有参照意义。其他五个关键词都出现在后孔子时代。
先看“温柔敦厚”。什么是“温柔敦厚”?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68,1368页。《经解》说,如果进入某一诸侯国,看到该国民众脸上颜色温润,性情和柔,那么就可以认定该国民众受到《诗》的教化。为什么民众学《诗》之后性情就会变得“温柔敦厚”?这是因为,先秦人们认为《诗》是一部讽谏政治的诗集,但是诗人讽谏政治并不是直说,而是依违讽谏,委婉托讽。如何做到依违讽谏呢?战国秦汉儒家为此提出了一个专门的关键词:比兴。什么是比兴?《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郑玄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0页。郑玄将《周礼》“比兴”视为两种修辞手法,有学者认为,《周礼》中“比兴”是“六诗”中的两种诗体,并不是修辞手法。郑玄以为,比专用于讽刺,而兴专用于赞美。其实,比不必局限于讽刺,赞美也可以用比;兴也不必拘泥于赞美,讽刺也可以用兴。正如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说:“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比兴的共同点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是直说。例如,按照《鲁诗》的解说,《诗三百》第一篇《关雎》是讽刺周康王迷恋女色不愿早朝,但是诗人的讽刺不是将周康王指名道姓地痛斥一番,而是写河边的一对小鸟交颈和鸣,它的喻义是,小鸟尚且能够如此贞洁,身为天子的周康王怎么能够不顾妃匹伦理而荒废朝政呢?《关雎》以小鸟委婉托讽,通过比兴手法来寄寓讽谏主旨,不直接说破,由此维护了周康王的面子,给周康王一个回味、反思、纠正的空间,这就是诗人温柔敦厚品格的体现。不过,“温柔敦厚”之说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以“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理论内涵,它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诗》学理论界已经提出比兴学说。中国的比兴理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论语》中孔子虽然提出“兴观群怨”之说,但此处的“兴”是指“感发志意”(朱熹说),它是从读者阅读角度提出来的,与作为诗歌创作手法的“兴”虽有一些联系,但两者区别更大。中国最早的比兴学说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610页。王朝乐官太师教习六诗,比兴是其中两项内容。《周礼》的写作年代,学术界一般把它定为战国中后期。这就是说,用比兴理论说《诗》,最早是在战国中后期。从比兴理论中提炼出“温柔敦厚”内涵,又需要一段时间。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还没有比兴理论,更没有“温柔敦厚”之说,他怎么可能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呢?
再看“疏通知远”。孔颖达将这四个字解释“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69,1083—1084,1086—1087,1087页。,这显然是望文生义。王文锦《礼记译解》将“疏通知远”翻译为“通达时政,远知古事”*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27页。,以“通达”来解释“疏通”,释义较孔疏为长。检阅文献,“疏通”一词又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文章载颛顼“疏通而知事”*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123页。。戴礼《大戴礼记集注》将“疏通”解释为“明足知远”*转引自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739,761,739页。。《五帝德》又载:“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123页。戴礼在《大戴礼记集注》中将此处“疏通”解释为“明察奸宄”*转引自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739,761,739页。。《五帝德》两次出现“疏通”,戴礼都是用一个“明”字来解释“疏通”,这堪称点睛之笔。今人黄怀信以“睿达”释“疏通”*转引自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739,761,739页。,释义近是。“疏通”之义与“洞明”相近。《尚书》记载虞、夏、商、周王侯卿士大夫处理政事的言论。对于受过《尚书》教化的人来说,《尚书》犹如照亮他们心灵的一盏明灯,理想的帝王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政治?未来的政治方向在哪里?这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接受《尚书》的教化,既能洞明古代圣王处理政事的言行风范,又可以远知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这就是“疏通知远,《书》教也”的内涵。《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答宰予关于五帝德行的问题,属于孔门七十子后学文献。从中可知“疏通知远”一词在孔子师徒时代就已使用。
再看“广博易良”。“广博易良”一词出现在什么时代?为什么接受《乐》教的人会养成“广博易良”的品质?《礼记·乐记》提供了旁证材料。先来看“广博”。《乐记》指出:“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69,1083—1084,1086—1087,1087页。怎样才能化解人们心中这些不良情绪呢?音乐就是疏导内心各种负面情绪、节制物欲的有效手段。《乐记》提出了乐教的最佳效应:“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音乐有不同的境界,最高境界的音乐与天地之间构成共同和谐的节奏,《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369,1083—1084,1086—1087,1087页。这种“大乐”对人的心胸具有涤荡、扫除、安抚、拓展等功能。在没有受到音乐教化之前,人心被物欲压迫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充满了躁动不安,种种悖乱忤逆的念头在潜滋暗长。音乐教化可以使穷贱者易安,幽居者靡闷,使人们躁动不安的心绪渐渐沉静下来,不合礼义的欲望慢慢消退了,此时心灵的空间一下子变得澄澈、开朗、阔大起来,最终达到“与天地同和”的广阔境界。《经解》所说的“广博”,就是指民众受到音乐教化之后的开朗、宽广、阔大心境。再来说“易良”。关于“易”,前人有“简易”“变易”“和易”几种解释,究竟哪一种解释接近《经解》的原意呢?《乐记》虽然两次提到“移风易俗”,其中的“易”都是“变易”的意思。如果取“变易”之意,那么“易良”就意为“变得善良”。这虽然文通字顺,但并不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广博易良”四字,“广”“博”“良”都作形容词来解,惟独一个“易”字解为动词“变易”,这种解释方法显然不符合作者原意。《乐记》又说:“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孔颖达疏:“易,谓和易。”*⑥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139,1368、1369页。《经解》“广博易良”之“易”,以释“和易”为妥。所谓“和易”,是指和悦平易,这是性情经过音乐教化之后所呈现的崭新面貌。《经解》的意思是说,民众经过乐教之后,心胸开朗阔大,性情和悦平易,品性纯朴善良。《礼记·乐记》是一个经过战国秦汉儒家学者不断增删的版本,它的作者与写作年代是一个古今学者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它的最早原稿作者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最晚的编辑者则是汉武帝时代的刘德、毛生或公孙尼。以此推测,“广博易良”乐教思想产生的最早年代,是在孔子再传弟子这个时期。
《经解》以民众“洁静精微”作为《易》教的结果。“洁”,原文作“絜”,“絜”通“潔”。值得注意的是,《经解》所说的是“洁静”而不是“洁净”。在《国语·楚语下》中,楚大夫观射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洁静”一词意义的参考:“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韦昭注:“爽,明也。携,离也。贰,二也。齐,一也。肃,敬也。衷,中也。”*上海师范大学古藉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9—560页。精爽不携贰,内心精粹,不含一点杂质,这就是“洁”。齐肃中正,心如止水,这就是“静”。心灵一尘不染,澄澈宁静,心境如同清亮见底的一潭止水,这就是“洁静”。“洁静”本来是对巫觋宗教素质的要求,为什么它会成为《易》教的效果呢?这是因为《周易》“以通神明之德”*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8,285,304、305页。,惟其与神明相通,所以对习《易》者的心理素养要求很高,“洁静”就是对习《易》者的基本心理素质要求。一个充满私心杂念的世俗之人,是没有办法通神明之德的。所以,《经解》用“洁静”来概括《易》教的效果,是非常准确的。关于“精微”,《系辞》中多有解释。例如,《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王弼注:“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8,285,304、305页。这是说《周易》穷尽未形之理,深研动微之会,这是对“精微”的一个很好解释。《系辞下》又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孔颖达疏:“此言人事之用,言圣人用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寂然不动,乃能致其所用。”*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8,285,304、305页。《周易》包含“精粹微妙之义”,受过《周易》教化的人,当然会从中领悟“精微”之义。《经解》认为,经过《易》教,民众心灵变得一尘不染,澄澈沉静,能够做到极深而研幾。“洁静精微”四个字不是同时产生的,“洁静”之说可以从《国语·楚语下》观射父之语中找到参考,其时大约在春秋中期,而“精微”则要从《系辞》上下篇中才能找到文献依据。这就是说,“洁静精微”之说至少要等到《周易·系辞》上下篇出来之后才会产生。《系辞》上下篇作于何时呢?战国秦汉儒家说孔子作《易》“十翼”,但据近人考证,《易传》大约作于战国中后期。《经解》“广博易良”之说应该是吸收了《周易·系辞》的思想。
最后看“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郑玄注:“《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孔颖达疏:“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⑥细绎文意,郑注与孔疏着眼点有所不同:郑注认为“属辞比事”是指春秋时期各国诸侯朝聘会同之时的文辞相接,实际上是指春秋行人外交辞令,而详细记载春秋外交辞令的著作是《左传》;孔疏则以为“属辞比事”是指《春秋》记载了诸侯会盟之辞并暗寓褒贬,而发明《春秋》暗寓褒贬微言大义的是《公羊传》《穀梁传》。战国秦汉人们所说的《春秋》不仅指鲁史《春秋》,那些为《春秋》作解释的著作如《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可以称之为《春秋》。可见郑注所理解的《春秋》是《左传》,而孔疏则把《春秋》理解为《公羊传》《穀梁传》。“属辞比事”是指在政治外交场合善于辞令,不存在暗寓褒贬问题,所以应该是郑注接近《经解》原意。王文锦在《礼记译解》中将“属辞比事”译为“善于连属文辞,排比事例”,这个翻译是准确的。《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而《公羊传》《穀梁传》在战国时期尚处于口头传授阶段,到汉景帝时期才著于简帛。《经解》用“属辞比事”来解释《春秋》之教,表明作者心目中的《春秋》应该是左氏所解释的《春秋》。这就意味着《经解》之作应该在《左传》问世之后*《礼记·经解》让孔子自己说出“《春秋》教”,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论语》不载孔子作《春秋》之事,大约作于战国前期的《左传》虽然隐隐约约地说《春秋》为圣人所作,但始终没有点明。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辑的《礼记·坊记》有一条记载:“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18页。)孔子在《春秋》之前加了一个“鲁”字,分明是暗示《春秋》是鲁国史官所作。第一个明确地说孔子作《春秋》的是战国中期的孟子。从孟子确认孔子作《春秋》,到诸侯国以《春秋》作为教化民众的教材,再到民众接受《春秋》的教化而发生性情变化,进而这种变化又从面色形体上体现出来,这期间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史记·孔子世家》可以知道,孔子生前在政治上屡屡碰壁,他甚至自嘲是丧家狗,即使是孔子真的作了《春秋》,又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拿《春秋》作为教化民众的教材呢?还有,如果孔子真的作了《春秋》,以他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他又怎么可能将《春秋》与《诗》《书》《礼》《乐》《易》这些先王经典并列,用《春秋》教化民众呢?但是,《礼记·经解》却公然让孔子说出《春秋》之教,这显然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即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经解》“孔子曰”并非孔子真言论,而是托名孔子之言。。
以上从词源上考察了“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的产生时代。其中“恭俭庄敬”思想最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产生;其次是“疏通知远”思想,大约产生于孔门七十子后学时代;“温柔敦厚”思想产生于《周礼》提出“比兴”概念之后;“属辞比事”思想产生于记载春秋行人辞令的《左传》问世之后;“广博易良”思想产生于《礼记·乐记》之后;“洁静精微”思想产生于《周易·系辞》之后。以上六个关键词,其参照文献较晚的是《周易·系辞》和《周礼》,而这两部文献都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按照情理,《经解》关键词的产生应该比它的参照文献还要略晚一些。以此推测,《礼记·经解》应该是战国后期的作品。
三、第二组关键词的考察
根据《礼》的折中精神,《经解》认为在施行六经之教时必须防止六种缺失:“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第1368页。《经解》提出的“六失”——“愚”“诬”“奢”“贼”“烦”“乱”——是我们考察《经解》写作年代的第二组关键词。其中的“贼”,因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旁证材料而暂且放下不论。
先讨论“《诗》之失愚”。“愚”意为“愚昧”。《经解》一方面提倡用《诗》培养民众“温柔敦厚”的品性,另一方面作者意识到,不能让“温柔敦厚”走向极端而陷入愚昧。破除愚昧的关键是要具备不盲从、不迷信的独立思考能力。儒家宗师孔子倡导独立思考,《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7,95、96页。。《论语》表明,孔子并没有把独立思考的精神贯彻到底,出于忠君的立场,他对君主时有回护之辞。《论语·述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7,95、96页。陈司败认为鲁昭公娶吴孟子违背了同姓不婚之礼,他想从孔子之处得到确认,孔子明知鲁昭公违礼却回答“知礼”。此举表明孔子虽有“温柔敦厚”之风,但难免有愚忠之嫌。到了孟子,这种讳称君主之恶的规则被打破。《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页。孟子不是愚昧地恪守君臣伦理,而是将仁义的价值置于君臣伦理之上,声称残贼仁义的人是“一夫”,而臣民对“一夫”是完全可以诛灭的。《孟子·离娄下》又载:“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0,364—365,364,306页。孟子认为君臣伦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臣民可以视君主对自己的态度而针锋相对地采取相应立场,臣民可以通过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来决定态度立场。由此可知,儒家“温柔敦厚而不愚”的理论问题,是到孟子以后才得到解决。
再来看“《书》之失诬”。“诬”是指言过其实。为什么阅读《尚书》会发生“诬”的问题?这是因为《尚书》中存在“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4页。之类的夸张语句。今天读者看到这些夸张语句,很容易知道这是语言修辞手法,但是在战国时代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先秦儒家何时开始认识到应该灵活地看待《尚书》中的夸饰语句呢?这可以从《孟子》中找到答案。《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0,364—365,364,306页。《武成》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文章,现已亡佚。文中记载武王伐纣的场景:“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飘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曰:“载事之辞,容有重称而过其实者,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不如无书之愈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0,364—365,364,306页。孟子认为,不能将《尚书·武成》中的“血流飘杵”视为真实描写。孟子是从“仁人无敌于天下”角度,推测武王伐纣不会发生“血流飘杵”现象。在《孟子·万章上》,孟子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0,364—365,364,306页。,从思想方法上解决了“《书》之失诬”的问题。所以,《经解》提出“《书》之失诬”,应该是在孟子之后。
再看“《乐》之失奢”。“奢”,意为“奢侈浪费”。推行《乐》教,需要置办钟鼓琴瑟等乐器,培养音乐演奏人员以及表演场地,这就涉及“奢”与“俭”的问题。孔子虽然在论及行礼时主张宁俭勿奢,但他并没有谈到音乐教化的奢俭问题。大力抨击音乐奢侈之风的是战国初年的墨子。墨子从下层人民的生存利益出发,呼吁王公大人停止音乐鉴赏。《墨子·非乐上》说:“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⑦⑧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55—156,156,159—160页。墨子尖锐地指出,王公大人的音乐欣赏是建立在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之上。墨子悲愤地问道:“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⑦为了满足王公大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扬干戚的耳目享受,而剥夺老百姓衣食之财,那么老百姓如何生存呢?墨子痛陈王公大人音乐享受对朝政和民生所赞成的危害:“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⑧王公大人沉溺于音乐欣赏,就会荒废国家大事;士君子沉溺于音乐欣赏,就会不能内治官府外收关税;匹夫匹妇沉溺于音乐,就会荒废男耕女织。墨子抨击王公大人享受豪奢的音乐现象,从当代考古发掘得到印证,1978年湖北省发掘曾侯乙墓,随(曾)国本是一个小国,可是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编钟、编磬、建鼓、琴、瑟、笙、箎、排萧8种共125件乐器,宛如一个宏大的地下乐器展厅,从中可见春秋战国诸侯贵族音乐享受是何等奢侈!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子对此现象痛下针砭。《经解》反对《乐》教过于奢侈,应该参考了墨子的意见。据此推测,“《乐》失之奢”的思想,应该产生于墨子倡导“非乐”之后。
关于“《礼》失之烦”,王文锦将“烦”译为“烦苛琐碎”。批评礼仪烦苛琐碎,可以在《晏子春秋》和《墨子》中找到相应材料。《晏子春秋·外篇·仲尼见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为不可第一》载:“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05—206页。按,晏子阻止齐景公封孔子之事,颇可怀疑。《论语·公冶长》载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从此语可以看出,孔子对晏婴为人充满敬意。《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论以礼治国的重要性:“礼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工(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此语与《晏子春秋》中晏婴反对孔丘以礼治国的记载互相矛盾。《墨子·非儒》中有一节与《晏子春秋》相近的文字:“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80页。太史公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将《晏子春秋》中晏婴之语进行压缩:“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11页。“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是对“《礼》失之烦”的一个极好注脚。晏婴长期担任齐国国相,他的言论是齐国史官记载对象,所以《晏子春秋》的素材应该是齐国史官的记录手稿。战国初年仰慕晏婴的人将其编辑成专书。《晏子春秋》在节俭问题上与《墨子》观点相近,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编者是墨家学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此推测,“《礼》失之烦”的思想应该产生于战国初年。
最后来看“《春秋》之失乱”。王文锦将“属辞比事”译为“善于连属文辞,排比事例”,将“乱”译为“乱加褒贬”。前文指出,“善于连属文辞,排比事例”是指《左传》所载行人善于辞令,而“乱加褒贬”则是指《公羊传》《穀梁传》所阐发的《春秋》暗寓褒贬。王文锦用《左传》之义译“属辞比事”,用《公羊传》《穀梁传》义译“乱”,前后不能互相配合。“乱”应该是指乱说话。不能乱说话的思想,在春秋时期即已产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子产赴晋朝贡,遭到晋人冷遇,子产命令随从拆毁晋国墙垣,以便安置车马。晋人前来问罪,子产慷慨陈辞,晋人知道理亏,由此善待子产。晋国大夫叔向闻知此事,发表评论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89页。“辑”意为“和谐”,“绎”意为“动听”,“辑”“绎”的反面就是“乱”,意即随便乱说。“《春秋》之失乱”的思想,应该产生于《左传》问世之后。
以上六教之失,除了“《易》之失贼”以外,“《诗》之失愚”“《书》之失诬”思想产生于孟子以后,“《乐》之失奢”“《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思想产生于战国前期以后。从总体上看,六教之失的思想应该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后。
四、《经解》作于战国后期
以上两节运用文献旁证的方法,对《经解》两组关键词的产生年代进行了考察。第一组关键词考察结果表明,《经解》大约作于战国后期;第二组关键词考察显示,《经解》大约作于战国中期以后。结合两组关键词考察情况,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经解》大约作于战国后期。惟其如此,作于战国后期的《荀子·王霸》和作于楚汉之间的《大戴礼记·礼察》才能引用《经解》的文字。
读者可能会提出疑问:以上两组关键词的考察充其量只能大致确定《经解》写作年代的上限,《经解》写作年代的下限又该如何确定呢?它有没有可能作于汉代呢?为了使文章结论更严谨一些,还需要对《经解》写作时间的下限进行研究。
《淮南子·泰族训》中有一段文字与《经解》颇有近似之处,可以作为研究《礼记·经解》的参照文献。朱自清在《诗言志辨·诗教》中,曾经将《礼记·经解》与《淮南子·泰族训》作了比较,认为《礼记·经解》可能作于《淮南子·泰族训》之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附和过朱自清的观点,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未必准确。为了便于比较,现将《淮南子·泰族训》一段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六艺异科而皆同道(《太平御览》无“同”字):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太平御览》“尊”作“揖”)让者,《礼》之为也。宽裕(《太平御览》‘裕’作‘和’)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太平御览》“几”作“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太平御览》“忮”作“乱”),《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高诱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53页。
将《泰族训》与《经解》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说经有同有异:释义相近的有两经,即《诗》之“温惠柔良”与“温柔敦厚”;《礼》之“恭俭尊让”与“恭俭庄敬”。释义相差较大的有四经,即《书》之“淳庞敦厚”与“疏通知远”;《乐》之“宽裕简易”与“广博易良”;《易》之“清明条达”与“洁静精微”;《春秋》之“刺几辨义”与“属辞比事”。《泰族训》所说的六艺之失,只有在“《诗》之失愚”一点上与《经解》相同,其他五经之失都不同于《经解》。《泰族训》某些关键词是战国末年至秦汉时代的产物。例如,《泰族训》以“淳庞敦厚”作为《书》教的效应,用“淳庞敦厚”思想解说《尚书》,始于汉代伏生《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把“颛顼”的“顼”解释为“信”“悫”*孙之騄辑:《尚书大传》卷1。,说明颛顼是用淳朴诚实的精神治理天下,这与“淳庞敦厚”精神相通。《经解》不用“淳庞敦厚”而以“疏通知远”来解说《书》教,这是它早于《泰族训》的词源证据。又如,“清明条达”思想应该是《周易·序卦》面世以后产生的,《序卦》的写作比《象辞》《彖辞》《系辞》要晚,大约作于战国末年甚至秦汉之间。《泰族训》以“清明条达”作为《易》教结果,说明它受到《周易·序卦》的影响,不像《经解》“洁静精微”受《周易·系辞》影响,这说明《经解》写作比《泰族训》要早。又如,《泰族训》“《易》之失鬼”的思想应该产生于荀子之后。《荀子·大略》说“善为《易》者不占”*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3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司马迁:《史记》,第2348页。《泰族训》“《易》之失鬼”之说应该是对荀子反对运用《周易》进行巫鬼活动思想的呼应。再如,“刺几辨义”“《春秋》之失訾”的思想主要是《公羊传》《穀梁传》大行之后,而《公羊传》《穀梁传》是在汉景帝时期书于简帛之后才大行于世的。《泰族训》以“刺几辩义”作为《春秋》教化的结果,并且提出要防止“《春秋》之失訾”,这说明它所取的是《公羊传》《穀梁传》解说的经义。以上剖析说明,《礼记·经解》作于《淮南子·泰族训》之前,《泰族训》的作者参照了《经解》,并根据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做了适当的调整。《淮南子》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道家著作,它的作者吸取《经解》,表明《经解》的传播已经有相当的时日了。总之,《礼记·经解》既不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也不会作于汉代,它应该是战国后期的儒家后学假借孔子名义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本文所论《经解》中关键词汇所对应的文献,只是限于现存文献,而上古文献亡佚甚多,这些亡佚文献中有没有关于《经解》的参考材料,目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