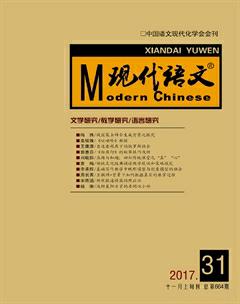简论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
摘 要:在新历史小说中,“非英雄化倾向”成为小说主要的价值命意及问题意识。与其它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相比,表现为英雄人物的“非英雄化”,表现浑噩的人生、揭示卑琐的欲望。它以普通人置换英雄人物,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重新挖掘出来,使悲观主义和绝望的宿命观成为反史诗性的必要注脚。同时,因为它过于表现历史的虚无、非理性特点,逐步远离了历史客体,虚构的成分也越来越高,使新历史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衰落并走向消亡。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非英雄化 浑噩人生 卑琐欲望 衰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变成了一个被解构的对象,新一代的作家以与革命年代作家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与现实生活:从解构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所发生的历史。这一代的作者不再像历史革命小说家那样通过再现历史来进行创作,他们听从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历史中寻找自己的话语场,运用自己的话语来“写历史”。所以,新历史小说作家通过发掘已“不在”的历史场景、历史事件,来对历史作出新的叙述。这一种叙述是对历史的再认识和新解构。但也因为过于的注重虚构和反思,没有使作品内容进一步的升华,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
在新历史小说家的再认识和新解构里,英雄人物的“非英雄化”变成了新时期创作的常见现象。但在以往文学作品中,英雄历程中通常有这样几个人物形象存在: “英雄”“導师”“阴影”等,“英雄”是主人公最终的归途,而“导师”则是在主人公成为“英雄”成长的道路上更好地发现自己的存在,“阴影”的存在则对主人公能否成为真正的英雄起到决定作用。而光芒四射的人生和伟大崇高的理想也是成为英雄历程中两个互为相关的方面。但新历史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都与以往的英雄蜕变历程,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他们的生命里有的只是浑噩的人生和卑琐的欲望。
一、“英雄”消解
英雄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在主人公经历种种磨难后,会有重大的改变,那就是曾经困扰他的难题都得到了解决,亦或是他所追逐的梦想得以实现。但他们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尊敬,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或者是其它的什么因素,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他人、集体、部落、国家或者是某种信仰和价值观牺牲了小我。自我牺牲是英雄最主要的特征。
在新历史小说中,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变成了历史滚动中的小齿轮,更甚连小齿轮都算不上。他们不像以往的主人公,就算没有强大的出身背景,也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迈向英雄的光环中去,新历史小说中大多数正面描写的对象是边缘人物,类似土匪、罪犯、妓女等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笔下都抛弃了简简单单、能以普通的好或者坏来界定自身人物形象的审美定式。
比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的曹杏花,就是一个长着瘿袋喜欢扯着嗓子骂人、斤斤计较、爱贪小便宜的女性形象。曹杏花是粗鄙的:因为觉得杨天宽分地不公平,扯着嗓子就骂村干部“猪哩,哪个托生的你呀?你前辈造了孽,欺负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了吧?”[1]曹杏花是自私的:在杨天宽叔伯兄弟收成不好时,拒绝接济他们;邻居家的葫芦长到自家来了,也能顺走两个;为烈属、军属担水也全是因为有四个工分的利诱;至于到地里上工时,就筋骨全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可这样一个女人“坏得不透”,因为她,一家八口虽然吃得不好,但是在粮食短缺的时候也没有饿死一个人。但曹杏花的行事方式是失去了英雄气概的:她没有民族气节,也没有什么大义,她只有眼前那一家八口人,不高兴就破口大骂,没有了粮食就东偷一点,西挪一点,甚至于还表扬女儿的偷盗行为,实在让人爱不起来,但是也谈不上恨。她就如同历史河流里的一粒沙,被卷动着往前走,没有崇高的理想,更谈不上什么大义牺牲。
二、“导师”消失
在其它的文学作品中,导师作为英雄心灵的守护者,始终起着“教育”的作用。他守护着英雄的良心,教会英雄什么是民族气节,什么是顶天立地,使主人公最终成长为无所畏惧且光明磊落的英雄,他是主人公在漫无目的、漫漫黑夜的英雄成长道路上的明灯。
但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的笔下主人公是单打独斗的,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导师来引导,他们是被历史滚轮推动着向前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忠孝礼义,也不知道什么自我奉献,他们的一切发展都只不过是受自己的本能驱使。
就像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枣树的故事》一文中,岫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来引领她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教她将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她所做的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不知民族节气,不用顶天立地,自我牺牲地活着。
文中是这样写她的:“想象中的岫云早死过许多次。没人能理解她心灵经过的不平凡历程。她从来没有死心塌地地爱过白脸,她所作的不过是对命运的一个顺从。”[2]岫云在经历丧夫、和杀夫仇人白脸在一起后,又勾引了自己做保姆的那户人家的先生老乔。在她的一生中,她仿佛不知道什么是仇恨,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也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与一些其它的女英雄角色相比较,她活得实在太无聊且卑微了:没有自己的追求和信念,一切得过且过。而白脸、尔勇在作者笔下加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也并非是有着何种抱负或思想觉悟,而只是为了各自的生存或报仇。在日本入侵,国共联合抗日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岫云等人被写成了一个个人的“小”历史,没有“刘胡兰”,也没有舍生取义。
三、“阴影”变换
“阴影”在英雄成长历程中被定义为被排斥和不能接受的向度,英雄往往只有打败“阴影”才能获得成长,所以“阴影”的作用就在于不断的挑战英雄,使主人公在击败自己的过程中获得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新历史小说中,由于其反对二元对立、凸显个人,“阴影”这一角色往往被置换成了主人公自己。新历史小说家刻画的主人公无一不用自己好坏不明的形象告诉读者:在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情况下,人的一切都会被毁灭和吞噬,而人性恶的一面会迅速生长,并变本加厉地显现。
苏童在《米》一文中就刻画了这样一个集生存欲、性欲、权力欲、掌控欲为一体的主人公形象——五龙。五龙由于故乡发大水闹饥荒而被迫来到了城里,这使五龙对米有着一种生存欲的寄托,为了生存他什么都肯做:被阿保踩在脚下让他叫爸爸;在冯老板的米店忍受压迫,不顾廉耻不计后果地使自己的生存欲望得到满足。在五龙的生存欲得到满足后,他心中的恶也仿佛找到了沃土,开始疯狂生长,逐渐蔓延到性欲上去了。他霸占米店老板的漂亮女儿织云、绮云,对其施行种种变态的行径,而五龙就是从这里开始将人类原始的欲望埋入沃土,让其迅速生长,将自己推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此,他的人性开始扭曲,也一辈子都浸没在生存和复仇之中,消失了自我,被欲望一直驱使着。在自我泯灭和湮灭别人之后,五龙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性、钱、权以及整整一火车的大米。到这里好像所有“阴影”都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在新历史小说中,“阴影”从来都不是外加的,都是衍生于主人公自身内心深处的“恶”欲望。当“恶”的欲望满足到极致、发挥到极致,五龙的生命也就要结束了,就在他拖着溃烂的身子,带着很多很多大米回到自己的故乡“枫杨树”时。endprint
在刘恒《白涡》中,主人公周兆路的“阴影”也是属于他内心深处的“欲望”。他和华乃倩的婚外情,源于对于性的欲望;他对钱老的尊重,源于对于权力的欲望;他对妻子的“责任”,源于对家庭安稳不为自己仕途添麻烦的欲望;以及对周围人的“和善”,源于为了在必要时能多得两票。他做这些我们看似正常的事情,都是为了让内心深处的欲望得到生长的肥料。直到最后文章写到:“周兆路已经没有恐惧。”这时,他内心的欲望虽然不一定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但他已经万劫不复,他已经被“阴影” 给吞噬了,只会被不断被欲望支配着。
四、浑噩人生
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其人生都是光芒四射、精彩绝伦的,他们往往都拥有着崇高的理想与目标。例如《红岩》《创业史》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其中的英雄主人公负载着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国家救亡启蒙、革命改造与构建社会正义的严肃使命,充当着人民大众的精神明灯、道德典范与救世主。”[3]
反观新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更没有“虽然身份平凡但是精神力量强大”的人物形象,只有家长里短、婚丧嫁娶、家庭兴衰等日常生活。
李锐的《旧址》中,故事發生的背景跨度非常大,从抗日到国共混战,再到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十七年文学”期间的写作手法,这将是一个人才辈出、英雄辈出的时间段。但白园中的三个人——白瑞德、白杨氏、杨琼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却上演了一场妻妾争夺的戏码:白杨氏因为多年没有为白瑞德生下一个儿子,想要将表妹杨琼琚变成白园的姨太太。洞悉一切的白瑞德在一次和白杨氏坦诚交流后,便顺水推舟纳了杨琼琚。但杨琼琚不久后就生下了个儿子,而年迈的白杨氏却开始嫉妒起来了,绝经则让她彻底陷入疯狂。于是关于白园的叙述通篇就在两个女人交锋中的杀子、下毒、诬陷等情节中展开。
苏童的《妻妾成群》也是如此,上过大学的颂莲,没有成为革命先进分子,而是成为了陈府后院四个女人争夺陈老爷“临幸”的一员。
叶兆言在《状元镜》中所描写的“张二胡”也是这般,浑浑噩噩、不知所以地活着,没有自我发现的过程,也没有让自己“真正”地活着。
五、卑琐欲望
新历史小说通过对个人欲望的重新书写,来深化作品对人自己本身的生命价值以及生存处境的表达,表达着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对生命个体价值的关怀,“也是对‘文学即人学这一经典文学主题的回归。”[4]新历史小说家们借着对人的欲望的关注来探索历史上人的“生存状况”,历史不再像以往一样是“革命的”“进化的”,历史开始充斥着个人私欲。
譬如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中,描写了马村普通老百姓为了权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生活气息,使历史在这里仅仅只是权力争夺的背景板;苏童在《罂粟之家》也写下了地主刘老侠为了满足自己能够占有父亲的姨太太翠花的情欲,而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白鹿原》中的女革命者白灵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虽然都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也都加入了共产党,但白灵是以掷币的方式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是为了和情人鹿兆海统一战线,白灵才退出国民党加入的共产党。
但林道静不同,她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加入的就是共产党,她有着一个为国为民的理想。这就是新历史小说和史诗性小说的不同之处:一个是以个人欲望为主旋律的偶然性历史进程;一个是塑造革命知识分子拼搏为理想奋斗的成长史。
在新历史小说中,对个体人性的探索免不了从人的生存和欲望下笔,在生存环境受不到保护时,人性免不了为自保不择手段,此时大义、民族情结、礼义廉耻都被生存碾压得所剩无几,每一个小人物的背后都只剩下了自己的欲望,因而这样的欲望在宏大的民族大义、崇高理想面前显得那么地微不足道和卑琐。
六、走向衰亡
就像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说的那样:“所有的叙述不只是简单地记录事件,在转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而是重新描写事件系列,解构最初语言模式中编码的结构以便在结尾时把事件在另一个模式中重新编码。”[7]新历史小说家注重对历史的解构,在历史反思、个人凸显、反对二元对立、政治化批评、关注女性的字里行间倾向人文主义,在不断解构和反思中,新历史小说使得历史和民族的存在有了自身独到的文化性和深远的历史性。
但新历史小说在演进过程中,逐步远离了历史客体,对人物的塑造也逐步变得扁平不立体起来,其文化意蕴也越来越淡薄,虚构的意味越来越重。虽然历史的偶然性不可忽视,但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偶然性,那历史也会变得荒诞起来,人文价值也会不复存在。因此,新历史小说最后因为矫枉过正而步入了庸俗化的境地,走向了衰亡。虽然读者可以接受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可以接受平庸的“个人历史”,也可以接受人性的丑陋,但是却无法忍受在这些不确定、平庸、丑陋人性的背后,没有对发生这类事件的社会原因进行深刻的挖掘和没有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注释:
[1]刘恒:《首届北京文学节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刘恒卷》,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2]叶兆言:《枣树的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00页。
[3]李胜清,周立琼:《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分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99-102页。
[4]李娴:《论新历史小说的欲望书写》,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5]张京媛译,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1]刘恒.首届北京文学节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刘恒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47.
[2]刘恒.首届北京文学节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刘恒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38.
(许可丹 湖南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4111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