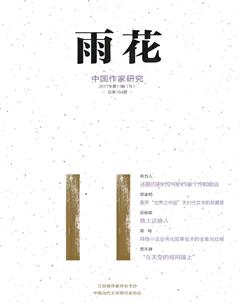为生命注笺
倪健
台湾的女性散文多以水气灵动、温馨细腻的特质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其中或甜或苦,或激越或安详,或绚烂或平淡,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爱的追求之真挚和执着,对生命的观照和珍重。这是台湾女性散文备受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而张晓风以其生命和生存本体意识的高度重视使得她在众多女散文家中独树一帜,正如大陆学者楼肇明所说的,“生命和生存本体论的诗性阐释,是这位女作家奉献给现代文学史的最大功绩”①。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晓风的创作更多的融入生命个体体验以及对生命本体的思考,纵身于生命呈现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和空间,对生命本体进行一再地阐释和追问,带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以诗意为生命作注笺,发现并阐释生命之美。
一
张晓风强烈的生命和存在意识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其实在她70年代创作的戏剧和小说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她的极有深度的现代剧富有锐意创新与实验精神,不断深入探索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以及宗教与人生的关系,使得她成为“台湾戏剧三大家”之一。由于她的剧本具有“辞章华茂,充满诗情画意,抒情色彩浓郁,而且说理成分厚重,注重情绪、意境的传达”、“充满‘诗剧中的象喻意义”②等特点,可能不是完全符合写实剧的要求,但这种独特使得她的剧被称为“散文剧”“意念剧”③。张晓风作为台湾科幻小说的拓荒者同样是凭借奇特的想象力,把对人生的价值观念、生命态度与生存法则的思考和观照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呈现出来,独具特色。张晓风深厚的国学功底、悲天悯人的心怀促成她在80年代散文创作质的飞跃。综观她的散文,她执于思索、追寻、质问,要向天地万物问出一个“解释”④。对于她而言,神话和诗需要一番“解释”,红尘素居、碌碌诸事同样需要一番“解释”,“解釋”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唯有了“好的解释”,宇宙才能端正庄严,万物方能含情脉脉。所谓“好的解释”绝不是对某事某物下科学的理性的精准的定义这么简单,其中包含着人的苦心、恕道和智慧。所以张晓风乐于在朗朗天日下,为乾坤万象作一次次简报,也欣喜于看到人们如何用语言、弦管、丹青,用静穆和爱,一一对万物费心注释。在《给我一个解释》中,张晓风是这样看待“解释”对其重要意义的,“物理学家可以说,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根杠杆,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而我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是的,只要给她一个“解释”,她可以不畏惧不后悔的选择长程的劳瘁。
生命对她而言,到底意味什么?她从生命最初的故事——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过程中开始欣赏起人体的繁星和苍穹,探索人体本身的种种奇奥,原来,那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却是大地倾身、诸天动容的一刹,历经千重磨难孕育而出的生命,不得不叫人肃然自重,人应该对生命有绝对的虔诚、敬畏和感恩。张晓风始终坚信,生命一定是美丽与危险并存的,她在《待理》《矛盾篇(之一)》和《矛盾篇(之三)》中惊呼生命是“一项不为而有不豫而成的美丽”,肉身的欲苦、饥饿、疲倦困顿,乃至是死亡也都是可庆可贺的,但同时,生命之中亦有其大悲和创痛,人不仅会经历无数次的离别,而和人际以外的环境和状况(比如说年轻的身体、曾经的记忆、知识和智慧)的一一告别的疼痛都是无法言说的尖锐和苍凉,生命是“一项随时可以中止的契约”,短暂而仓促。人在面对天地的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垠时是会彻底地“溃不成军”,低下骄傲的头颅而“从心底承认自己的卑微和渺小”,那么生命个体的存在还是否有意义?张晓风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不断驳辩、发难、思考之后,她顿悟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关于生命、关于存在的“解释”。张晓风时常思考自己在天地间的存在和位置,在《也是水湄》中称“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白,在一霎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她不以肉体的有限承认生命的意义,坚持“我”就是“我”,“我”的生命,“我”的存在既不是“架”“栋”“量”等单位计量,也绝不以公斤、公分、智商、学位来计量,“我,不纳入计量单位”(《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正如楼肇明很准确地指出了张晓风创作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在于她比一般人都要急切地去寻求那被连根拔起而飘浮悬置的灵魂的栖止,由此造成了一种“‘心与‘我的分离状态,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人格定格的冲动”④,这里的“心”是指理想化的自我,“我”是指有限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命个体。而张晓风意图把“心”与“我”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合二为一,完成“自我”的重新定位,理想化了的自我附加在有限的“我”的身上而成为蜕新的“我”,这个重生之“我”得以在八方四极、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中遨游自如。她同样看重生命体验,不厌其烦地把自己一路走来,所感所思,欢笑泪水都一一记下,这些过程让她成为唯一不二的生命个体,或遗憾或疼痛已不再重要,因为“活过了就是一场胜利,就有资格欢呼”(《矛盾篇(之三)》)。由此推出,张晓风在《也是水湄》《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和《我在》中急切想要回答宇宙乾坤、天地和历史“有个孩子‘在这里”“我在”,显然是张晓风对自我身份进一步的认定寻求,是强调“有我”之状态。
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如何生存、如何生存地有意义,张晓风扎根于最平凡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日常生活中,坚持以一种“从俗”的智慧,贴向生活,贴向平凡,生命的意义不可用金钱去衡量,让飞翔的且去飞翔,扎根的且去扎根,美丽的且尽情绽放美丽。她在《秋天秋天》这篇散文中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对于生命之理想状态:“愿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太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漂浮夏云、没有喧哗、没有旋转着的五彩,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只有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只有梦,像一树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我在”⑤是张晓风艺术人格构成中的主体性的体现,她向宇宙乾坤、历史、现实坚定地喊出“我在”,把“我在”理解成“认识自己领有在”,在生命中时刻保持“我在”的姿态,这种姿态实质上就是把自己置身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里,在时空谱系里进行人格自我定位,时间不是单向度的直线,它可以轮回、反演,空间则是立体的,可重叠、复合,时间一定要联系于空间,相对于空间而有时间,相对于时间而有空间,时空是“此在”所必须有的一个广阔的价值参考系,是生命价值和存在价值得以实现的舞台。张晓风瞿然四顾,置身于时空纵横交错中,于过去、于当下、于国家、于天地之间寻求一个“解释”,选择把诗与解释学相互渗透、转化和融合,以“待兴而发”的灵动诗意地对生命和存在本体进行一再的阐释,发现和享受着生命之美,并且随时都能够坚定地说“我在,我在这里。”endprint
二
时间和空间是生命得以延展的境域,渗透着人类的生命情怀和命运感,张晓风作品之所以能在同时期作家中脱颍而出,的确在于她站在生命的高度俯览人生。她有很浓烈的时间感和历史感,常常是纵横经史出入古今,与仲尼、米开朗琪罗、汤显祖对话,更是在诗词曲赋中流连忘返。临溪水、石头、柳树而立时,思绪神驰遥远的过去,不禁发出“谁在溪中投下千面巨石?谁在石间播下春芜秋草?谁在草中立起大树如碑?谁在树上裁剪三月的翠叶如酒旆?谁起这无数张招展的酒旆间酝酿亿万年陈久而新鲜的芬芳?”⑥的质问,境域开阔,如虹之豪气一以贯之。张晓风另一个建立自己艺术人格的根本途徑在于空间书写的独特。空间书写并不仅简单的指她对于地理空间的描绘,其中更是蕴含了张晓风对于宇宙天地的思考、人类文化的态度和情感。其中一例,张晓风对中国的多方位、多侧面的吟唱是很多作家所不能及的,在她的笔下,中国不仅仅是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大量地来自唐诗宋词,是一已被中国古典人文精神诗化了的华夏九州”,她更关注的是一个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踯躅前行的中国,常常“以唐宋时代的诗话了的历史时空来烛照身之所栖现代社会、现代中国”,显示出其“心域”可以很广阔,思维空间可以很广阔。
如今,强调多元化的世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张晓风用自身的实践给出了答案。她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人了,无论是身处台湾还是异国,她无时无刻不把中国放在心底,其中既有客体层面的对故土的浓厚乡思与乡愁,如《远程串门子》《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等,也有在文化层面的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寻根意识,如《愁乡石》《炎方的救赎》等,更着力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释、批判、反思、传承和发扬,如《想你的时候》《孤意与深情》《眼神四则》《矛盾篇(之二)》《地勺》《两岸》等。她对中国的情绪太复杂,“我的中国被烙铁烙过,被污水漫过,又圣洁又烂脓,又崇伟又残破,被祝福亦被诅咒,是天堂亦是地狱,有远景亦有绝望”“有一个名字不容任何人污蔑,有一个话题绝不容别人占上风,有一份旧爱不准他人来置喙。总之,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我会一面谦卑地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有一言伤及它,我会立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在所不惜。”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对传统的悲痛的孤意,深情使生命波澜壮阔。对于海峡两岸的相对而立,她自有巧妙的角度,“只因为这世上有河,因此就必须有两岸”“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纵然被河道凿开,却不曾分离。年年春来时,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在河底秘密地挽起。”真正的中国人不在于身处何处,而在于把中国放置于心的何处,难道说“那些住在自己国土上的人就不背井离乡了吗?”“像塑料花一样繁艳夸张、毫不惭愧地成为无所不在的装饰品,却从来不知在故土上扎根布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是整个一卷生命都不值得打开一看的”。现代的中国如果能融入被她慧眼捕捉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那么中国智慧将在她的注笺下能够历久弥新。
人是现实社会的个体,自然有其局限,当面对“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时,张晓风亦觉生命的可贵之处。《当我去即山》的构思新颖别致,想常人不能之想,对时空作出的独特体思叫人称奇。
我去即山,越过的是空间,平的空间,以及直的空间。
但山来即我,越过的是时间,从太初,它缓慢地走来,一场十万年或百万年的约会。
当我去即山,山早已来即我,我们终于相遇。
......
人和山的恋爱也是如此,相遇在无限的时间,交汇于无限的空间,一个小小的恋情缔结在那交叉点上,如一个小小鸟巢,偶筑在纵横的枝柯间。
“我去即山”“山来即我”,“我”和“山”相遇相恋,恐怕再没有人思维如此跳跃,我和山的“恋情”因为时间的绵延、空间的广阔而有一种深度和厚度,让人不容置喙,为之动容。
再如另外一篇散文《秋千上的女子》,作者并不简单描写了一个荡秋千的女子的爱情故事,而是从“秋千”入手,翻拣出它的祖籍,它由北方山戎入汉的过程,它在汉家典籍中的描述,进而揭示出“秋千”为何竟成为汉家女子看见“狱门以外的世界”的工具。这篇散文中的两个人物形象耐人寻味,一个是打秋千的女子,另外一个就是“我”。秋千上的女子“摇摆”于深深闺阁与世界之间,“摇摆”于束缚与“自我”之间,因为“身为女子,便等于‘作女监,所不同的是有些秋千狭小愀隘,有些监狱华美典雅,而秋千却给了她们合法的越狱权,她们于是看到远方,也许不是太远的远方,但毕竟是狱门以外的世界”,于是,“远方”便是希望和理想的象征,而秋千自然也就成了功能有限的工具。而“我”的形象的塑造也是耐人寻味的,“我”是成长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女子,我在现实生活和想象世界中“摇摆”,我与古代打秋千的女子相遇,是有限的时间(此刻)和无限的时空(古代)的相遇,一瞬间竟觉生命可以如此浩瀚森森,“将无垠,握在手中,见永恒,于一瞬间。”张晓风突破和更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对生命的思考以时空的维度来呈现时,更显其有力量有深度。张晓风的作品时时透露着对过去-现在-未来纵深地思考,常常是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的,寻找着生命个体要走的路。
三
张晓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的体悟极具天赋和灵性,古典诗词信手拈来,中国文化之精髓在她的咀嚼中历久弥新。同时,因对世间万物有着湛湛深情,生命在她的手指间犹如三月春风,温暖如酥。所以,在张晓风的笔下,生命是极其美丽的,因为生命有厚度,也有温度。有学者把张晓风描绘生命之美的艺术技法称作为诗性阐释。苏延红在《感悟晓风——张晓风诗性解释学散文初探》中对诗性阐释学散文有这样一句说明和定义:诗性阐释学散文是民族文化积累和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自然延伸,其核心是关于生命本体和存在本体且具有感性形态的诗化哲学,目的在于发掘生命之美。⑦笔者认为,张晓风的诗意阐释既体现在审美对象上,也体现在独特的艺术追求上。张晓风善于发现常人所忽略的东西,日常生活琐事或者是那些不易察觉的事物在她的世界里都蕴含着美。例如在《属于一枚咸鸭蛋的单纯》这篇散文中,张晓风心思何等细腻,竟然从再普通不过的咸鸭蛋中看出生命的意义——单纯地活着,融入对时间、生活、人生的种种思量。endprint
关于张晓风散文诗意阐释的诸多艺术手法,很多学者都发掘出她从传统与现代中汲取养分,这里主要是列举出她的诗性阐释中具有创意并已然形成一种独特风格的艺术手法。
第一,她擅长发挥丰富的想象,观察事物的视角也是多变的。例如张晓风从内容和形式上模仿古老的字典如《尔雅》来为已有的名词作注解,如《地篇》《地泉》和《色识》。注解已然富有诗意,更何况张晓风动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各种器官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使读者在散文中简直能看到艳丽画幅、听到悦耳歌声,再引出诗词歌赋、古今中外神话,恍如置身仙境。
第二,张晓风尝试吸收融入西方的、现代的写作技巧,抒情方式上渐渐有了“跳跃式,闪现状,像一支变奏曲,无迹可循,一片凌乱,犹如走夜路,不见前路,也不见全景方位,只能凭触摸感觉抓住一切可辨可感之物来确定路况与方位”的特色,笔尖随着意识的流动而流转,随心随性、天马行空、无所束缚,自有不可阻滞的气势。比如《星约》是这类艺术营构的典型的文章。
第三,张晓风散文诗性阐释既注重有“感性的感动”,也希望融入“知性的深度”。例如她时常用禅定式的艺术思维把参禅悟道的意境引入散文,对禅具有自觉的追求,体现在文章上则是具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和哲理意味,体现在生命个体价值上则是将人生诗意化达到“诗意栖居”(海德格尔)的目的。具体以《地勺》中的一段描写为例:
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吗?却有私下希望那只瓢能大一点深一点.而湖便是那只大勺,清可见底,甘洌可饮。抬头望天,群星灿然中我只识得北斗七星,此星凑巧也叫做“勺子星”。不知这只瓢勺意欲舀些什么。舀些玄思吗?舀些光芒吗?舀亿万年来人类的仰望吗?在星子的天勺与大湖的地勺之间,我们的小舟也许也是一只小勺吧?只舀一小时的湖上良辰。我自己也是一只小勺吧?舀一生或痴或狂的欲情。
语言作者以“地勺”喻湖,继而写天上的星勺,又联想到所乘的小舟以及舟上的人皆是“勺”,这个新奇的比喻之所以有效,在于作者抓住了“勺”的特点——舀,舀些玄思、舀些美景或者是舀一生的欲情,是作者对于天地万物与生命个体的沉思。這种以小物联想到宇宙大化,由天地继而到个体的禅定式思维在张晓风的多篇比如说《咏物篇》《花朝手记》《春俎》《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等等文章中均有体现,虽然不免有为情造文和人为雕琢之嫌,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家已将这种思维融入生命本身并且在审美趣味上对其进行自觉的追求和实践。
第四,张晓风对于中国古诗古语古韵的熟稔运用,即便是把语序或词语的颠倒、打散、错位、重组,也丝毫不会减少其中的韵味。举张晓风读汤显祖的《牡丹亭》而写的《炎方的救赎》为例,全文分为四个片段,每一片段都有一个很有诗韵的标题,分别是“两组数字”“他们的坐标”“然而,她在岭北,他在岭南”“如果你呼唤我,我将跨越冥河而来”,欣赏品读古典文学也用如此古风韵味的表达方式来写,令人惊叹。其中的语句充溢着古之幽情,人称的不断转换,看似不经意的随性而发,其实饱含着感性和妙悟,给人以新奇美妙的审美体验。再有,张晓风更喜欢用较为陌生的古人古语,既有新意又为散文增添了几分深雅和醇厚,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问题的思考:古人的智慧应融于每个人的骨子里,而绝非绣花拳脚,生活的诗意同样是一种态度而非形式。
张晓风是一个对生命本体和生存本体极为观照的作家,以感性和智慧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寻找生命之美,寻找一种“我在”的姿态。她出入古典书籍,用温度温暖了苍白的故纸堆,古今中外,无所不寻,用生花妙笔绘制一幅幅有层次感的“生命之图”。
注释:
①楼肇明:《星约·情冢·诗课——张晓风散文论》,见王鼎钧编《星约·情冢·诗课·序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②林丹娅:《台湾现代女性戏剧》,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2页。
③转引自林丹娅:《台湾现代女性戏剧》,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4,687页。
④张晓风:《晓风素描》,徐学选编《再生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⑤张晓风:《给我一个解释》,刘俊选编:《从你美丽的流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⑥张晓风:《我在》,刘俊选编:《从你美丽的流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⑦苏延红:《感悟晓风》——张晓风《诗性解释学散文初探》,《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