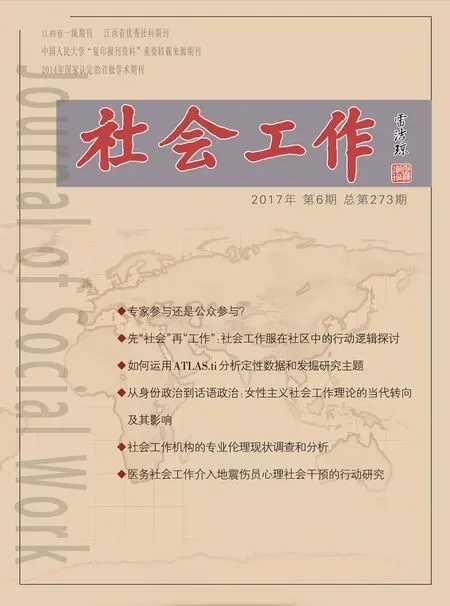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地震伤员心理社会干预的行动研究①
——以8·3鲁甸地震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社工站为例
杨婉秋 沈文伟 刘桂昌
一、背景介绍
2012、2014年云南省昭通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9·7彝良地震”(震级5.7)、8·3鲁甸地震”(震级6.5)。8·3地震导致617人死亡,114人失踪,3143人受伤,108.84万人受灾,8.09万间房屋倒塌②来源:各类自然灾害致全国逾2亿人次受灾1583人死亡[EB/OL].中国新闻网,2015-01-05.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05/6936304.shtml.。国家民政部启动了支援鲁甸灾区的社会工作方案,号召北京、上海、四川、广东、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多支省外社会工作(以下简称“社工”)队伍和云南本省社工整合力量,奔赴灾区,积极展开救援(任嘉威、王维悦,2016)。在民政部统一指挥下,云南省民政厅指派当地三支社工队伍进驻灾区,其中一支为医务社工,负责在伤员集中救治的医院开展心理救援工作。
8·3地震后昭通第一人民医院共收治伤员五百余人,其中住院超过一周的375人,该院集中了最多、最重的伤员。地震伤员是一类特殊的受灾群体,心理上的创伤较为严重。8·3地震伤员来自鲁甸贫困山区,文化程度低,多数为文盲,家庭年收入低,伤员和家属都缺乏现代医疗服务的经验和常识。灾难后调动医务工作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好医疗救治、心理援助等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陈竺,2012)。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自9·7地震”后,初步尝试把心理援助融入医疗救治中,全院医务人员对心理援助有着良好的意识。8·3地震后,云南省民政厅、昭通市民政局和卫生局合作,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了医务社会工作站(以下简称“社工站”),组建了一支跨专业的心理救援队伍,以医务社工为组织者和联络者,整合了院内和本地心理救援资源,对伤病员提供心理社会干预。探索灾后紧急救援期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以期推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时,为我国的灾害管理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灾后心理救援现状
灾难导致财产的毁损、打破人们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环境,挫伤乃至摧毁人们的安全感,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程度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损伤。重大灾难后30%-50%的幸存者将出现中度或重度的心理失调,心理危机干预和事后支持将帮助症状的缓解;灾难后一年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Mental Health Division of WHO,1992)(程奇,2009)。灾难引发的各种精神卫生问题,包括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抑郁与焦虑障碍、自杀等行为问题(Wickrama,2008),其中PTSD发生率最高、后果严重(王丽颖,2004)。
在我国灾难后的心理救援始于1996年新疆克拉玛依火灾(白渝,2002)。随后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灾难后对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外心理干预理论的介绍,但是本土化的心理援助的实践研究很少(钱铭怡,2005)。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国内首次开展了大规模的心理援助,心理救援的研究如雨后春,相关的心理干预的文章急增。“5.12”地震后奔赴灾区的心理援助队伍良莠不齐,“心理救援”在灾区颇受争议。2008年5月原卫生部发布了《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性原则》目的是指导各地科学、规范地开展四川汶川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我国各类灾难的频频发生,迫使心理援助工作深入开展,并在理论和实践研究有了较多积淀。目前国内关于灾难后的心理援助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心理援助组织体系、实施方法的本土文化思考;灾后不同群体的心理状况评估和干预方法;不同干预方法的效果研究;国外心理援助介绍和启示等(康岚,唐登华,2008)。
(二)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心理救援
灾难后,人们身体上的救治固然重要,但缓解和疏导灾害对人们心理损伤的程度不容忽视。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理事马洪路(2006:130)说:“只救命不救人的医疗是不完整的”。在国际上,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心理援助已经比较成熟,例如,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灾后社会工作介入心理危机的经验,并逐渐形成了救助体系(边慧敏,2013)。根据台湾9.21地震的启示,灾后社会工作可以按时间划分阶段完成心理重建(冯燕,2008)。我国学者王思斌和顾东辉等提出,社会工作在灾后心理救援中往往协助政府,承担着助手的角色;在灾后心理援助中,社会工作提供着危机心理干预、应激性心理障碍追踪治疗、社区心理重建等服务(王思斌,2008)。社会工作是“灾后心理援助的极佳途径和行之有效的策略与方法”(贾晓明,2009)。
“5.12”汶川地震后,在外力的作用下,社会工作蓬勃发展,并催生了不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Sim et al.,2013),然而,医务社会工作并没有在灾后紧急救援阶段介入,关于灾后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鲜见于文献。大量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表明,灾难导致的躯体外伤者有更严重的心理创伤(Haagsma JA,2011),但对躯体外伤患者的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仍然不够。灾难后,在医院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对住院伤员提供心理救援,促进伤员身心康复,应当属于灾后社会工作的重要范畴。
三、干预理论介绍
近年来,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危机干预越来越受到重视,它是重大灾难事件后的危机干预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一)危机干预的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是由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提出,它把个体看作是与周围其他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系统。生态系统理论把环境分为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4个层次,强调各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刘杰、孟会敏,2009)。生态系统理论下的危机干预的是综合幸存者身上所有因素,并持有一种动态的、社会文化论及多元文化论的观点(康岚、唐登华,2008)。在进行危机干预时必须将整个生态系统的因素都加以考虑,不仅是当事人,而且包括与当事人相关的个体(赵映霞,2008)。生态系统理论下的危机干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满足危机干预工作的要求,系统应包含多种交叉学科合作(Gillilang B E,2011)。第二,为了解决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系统内必须包含多种理论,各学科的理论密切配合。第三,各种环境因素应全面的纳入考虑的范围,考察其对幸存者的影响(吕娜,2015)。
(二)灾后紧急救援——灾后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
本文采用的心理援助定义,指重大灾难后对幸存者所提供心理帮助的途径与方法,以应对因灾难引发的各种心理困扰、心理创伤,并逐步恢复正常心理状态的过程,这包括灾难初期的心理急救和长期的心理重建(贾晓明,2009)。
对灾后幸存者的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灾后早期重要的心理干预,为灾后幸存者提供社会心理支持,是克服痛苦和逆境的手段(Shultz,2014)。在灾害频发的21世纪,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得到广泛认可,是早期心理干预的首选的方法(Halpern J,2007),美国国立儿童创伤应激中心(NCCTS)和美国国立PTSD中心共同编制了的《心理急救》一书中,将心理急救(PFA)定义为:用来减轻灾难事件所带来的痛苦,并增强短期和长期的功能性适应能力的方法之一(WHO,2007)。PFA的操作过程有八个要素:(1)接触幸存者并承诺协助;(2)给幸存者提供安全感;(3)帮助幸存者稳定情绪;(4)识别需要关注或澄清的问题,给予可能的解释;(5)为幸存者提供实际的帮助;(6)帮助幸存者同家庭、朋友、社区等层面建立可利用资源的联系;(7)提供正确资信,以应对困境、减少适应不良和增强适应性能力;(8)帮助幸存者获得可利用的服务,并且甄别处理(WHO,2011)。灾难事件发生后,即刻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干预,干预的参与人员不仅包括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医师,社工、护士、学校教职人员等均可掌握与传播(Oflaz F,2008)。
由此可见,灾后紧急救援期心理急救是社会工作者的首先方法。简言之,社工可以采用心理急救的“三L”原则,遵循心理急救的八大操作步骤,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即“Look”:检查安全感、检查急需帮助的人、检查情绪不稳定的人;“Listen”:了解对方所需要、了解对方关心什么、安静地倾听对方的倾述。“Link”:保障基本需求、提供实际帮助、联络社会资源。
(三)灾后长程心理干预——心理社会干预(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缺乏持续的支持是许多灾难心理救援项目失败或不具推广性的原因。心理救援是个长期的、持久的过程,“蜻蜓点水”式的心理干预应该被禁止。当心理急救期过后,接下来的心理救援应采用心理社会干预的模式。这不仅满足灾后人们的心理需求,而且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疾病的康复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的康复。心理社会干预(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或称为心理社会处置(psychosocial treatment),是指综合各种心理和社会康复措施与手段,是康复精神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灾难后幸存者采用心理社会干预的效果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例如,美国9.11事件后,对幸存者采取以循证为本的社会心理干预,即公共心理健康计划,包括需求评估、开发筛选、监测和评价方案、灾后的抗逆力等,干预人员包括儿童、成人、家庭、救援人员等,该计划也提升对灾后国家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Watson P J,2011)。然而,何为好的灾后社会心理干预计划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鉴于此,Jonathan等人对来自25个国家的106名专家采用专家咨询法,完成以循证为本灾后社会心理指南的研究,研究发现:(1)不建议采用专业(正式)干预对每个个体进行介入,建议使用心理急救方法,反对基于个人的心理危机晤谈法;(2)不一定使用正式筛查,但它可以是帮助识别处于困境中的个体;(3)灾难后的健康教育非常重要,通过提供充分信息、解释灾难的后果和开展社区教育,并重点强调抗逆力和自然与人力资源;(4)强大的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和资源;(5)采用阶梯式的介入模式:对所有幸存者都采用心理或者药物治疗是不适当的,也不是所有幸存者都适于采用灾后的认知行为治疗(CBT),也可以采用快速眼动疗法(EMDR)和压力管理的等可替代的疗法(Bisson J I,2010)。
灾难中丧亲、伤亡的人们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生活上的重创更为突出。如果在灾后的三到六个月缺乏心理危机干预,则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将影响其数年,乃至终身。对集中在医院的伤病人,提供及时的社会心理干预,将有效地降低PTSD的发病率,降低治疗成本,恢复社会功能(IASC,2007)。
四、研究介入过程方法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范式。行动研究是指研究课题来源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实际工作即是研究的过程,以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社会行动为目的(古学斌,2013)。研究者通常就是实际工作者。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加深的发展过程,通常分为六个具体的研究步骤:预诊、收集资料初步研究、拟定总体计划、制定具体计划、行动和总结。
本文尝试通过对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医院”)的375名躯体外伤患者(其中175名患者住院超过1个月)进行社会工作行动介入,探索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后伤员心理干预的模式。根据行动研究的六个步骤,具体研究过程如下:
(一)预诊(发现问题)
8·3地震后第3日医务社工救援队进入医院,通过调查,进行初步的需求评估。首先,对伤员比较集中的创伤外科以及儿童病房的小朋友及家属进行了访谈。在此阶段有两个“发现”:一是伤员需要分层干预,家属是干预的重要资源;二是对医院心理救援资源进行评估,医院已有的“心理护士”小组、神经内科医生及当地的心理咨询师等人力资源可以与社工队伍进行整合。
(二)收集资料初步研究
对预诊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整合资源,成立了“医务社工站”,形成一支跨专业合作的队伍,这支队伍由社工、医护、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组成。“医务社工站”的成员从不同专业的视角提出心理救援的意见。
(三)拟定总体计划
“医务社工站”拟定总体服务计划,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心理救援团队进行危机干预培训和督导。二是全面、系统地对伤员进行心理追踪评估;三是从系统角度出发,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对伤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四)制定具体计划
行动研究法是动态的开放系统,总体计划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修正的过程。根据总体的服务计划,细化服务内容及评估的指标(详见表1).

表1 地震伤员的心理社会干预方案
(五)干预过程
本研究主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干预:
1.在微观个人层面的干预
第一,为病人建立“心理档案”,进行精神健康风险评估和监测。地震后1周,社工站为住院的伤员进行心理筛查,并且建立档案。将伤病人分类(A-B-C三类),分别采用不同介入措施:A类伤员(丧亲/伤残、伴有异常应激反应),采取“药物治疗、个案咨询”;B类伤员(社会支持水平较低、伤情稳定)采用“心理陪伴、病人小组、康乐活动”、C类伤员(伤情比较轻、社会支持良好)采用“病人小组、康乐活动”。
第二,形成“心理查房”、“碰头会”制度,为病人提供个性化服务。社工的每天“心理查房”写进病人的查房记录,便于医护人员了解伤员的情绪状态。“碰头会”制度,即心理危机干预队伍的人员和各科室的主管护师参与,会上通报需要重点关注的伤员及其介入方案。“碰头会”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危机预警的作用,尤其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三,电话追踪回访出院伤员,以评估其康复情况。“社工站”在灾后1个月、3个月对出院的、能联系上的110位、113位病人进行电话追踪回访。电话回访的目的在于:一是评估伤员的身心康复情况,以及出院伤员在社区里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二是通过反馈,为仍住院治疗的伤员提供资讯,了解社区可以利用的医疗等资源,增强其回归社区的适应能力,三是为社工站的社区探访做准备,筛查出需要进行社区探访的病人。
2.在中观(医院//社区)层面的干预
社会支持系统对心理疾病具有防治的功能,因此灾后心理社会干预重点在以资源为取向,搅动伤员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构建社会支持系统,提升抗逆力。
第一,促进家庭资源的有效利用。灾后的自救与互助是从家庭开始,灾难面前家庭的凝聚力增强,因此,对家庭成员的干预是重要的内容。社工站开展了“丧亲家属支持小组”、“儿童家长支持小组”。其目的在于:一是帮助家属舒缓压力,促进家属之间相互支持;二是讲解灾后心理应激的表现和处理方法,增强家属疏导伤员负性情绪能力;三是讲解护理知识(尤其是骨伤的儿童)和康复营养知识,改善家属护理的水平。
第二,构建病友互助支持系统。灾后互助和助人行为可促进病人的身心康复(沈文伟、陈会全,2015)。在“病房活动”中,社工挖掘“榜样人物”,让其带动大家分享故事、说笑话、唱山歌,这些故事和山歌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增进了病人间亲近感和凝聚力。在“少儿玩教中心”和“家庭资源中心”开展小组活动、康乐活动和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拓展病人的互助系统。“少儿玩教中心”,主要依托本地幼儿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开展幼儿绘画、手工、歌唱、说故事、舞蹈等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方式。表达性艺术治疗主要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达到增强沟通、心理宣泄和心理治疗的作用(汤晓霞,2011)。社工站开展“出院计划小组”,请驻扎灾区的社工组织,讲解伤员回归社区将面临的挑战,以及社区中可以获得的支持等;请康复师讲解自我康复知识;伤员们集思广益,共同讨论如何应对出院后遇到的生活及身体、心理上的挑战。
第三,改善医患关系,增强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支持。在医院伤病员往往会经历“蜜月期”到正常化的过程。所谓“蜜月期”就是伤员受万众瞩目,得到媒体、志愿者、爱心人士蜂拥而至的关爱。当“爱心”逐渐减少,医患矛盾逐渐显现,社工就必须充当矛盾的调解者,好比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伤员常因卫生知识的缺乏或对医生没有信任感而延误治疗或要求过度治疗。在灾后的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已认识到心理救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表示“我们很想宽慰病人,但不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该怎样做”。鉴于医护人员的需求,“社工站”开展了面向全体医护人员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将病人的心理疏导寓于日常的点滴医护工作中。
第四,积极调动本土的社会资源为病人提供支持。为了可持续发展,“社工站”积极动员本土的社会资源,组建由当地高校学生、咨询师组成了一支志愿者团队。在“社工站”的督导下,病人康乐活动的设计和开展由志愿者负责。康乐活动主要包括:茶话会、手工编制、生活安全常识讲坛、心理电影赏析等,每次活动内容都贴近病人的需求,符合当地的文化。除此之外,社工站连接当地的民间组织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助学、经济帮扶、法律援助等支持。
综上所述,中观层面的心理社会化干预可以用下图(详见图1)表示:

图1 中观层面的伤员心理社会干预网络图
3.在宏观层面的干预
8·3地震后,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工队伍进入灾区,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了灾后医务社工站。社工站以“合法”的地位极大程度地保证医院心理救援工作的顺利推进,对病人开始了规范、科学、有序的服务。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社工站”的服务得到了病人和医护人员的赞赏,缓解了医患矛盾。医院对社工站的态度从配合到信任再到大力发展。目前,该医院意识到医务社工纳入诊疗过程是“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医务社工站从灾后应急服务,转变到医院的常规工作,成为医院的一个部门。这是云南省第一个医务社工站,也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灾后医务社工站。
通过上述,微、中、宏观干预的介绍,我们试图采用系统的、清晰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服务,但事实上,这三个层次的干预是相互渗透、融合和互动的。
(六)总结
对灾后伤员的心理救援是在行动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在实际过程中不断地解决问题、修正计划,保证研究的规范性和可行性,研究结果证明了研究的有效性。
1.灾后 11周内的评估
灾后1周对住院伤员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自然灾害受灾民众严重症状评定表》(沈文伟、崔珂,2015),该工具适用于灾害或紧急情况下,幸存者的精神健康问题评估,目的在于识别优先需要精神健康护理的人群。该工具适用于18岁以上的人群,调查内容共6个问题,其中3个或3个以上问题选择“总是”或“大多数时间”或“有时”即标记为阳性。被标记为阳性的灾民应优先考虑给与精神健康护理或介入。
住院伤员375名,其中340名为满18岁,对其进行调查,有115人调查结果为阳性,即阳性检出率为34%(115/340),即在周后一周发现,34%的伤员优先需要精神健康护理。
2.灾后 11个月和 33个月的评估
灾后1个月对174名住院伤员进行调查;灾后3个月在对住院伤员及返回社区的共162名伤员进行追踪评估,脱落12人,脱落率为6.85%(12/175)。调查内容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自评量表(PCLC)。PCL-C量表由17项条目组成。每题为5级评分(1分代表从来没有,5分是几乎总是),总分范围为17-85分,筛查的阳性界值为分数50分,即总分大于或等于50分,就很有可能被诊断为PTSD阳性症状(刘瑛,陈宝困,2015)。

表2 灾后1个月、3个月PTSD的筛查情况
本研究发现,灾后1个月、3个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检出率分别为22.86%和13.58%,说明随着时间推移,经过干预,伤员的PTSD检出率在下降。
从三次追踪研究的结果发现,伤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在好转,PTSD的检出率在降低,并低于国内相关研究的PTSD发生率(详见下文),可见干预效果是显著的。
五、研究发现
(一)从系统生态观出发,在医院开展伤员的心理社会干预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是在生态系统理论下的心理救援的行动研究。灾难事件改变了人们的整个生态结构,因此,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的三个层次的干预,并强调“跨学科、以本土文化为本”的理念,遵循系统生态理论的危机干预原则,因地制宜地开展“跨学科合作、尊重本土文化和挖掘本土资源”的社会心理干预。
医院提供了伤员心理社会干预的天然条件,保证了研究的可行性。通常伤员入院时间为15天到1个月,保证了危机干预的介入时间;第二,医院注重“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把伤员的心理救援纳入救治范围;第三,家属陪伴伤员为干预提供了家庭资源保障;第四,医院也为“跨专业”多学科合作提供了可能。8·3灾后,医院涌入了大量的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在社工站和医院护理部的通力合作下,快速筛选出一支由医护人员、社工、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组成的干预队伍。“社工站”运用个案管理方法,充当个案管理的评估者、倡导者、协调者以及资源的链接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团队里的各专业优势,从而保证“跨专业”合作落在实处,提高心理救援的效率。
研究结果显示了心理社会干预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灾后1个月、3个月的PTSD检出率分别为22.86%和13.58%,PTSD发生率显著低于同类研究。国外相关研究报道,灾难后6个月躯体外伤的患者(因交通或其他事故、暴力恐怖袭击)PTSD发生率为25.5%(Shalev,1996)。国内相关研究报道,汶川地震后1个月躯体外伤患者的PTSD发生率为分别为39.15%(高雪屏,罗兴伟,2009)。研究结果显示,对躯体外伤的心理伤害干预降低了PTSD的发生率。因为本研究是在灾难后紧急救援的实际情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研究的关键,在干预效果的评估上未设置空白对照组(即对该组成员不进行心理救援),因此,在研究结论上需要谨慎,研究结果显示了心理社会干预在心理救援中起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以“本土文化为取向、挖掘本地资源为重点”的心理社会干预
在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中,心理救援一定要考虑文化的适应性。心理康复模式应具有文化适应性,即借助于文化对灾民本身具有的表达功能、交流功能、认知信念、行为习俗的共同方面,发展出符合灾民需求和文化、可接受性的心理干预方式,使灾民的个人体验、态度和情感得到充分的宣泄和表达(李娜、谢玲、徐佳军、杨彦春,2010)。鲁甸是回族聚居、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等因素使得灾后心理援助面临特殊的情况,常规的心理干预方法并非适用。因此,尝试寻找信仰中积极的教意、宗教行为中具有治疗意义的仪式。例如,我们在社工站的家庭资源中心,专门设置了礼拜堂,鼓励能走动的病人去礼拜,支持病人参与宗教活动;谨慎处理民族风俗习惯、地方风俗与心理咨询冲突的地方等;维护灾后人们本土文化生活和宗教活动的正常化,这些都是对本土化的心理干预。同时,挖掘和利用“本土”专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偏远、文化水平偏低的人们心目中,“空降”专家,没有太多的专家效应,相反“本土”专家和受灾群众有共同的语境,他们在接受心理危机干预知识和技能后的培训后,结合自身的优势,开展服务,效果理想。
本土文化取向的社会心理干预尤其重视家庭层面的干预。在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家庭会变得异乎寻常的紧密,用家庭保存下来的资源(物质的、经济的、情感的、行为方面的)立即对家庭成员进行救护(李静、杨彦春,2012:33)。这也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纽带,以“血缘”为本的文化结构。这些都是家庭抗逆力的宝贵资源。尤其在自然条件越恶劣的农村地区,家、家族的观念更强,多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长者在家庭中具有权威地位。8·3受灾地区,有的山坡上住着就是一个大家族的人,或者三、五家人就是一个寨子。天然形成这些家庭之间、家族中的人相互支持,以保证生存和繁衍。在他们的观念里的家庭就是扩大家庭,叔伯兄弟组成的家庭。如果在做家庭辅导过程中,沿用西方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家庭治疗的理论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在中国“家本位”的文化背景下,讨论家庭抗逆力是最有必要的和最有效的。服务过程中,我们在家庭层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家庭辅导、家属互助小组、家长小组、家庭安全知识小讲堂等,其目标在于“借力”家庭的资源,让家庭自助,提升家庭的抗逆力。在服务中,伤员的家庭总给我们“绝处逢生”的惊奇。真正理解到,家庭蕴含的力量非常强大(Walsh,2013:101)。
(三)对于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健康教育是灾后心理社会干预的重要方法
服务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两个现象:第一,医生反映同样伤情,地震伤员康复情况比非地震伤员差很多,究其原因是伤员主动康复训练和自我护理的意识差;第二,对现代医疗技术认同度低,信赖传统医学(中医),具体表现在,部分伤员使用康复辅具随意性大,甚至任意抛弃辅具,在院外寻求民间“名医”治疗,有的理念有悖于医院的规范治疗。
鉴于以上情况,“社工站”邀请医院康复科和中医科医生,进行健康教育,灌输现代科学的医学常识,增强伤员疾病管理、自我护理、康复训练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同时,社工在病人的康乐活动中,监督和敦促病人每天主动康复训练,让病人真正理解到“疾病的护理靠自己,而不是靠医院”,把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
社工站利用“两个中心”为患者提供健康促进的活动,具体开展内容:① 疾病知识教育:讲解相关损伤与疾病以及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②康复训练教育:讲解康复的自我管理方法、患处的护理、生活护理、康复操等;③开展“出院准备”小组,即请驻扎灾区的其他社工组织,讲解伤员回归社区将面临的挑战,以及社区中可以获得支持等。④康乐活动,社工带领伤员进行棋牌、手工、影评等康乐活动。现有研究证明,健康教育与心理教育在灾难创伤中的作用是被认可的(Oflaz F,2008)。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健康教育是帮助伤员康复的重要方法。只有转变的伤员的疾病观念,伤情康复预后才可以期待,同时,健康教育能明显改善医患关系,增强病人对治疗的配合程度。
六、结论与讨论
(一)灾后心理援助的新视角——灾后社会工作
5·12汶川地震后,大量的心理工作者涌入灾区开展心理救援,由于心理工作者水平良莠不齐、专业方法不一等的限制,导致在灾区流传着“防火、防盗、防心理辅导”的流言,一度让心理救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8·3鲁甸地震,国家民政部首次把社会工作纳入救灾体系中,社工以“合法“认可的方式进入灾区,展开系统的服务,服务能力得到了灾区民众的肯定。医务社工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医院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以及患者、家属的充分肯定。我们从实践工作中得出结论:社会工作为灾后心理救援提出新的工作理念与方法。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开展的灾后心理救援具有适用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社会工作以“常态化”的视角看待受灾群众灾后心理反应。主流的心理援助者是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精神科医生。然而,这样的专业身份使其服务对象很容易被贴上精神病患者的标签,引起灾区群众的排斥(贾晓明,2009)。现有研究表明,灾后心理治疗的目标人群并非全体受灾群众。“常态化”视角,强调并非经历了重大灾难创伤之后一定会有心理问题,需要心理的介入。社工“常态化”的介入也可以减少对灾区群众的负面心理暗示。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更强调平等、人道主义和改善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理想追求。社工专业价值决定了专业的角色的“平等”和“多元化”,容易被灾区群众接纳。社工是协同者的角色,强调心理救援中的陪伴功能。社工常不以“专家”、“教育者”和“权威”的身份出现,强调“仆人”精神,拉近了与受灾群众的距离。在服务过程中,社工灵活运用各种角色,如协调者、资源整合者、倡导者、个案管理者等,在灾后无序的状态下,社工充当资源整合者,利用的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同时,在群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必要时,运用倡导策略,推动相关社会政策的完善。
第三,社会工作方法强调行动和资源的整合,解决实际困难,具体工作方法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社会工作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灾难现场提供人员的安置、物资的发放、伤亡抚恤、协助殡葬处理、伤者的照顾、哀伤辅导等等,例如,医务社工在医院,帮助无家属陪伴的病人洗头、照顾病人,陪伤员检查等。总之,社工在遵从专业理论规范的前提下,通常首先满足群众急需的生理、生存需求,协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这样“接地气”的灾后救援,群众乐于接受,感受到的是平等和支持。
第四,社会工作方法取向的心理救援往往是在“无为”状态下的有所为。心理咨询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原则(张日晟,1999),并不适于灾难后的情景。社会工作对于受灾群体应该是“来者不拒,去者要追”,主动关注,并提供适时,适宜的援助非常重要。常用的心理援助方法,如心理辅导/咨询/治疗、危机干预、团体辅导等,常被规范在心理层面开展工作,似乎心理援助并不关注灾后人们的实际生理和心理需求,导致灾区群众对心理援助的疏离和不信任。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心理援助以解决幸存者的实际困难为出发点。只有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才有可能采用具体的心理治疗理论以及助人技巧进行介入。社工的心理救援行动,从一开始的陪群众聊天、做农活、打麻将、跳广场舞,到哀伤辅导、心理咨询、小组工作等,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显山不露水的过程,只有采用这样的方法,灾区群众才易接纳和配合。
心理援助应被视为所有心理帮助的途径与方法,这样的心理援助概念为心理救援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讨论空间,跳出了心理咨询/治疗、心理危机干预的“制式化”、“正规化”的语境,从多元的视角去看灾后心理救援(林耀盛,2005)。而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二)政社合作保障灾后社会工作救援的力度
8·3后医务社工进入医院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行政”的色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当地卫生、民政系统的支持,医务社工才得以在医院开展跨专业的服务,并且社工站的工作也被纳入医院伤病员救治的一个环节。然而,这是个双刃剑,也给我们的工作带了不利的一面,医生和患者都认为,“你们是政府派来解决问题的人”,在服务过程中,某些涉及医院和患者的实际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社工只有倡导的权利和义务,而医院和患者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医院和患者的很多实际问题是需要政府部门之间协商,要有相应政策出台,比如,灾后紧急救援期三个月的医疗救治是减免的,但三个月后医疗费怎么办?对于骨折患者一年后拆除“内固定”的费用谁来出?免费救治范围只是地震伤,但是疾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很难对“某个症状”确定是否是地震导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灾后医疗、心理救助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监督之下进行。虽然政府已颁布了许多政策性文件和许多法律法规,但是关于灾后医疗救助、心理重建这部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仍体现不够(边慧敏,2011)。从5·12灾后的经验来看,灾后社会工作应在“政府为主、社工协助、群众参与、义工服务”的灾害救助格局下,社工只有与政府、企业以及灾区人民等的协调配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边慧敏,2011)。8·3鲁甸灾后,国家民政部首次正式把社工、社会组织纳入救灾体系中,这样的政社合作形式,保障和提升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张高陵,2014)。
8·3鲁甸灾后救援是政社合作形式的一大突破,民政部派出的五支队伍和云南本地队伍,在云南省民政厅社工处的指导下,搭建了“8.03”鲁甸社会工作公共平台。公共平台的搭建,使得几支社工队伍共享资源、互换信息,避免了有的地方资源匮乏或过度集中,更重要的是,平台加强了政府部门和社工组织的对话,把政社合作,落实到实处。医务社工是救援队伍中相对特殊的队伍,服务集中在医院,通过公共平台,医务社工向伤员传递灾区的情况,提供返回灾区后可以获得的资源信息;出院的伤员,如果需要跟进的,医务社工转介给社区的社工组织。
总之,8·3地震后,中国首次尝试医务社工介入灾后伤员的心理救援,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模式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地推动与执行,得益于国家民政部、云南省民政厅、昭通市卫生局以及当地医院管理者在政策上、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得益于香港择善基金会、思健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该干预方案虽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为开展灾后社会心理干预提供了参考。
[1] 白渝,2002,《浅谈灾后心理创伤的安抚问题》,《防灾博览》第5期。
[2] 边慧敏、林胜冰、邓湘树,2011,《灾害社会工作: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情况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3]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2013,《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4] 陈竺、沈骥、康均行,2012,《特大地震应急医学救援:来自汶川的经验》,《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第4期。
[5] 程奇,2009,《国外灾难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综述》,《福建医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6] 冯燕,2003,《九二一灾后儿童生活照顾状况报告书》,台北: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
[7] 高雪屏、罗兴伟,2009,《汶川地震后1月内脱离/未脱离震区的亲历者PTSD筛查阳性的发生及心理影响因素》,《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第6期。
[8] 古学斌,2013,《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0期。
[9] 贾晓明,2009,《地震灾后心理援助的新视角》,《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7期。
[10] 康岚、唐登华,2008,《地震灾后心理重建》,《中国护理管理》第10期。
[11] 李静、杨彦春,2012,《本土化心理干预指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12] 李娜、谢玲、徐佳军、杨彦春,2010,《文化脑、认知与灾后康复》,《上海精神医学》第88期。
[13] 林耀盛,2005,《说是一物即不中:从伦理性转向痊愈观点.反思灾后存活者的悲悼历程》,《本土心理学研究》第23期。
[14] 刘杰、孟会敏,2009,《关于布朗分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中国健康心理志》第2期。
[15] 刘瑛、陈宝困,2015,《创伤后应激障碍评估量表综述》,《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第1期。
[16] 吕娜,2015,《生态系统视域下灾难危机干预的“团体”解析》,《青少年学刊》第2期。
[17] 马洪路,2006,《医务社会工作个案研究》,王思斌,《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3-2004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130。
[18] 钱铭怡,2005,《国内外重大灾难心理干预之比较》,《心理与健康》第4期。
[19] 任嘉威、王维悦,2016,《方法与模式: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心理援助探究》,《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版)第16期。
[20] 沈文伟、崔珂,2014,《灾后社会心理需求评估工具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 汤晓霞,2011,《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浅议及运用》,《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2期。
[22] 王丽颖、杨蕴萍,2004,《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进展(一)》,《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第1期。
[23] 王思斌,2008,《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社会工作》第21期。
[24] 张日晟,1999,《咨询心理学》(第一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5]赵映霞,2008,《心理危机与危机干预理论概述》,《安徽文学:评论研究》第3期。
[26] B.E.Gillilang,B.K.James.2011,《危机干预概述》,《心理咨询师》第6期。
[27] Bisson J I,Tavakoly B,Witteveen A B,et al.2010,TENTS guidelines:development of post-disaster psychosocial care guidelines through a Delphi process.[J].Br J Psychiatry,196(1):69-74.
[28] Froma Walsh,2013,《家庭抗逆力》,朱眉华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9] Haagsma JA,Polinder S,Toet H,et al.2011,Beyond the neglect of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creases the non-fatal burden of injury by more than 50%.Injury prevention: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Injury Prevention,17(1):21-26.
[30] Halpern J,Tramontim M.2007,Disastermental health:theory and practice.Belmont:CA:Thomson Brooks Cole,:35.
[31]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2007).IASC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Geneva:IASC.
[32] Oflaz F,Hatipoglu S,Aydin H.2008,Effectiveness of psychoeducation interventiono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coping styles of earthquake survivors.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17(5):677-687.
[33] Shalev A Y,Peri T,Canetti L,et al.1996,Predictors of PTSD in injured trauma survivors:a prospective study.[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53(2):219-225.
[34] Shultz,J.M.and D.Forbes,2014,Psychological First Aid:Rapid prolife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evidence.Disaster Health,2(1):3-12.
[35] Sim,T.,Yuen,W.K.A.,Chen,H.Q.,Qi,H.D.(2013).Rising to the occasion:China disaster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56(4),544-562.
[36] Watson P J,Brymer M J,Bonanno G A.2011,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ince 9/11.American Psychologist,66(6):482-94.
[37] Wickrama,K.A.and K.A.Wickrama,2008.Family context of mental health risk in Tsunami affected mothers:findings from a pilot study in Sri Lanka.Soc Sci Med,66(4):994-1007.
——医务工作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