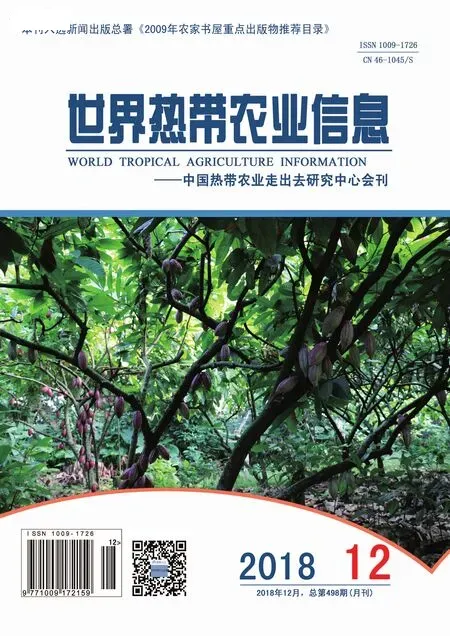命名·功能·历史
——海南油茶产业文化初探①
曹转莹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南海口570100)
克鲁伯成书于1944年《文化的成长形貌》 将整个文化系统可划分为2部分, 即基本形貌和次级形貌。基本形貌指的是与生存、 生计有关的文化事物; 次级形貌则是与创造力、 艺术活动有关的文化渐动, 如克鲁伯成书于1944年《文化的成长形貌》 将整个文化系统可划分为2部分, 即基本形貌和次级形貌。 基本形貌指的是与生存、 生计有关的文化事物; 次级形貌则是与创造力、 艺术活动有关的文化渐动, 如语言、艺术文学和音乐等。 他认为, 在任何文化系统中, 只有当生存问题解决后, 才有可能出现次级形貌的繁荣。 基本形貌必须对现实、 次级形貌则面对价值[1]。 按照如此定义, 海南油茶文化的选题属于文化的基本形貌。 海南油茶作为一种从种植到使用经历了500多年的产物, 它以一种有形的文化事物寄托着海南当地的民俗文化、 木料作物的种植变迁文化。
古典诗词对于茶油树的书写多关注在油茶花即“山茶花”, 并没有对茶油果实压榨茶油的描写。 一方面这与古典诗词的描写对象本身的选择有关, 另一方面也说明油茶在很长历史时期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食用油。 此外, 对于油茶树的真正命名确认也存在与茶叶树的交叉而出现古籍记载的混淆。 “山茶叶似茶树, 高者丈余, 花大盈寸, 色如绯, 十二月开。” (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丽紫妖红, 争春而取宠, 然后知白山茶之韵胜也。” (北宋黄庭坚《白山茶赋》) “黄山茶、 白山茶、 红白茶、 红白茶梅, 皆九月开。 山茶花大而韵, 亦茶中之贵品” (明代王世懋《闽部疏·花疏》) 都是对油茶花朵的形状和颜色的3种种质资源的文学记载。
1 海南油茶的命名渊源
福柯在著作《词与物》 中, 揭示他的研究主题就是人文科学中事物的秩序在词语中的再现。 如果它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话, 那它就是关于“再现” 本身[2]。 福科试图通过否定所有历史描述与解释的传统范畴, 从而找到历史意识本身的“临界点”[3]。 知识考古学理论的创始人福柯这种“再现” 在文化研究中表现为对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 命名的演变的秩序与历史。 而关于油茶的根源、 海南油茶的命名都是这种概念本身的考证。 有学者已经对中国油茶的起源的探究作出了知识谱系的古籍的辨析, 但是一些尚未盖棺论定的结论仍旧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循环往复既已存在的争议。 海南山柚油的命名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约定成俗的叫法, 而这个油茶的概念显然不同于内地的多种事物混合而成的类似主食的食物。从植物学的分类看:油茶, 山茶科(Theaceae) 山茶属(Camellia) 植物中油脂含量较高且具有栽培经济价值的一类植物的总称[4]。 又名茶子树、 油茶树, 在海南被称为山柚茶, 与橄榄、 油棕、 椰子并称为世界4大木本油料植物[5]。 早在先秦年间的书籍《山海经·东山经》 中有“东二百里曰太山, 上多金玉祯木”。多数研究油茶文化的学者以此作为中国油茶存在的最早证明, 认为中国油茶已有2 300多年历史。 但是正如杨抑关于中国油茶起源的探究所言, 关于“贞木” 或者“祯木” 是否是茶油树的名字记载尚不足以证明, 甚至存在很多疑问, 这就足以说明, 《山海经·东山经》 无法成为中国油茶的最早证明。
江西宜春是当前中国重要的油茶产地, 宜春学院杨抑老师在文章《中国油茶起源初探》 中对于油茶在古籍中的考证得出, 油茶真正作为油料作物栽种应该始于明代。 明初俞宗本的《种树书》 中写到“九月移山茶” “十月收茶子”。 明末成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 对油茶籽榨油和使用的记载充分说明油茶在南方省份的普遍使用。 《农政全书》 中写到“植木生闽广、 江右山谷间, 橡栗之属也……实如橡斗, 斗中函子, 或一二(颗)、 或三四(颗), 甚似栗而壳甚薄。 壳中仁皮色如榧, 瓤肉亦如栗, 味甚苦, 而多膏油, 江右、 闽广人用此油, 燃灯甚明, 胜于诸油, 亦可食。” 而“植” 的特征描述完全可以确认就是现在的油茶树, 书中记载两广、 福建、 江西等省广泛采用油茶榨油。
清代农学家张宗法《三农纪》 中, 称油茶为“南方油实也”。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 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书中以“搽子” 命名“油茶籽” 把油茶排在芝麻、 萝卜子、 黄豆、 白菜子、 苏麻、 油菜子之后, 排名植物油料第7位。 杨抑认为, 宋应星为了避开茶叶树作为油料的茶叶籽, 称油茶为“搽子”。 至今湖南、 江西一带人们依然称油茶为“茶子树”。
就海南而言, 在明代唐胄编撰的《琼台志》 中记载:“山柚, 文昌多。 花白, 即闽中茶油。” 海南将越南油茶品种称海南山柚, 源于《正德琼台志》 中的记载距今已经500多年。 据此推断, 海南油茶的种植历史至少在500年前。 当时正值明朝年间, 明太祖朱元璋称海南为“南溟奇甸”, 开启了海南岛与内陆互通发展的序幕。 在政府引导扶持下, 福建、 两广大量移民海南岛, 海南进入大发展时代, 移民大致在这个阶段将内陆先进农林生产技术和物种传入此地, 油茶由此从大陆地区传入海岛。 最终, 由于热带地区海岛气候与土壤的滋润, 形成独具特色的神奇油料作物海南山柚油。 海南大学副校长胡新文率领团队,专门从事海南油茶产业的研究, 编制了《海南省油茶产业调查报告》、 《海南省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等重要文件。 海南省屯昌县新兴镇有“山柚园村”, 从屯昌县以乡榕仔村、 枫木镇大葵村等植物命名的习惯,可以见出山柚油茶树种植的普遍性和渊源深远。
2 “万能油” 的功能文化
哈里斯认为马克思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 辩证唯物史观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在文化研究上便是物质文化的双重现场性。 油茶的命名、 种植、 更重要的是使用最能反映出海南油茶文化的变迁。 他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所断定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普通结构……依赖于思想与行为的区别及主位与客位的区别”[7]主客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林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建构都是人对物的实际使用与长期积习而成的稳定形态。 因此, 油茶文化中关于油茶的功效本身就存在各式各样的传说, 而海南人民对油茶使用和言说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被挖掘。
油茶树由于挂果周期长, 果实产量低, 而茶油又营养成分高、 用途广泛, 因此是珍贵“东方橄榄油”, 深受汉族同胞喜爱, 而且还传到了黎族地区。 清代《崖州志》 中舆地志三, 木类中就有黎族百姓种茶树、 收果、 榨油的记载:“山油, 黎人每种, 取其子打油, 香气袭人。 又名木油。”[8]《农政全书》 中关于油茶功能记载: “植在南中为利甚广” , “茶油能疗一切疮疥,涂数次即愈。 其性寒。 能退湿热,用造印色,生者亦不沁。 或云, 以泽首, 尤胜诸膏油, 不染衣, 不腻发……” 所言与海南民间所流传的具有蚊虫叮咬后消肿、 止痒、 润肠、 促进刀伤、 烫伤、 撞伤等伤口消炎和愈合的药用功能以及除皱、 护发、 乌发、 护肤、 防晒等美容功能完全对应。 尤其是对于药物敏感的婴幼儿, 山柚油的“万能” 功能被充分肯定, 屡试不爽。 同时, 山柚油作为高品质的食用油, 加入姜末和盐巴调制的蘸料, 搭配海南当地白切鸡等偏原生态的清淡饮食已经成为一种饮食文化, 作为“月子油” 可促进产妇身体恢复、 增加乳汁分泌,促进婴儿食欲和成长。
海南独特的地理维度造就的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具有海南特色的油茶种质资源, 产出了品质优良的山柚油。 海南油茶所产油茶茶籽油的独特性在于不仅没有苦味且有特殊香味道, 品质高于大陆茶油, 是中国茶油品质中的“王中之王” 产品, 市场价普遍高于普通油茶茶籽油3倍。 吴友根从物种、产地环境、 茶油风味成分3方面的差异来分析海南油茶不同于大陆的原因。 大陆多种植普通油茶, 而海南土壤富硒且山柚多是特异地理小种。 此外, 海南山柚香气主要成分为吡嗪类杂环化合物, 而大陆则是醛类、 酸类。 “岭南火, 太阳之精液所发。 其草木多香。 有力者皆降皆而香木得太阳烈气之全, 校、 干、根、 株, 皆能自为一香”, 故语日:“海南多阳, 一木五香。” 海南以万安黎母东峒香为胜。 其地居京岛正东, 得朝阳之气又早[8]。 从海南沉香独特芳香生成的自然气候条件可以见出海南山柚油茶树在同样的气候资源环境下也出现同类芳香气味的微妙和谐。
由油茶的神奇功效所引发的传奇故事很多, 其中关于慈禧太后、 宋美龄2位历史上的爱美人物传说都有在使用茶花籽油护肤。 汉高祖刘邦因在武陟受伤后使用了茶花籽油而痊愈, 特赐予其“宫廷御膳” 的称号, 更有雍正皇帝对怀庆油茶的赞扬“怀庆油茶润如酥, 山珍海味难媲美”。 茶油的特殊功效以物质形态的载体进行着文化的传承。 虽然海南油茶的种植与使用与中国油茶的有准确种植、 使用的记载时期同步, 但是关于油茶的使用的传说却缺乏挖掘。
3 油茶种植的历史文化
据1990年《海南省志》 记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油茶在海南分布范围很广, 在屯昌县、 澄迈县、 文昌县、 琼山县、 临高县、 儋县、 定安县和琼中县均有栽培。 其中以屯昌县的乌坡、 南吕、 新兴、 大同,澄迈县的中兴、 仁兴、 加乐、 石浮, 文昌县蓬莱, 琼山县甲子栽培较多。 至20世纪90年代末, 由于当时油茶的产量低, 经济效益差, 在海南岛分布的油茶普遍被砍伐种植橡胶和槟榔等经济作物。 海南大学教授吴友根说:“皇桐镇是个好例子, 大致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后海南油茶种植主要经历的3个阶段, 从波峰到波谷, 又重新兴盛。” “目前, 我省处于丰产期的油茶多为1950~1970年代引进种植的。” 早在1960年代, 皇桐镇就种植了不少油茶树, 多生长在田边路边, 本地村民也有用果实榨油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由于油茶价格上不去, 很多树被砍。 2010年前后, 该镇只有零星种植的油茶树[9]。 当前海南油茶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根据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 海南不是中国的油茶主产区, 而海南油茶资源的独特价值也常常被国内学者所忽视。 油茶是海南的传统植物, 海南有野生油茶原生种分布, 油茶资源丰富, 栽培历史悠久。 油茶树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秋、 冬、 春、 夏、 秋5个季节, 花期长, 从10月到翌年1月, 花果并存同枝共茂, 民间有“抱子怀胎” 的说法。
海南油茶包括野生资源与栽培种, 经省农科院郑道君等人对遍布9个市县38个乡镇的34个油茶林、 农场的总面积约1 167.3 hm2油茶资源实地调查。 根据各地油茶的形态特征, 经初步鉴定, 海南油茶资源为越南油茶(C.vietnamensis)、 普通油茶(Camellia oleifera) 和小果油茶(C.meiocarpa), 其中栽培最为广泛的是普通油茶。 定安、 澄迈、 屯昌和琼海的部分地区保存有林龄较长的油茶林, 其中澄迈县现有老的油茶林或油茶树最多, 最大植株地径达150 cm。 澄迈年代较长远的油茶林有约106.6 hm2。 油茶在海南主要分布在琼海的石壁、 中原、 阳江、 会山、 龙江和大路、 东红农场, 定安的岭口、 中瑞农场、 翰林和龙湖,文昌的锦山、 潭牛和蓬莱, 海口的三江、 甲子、 石山和永兴, 临高的皇桐、 和舍、 南宝和多文, 澄迈的文儒、 加乐、 中兴和仁兴, 屯昌的黄岭、 坡心、 新兴和乌坡, 琼中的湾岭、 长征和黎母山镇, 五指山的通什、 南圣、 畅好和水满。 其中, 定安、 澄迈、 屯昌和琼海的个别地方保存有林龄或树龄较长的林分或植株, 而成片面积最大的老油茶林在澄迈文儒镇岸岭村。 海南油茶最大地径植株在澄迈的中兴镇, 达150 cm, 而成片面积最大的老油茶林在澄迈县文儒镇岸岭村。 如琼海会山镇中酒村的路边, 据当地政府考究,其树龄有300a以上, 地径为89 cm; 屯晶黄岭镇石银岭村路边的油茶林, 最大地径为68 cm; 澄迈石浮槟榔根油茶林最大地径为80 cm; 文儒岸岭村后坡油茶林最大地径为75 cm[10]。 在对全省油茶种质资源调查中发现全省有5株油茶王, 其中琼海会山有3株树龄不低于300年的油茶树王, 定安龙湖和琼海阳江等地有上百年的油茶古树。 琼海市会山镇中酒村有棵树龄传说达590多年的“山柚树王”。 山柚果据茶树主人陈家辉介绍, 这棵老树果大、 籽多, 油质优良。 油茶王结的果大如拳头, 最多能有12个籽粒。 对于古老油茶树的保护与“故事” 讲述也是海南油茶文化载体的保护与代言。
4 海南油茶文化的隐没
据《中国植物志》 记载, 海南岛800m以上原始森林中有普通油茶原生种[11]。 《海南植物志》[12]、《海南岛作物(植物) 种质资源考察文集》[13]和《海南及广东沿海岛屿植物名录》[14]均记载, 海南岛分布有普通油茶野生资源。 根据专业书籍、 植物标本记载, 以及野生资源调查结果, 油茶是海南岛的传统植物资源, 其种植历史至少可推至明代。 近年的科研结果表明, 海南山柚的叶、 花、 果等形态方面存在丰富的变异, 且结果性能好。 海南是越南油茶种植的适宜区之结果期和盛产期分别比国内其他产区提早1~2年[15]。 2015年海南省油茶加工厂(含小作坊) 82家, 其中,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的企业有10余家, 主要分布在琼海、 琼中、 澄迈3个市县。 每年11月下旬开始加工生产, 至春节结束。 主要注册商标有“量子牌”“百寿山”、 “侯臣”、 “健源”、 “白石岭”、 “琼中”、 “文奥”、 “野生山柚油”、 “北仍山” 等10个品牌山柚油[10]。 对于海南油茶的品牌建设重视不足, 产品多用于内销。
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由中国经济林协会评定、 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油茶之乡” 包括有湖南常宁、邵阳县, 湖北麻城市、 兴远县, 江西丰城市、 上饶市, 广东兴宁市、 平远县、 连南县, 福建省福安市、浦城县,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等。 这些油茶之乡也常借助举办油茶文化节的方式向外推广当地的油茶文化, 而海南目前尚未举办过油茶文化节等活动, 同时对于油茶的研究多停留在“技术” 层面, 缺乏“软装”。 目前仅有周亚东等少量研究者站在文化的角度上来为海南油茶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 为当前的海南油茶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严峻要求。 2018年海南省林业局颁布《海南省油茶发展规划(2017~2025)》 的文件, 明确提出要加大油茶产业的文化建设, 解决好当前受制于海南油茶发展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宣传不到位、 产业化水平低, 海南山柚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岛屿内部民众的“独乐” 产物, 不能走出海南成为“众乐” 的宝物的问题。 虽然海南油茶不是中国主要的油茶产地, 但是在绿生态发展的大环境下, 油茶产业前景发展良好, 同时海南油茶又占据着特有的区位优势, 因此要从长远的油茶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油茶文化的研究和产业文化的构建, 避免油茶产业发展的局限, 实现林业、 农业、 旅游、 文化等不同领域共谋共赢发展的生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