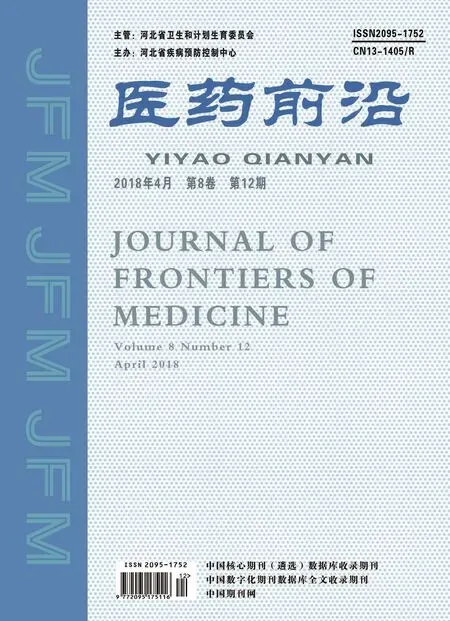中国与欧美GCP比较和思考
王少妍 李慧丽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上海201210)
引言
任何药品在上市前都必须经过临床试验,由于这是药物第一次用于人体,是否会造成损害、有多大损害不得而知,因此,大多数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临床试验,保证试验的顺利进行,保护受试者的权益。
中国的临床试验起步较晚,其质量管理规范是以世界卫生组织和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为蓝本,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拟定。和欧美GCP比较,中国GCP在临床研究批准、试验基地、IRB/EC设置、职责和组成要求、申办者职责、研究者资质、监察员要求、研究者手册和试验资料保存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本文结合最近影响较大的几个案例对中国与欧美GCP的比较进行几点思考。
1.中国和欧美GCP审批制度不同
国外的临床试验是“宽进严出”,侧重于研究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美国对临床试验申请实行较为宽松的备案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新药试验申请日起30天内,申办者如未收到FDA任何有异议通知,即可自行开始新药试验,但中间质量监督、安全性报控及最后准不准许生产的审批将会非常苛刻和严格。由于国外的临床研究已经进行了许多年,有比较完备的规范和成熟的经验,各大制药公司与监管部门有非常良好的互动,往往是一个新药从研发开始就已经在监管部门有了备案。同时,美国FDA有四条特别审批通道,即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批准和突破性药物通道。相对于普通药物而言,进入特别审批通道的药物批准速度明显加快,上市周期明显缩短,制药公司可以尽快从中获得利润,患者也可以尽快从新药中获益。
而中国的临床试验管理倾向于“严进宽出”,注重加强临床研究的批准权和管理权的集中控制,即批准研究在制度上要求较高,很看重允不允许做,谁有资格做临床研究,什么时间内能做。采用“先审批,后试验”。
中国采用的这种审批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低水平重复、投机性的临床试验。但是,由于审批流程涉及多个国家部门,加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专家人数不够,某些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审批时间比美国长得多。按照国家规定,无论国产创新药物还是进口药品,都必须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后方可上市,而审批过程的拖沓,参与临床试验各方的经验不足,都会导致上市日期比国外晚了几年。一个明显不利的后果创新药物无法及时上市,使得患者无法及时从创新科技中获益。
2010年发生的“眼药门”事件,就是与药品无法在中国及时上市,而病人对该药品却有着迫切需求有关。安维汀是一种能抑制新生血管的新药,美国FDA已批准老年黄斑变性是安维汀治疗的适应症之一。较之其他医疗手段,安维汀治疗效果非常好,价格也相对便宜。在中国大陆,即使安维汀已于2013年9月份上市,但是仅批准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并不能用于眼科用药。许多患有老年黄斑变性的病人便冒险从国外或者香港采购安维汀,由于每次用量不多,每瓶药被用于多个病人,这便带来药品污染和交叉感染的危险。2010年9月9日,上海市卫生局发布消息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对患有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进行眼内注射安维汀药物后,有55例患者出现眼部红肿、视力模糊等局部反应症状。眼科界专家指出,国内立法对药物审批的滞后,使人们无法及时和合法地使用国外最新品种的药物,而严格不允许适应症外应用的现状,则可能打击医生进行临床试验的积极性。
从上述比较来看,备案制能够更好保护制药公司和研发机构的创新积极性,从“先审批后试验”到备案制的过渡是今后的趋势,随着中国临床研究走向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全球项目将中国纳入研究目标,以求加快在中国大陆的上市速度,这就要求中国改进审批制度,各方都严格按照试验方案进行试验,各司其职,同时中国临床试验经验的积累,法律法规的日益规范更会为备案制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平台。
2.药品临床试验机构不同
在我国,药监局要求临床试验必须在实验基地进行。目前,药监局批准的临床药理基地只有400家左右,对于每个适应症,可能只有几十家基地可以选择,这就严重限制了临床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有限的几家临床药理基地经常项目扎堆,再加上都是三甲医院,本身就人满为患,工作繁忙的医生们是否有时间和精力来开展临床试验,管理试验质量是否有保证都是个问题。
而在欧美,ICH-GCP里面提到的“Investigator/Institution”,并不特指公立医院,符合条件的私人诊所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遍地开花,这样就使得病人入组容易了许多。
从2008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渐兴起临床试验机构管理组织(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MO),协助临床试验机构进行现场管理、临床研究的执行和具体的操作。SMO通过派遣临床研究协调员(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 CRC)给临床试验机构提供专业支持,获取高质量的试验数据等一系列非医学判断性工作,确保临床研究过程严格按照GCP原则和研究方案的规定执行。委托合同研究机构(CRO)或药厂委托SMO进行临床研究并彼此签署临床研究合同,SMO与各个研究中心签署合同,根据研究者在临床研究中的实际工作量,付给研究者费用。同时,SMO还负责研究者的培训、帮助受试者入选、伦理委员会申报、不良事件报告、知情同意书的准备或翻译、财务管理和税务的申报等等,可以减少医生的负担,提高研究质量。
比较欧美各国,由于他们的医疗体系的完善和临床试验条件的成熟,SMO开展得并不多,许多研究者不但研究经验丰富,而且人员配备充足,设备完善,并不需要SMO的协助。就算有SMO参与其中,也往往不派遣CRC,而是使用研究中心自己的护士等工作人员。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目前临床试验水平较低、研究者经验不足、工作繁忙等情况,SMO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能够帮助我们快速赶上欧美国家,参与到全球试验项目中去。
3.对患者的保险制度的不同
中国与欧美对患者的保险制度有不一样的规定。我国规定药物临床试验的申办方对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保险。但在ICH-GCP中,保险并不是提供给个人,而是给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也就是合同的双方是申办方和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与受试者无关,一旦受试者受到与试验相关的伤害,申办方只需要支付其治疗费用即可。
2013年初引起争论的拜耳老太休克案就是两边法规不一致导致的纠纷。
据新闻报道,张女士在阅读了《患者须知》和关于参加新药试验的《知情同意书》后,同意参加拜耳医药公司生产的一种预防术后血栓的新药BAY59-7939片剂的临床试验。该临床试验内容包括双下肢静脉造影检查。在造影结束时,患者出现了休克。事后,拜耳医药公司只给付了她医保报销以外自行负担的部分医药费,未予其他赔偿。张女士遂将拜耳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拜耳医药公司在保险合同为每个受试者的最高保额50万欧元范围内赔偿15万欧元,同时承担临床试验的医院负有连带责任。
针对拜耳公司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赔偿,纠纷各方有着不同的意见。
张女士认为,她与拜耳医药公司之间存在新药试验合同关系,人民医院与拜耳医药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她所出现的休克属新药试验中的严重不良事件,故拜耳医药公司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拜耳医药公司认为,公司与人民医院有委托其进行新药试验的协议,与张女士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张女士在静脉造影过程中休克并非试用新药造成,而是造影剂过敏,因此不同意对她进行赔偿。
医院认为,拜耳医药公司应购买特殊保险,以保护受试者的经济损失,保险赔付范围应包括受试者因参加本次试验包括有关药物等所致的损害,每例患者保额为50万欧元。原告知悉《患者须知》的内容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表明其愿意承担造影剂过敏风险。医院受拜耳医药公司委托,与原告发生新药试验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相应责任应由拜耳医药公司承担。
实际上,从上述引用的两地的GCP,可以看出纠纷的由来是由于制度及解读的不同所致。在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被纳入临床试验研究的今天,应当完善保险制度,保证保险是针对受试者个人,而不是研究者或者研究机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利益,以保证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4.结语
加快药品的上市速度,是各个制药公司所追求的,出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考虑,制药公司往往在实验室阶段便申请药品专利,药品晚上市一天便会有巨额的市场损失,因此缩短临床试验期,尽快拿到申请上市所需要的数据,就成为各方努力的目标,这就要求参与临床试验的各方相互协作,共同推动项目前进。
我国得益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制药公司将我国纳入临床试验基地;而鉴于中国临床试验的现状:起步较晚、水平较低、对法律法规理解不够透彻、审批时间过长等问题,我们应当尽快与国际接轨,尽量参与到国际多中心试验中去,在法律法规甚至理念上与国际通行标准靠拢,认真学习欧美的先进经验,在客观条件仍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发展临床研究合作组织,如SMO和CRO,协助试验基地和制药公司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保证试验能严格按照试验方案进行和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
】
[1]《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局令第2号).
[2]《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局令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