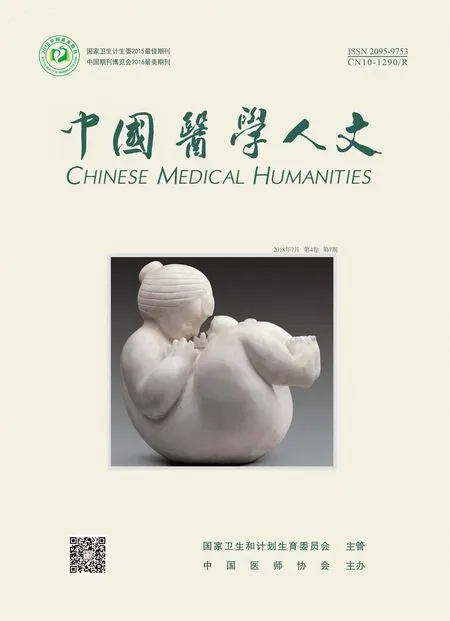我为什么选择学医
文/严 欣
我为什么选择学医?这曾是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与许多自幼立志学医的人不同,幼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医生。相反,我对医院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毕竟只有在痛苦时才会想到的地方是不会给一个孩子留下什么好印象的。与成为医生相比,作家或者工程师的角色似乎更吸引我。然而我最终却选择了医学,这究竟是宿命的定数,还是上天的玩笑?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是否蕴藏着某些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必然?
选择医学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本心,它更多是父母的决定,只是我对这个决定并不反感。在中国,无论你是富家子弟还是市井平民,你都需要掌握一项赖以谋生的技艺,区别只不过是富家子弟劳心,而市井平民卖力罢了。出身平凡的我,自然无法选择金融或政治这样劳心而获利巨大的行业,于是踏实的学一门可以让自己过上体面生活的技艺,便成了父母对我的要求。我至今仍无法忘记父亲帮我选择医学的苦心:“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医生。学医很难让你富贵,但足以让你生活安稳,衣食无忧。”我明白,这是半生操劳的父亲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我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啊,父亲!我那出身寒门的父亲,十三岁时便离家求学,历经艰辛考上大学,却因时运不佳而被迫回乡教书,一腔热血从此消磨在枯燥与琐屑的生活中;我知道您是害怕我像您一样空有抱负却壮志难酬,折戟沉沙,所以才为我选择了这条艰苦但却安稳的道路,这份舐犊之情太厚重,容不得我拒绝。
表面看来,这似乎足以解释我为何选择学医,而这也确实是我回答很多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当我静下心来思考时,疑虑总会涌上我的心头:“选择医学,仅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吗?医学中是否蕴藏着某些能让我超越生存本能的追求?”
循着逻辑的链条,我找到了与医学距离最近的事物:死亡,新生。
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一直是一个让人避讳的词语,我们畏惧死亡,犹如孩童畏惧黑夜,因为两者都意味着完全的未知和与熟悉环境的隔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死”逐渐演变为悲伤的源泉,它代表的,往往是逝者诸多的不舍和遗憾,以及生者无尽的缅怀和思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手携稚子夜归院,月冷空房不见人。”“同穴共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无怪培根会说:“最催人泪下的故事,不外乎生离死别。”
当我们摆脱对死亡近乎偏执的恐惧后,我们终究会发现死亡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用冷静的目光去审视生命,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我们“生”的时间,其实远比“死”短暂。死亡才是生命最自然的状态,有如自然界总是倾向于无序而非有序,生命也在一刻不停地奔向它最终的归宿——死亡。死亡就像一座灯塔,无论你身在何方,你最终都要驶向它指引的方向,一切都会逝去,唯有死神永生。倘若懂得了这一点,便无需为生死隔断的遗憾悲伤,更不会对那必然会到来的死亡恐惧。遗憾的是,死亡带给人的痛苦和震撼实在是太强烈了,尤其是当生前还有愿望没有实现时,那份萦绕在心头的不甘,如刺骨之锥般让人从灵魂深处感到苦楚。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即使威猛如魏武,也会有“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惆怅;睿智如诸葛,也会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喟叹,豪迈如稼轩,也会生出“可怜白发生”的悲凉。死的痛苦如果无法被化解,生的喜悦也就不会被感受。而医生,毫无疑问是沟通横跨在生与死之间冥河的摆渡人。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职业会像医生那样如此直接的面对死亡。倘若这世上真有人能助人超越死亡,也只因他是医者。
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哲学命题。我们无法回答,因为我们都置身其中,无法用超越自身的视角去客观的审视它。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既造就了我们,也创造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对它太过熟悉,熟悉到可以从容地忽视它的宝贵。我曾在公共汽车上看到路边一条被汽车轧伤的小狗,在血泊中痛苦地嚎叫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地从它身旁经过,却没有一人为它停下过脚步。等我下车后赶回来想要救治它时,现场早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短短几分钟内,一条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可曾有人听到过它痛苦的呻吟?可曾有人注意到它眼中对生的渴望?可曾有人意识到从它伤口涌出的鲜血,和我们是同一种颜色?想来多半是没有吧,可你却不能去责备他们,因为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在柔软的心灵经历久了都难免迟钝。所以我时常在想,倘若造物主也是可以责备的,那我要责备他把这世上的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以至于平添了许多本没有必要的悲剧,浪费着许多本不用流下的泪水。
无论我们怎么掩饰,对生命的漠视已如附骨之蛆一般深入许多人的骨髓,而我也难以例外。但当我在产房里抱起刚出生的婴儿时,一种不可抗拒的崇高感还是从我的心中涌起。我怀中的小生命,为了来到世界,历经二百八十个日夜,从受精卵到成熟胎儿,从母体子宫到外部世界,中间哪一个步骤出了差错她都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即使顺利的出生、艰苦的生活、变幻的环境、未知的将来……都足以让她感受到作为人的困窘。可她终究还是选择了生,尽管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去形容她,我想没有什么比“英雄”更合适了。这是生命最本源的豪迈,这是世上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壮举,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夕阳里,婴儿对这个世界发出了第一声啼鸣,恍若圣殿中庄严地梵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何会选择学医:因为我从未停止对死亡的思考和为超越它而做出的努力,因为我从没有丧失对生命的敬畏,对弱小生灵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