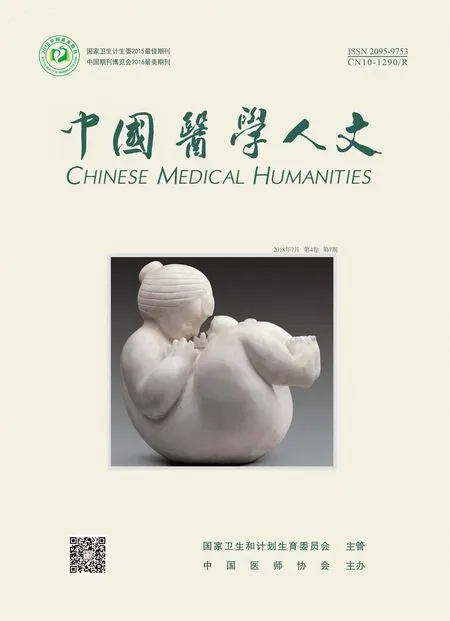秦医生手记
—— 亮剑方为真豪杰 放手如何不丈夫
文/秦锡虎
《圣经》云:“凡事皆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西方人更容易谈论死亡,而在我们东方人的生死观里,死亡一向都是一个避讳的话题。虽然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而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通向死亡之路数不胜数,能让人们各自退却离去,而肿瘤便是其中一条。
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恶性肿瘤悄然跃居中国城市居民死因第一位,在农村居民死因中位居第二,且近年来还在直线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从事肿瘤治疗工作的医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契机。说好听的,这是施展才能的舞台;说难听的,这是提供战斗的战场。
我们的医生们都很敬业,就像李云龙看到了亮剑机会:外科医生举着刀、内科医生捧着药、放疗科医生拿着射线,还有很多特种部队持有分子靶向等秘密武器,纷纷冲上阵去。一时间,战场上血肉横飞、哀鸿遍野,外加众多游击队、土匪帮扛着大刀长矛一哄而上,整个肿瘤战场上是一片混乱。战争结束后,大家迫不及待地清点战场、盘点战果,三年生存率怎么样、五年生存率怎么样、十年生存率怎么样、无瘤生存期、中位数如何?因为生存率越高,SCI论文的分值就越高。
我们将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肿瘤患者生存率这一数字上,大部分学术论文都在探讨如何提高肿瘤患者生命的数量。那么,谁又来关注他们生命的质量呢?他们的三年、五年、十年是快乐地生活、工作、学习、与家人团聚?还是要躺在床上,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苟延残喘、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呢?
上世纪50年代初,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面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时代”。这句话再贴切不过地描述了当前肿瘤治疗的困境:生命的长度与质量,孰轻孰重?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三则故事。
第一则:据报道,巴金先生晚年身患恶性间皮细胞瘤。在巴老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因为生存质量太差,“勉强”活着令他倍感艰辛,他不止一次地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第二则: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晚期恶性肿瘤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回到家乡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他给孩子们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第三则:兰迪·鲍许(Randy Pausch),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2006年被诊断为胰腺癌。但他积极地投身到抗癌大战中,从费城前往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手术,然后南下德克萨斯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进行化疗。世上最强的两大医学中心联合出击,然而并没有阻止癌症前进的脚步,2007年8月他被确诊肝转移,预期寿命仅为3-6个月。当时,他正值壮年(46岁),外表看起来身强体健、精力充沛,与癌症缠斗的资本还很充足。然而他毅然放弃治疗,为实现童年的梦想,去开启生命的旅程。9月,他在母校做了《最后的演讲》,讲述如何“继续快乐的生活”,随后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为胰腺癌患者募集资金,奇迹般地又生活了10个月。
故事的意义显而易见,我的答案也毋庸置疑: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长度同等重要。医学伦理上有句名言:“无限制的延长没有质量的生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一名优秀的肿瘤医生不仅应是手握武器的战士,也应是手捧圣经的牧师,更应是口中颂着心经、心中怀着悲悯的大师。但愿“大师”的队伍愈加壮大,在延长肿瘤患者生命长度的同时,帮助其减轻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让生命完满且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