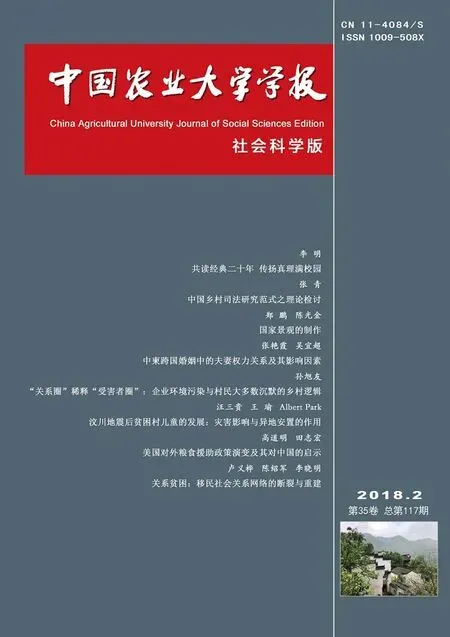“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
孙旭友
一、问题提出
环境污染与抗争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实践关系,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都能够引发集体抗争。面对污染企业对村庄环境破坏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干扰,大多数村民为何选择沉默(Quiescence)?这是一个与“环境抗争何以发生”同等重要的学术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主要涉及以下维度:
(1)坚持经济理性分析视角的学者认为,污染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满足的控制力导致受害居民对污染企业的“经济依赖”,迫使受害群体为了生存需求和生活需要,不愿意或没能力维护自我权益而去抗争污染企业。例如Gould指出,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或许是当地社区经济来源之所,而居民收入的经济依赖弱化了社区抗争的可能性[1]。另外,污染企业对居民经济来源控制即为权力生成的过程,而企业借助政府、社区精英等外在力量的“去权力化”的权力机制运作结果之一,即社区居民面对环境污染而不得不保持沉默[2]。
(2)环境污染的认知框架指出,只有当企业环境污染及其危害具有可见性,并为居民个体或社区集体所认知,才有可能促成环境抗争,否则村民就会保持沉默。这一分析视角,一方面坚持“污染危险的认知差异”是否引发集体抗争的重要机制。如刘春燕的研究发现,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既与人们所实际体认到的物理性的客观环境遭到污染、破坏乃至生态危机的事实直接相关,也与民众对资源利益与环境后果的分配与承担的制度安排与操作是否公平的感受及认识密切相关[3]。另一方面社区居民面对同样的环境污染,不同的认知框架会导致不同的环境行为和社区分化。例如Lora-Wainwright对四川村民“癌病”认知的人类学分析,提出有的村民把癌症看作个人卫生导致的,有的却认为是环境污染的结果[4]。
(3)社区文化分析视角把污染受害者与污染来源的现实关联所形塑的价值观念、态度倾向以及关系认知等作为研究重心,提出关系粘连的文化认同是塑造村民沉默的内在机制。持这种视角的学者从“差序格局的网络以及该网络的疏通能力”[5]、“差序礼仪”[6]以及居民与企业在“需求—满足”逻辑下形成类似中国单位制的“父爱关联文化”[7]等本土概念出发,提出村庄集体沉默是村民基于社区/传统文化考量而做出的主动或无奈的环境选择。例如邓燕华和杨国斌的分析指出,面对本村人开办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村民基于“自己人”的我群意识表现出了更大的容忍度[8]。
已有研究对村民沉默行为的多维度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也缺乏对村庄类型、污染企业类型、乡村社会分化、居住格局等因素及其关联效应,如何影响受害村民环境抗争意愿和环境行为选择的分析。面对中国乡村所呈现的集体式微与个体凸显、现代文明与传统习惯并存、乡村分化与秩序重建、环境意识增强与粗放式生活方式等转型特征与混合状态,需要提出更具统合性和切合乡村复杂现实的分析框架,解读“面对企业污染村民为何沉默”的理论议题。本文以山东N村内生的手套加工厂*本文对所有涉及的地名与人名均作了技术处理。本文资料主要是笔者利用2015年7—9月与2016年1—3月期间,对N村的实地考察、手套加工企业生产及其污染的参与观察以及对维权村民、沉默村民、企业职工等二十多人的访谈。此处所谓的村庄内生型企业,是指由村集体或村民个体建设的企业,而非由城市移植或外村人承办。及其环境影响为切入点,分析企业类型、乡村分化与关系嵌入影响大多数村民环境沉默行为的乡村逻辑。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N村村民建设的手套加工厂对整个村庄造成的环境危害而塑造的受害者圈,在自己人理念和熟人关系的社区文化消解下,被村庄居住格局与利益关系等乡村社会分化维度的叠加效应进一步“稀释”,导致大部分村民无法对企业采取环境抗争而制止企业污染,进而夯实了乡村“小散乱污”型企业存活的社区基础。
二、从建厂生产到污染感知:N村受害者圈形成过程
就N村手套厂环境污染的社区影响而言,整个村庄包括企业系统都是受害者圈的一部分,手套厂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整个村庄来承担。这是一个“建厂生产—环境污染与生活困扰—受害者圈形成”的村庄日常生活建构过程。
(一)建厂生产
N村地处鲁西南沂蒙山区。山地丘陵的地质地貌使得整个村庄只能种植地瓜、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果树、金银花等经济作物。地少人多的现实和多山地丘陵的地理生存环境,决定整个村都过着靠天吃饭,以地为生,过着可以吃饱没有闲钱的小农经济生活。伴随改革开放、城乡流动以及村内省道、乡道公路的畅通,N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村民开始走出大山和村庄,有的买了货车跑长途、有的去外地卖糖葫芦,有的在家开办工厂。N村的手套加工厂就在“要致富先修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市场经济话语鼓动下建立的。
2010年左右,在N村“下庄*“下庄”是N村的一部分,为本村自起的称谓。N村共有三部分组成即下庄、河北与北山。”的西边新居住地带,由葛姓村民建立起一家手套加工厂,后来多家手套加工厂陆续建立。截至2016年底,大约有8家手套加工厂和一家鸭子养殖场在此集中。虽然这些“小散乱污”类企业*“小散乱污”企业是指规模小、分布散乱、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等类型企业。具体参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原先的选址都在N村西边的边缘地带,远离村民集中区域,但是随着农村宅基地随意扩展和村庄联结合并,厂房周围的住户越来越多,其环境影响也越发延展。聚集在N村边缘地带的手套加工厂带有农村手工作坊的痕迹:厂房就建在自家院子里,生产与生活二合一,企业主自己也参与手套生产的各个工序。每一家大概雇佣3到5个工人,从事烧锅炉、看编织机器、值夜班或接手套棉线头等工作。编织白色棉线手套的机器,每一家从20几台到上百台不等,24小时不间断作业,源源不断的手套被机器生产出来,送往远离N村上百公里外的批发市场去售卖。
(二)环境污染与日常生活困扰
“日常生活的干扰”是斯诺(Snow)研究集体行动发生动力学提出的概念。在斯诺的研究视野,“日常生活”即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无需思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斯诺认为当人们不能再按照以往的方式从事日常实践活动,当人们认识到“事情应该是这样,但现在它却不是这样”的时候,就出现“日常生活的扰乱”[9]。村庄西边几家手套加工厂对整个村庄环境的污染,的确对全体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惯常出行路线等造成了困扰,也被村民所认知。就像村民王大爷所说:“影响肯定有。别的咱不说,就说我出去干活,气味真难闻,每次从那边走(路过企业),都难闻的要死。整个庄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日常生活的困扰”是因外界力量的干扰和伤害而呈现长期性或暂时性的反常状态,涉及从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及其态度,向另一种非常态化生活状态的转变及其过程。这种转变既是一种现实境遇或可预期的后果,也是一种心理困扰和负面生活体验。
手套加工厂刚生产的那几年,村里人都很羡慕他们发财致富的能力和捕捉经济收入增长方式的眼光。但是没过多久,村民们慢慢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逐渐深受其害,手套加工厂对整个村庄的环境污染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困扰逐渐显现。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污染对村庄的危害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厂房夜晚照明灯的强光刺眼。手套加工企业出于安全和生产的需要,厂区几千瓦的照明灯到晚上会一直亮着,覆盖范围几百米,所到之处如白昼一般,严重影响周围村民的睡眠质量;二是手套生产机器噪音。手套编织机器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机器噪音辐射企业周边几百米,机器发出的“沙沙”音吵得周围的村民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早已困扰着离企业较近的村民;三是浓烟和灰尘污染。手套加工厂用煤烧制粘胶而产生的浓烟,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入空中,而且每过几天就需要人工清理烟囱,很多带着粘性的灰尘随风飘动,影响了村民的用水和生活环境;四是工厂废旧垃圾。煤渣、线头、废胶等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一起,随时倾倒在路边的沟壑。
(三)受害者圈形成
“受害者圈”是由日本学者舩桥晴俊干线公害研究中提炼形成的,是指在新干线这样的项目中,形成不同的受益空间和受害空间[10]。受益圈/受害圈理论的核心即是分辨哪些群体为受益人群,哪些为受害人群;受益人群和受害人群处于怎样的格局当中,受益圈与受害圈属于“分离型”还是“重叠型”。其理论旨趣主要关注环境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在不同空间与群体的分布状况,带有“受益—受害”双方二元对立和边界划分的内在特征。N村环境污染受害者圈的建构基于两种认知逻辑:一是村民作为朴素的环境社会学家,他们对环境污染的危害、影响群体和范围,具备自然认知和评价能力;二是包括个别村民的激烈抗议与矛盾冲突,县环保局与基层政府等在内的外在力量对环境污染的干预、受害者范畴的认定和国家惩戒力度等,所引发的村庄环境担忧气氛与村民集体感知。
N村手套加工企业环境污染所建构出的受害者圈,既坚持一种利益相关性和环境危害的共担,也突出村庄居住环境的整体性。N村的每个村民包括企业场主与职工都是环境污染受害者,因为只要生活于村庄之内,每个村民都需要承受污染之苦,受害者圈覆盖整个村落。倘若从环境污染的社区影响和村民真实的生活体验上看,日常生活困扰的被感知和被认知,无论是否会引发个体或集体的环境抗争,都把所有深受日常生活困扰的人建构成了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受害者,进而建构出因环境污染而具有共同基础的受害者圈。
三、共同体意识与利益分化:N村“双重圈层”对受害者圈的稀释
伴随着N村逐渐对外开放和人口流动性加大,在乡土逻辑依然可以塑造村庄整合性而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同时,职业、身份、学历、财富等已经成为构建具有重叠性圈子的重要依据。村落集体的共同体意识与村民个体的利益考量,构成N村社会秩序和个体行动的双重逻辑,共同主导着村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这种现代乡村与传统乡村并存的村庄现实,构成N村手套加工企业存活的社区基础。村落共同体意识与个体(家庭)理性构成村民解读村落手套加工厂及其污染问题的认知框架,也形塑着村民的环境行为分化。
(一)“同住一个村”:共同体意识对受害者抗争行为的制约
传统乡村的地缘血缘关系互嵌及其建构的共同体意识,依然对当下众多村落中的人际关系建构和行动导向影响明显。从N村田野经验来看,无论是村民个体抗争、还是大多数的怒而不斥、视而不见和沉默不语,由污染企业引发的村民环境行为差异及其诉求,既带有某种乡土版的“邻避抗争”意味,也被囊括在集体性共同体意识之下。这就使得大多数村民不会/不愿选择环境抗争的方式去应对“一个村的自己人”开办的企业,而少数环境受害者的环境抗争也较为克制,并带有把环境冲突向邻里矛盾转向的自我认识和现实表征。
首先是大多数村民积极对待环境污染而消极对待环境抗争。大部分村民在认同“自己人”的概念里,把开办企业的村民及其企业都划归为扩展性自我范畴,需要遵从“自己人”的行动逻辑,更需要把情感、血缘关系和人情、面子等乡土因素,编织进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社区人际关系建构进程。就像邵大嫂跟笔者聊天时所言:“影响肯定有,经常有烟灰过来,很讨厌,也没办法。为啥?都是一个村的,哪好意思啊(找说法)。再说了,环保局的都来查了,也罚款了,还不照样!还能怎么办,自己多注意。把水池子的水盖住,多打扫院子”。N村作为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血缘地缘共同体,“共同体意识”不仅带有滕尼斯“荣辱与共、息息相关和亲密不见、默认一致”的亲密关系,也呈现出涂尔干“机械团结”和费孝通“差序格局”等概念内在表征的理性缺失、权利禁锢和关系冲突[11]。村民们“都是一个村的”的共同体意识,把社区情感和村庄人际关系和谐,放置于环境权利追求之上,消解了环境抗争意愿,不愿意或不好意思去抗议手套加工厂的环境污染及其对自己生活干扰和身体危害。
大多数村民在“同住一个村”的关系处理逻辑下,积极对待环境污染而消极对待环境抗争,采取了非抗争但是比沉默*面对环境污染及其危害而保持沉默,只是一种相比较环境抗争或集体行动意义上的结构性论述。更为复杂的环境态度或行为表达方式:一方面,面对企业环境污染及其危害,个体采取了更具个体性和艺术化的生活实践。对生活在村庄环境和具备主体能动性的村民而言,除了抗争或沉默,环境行为的选择有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例如私下抱怨、与企业主保持适当社区交往距离、暗中破坏企业主家庭财产以泄私愤等日常抗争形式,以及绕开手套厂的活动空间、搬离居住地、购买饮水设施等自我补救措施或个体自我隔离手段;另一方面,作为身处N村关系场和正在编织关系网的村民,面对少数村民的环境抗争,他们可能正在旁观,把因环境权利追求而导致的冲突矮化成村庄内部正常的人际矛盾,而不适合插手和参与;或许怒而不斥的准备搭环境抗争分子的便车,因为村民们感受到了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和内在的不满,但基于村落熟人关系而无法“出头”;他们或许感觉抗争没有意义,因为手套加工厂环境污染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干扰和不便而引发的个别村民的抗议冲突和环境主管部门的干预性后果,如停工、罚款等行政手段,都无法阻止污染企业的存活和继续生产。这给沉默村民的潜在抗争设置了一种“抗争无意义”的消极情绪和扮演“睿智的沉默者”[12]以自我说服理由。
其次是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与邻里化转向。N村手套加工企业的环境危害与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干扰程度以及村民环境行为选择,受到企业驻地及其与村民家庭距离的影响。虽然环境污染带有负面扩散和跨界性,但是企业污染及其环境危害是否会引发环境抗争以及受害者抗争卷入程度,受到污染范围和影响空间的限制。靠近污染企业的村民及其家庭,由于受到环境污染更大的伤害,其抗争意愿更强烈,抗争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现代社会频发的“邻避冲突”类的环境运动,就是当地社区对邻避设施的环境危害的抗争,人们反对的不是邻避设施而是建设地点,而且邻避抗争者更多是受影响的地方社区民众。
按照企业污染及其影响延展的逻辑,环境污染及其危害以污染企业厂址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呈递减趋势和边际效应。N村整个村庄的受害者圈可化约为三个圈层,即重受害者圈、中度受害者圈和弱受害者圈。从重受害者圈到弱受害者圈,随着受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递减,其抗争的可能性也逐渐弱化,环境受害村民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环境行为。重受害者圈由于靠近污染企业,其邻避情节更强,邻避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这一圈层主要是指围绕手套加工企业,周边范围在300~500米以内的个人和家庭,由于居住点临近手套加工厂,其受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其可能性最为严重。重受害者圈内的家庭和村民所承受的环境危害大体相同且极为严重,他们最有抗争的动力和意愿。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一现实又是意料之中:即使靠近污染企业和深受其害,很多受害者选择了无视污染企业的负外部性,而保持沉默。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乡土关系和社区分化等乡村力量,对环境抗争意愿的消解。,只有少数村民采取了实际行动:一是通过市长热线12345的制度化渠道来投诉,让县环保局来查;二是直接采取对话或冲突等个体化方式来解决。
G(男,50岁)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向环境部门投诉甚至直接与手套加工企业进行交涉、发生冲突的抗争积极分子之一:
也可能有别人打(投诉电话)吧。我偶尔也打,我也跟他们(手套加工厂)明说了,也偶尔去找他们理论,还起过冲突。他们这样,日子没法过,搞得我们一家睡不好觉,机器响个没完,烟灰满院子都是。但是没什么效果,还要天天忍着。环保局下来查作用也不大,顶多停几天又开始了。最后也是没办法,都是一个村的,也不好太过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不能打得头破血流,让大家都没法活。
即使是重受害者圈内、居住在污染企业附近的个别村民抗争,也是较为克制和去政治化的。个别的重受害者爆出的冲突和争吵,也被看作需要保持一定克制的“邻里矛盾”而非因环境公民权诉求的正义抗争。因为世代同住一个村的村民不可能老死不往来,还需要长期的在一个地方居住和人情来往。N村个别村民的环境抗争,虽受到权利受损、利益争取的自我动员,但更多是基于邻避情节*本文的邻避情节主要考量污染企业的空间位置和邻避抗争者额参与动机,而不指向企业或设施的公共用途;而且这里的邻避冲突更是个人意义上的,而非社区集体性质。的影响:即企业可以建,但是不要建在我家旁边;污染可以有,最好不要干扰我的生活。这是一种基于乡土人情关系、利益考量和个体环境公民权等多种行为动机的混合心理状态。而这种乡村邻避抗争及其后果带来的消极情绪和“住的近、伤的深、闹的凶”的行动逻辑,在村落关系网的文化认知和向邻里矛盾转化的实践中,更加稀释了受害者圈。
(二)获利者默许:利益关系对受害者圈的分化
在现代社会,由于污染所具有的地方空间性特征,如弗里曼认为,基于环境污染危害是在特定地理空间内表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一个社区往往就是一个环境保护的利益群体[13]。这种由污染而带来的环境保护的利益群体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区内部或环境保护利益群体内部的分化。N村社区环境保护利益群体和受害者圈的整体性,因职业行为引起的经济依赖和利益关联而受到分化,形成“获利者—受害者”和“非获利者—受害者”两个圈层。这两个利益群体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有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意愿,但是他们对污染企业的态度和环境行为选择具有极大不同。如果说更多的“非获利者—受害者”村民是一种沉默和怒而不争的态度,那么“获利者—受害者”群体呈现出默许甚至支持的意愿。
N村受害者圈内的获利者,如企业主、在企业打工的村民、借钱/高利贷给企业的村民以及有业务往来的村民等。这些获利村民围绕污染企业形成了受益者群体,他们对污染企业和企业污染的态度和行为,更加带有经济理性的利益取向,在环境权利与利益获得之间偏向后者,进而带有宽容甚至纵容企业污染的意味。经常给手套加工厂运送原材料和手套的运输司机翟师傅:
我是经常给他们厂子送手套到市里,也帮拉棉线、胶这些东西。要说有影响,肯定有,要不然县环保局不会来罚款。我管不了别人,但是对我来说,我不会投诉的,毕竟有时候靠这个吃饭,一个月好几千,要不然怎么办?这也算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不好说什么。
企业污染及其环境危害程度虽然影响获利群体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从生活环境移向了经济收入。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依赖甚至是经济支持也减少了环境抗争甚至关注的可能。就像Gould的研究所指出,污染企业所提供的生活资源可以有效弱化甚至阻碍居民个体抗争的可能性[14]。即使是获利者深受其害,他们也不会采取投诉或者抗议的方式来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及其对自己的伤害,他们只会采取“主动性隔离”[15]的方式达成自我保护而非保护环境,以事不关己的姿态继续保持沉默。
彭大哥曾经在手套加工厂里面帮着烧锅炉,一个月1 500元工钱,干了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据他自己说,天天烟熏火燎的,胶水刺鼻,自己的身体受不了,得了肺病,不能再干了。他还压低声音给笔者说:
这不是人干的活,给多少钱都不去了。我也没跟老葛家(企业主)说因为身体问题,就说不想干了,太熬时间。更没跟庄子里任何人说,只能自己受着。不去就完了。(当被问及原因时,彭大哥颇为无奈)都是一个村的,咱们是去干活赚钱,想赚就去,不去就算了,不能断了他们的财路啊!现在村里很多人也对他开厂子有意见,也被罚了很多钱,我再说这些话不好!毕竟人家也是好心,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了!
手套加工企业污染及其危害在形构出N村整个受害者圈的同时,也建构了内部识别度颇高的获利群体。这些获利村民,是环境受害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或协助者”,更是环境污染的获益者。与此相对应,那些无法或者没有从企业获利的村民,就成为纯粹的污染受害者。正是基于“是否从企业获利”的自我认知和社区现实,N村受害者圈被划分为“获利者—受害者”和“非获利者—受害者”两个圈层。如同Tilt在研究职业群体与环境认知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不同群体之间对环境污染及其危害的认识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各自环境行为的选择[16]。N村划分的这两个圈层或群体对环境污染的关注、污染企业的态度及其环境行为选择,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非获利者—受害者”圈层内的沉默村民相比,“获利者—受害者”圈层因渗透进利益相关和经济依赖因素,对企业的环境污染更加沉默甚至默许。
四、结论与讨论
手套加工企业的生产污染对N村环境危害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建构出的整体性受害者圈覆盖于N村关系圈之上,而受害者村民的“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消解了大部分村民环境抗争意愿和行为。与此同时,村民居住点与企业的空间距离、村民是否跟企业有经济关联又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对整个村落的受害者圈而言,受到整个村庄弥散性的“自己人—价值理性”和部分村民特殊性的“自己人—经济理性”两种行为逻辑的双重稀释。N村的环境受害者圈被“同住一个村”的社区意识和乡村社会的分化及其叠加效应所稀释,导致了大部分村民即使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也没有抗争的意愿和行动表征,使得借助社区公共参与来制止企业污染成为不可能。农村内生企业的内生逻辑和嵌入属性,不仅加深了村落社会的社会分化、人际隔阂与关系碎片化,而且侵蚀了基层治理单元和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阻隔了通过提升村落环境和村民生活,带来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生态文明等目标实现路径。
面对“小散乱污”等乡村内生型企业的环境危害,当地村民何以容忍或者为何屡禁不止,一直是环境保护和环保执法的难题。而能够防止企业污染的路径有三种:一是国家行政力量执法力度和精准度;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自我提升;三是受污染影响者抗议或抗争的有效性。这三种环保力量的治理效力及其合作治理路径,受到实践情境和农村具体情况的影响,如何在国家环境执法、企业环境保护和村民抗争三者达成一致,是一个需要实践情景分析的议题。而农村污染企业类型与治理对策、污染企业的关系嵌入以及环境维度对农村分化的叠加效用,提醒需要对治理企业污染以及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加深认知:
一是在对乡村污染企业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做出应对性的环境治理对策。村庄外来的污染企业更多受到国家政策和基层政府的支持,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村落集体的力量去改变。而村落内生的“小散乱污”类企业,由于村民的分化和企业关系的社区嵌入,这就需要借助国家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整治,进而切断企业与社区的嵌入关系。
二是乡村分化已成事实,需要在关注原本利益差别、阶层分化的同时,考查环境维度导致的乡村分化后果以及与其他分化维度的叠加效应。在村落内是否具备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抗争意愿和能力的人员分布以及环境权利诉求、乡土关系对环境抗争的作用认知等,都成为当下乡村社会结构复杂化的事实和分化维度。
三是农村环境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这不仅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力量推行和资源支持,也需要关注村落社区类型、文化传统和生活空间的社区影响,更需要把村民日常生活的经济关联、生活便利性和人际交往逻辑等因素,纳入农村环境治理范畴而加以考量。
[参考文献]
[1] Gould, Kenneth A. The sweet smell of money: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local environmentalpolitical mobilization.Society&NaturalResources,1991(4):133-150
[2] Gaventa J.PowerandPowerlessness:QuiescenceandRebellioninanAppalachianVall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3] 刘春燕.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社会,2012(1):174-196
[4] Lora-Wainwright, Anna. An anthropology of “cancer villages”: villagers’ perspec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2010(19):79-99
[5] 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122-132
[6] 罗亚娟.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59-67
[7] Solecki, William D. Paternalism, pollution and protest in a company town.PoliticalGeography,1996(1):5-20
[8] Yanhua Deng,Guobin Yang. Pollution and Protest in China: Environmental Mobilization in Context.ChinaQuarterly,2013(214):321-336
[9] Snow, D. A. “Disrupting the Quotidian”: Re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akdown and the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Action.Mobilization:AnInternationalJournal, 1998(1):1-22
[10] 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宋金文,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11] 孙旭友,芦信珠.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3-99
[12] 谭宏泽,Geir Inge Orderud.地方性环境保护政策的未预后果:以天津水源保护措施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7(1):213-223
[13] Freeman M R. Issues Affecting Subsistence Security in Arctic Societies.ArcticAnthropology,1997( 34):7-17
[14] Gould, Kenneth A. Pollution and Perception: Social Visibility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Mobilization.QualitativeSociology, 1993(16):157-178
[15] Andrew Szasz.ShoppingOurWaytoSafety:HowweChangedfromprotectingtheEnvirnmenttoProtectingoursel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16] Tilt, Bryan. Perceptions of risk from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a comparison of occu-pational groups.HumanOrganization, 2006(2):11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