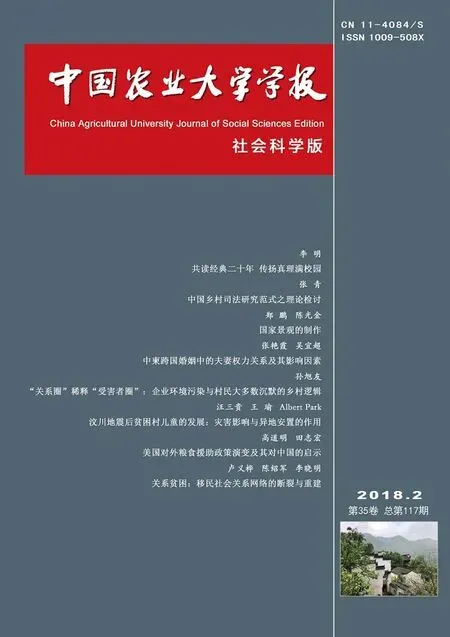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张艳霞 吴宜超
一、研究背景
中国大约在四千年前进入父系社会,父权制度和从夫居婚姻赋予男性在私有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和家庭权力等方面有比女性更优越的地位,并且父系家族制度主要依赖普婚、早婚和早育来维持。在这种“父权和普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中国历史上持续存在着相当数量陷入婚姻困境的大龄未婚男性[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2010年全国总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5.20,福建省的男女性别比为105.96*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据估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 000万人左右,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农村婚姻市场性别失衡问题突出,“光棍”现象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2]。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缔结。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凸显,“外娶型”跨国婚姻(本土丈夫迎娶外国新娘)逐渐盛行。跨国婚姻是“一国公民和另一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双重国籍人)之间的婚姻”[3]。它的出现揭示了以婚姻关系为代表的正在发生的从传统社会文化向现代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4]。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与日俱增。为了从总体上把握跨国婚姻的数量和特征,笔者收集了2009—2013年间福建省涉外婚姻的各项统计数据,梳理比较后制成表1。如表1所示,2009—2013年间,福建省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比重持续排在全国第一位。涉外结婚数量都在1万对左右,涉外结婚最高达到1.1万对,占全国结婚的比重为0.09%,占福建省结婚的比重高达2.88%,跨国婚姻成为了福建省婚姻构成形式的重要方式。但是跨国婚姻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与法律问题。由于跨国婚姻涉及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文化、家庭习俗,所以比一般的国内婚姻更加容易爆发冲突和危机。

表1 2009—2013年福建省涉外婚姻总体时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结婚总量的数据来自2009—2013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婚姻服务”的结婚登记数据,各项比重和排名基于全国及各地区相应数据计算和比较得到。
国外对于跨国婚姻的探讨和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于“邮购新娘”的探讨,认为跨国婚姻是商品经济下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女性为了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而采取的策略或手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亚洲地区也开始盛行[5]。国外跨国婚姻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从咨询和建议的角度分析夫妻双方的文化差异,并提出克服差异、减少冲突的方法,以帮助稳定家庭关系[6]。
国内跨国婚姻研究则主要围绕“跨国婚姻的运行机制”、“跨国婚姻带来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展开探讨,同时也注重分析跨国婚姻的性质、过程及影响[7]。研究者认为跨国婚姻中女性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是一种全球化现象[8],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附属品。尽管跨国婚姻的形成与男性受本国婚姻市场排挤的因素有关[9],但涉外婚姻更多是在全球经济裹挟之下,女性婚姻当事人想要改变自身现状的策略选择结果[10]。近年来大量的民族学、社会学、法学学者对于跨国婚姻的发生机制、社会功能、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和社会适应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分析主要从两个视角出发:一是以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看待跨国婚姻引起的社会问题,二是以研究对象的个人生活为本探究当事人的主观体验。
夫妻关系指由合法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两性在家庭领域的角色关系,反映了家庭中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情感、权力和义务的关系,是一种姻亲关系。夫妻权力关系是夫妻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于跨国婚姻中夫妻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制定与完善涉外夫妻关系冲突规范,妥善解决涉外夫妻关系法律冲突[11];以及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12]。对于跨国婚姻夫妻权力关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既有文献的分析研究显得不足。
学术界对于夫妻关系尤其是夫妻权力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西方资源理论开始。布拉德和沃尔夫的资源理论指出:现代社会中,比较资源已经取代了传统(父权制)成为家庭权力的新来源[13]。布拉德和沃尔夫区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夫妻权力模式:丈夫主导型、妻子主导型、分权平等型、权力共享型。他们认为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资源决定了其相对权力,配偶中具有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资源优势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决策权。资源理论主要在家庭单位内考察夫妻之间的权力结构,因而忽视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社会学家海曼·罗德曼首先对其进行了修正,他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具有浓厚家族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父权制规范尚占统治地位,当地丈夫在婚姻中的权力与其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关系呈现为负相关。因此他将关于夫妻权力格局的社会文化规范因素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考察文化规范作为控制变量下的资源与权力关系,提出了“文化背景中的资源理论”(规范- 资源理论),认为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再取决于布拉德和沃尔夫意义上的单一资源,而是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1)丈夫与妻子的比较资源,(2)特定的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14]。可见,罗德曼分析框架中的“规范”与“资源”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规范”是开放性的社会背景因素,而“资源”在任何“规范”条件下都是绝对的,实质上还是一种“资源竞争”的思路。
在规范- 资源理论出现的同时,交换- 权力理论也开始尝试对资源理论进行补充。希尔认为丈夫贡献的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与妻子在婚姻外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丈夫的权力越大,反之亦然。从而解释了一方对维持关系的兴趣较小的原因:与对方的情形相比,自己贡献的资源的现实回报与潜在回报的落差更大[15]。萨菲里奥斯- 罗斯柴尔德则提出了“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认为赋予婚姻关系以及对方提供的资源以更高价值的一方将处于弱势权力地位,而付出较少感情的一方往往可以更自由、更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从而占据优势权力地位[16]。总而言之,“规范—资源”框架和“交换- 权力”理论,都没有否定资源理论的基本观点——家庭中的权力与有价值的资源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17]。
有学者认为相对资源理论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不同阶层家庭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夫妻收入、教育和职业地位的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格局影响显著;夫妻权力关系在中国体现出阶层差异化发展特征,中下层家庭更加注重夫妻间经济物质资源的比较[18]。夫妻双方的关系格局受到附着在他们各自身上的资源、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等的影响[19]。城乡家庭夫妻权力结构差异显著,中国城市夫妻权力关系正在从“夫主妻从”到“夫妻平权”[20-22]。也有学者分析认为资源假设理论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经济贡献对家庭各项权力的影响十分显著[23]。部分学者认为资源因素和文化规范型塑了中国农村家庭中的夫妻权力模式,农村家庭仍保留“夫权”特色,农村家庭夫妻权力关系主要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规范所型塑[24]。中国农村两性不平等的状况仍然严重,“夫主妻从”的模式一直存在[25],“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在农村地区仍得到较高程度的认同[26]。
布拉德和沃尔夫的资源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源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在夫妻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夫妻权力结构上的作用,有意识地反应其与传统家庭权力结构(父权制)的不同。罗德曼和希尔等人在随后发展的规范- 资源理论、交换- 权力理论无疑都是在对资源对夫妻权力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一判断的认可上构建的。资源理论将妻子和丈夫给婚姻带来的比较资源,包括个人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作为夫妻权力关系构成的基础。交换- 权力理论中提倡的“贡献与回报”、“相对的爱和需要”其实质上还是在资源理论的框架内,是根据夫妻双方对彼此掌握资源的实际需求的不同对资源进行价值区分,本质上相信资源的价值差异。在已有的夫妻权力关系研究中,资源理论、规范- 资源理论和交换- 权力理论其核心都是资源,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分析夫妻权力关系时应当清楚地定义资源的内涵并区分其价值差异。布拉德等着眼于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物质资源的相对数量差异;希尔强调的是婚姻内外获取资源能力的差异,明确了资源交换的逻辑并将之扩大到婚姻外;萨菲里奥斯则是提出了婚姻中资源会被赋予不同价值并将爱、性、陪伴、照顾等作为情感资源,并将其也作为一种影响权力地位的因素。在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发展和扩充中,作为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对资源的内涵经历了长久发展。在范围上,相对资源经历了从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物质资源到爱、性、陪伴、照顾等情感资源的扩充。在交换逻辑上,由以相对数量解释相对权力到区分资源的需求差异和价值差异。因此,在分析夫妻权力关系时应当注意,资源理论中资源的范围包括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而夫妻双方的需求程度和获取能力的差异影响了资源在价值上的差异,对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影响程度有明显差异。
本研究旨在探究跨国婚姻中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在布拉德和沃尔夫的资源理论、罗德曼的规范—资源理论以及希尔等人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将资源定义为:能够对夫妻权力关系产生影响的金钱收入、职业等物质资源和生育、爱、性、陪伴、照顾等情感资源;并区分了由于夫妻双方的需求程度和获取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资源在价值上的差异。本文通过将文化和资源作为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尝试对福建省松溪县的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调查地点与研究方法概述
本次研究地点是福建省北部山区的松溪县,位于闽浙交界处,武夷山麓东南侧,属传统农业县,下辖3个镇、6个乡。根据福建省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松溪县2013年年末户籍统计总人口16.5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19万人,农业人口12.34万人,男性8.59万人,女性7.95万人(男女性别比例约为108)。福建省2014年统计年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松溪县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35.6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1.44亿元,第二产业13.17亿元,第三产业11.06亿元,人均GDP达到29 721元*福建省统计年鉴http:∥www.stats-fj.gov.cn/tongjinianjian/dz2013/index-cn.htm。,低于福建省和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全国的人均GDP为41 908元,福建省的人均GDP为57 856元,参见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
根据松溪县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资料*从福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目前跨国婚姻结婚登记必须在市级公安局进行登记,不同于国内婚姻的登记制度。,2008年以来,福建松溪县中柬外娶型跨国婚姻的数量持续增加,已经远超中越外娶型跨国婚姻的数量。中柬跨国婚姻已经成为了一种解决当地农村男性不婚问题的重要途径。与出现时间更久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不同的是,中柬跨国婚姻是在婚介公司介绍后经由国家合法程序结成的外娶型跨国婚姻。本土丈夫与外籍配偶通过合法手段结成的夫妻关系在经受住了各方面挑战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截至2015年3月1日共有511名外国籍女性在松溪登记结婚(外娶型跨国婚姻*外娶型跨国婚姻,指本土丈夫迎娶外国新娘,婚后从夫居的婚娶形式。),约占总人口0.32%。其中柬埔寨国籍371人,越南国籍140人,结婚时外籍新娘的年龄主要集中分布在21~25岁。跨国婚姻本地农村男性结婚时的年龄集中在30~45岁。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中介公司在花了60 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后办理了合法手续迎娶的外籍新娘。年龄的差距、独特的婚姻缔结形式使得这种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与传统婚姻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大不相同。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笔者通过查阅已有文献,了解到了国内民族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跨国婚姻的发生机制、社会功能、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和社会适应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查阅了调查地点福建省松溪县的县志、福建省年鉴、福建省松溪县公安局的相关统计数据以了解松溪县的跨国婚姻现状。
笔者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在2015年上半年深度观察了福建省松溪县跨国婚姻家庭的家庭生活,深入了解了中柬夫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适应情况。同时还参与观察了外籍配偶举办的聚会、社区居民与中柬夫妻的社会交往情况。
笔者还运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于2015年2月在福建省松溪县的6个乡镇访谈了17户生活在福建省松溪县内的中柬跨国夫妻。接受访谈的这17对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中,外籍配偶的年龄分布在22岁至28岁之间,本土丈夫年龄分布差异较大,从27岁至43岁不等。所有夫妻的教育水平最高为高中,普遍接受了初中教育。这些跨国婚姻的夫妻其家庭经济情况处在当地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属于中下层家庭。
笔者从这17对跨国夫妻中挑选了的6对典型户进行了长期观察和多次深入访谈。这6户包括三种类型夫妻:生活和谐,少有矛盾的夫妻2对;生活中偶有矛盾,能维持婚姻现状的夫妻3对;家庭生活中常常爆发激烈冲突,婚姻关系难以维持的夫妻1对。并同时对其亲属以及社区居民等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的婚姻状况和双方的社会生活情况。
三、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关系现状
夫妻关系是两性在家庭领域的角色关系,包括了夫妻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情感关系和权力关系。夫妻权力关系作为夫妻关系的重要方面,与夫妻经济关系和情感关系有着密切联系。经济关系、情感关系说明的是夫妻在收入、家庭财务等物质资源和爱、陪伴等情感资源上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夫妻双方的物质资源关系和情感资源关系,展现的是夫妻双方对不同资源需求程度和获取能力的差异,既有助于全面反映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关系现状,也是进一步深入分析跨国夫妻权力关系影响因素的关键。
(一)夫妻经济关系
夫妻经济关系是夫妻双方最主要的物质资源关系。夫妻经济关系是一个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核心家庭中最主要的经济关系。夫妻经济关系包括夫妻的收入比例、家庭财务管理两个最主要的方面。
1.收入比例
调查发现,外籍配偶没有正式工作是一个普遍现象。外籍配偶在进入中国国境的时候办理的都是旅游签证,虽然在中国结婚后是从夫居,但是要想在国内参加正式的工作则需要先在中国居住三年,住满三年后还需办理复杂的相关手续。所以在没有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外籍配偶不敢冒着被罚款和遣送回国的风险参加正式工作。此外,松溪县的柬埔寨籍外籍配偶主要是在2008年后嫁入中国,正处于20岁至30岁的生育年龄,因为生育或抚养、照顾年幼的孩子而无暇参与工作。
绝大多数外籍配偶只能参加一些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例如同家人一起接种木耳、晒木耳、收玉米、晒稻谷等。但是外籍配偶参与的这类农业生产活动不会使得她们个人获得直接的经济收入,她们仅仅是作为家庭主要劳动人员的帮手。本土丈夫都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在工厂打工。除了上述法律和生育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之外,本土丈夫对外籍配偶参加工作的态度以及外籍配偶本人的工作意愿也影响了她们参与正式工作的情况。
艾先生:“我38岁的时候用父亲老家的林地凑了6万元,二婚娶了一个柬埔寨老婆。我是家里的老大,家人希望我能早点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我觉得老婆就在家里看孩子,做好家务就行了,娶个老婆不是为了让她帮忙挣钱,而且她也挣不到多少钱。”(案例一,42岁,流动商贩,结婚4年)
达女士(艾先生配偶,27岁)17岁就开始帮人洗衣服供养弟弟妹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孩子、洗衣服和做饭等家务。她过去在柬埔寨基本上是没钱了就工作,有钱了就不工作直到没钱花了再重新去工作,婚后她和丈夫的想法一样。她觉得现在她丈夫的工作能够满足家里的基本生活,她不需要也不想去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就好了,家务有时候也不太想做。达女士等外籍配偶对于工作的不积极态度、家庭以及生育的牵绊还有法律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她们在婚后始终处于无工作状态。本土丈夫通过打工、务农等工作获取的收入成为了家庭的唯一经济收入,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比例呈现为极度失衡状况。这种状况下的跨国婚姻一方面由于只有丈夫单方面收入使得家庭经济状况成为隐忧,另一方面丈夫与外籍配偶的极度不平衡的收入比例决定了夫妻双方的经济地位,也会影响二者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
2.家庭财务管理
在中柬跨国婚姻家庭中,家庭财务的管理权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家庭财务支出以本土丈夫意愿为主,外籍配偶仅在一些日常生活的基本花销上有管理权,甚至无法参与、决定家庭日常开支。
王先生:“自己赚的钱自己存起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把大概够用的生活费放在家,她买菜和零花钱在那儿。钱肯定要自己放的,大家都这样,这柬埔寨娶来的老婆,那怎么说也要小心一点。自己赚的钱放在自己这里,一个是心里有数,不用担心她带着钱跑了,一个也能控制一下她花的钱嘛,这个家肯定还是要我说了算的。”(案例二,38岁,工厂工人,结婚5年)
王先生现在和父母共同居住在农村。王先生的工作是在村庄附近的工厂打工,他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平常家里的日常家庭开支由父母管理,他每月会给父母一定的现金。而他的妻子则没有自主支配、管理家庭财务的权力,如果想要买什么或者其他的花费都必须向丈夫说明用处再向丈夫索要。
在跨国婚姻家庭中,王先生等本土丈夫在经济收入上的绝对优势保证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同时,由于对外籍配偶敏感身份的考虑,他们更倾向于自己掌控家庭财务管理权,仅让外籍配偶接触少数日常开支所必须的财务,甚至直接控制配偶的可支配现金。外籍配偶处在家庭财务管理的劣势地位,这种地位在她们的婚姻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伴随着婚姻年数的增长,夫妻关系的稳定,彼此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公婆等其他家庭成员干预的减少,外籍配偶才会逐渐获得更大的家庭财务管理权。
(二)夫妻情感关系
夫妻情感关系是夫妻双方最主要的情感资源关系。夫妻情感关系是夫妻关系中的抽象方面,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情感关系沟通、矛盾冲突等。
1.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和陪伴
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和陪伴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中柬跨国婚姻中,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受到了语言的限制。松溪县的两种通用语言是方言和普通话。柬埔寨籍妇女只能依靠嫁入中国之前在柬埔寨参加的由婚介公司组织培训的汉语学习班中学习到的简单的日常用语进行交流。对于来自柬埔寨的外籍配偶来说,用普通话交流都是痛苦且艰难的。她们无法听懂别人话语,无法用普通话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不懂”、“我不会说”成了“口头禅”。语言不通成为夫妻情感交流的障碍。
艾先生:“和她说话很麻烦,本地话她又不会说,普通话我自己都说不好,一句话要说半天才能弄明白。” (案例一,42岁,流动商贩,结婚4年)
语言不通使得本土丈夫与外籍配偶的情感沟通产生了阻碍,这种障碍是客观的,是基本的、不容忽视的。然而,即使是在语言能够满足基本交流的前提下,跨国婚姻夫妻生活中,丈夫仍然很少与妻子进行情感交流、沟通。张先生(案例五,33岁,建筑工人,结婚5年)与Z女士的家庭生活比较和谐,两人表示很少有吵架的时候,但是两人也很少有情感交流。夫妻双方在情感上的沟通显得尤为稀少,彼此的交流都是发生在对日常生活上的一些简单交流。张先生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像一般农村男性一样不善于表达情感、不善言谈,再加上长期在工地上班,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使他更喜欢在家时候保持沉默或者一个人休息。本土丈夫的沉默使得夫妻的情感交流更加难以维持,也使得外籍配偶产生了不满。
外籍配偶:“我们平时也很少说话的,他每天都要出去卖东西,我就在家带孩子啊做饭啊,他晚上回来要么就出去玩了,要么就说很累,看看电视就睡了,我找不到人说话。”(案例一,27岁,结婚4年)
与本土丈夫不同,外籍配偶从原生家庭嫁入中国后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社会环境的巨大不同使得她们对现在所在社会缺少了认同感。语言的不通畅使得外籍配偶无法顺畅地与亲友交流,在无法参与工作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呆在家里,承担家庭劳务工作。因此,她们的交流对象就局限于与丈夫,她们渴望与丈夫进行情感交流。
2.夫妻间的矛盾冲突
在婚姻家庭中,矛盾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夫妻双方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发生意见不和、冲突甚至是争吵、冷战、动手。在跨国婚姻中,夫妻双方间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的。
外籍配偶:“他晚上特别爱出去玩,前两天我们刚刚吵架,他出门卖水果回来,吃个饭就出去玩了。女儿晚上发烧了,我又弄不来,都快急死了,就打电话给他叫他回来。虽然他很快就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很生气。” (案例一,27岁,结婚4年)
艾先生:“我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从柬埔寨取了个老婆回来,不要她赚钱、漂亮,但她起码家务活要干啊。我每天都要工作,就指望她在家里做家务,结果她又懒,学得还慢,连饭都做不好,能不生气吗?” (案例一,42岁,流动商贩,结婚4年)
外籍配偶在婚姻后,需要在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背景下承担家里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她们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希望得到丈夫的帮助,而本土丈夫则希望外籍配偶能负担所有家庭事务,夫妻双方缺少足够的关心和互助。民族、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都会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身上烙下本土文化的烙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夫妻在脱离了自己生存的原生家庭即父母的家庭与对方结婚构成新的家庭之后,出现了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这些差异容易使得他们在生活中产生摩擦,并且累积,造成大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夫妻感情。李先生(案例六,32岁,农民,结婚5年)与柬埔寨配偶的婚后夫妻感情不合。由于李先生爱喝酒,喝酒之后比较容易冲动,而他的妻子性格比较外向,经常去找其他来自柬埔寨的朋友。李先生在2014年秋天,一次酒后回家,发现妻子没在家,带怒出门寻找,找到后施行了家暴,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夫妻关系破裂无法缓和。由于外籍配偶多次被殴打,在邻居报警,警察三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公安局只能将其安排回国。
在松溪县的调查发现,中国政府部门对于外籍配偶的保护比较单一。一般是夫妻出现矛盾有人报警后,由公安局出面调解、警告。如果调解、警告无效,夫妻双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经常会出现一种结果:双方在公安局的介入下离婚,外籍配偶被遣送回国。此外,在警察介入的同时,外籍配偶也可能利用一些手段筹集到回家的路费并偷偷外逃,如平时积攒、从丈夫那儿偷拿、向其他嫁到中国的来自柬埔寨的朋友借取或索要。因此,本土丈夫出于对自己娶妻所花费的大额金钱的考虑,往往在夫妻冲突激化时更容易妥协,以防止双方在公安局的介入下离婚,妻子被送遣回国的极端情况出现。
(三)夫妻权力关系
在跨国婚姻夫妻关系中,夫妻间的权力关系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跨国婚姻夫妻间的权力关系不仅会影响到夫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又受到夫妻的各种因素影响。跨国婚姻夫妻权力关系可以从夫妻双方在家庭主要事件决策权力分配情况、家务劳动分工情况等方面进行观察分析。同时,夫妻双方对于自我在夫妻权力关系地位的主观评价也是分析跨国婚姻夫妻权力关系状况的重要内容。
1.家庭主要事件决策权力
家庭主要事件的决策权力分配问题,是跨国婚姻家庭在面临一些较为重大事件时的决策者倾向问题。家庭的主要事件是指购买高档商品、孩子就学、买房、盖房、借贷等对于家庭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在这种事件的决策过程中,权力的归属呈现为一边倒状态。
王先生(案例二,38岁,工厂工人,结婚5年)在存钱打算盖新房时只与父母商量,关于建什么样的房子,建在哪儿,建多大等他从来没有与妻子商量过。在前面为家里置办彩电、冰箱的时候,他也未曾与妻子说过。W女士(王先生配偶)通常是在他做出决定并已经行动后才后知后觉。
跨国婚姻中夫妻的家庭主要事件基本都是由本土丈夫决定,外籍配偶很少参与决策。外籍配偶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家务劳动中承担较大,并且获得了一些决策权力。但是在主要事件中,丈夫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都必须是经过丈夫的同意,外籍配偶的意见更多地被忽略,她们往往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此外,外籍配偶,尤其来到中国时间不长的配偶,对于家庭所处的环境情况了解不深入,不能给与丈夫足够有价值的建议。所以,她们在多数时候保持了静默或仅仅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和需求,而丈夫也因此更倾向于自己做决定。
2.家务劳动分工
家务劳动分工是家庭生活的必要活动,是夫妻权力关系的一个最基本方面。家务劳动分工是夫妻双方在家务劳动上达成的不成文协议,在跨国婚姻中与其他直系亲属以及家庭内部环境有重要关联。在中柬跨国婚姻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分工主要呈现为女多男少的现状。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尤其是洗衣做饭、清洁整理、照顾孩子等活动基本都是由外籍配偶承担,而本土丈夫一般仅负责一些体力家务活动,如搬运和维修。此外,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往往会与本土丈夫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外籍配偶能够从公婆或其他亲属获得一些帮助。这些帮助在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一些差异,但多数都是带孩子、买菜、做饭等,洗衣服则是所有外籍配偶必须亲力亲为的。
沈先生(案例三,30岁,务农,结婚3年)娶了柬埔寨的妻子 (S女士)与父母住在一起。由于家里主要从事木耳生产工作,因为木耳生产需要大量人手,所以沈先生与父母经常都是早出晚归,因此家里的家务劳动尤其是洗衣服和打扫卫生主要由外籍配偶负责。但是由于现在她已经有了身孕,她的婆婆会把家里的家务做完后再去干活,因为家人觉得她做的饭不好吃,所以做饭一直都是婆婆负责,她只帮忙打打下手。而沈先生个人则基本未参加过家务劳动,只有当遇到一些体力劳动的时候才会帮忙解决。
当然,这种分工状况也不是绝对,在个别特殊家庭,外籍配偶也有可能仅仅负责很少数的家务劳动。宝姨的儿媳妇就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仅是为数不多的特例。宝姨在2011年为自己27岁的儿子熊先生从柬埔寨娶了个老婆,但是儿子和儿媳妇之间的关系很不好。但是洗衣做饭的工作还是自己来做,儿媳妇只是帮忙打打下手,有时还会一个人一天呆在房间不出门,很少承担家务劳动。这是由于她的儿子年幼高烧后而导致智力发育不完全,虽说不至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但是却有些缺陷,而宝姨为了维持儿子和外籍配偶的婚姻关系做出了特殊的努力。
综上所述,跨国婚姻中的家务劳动分工情况虽然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一种情况,但在松溪县的多数中柬跨国婚姻中,就像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家务劳动大部分也都是由妻子承担的一样,多数外籍配偶会被要求扮演这种贤妻良母的角色,成为全职太太负责主要家务劳动。
3.权力关系的自我评价
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夫妻关系有着较多的契合。男女双方在家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的互占一半,他们对夫妻权力关系合理性的判断主要依据各自家庭的实际情况,通常是比较认同。
张先生(案例五,33岁,建筑工人,结婚5年)在娶妻之初,家务劳动由谁做,怎么做,家庭财产怎么用等都是张先生一个人决定。在结婚一年后,张先生有了一个孩子,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情况,他在工地上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家庭权力的掌控越来越有心无力。于是,在妻子(Z女士)的一次主动请缨下,他让妻子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夫妻间权力分配在受到生活实际的制约的同时还因夫妻双方的意愿、协商得到调整。Z女士在主动承担家里的家务并展示出操办家务的能力并取得丈夫的信任后,获得了掌管家庭生活开支的权力。近两年,由于从事中柬婚介工作而有着丰厚收入的她在家里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夫妻对于家庭权力调整后的分配十分满意。
在多数案例中,外籍配偶对于现在家庭权力关系的自我评价是家庭权力分配比较合理,虽然自己拥有的家庭权力通常少于丈夫,但是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相近的。她们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外来媳妇,在家庭中各项权力受到丈夫的制约,同时也对这种制约表达出相似的妥协的想法。也有像Z女士一样的少数外籍配偶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用更多的权力,而不是被禁锢在家庭内,只能负责家务劳动。而本土丈夫由于经济地位优势,处于熟悉的家庭环境之中的他们更倾向于控制家庭权力分配,但也可能会因为配偶的要求或实际需要而做出改变,这使得夫妻间的权力分配更符合家庭实际,以及夫妻双方的想法。
跨国婚姻夫妻权力关系特征显著,具体表现为夫妻双方在家庭主要事件决策权力分配结构是男多女少,决策权力主要归属于男方;在家务劳动分工的分配情况是女多男少,女方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劳动;在家庭中夫妻双方对其本人权力地位比较认同。夫妻双方在家庭主要事件决策权力的分配、家务劳动分工的分配上差异明显,但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权力关系现状比较认同。
四、影响跨国婚姻夫妻权力关系的因素分析
影响跨国婚姻的夫妻权力关系的因素有很多。笔者基于跨国婚姻中夫妻双方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有文化差异、资源占有差异等特点;借鉴布拉德和沃尔夫的资源理论、罗德曼的规范—资源理论以及希尔等人的相关理论将文化和资源作为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从跨国婚姻中社会的文化规范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情感资源份额和资源价值的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展开分析。
(一)文化规范
福建省松溪县有着“从夫居”的文化传统,男权文化浓厚,“男主外女主内”、“夫主妻从”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盛行,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男性一般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同时,当地传统的宗族主义和“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思想浓厚,男性在生育子嗣方面有着极强的意愿和需求。
“外娶型”跨国婚姻的居住模式遵循着中国传统“从夫居”的文化传统。“从夫居”作为父系制时代最流行的一种婚姻居住形式,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男子逐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妇女沦于从属地位后的产物。“从夫居”作为父权制的根基,还衍生出父系继承、父系养老的父系社会制度体系;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从夫居、子女随父姓和养儿防老都是父权制的制度安排[27]。“从夫居”的居住形式的出现意味着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和父权、夫权制度和文化的壮大。在父权制的文化传统下,丈夫主导型的家庭权力结构被赋予了规范性和指导性的涵义。妇从夫居的居住模式实际上就是消减、剥夺了妇女在婚后生活的独立和自主,使她们更多地依赖于男性。
在传统男权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思想赋予男性以主导和支配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中国的农村家庭依然保留“夫权”特色,而中柬跨国婚姻虽然不属于本土传统农村家庭,但本土丈夫作为婚姻的一方,其原生家庭是农村家庭,拥有明显的农村家庭特点,使得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权力关系主要受到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规范所型塑。在中柬跨国婚姻中,沈先生等本土丈夫与外籍配偶的家务劳动分工由本土丈夫分配,女多男少现象明显。尤其是洗衣做饭、清洁整理、照顾孩子等活动基本都是由外籍配偶承担,而本土丈夫一般仅负责一些体力家务活动,如搬运、维修。本土丈夫要求妻子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劳动并且往往更愿意自己掌控住对家庭主要事件的决策权力。这样的权力结构意味着本土丈夫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对家庭事务进行分配。松溪县当地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父权制规范依旧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思想以及“从夫居”居住模式构成了罗德曼理论中的“特定的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并对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产生形塑作用。根据罗德曼的规范- 资源理论,本土丈夫必然成为了夫妻权力关系的支配方。
与此同时,松溪县盛行的宗族主义和“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使得本土丈夫在生育子嗣方面有着极强的意愿和需求。跨国婚姻构建的伊始就是本土丈夫组建家庭、传宗接代的需求和压力的反映。这种需求和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其个人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个人、家庭尤其是本土丈夫的双亲的“传宗接代”需求和社会舆论倾向。下面的讨论将进一步阐述本土丈夫强烈的生育子嗣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婚姻中的权力地位优势,使得跨国婚姻中夫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均衡。
(二)资源差异互补
资源对夫妻权力关系的影响来源于夫妻双方对资源的需求和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夫妻双方由于国籍、政策、原生家庭条件甚至是性别、性格等差异引起的对各种资源需求程度和获取能力产生差异。这使得夫妻中的一方在需求某种资源而缺乏相应的获取能力时会赋予有相应的获取能力的另一方以更高地位。即夫妻中的一方在婚姻内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的价值大于婚姻外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的价值时,处于婚姻中的获利方。此时,其赋予婚姻关系以更高价值,也将在夫妻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跨国婚姻中,物质资源(收入、职业等)差异对于跨国婚姻中夫妻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中柬跨国婚姻中由于外籍配偶长期处在无工作状态,资源差异主要包括夫妻双方原生家庭经济的差异、在构建婚姻关系过程中双方所承受经济代价的差异、婚后生活中夫妻经济收入的差异造成的夫妻经济地位差异、交际网络(社会资源)差异等。跨国婚姻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经济情况一般是处于各自地域的中等偏下水平。在调查的17对案例中,外籍配偶的原生家庭经济都是在温饱线上徘徊,也正是这种生存压力下,她们才在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选择了远嫁中国。虽然各自的原生家庭都处于各自社会的底层,但是彼此间还是有较大差异。本土丈夫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虽然在本地并不优越,但是都能满足生存需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发展需求,这是外籍配偶的原生家庭所不具备的。简而言之,丈夫的原生家庭经济水平优越于配偶原生家庭经济水平,外籍配偶有更强烈的物质需求。
与此同时,外籍配偶强烈的物质需求无法在婚姻外部实现。由于国内政策规定,婚姻移民来的未获得中国户籍的外国配偶需要到有关部门办理工作证后才能正式工作,否则将给予遣送回国等处罚。复杂繁琐的手续以及生育、语言障碍等阻碍因素的制约下,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外籍妇女往往没有正式工作,在经济上处于依附状态,无法拥有经济话语权。丈夫单方面收入使得家庭经济状况成为隐忧,另一方面丈夫与外籍配偶的极度不平衡的收入比例也会影响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外籍配偶强烈的物质需求没有相应的获取能力支持,只能在婚姻内部实现。因此外籍配偶在物质需求上赋予丈夫更高地位,丈夫在经济上拥有完全支配地位,夫妻间的地位处于不均衡状况,外籍配偶在经济劣势的情况下无法与丈夫进行公平对话。资源优势的一方(男方)左右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家庭权力地位严重失衡。
另一方面,中柬跨国婚姻中情感资源差异也影响了夫妻权力关系。上述松溪农村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的思想使得本土丈夫在生育子嗣这一情感资源上有着极强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在婚姻中得到实现。在婚姻缔结后,丈夫因为赋予婚姻关系以及生育子嗣这一情感资源以更高价值而处于一定弱势权力地位,而付出较少代价和需求的外籍可以更自由、更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优势权力地位。
夫妻双方对资源的需求和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影响了中柬跨国婚姻中夫妻权力关系。本土丈夫在跨国婚姻中拥有明显物质资源优势,而外籍配偶则拥有明显的情感资源优势。本土丈夫贡献的物质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与妻子在婚姻外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较大,夫妻权力关系中丈夫的权力地位得到提升;但与此同时,本土丈夫需要通过外籍配偶满足他们对生育、爱、性等情感资源的需求,因而赋予了婚姻关系以及外籍配偶提供的生育、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以更高价值的本土丈夫的权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外籍配偶的家庭权力得以加强。中柬跨国婚姻中夫妻在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的需求和占有差异使得其夫妻权力关系相互制衡、动态平衡。
五、讨论与结论
逐渐盛行于福建省松溪县的中柬跨国婚姻是当地农村大龄男性在遭遇婚姻挤压后的一种无奈选择。本研究发现在夫妻经济关系方面,外籍配偶长期处于对丈夫经济依附的状态。外籍配偶由于受本人对于工作的不积极态度、家庭以及生育的牵绊还有国内相关法律限制等多因素的影响,在婚后始终处于无正式工作的状态,没有直接收入。本土丈夫的经济收入因此成为了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比例呈现为极度失衡状况。家庭财务支出主要以本土丈夫意愿为主,外籍配偶仅在一些日常生活的基本花销上有管理权。
中柬跨国婚姻夫妻双方因为语言不通而引起交流障碍;因农村男性不善于情感表达和关心妻子而产生许多沟通问题。外籍配偶从原生家庭嫁入中国后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社会环境的不同使得她们对现在所处的社会缺少了认同感。语言的不通畅使得外籍配偶无法顺畅地与亲友交流,在无法参与工作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呆在家里,承担家务劳动。因此,她们的交流对象就局限于丈夫,本土丈夫的陪伴和情感交流成为了她们希望得到的情感资源。而本土丈夫的沉默却使得夫妻的情感交流更加难以维持,也使得外籍配偶产生了不满,夫妻双方的情感和生活中矛盾与冲突不断。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是情感破裂、外力介入离婚或者外籍配偶私逃回国。夫妻情感关系一方面受到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作用于它们尤其是权力分配。在中柬跨国婚姻中经济关系、情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夫妻双方的物质资源关系和情感资源关系,夫妻双方对不同资源需求程度和获取能力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
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始终受到资源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中柬跨国婚姻里,丈夫所掌握的经济、社会等物质资源明显优于外籍配偶,并且外籍配偶具有强烈的物质需求,并赋予物质资源以极高的价值,却没有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物质资源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只能从婚姻内部获取。此外,语言不通而引起交流障碍和外籍配偶从原生家庭嫁入中国后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使得她们的交流对象局限于丈夫,本土丈夫的陪伴和情感交流成为了她们希望得到的情感资源。因此,具有物质资源和情感优势的本土丈夫获得了夫妻权力关系的优势地位。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的思想使得本土丈夫对生育子嗣这一情感资源有着极强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在婚姻中得到实现。本土丈夫需要通过外籍配偶实现他们对生育、爱、性等情感资源的需求,由此赋予了婚姻关系以及外籍配偶提供的生育、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以更高价值的本土丈夫的权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外籍配偶的家庭权力得以加强。资源需求程度体现的是不同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对于夫妻双方的真正价值,而获取能力体现了该资源对于夫妻双方的稀缺程度。对于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双方而言,不同资源的真正价值和稀缺程度具有明显差异。
而文化和资源作为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正是通过社会的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方式与国内传统婚姻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跨国婚姻中,外籍配偶的原生家庭经济水平与本土丈夫的差距极大,外籍配偶拥有更强烈的物质资源需求和对陪伴等情感需求却没有相应的获取资源能力;本土丈夫强烈的生育子嗣的情感资源需求遭遇婚姻挤压后难以实现。本土丈夫在跨国婚姻拥有明显物质资源优势和一定的情感资源优势,而外籍配偶则拥有明显的情感资源优势。夫妻双方在跨国婚姻中对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的需求和占有差异使得其夫妻权力关系相互制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夫妻权力关系的均衡。而当地家族主义传统、父权制规范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思想以及“从夫居”的居住模式构成了罗德曼理论中的“特定的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对夫妻权力关系的影响。本土丈夫在文化规范的作用下在夫妻关系中拥有了更高的权力地位。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的需求和占有差异使得其夫妻权力关系相互制衡以及传统的父权制规范的文化背景使得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呈现为丈夫主导型。文化和资源作为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正是通过社会的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方式与国内传统婚姻有着明显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与本土家庭的巨大差异的存在,才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认识中柬跨国婚姻的特殊性,深入分析跨国婚姻中夫妻权力关系的影响因素,这正是笔者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文主要揭示了上述文化和资源因素对中柬跨国婚姻中夫妻关系的影响。但是毫无疑问,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远不止这些,婆媳关系、社会政策、社区支持网络等其他因素也会对夫妻关系产生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研究视角在郑丹丹为代表的学者的扩展下,不再把权力过程作为一种补充,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表现形式来进行研究,将夫妻生活中丰富生动的互动过程纳入研究范围。郑丹丹认为,根据福柯的权力观,权力不是物,因而不能交换;权力是流动的,因而也没有固定的形态,不存在始终不变的权力模式。换言之,权力总是表现为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寄寓于一系列事件之中,通过这些事件在互动过程中得以型塑。所以,通过对家庭中夫妻互动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透视权力关系如何同时体现为一系列的权力技术、策略[28]。斯科佐尼也批判了将家庭权力看作是静态现象来研究的倾向,主张将家庭权力研究的重点,从对“谁做出最终决策”这一问题的追问转移到对交换/权力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变化的关注上[29]。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韦艳,张力.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人口研究,2011(5):58-70
[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研究,2007(1):1-10
[3] 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4] 郑宇,杨红巧.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 学术探索,2009(5):57-61
[5] Jones G.InternationalmarriageinAsia:Whatdoweknow,andwhatdoweneedtoknow?.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R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2
[6] Jones G, Shen H H. International marriag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ends and research emphases.CitizenshipStudies, 2008(1): 9-25
[7] 李海芳. 龙村景颇族跨国婚姻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8] 夏晓娟.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9)
[9] 萧昭娟.国际迁移之调试研究:以彰化先头社“外籍新娘”为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10] 叶钦地. 福州涉外婚姻初探. 福州党校学报,2005(1):81-84
[11] 姜绚丽. 涉外夫妻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12] 张晓,欧小卫,裴氏秋.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59-64
[13] Blood R O, Wolfe D M.Husbands&wives:Thedynamicsofmarriedliving. Glencoe, Ill: Free Press,1960
[14] Rodman, Hyman. Marital Power in France, Greece, Yugoslav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National Discussion.JournalofMarriageandtheFamily, 1967(2)
[15] Heer, David M. The Measurement and Bases of Family Power: An Overview.MarriageandFamilyLiving, 1963(2)
[16] Safilios-Rothschild, Constantina. A Macro- and Micro-Examination of Family Power and Love: An Exchange Model.JournalofMarriageandtheFamily, 1976(2)
[17] 张丽梅. 西方夫妻权力研究理论述评. 妇女研究论丛,2008(3):75-81
[18] 李建新,郭牧琦. 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妇女研究论丛,2015(6):17-23
[19] 潘鸿雁,孟献平. 家庭策略与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 新疆社会科学,2006(6):84-89
[20] 沈崇麟,李东山.变迁中的城乡家庭.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1] 王跃生. 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 社会,2006(3):118-136
[22] 赵瑞芳,林明鲜,唐国建. 城市老年人夫妻权力模式与夫妻关系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5):31-34
[23] 李静雅. 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妇女研究论丛,2013(5):19-26
[24] 时聪聪. 资源因素、文化规范和城乡家庭夫妻权力.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5] 单艺斌.女性社会地位评价方法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26] 李文. 中国农村夫妻权力关系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分析.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3):64-70
[27] 南储鑫. 寻找打破从夫居坚冰的多重力量. 中国妇女报,2014-05-13(02)
[28] 郑丹丹,杨善华. 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 社会学研究,2003(4):96-105
[29] McDonald, Gerald W. Family Power: The Assessment of a Decad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970-1979.JournalofMarriageandtheFamily, 1980(4)
——张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