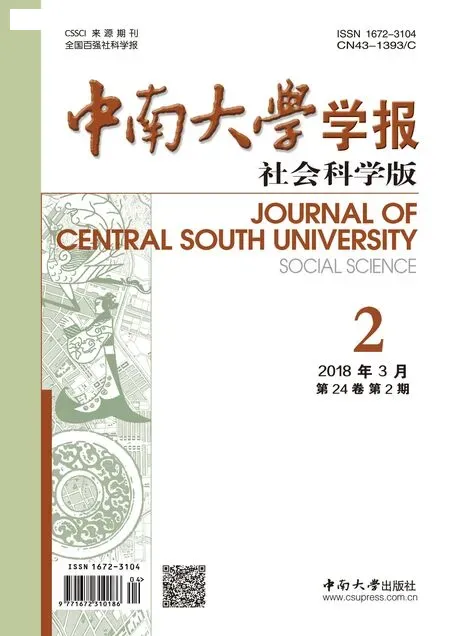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复调与现代性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在19世纪中叶,当无所不在的现代性将俄罗斯卷入其中之时,曾把人和上帝联系起来的旧的认知范式①已不足以解释俄罗斯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现象。在这场变革里,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竞争。每个范式不但有拥护者,而且都有以该范式解释的事实作为支撑。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权威的观点通常只有一个,现代人却被无数互相对立的观点所吸引。这些观点彼此竞争,同时念念不忘瓦解其他的观点。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思潮还未走向“上帝之死”的极端,但宗教信仰的力量正在不断衰弱,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寻找适应俄罗斯现代转型的新范式。例如,他的《地下室手记》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构建的乌托邦的反思和辩驳。这展现出两种不同范式之间的争斗,也展现了现代性是一个自身内部有着冲突的矛盾复合体。
复调艺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的认知范式的表现。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作者的权威性话语,采用小型对话与大型对话构成的复调来表现作品中的思想冲突。因此,许多读者往往分不清地下室人的观点、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观点、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观点与作家本人观点之间的区别[1](13)。如果现代性在社会思想领域的文化症候是“上帝之死”,那么其在文本世界里则表现为拥有上帝般权力的“作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退位”了,或者说与叙述者话语、人物话语进行了争辩。在巴赫金之后,英美斯拉夫研究者马尔科姆·琼斯(Malcolm Jones)更激进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解构特征”。他甚至认为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得“过于舒服了”,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钟爱的“颠覆”,而这是解构主义所擅长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是要寻求重新发现‘鲜活的生命’的源泉,他似乎越是发现它们从属于被解构主义批评称之为‘无限拖延’和‘推迟’的东西。……这个发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意识形态层面出现,但不是简单地针对这个世界(真实的或再现的世界)的一个说法。它起源于话语本质本身。”[2](13)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走到“解构”那么远,但是“作者之死”是“现代狂欢”的重要部分。复调艺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描绘在文本意义上脱离了严苛的宇宙秩序,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解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予在作品中的现代性体验。
一、复调艺术与现代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思想、体裁等特点指出了其作品的复调特点和对话立场,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创作的主要激情,既从形式方面也从内容方面,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人的各种关系以及人的所有价值所发生的物化所进行的斗争……但我们要再重复一次,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批判中抽象理论方面与政治方面,而是他的艺术形式所含有的解放人和使人摆脱物化的意义”[3](70)。巴赫金在这里点出的“艺术形式”与“所含的解放人和使人摆脱物化”相结合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指出,巴赫金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他拒绝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正如他与俄国形式主义者进行的批评性对话所显示的那样,他强调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艺术之外的社会环境在从外部作用艺术的同时,在艺术的内部也找到了间接的回声”[4](80)。因此,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忽视了他的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却在小说中截取出来的所谓内容去寻找创作特点的缺憾,以对陀氏作品艺术视角、体裁特点、情节布局、语言类型等的深刻解析,从中发掘出这些‘艺术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思想”[5](13)。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是从艺术形式开始的,但他从没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对社会、对人性的种种展示。巴赫金的贡献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人的种种需求、欲望与挣扎的思考,对启蒙现代性尤其是西方理性主宰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现代社会中复杂多样的现代体验的描绘。展现复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如何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性的思考是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时极富价值与预见性的成就。在今天,对现代性进行思考的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调艺术展现了现代性萌发初期的一些特征,同时“地下室人”这一文学类型已经被收入现代文化意识的词汇表。
如果把现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里现代人是生活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中世纪的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着稳定的秩序。到了启蒙时期,随着人的意识逐渐觉醒,神逐渐退位,先前那个稳定的秩序摇摇欲坠。呼应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启蒙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理想蓝图和哲理设计的方案。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终结了以宗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观, 起着去神圣化、促进世俗化的作用,使人们从超验领域转向世俗事务;而另一方面,启蒙现代性以资本主义变革为发展动力,片面强调理性和秩序的价值,抑制感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人们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物质的兴盛”进一步摧毁了基督教宇宙观,甚至破坏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现代性的进展在信仰领域所带来的改变就是尼采所言的“上帝之死”。所谓的“上帝之死”指的是来自神的圣恩和对超验的追求不再是人类世界的社会道德标准与终极目的,因而,“上帝之死”使人失去了稳固的宇宙秩序,面临一个新的流动的世界。在俄国也是如此。正如巴枯宁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当时的俄国,“建立在宗教、宗法制和文学的社会权威基础上的旧道德永远地崩溃了。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起来……”[6](163)。上帝之死敞开了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大门,这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状态。但事实上,现代性所引发的信仰领域的改变不能认为现代性本身是无神论的、反宗教的。而是应该将现代性看作一种努力,即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找到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回答。马林内斯库认为这将是一个不断进展的过程,并且“上帝之死似乎开启了宗教求索的一个新纪元——事实上往往不再从其结果而是从其纯粹强度得到衡量与评价的求索,一种走在以自身为目的的途中的求索”[7](70)。在这样一个大世界里,艺术家的小世界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预感到以基督教上帝为基础的信仰体系的崩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他以细腻而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面对神退位的世界失去信仰而濒临掉入虚无主义深渊的人:地下室人、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拉斯科利尼科夫、伊万·卡拉马佐夫。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一切都可以做”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的先驱,唱响了现代人的悲喜双重奏。
复调艺术也是现代性所促成的流动世界的一种再现。区别于之前的独白小说,巴赫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复调小说。过去的独白小说是由作者统领全局,虽然其中不同人物相互交织,但不过是一种“同声齐唱”。在这种小说中,有时虽然人物众多,但人物意识从属于作者,人物与作者不处于同等地位。同时,在独白构思中,主人公是封闭的,他的思维界限也是被严格划定的,受制于自己的性格、气质、社会身份。“这样的形象是建立在按其与主人公意识的关系是客观的这一作者世界上的;这个世界的建立——具有它的观点和各种完成性定义——预示了外在的固定立场、固定的作者视域。”[3](57)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这一独白式的前提,走在了文学表现现代世界“多声部”的先驱道路上。从西方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一直被认为是作品的出发点,是作品的生产者,是叙述行为的唯一主体。就此而言,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契合于哲学上的柏拉图主义——作者处于这种二元论哲学的支配者一方。然而20世纪以来,这一认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罗兰·巴特甚至提出“作者之死”的观点。在文论界,既有米歇尔·福柯那样从宏大的历史谱系角度来论证“人只是变化着的知识型偶然捕捉到的一个中心”,通过颠覆“人”的统治地位从而消解了作者在文本中的权威;亦有具有实践精神的文论家兢兢业业地潜入文本机制中寻找不同于作者的写作主体。既然作者不再控制一切,那么作品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呢?故事内容的言说者又是谁呢?叙事理论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没有认识到叙事的复杂性,叙事的真正执行者应该是隐含作者。而隐含作者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不同的叙述者,因此叙述主体的意识在文本中处于分化状态。如果我们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复调现象,身处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走在了在创作中分化叙述主体意识的先行者的道路上。对他而言,艺术上这种多声部现象从根本上而言,是与他所要表达的对现代生活的思考相关的。“当古典主义根植于古老传统的土壤,复调话语显然是现代形式构建的原则,确定了所有意识形态生活中单独意识的自足。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膨胀的主体的回应,不是形式的终结,而是新形式的创造:复调小说。……现代性在这里不是阶段而是界限,是主人公被悲剧时刻逮捕的门槛:个人主义的,无根的,他发现自己与周围的声音不搭调。”[8](79)俄罗斯的现代性来得较晚,强度却一点也不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时代是多声部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感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本中试图表现多种话语的争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主人公们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复调小说中,作者不是像在福楼拜的小说中那样消失不见,而是与主人公进行“对话”,因此不同于所谓的“客观小说”。正如巴赫金指出的,那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没有表现出丝毫作者意识的观点是荒谬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复调小说中新的作者立场所具有的积极性。复调小说创造者的意识经常地、无所不在地出现在这种小说里,而且在其中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不过,与在独白小说中相比,这个意识的功能、其积极性的形式是不同的,这个意识不会把其他的他人意识(即主人公们的意识)变成客体,不会从背后对它们做出完成性定义[3](76)。
二、对话精神与现代性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将“对秩序的追求”作为思考现代性的杠杆。他认为在现代这一历史时期中,无论是文化规划还是社会规划,实质都是建立在对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追求上。在启蒙理性的作用下,启蒙现代性逐渐转化为对统一、秩序、绝对和永恒的迷恋。但同时,他又指出了在追求秩序的过程中存在着矛盾以及因之形成的张力。“现代存在(modern existence)不断地受到现代意识的纠缠并被搅和成一种焦躁的行动;而现代意识则对现存秩序有着不确定性的怀疑或觉察。这一意识是由对秩序设计(即消除矛盾之筹划)的不相洽性(inadequacy),或进而言之非可行性,亦即对构成这一意识的世界的随机性和身份(identity)的偶然性的预先警告所激起并为其所左右。”[9](170)鲍曼所指出的现代意识是一种与启蒙现代性形成“对峙”与互动的反思、批判意识,往往以审美现代性的方式作用于启蒙现代性,形成了现代性内部的张力。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得益于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和社会的急速变化,另一方面又成为启蒙现代性的内部瓦解因素,不可避免地反对启蒙现代性。当我们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形式的对话性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对话这一形式所蕴含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对话”精神贯穿始终,结构上的大型对话与一些话语中重音所形成的微型对话打破了启蒙现代性对秩序的过度追求所造成的精神“铁笼”。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对话精神所表现出的审美现代性力量使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斯蒂芬·斯彭德(Sir Stephen Spender)在《现代的斗争》中指出:“现代艺术就是,艺术家在其形式与风格中反映出对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情境的意识。较之在主题中,我称之为现代的那种特质更多地表现在实现了的风格与形式感中。……现代人的写作是意识到环境活动的观察者观察他们自身感受的艺术。他们的批评意识包括反讽式的自我批评。”[7](100)这里所谓的自我批评其实是一种自我对话,而在这种自我对话中,他人的声音以自我意识的方式反映出来。例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经常想象着别人对他的评价和对他发表的见解的评价,他竭力设想每一种关于他的他人意识,每一种对他的看法。他绞尽脑汁猜测着他人评价的语调,同时在论述时虚构出在场的他者。虽然身处封闭的地下室,地下室人了解一切,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他以自己那奇特的视野在内心深处反复咀嚼着一切。在与他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对话中,地下室人所试图呈现出的是作为人的独立性和未完成性。这种对话意识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巴赫金所称的微型对话。再例如《罪与罚》的开篇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接到母亲来信之后那段内心独白也是微型对话的例子。
显然,应该事事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不是别人,正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哦,可不是吗!应该为他创造幸福,供他上大学,使他成为事务所的合股人,保证他的整个前途;大概他会成为一个富翁,受人尊敬,也许,他到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有名誉的人!可是母亲呢?啊,要知道这是罗佳,最宝贵的罗佳,长子!嗯,为了这样的长子,哪怕是这样的女儿又怎么不能牺牲呢?噢,慈祥而又不公正的心!为什么不能呢:大概我们现在就不会拒绝索涅奇卡的牺牲!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拉美托夫,不朽的索涅奇卡,世界暂时还是完好的。牺牲,你们对这两种牺牲全面衡量过了吗?是这样吗?能得到吗?有好处吗?合理吗?你们知道吗,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卢仁老爷的命运更下贱……[10](100)
在这一内心独白里,我们可以听到许多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和妹妹,马拉美托夫)的声音,它们统统反映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识里,因此该内心独白是对话化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时而想象着妹妹或者母亲的话语,时而想象着马拉美托夫与索尼娅的话语,同时在这些他人话语中又有着他自身意识的音调。“拉斯科利尼科夫实际上在这段独白的开头就重现了杜尼娅的话及其评价的音调和肯定的音调,并且给她的音调加上自己的音调——讽刺的、愤懑的、担心的音调。就是说,在这些话里同时响着两个声音——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声音和杜尼娅的声音。在下面的话里(‘要知道这是罗佳,最宝贵的罗佳,长子!’等等),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声音一同响起的,就已经是母亲的声音了。母亲的声音带着爱与温柔的音调,而拉斯科利尼科夫的音调则充满了痛苦的嘲笑、愤懑(自我牺牲)以及悲伤回答的爱。我们在拉斯科利尼科夫后来的话里又听到了索尼娅和马拉美托夫的声音。对话渗透在每句话内部,在其中唤起各种声音的争斗与间断。这就是微型对话。”[3](83−84)
与微型对话同时展开的是作品中的大型对话,读者可以听到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具有拿破仑情节的个人主义理论,也可以听到索尼娅·马拉美托娃的东正教救赎思想,还有波利菲里的实证主义,同时也隐含了作者的话语。这些声音不是彼此封闭的,它们时刻都在倾听对方,彼此响应。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名秉持东正教神学思想、认为基督重于真理的作家,却没有给自己的作者身份太多的特权。而是与诸多人物一起较为平等地参与到作品中的大型对话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读者会感到索尼娅所宣扬的救赎思想显得“苍白”,而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精神复活直到小说的结尾才露出端倪。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种贯彻到底的对话立场,肯定了主人公的独立性、内部自由、未完成性和不可决定性。这样的主人公走在不断探索自我的道路上,这是一种极具现代意识的生活态度。有学者指出这一“未完成性”是由现代性的“虚幻”造成的:伯曼(Marshall Berman)指出由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是欠发达的,因此俄罗斯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印象往往是想象式的。这种“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对现代性的想象式描绘使俄罗斯作家对现代生活的探索和他们笔下的现代人物都不存在稳固的基础,更多是发展的、流动的。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未完成性”与现代意识自身的解构特质有关:马尔科姆·琼斯认为现代性本身包含了解构因素,并存在于现代性本身的矛盾之中。在琼斯看来,地下室人的自我建构过程是与自我解构同时进行的。“也许,我们应该再加进一种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ve)分析。因为地下室人的哲学的思考颇可被解读为一种解构现象的演示:在此,原有的理性/意志(在该对关系中,理性被看作重于意志,而意志被压抑并矛盾地彰显)的对立等级秩序被颠倒了过来,意志由原来的次要地位被升到了显要的地位。结果是,个人意志/社会和谐的二元对立也同样面临被颠覆、倒置的威胁。……我想提出的是,《地下室手记》写作上那种令人痛苦的自我暴露的风格正是解构主义批评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整体主义(逻各斯中心的,logo centric)的文本或意识形态里都隐藏着自我消解和颠覆的种子。在这里,启动解构主义进程的动力是狂暴的感情冲动。从这一点上来讲,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启蒙运动应该是关注的主体。”[2](80)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文本所希望陈述的观点往往以自我解构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整个文本便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大型对话”的形态,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彼此争论,甚至驳斥对方,解构的形态就是这样形成的。例如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对他想象中的受叙者“先生们”的反驳并不是直接提出了和“先生们”观点相反的一整套理论,而是游戏一番对方的词汇和逻辑,指出对方使用的能指(signifier)和对方宣称的所指(signified)并不相等。地下人挑战“先生们”所坚持的所指,同时使能指活起来,呈现多义,以此“游戏”对方所谓的完整体系,使之变为开放性的、可以讨论的话语,这恰好是解构艺术的手段。正是这种解构式游戏,使地下室人和隐含作者一样具有双重视角,能见常人之所见,又能见常人之所不见。
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正常的人,他的慈母——把他仁慈地生养到人世间来的造化,希望看到他的也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我十分嫉妒,嫉妒到肝火上升,不能自已。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的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11](183)
地下室人常常站在“先生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又用自己的话语“混淆”了聪明/正常与愚蠢这两个标准,因为他认为在评判这两个性质的标准上他与“先生们”的定义是不同的,与日常定义也是不同的。他用“先生们”的词汇表达了自己的标准,从而对先生们的话语进行了变形。因而本已固定完整的社会话语体系在地下室人戏谑的叙述中被打破了,并被迫开放成一个混杂的话语场域,这体现了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地下室人也通过这种话语的混杂表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自主权和“未完成性”。
三、体裁的“狂欢化”与现代性
从体裁的角度同样可以辨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反映的现代性。巴赫金对体裁不受重视这一现象感到十分遗憾,他认为体裁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诗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体裁形式蕴含着艺术家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属于“梅尼普斯体”②系统,具有“狂欢化”特点。这种梅尼普斯体将古希腊罗马的伦理规范遭到破坏、人的命运的史诗式或悲剧式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的时代之生活内容“铸进体裁形式里”,因此具有尖锐的时代特色和杂声多体的特色。同样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生活的时代,俄罗斯正经历着现代转型,一切仿佛处在门槛上,前现代的稳定社会秩序逐渐瓦解,道德规范遭到破坏,形成了宗教与哲学上无数不同派别、潮流之间的紧张斗争。那个时代像梅尼普斯体所形成的时代一样是及其多声部的,那么表现在文学体裁上不会是独白小说,而是复调的、狂欢化的文学体裁。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19世纪末充分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描写了经历现代性而动荡的社会,指出“这里一切都在骚动,什么都未定型,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里小说的对象不是社会的生活,而是社会的运动。我们所有优秀的小说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把社会的运动当作自己创作的主要对象”[12](11)。
梅尼普斯体属于严肃-笑谑领域里的体裁,狂欢化已经深入到这种体裁的形而上学内核,同时有着生成新体裁的力量。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生活,这是脱离自己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颠倒的生活’、‘反面的世界’。”[3](135)与“狂欢化”特征相关,梅尼普斯体的典型特点是在情节和哲学上进行着虚构的极端自由,冲破了界限,真理出入于马路、妓院、广场、集市、小酒馆等等。在这种体裁中,讨论终极问题是以狂欢式的相对性来进行的,打破种种壁垒,逾越一切障碍,因而具有颠覆解构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描绘的小酒馆、客厅、赌场等空间地点即属于具有狂欢化特征的体裁的典型场景。在这些场所,壁垒与界限往往被打破,真理在极端冲突中凸显。例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阿廖沙相遇的小酒馆,位于偏僻小城集市广场。在酒馆风琴声中,在台球撞击声中,在酒瓶碰撞声中,一个无神论者与一个见习修士在热烈地讨论关于信仰有无的终极问题。再例如,在《白痴》中,只要梅什金公爵出现的地方,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壁垒就会突然变得透明,个体之间便会有内在接触,甚至颠倒等级秩序,形成狂欢式的交流。小说开始于火车的三等车厢(巴赫金认为三等车厢类似于梅尼普斯体作品中的船甲板,是不同地位的人可以彼此狎昵交往的广场的替代物),在车厢里梅什金公爵遇到了罗戈任。梅什金公爵因病而长期在国外治疗,因此,他是一个脱离社会,行为不合时宜,在许多人看来十分怪诞的人物。而罗戈任的性格中也有着许多狂暴非理性的成分,欲望则是他人格的关键词。梅什金公爵以自己的真诚激发了罗戈任的交流欲望,而罗戈任以狂欢式的坦率讲述了他对纳斯塔霞·费里帕夫娜的迷恋。接下去,在叶潘钦将军的家里,梅什金公爵同样用狂欢式的方式冲破了等级的藩篱,例如他讲述了他与疯癫的玛丽的故事。甚至,他用死刑犯的故事冲破了生与死的界限(即将行刑的死刑犯是踏在生与死的门坎上),而叶潘钦将军一家被吸入梅什金公爵所创造的狂欢式氛围中。与男主人公梅什金相呼应,女主人公纳斯塔霞·费里帕夫娜同样脱离了通常的生活逻辑和生活关系,在巴赫金看来,她是个“疯子”。她渴望摆脱屈辱的状态,但是却又真诚地“热爱”着自己的屈辱,因为屈辱才能证明她自尊的力度。因此,《白痴》是围绕着两个奇异的中心形象“白痴”和“疯子”展开的,作品中的整个生活都狂欢化了,变成了“里朝外”的世界。纳斯塔霞的客厅也是一个如同广场的地方,有着混杂的人物:既有属于贵族阶层的将军,又有罗戈任周围那些醉醺醺的底层人物。而纳斯塔霞本人则扮演了连接者的角色,同时她的疯狂使所有人卷入了迅疾的狂欢氛围中。在娜斯塔霞命名日宴会上,叙述的节奏一再加快,直到顶点(如梅什金公爵挨耳光,纳斯塔霞怒焚十万卢布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部作品《群魔》中,市长夫人为给女教师筹款而举办的游艺会也是典型的广场式场所。这里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起码来了一些甚至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来自附近各县,还来自别的什么地方。这些无票闯入的混混们,一走进大厅就异口同声地打听酒吧在哪……”,“上层圈子里的人居然没有一家前来参加舞会;甚至地位稍高的官员亦付阙如……尉官的不入流的太太,省邮政局和市衙门里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女眷……”。正是在这场游艺会进行过程中,在一切混乱的过程中,原本坚固的社会壁垒被冲破了,不同的社会思潮在这里相聚并发生冲突。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代表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发表了自由主义挽歌式的演说,虚无主义者利普金嘲笑了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所宣扬的自由主义者的“美与崇高”,并试图用虚无主义理论颠覆社会基石。小市民也同时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核心人物斯塔夫罗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游艺会,但他的影响却渗透到这混乱的广场式场景中,从而将整部作品的形而上思考融入狂欢戏谑的时空体中。“在他挥霍的力量中,他的朋友们看到了俄罗斯潜在的混乱和心神错乱。人们希望斯塔夫罗金来领导,而他也在寻找负担。尽管他从未参加游艺会,但这却成为一个展示他的所有混乱的场所。”[13](60)在狂欢化体裁力量的引领下,整个游艺会成为不同思想对话、冲突、较量的话语场域。
巴赫金以历史诗学的角度来研究体裁,对体裁进行了历史溯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者,巴赫金认为体裁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创造。因此,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体裁的“狂欢化”时,他追溯了这种体裁的古代渊源。因此,俄国学者波克什茨基(Бокшицкий)在阐释巴赫金体裁分析中的古希腊罗马资源时指出:“属于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梅尼普斯体对巴赫金来说充当着一种面具作用,在这一面具下巴赫金揭示着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看法。”[14](236)巴赫金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裁的“狂欢化”特征是与作家所思考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即俄罗斯人作为主体面对着一个多声混杂的现代世界该如何应对。
四、结语
“现代性”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在现代性的多元建构中,文化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因此,不少思考“现代性”的学者在解析现代性逻辑矛盾时把文化现象作为基本矛盾的一方加以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体现出的种种探索与文化现代性相关,作为一名持“根基主义”③立场的俄国作家,他十分关注俄国社会的男男女女的悲欢、信仰、迷茫、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方面对“现代性”体验进行再现,另一方面也对作为现代性之表征的俄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思考。
在复调小说中,作者、叙述者、人物的声音同等重要,并互相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认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现代转型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是多声部的。为了表现这种现代性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也是众声喧哗的。同时,这种多声部效应表现了人的独立自主、未完成性和探索本能。当现代人类脱离了森严的秩序,当上帝不再成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和最终皈依,人类将在一个话语混杂的世界里寻找自身的价值。在体裁上,巴赫金则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与渗透了狂欢精神的梅尼普斯体一脉相承。这种狂欢精神与对话精神是相呼应的。在作品狂欢化的艺术形态中,等级森严的壁垒被打破了,不同的人狎昵交往。这是一个失去上帝的世界,也是一个寻找新信仰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颠覆性的狂欢精神对启蒙现代性的理性牢笼进行了反思。总的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里的现代性体验和对现代性的思考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是动态的。
注释:
①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当一个一直以来在某一领域起支配作用的认知范式(paradigm),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不适应,并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科学就会产生周期性危机。那时,新的范式就会被介绍进来,并促使对先前占支配地位的范式的重新评价。
② 梅尼普斯(Menippus,约活动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伽达拉人,犬儒派哲学家,以讽刺手法推广犬儒派对生活的看法而闻名。其作品包括:《降入地狱》《意愿》以及《诸神信札》,但这些作品仅存一些残篇,史书记载其原为奴隶,后被赎身,成为底比斯的自由民。
③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根基主义,中文又译根基派或土壤派,是俄国19世纪斯拉夫主义运动中离现代最近的一个社会文化与文学批评派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是该派的代表人物。
[1]Walter Kaufmann.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M].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0.
[2]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M].赵亚莉, 陈红薇, 魏玉杰, 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4]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C]//吴晓都, 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5]董晓.超越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试析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J].国外文学, 2000(2):10-13.
[6]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А.Воронского.Статьи М.Горького, Н.Бельчикова, Н. Кравцова, Шесисятники[C]. 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ая Рассия, 1984.
[7]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8]Ilya Kilger.Dostoevsky and the Novel-Tragedy: Genre and Modernity in Ivanov, Pumpyansky, and Bakhtin[J].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1(1): 73−87.
[9]齐格蒙特·鲍曼.对秩序的追求[C]//邵迎生,译.文化现代性读本.周宪, 编.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岳麟,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1]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2]弗·谢·索洛维约夫.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M].徐振亚,娄自良,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3]Irving Howe.Dostoevsky: The politics of salvation[C]//Rene Wellek.Dostoevsky: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Prentice-Hall,Inc., 1962.
[14]Бокшицкий А Л.Анакриза в тексте М.Бахтина[C]//ред.К.Р.Исупов. кн. Бахтин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ереводы,публикации, Сост., С-Пб.: Изд-во «Алетейя»,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