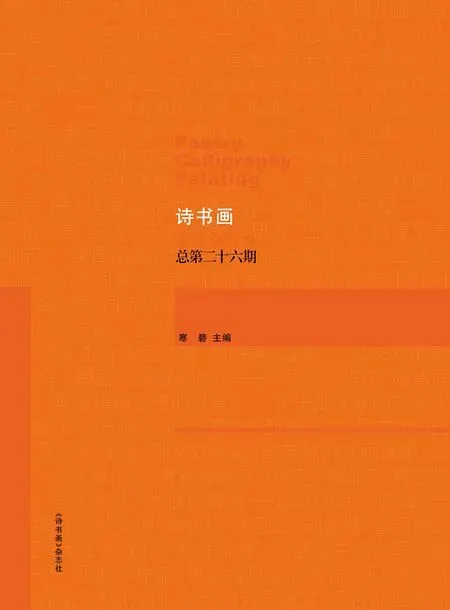纪念碑到文献,蒙太奇到拼贴
——邵文欢的自我《界破》
姜 俊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是一个重要的转换,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从而带动了生产力的迅猛推进,自一八三七年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摄影技术以来,图像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时也带动了感知形式的更新。
技术复制(die techi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和感性形式变革的问题首先是由本雅明提出。惟妙惟肖的复制技术打开了艺术创作的新世界,直到今天还规定着我们的实践。无论是机械复制还是今天的数码复制,或者是基因复制都可以认为是对于既有图形(像素、数列分布、DNA图谱)的自由编辑、复制和传播。它们被归结到一个词上—“collage”(拼贴)。
如果我们只是在中文“拼贴”的动词下理解它,就显得非常狭隘。除了拼和贴之外,collage的另一个意思是:多样事物的任意结集(any collection of diverse things)。collage本质上可以被认为是从解构到重构的过程。在此,任意图形都可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模块(module),然后便是进入“多元拼合、聚合或融合”之中,从声音到图像、从平面到空间,图像的生成将因此进入无限加速之境。
在今天,这一逻辑几乎出现于任何一门艺术的创作中。拼贴的运用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当代性格,即自由、平等和高效。正是由于工业化复制的普及和成本的不断压缩,才使得拼贴能任意和加速运作,并从平面图像扩展到空间造型之上。杜尚二十世纪初开创的“现成品”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拼贴的一种空间形式。
在邵文欢的艺术作品中除了人们一直讨论的跨媒介之外(摄影绘画),还有一个维度并未被仔细审视—拼贴中的纪念碑性。在他的作品《跌水须弥之九十方》中,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北宋巨嶂山水的纪念碑式运用,另一方面同一座山水的不同时间、角度被并置和集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文献上的陈列。
十九世纪摄影自发明不久就被用于文献记录,无论是用于人物档案,还是城市风貌采集、科学研究、案件记录,它的确协助了福柯所谓的现代治理术的转型—从前现代的纪念碑(monument)转向现代治理的文献化(document)、档案化。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归入其中,在各种文件、档案和证件中被自我标示,成为了活体管理的对象—生命政治。这也导致了感性层面和艺术创作方式的变革,同时代的印象派画家莫奈反复地绘画具有文献意义的巴黎圣母院—呈现不同的时间和光线下的单一客体。我们必须知道,在摄影归档出现之前,这一创作举动是不可被想象的。
在晚期传统中国绘画中,模块化非常清晰的体现在《芥子园画谱》中,这无疑和中国过于早熟的治理术也密切相关,在中国治史传统中文献化和档案化由来已久。当文人画成为了一种文人间高雅的交际手段后,迅速掌握一种有效的程式也成为了迫切的需求。
《芥子园画谱》作为一种图式辞典就应运而生。传统山水画中,既定图像群的反复组合构成了山水艺术千变万化的基础。它们以一种有“过渡”和“渲染”的方式施行软性的拼贴,从而达成有机的一体性,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蒙太奇手法(montage)。
如果说《跌水须弥之九十方》中的山水是摄影文献式的、是拼贴的,那么《暮生园之八》就是典型的蒙太奇(montage)了。画面的构图让人联想到《游春图》,苏州环秀山庄的巨型假山体同样也来自大量不同角度和时间拍摄的局部照片,在过渡和渲染下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统一体,有气势恢宏的纪念碑效果。纪念碑往往伴随着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如同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所写的:

邵文欢《暮生园之七》(摄影、明胶银手工涂绘感光、丙烯绘画)
“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浪漫化了。”
如果拼贴是冰冷的现代理性,它有坚硬的分界线,就如同Becher夫妇著名的水塔系列摄影那样,展现了一种文献式的中立和客观。那么相反,蒙太奇就是诗意的大叙述,并诉诸于情感维度,柔和的边缘弥合了多个渺小视角的断裂,它们共同组成的山水构成了某种崇高。
邵文欢的艺术创作回旋于文献式的理性和纪念碑式的感性之间,在这两极中存在着某种悖反和辩证。园林对于古典文人是一种桃花源式的逃逸,它补偿着都市俗务的纠缠和面对生活琐碎的苟且。儒家规制的房屋格局和道家园林的天马行空构成了最为形象的空间对比,自然仿佛在微缩山水的象征中获得了超越。在今天我们依然拥有着这一份怀旧,它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形式构成了对于不堪的现代化生活之补偿。如同福柯而言,现代社会是一种被监视和档案化的监狱群岛,那么我们同样需要纪念碑,需要诗意,需要使得卑微之物被贸然幻化为崇高的升华。
而过度的浪漫主义却终只是一种自慰,在邵文欢的作品中纪念碑似乎又物极必反的转向了文献,《暮生园之八》中央的深色长方形正打破了某种怀旧,使得纪念碑不再稳定,并摆向了在《跌水须弥之九十方》中对无数种观看和时间的并置。它们层层叠叠,某些图片不只是左右上下,甚至是前后叠加,山上的流水仿佛涓涓不息,让人联想到Eadweard Muybridge于一八八七年实施的摄影试验—运动的过程。
一种北宋纪念碑式的巨嶂在导向对于自然崇高的赞美时就被打断了,尖锐的拼贴代替了柔和的蒙太奇,反向诉说着机械式的观看、多重感知下的时间。这是一重悖反,但随即它又折向另一边,瀑布在分裂的视角中辗转汇集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在支离破碎中又统一起来,重塑着流动的和时间差异的纪念碑。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关于感性纪念碑说到:
“一个纪念碑无意于欢庆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是把由这些的事件所形塑成的持续流传的感性知觉托付给未来的耳朵。”
好的艺术回望着过去,过去在今天分解,却在明天重塑。它构成了翻转之翻转的否定辩证,统一将永远不会出现。我们可以把邵文欢的作品理解为一种反复的回旋运动—从纪念碑到文献,从文献到纪念碑,从蒙太奇到拼贴,从拼贴到蒙太奇。

邵文欢《夜空中星尘的光之一》(摄影、明胶银手工涂绘感光、铝金属)

邵文欢《霉绿04》(亚麻布明胶银手工涂绘感光、暗房冲洗、矿物色及丙烯绘画)

邵文欢《暖冬》(摄影、负像绘画、明胶银乳剂涂绘感光、丙烯绘画)

邵文欢《不明之一》(摄影、明胶银手工涂绘感光)

邵文欢《浮玉No.01》(全数字虚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