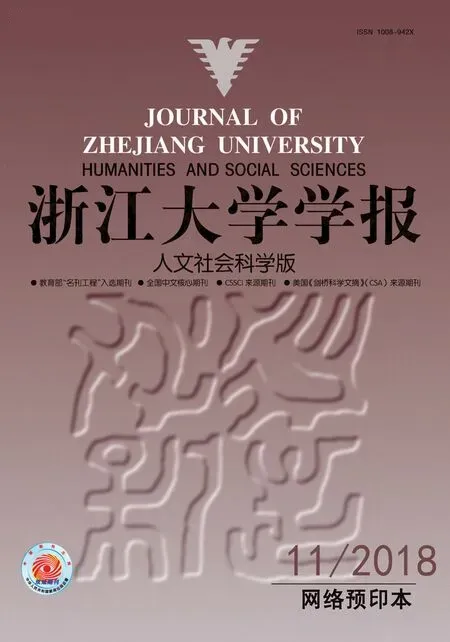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
——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陈东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清代学者在考据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少方面堪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笔者长期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阅读了大量清人文集、笔记、日记、年谱等,发现不少清代学者消息灵通,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学术信息,“闭门造车”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本文所言之学术信息主要是指新的学术信息,诸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在做什么研究,刊行了哪些新的论著,同时也包括相关学者以前尚未寓目之典籍(尤其是珍本秘册)。在那个通信、交通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的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学术信息的,当属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前的论著很少涉及这一问题,更未见关于此问题的专文。当然,一些论著的某些部分与此问题有一定的关联,如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又如:王华宝的《段玉裁年谱长编》、王章涛的《阮元年谱》和《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涉及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游;陈居渊的《清人书札与乾嘉学术——从〈昭代经师手简〉二种谈起》,着重强调了函札对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罗检秋的《士人交游与文献传播》涉及清代学者借阅图书之若干情况①[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对艾尔曼的观点有所阐发,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 1期,后收入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3180页;[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版;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扬州)广陵书社 2006年版;陈居渊《清人书札与乾嘉学术——从〈昭代经师手简〉二种谈起》,载《汉学研究》(台北)2007年第 25卷第 2期,第 265294页;罗检秋《士人交游与文献传播》,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第913页。。不过上述论著均非专门研究此问题,只是有所涉及,缺乏系统性。笔者经过长时间的考察,认为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以下详论之。
一、当面交流
当面交流最为直接,尤其在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的清代,其作用是其他交流方式无法取代的。大量的学术信息正是在当面讨论相关问题乃至闲聊中获取的。
当一些学者长时间在同一个城市时,当面交流通常较多。如道光十四年(1834)春夏,俞正燮在严州(今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期间,曾多次与许瀚①许瀚从道光十一年(1831)开始在杭州学署校文,历时三年。一同拜访当时在严州任建德教谕的严可均。俞正燮在《全三古至隋文目录不全本识语》中提到:“道光甲午春夏间,两次见其本于严州铁桥官舍,叹服其用心。日照许印林司马出所携金石拓本,彼此相勘,或改补一两字,相视大笑。”[1]卷一二,487又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朱筠由安徽学政调任翰林院编修,此后在北京的数年乃其一生中交游最广的时期。当时朱筠与纪昀、翁方纲、钱大昕、程晋芳、任大椿、戴震、姚鼐、王昶、邵晋涵、周永年、蒋雍植、章学诚、蔡嘉等著名学者经常见面并交流[2]。另据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一《跋朱性甫珊瑚木难手稿》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初八,罗聘、桂馥、吴锡麟、赵怀玉、冯敏昌诸学者在北京翁方纲的宝苏室一同观看明代朱理存(字性甫)的《珊瑚木难》手稿[3]卷三一,647。不过当时学者们在茶馆、酒楼的聚会很少,而是大多在某一位学者家中,并且总体上聚会比较少。因此聚会并非乾嘉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一点与清末和民国时期不同。
当学者不在同一城市,专程赴外地拜访同人大多是距离比较近的。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段玉裁自金坛至常州,以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嘱臧庸为之校雠;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臧庸从武进到苏州,与钱大昕、段玉裁、王昶等相见;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当时侨居苏州的段玉裁到了杭州,与丁杰相识。
因清代的交通与今天相比显得十分不便,故距离较远的异地专程拜访的事例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情况是路过某地时顺便拜访。如乾隆十九年(1754),全祖望赴扬州养病,途经杭州时,与故友赵昱之子赵一清共同研讨《水经注》。
另外,由于不少清代学者同时是官员,在赴任、离任途中,他们往往有交流。如阮元作为清代中后期号称“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元老”的封疆大吏,曾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兵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浙江巡抚、江西巡抚、河南巡抚、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内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长期在全国各地为官。在无数次赴任、离任途中,常常与师友、门生等晤面、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能够获取一些最新的学术信息。
又如,嘉庆元年(1796),桂馥获选云南永平知县,是年七月启程远赴滇南上任。是年八月,桂馥路过天津,与翁方纲等会面。嘉庆二年(1797),桂馥路过杭州,与丁杰相见时,丁杰还将梁玉绳的《汉书人表考》赠予丁杰。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一路停顿,直至嘉庆二年(1797)四月,桂馥方才到达云南②参见张毅巍《桂馥年谱》,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9-72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学者当面交流之不易。再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段玉裁由四川巫山县令致仕,返回故乡金坛途中路过南京,到钟山书院拜访了钱大昕。另外,道光元年(1821)十月,王引之赴杭州主持浙江乡试结束之后,返回京城途中路过扬州,与顾广圻见面,并将新刻的《读书杂志·淮南内篇》赠送给顾氏。
有时路过某地,由于时间有限等原因,学者不一定前往友人寓所晤面,而是采用致函的方式①因为同在一地,距离近,所以很快就可以寄到。,邀对方到其所乘之舟车中相见。如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末,阮元在赴任浙江学政途中经过苏州,因获悉段玉裁居所“距城颇远,本当亲诣高斋,奈皇华期迫,不能久延”,故致函段玉裁,并且附其近刻数篇,又碑刻一种,“谨令县中人备舆奉迓,至弟舟一谈。大著《说文读》及诸《汉读》、《诗、书小学》稿本,务必携来”[4]743。
学者相见时所获取的信息并不仅仅限于对方的学术动态,往往还会涉及他人,相互交流自己所知晓的他人的学术动态,品评他人之作。如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乾隆五十八年(1793)条提到:“钮树玉来访。先生与论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得失。”[5]931
书院也是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场所。如嘉庆年间阮元在杭州创办的诂经精舍,不仅是一所教育机构,而且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精舍创建初期,除了阮元和主讲王昶、孙星衍之外,尚有讲学之士等教学人员。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记载,当时汪家禧、陈鸿寿、陈文述、钱林、胡敬、孙同元、陆尧春、王述曾、吴文健、严杰、周诰、查揆、李富孙、孙凤起、吴东发、朱为弼、周中孚、严元照、徐养原、何兰汀、周师濂、汪继培、徐鲲、周治平、洪颐煊、洪震煊、金鹗、吴杰等著名学者都曾在精舍讲学,共计 92人[6]卷下,545-547。另外,苏州紫阳书院也汇集了一大批学者,如“吴中七子”钱大昕、曹仁虎、王昶、赵文哲、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就曾在书院一同肄业,时在苏州的惠栋作为长辈,对钱大昕等也给予了指导。书院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游幕同样有助于学术信息的获取。尚小明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中论述了幕府宾主间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幕府内的学术争论、游幕与学术传播等问题。作者认为:“在幕府内,最普遍的学术交流方式是就某些学术问题或某一方面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交换研究心得、研究信息或研究成果。这方面的例子很多。”[7]293林存阳的《乾嘉四大幕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幕府为研究对象,从中可以看出幕府乃学术交流之重要场所。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朱筠担任安徽学政,“一时人士会集最盛,如张布衣凤翔、王水部念孙、邵编修晋涵、章进士学诚、吴孝廉兰庭、高孝廉文照、庄大令炘、瞿上舍华,与余及黄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经中,亦时至”[8]289-290。另外,凌廷堪曾在谢启昆幕府中与卢文弨一见如故。
还有,清廷的修书活动,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明史》《续通典》《续通志》等大型图书的编纂,以及各省的方志修纂,均汇聚了一批学者,并且编纂时间往往较长。如负责《续通典》《续通志》《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等编纂的三通馆,就集中了钱大昕、彭元瑞、孙星衍、邵晋涵、王昶、纪昀、齐召南、陈昌齐等著名学者。学者们可以由此获取不少学术信息。
此外,参加科举考试也是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好机会。如阮元与郝懿行,钱大昕与邵晋涵、李文藻就相识于科场。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王念孙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前后,王念孙拜谒朱筠,得与朱筠弟子任大椿多有交往。复获见江永《古韵标准》,始知顾炎武所分十部尤有罅漏[9]15。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之间的初次见面大多在京师北京,后来的当面交流也大多在北京。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章学诚与戴震初见于北京休宁会馆;乾隆二十八年(1763),段玉裁与戴震在京师相识;乾隆三十四年(1769),段玉裁第三次入京参加会试,与戴震确定师生关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段玉裁与王念孙在京城首次晤面。此外,戴震与秦蕙田、钱大昕、纪昀、王鸣盛、阮元、王昶、朱筠,钱大昕与纪昀、朱筠、卢文弨、毕沅、赵翼、程晋芳、翁方纲、陆锡熊,阮元与王念孙、桂馥、邵晋涵、任大椿,陈奂与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凌廷堪与孔广森、武忆,王念孙与程瑶田,段玉裁与陈鳣等,最初也都是在北京相识的。京城的初次晤面往往对学者以后的发展乃至终身学术方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
王汝丰主编的《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收录了一百多位曾经在清代“宣南”①当时京城宣武门以南一带之泛称,大体上属于原北京市宣武区的管辖范围。居住的知名人士,包括顾炎武、赵吉士、朱彝尊、徐乾学、阎若璩、陈廷敬、汪懋麟、万斯同、李光地、查慎行、黄叔琳、齐召南、卢文弨、程晋芳、王鸣盛、戴震、纪昀、王昶、钱大昕、朱筠、毕沅、翁方纲、陆锡熊、王念孙、洪亮吉、黄景仁、凌廷堪、阮元、王引之、包世臣、陶澍、徐松、钱仪吉、陈奂、龚自珍、何绍基等[10]26-359,其中有不少是同一时期住在此地,堪称大家云集。学者生活在同一区域,交流自然多了。
此外,当时的一些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扬州等,也成为清代学者之间初次见面的地点。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段玉裁因避祸侨居苏州,在此结识黄丕烈、顾广圻、王鸣盛等,并因钱大昕与藏书家周锡瓒相识[11]222-223。据刘盼遂的《段玉裁先生年谱》,嘉庆二年(1797),程瑶田到了苏州,与侨居于此的段玉裁初次相见,“登其堂,促席论难,匆遽之间,虽未能罄其底蕴,然偶举一端,必令人心开目明”[12]462。道光十九年(1839)八月,张文虎校书于杭州文澜阁,得识胡培翚,后经胡氏介绍,在八月十七日与陈奂相识于杭州汪氏水北楼[13]393。阮元与凌廷堪、汪中等,江藩与凌廷堪的初晤之地点在扬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离开北京赴扬州,入卢见曾幕府,在此与惠栋相识并深入交流。这次晤面对戴氏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今有不少论著认为,苏州、徽州、扬州、常州乃乾嘉时期之学术中心,这固然没有问题,但当时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应该是相关论著没有提及的北京。因为所谓学术中心,应该是学术交流最为频繁、学术信息最为集中之地区,具备影响全国的实力,就此而言,北京无疑居于首位。并且,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集中于京城,有力地促进了南北学术的互动和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这一点是在其他城市难以做到的。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提出了“江南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学术信息获取是学术共同体得以逐渐形成和巩固,并且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保证。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术信息的及时、不断获取,学术共同体将是支离破碎的,甚至不复存在。学术信息的交流堪称维系学术共同体之纽带。
笔者注意到,学术共同体的地理分布并不仅仅局限于江南,北京也是清代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城的学者无论居住时间长短,大多来自江南地区,京城、江南二地的学者学脉相通,互动频繁,遥相呼应。因此,北京、江南堪称清代学术共同体的两大核心地区,而江南地区又以苏州、扬州、杭州、常州等城市为支撑点,点面结合,以点带面。这一学术共同体的范围不宜使用半径来表述,而是以核心地区为基础,同时其影响力扩散到周边乃至边远地区,从而形成疏密不一的学术网络。
当面交流尤其是多位学者集中一处交流时,信息量往往较大,内容也比较丰富。这种交流是直接的、面对面的,相关学者所获取的学术信息数量总体上应该超过函札,从而对交流双方的学术研究更容易产生影响。一些初步的学术见解通过当面切磋、碰撞而逐渐趋于成熟、完善,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者晤面时的相互鼓励、帮助、启发、质疑以及相互交换资料等皆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催化剂。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以前的某些观点存在偏颇之处,可以补充、修正。如梁启超曾曰: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则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14]64
梁氏充分关注到函札对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作用,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不过这一论述不够全面,除了函札之外,清代学者之当面交流不容忽视。
美国学者艾尔曼指出:“18世纪,考据学者接受了官方赞助,担任官员的幕宾,不论这些官员是在何时何地聘用他们。他们严肃认真地承担起编著经注、史书、方志的任务,除此之外,就在书院任教。这种学术发展模式持续到 19世纪,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突然中断学术事业发展时,才告结束……反之,学者到全国各地漫游寻找赞助时,必须具备完成其学术研究必需的专业知识,也必须随时准备校勘经籍,收集地方史志材料,校勘经史典籍中的错讹之处。而这种学术体制也为考据学者创造了相互交流、查阅善本文献、参预重要课题的机会。”[15]79艾尔曼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他所说的这种学术体制应该并非当时学者获取学术信息之主要途径。
二、往来函札
清代学者之间的往来函札大多不是一般的问候、闲聊,而往往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如段玉裁与王念孙之间有大量的函札往来。乾隆五十四年(1785)段玉裁与王念孙在京城相识之后,主要通过函札交流。胡楚生的《段玉裁与王念孙之交谊及论学》对此有较为充分的探讨[16]。
段玉裁《与刘端临第十三书》曰:“训诂之学,都门无有好于王伯申者。陈仲鱼新刊《论语古训》已成,弟之《说文》,亦写刻本二卷,嘱江艮庭篆书,剞劂之工,大约动于明冬。顾抱冲刻宋本《烈女传》,黄荛圃刻宋明道二年《国语》未成,明道本影抄在黄处,与乡时临本不同,临本失之疏略也……”[12]401这封函札字数虽然不多,但提供的学术信息十分丰富。
道光三年(1823)三月二十五日,王念孙的《答江晋三书三》内容同样很充实。在函中,王念孙对江氏在来信中所提到的问题一一作答,并专门就四声问题阐述了己见,同时还提到:“《广雅疏证》一书,成于嘉庆元年,其中遗漏者十之一二,错误者亦百之一二,书已付梓,不能追改,今取一部寄呈,唯足下纠而正之。”[17]89
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致函孙星衍,就孙氏《问字堂集》提出若干商榷意见[18]9-12。嘉庆十四年(1809)十一月十三日,郝懿行致函王引之,其中有云:“某近为《尔雅义疏》,《释诂》一篇,尚未了毕。”[19]卷一,5238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臧庸致函王念孙,就《小学钩沉》相关之三个问题请教王氏,王念孙随即复函,阐明自己的观点。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王引之致陈奂函中曰:“《荀子杂志》已刻完两卷,大约明年夏秋间方可毕。拙刻《经义述闻·通说》已刻一卷,弟二卷须俟正、二月方可蒇事。”[20]卷四,395道光十年(1830)正月二十五日,王绍兰致王引之函中曰:
向尝从事《说文》,实无心得,自茂堂大令书出后,早经中辍,今惟取其阙者补之,误者订之,谓之《说文段注补订》,已积有百余条,但段书可商榷者尚不止此,当再为之卒业。然亦不能自信果否?此是彼非。俟暇日录寄,以求折中焉可耳。袁宏《后汉记》补证三十卷,业经脱稿,尚未付抄。[21]181
这类函札有时很长,其内容往往厚重、精彩,有些类似学术论文。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戴震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撰写了长达六千多字的函札《答段若膺论韵》[22],涉及古音学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将古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堪称戴震关于古韵分部最重要的成就。此后,鉴于《答段若膺论韵》学术价值甚高,段玉裁将其置于孔继涵刻《戴氏遗书》中的《声类表》卷首,并为《声类表》这部戴震考证古音的绝笔之作写序。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四十二年(1777),戴震、段玉裁论韵达15年。戴震去世后,嘉庆十七年(1812)段玉裁结识江有诰,又继续讨论古音问题[23]。而这些讨论大多是通过函札进行的。函札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近期对方的研究内容、学术观点等,这样的交流对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极有助益。
此外,收入中华书局1980年版《戴震文集》卷三的《与王内翰凤喈书》《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与卢侍讲召弓书》《再与卢侍讲书》《答江慎修卢侍讲书》,卷九的《与是仲明论学书》,中华书局1998年版的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三的《与焦里堂论路寝书》《与胡敬仲书》《与阮伯元阁学论画舫录书》,卷二四的《答孙符如同年书》《与孙渊如观察书》《复钱晓徵先生书》,卷二五的《与阮伯元侍郎论乐书》《与阮中丞论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的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六的《答丁小山书》等,篇幅都较长,学术含量甚高,相当于一篇专文。
当学者身处边远地区时,当面交流不便,更加依赖函札往来。据《雷塘庵主弟子记》(即《阮元年谱》)“道光九年己丑六十六岁”条记载:“十二月,粤东将刻成《皇清经解》,寄到滇南。福案:是书大人于道光五年在粤编辑开雕,六年夏,移节来滇,乃嘱粮道夏观察(修恕)接理其事,严厚民先生(杰)总司编集。凡书之应刻与否,大半皆是邮筒商酌所定。”[24]165
函札也有托人转递的。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王念孙在《与刘端临书(三)》中有云,“若膺、容甫札俱祈转致”[25]卷四,153。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二十七日,顾广圻《致王引之书(二)》曰,“献岁由南雅学士付下手书”[21]408-409。
较之于准备公开的序跋,当初无意公开的函札时常指出对方论著的不足之处。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钱大昕的《与段若膺论尚书书》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中今古文经字的划分提出不同见解[26]卷三三,539-540。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臧庸在《与段若膺明府论校尔雅书》中,跟段玉裁商榷段氏所校《尔雅》疏误之处[27]卷二,123-124。嘉庆十四年(1809),段玉裁的《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指出黄丕烈所刻《孟子音义》中的误字[12]84-85。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九日,宋翔凤致函王引之,将自己关于《尚书》的最新研究心得与王氏讨论。王引之对宋翔凤的卓见十分认可,将这封篇幅长、学术性强的函札略作改动并题名为《某孝廉书》,收入《经义述闻》[28]卷四,264-269。
与当面交流类似,函札也会涉及他人的学术动态,评价他人之作。如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二十日,焦循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中说:
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黜明、阎潜邱。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29]卷一三,245-247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对清代著名考据学家进行了点评,可以视为重要的学术信息。
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十一月,段玉裁在致孙星衍函中提到,陈鳣的《郑康成年谱》引用了《唐会要》和《孝经正义》中关于郑玄自序之材料,而未引其所本的《文苑英华》所收的刘知幾《孝经老子注周易传议》。段玉裁谓此乃“逐杪而忘本,泳沫而忘源也”[12]卷五,100。嘉庆十四年十一月,段玉裁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中用两千多字详细论述了自己对赵一清、戴震《水经注》相袭之事的看法,极力替其师戴震申辩[12]卷七,172-174。道光元年(1821)八月,王引之《致王绍兰书(一)》[20]卷四,392和《致王绍兰书(二)》[20]卷四,392-393以及王绍兰《致王引之书(一)》[21]161-162中,均提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某些疏误。道光十年(1830),王引之在《与陈奂书(七)》中提到:“段茂堂先生《诗经小学》考订精审,而所引它人之说间有不足存者。如王中丞汝璧之解‘日居月诸’,穿凿支离,而乃见采择,似择焉而不精矣。想尊著内必不守此曲说也。金诚斋考订三礼,颇为精核。”[20]卷四,396
有的函札还蕴含着重要的学术理论。如卢文弨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辛丑)》中指出:“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板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徧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30]卷二○,389此系精湛的校勘学理论,乃卢氏长期治学经验之总结,堪称厚积薄发,非常值得重视。
通过函札往来,清代学者可以较快获悉对方最近在从事哪些研究。这在当时是简单、经济、有效的信息交流方法,有时比当面交流更加深入、具体。并且,不少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是在函札中首次公布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函札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对乾嘉时期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助益极大。并且,函札往来不受地域、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堪称流动的学术媒介,在本文所提及的五种学术信息获取方式中最为便捷。
清代学者函札数量十分庞大,其中大部分未收入相关文集并刊刻,而以各种方式经过整理点校后公布的,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清代著名学者刘文淇的后人曾于1984年将珍贵的《青溪旧屋尺牍》(计2409页)和《通义堂尺牍》(计2153页)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收藏。《青溪旧屋尺牍》系刘文淇与225人之间的函札,《通义堂尺牍》系刘毓崧与241人之间的函札,二者合计5000余通,价值甚高,目前正在由海峡两岸的相关学者进行整理识读,准备正式出版。我们热切期待更多的这类函札能够尽早与读者见面,这对本文所涉及之问题的深入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
三、撰写序跋
清代学人的著述一般都有序跋,大体上可以分为诗文集之序跋、学术著作之序跋,其中学术著作之序跋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往往比函札更加系统、深入。序跋除了对相关著作进行评价之外,有时还会就某些学术问题做进一步发挥。一些学术著作有多篇序跋,其中不少出自名人之手。如阮元等撰集的《经籍籑诂》,分别有王引之、钱大昕、臧镛堂(即臧庸)之序;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分别有宋翔凤、胡珽之序;凌廷堪的《校礼堂文集》,分别有卢文弨、江藩之序;刘淇的《助字辨略》,分别有卢承琰、国泰之序和刘毓崧之跋。
清代学者、文人在著作完成之后往往会向友人索序。如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二日,段玉裁在《致王念孙书(二)》中有云:“《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21]17于是有了后来著名的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该序共计439字,言简意赅,堪称清人序跋的典范之作。同时,段玉裁的《广雅疏证序》、阮元的《经义述闻序》、钱大昕的《廿二史札记序》等字数也不多,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阮元作为清代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一生中为他人著作撰写了大量序跋,如为段玉裁《周礼汉读考》、王引之《经传释词》所撰之序,学术性极强。又如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十五日,王念孙读臧庸《拜经日记》毕,为之作序。此外,桂馥的《说文统系图》,程瑶田、卢文弨、翁方纲、张埙等多位学者为其作了题跋。
作序者大多可以在索序者的学术著作完成之后、刊布之前,利用作序的机会,在第一时间先睹为快,成为相关学术信息的首先获取者;而索序者常常也可以从刚刚撰写完毕的序中了解新的学术信息。如嘉庆二十年(1815),王引之将自己的力作《经义述闻》之手订全帙寄给阮元,阮元将其交给南昌卢宣旬刊刻,后来又为该书作序。
学者之间常常相互作序。如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六日,卢文弨为凌廷堪作《校礼堂初稿序》;同年,凌廷堪为卢文弨撰《仪礼注疏详校》写序。
清人论著中还有一种体裁是“书后”,这是题跋的一种,相当于读后感,类似于现在的书评。“书后”大多比序跋、函札更为具体、深入,往往会对原书做一些补充,有时还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如王念孙的《六书音韵表书后》、顾广圻的《书毛诗故训传定本后》、方东树的《书徐氏四声韵谱后》、江藩的《书夏小正后》、胡培翚的《仪礼集释书后》和《仪礼经注校本书后》等,各有千秋,价值甚高。
清人文集中,序跋等往往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共计三十卷,主要内容是序跋、函札以及传记、墓志铭、题辞、对策等,其中序五卷,跋九卷,书(函札)五卷。但这并不等于说《抱经堂文集》的学术水平不高。正如王文锦在其所点校的《抱经堂文集》之“前言”中所云:“卢氏的序跋书信,在文集中占很大比重,这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作者古籍知识丰富,见解高明,特别是他的校理经验,最值得注意和借鉴……卢氏的经验之谈,对今天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很有指导意义,不能忽视。”[31]前言,3-5整体而言,《抱经堂文集》堪称清代一流学术文集,笔者在主编《卢文弨全集》之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
毋庸讳言,作序者与原书作者基本上是友人或师生关系,因此序中有时不乏溢美之词。不过,这并不影响相关学者及时获取学术信息。
四、购买、借阅图书
清代学者大多本身拥有较多藏书,主要靠自己的藏书获取相关学术信息,同时也注重利用他人的藏书。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朱彝尊以及乾嘉学派中的吴派代表人物惠栋曾大量购书,收藏甚丰。一些贫寒的学者如汪中、周永年等也节衣缩食,想方设法买了不少书,以便及时获取学术信息。许瀚《涉江采珍录》记载了他所购买的大量典籍,有的还具体注明购买处所、时间及支付的书款等。如:“仿宋《韩非子》二十卷附顾广里《识误》三卷,四册。辛卯腊,二十八日,苏州阊门买。京钱千文。”[32]1
朱彝尊除了大量购书之外,还抄录了大量书籍。他在京参修《明史》期间,经常从史馆借抄,并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塘龚氏、宁波范氏等明末清初的藏书世家。历年所抄达三万余卷,占其全部藏书的近四成。又如钱大昕的个人藏书并不是太丰富,但他在治学过程中曾多次向黄丕烈、袁廷梼、卢文弨、周锡瓒、顾之逵、戈宙襄、严元照、何元锡、刘桐、吴骞等人借抄图书[33]卷一,527-557,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学术信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善本钱大昕未曾寓目,从而使其个别考证的精确性稍受影响。如傅增湘在为张元济的《校史随笔》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窃惟史籍浩繁,号为难治。近代鸿著,无如王氏《商榷》、钱氏《考异》、赵氏《札记》。三君皆当代硕儒,竭毕生之力以成此书。其考辨精深,征引翔实,足为读史之津寄。然于疑、误、夺、失之处,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籍,咸能推断,以识其乖违,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则以未获多见旧本,无所取证也。第旧本难致,自昔已然。钱氏晓征博极群书,然观其《旧唐书考异》,言关内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似于闻人诠本未全寓目。明刻如此,遑论宋、元。[34]序言,1-2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纠正了正史刊本中的诸多讹误,水平甚高。然而,由于他们未能见到更多的宋元善本,致使个别考证失误①参见张元济《校史随笔》“金史·考异所指有误”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8-139页。。同时,钱、王凭借个人学识指出的《五代史记》时本中的某些错误,在张元济所见之宋庆元刊本中不误,并且尚有不少未及指出者②参见张元济《校史随笔》“五代史记·钱大昕考异所指此不误”条、“五代史记·王鸣盛商榷所指此不误”条、“五代史记·时本讹夺多可纠正”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 119-122页。。从某种意义上说,钱、王的上述考订变成了无效劳动。如果他们当时能见到更多的宋元善本,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的质量也将更高[35]。这一事例从反面说明了学术信息之于考证的重要作用。
学者之间还相互借书,如朱彝尊与王士禛之间就是如此。当然,也有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出借藏书(尤其是珍本秘籍)者。如段玉裁在《与刘端临第三书》中提及:“黄韶圃孝廉所购宋本好书极多,而悭不肯借,殊为可憾。”[12]393这同样也从反面说明了学术信息之于研究的重要意义。
清代学者利用官方藏书获取学术信息的情况不多,所占比重甚小。这与当时官方藏书数量有限并且集中在重要城市(尤其是京城),难以被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包括不少乡村)的学者利用直接相关。同时,与今天相比,学者治学所需要的资料数量有限,在很多情况下利用自己的藏书就已经够了。还有,在交通不便并且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当时,学者要靠利用图书馆为主来治学也不现实。因此,在当时图书馆并非治学之必需。而进入民国时期,直至20世纪末,各类论著与清代相比呈几何级数增长,并且此时学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图书馆的重要性显得十分突出。近年来,随着数据库、电子书的大规模普及,E时代的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大大改变,图书馆(此处指实体图书馆)的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清代学者购买书籍主要是通过固定书铺,也有部分书籍购自临时书摊、流动书船等。北京琉璃厂堪称当时固定书铺最为集中之地,无论是常住京城,还是临时赴京的清代学者,琉璃厂往往是他们的必到之地。翁方纲在四库全书馆供职期间,通常是上午校阅图书,午饭之后便携带应考证之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查。另有钱大昕、朱筠、桂馥、丁杰等四库馆臣,也经常与翁氏一同去琉璃厂访书。可见琉璃厂书肆乃参与《四库全书》编纂之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渠道。
像琉璃厂这样的学者经常光顾的书店街既是购书之处,也是学者晤面、交流之场所。此处还留下了中外学者交流之史实。如黄丕烈就是于嘉庆六年(1801)在琉璃厂陶正祥、陶珠琳父子经营的五柳居书坊,与朝鲜著名的“北学派”代表人物和“诗文四大家”之一的朴齐家(1750—1805)结识的[36]。
同时,人文荟萃的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也是书铺林立,为清代学者及时获取学术信息提供了很大便利。
书肆中不但有学者之间的交流,还有学者、店主之间的交流。清代书肆主人由于每天接触各类典籍及学者,耳濡目染,在学术信息方面有时比学者还灵通。他们往往知道某位学者喜好某类书籍,另一位学者最近关注哪些书、做哪方面的研究等等。因此,与店主的闲聊,也常常使学者多少有些收获,甚至知晓意想不到的重要学术信息。此外,少数学者还充分利用在书肆当伙计的机会,刻苦学习,搜集资料。如年仅十四岁就进入书店当学徒,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汪中即为典型代表。
此外,为他人刻书期间通常可以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如阮元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曾经刻印了钱大昕《三统术衍》三卷、孔广森《仪郑堂文集》二卷、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十卷、胡廷森《西琴诗草》一卷、张惠言《周易虞氏易》九卷和《周易虞氏消息》二卷,以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其中一卷)等多种当时学者的著作。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阮元自己也及时获取了宝贵的学术信息。
不过,当学者在边远地区时,购买或借阅图书较为困难。如嘉庆九年(1804),桂馥《上阮中丞书》提到:“馥所理《说文》,本拟七十后写定,滇南无书,不能复有勘校,仅检旧录签条排比付录。”[37]卷六,697
五、相互赠书
如果说一般的传世典籍主要来自于购买,那么新近刊布的同时代学者的著作除了购买、借阅之外,学者之间的相互赠送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著名学者获赠的机会更多,这使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读到同行的著作。《经义述闻》堪称一部大书,王引之将其赠送给翁方纲、段玉裁、朱彬、王绍兰、焦循、阮元、许宗彦、陈寿祺、张澍、陈奂、许瀚等多位学者。部头不大的著作,赠送就更为普遍了。
赠书可以有多种方式,有拜谒时当面赠送的,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冬,王引之拜谒翁方纲,以所刻《经义述闻》就正,翁方纲“览至《周易》‘噫!亦要存亡吉凶’一条,以读‘噫’为‘抑’,为不易之论。又告以说经当举其大者”[20]卷三,391;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鲍廷博将《知不足斋丛书》一至五集赠送给同在杭州的卢文弨。也有托人转递的,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初四,许宗彦致函王引之,谢春岁经由阮常生转递书信及馈赠《经义述闻》;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三月间,陈寿祺接到经由孙尔准转递的王引之赠送的《经传释词》;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王念孙在致朱彬函中告之收到由其子朱士达转递的书信及赠送的大著《礼记训纂》,王氏读之以为有功经学甚巨,唯有献疑者数处,故附签28条寄示朱氏求正[9]321-322。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十年(1830)九月,王引之在《与陈奂书(八)》中说:“《仪礼管见》及致胡主政书已送交。《管见》学力深而用心细,实不可少之书,便中仍望见赐一部。”[20]卷四,396可见王引之利用为陈奂转递陈氏本人所著《仪礼管见》及书信给胡培翚之机会,先睹为快,趁便希望陈奂也赠送一部给自己。
因为当面赠送和托人转递的机会较少,所以赠书更多是采用邮寄的方式。赠书往往伴随着函札往来。如:嘉庆八年(1803),阮元寄赠《经籍籑诂》《浙江图考》给凌廷堪;嘉庆十一年,阮元寄赠《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给黄承吉;道光十年,王引之将王念孙的《荀子杂志》寄送给陈奂。
邮寄时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就是并非著者本人寄出,而是经过著者委托,从著作的刻印地直接寄出。这在当时可以节省不少费用和时间,也更有利于受赠者及时获取学术信息。如段玉裁《致王念孙书(三)》云:“拙著《说文》,阮公已为刻一卷,曾由邗江寄呈,未知已达否?”[21]20
托人转递和邮寄(不含从刻印地寄出者)一般同时附有函札,这样的函札大多涉及与所赠之书相关问题的探讨,因此学术含量往往很高。受赠者也大多有复函,除了致谢之外,主要篇幅通常是对所赠之书的评价以及相关问题的阐发、补充、商榷等,当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张澍收到王引之寄赠的《经义述闻》和《广雅疏证》后复函王引之时提到:
曩岁作《姓氏五书》,内有《姓氏辩误》二十六卷,讨论前人言姓氏之舛错者,妄自谓精审。而阁下《经义述闻》中颇言及姓氏,往往与愚说不合。窃又自疑其说之未必当,恨无由面质之于大雅也。兹略举数条言之,冀得是正为幸……凡此数端,虽于经义无关,然实事求是,则阁下之说或有未谛当者,敢献其疑,并望恕其直而教之以所未闻焉,则幸甚。[38]卷一五,600-601
关系特别密切的学者还有机会获得挚友赠送的珍贵的初印本。如阮元《与王伯申书一》曰:
蒙示《经义述闻》,略为翻阅,并皆洽心,好在条条新奇,而无语不确耳。见索拙论曾子一贯之义,详在《诂经精舍文集》内。今以一部奉寄,其言“邮表畷”似亦有可采者。拙撰《曾子注释》出京后又有改动,因今年正月鸠工刻雅颂集,工已集而书未校写。不能众工闲居,因即以此稿付刻,其实不能算定本,其中讲博学一贯等事,或可少挽禅悟之横流。至于训诂,多所未安,顷翻《经义述闻》“勿”“虑”等训,尚当采用尊府之说,将板挖改也。《注释》一本呈览,初印不过三十本,概未送人,乞秘之,勿示外人,缘将来改者尚多也。[21]223-224
这段文字内容丰富,除了涉及《曾子注释》初印本之外,还可以获悉阮元翻阅王引之赠送的《经义述闻》之后,觉得《曾子注释》中的个别训诂当采用《经义述闻》之说,故函中有“将板挖改也”之语。此例充分表明了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性。另外,初印本之赠送者未必都是著者本人,有时也可以是刊行者。如嘉庆九年(1804)六月,冯鹭庭将其刚刚刊刻的惠栋的《后汉书补注》寄赠给阮元[39]卷七,385。
赠书不仅仅限于刻本,还有稿本、未定本等。如道光十年(1830)十一月,朱彬致函王念孙,并呈上刚有成稿的《礼记训纂》①参看朱彬《致王念孙书(五)》《致王念孙书(六)》,见赖贵三编著《昭代经师手简笺释——清儒致高邮二王论学书》,(台北)里仁书局 1999年版,第45-48页;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19-320页。。又如,陈奂《师友渊源记》有如下记载:
江讳沅,字子兰,一字铁君……若膺师著《经韵楼文集》未定本,切属弗借予人。奂私心选录,加小圈以为记。若膺师曰:“子兰何复借予人邪?”师猝无以应,唯曰:“我馆陈徒好书,或者是。”若膺师指示圈记乃曰:“果是陈徒,陈徒读书种子也,吾将往见之。”奂因是得识若膺师。[40]200
这段文字说明了段玉裁将《经韵楼文集》的未定本给了江沅,陈奂因从江沅受学而得以选录该未定本,获取了从业已刊行的著作中无法获取的学术信息。同时,段氏“切属弗借予人”,也可以理解,毕竟是未定本。
赠书并不仅仅局限于本人的著述,也包括他人作品。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邵二云以先生(引者按:指段玉裁)《韵谱》稿本示钱竹汀,竹汀以为凿破混沌,为制序”[41]460。乾隆五十九年(1794)春,阮元致王引之函中提到:“兹渎者,在山东寻得吴中珩《广雅》本,特为寄上老伯校正《广雅》之用。”[21]270道光元年(1821)八月,王引之致函王绍兰:“两承芳讯下颁,并快读尊著,及拜赐《经韵楼集》。”[20]392道光十一年(1831)春,陈寿祺致王引之函附有其子陈乔枞的《礼说》和《毛诗笺说》之书稿。再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五月间,阮元致王引之函中曰:“春间,曾将吴中珩《广雅》本寄上,未知曾收到否?曾校毕否?”[21]244这应该是阮元将吴中珩所校的《古今逸史》本《广雅》寄赠给王引之,供其父王念孙撰写《广雅疏证》时使用。当时阮元正在山东学政任上,此函是从济南发往北京。这说明当时函札传递时间较长,有时也存在邮寄过程中遗失的情况。
另有代他人索书之事例。如嘉庆元年(1796)元月初九,段玉裁《与邵二云书二》有以下内容:“苏州有博而且精之顾广圻,字千里。欲得尊著《尔雅疏》一部,望乞之为祷。即交小壻邮寄可也。”[12]389又如王引之在为《读书杂志》中的顾校《淮南子》各条所撰之说明中提到:“岁在庚辰,元和顾涧蘋文学,寓书于顾南雅学士,索家大人《读书杂志》。乃先诒以《淮南杂志》一种,而求其详识宋本与《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订是书之讹,为家刻所无者,补刻以遗后学。数月书来,果录宋本佳处以示,又示以所订诸条。其心之细、识之精,实为近今所罕有。非熟于古书之体例而能以类推者,不能平允如是。”[42]2498这段文字充分反映出索书、赠书带来的及时的学术交流。
也有当初有幸见到了某书,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及时获取并利用的情况。如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岁”条记载:“是年玉裁入都会试,见先生云‘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谓《孟子字义疏证》也。玉裁未能遽请读,先生没后,孔户部付刻,乃得见,近日始窥其阃奥。”[43]附录,228
六、结 语
清代学者总人数有限,做相同领域研究的则更少,学人圈较小,并且做相同领域研究的学者往往互有联系。再者,当时学术著作数量也不多。因此,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与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相适应。以上五种获取方式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信息获取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状态。中国古代十分讲究师生关系,同门联系较多。不过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学者的交流绝不仅仅局限于同门。不同学派、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之学者相互获取学术信息,大大开阔了视野,从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而系统的、立体化的清代学术圈。多样且较为有效的学术信息获取方式,使得清代学术圈的范围扩大了,联系增多了,交流丰富了,活力增强了。此类纵向、横向相结合的知识群体互动也促进了知识传播,对清代学术的发展颇有助益。
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的重复性和片面性,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段玉裁开始撰写《说文解字读》,王念孙也在同年开始为《说文》作注。当王氏完成两卷之后见到了段氏《说文解字读》,为了避免重复,于是不再继续作注了。这一点对崇尚考据学的乾嘉学者尤为重要。当时的学者普遍重视实证研究,从而很关注学术研究中的发明权。学术信息的及时获取显然有助于学术规范的建立和自觉遵守。
总体而言,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够及时获取学术信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相对完备的函札传递渠道,同时也得益于当时发达的私家藏书体系。不过,清代的交通相对于现在还是极不便利的。即便是距离不远的邻省邻府乃至邻县,交流都不太方便,更不用说相距数百里乃至上千里的两地。因此,当学者处于偏僻地区时,学术信息获取有时是比较困难的。同时,由于条件所限,清代学者学术信息的获取在总体上未能系统化,尤其是尚未进入核心学术圈的中底层学者及初学者等,难以及时获取相关学术信息。因此,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