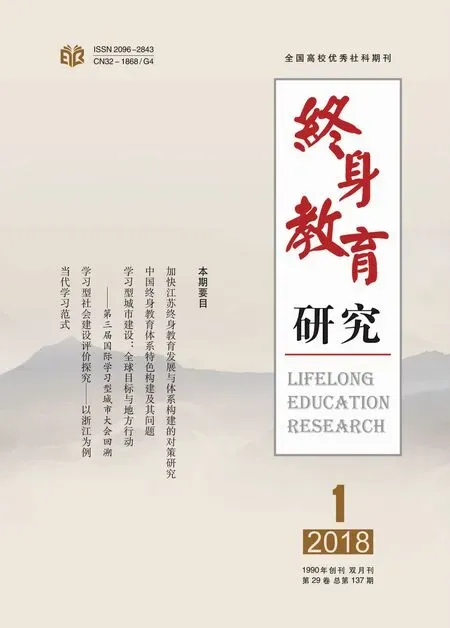当代学习范式
□ 文/杰克·麦基罗 □ 译/朱 莉
学习的意义取决于一套假设。学习理论必须根据这些假设来理解,但也要考虑到与那些学习理论本质和功能有关的假设。在漫长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理性、语言和发展等概念正经受挑战,而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具有争议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概念正经历着重大的转变。
作为成人学习的一种批判性理论,质变理论提供了一种辩证的综合和第三种选择,以全新的方式审视学习和学习理论的本质。[1]本文对这三种范式语境的原则和假设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将质变理论作为一种学习理论,阐述了其与学习所在的地方文化之间的现实关系。
一、客观主义范式:西方理性传统
John Searle认为,西方理性传统主要建立在以下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1)现实独立存在于精神和语言的表征世界,如信仰、经验、陈述和理论。
(2)语言的功能之一是演讲者传达给听众,实现有意义的交流,交流的意义包括世界上那些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事物。真理代表着准确性。陈述就是试图描述事物的状态。如果世界上的事物正如人类所说的那样,那这些陈述都是真的。
(3)知识是客观的。它来源于又独立于某一特定研究者的主观态度和感觉。“问题的关键在于,主张的客观真实或虚假陈述完全独立于发起者的动机、道德甚至性别、种族或民族”。[2]66
(4)逻辑和理性是关联的。其主要包括两种原因:从理论上看,逻辑的目标在于寻求什么是合理的信念;从实践上看,理性的目标在于寻求做什么才是合理的。逻辑是概念的核心。程序、方法、标准和规则只能在给定的一系列定理、假设、目标和客观事实的语境中运行。
(5)智力标准不是随意的。智力成就和卓越行为涵盖了客观和主观的有效标准。部分“客观的”标准独立于标准应用者的个人情感;另外一些主观的标准,则体现了人类情感广泛分享的特征。[2]
在西方传统中,学习和认知世界对于学习者来说是敏感的,或者说学习者对客观世界的反应是敏感的。学习和认知系统是行为产生的关键。行为能够实现“可适应的”拓展,通过所学到的东西与现实和行为相匹配。语言由认知引导。如果语言的范畴反映了认知系统结构,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认知系统结构有关联,认知系统就能够真实地反映世界,我们就会实现交流,理解知识。语言传递知识,但不构成知识,它是表达个人认知状态的载体。教育过程是为了传达真实世界的准确表征,并最好通过科学测试来实现。
上述立场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观点,即关注自由、责任和理性的判断——谁的声音应该被倾听、谁应该得到奖励、应该教什么以及禁止什么,应该根据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和普遍的标准,由所有知情的、客观的和理性的人来决定。根据Henry的观点,“有些思想比其他的思想好,有些价值更持久,有些更普遍。有些文化,虽然我们不敢评论,但比别的文化更有成就,因此更值得学习。”[3]
二、解释主义范式:认知革命
西方理性传统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时期。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个人的基本能力——即个人的组织、选择、参与或以其他方式对特定环境采取行动的能力。[4]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语言发展论的批判打响了“认知革命”的第一枪,在后者看来,学习一门语言最基本的是要考虑学习者先天的语言能力。[5]这一研究以及其他人的工作,促成了肖明和格根所称赞的“认知革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与世界接触对于思维结构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结构对于自我倾向延续的重要性。
维果斯基认为,认知范畴本质上具有社会性,是嵌入式的思维形式。所以,理解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生物行为;它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人认为,个人认知可被理解为公开地分享话语的内在产物。[4]
正如巴格诺尔所言:“人类的知觉聚焦于从我们已知的、期望的、潜在的意识中感知任务。鉴于这些要素存在不可调和的规范性,我们也无法将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完全分开,事实甚至可以简化为价值。所有的信念,是以视觉、知觉和语言的框架为中介的,所有的知识相对于它那一代的环境而言被认为是暂时的。”[6]
现象学家借鉴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成果,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如果经验主体和经验客体割裂开来,无疑具有误导性。这是因为,经验主体具有自己的参照框架,这是构成经验的一个整体要素,但是要了解他人,就必须获得他们的生活经验,以澄清和阐明他们的解释方式。
作为对传统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解释主义——即对文本意义的研究,拓宽了话语聚焦的范围和解释性理解的发展。在社会学研究中,符号互动主义和人类学已经发展为其他的“质性”研究方法,用来研究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传统进行强有力的批判,试图解构传统,[7-9]福柯展示了社会现实是如何被统治者、权力以及影响力的性质和支配所定义的。[10-12]除他们以外,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的工作,都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快速商品化的广泛关注,及其对元叙事产生深刻质疑,包括理性和话语的概念。[13-16]对于部分人来说,上述论断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理念,即在语言游戏的环境中,真理必须被理解,而这些规则往往由某些本地玩家制定。真理成为一种偶然的、独特地方文化的简述。被视为启蒙运动产物的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等这类普世价值,在这些批判者看来,体现出现代化的失败,其根源与西方文化息息相关。
社会认知主义者认为主体性、意向性和学习是生命形式和语言体系的功能,它们是被语言学所揭示世界中的元素。这个世界主张地方特色的真实性、话语性和有效性。研究假定了意义结构的内在社会性质、思想范畴的历史和文化的可变性,以及它们在社会和物质再生产的变化形式的相互依存度。
在近期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世界人权会议上,40个亚洲国家批准了一份声明,声称正义和公平的标准应该受到“地区特色和各种历史、文化及宗教背景的影响”。《纽约时报》1993年6月13日一篇标题为“结束酷刑而不是殖民主义”的社论写道:有7个国家试图将人权重新定义为“西方人权”。
对于许多挑战理性传统的人来说,理解存在于用来描述或解释世界的语言中,而不是外部世界本身。语言包括对特定的事实、时间和空间进行概括,从而使“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另一个像自己的具有代理意识的人有关)成为可能。
语法和语义为语言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结构。字典里对人类特征的定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理想化的语义抽象,成为人们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人与世界的知识和信息都嵌入在语言的媒介中。我们在本质上是理性的。
文字通过社会交换词汇之间的关系、意义图式或“语言游戏”来获得意义。因此,语言的起源、使用和含义都是完全社会化的。现实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并不独立于社会行为而存在。语言能够使人际关系更理性化,文化生活更合理化,对他人的表达更有感染力,能够使我们对事物作出判断。
综上所述,认知革命产生了一种争论,即人类总是具有本土性、短暂性、局部性、具体性、目的性、主观性或普遍具有理性。
批评理性传统的人会问,如果认知结构会限制和歪曲我们对经验的理解,那么怎么才能突出学习和教育比现有形式的具体文化更具有重要性呢?教育工作者如何才能真正地将不符合现有理解的事实与文化相融?文化永存的途径就是通过学习来获得理解。文化定义的参考模式构成了学习者区分、整合经验的方法和形式。学习是一个使人更加充分认识到文化定义的参考模式或者说是获取新的文化意义范式的问题。
三、解放主义范式:质变理论
质变理论是成人学习的一种进化理论,以它目前的思想主张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12个关键命题:
(1)学习理论应该被定义为一般的、抽象的和理想化的模型,可以解释学习过程中的一般结构、维度和动力学,对于以行动为导向的成人教育者来说是有用的。一种学习理论应该建立在人类交流的本质上。人类交流和学习过程的核心就是在我们的解释和信念上寻求一致。
(2)学习被理解为使用先前的解释来指导某个人对未来行动的经验进行重新解释,或者解释某个意义修正的过程。
(3)我们通过图像和符号模型的投射来创造意义,也就是基于先前的学习,基于我们的感官经验,用类比来解释新的经验。
(4)建构意义的命题是有意的、命题性的(无意的、偶然的)或表象的(当我们辨别或感受存在、运动方向、运动经验时,不必使用言语)。[17]
(5)感官知觉通过参照框架来进行过滤,参照框架通过倾向于我们的意图、期望和目的,选择性地塑造和界定认知与感觉。
(6)参照框架由两个维度组成:一是意义观点(思想习惯),包括广泛的、广义的、定向的倾向;二是意义图式,由特定信念、情感、态度和解释性的价值判断组成,并相应地形成某种解释。一个全面发展(功能多样)的参照框架应该具有:包含性;区分性;可渗透性;批判性;经验整合性。[1]
(7)信念是用于指导行动的一种习惯。信念在概念中变得明确。任何以信念为指导的行动也是对该信念的考验。当信念所指导的行为(以及阐明它们的解释)在实践中失败或因不断变化的情况存在问题时,我们的参照框架可能会通过对其假设的批判性反思来改变。寻求对批判性反思的解释、信念、可能性和潜能的认同,被视作为成人学习过程中的基本概念。
(8)学习往往通过阐释现有意义图式、学习新的意义图式、变革意义图式或改变意义观点来发生。变革往往是划时代或重大的突破。文本解构或重新定义面向任务的问题涉及“客观重构”,调整自身功能失调的参照框架,及认识“主观重构”的必要性。当然,最重要的改变是自我批评。
(9)工具性学习,即操纵、控制环境和其他人的学习;交流性学习,即了解别人与你交流意图的学习。这两种学习目的不同、逻辑起点不同,以及信念的验证模式不同。[18]
(10)在工具性学习中,我们通过实证研究来对那些不确定信念给予有效回应,从而验证真理——即一种被称之为断言的真理。在交流性学习中,我们通过批判传统、权威、暴力或理性的话语来确定问题信念的原因。话语包括对客观原因、证据与论据等要素的知情,客观、理性和直觉的评估,并获得初步的、协商一致的和最佳的判断。达成共识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需要更广泛的参与者参与审查。人类交流的本质意味着话语处于理想状态(成人学习和教育也是如此)。
(11)对反思性的见解采取行动,常常受到情境、情感和信息的限制,这也可能需要新的学习经验。质变学习需要学习者做出信息畅通的、反思性的决策行为。这可能导致及时的行动,也可能导致对现有行动方式的合理重申,如果行动延迟往往是由于情境的限制或缺乏行动的信息等引发的。
(12)成年期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过程。在应对外部世界时,工具性能力包括实现任务导向的行为技能,这些技能可能涉及反思性问题的解决,有时候包括问题的陈述。沟通能力是指学习者谈论目的、价值观和意义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别人的能力。学习者可以通过更清晰的意识和批判性的反思假设来更加自由地参与话语,并摆脱反思行动的限制,从而获得交际能力。
解放主义范式的发展路线为质变理论提供了理论根基,苏格拉底(Socrates)指出,“言行体现出基本的信念,这是一种自我反思——我们不必通过暴政和虚假舆论来束缚自由”。[19]继哈贝马斯之后,质变理论体现出学习的客观主义范式、解释主义范式、社会建构主义的结构、语言在创造意义中的重要性、批判的中心性和对文化多样性、敏感性的辩证结合。同时,哈贝马斯的思想主张和质变理论超越了这种结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理性、学习以及理论本身的性质。
哈贝马斯通过实地了解和学习人际交往的结构,既超越了理性的传统,也超越了认知革命。除非能评估我们言行中隐含要求(理由)的合法性,否则,我们无法意识到意义、理解和解释的概念。论证一个行为或一个言论是否理性,在于行为或言论是否可以被批评或辩护; 毕竟我们对行为或陈述的论证是有标准的。
如果工具性学习限制了理性行为对客观世界知识的表达与辩解,那么至少应满足其中一个人的理解需求与条件,交流性学习才会使某些事情变得理性。人类交往的内在目标是达成共识和相互信任。理解话语的意义和评估要求的有效性是一致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作者为什么有资格提出某些断言为真,承认某些价值和规范是正确的,我们才能理解文本的含义并真诚地表达某些经验。行为主体对有效性声明的合理辩解,使得有意义的学习过程成为可能。
意义、解释和理解有利于实现对人与人相互沟通的有效性要求进行理性评价。我们必须理解他/她行为的合理理由是什么,并以我们的理性标准来评估这些理由,即使我们不分享它们。伯恩斯坦写道,“我们总是处在种族主义的危险当中,但我们永远无法脱离理性的地平线”。[19]10
话语能够使我们检验信念和解释的有效性。它以支持某个信念为由,允许我们审查和判断观点的正误,以作出达成共识的最佳判断。我认为,最佳的判断只有等到有新证据、论据或观点才能作出;达成共识的验证是一个持续性学习过程。在实践中,话语可能与某段时间内的个人有关,包括文本的作者或大小不同的样本。
因此,质变理论是对传统的客观主义学习进行辩证的综合性假设,它融合了意义结构的概念,并结合了对认知革命规律性和解释性学习的洞察力的研究,包括对重要、敏感又具有象征性交互意义的解读。质变理论超越了主体间交往能力的结构,专注于批判反思性解放的理性传统和认知革命。通过批判性反思,我们可以摆脱文化约束和歪曲的影响,自由充分地参与话语交流。
席勒的西方理性传统的前三项原则主要通过工具性学习的解释来实现。质变理论通过交流性学习来补充这些认知原则,但并不突出语言建构的独特作用、话语和反思行为。席勒关于理性与逻辑的第四个原则和关于知识标准的第五个原则都涉及工具性学习和交流性学习两个领域。
无论区别工具性学习和交流性学习多么重要,但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两个领域完整分开。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大部分学习都包含工具性和交流性元素。批判主义理论突出了工具性理性行为霸权的危险性,即我们在社会中试图取代交流性的理性行为,去创造一种物化、商品化和分离的力量。
卢志文:中国校长会遭遇方方面面的限制,但最大的限制主要来自自身及其团队。我们希望他者来改变,但我们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做一些改变,才会变得更好。学校在变成教育集团的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不同形态的办学样式。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每天遭遇的困惑和他人有相同的一面,当我们尝试去解决自己当下遇到的问题时,已经在为他人探路,每做一件事其实都是一种摸索,可以叫“实践的思考”和“思考的实践”。大体上,这几乎是所有校长职业生涯道路中的常态,我们必须在道路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每个人都不埋怨,把脚下的路走好。
同交流性学习一样,工具性学习中问题的解决,往往嵌入在一系列人类参与所达成共识而建立的假设当中。库恩说明了范式是如何给科研单位带来更多挑战,以及科学研究是如何试图通过合理的假设从而对最新发现的数据进行批判性思考。他还指出,对于调查条件来说,话语产生的作用是有效的,尤其是当调查结果与科学界的一般性理论相违背时。工具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不仅仅是认知。动机、意志、直觉、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和情绪也是解决任务导向型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20]
1.学习理论
哈贝马斯指出,要理解传统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我们就必须从重构理论中区分出实证分析理论,如乔姆斯基、皮亚杰和科尔伯格。重构理论试图解释语言能力、认知和道德发展以及人类交流本质的普遍条件和规则。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重构理论。[18,21]质变理论也是一种重构理论,其重点是成人学习,其主要的受众是成人教育者。作为一种重构理论,它试图建立一个一般的、抽象的、理想化模型,目的是解释学习过程的一般结构、维度和动力性。一些批评此理论的人认为,该目标导致一种构想,就是没能认识到地方文化压倒性的力量及其结构性的不平等容易歪曲理论,这是除公然的政治行动外的一种行动假定形式。
建立一种普遍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成人学习模式是一种不同的事业,而不是承担特定的文化分析、设法歪曲理性话语以及扼杀那些被压迫的声音。我的方案就是试图确定成人学习的共同因素、作用以及人类沟通中隐含的普遍意愿,教育者可以通过这些理念来调查和评估当地的实践,并指导他们的实践,从而形成成人教育哲学。该模型为不同文化的研究性学习提供了框架。
传统文化往往强调通过建立意义图式进行学习,指定学术骨干在传统假设下制定新的意义图式。传统文化更加强调通过吸引传统和权威而不是理性的话语来解决信念冲突。信念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传统、权威、力量或话语来建立。有些文化可以通过一个宗教领袖或部落首领来界定其权威性,其他人则以法庭或政治家的方式来界定权威。有些文化可识别记忆性学习,并对假设的批判性反思概念进行抵制,可能限制了指定组织领导人的话语权。传统和现代文化都界定了话语拥有者和各种形式的话语。美国土著部落的酋长们会通过一根和平管的传递进行演讲,每个人都会等待这根和平管传递到自己手里来。一种文化对实践的阻碍由于个人或集体对反思性批判的洞察力,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传统文化的话语通常用于验证信念,尽管批判性反思的假设可能并不常见。然而,费雷尔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传统的村庄文化中,质变学习也可以通过教育干预来实现。[22]
质变理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文化批判,而是通过提供模型结构、语言、类别和动态,使其他人能够了解成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是如何学习的。这些措施包括:区别工具性学习和交流性学习;明确学习的四种类型;意义图式的本质与展望;建立一个更好的参考框架;重构过去事件的想象力的记忆投射;通过诉诸传统、权威、力量或话语来验证信念;另类的反思形式;对问题情境的批判性反思;作为意义结构质变的过程和前提;划时代的积累变化;理想的话语条件及交际能力。在这些被使用的描述词中,使用的优先级别和使用的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它们的有效性。
话语的理想条件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模式,作为理想化的标准,很少能完全地在实践中实现。不失真的传播是人类传播的本质含义,它不是一个刚性的、规范性标准,而是反映一个人或一种文化。
如果没有拜尔的反对,人们可能会把理性作为理解学习本质的基本结构。 拜尔认为,我们的推理能力取决于我们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从事理性的事业,通过社会化成长,将公认的一般性原则的知识推理从一个阶段传递到另一个阶段,从而将它们应用到特定的情况下并得到进一步改善。[23]
因为重构理论属于证实或证伪原则。因此,质变理论应通过持续性和批判性的反思性话语进行严格评估,以确定其结构的有效性,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不同当地文化引发的学习过程障碍上。
2.情境学习
为了理解学习是如何受当代文化和社会力量的“情境性”影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影响如何对人类传记、社会现实的意义观点和图式产生影响,同时也包括对其中的有效性和实践性的审查。意义观点是固定不变的,很少具有可渗透性,更是难以捉摸的思维习惯。意义图式通过日常洞察力转化为观点,揭示了价值观、感觉、态度和概念在具体应用中被歪曲的影响。Margolis认为,人们可以“尝试”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但不能“尝试”得到一种思维习惯。这可能是意义图式相对容易转变的关键原因。[25]
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社会文化力量促成了质变学习,它们允许、鼓励批判性反思和理性话语。这对于成人学习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会描述谁的话语具有优势和谁的话语能够被听到。这样做会改变(成人)完全自由参与话语的意愿。这些学习者会将他/她的意义观点带到情境学习的经验当中。当前社会形势影响了他/她在特定解释中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在意义图式中被实例化,不仅仅涉及概念,还涉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和信仰。
我们形成了一套包含意义图式和意义观点的辩证法:意义图式往往是高度互动的且被情境学习经验所影响;意义观点是一系列只能间接地被当前社会力量所影响的既定倾向。
在某个人的意义观点范围内,个体可能获得那些不同的但数量有限的意义图式。那些长期受到社会认可的计划所拥有的意义观点,往往会得到社会强大影响力的强化。那些因计划不合理而产生的不和谐或不均衡问题,也不会使人迸发出有意义的想法。文化决定了信念冲突解决的方式。质变理论并不意味着个体学习者想象的分离,而是一个以对话为特征的学习过程。社会层面是核心,历史和文化层面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如此。它们一起为我们提供了意义观点和意义图式,而社会层面决定了哪些特权的声音可以充分和自由地参与话语,批判性反思的限制又是什么。
3.文化障碍
对于以对话交流为特征的学习,我们的文化会充满着明显的阻碍。我们非常熟知那些与阶级、种族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霸权主义是另一种重要的扭曲,就像我们倾向于允许它在不适当的领域取代交往合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工具理性倾向于个性化、具体化,涉及技术控制和操作,并且会导致文化商品化。交往理性强调人际交往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主体间性、团结性和批判性反思、理性话语、共识决策及反思行动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指出:这种制度——货币制度、官僚制度和它的工具理性倾向于取代它的“生活世界”和交往合理性。社会运动和成人教育可以改变这种不平衡。[21]
Tannen指出,有效沟通是另一种重要的文化扭曲。她把我们称作一种“批判性文化”,用对抗性对话取代了话语权。我们不是试图去了解别人的意见,而是通过与其他人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听取其他人的观点和论据,并且研究证据,从而找到一个最佳的、协商一致的解释,那样我们就已经走向了一个损人利己(win-lose)的局面。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让别人犯错。 议论性话语是指提出论点。Tannen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议论性话语往往被普遍地误解为一场争论或争吵。然而,我们没有听信其他人,是为了理解他或她所说的话,并不能证明我们会歪曲事实或让别人看起来难堪。当你处于一场争斗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倾向,即让你否认事实而支持你对手的观点。如果公共话语是一场斗争,那么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有两个方面——不多也不少。即使人们忽视科学的边界或疯狂地去寻找它的边缘,但展示“另一面”也是至关重要的。[26]28
对抗性对话倾向于擅长言辞的人,其他人则只能从参与中汲取信息。这种将他人置于对抗状态的文化倾向,在当代新闻界,尤其是在电视脱口秀节目和访谈节目中司空见惯。它也越来越成为大学课堂参与的一种风格。Tannen写道:
尽管批评无疑是批判性思维的一种形式,但是将不同领域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并考察它们所产生的背景也是如此。当我们从来不问“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建立新的理论和新的认识?”而只问“这个论点有什么问题?”时,反对派并不会引导出真相。当反对派掌握了主导的探究要道时,当反对派的欲望抬高了极端的看法,掩盖了复杂性时,当我们急于找到自己的弱点以致蒙蔽我们的优势时,当敌对的气氛防碍并挑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批评文化就会扼杀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它,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相。[26]28
与这种文化扭曲相反,话语不是一场战争或一场辩论;寻求一致、建立新的认识是一种持续的努力,有时候通过发现观点的交集,有时候通过延迟决策和解决问题来产生一个更清晰的理解。达成共识是理论上的目标,而不是话语的唯一功能。
建立参与者之间的团结意识是有效话语的一个重要前提。在鼓励群体话语的早期努力中,人际关系的发展处于优先位置。在听取更多信息或其他观点之前,共识可能会被故意推迟。一个重要的判断可以被简单地置于更多的证据或论证的等待中。推迟达成共识对于形成新颖的思维方式和消除分歧是非常重要的。沟通的内在目标是“达成一种以互惠理解、共享知识、相互信任和相互协调为主体的互助关系的共识”。[27]3
因此,William Isaacs 认为:“对话(话语)试图让人们学会如何共同思考——不仅仅是分析一个共同的问题,而是从基本假设出发,深入了解它们产生的原因。对话可以形成一个使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创造共同意义的环境。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开始把他们的关系与更大规模的集体经验分开。只有这样,共享的意义才能产生新的、一致的行动。”[27]
4.学习的理想条件
自由、正义、民主、参与、和平等被西方启蒙运动狭隘的政治产物所攻击,而质变理论拯救了这些被批判的概念。质变理论坚持诸如此类的价值观——信任、宽容、教育、开放和关怀对于实现正常的沟通非常必要。在最佳条件下,参与者的话语将会:(1)具有准确和完整的信息;(2)不受强迫和歪曲的自我欺骗;(3)客观地衡量证据和评估论据;(3)开放地接受新观点;(4)批判性地反思假设及其后果;(5)平等的参与机会(包括挑战、质疑、驳斥、反思和听取其他人的机会);(6)能够接受知情的、客观的和理性的共识作为合法的有效性检验。[1]
这些最佳的话语条件也是学习的最佳条件,对教育有着明显的影响。就我们可能想到的一个当代社会学习的共同过程而言,我们也可能暂时与这些从我们的共同经验演变而来的理想条件达成部分共识。这些理想条件为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提供了成人学习的基础。在成人教育背景下实施这些理想条件,意味着教育者需要有意识地去努力建立和执行学习情境中的规则,这种规则能抵消或大大减少权力的影响、损人利己的对话和工具理性在社会其他领域的霸权。成人教育需要建立反思和话语的自由空间,减少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权力差异。教育者应该被视为一个合作的学习者,将自己从协助者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协作学习者,贡献出他的经验,从而达成最佳协商一致的判断。在理想条件下(这是成人教育的特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同伴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在儿童教育中并不罕见。
在成人教育领域,教育和灌输之间有着良好的规范。因此,由于文化的局限性,成人教育可能被理解为对后现代威胁的一种可信的应对,即社会的权力和影响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批判性话语和理性。成人教育是对这种威胁的批判性反思,并致力于防止沟通曲解和成人学习过程的变形。
[1] Mezirow J.Transformative dimensions in adult learning[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1.
[2] Searle J R.Rationality and realism, what is at stake?[J].Daedalus,1993,122(4):55-83.
[3] Henry W A.In defense of eliteism[M].New York: Doubleday,1994:30.
[4] Semin G R ,Gergen K J.Everyday understanding[M].London: Sage,1990.
[5] Chomsky N.Review of verbal behavior by B.F.Skinner[M].New York: Irvengton,1991.
[6] Bagrall R G.Continuing education in postmodernity:Four semantic tens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1994(7-8):265-279.
[7] Derrida J.Of grammatology[M].Spivak G, tran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8] Derrida J.Writing and difference[M].Bass A,trans.London: Rutledge & Kegan Paul,1978.
[9] Derrida J.A discourse on method[M].London: J.M.Dent,1986.
[10] Foucault 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London: Travistock,1974.
[11] Foucault M.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M].Brighton: Harvester Press,1980.
[12] Foucault M.The subject and power[C]∥Dreyfus H,Rabinow P(Eds.).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Brighton:Harvester Press,1982.
[13] Baudrillard J.Simulations[M].New York: Semiotext,1983.
[14] Baudrillard J.Selected works[C].M.Poster (Eds.).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
[15] Baudrillard J.Cool memories[M].London: Verso,1990.
[16] Lyotard J.The 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17] Heron J.Validity in cooperative inquiry[C]∥Reason P(Eds.).Human inquiry in action: Developments in paradigm research,London:Sage,1988.
[18] Habermas J.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M].McCarthy T,trans.Boston:Beacon Press,1984.
[19] Bernstein R J.Introduction[C]∥Richard J.Bernstein (Eds.).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
[20] 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0.
[21] Habermas J.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II).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M].McCarthy T,trans.Boston: Beacon Press,1987.
[22] Freire P.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New York: Herter and Herter,1970.
[23] Baier K.The rational and the moral order[M].Peru: Open Court,1994.
[24] Tennant M.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dult development[J].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1993,44:34-42.
[25] Margolis H.Patterns,thinking and cognition: A theory of judgment[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7.
[26] Tannen D.The triumph of the yell[N].The New York Times,1994-01-14.
[27] Habermas J.Communic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M].Mccarthy T,trans.Boston: Beacon Press,1979:3.
[28] Isaacs W.Taking flight: Dialogue,collective think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M].Cambridge.M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enter,1993: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