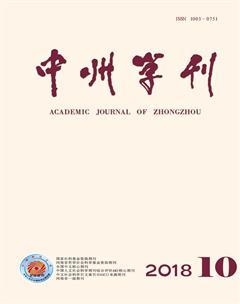试论数字影像的像似性
张骋
摘 要:在数字电影时代,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摄影技术已经逐渐被数字技术取代。但是,这种挑战并没有真正威胁到“摄影影像本体论”在数字电影时代的适用性,因为巴赞的理论不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手段,而是一种真实观,这种真实观追求的是建立在文化规约和情感体验基础上的艺术真实。同时,我们也需要超越巴赞,找到数字影像的视觉性像似,进而理解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不是在物理层面和视觉感官上具有同一性,而是在文化层面和原型图式上具有同一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在数字电影时代依然适用的原因。
关键词:数字影像;视觉性像似;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53-06
“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经典电影理论时期电影批评家们重点探讨的话题。法国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就这一话题提出了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在巴赞看来,电影影像就像指纹一样逼真地反映现实,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具有同一性。如果我们把影像视为一种符号的话,依照巴赞的思路,影像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看起来一定是高度相似的,这种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在视觉感官上的相似在符号学领域里被称为“视觉性像似”。因为巴赞认为,摄影是生成电影影像的唯一方式,而“摄影的得天独厚在于它可以把客观如实地转现到它的摹本上,不管我们用批判精神提出多少异议,我们不得不相信被摹写的原物是确实存在的”①。因此,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才被称为“摄影影像本体论”。但是,在数字电影时代,当摄影不再是生成影像的唯一方式时,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是否还成立?当电影影像与现实之间在视觉感官上不再相似时,作为符号的数字影像是否还具有视觉性像似?
一、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的挑战
1.数字电影对“摄影影像本体论”的挑战
自从电影诞生以来,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以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的出现为开端,数字技术正式被运用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之中。数字技术的引入标志着电影影像的生成不再依赖摄影技术,只需要计算机自动生成即可;电影影像的载体也不再是电影胶片,而是虚拟的二进制代码。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使得电影影像不再需要与现实中的事物在视觉上相似,只需要根据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就可以制作出影像,影像里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是现实中没有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制作出《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加勒比海盗》《阿凡达》《星际穿越》等在前数字电影时代想都不敢想的电影题材,因为这些电影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完全依赖于制
作者的虚构想象。
由此可见,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在数字电影时代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他的“影像本体论”正是建立在摄影技术之上。巴赞之所以认为电影影像可以像指纹一样逼真地反映现实,就是因为“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形式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无须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摄影师的个性只是在选择拍摄对象,确定拍摄角度和解释现象时表现出来”,“一切艺术都以人的参与为基础,唯独在摄影中,我们享有不让人介入的特权”。②
但是,在数字电影时代,随着摄影技术逐渐被数字技术取代,摄影技术所强调的区别于其他艺术的“不让人介入”的特权也不复存在,因为数字电影的前期制作需要人利用二进制程序进行编码,后期制作也需要人利用数字特效技术改变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由此,数字电影将被巴赞置于边缘地位的“人的参与”重新置于核心地位。由是观之,数字技术对电影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声音对无声电影、彩色对黑白电影带来的挑战。数字技术颠覆了我们自电影诞生以来一直都对电影持有的“纪实主义”传统,使我们对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因此,數字电影时代也被很多学者称为“后电影”时代。
2.数字影像对“视觉性像似”的挑战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的组成分为三个部分:再现体、对象、解释项。其中,再现体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对象是符号所替代的不在场的事物,解释项是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同时,皮尔斯又根据再现体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三种:像似符号、标示符号、规约符号。其中,像似符号指向其对象的方式就是依靠“像似”,即“因为再现体与对象之间的相似”。也就是说,像似符号之所以可以替代和再现不在场的某事物,是因为其再现体在视觉上与之相似。
按照巴赞的观点,电影影像一定是像似符号,影像符号的再现体也一定与其对象在视觉感官上相似,因为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电影影像可以像指纹一样逼真地反映和再现现实,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具有同一性。但是,到了数字电影时代,当数字技术取代摄影技术成为生成电影影像的主要手段时,电影影像只需要依照一个理想模型即可生成。这样生成的数字影像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原物,比如《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阿凡达》中的阿凡达,《复仇者联盟》中的绿巨人,等等。这种依照理想模型生成的影像符号在文化学领域被称为“仿真”。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指出:从文艺复兴开始,“拟像”的发展经历了仿造、生产、仿真三个阶段,“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仿真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导模式”。③在“仿造”阶段,现实中原物的地位至高无上,拟像都是模仿原物而生成。而到了“仿真”阶段,拟像的生成已经不需要现实中的原物,只需要依照符号化的模型即可生成。由此可见,数字影像的生成方式显然处在“仿真”阶段,所以,数字影像在现实中通常找不到与之在视觉感官上相似的原物,作为符号的数字影像的视觉性像似也就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的挑战;二是对依照巴赞的思想延伸出来的“视觉性像似”的挑战。笔者这里之所以用“挑战”,而不用“颠覆”,原因在于:笔者认为,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和“视觉性像似”在数字电影时代只是遭到挑战,而没有被颠覆。要理解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为什么在数字电影时代仍然适用,首先需要我们回到巴赞,重新理解“摄影影像本体论”。
二、回到巴赞:重新理解“摄影影像本体论”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数字电影的出现推翻了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是因为他们对巴赞的误读。在理解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时,人们通常强调其“电影影像就像指纹一样逼真地反映现实”的观点,而相对忽略了巴赞对“电影真实”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巴赞在谈到“电影真实”的时候确实强调了客观的真实,即影像世界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但是,巴赞还强调了心理和情感上的主观真实。其实,巴赞也意识到电影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反映现实,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因为电影是一门艺术,艺术对真实的追求与科学对真实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科学真实是追求认识的客观性,让认识主体在不受主观因素干扰的条件下认识到客体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艺术真实追求认识的主观性,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怀的基础上来认识客体事物,从而让客观事物变成主体的情感和意志的产物。如果我们以“科学真实”的视角来理解,“日出日落”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现象,但如果我们以“艺术真实”的视角来理解,“日出日落”就不再是一种宇宙现象,而是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历程中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的结果,即认识主体借“日出日落”来抒发和表达自身的情感和意愿。在文学史上,古人就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咏“日出日落”的诗句。
既然电影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反映现实,巴赞就指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也就是说,在巴赞看来,电影所追求的是目的的真实,而非手段的真实。这种目的的真实主要体现在电影带给观众的真实感。比如,虽然观众都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存在金刚、绿巨人、蝙蝠侠、蜘蛛侠,但是观众并不会因为这些“不真实”的形象就不喜欢看这些电影。因为这些“不真实”的形象真实地诠释了隐藏在观众心中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观众扬善惩恶的心理期待,符合观众内心真善美的评判标准。
由此可见,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是要阐释一种真实的观念,而不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手段和过程。只是巴赞不知道电影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影摆脱了对摄影技术的依赖。摄影技术的确可以使电影通过手段的真实来达到目的的真实,但是数字技术可以通过非真实的手段来达到真实的目的。这里所谓的“非真实的手段”是指数字电影中的影像都不是通过摄影技术拍摄出来的,而是直接通过数字技术合成的,这些通过数字技术合成的影像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在视觉感官上相似的对应物。但这丝毫不妨碍数字电影对真实的追求,只是数字电影追求真实的手段与传统电影不一样,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给观众带来真实感。也就是說,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电影的本质,因为电影的本质不应该由生成电影影像的手段来界定。
关于“电影本质”的探讨,笔者非常认同美国当代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的观点。他认为电影的本质不是由影像的来源方式决定的,而是由电影艺术的自动机制决定的。而艺术的自动机制“除了指艺术的技巧和技术之外,其涵义还包括长久以来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形式、仪式等形而上的内容。自动机制是人们下意识中对传统和习惯的依赖,尽管艺术一直不断在追求自由的个性,但是这种绝对的自由只有在乌托邦才存在,任何艺术都在本质上遵循着艺术的潜规则”④。在卡维尔看来,电影艺术的自动机制是指满足人们窥探现实世界的心理需要,进而通过观看影像来代替个体内心的幻想和欲望。由是观之,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直不变的本质就是通过具有“真实感”的影像来满足观众观看现实世界的需要。
应该说,卡维尔对于“电影本质”的理解与巴赞是不谋而合的。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也是强调电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本质就在于电影影像对现实的反映能够给观众带来真实感。虽然数字电影的影像都是由数字技术合成,表面上看没有反映现实,但是它反映了现实的本质,这个现实的本质就是指观众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期望。也就是说,虽然数字电影中的很多形象在现实中没有,但是与现实也紧密相连,因为这些形象都是通过对现实的理解而提炼出来的,因而能带给人们真实感。
综上所述,数字电影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终结,最多只是去掉了“摄影”二字,“影像本体论”永远都成立,因为电影的本质永远都是通过反映现实的影像来追求真实感,进而满足观众窥视现实世界的欲望。数字技术只是丰富了电影反映现实和追求真实感的手段而已。不过,想要充分理解为什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在数字电影时代仍然适用,除了需要回到巴赞,更需要超越巴赞。巴赞的“影像本体论”之所以容易被人误读,原因就在于巴赞并没有论述清楚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同一性,这就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仅仅停留在影像通过与现实之间在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来反映现实的层次。笔者在下一部分将重点分析“数字影像”这个符号,弄清楚数字影像是在哪个层次上反映现实的,进而论证数字影像的视觉性像似。
三、超越巴赞:数字影像的视觉性像似
“视觉性像似”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似乎只要符号的再现体与对象之间具有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此符号也就具有了视觉性像似。事实上,符号的视觉性像似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很多人之所以对“视觉性像似”这个概念有误解,一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相似”与“像似”这两个概念;二是因为他们对“视觉性”这个概念的曲解。这两个原因也直接导致我们对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误读。
1.混淆“相似”与“像似”导致的误读
“相似”是指两个事物之间具有物理形态上的相近,并且这种物理形态上的相近动物都能感知到。众所周知,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目的,不仅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具有模仿其他对象或周围环境的能力,而且较低级的变色龙、枯叶蛾等也具有这种模仿能力。而模仿一定是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动物一定是首先感知到了两个事物在物理形态上的相近之后才能进行模仿。
但是,这些动物感知到的“相似”能否直接上升为“像似”,换言之,动物界是否存在符号的像似性?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像似”的“像”是指“人造物,是人们模拟对象而创生的符号世界”⑤。因此,符号与对象之间只可能具有像似性,不可能具有相似性。著名符号学家约翰·迪利指出:“符号是客体预先设定的东西。”⑥也就是说,符号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设定的。这种人为设定的符号意指关系不是对自然规律和关系的发现,而是人的心理感知和文化阐释的结果。赵毅衡先生也曾指出,符号学不能代替医学、地质学等,因为医学和地质学经常用到的标示符号与图像符号的表意需要经验积累,需要专门知识,不能靠社会约定。换言之,“符号学的任务,只是设法理解人的理解方式中,意义和物是如何混合的”⑦,自然客觀的相近不进入符号学研究的范畴。动物感知到的“相似”之所以不能直接上升为“像似”,原因就在于“像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而“相似”不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相似”只有经过人的解释才能上升为“像似”。
由此可见,“像似”是两个事物之间具有心理感知和文化阐释上的相近。符号的像似性必须是人类根据一定的文化背景而阐释的结果。英国哲学家保罗·科布利指出:“仅仅相似并不构成像似符,如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并不构成彼此的符号;镜子里的影像如此像我,但也并不是我的像似符。因此,像似符必须是在社会实践中对‘相似性——社会习规约定之后的结果。符号的像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相似。它是在规约基础上的抽象。”⑧这里也表明符号的像似性建立在规约性之上。
符号的规约性是指符号与对象的关系靠社会约定形成,解释者需要靠社会约定的文化规则来解释符号的意义。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就坚持符号规约性的根本地位,他认为像似符号与对象也可以没有任何物理形态上的相近而产生同一效应,“导致我们面对物理成分完全不同的事物产生同一效应的根本原因是已有知识”⑨。也就是说,在艾柯看来,像似符号必须依靠符号接受者根据文化规约对符号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才能表意。如果我们按照皮尔斯对符号的三分来理解,符号的像似性不是仅仅发生在“再现体”和“对象”之间,必须加入解释项,“再现体”与“对象”之间的像似关系才能确立。简言之,符号的像似性必须通过人的解释才能成立。
此外,像似性还很容易被误解为图像性,像似性和图像性在英语中都被译为“iconicity”。事实上,图像性和像似性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符号的类型。图像性是从媒介的视角来划分符号的类型,与图像相对的媒介分类有语言、声音、文字等。像似性是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的视角来划分符号的类型,与像似性相对的有规约性和标示性。由此可见,像似性不仅有图像像似,还有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其中,图像像似侧重外形上的相似,比较清楚自然;图表像似侧重结构上的相似,比喻像似侧重思维上的相似,二者都比较抽象含糊。
因此,不仅图像符号具有像似性,语言符号、文学符号等非图像符号也具有像似性。这种非图像符号的像似性不是去再现具体的事物,而是去再现抽象的心象。对心象的再现不是去模仿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去表现内心世界的真实。这一点在艺术符号的像似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西方逐渐兴起了艺术的“表现说”。“表现说”也是由“再现说”发展而来,只是再现的对象由外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也就是说,艺术符号的像似性主要体现在对艺术家“心象”的再现。这种再现不是模仿,而是对客观对象的超越,这种超越是通向艺术理式之真,即“超真实”。例如,我们经常用被画者“本人”的样貌来评价一幅肖像画的逼真程度。事实上,这里作为评价依据的“本人”不是这个自然人的全部,而是他最接近绘制肖像画时的样子。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用“本人”的样貌来评价肖像画的逼真程度,比如,本人憔悴时候的样貌。我的肖像画可能比憔悴时的我更像“我”,因为这里预设了一个理想状态的“我”作为原物,憔悴时的我并不能很好地再现这个原物,肖像画反而更能够再现理想状态的“我”。因此,“原物”并不是一个终极存在,而是人们进行符号表意时暂时预设的“心象”。艺术符号也不是像似于一个具体事物,而是像似于超越具体事物的艺术理式,进而通向艺术真实。
由是观之,数字影像虽然在现实中不一定有具体的对应之物,但是仍然具有像似性。因为像似性不是去再现现实中的具体事物,而是去再现暂时预设的“心象”,这个暂时预设的“心象”是人们通过对现实事物的解释而建立起来的。进言之,不仅是数字影像,所有影像都是通过与现实之间的像似而非相似来反映现实的。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不是在物理层面具有同一性,而是在文化层面具有同一性。巴赞对这个问题没有阐述清楚,这就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对他“摄影影像本体论”的误读。
2.对“视觉性”的曲解导致的误读
对“视觉性”这个概念的曲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对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误读。我们通常将“视觉性”理解为事物或事件在视觉感官上的可见性,而造成这种视觉感官上的可见性的原因通常也被理解为图像生产、传播、接受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事实上,视觉性与生理学意义上的视觉感官没有必然联系,与图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没什么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对于“世界图像时代”的阐述来理解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⑩。这一著名观点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也就是说,“世界图像时代”并不是指世界上图像数量的增多,而是指人类以“图像的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
这里的“图像”可以拆分为“图”和“像”两部分。其中,“图”是以视觉感官为基础的外在的形式要素;“像”是人类意识感知和阐释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图像视为一个符号的话,“图”就相当于符号的能指,“像”就相当于符号的所指。因此,图像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一个存在于人类感知和理解之中的对象。由是观之,图像是以人类先验原型为基础而存在的。原型的本意是指原初的图式。“图式”这个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将图式界定为“限制知性概念使用的形式和纯粹感性条件”B11。也就是说,图式是基于人类经验知识的一种先验结构样式,只有通过这个先验结构样式,人类才能认识和理解世界。因此,人类以“图像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就是指人类以图式来理解世界,世界因图式而被把握为图像,这里的图式就是指图像的构成方式。
图式与图像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是普遍的、共性的语法结构,而言语是对语法结构的个别的、具体的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同一个语法模型,写出无数个不同的句子。同样,图式是图像的语法结构,是从复杂多样的图像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性模型。这个普遍性模型也可以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图像,并将这些不同的图像联系起来。比如,在西方中世纪以来表现“天使报喜”主题的艺术作品中,无论绘画还是雕刻,都来自“百合花”这个原型图式。由此可见,所有图像都有自己的图式,并且都以自己的图式为基础转化而来。我们也只有通过图式才能真正理解图像的意义。
当代著名图像学家米歇尔用“image”和“picture”两个不同的英文单词来分别指称原初图像和物理图像。其中,作为物理图像的“picture”就如同一张图片,可以随意修改和涂抹,但作为原初图像的“image”不能被修改和涂抹,它以基因密码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picture”中。在米歇尔看来,今日的数码复制与本雅明时代的机械复制不同,机械复制会使图像由于脱离原初的“灵韵”而失真,但是数码复制不会使图像失真。因为数码技术复制的不是图像的物理外观,而是图像的基因密码,虽然仍然会脱离原初的“灵韵”,但是基因密码不会改变,因此不存在失真的问题。概言之,米歇尔这里的“image”就相当于原型图式,“picture”相当于根据图式转化而来的图像,并且,他也认为,我们只有通过“image”才能理解“picture”。
综上所述,视觉性不是视觉感官上的可见性,而是一种以先验图式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可以使万事万物都具有视觉性,使万事万物都以图像的方式展现出来。“对文学来说,视觉性就是作者借助语言文字的描述来展现事物的图像,也是读者借助想象来将所读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图像。”B12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都是语言文字,但是作者通过书写这些语言文字可以向读者展示出一个个的图像,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语言文字感知到一个个的图像,这里的图像不是指物理形态的图片,而是指诉诸内心的心象。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作者和读者都使用以先验图式为基础的认知方式。由此可见,两个事物之间的视觉性像似不是指两个事物在物理形态上的相似,而是指两个事物在原型图式上的像似,这种像似不诉诸视觉感官,而是訴诸先验图式的认知方式。
因此,我们通过对“视觉性”的分析也可以发现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在数字电影时代仍然是适用的。因为在数字电影中,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不是在视觉感官上具有同一性,而是在原型图式上具有同一性。具体而言,数字电影中所有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直接对应物的形象,其实都是依据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图式而制作出来的,两者之间具有视觉性像似。然而,巴赞在他的论述中回避了这个问题,这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对其“摄影影像本体论”的误读。
四、结语
在数字影像时代,虽然电影影像的制作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巴赞在70多年前提出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在数字影像时代仍然适用。因为“摄影影像本体论”不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手段,而是一种真实观,即通过反映现实来给观众带来一种真实感,并且这种真实观代表了电影的本质,无论电影技术如何发展,电影之为电影的本质不会改变。但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影像”这个符号,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影像。因为影像是电影独有的表意媒介,也是电影学最直接、最核心的研究对象。我们只有找到影像(数字影像)这个符号的表意特征,才能真正理解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也才能真正理解“摄影影像本体论”为什么在数字影像时代仍然适用。
注释
①[法]安德烈·巴赞:《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崔君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②[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③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ress, 1993, p.50.
④王静:《超越电影本体论:数字时代电影艺术的“自动机制理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⑤胡易容:《“象似”还是“像似”?一个至关重要的符号学术语的考察与建议》,《符号与传媒》2014年春季号。
⑥[美]约翰·迪利:《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周劲松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⑦宗争:《马克思辩证法视野下的符号——意义论》,《符号与传媒》2016年秋季号。
⑧Cobley,Paul,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242.
⑨[意]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⑩[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第899页。
B1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B12段炼:《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责任编辑:采 薇
Research on the Iconicity of Digital Images
— Re-understanding Bazin′s "Photographic Image Ontology" in Digital Cinema Era
Zhang Che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cinema, Bazin′s "photographic image ontology" has been challenged unprecedentedly, because photography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However, this challenge has not really threaten the applicability of "photography image ontology" in the digital film era, because Bazin′s theory is not a means to pursue reality, but a view of reality, which pursues the artistic reality based on cultural convention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transcend Bazin to find the visual iconicity of digital images, and then understand that the image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 are not identical in the physical and visual sense, but identical in the cultural level of identity. Only in this way we can really find out why Bazin′s "photographic image ontology" is still applicable in the era of digital cinema.
Key words:digital image; visual iconicity; Bazin; photographic image ont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