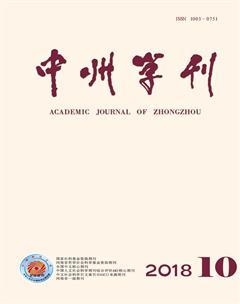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及其价值支撑
殷辂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成为研究贫困等边缘化问题的新路径。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认识弱势群体的动态视野,但如果仅停留在排斥的表象上而不触及内在的机制以及支撑这种机制的价值体系,其意义是有限的。从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出发认识社会排斥的一贯性,其系统性、结构性以及价值维度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社会排斥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秩序,又是一种“价值”。排斥性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在其背后是排斥性的价值体系。若不触动其内在的价值,外在的社会改造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是生物状态下排斥性的自发秩序,而是人文意义上的自然而當然的秩序。
关键词:社会排斥;系统性;结构性;秩序;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072-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成为研究贫困等边缘化问题的新路径。然而,当社会排斥几乎成为这些问题的代名词的时候,人们发现边缘化问题并不会因为出现新的分析范式就能得到解决。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认识边缘群体的动态视野,但若仅仅停留于此,就会陷入主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格局之中。从边缘群体出发去发现其所受到的排斥,很容易将外在的境遇等同于排斥,不但忽略了结构内的排斥,还将社会排斥的关联性、连续性排斥在外。社会结构之内的群体与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群体之间存在断裂,并不意味着结构内不存在排斥,也不意味着内外的排斥是断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排斥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才造成了社会的断裂。如果没有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也就没有被甩在结构之外的群体,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排斥已经越来越清晰。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体系,社会排斥的关联性越来越强,虽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时段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机理并无二致。认清其背后的一贯性,成为消解社会排斥的关键。
一、社会排斥理论的内涵及其缺失
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用“社会排斥”描述被排斥在就业及生活保障之外的“不适应群体”,这些特殊群体主要包括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①自勒内之后,社会排斥逐渐成为分析弱势群体困厄境况的重要概念,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等其他领域。社会成员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没有获得必要的经济资源、就业机会,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方面受限,或者社会生活中参与权丧失等都可以被视为社会排斥。英国社会排斥办公室指出:“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简洁的术语,指的是某些人或地区遭受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②社会排斥概念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解释力较强,不只是贫困问题,几乎所有边缘化问题都可以纳入这一概念之中。
它改变了孤立和静止的思维范式,代之以多维、动态的方法,试图深入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排斥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概念,而一旦与弱势群体联系起来,人们发现其理论内涵非常丰富。其分析路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其一,从边缘或弱势群体自身角度认识社会排斥。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排斥与边缘或弱势群体的自我排斥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缘或弱势群体自身的反社会、去主流行为是遭受排斥的重要原因。其二,从社会整合的视角出发,将社会排斥视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纽带的断裂。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凝聚力下降的结果,其直接表现就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普遍的社会联系之外,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三,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社会排斥,将社会排斥定义为集团垄断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秩序是利益集团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优势群体有意无意地通过权力和歧视性政策垄断稀有资源,并通过社会封闭限制外来者进入,从而永久性地保持这种利益。
社会排斥如果仅仅作为贫穷、边缘化等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无意义的。社会排斥是社会性的,将个体的特殊性或自我边缘化视为社会排斥,显然是将两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从边缘群体所受到的困厄出发去发现排斥,很容易将社会问题和个体现象混淆,将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转变为个体问题。以社会凝聚力下降解释社会排斥,这是一种社会视野,但这种分析范式存在这样的问题:是社会排斥造成了凝聚力下降还是凝聚力下降造成了社会排斥?当社会排斥成为一种机制时,个体和社会之间是无法找到链接的纽带的,所谓凝聚力下降只是对这种变化的描述,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将社会排斥归咎于强势集团的垄断,这种解释直截了当,但使得所谓的强势集团成了游离于排斥机制之外的无因之物。其实,强势集团的垄断既是排斥的原因,同样也是排斥的结果,正是在社会排斥之下,强势集团才会形成并逐步寡头化。当社会排斥成为一种内在机制时,一部分人的失利或弱势化正是另一部分人精英化、强势化的原因。以垄断的方式强化社会排斥,最终会因为将多数人排斥在外而改变力量对比,而在社会排斥机制没有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只是新的强势集团形成并逐步寡头化而已,固有的循环并没有消失。因此,抛开社会排斥的动力机制而单纯强调“集团垄断”,这种理论是不全面的。
社会排斥为我们认识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视野,但如果仅从局部出发去发现受困群体所受的排斥而不触及内在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动力机制,其内在的意义就无法显现。比如从“鳏寡孤独”所面临的困厄出发,也能发现其所受到的排斥,而这只是对现状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排斥。“鳏寡孤独”是弱势群体,这种弱势是个体不幸造成的,它与社会性弱势群体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后者不是外部风险带来的,而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解决“鳏寡孤独”的困苦需要社会救济,但社会性贫困问题却是社会排斥的结果,不改变排斥的内在机制而单纯依靠救济,这无异于扬汤止沸。也就是说,社会救济能解决“鳏寡孤独”的困苦,却无法解决社会性、系统性的弱势群体问题。社会排斥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弱势群体的窘迫处境,但前提是发现社会性排斥,而不是简单地将窘迫处境等同于排斥。
认识社会排斥应该从整体结构出发,认识其内在机理,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排斥的表象上。如果排斥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那么就必然会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连续体,而排斥理论中主流和边缘的两分法掩盖了这一问题的本质。在这种相对的取舍中,主流与边缘的差异成为聚焦点,而各自内部的差异或排斥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性问题变成了局部问题。从社会排斥出发,可以发现,社会性边缘群体不仅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及政策方面的具体排斥,而且这种具体排斥存在其内在的联系。社会排斥既是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机制;它是游戏规则问题,更是秩序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关联性已经越来越清晰。
二、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
社会排斥理论是以西欧以及其他一些具有较高社会福利国家为分析对象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危机是其社会背景,主流与边缘的断裂是其聚焦点。但是,社会排斥绝非边缘化问题的代名词,仅以西欧等特殊区域为研究对象,或仅停留在社会福利领域,其本质是无法显现的。将视野扩展,社会排斥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世界体系之中,其系统性、关联性非常清晰,表现为各种层次的排斥相互作用:一是世界体系中上层国家内部的社会排斥;二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排斥;三是落后国家内部的社会排斥。这三种情况是社会排斥机制体系化的结果。由于第二、三种情况的存在,发达国家内部排斥带来的对立没有落后国家和区域严重,体系或秩序中内含的问题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其整体表现却是另一种情形。
托瑞纳(Touraine)認为,社会排斥概念属于后现代社会的分析范畴。与激进理论不同的是,他不再将贫穷问题视为少数富人或资产阶级对多数人的剥削,而是在水平面上观察中心与边缘。他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研究者讨论的是,一些人被社会排斥出主流和中心社会的边缘。”③在托瑞纳看来,研究方法的转变是顺应社会变迁的结果。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从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转型的时代中,过去我们知道的社会是一个有些人位于社会的顶层、有些人生活在底层的阶级社会,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些社会成员在社会的中心还是在社会的边缘。今天人们不再说他们在上层还是下层,而是关心他们是在主流社会里面还是外面。”④在西欧及其他一些具有高福利制度的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实现了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化的过程,其社会排斥表现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不是垂直的上下关系。但是,垂直型结构是怎样变为水平型结构的?这种转型难道是单独完成的?难道可以脱离世界体系而孤立地实现?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难道也是平面式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从国际背景来看,水平型社会的形成是以国家、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为代价的。若将这种局部矛盾的缓和作为普遍的规律,显然缺乏系统性的思维。水平性本身是和垂直性相对的,不但是时间序列的相对,更是空间的相对。没有国家、区域的分化,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或水平式的社会也就不存在,其内部的福利制度以及各项调节性政策也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奏效。也就是说,西欧社会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以更大范围内的垂直性分化为代价的,所谓后现代社会并非简单的时间排序,它与空间结构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并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能够这样。看不到问题在空间或区域之间的转移,将排斥的结果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停留在局部的认识方法难以使人认清社会变迁的脉络。
认识社会排斥问题无须抱着激进的立场和态度,但不能抛开系统观。从世界整体的关系体系出发认识社会排斥在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的表现及相互影响,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抛开整体性和系统性,抛开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联,将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的转型看成是一种历史的趋势,社会排斥的本质就会被掩盖。如果存在托瑞纳所谓“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转型”的趋势,那么它应该在世界体系内得到验证,收入差距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应该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整体结构也应该存在由垂直型向水平型的转变,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拉大,整体的垂直型结构并没有改变,底层区域和人数并没有因全球化而缩小,反而逐步扩大。脱离与其他区域和国家的关系而孤立看待所谓趋势,将局部的变化视为一般的趋势,本身就存在误导性。只有打破时空的障碍,站在时代的高处,在世界整体范围内、从时间的连续性出发看待社会排斥,问题的本质才能显现。在这种视野下,垂直型结构向水平型结构在特定区域和国家内的转型本身就是社会排斥的结果。局部的水平型结构实际上是垂直秩序下的小平台,这种平台的存在并没有改变整体的垂直型结构。
从世界整体的视阈看,国家的界限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排斥,它剥夺了人们的迁徙权、流动权。这对于优势国家来说,是典型的社会封闭,借用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家的话说,这是将既定的优势固化。在这种社会排斥之下,大量的贫穷国家或区域处在垂直性的或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在贫穷国家内部这种结构更加明显,不但层级分明,还有不少被甩在结构之外的特殊群体。与此相对的是发达国家整体处在金字塔上层,其内部在特定时段内呈现出所谓橄榄型或水平式社会结构。这并非简单的发展阶段的问题,而是世界体系内结构问题的体现。将体系内的位置、结构问题简化为时间序列(先发与后发,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问题,是缺乏系统思维的表现。应该看到,在局部的水平式社会中,其主流和边缘的分化较为清晰,并且主流社会占据了人数上的多数。而在垂直性的社会中,只有中心和主导而没有人数上的主流;只有距离中心(顶层)远近的问题,而没有主流与边缘的真正分界;只有数字意义上的中间者,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中间阶层。因此,如果站在整体和时代的高度看问题,世界并没有改变垂直性或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局部的水平或橄榄型结构只是排斥过程中的局部现象,是社会排斥在特定区域及时段内的特殊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部的平台也会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即使是西欧社会内部的社会排斥也在发生变化,中间阶层开始萎缩,边缘人数在扩大,这种排斥的动态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明显。
要认识社会排斥的本质,应该观察其系统性和关联性。系统性不是问题的罗列,而是找到问题背后的一贯性;关联性不是停留在过程中,而是在各种关系体系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此出发,作为一种机制的社会排斥就能够显现出来。当排斥成为一种机制时,一部分人的“上升”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下降”。同时,排斥不会停留在特定领域、区域及群体之内,必然会在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也必然向所有地区和群体扩展。无论是发达地区内部的中心与边缘的脱节,还是落后地区内的结构断裂,无论是排斥的主体还是排斥的客体,都存在于社会排斥的机制之内。
三、社会排斥机制的价值支撑
社会差异与社会排斥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一些研究者从群体性差异出发认识排斥,但差异并不一定产生排斥和对立,同于私利的差异才会表现为排斥和对立。比如,各种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只有当文明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的时候,冲突和对立才会出现。将外在差异本质化为品性和能力问题,进而取消一部分群体进入或参与社会的权利,这是社会排斥与歧视的表现。然而,以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姿态认可、尊重差异同样有可能出自排斥与歧视。法国思想家塔吉耶夫在研究新型种族主义时指出,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在当代可以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的名义实施”⑤,捍卫“差别权”成为封闭、隔离、排斥的新理由。文化、种族的差异可以在“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之下转变为排斥与歧视,然而当这种直接的种族主义被唾弃之后,“我们与他们”的划分并没有消失,“差别权”竟然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限制外来者进入的旗号,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这说明,只要支撐排斥的价值体系没有消失,尊重差异、多元主义同样会成为排斥与歧视的遁词。因此,从差异入手研究排斥,并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因为无论是差异导致的排斥还是排斥导致的差异,都是在特定价值基础上实现的。在特定的价值体系之下,差异不但是排斥的原因,更是排斥的结果。只有直接深入到差异背后的价值体系,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
民国高僧、著名思想家太虚大师在论及近代以来世界主导价值及立国、做人之道时,用“纵我制物”四字加以概括,并将其视为近代文明的源泉。这种主导价值“以扩充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与自我相对的皆为外物,谋所以利用而制服之,据此为一切发动力的根本精神”⑥。“‘我指私己及由私己引发的贪欲、忿争,‘物指自然界万物及家庭、国家、社会、经济等。”⑦所纵之“我”,“非必以个人为本位,或以一民族为本位,或以一国家为本位,或以一阶级为本位。一民族为本位,则发展一民族的自我,纵使制服自然界及他民族;一国家为本位,则发展一国家的自我,纵使制服自然界及他国家;一阶级为本位,则发展一阶级的自我,纵使制服自然界及他阶级,然终以个人的自我为根本”⑧。在“纵我制物”的价值观念之下,自然环境成为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其他人、其他阶级、其他民族、其他国家都成了与我争利的敌对力量。自由是自我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本质其实是不自由(被私欲所桎梏),自由的扩张必然造成他人的不自由;利益是自我的利益,而自我利益是在人我对立中取舍出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必然损耗他人;和平是自我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并非源于自他调和,局部和平必然以整体的不和平为代价;安全是自身的安全,这种安全无关乎整体,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过程就是促使整体毁灭的过程。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主导价值本身就是建立在排斥基础之上的,以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价值,与自我相对的一切都成了制服和排斥的对象,社会排斥机制的价值支撑就在于此。
太虚大师之所以将“纵我制物”视为近代以来的主导价值,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现实的观察,更重要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合理化。“扩充自我”被视为自我价值的体现,成为创造财富、增进经济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人皆欲自专财利,斗争劫夺、相互排斥就成为一种常态。当“纵我制物”成为主导价值之时,则必有相应的行为方式,也必有相对应的胜负秩序,其内在机理与竞技体育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竞技体育中,所谓的游戏规则无一不是为分出胜负服务的,无论怎样取舍、简化和改进,都跳不出竞争的主题。同时,竞争的各方无一例外地以“犯规技术”冲撞规则的底线。社会及经济秩序同样也是这样。首先,制度与规则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无法真正超脱于主导价值之外。如果制度与规则顺应排斥性的价值体系,形成排斥性制度与排斥性行为交互作用的态势,那么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社会割裂和贫富对立;对排斥性行为进行外部制约,只是控制了竞争的节奏和激烈程度,延长了竞争的周期。在人类行为受排斥性价值支配的前提下,从制度上强行抹平差异,最多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不但不能消除排斥,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因此,外部性改造手段无论顺逆,都在主导价值体系的框架之内,无法真正改变排斥性秩序。其次,在社会竞技场中,竞争各方同样也是向底线冲撞,形成制度不断完善而永远不能完善的状况。当权力也成为竞争的主体之时,其恶性程度将更加严重。最后,在排斥的主题和秩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福利制度和救济制度能起到缓冲作用,但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如果市场完全被排斥性价值所支配,所谓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可能真正奏效,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可能普及。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体系,这一点尤为明显。
可见,一个时代的主导价值与特定的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排斥是秩序问题,同时也是价值体系问题。特定的社会秩序背后必然有特定的价值体系支撑,同时一个时代的主导价值也必然会在秩序上体现出来。认清价值体系、制度、秩序三者的关系,就会清楚地知道,单纯的制度层面的改造并不能消除社会排斥,只要“纵我制物”主导价值不改变,排斥的机制和秩序就不会消失。人人扩充自我、征服他物,则必然互相争夺,相争必有排斥,最终必然排斥其他人的最基本权益。在排斥的秩序之下,人人都处在排斥与被排斥的状态之中,所谓边缘与中心、结构之外与结构之内只是相对存在,而不是排斥与非排斥的差别。用外部力量让一部分进入关注视线的边缘群体回归主流社会,必然还有新的替代者。看不到排斥的价值支撑及相应的机制秩序,在排斥的框架内解决排斥问题,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
四、去排斥的秩序:“义分”的探索
有学者指出:“社会排斥实际上是社会分化整合这个古老的社会学课题的延续。社会排斥强调的是社会连接的断裂,社会排斥概念指向一个社会中存在两种社会层级的危机,或者,它还包含了福利依赖层的重新组合,它表明了比社会不平等更复杂的意义。”⑨实际上,如果从分化整合这个古老话题出发,那么社会排斥意味着只有分化而没有整合,因为这种分化本身就是整合的对立物。社会连接断裂的原因不是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的自我隔绝,而是排斥的结果。在社会排斥之下,只有胜负的分化,不存在贯通、统合不同群体的整合机制。
社会排斥下的分化与社会合理的分工、分序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一个问题,而后者是和谐秩序的自然显现。和谐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往往求之而不能得,其原因不在于分序,而在于没有自然而然的合理分序。自然合理之“分”在荀子看来是“义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⑩
荀子将“分”看成“群”(社会)的基础,看成是人与物之别的根本标志。禽兽也有集体生活,但这是建立在本能基础上的,有集体而无集体之理。其秩序是禽兽行为的结果,因为行为被习性物欲所支配而无解蔽的可能,所以其秩序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只能在不变的秩序中变换群主。只有人有可能解除物欲习气的蔽障,能够依义理形成自然合理的分序,这就是“义分”。东方哲人将“一体之仁”视为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而“义”则是这种关系的体现,正所谓“心之制、事之宜”。父子、夫妇、朋友乃至路人,家庭、社区乃至市场关系,都有相应的适宜之道。由此出发,则和谐有序,相反,将社会、经济看成交相争利的竞技场,则必然你争我夺。人身体的各部分各不相同,但并不停留并终结于“不同”之上,它们各得其宜、一以贯之,故能相合而成肌体。如果借用分化与整合的现代词汇的话,那么分化并不外于整合,整合也不在分化之外。无贯通之义的“不同”要么互不相干,要么互相争斗,绝对不可能有和谐。将社会、市场看成是私欲、私利的竞技场,即使有秩序也是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暂时平衡,绝不可能形成和谐的局面。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都执其私利,最终只能依靠争夺解决问题,这种所谓自然的秩序其实没有摆脱动物的状态,其内在的排斥永远无法停止。
“人生而有欲”,这是生物状态,若被其支配,则近于禽兽。不为物欲所蔽,在日用起居、饮食男女中存理存义,这才是与人相应的文明状态,在此基础上的分序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秩序,即所谓“义分”。阳明先生描述了唐尧、虞舜及三代之世“分而无分”的和谐状态:“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B11所谓一家之亲,即不被私欲所支配的天然情义,这种天然的情义本源于“人心之大同”,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真切笃实,所以古人将这种家庭情义视为良知的发端之处。阳明先生认为,上古时期道义通流,其社会分工如一家之务,各得其分、各遂其志、各适其宜。家庭之义与社会之义、市场之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其本源却无二致。无论是简单的农业社会还是复杂的现代社会,只要本然之义不被破坏,合理的分序都能够实现。这种分工与分序不是私利相争的结果,而是“义理之和”的体现。上古时期的这种和谐状况在目前已经越来越成为理想,后世只有趋向和谐的程度之分,而没有了真正的和谐,其中的原因在于“义”的一贯性被破坏。从社会的演变进程可以看出,本然之“义”扩充越远,越是没有障碍,越是贯穿于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的和谐程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所谓的“市场原则”肆意扩张,最终连家庭之义都无法实现,社会必然纷争不断。
太虚大师认为,社会的构成大概有二:一是要有分离,二是要有总合。B12分是合之分,合是分之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的状态。如果只有分离而没有总合,“人各为其人,国各为其国,团体各为其团体,阶级各为其阶级,互相矛盾而起种种战争”B13。同时,单纯强调总合,强行抹平各种差异,依靠权威、权力保证社会的同质性,这种所谓的整合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所谓的合也只能是苟合、强合。太虚大师关于分化整合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哲人是一致的。分是义之分,不离总合,所以分而能摄;合是义之贯,不碍分界,所以“和而不同”。这种分而无分、无分而分的“义分”是体现天理自然的秩序,又是人文化成的秩序。首先,这种秩序不是强行地“为物作则”,不是刻意地设计安排,而是“物各付物”。虽然离不开制度和法律,但制度和法律却不外乎天理人情,不是特殊意志的产物,而是当然之理的体现,上下之分也绝非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自然而然的基于义的分别。虽然存在权力,但绝大多数人却感受不到权力的存在。其次,这种秩序是人类自觉行为的结果,是建立在人的秉彝之性基础上的,是对被物欲习气支配的动物非自由状态的扬弃。明了人禽之别,以文明化除蒙昧,在此基础上才有“义分”的秩序。最后,这种秩序是一种社会理想,但并不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它是基于人类自身提升而形成的秩序,人人向上发展、明乎理义,则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就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义分”的秩序就不是一种幻想,相反,将生物意义上的习性视为永恒,将交骛于利视为社会运转的动力,那么“义分”的秩序就成为永远无法實现的“乌托邦”。
因此,“义分”不是生物层面上的自然秩序,而是人文意义上的自然而当然的秩序。其制度安排不是强制、偏私的,而是当然之理的体现;其文化不是用强力强权再造人类,而是出自“心之所同然”。合乎本然之性,所以“自然”;超越人禽之同,所以“当然”。这种自然而当然的秩序才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义分”是理想的秩序,但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人类的自觉。建立在本然明德基础上的人文之学是连接现实与理想的桥梁,也是消解人与制度、自由与秩序矛盾的关键所在。
五、結语
社会排斥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分析范式,其特点是不再孤立地讨论贫困等问题,而是将其纳入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然而,由于没能超越西欧社会这个特殊的环境,社会关系体系被简化为主流与边缘,从而社会排斥的全局性、连续性、系统性、结构性及内在机理不能得到真正认识。从社会整体看,社会排斥是一个秩序性问题,这种秩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类经济、社会、政治行为的结果,是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朱子在论及社会弊病之时,区分了“时弊”和“法弊”的概念。朱子指出:“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B14所谓时弊,就是时代之弊,是系统性、秩序性弊病,时弊的根本在人,因此归根到底是人心之弊。朱子认为,若仅仅是制度形式、法律和政策本身的问题,改变起来并不困难,但人的问题却不是外在的社会改造所能解决的,必须“变之以心”。在很多时候,制度问题其实是时弊的表现形式,若仅仅在表象上下功夫,只能是“灭于东而生于西”。因此,制度之弊并不是单纯的制度形式的问题,而是与人联系在一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制度的背后是秩序,而秩序问题是与人类行为及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整体秩序存在问题,那一定是系统性“时弊”,若不触动支撑这种秩序的价值体系,外在改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自发秩序”,还是人为制造的秩序,都没有摆脱时代的牢笼,它们是特定价值体系的两端。如果将沉迷不觉的生物状态以“自发秩序”的名义合理化,那么排斥就成为不可改变的问题。同时,在排斥性的价值体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强行从结果上消除差异,则问题必然会以另一种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实际上,社会排斥绝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如果人类摆脱无明、解除人心蔽障,社会秩序将是另一种形态。将人之道与经济生活割裂,将文化与公共秩序分离,这实际上是分而无理,停留在此,人类社会无法真正得到改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日益激烈的今天,人类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排斥的外在制约,而是对排斥性价值体系的摒弃。
注释
①[印]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②景晓芬:《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第2期。
③Touraine A. Face l'exclusion. Esprit, 1991, Vol.169, No.2, pp.7-13.
④Gordon,D., et al.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2000, pp.54-67.
⑤[法]塔基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4页。
⑥B12B13明立志:《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31、57—58、57—58页。
⑦⑧《太虚大师全书》第25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4、75页。
⑨彭华民:《社会排斥概念之解析》,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3—54页。
⑩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5页。
B11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B14黎靖德:《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7年,第2420页。
责任编辑:海 玉
Systematicness, Structure and Value Support of Social Exclusion
Yin Lu
Abstract:Since the 1990s, social exclusion has become a new way to study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overty. It provides a dynamic vision of recognizing vulnerable groups, but its significance is limited if it only stays on the appearance of exclusion without touching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the value system supporting this mechanism. If the consistency of social exclusion is analyzed through social systemic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 the value dimension can be clearly revealed. Social exclusion is both a result and a process; it is both an order and a value. Repulsive order is the result of human behavior, and behind it is an exclusive value system. If the value system of exclusion can not be touched, rebuilding the society externally can only change the form of problem expression. The order that human society needs is the natural and logical order in the humanistic sense, but not the spontaneous and exclusionary order in the biological state.
Key words:social exclusion; systematicness; structure; sequenc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