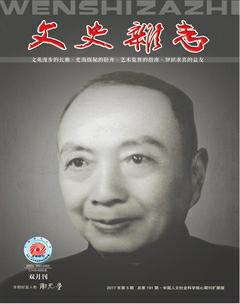四川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
屈小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传统乡贤是指地方上有道德声望,对乡邑建设有贡献的乡绅或者知识分子,也包括从乡邑走出去和走出去又走回来,对建设乡邑、服务乡邑、宣传乡邑做出成绩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及其他精英。就这点而言,新乡贤与之并无多大差异。当然,新旧乡贤所处的时代背景大不一样,这是无需多言的,但是,与乡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即使曾经远离故土,也是满怀乡愁,最终落叶归根)——则是共通的。诚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所言:“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1]。费孝通先生还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传统乡贤文化乃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是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的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今天建设新乡贤文化,自然当从传统中寻找经验,并利用传统乡贤文化的资源而赋予其新的生命。
一、学术文化源远流长
四川乡土学术文化堪称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惠文王时代尸子入蜀讲学著书。尸子以后,“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鬼谷(子)蛰伏峨眉,传纵横之术;鹖冠(子)隐于賨人(居于今四川渠县一带),述用兵之法……总之先秦哲人纷纷入蜀授徒播道,使四川乡土文化很早便接受了秦地及中原先进文化的濡染,开阔了巴蜀乡土学者及社会普通民众的眼界。
入汉以后,“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汉书·地理志下》)这说的是蜀地民众学养的进一步提升;此后,“巴、汉亦化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整个今川渝地区,包括今陕西南部民众,都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四川乡土文化的学术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
有了上述前提,四川乡土的易学、道学的普及才会拥有深厚的基础,也才具有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大气象、大格局。严君平是蜀中易学之宗;扬雄的《太玄经》等哲学著作亦可归入易学之列,他本人也是继严君平后的一位易学大师。蜀中易学由严君平开宗,中经汉代孟喜(东海兰陵人)、赵宾(师承孟喜)、谯玄、谯瑛,晋代成汉范长生,北朝卫元嵩,唐代阴弘道、李鼎祚,直至宋代陈抟、“三苏”而达到顶峰。宋代易学人才济济,成果累累(仅专著即达七十余部之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多能讲易。《宋史·隐逸下·谯定列传》记载的程颢、程颐在成都接受一位箍桶匠关于《易·未济》的耳提面命的故事,至今还被学者津津乐道。这说明其时易学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四川乡土文化的一部分。
古代四川不仅人文科学发达,而且自然科学更十分了得,它们大多渊源于民间,或可视为系由四川乡土文化的泉水所浇灌培育。如临邛火井(天然气井)与井盐的开发实受当地百姓“以竹木投以取火”的启迪;雕版印刷术的起步当归功于西川刻印历书的民间书坊;交子的推出是源自成都十六家商户的“制楮为券”。至于太初历和浑天仪的发明者落下闳则是从阆中走进长安的平民科学家;写《老子指归》、被常璩称为“道书之宗”的严君平一直生活于底层,在成都卖卜为业,做算命先生(今成都有君平街纪念他);严君平和张霸、杨宣、杨厚、董扶、折像、任安、杜抚等还开私塾授徒,各自门下动辄数百上千甚至数千人,为当时教化一方的乡贤,属于纯粹的民间学者……这里尤须推崇的是,当落下闳创历成功后,汉武帝请他担任侍中(顾问),他竟辞而不受,自己挟着行李悄悄返回了故乡。他来自乡土,自认为根基在乡土,归宿也当在乡土。类似落下闳这种淡泊名利,谋道不谋富,始终保持乡土本色的乡贤人物,在四川历史上还有很多,颇值得挖掘与褒扬。
二、文化世家薪接火传
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世家是指以诗书(或诗礼)传世的耕读世家,一般属于缙绅家族(或宗族)或知识分子家庭。清嘉庆四年(1799年)的状元郎姚文田(官至礼部尚书)曾自题一副书房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联语强调“积德”,而后才讲“读书”,说明旧时人们眼中的文化世家首先需有德行,无德的文化家庭其实并无文化;唯有诗、礼兼之,才能在乡土社会起到表率作用,推动乡邑建设的持续发展。
农耕文明时期的一个政治情况是:皇权不下县。四川县以下的基层,全靠乡绅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统治,有德行、有知识的乡绅可以决定基层社会的治理面貌。因此所谓文化世家的优势于此便显得格外重要。而这类文化世家的核心价值是学术文化。旧时四川乡土社会的文化世家的学术渊源都比较深厚。像宋代眉山“三苏”世家(苏洵、苏轼、苏辙及苏过)、华阳“三范”(范镇、范祖禹、范冲)、阆中“三陳”(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井研“四李”(李舜臣、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等就不必说了(其所出地域文化氛围之浓厚令人惊羡),即如近代的成都李氏(李璠、李镛、李尧棠即巴金)、成都双流刘氏(刘沅、刘松文、刘梖文、刘桂文、刘咸焌、刘咸荥、刘咸燡、刘咸炘、刘东父、刘伯谷、刘奇晋)、自贡龚(扇)氏(龚爵五、龚玉璋、龚长荣、龚长生、龚道勇、龚菊芬、龚倩、龚瑶妤、龚平)等,也都是名噪百年的学术世家、工艺世家。这样一类的世家大族以及更为广泛的城乡开明士绅、文人学子、艺人技工不仅通过自身的善独向善、学术技艺上的精益求精以及架桥修路、赈灾扶贫、兴学兴文、秉公用权等行为率先垂范,而且还通过家风、家训、家书、家谱和口传心授的方式教育子孙后代并影响到整个乡邑的进步、发展。这方面的事例自可为今用。其在县志一类的乡邦文献中随处可见,可谓史不绝书,稍加爬梳,即可获得。
如果按照费孝通先生的“乡土社会”说,那么,旧时文化世家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其实就是“长老权力”或“长老统治”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3]。而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和执行者,除了世家长老(族长、乡约、头人等)以外,还包括其身边和外围的乡村知识分子,如约史、账房、乡村教师(包括私塾、义学先生)、民族地区的巫师(如羌族释比、彝族毕摩)等。连同长老在内的有德望、有清声的乡村知识分子于社会动荡、乡土危难之际(譬如在战争时期)更能显出英雄本色,成为乡民“主心骨”式的“文化英雄”。费孝通先生说,这是因为他们“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并非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也不是由社会所授权,而是由乡民诚心诚意所拥戴、所服从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4]抗战时期四川乡间的王者成、王建堂父子就是这样的文化英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建堂(1912—1992)作为安县曲山镇(今属北川县)的一名普通乡村小学教师为民族大义所激,登高疾呼,在当地迅即组织起一支拥有176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后改名“安县特征义勇队”),以血书请求上阵杀敌,获得政府批准。就在即将奔赴抗日前线前夕,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送来一幅他连夜赶制出的旗帜为队伍壮行。旗帜为一方大白布,正中以浓墨书一擘窠大字“死”;右侧为两行有力楷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为一组四言韵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