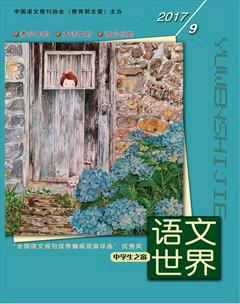似曾相识的精灵
无论是一首简朴的歌谣,还是一部复杂的交响曲,真正美妙的音乐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就像是神借用一双平庸的手所写下的布满玄机的文字,它是天堂所泄漏的一线灵光。没有哪一个词比“天籁”更能描述它的性质了。对于听者来说,即便他第一次听到某个旋律、某首曲子,亦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仿佛耳畔的旋律只是引动了他内心隐秘、沉睡的情感,如同一道闪电在顷刻之间照亮了他心底的黑暗。于是,他完全被震慑住了,忘掉了尘世的一切,他的大脑开始失神,灵魂遁入邈杳的远方。
在这个奇妙的瞬间,他心灵中的某个神祇复活了。这种感觉并不总是能够用“喜悦”“忧伤”一类的概念加以解释的,人们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迷失”。
迷失,既是遗忘,现实世界的一切羁绊顿时冰释;又是一种深刻的记忆,仿佛听者本人,他的整个灵魂和肉体都是一个久远的闪电所留下的雷声,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个尘世,通往未知世界的神秘、浩瀚的门被打开了。
在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音乐的规戒与禁忌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仅仅与过分的感官享乐有关,所谓逸乐亡身,淫曲丧邦。在一系列简单的事实与经验背后,是人类对于“迷失”的担忧与无所适从。它与古老的宗教热忱——超脱尘世的行动与情感相比,犹如夜晚之于白天。音乐成为宗教附庸、教化手段的历史如此漫长,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们从“美国之音”中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偷尝禁果的快乐以及在靡靡之音中意志瓦解的恐惧。
让我们重新回到闪电这个比喻。
与雷声的到来不同,闪电的出现毫无预感。闪电过去了,可它那被燃烧的枝形光弧依然停留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当我们听到一首曲子并被它打動时,所有的感觉都朝它开放。音乐消失了,心灵依旧眷恋着它。你感到超凡入圣,宠辱尽失,可道又不可道,这种感觉究竟来自何处。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第一次听到《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时的情景。它像一道被打开的陈旧布景,敞露出三月末的空旷的乡间田野。当时,我从邻近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这首歌。那天风很大,歌声随着风向的变化断断续续地传过来,忽隐忽现。就像田里的麦苗和河滩里的青草,只有风吹过时,才能看到绿色柔软的波动,这首歌的节奏就是风的节奏,是河水波纹的节奏,是临近中午时寂静无人的旷野的慵懒与静谧。我站在河边的树下,竖起耳朵,等着风送来令人沉醉的旋律,送来三月初春的芳香。
然而歌很快就消失了,接下去是天气预报。我感到若有所失,抑郁不欢。刚才还是阳光灿烂,鸟语花香,平庸、猥琐、习以为常的事物在阳光下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可一转眼,不知从哪儿飘来一片乌云,我看到阳光已经收敛,小鸟飞向远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堆积在心头的幸福也在一点一点的冷却,变得淡漠、模糊,终至于完全消失了。
这支歌曲有着摇篮的节奏,带有眠歌的色彩,应和着少年人的落寞和幽光狂慧,然而,当时它所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对春天的赞美。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首歌曲能够像它一样激起我对春天的眷恋,后来,我曾反复聆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维瓦尔弟的《四季》、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始终未能复活初听《洪湖水,浪打浪》时对于春天的感觉,未能再现那个春天的绚烂多姿。甚至,我成年再听这部歌剧,竟也觉得它是那么稀松平常,而且,歌曲所描述的是遍地菱角的深秋,与春毫无关系。这与恋爱的情形十分类似,初次见面的新娘与日后同床共枕的伴侣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人。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当初使我震慑的那个精灵究竟是什么?它藏于旋律之中,依附于回忆中的一草一木,要向我传达怎样的信息?或者说,我内心被激动的真实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去了何方?由此,我想到两个词语:突然和重现。
突然。我拐过一个街角,看到了她,我们原先并不相识,但直感告诉我,我认识她。我似乎在梦中见到过她,并与她肌肤相亲。也许按照一般的看法,她并无任何出众之处,但我还是被她迷住了,心被锋利的刀片划了一下,我站住了,看着她,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她在人群中消失。有时,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局部,她身上的某一件色彩艳丽的饰物,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的如痴如醉。我的心在狂跳。
在这一刻,我并不喜悦,尽管有那么一点兴奋,也不悲伤和忧戚,更多的是惘然。我看到了那个被重重包裹的核,它不在少女身上,不在乐曲之中,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一个更高规格的存在物,就像闪电,在短短的一瞬中,我与它不期而遇,却又得而复失。领受天籁的经验使我不顾一切地想抓住它,留住它,并渴望着再次回到它温暖的巢穴中去。
突然,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但只要你被音乐打动,每一次都包含了“突然”性质,包含了一个让人迷失的固执的命令。
晚年的博尔赫斯双目失明。有一次,他在一个咖啡馆里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让他谈一谈,他在漫长而短暂的一生中所感受到的生活的意义。诗人没有片刻的犹豫,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他在《怀念安赫利卡》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假如我死了,我失去的,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去……”
而在另一首短诗中,博尔赫斯曾坦率地承认,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幸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罪过。诗人的这一回答是我们可以预料的。然而,博尔赫斯在给出这个回答之后,立即又补充了一句:“不,请等一等。”他似乎想起了一件事,陷入了沉思,好像这件事最终将改变他刚才的回答。他凝神屏息,侧耳倾听。此时,咖啡馆里正在播放着一首他所熟悉的乐曲。是巴赫,还是莫扎特?你无法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光泽,甚至,他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然而毫无疑问,诗人在出神。
“不,”终于,博尔赫斯认真地修改了他刚才的回答,“只要音乐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意义的。”
不久之后,博尔赫斯发表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题目就叫《只要音乐还在继续》。
在那个时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家咖啡馆中,音乐所肯定的并不是他的生活,它没有改变什么,它只是提供了个可能——用它来重新解释庸常的生活中所隐藏的事物,用它重新为我们的习惯命名。它给出了一个假定性的情境,一只容器。所有的经验都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因为虚幻,所以真实。endprint
重现。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刻,我再次与她不期而遇。过去不经意式痴迷的一瞥所埋下的种子已经发芽,并生根开花。眷恋加深了。我与她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契约。不管物是人非,沧桑变幻,我还是闻到了同样的芬芳,感受到了同样的阳光或蒙蒙细雨。每一次都向前一次回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繁殖,契约正在变得牢不可破。我感到神清气爽,只要一看到她,什么担心都没有了。没有贪欲,没有失去它的恐惧与焦虑。她招之即来,我只要按下一个键钮,拿起一张唱片,马上就要与她亲近的预感充满了我的整个身心。一次渴望着另一次,就像海浪,永远在说着下一次……
有时,你对一首曲子已烂熟于心。你甚至能随时唱出它的全部旋律,于是,渐渐地,你对它感到了厌倦。当你一口气把肖邦的一首馬祖卡听上二十遍,你就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听它了。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曾经谈到过如下感受:十月革命之后,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是最受当局青睐的音乐家。这就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只要你打开收音机,从里面传出的一定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在傍晚时分你走进一幢建筑物,家家户户的窗口飘荡出来的总是《天鹅湖》。《天鹅湖》成了一场噩梦。
然而《天鹅湖》注定了不会从人间消失。听了二十遍的马祖卡不会消失。有一天,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回荡在你的耳边,你还是会怦然心动。与第一次听到它时的激动相比,你会惊异地发现,它依然完好无损,什么也没有减少。
列文曾一度发誓不再与吉提见面。他无法原谅吉提的伤害。当吉提的马车经过他的农庄时,他远远地注视着马车,想象着她的样子。没有她,生活依然在延续。可是,他在奥勃浪斯基公爵的家庭聚会上再度见到吉提时,他脆弱的内心立刻变成了风暴中的海洋。
“看见”取消了“想象”:哦,她就在那里,坐在客厅的一角望着自己,她是那么的生动,那么的具体。伤害、嫉妒、仇视、憎恨顿时烟消云散。列文的心战栗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与她靠近。当他与吉提重修旧好、从公爵家中出来之后,正是鸽子飞过蓝天的黄昏时间,他感到天空那么高远,那么幽蓝,他的体内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将整幢房子举起来。
试图解释或想象音乐也许是可笑的。音乐的出现是一种即时的场景,它是即兴的。它联结着记忆,但它全部的奥秘却在于“此刻”。此刻,我在聆听,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听,既是通往音乐深处的手段,又是根本目的。
我曾经听过数千遍的《东方红》旋律。但当它作为《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华彩乐句出现在第四乐章的尾声,我还是被它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旋律是不是江青授意加进去的,对我来说毫无关系。在我期待它出现的时候它出现了,这就足够了。
(选摘自《格非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