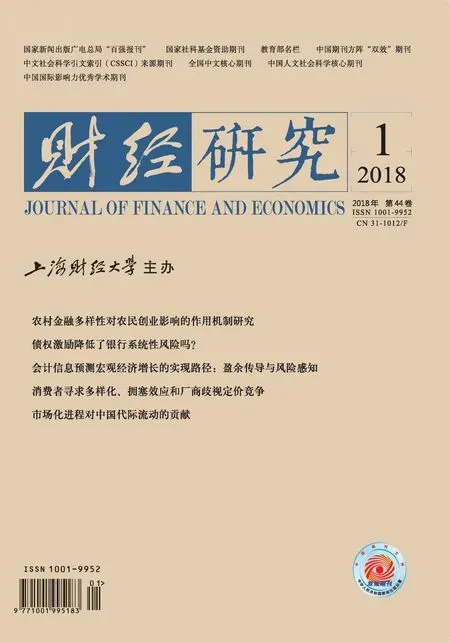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杨慧辉,汪建新,郑月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会计学院,上海 201620;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1620)
一、引 言
探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时,不应忽视公司控股股东的作用。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控股股东会对股权激励下的公司信贷融资需求产生影响。同时,基于信号传递效应,控股股东会影响作为信贷供给方的银行的信贷决策,从而影响股权激励下的公司信贷融资能力。对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政府干预以及隐性担保等会对银行的信贷决策产生影响(方军雄,2007;曹春方等,2015)。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治理动机和权力的差异会对股权激励的信号传递效应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评估,最终影响信贷契约选择(肖作平等,2012;冉茂盛等,2015)。
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信贷契约选择的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管理层代理问题展开。一方面,股权激励可以减弱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和风险厌恶倾向(Jensen和Meckling,1976),提高会计盈余质量(Gong和Li,2013),进而缓解与银行等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债务代理成本(Garvey和Mawani,2005)。在股权激励下,银行等债权人可能愿意提供规模更大、期限更长和成本更低的债务融资(Harris和 Raviv,1991;Bae和 Goyal,2009)。但另一方面,股权激励(尤其是股票期权激励)会使高管具有更强的侵占债权人利益的动机(Coles等,2006;Panousi等,2012),由此产生新的代理问题(Bebchuk和Fried,2010)。此时,银行等债权人会通过降低信用评级(Kuang和Qin,2013)、增加债务保护性条款(Ge等,2012)、缩减融资规模(Hackbarth 等,2006;Bebchuk 和 Fried,2010)、缩短融资期限(Datta 等,2005;胡国强和盖地,2014)以及索要更高风险溢价(Shaw,2012;Kabir等,2013)等方式进行自我保护。然而,上述研究忽略了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本文将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层和银行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剖析控股股东的治理效应下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影响。
本文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特征的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下的信贷契约选择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第一,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当前有关股权激励与信贷契约之间关系存在广泛争议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金融机构甄别并控制股权激励公司的信贷风险、国企深化改革中政府放权以及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激励、国有控股股东与信贷契约选择
在国有控股股东治理无效的“所有者缺位”的环境中推行股权激励容易诱发更多的过度投资;而过度投资需要包括银行信贷在内的资金(特别是长期资金)支持,但这也将影响银行所需要的风险溢价。首先,与国有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存在管制类似,国资委对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薪酬也进行了管制,①按照2008年国资委颁发的《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行权有效期内,高管股权激励收益占本期股权激励授予时薪酬总水平(含股权激励收益)的最高比重,境内上市公司原则上不得超过40%;股权激励实际收益超出上述比重的,尚未行权的股权激励不再行使或将行权收益上交公司。这会降低高管可实现的股权激励薪酬。当国企管理层的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薪酬都受到管制而无法实现收益最大化时,其对在职消费和政治晋升等隐性激励的追求就会增大。管理层可能通过过度投资的“帝国构建”行为一方面扩大所有者天然的信息劣势(钟海燕等,2010;李延喜等,2015),使其在职消费更加隐蔽和难以发现;另一方面迎合政治晋升所需的增长和发展的政绩要求(白俊等,2014;靳庆鲁等,2016)。其次,股权激励薪酬最终需要通过标的股票的高位抛售实现。在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现实环境中,当投资者短视而不容易判断损害企业价值的过度投资时,通过过度投资营造企业发展态势良好的假象以最大化短期股票价格是理性的管理者最大化自身股权激励薪酬的重要手段(Polk和Sapienza,2009)。那么,如何满足股权激励诱发的过度投资的资金需求?这需要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来交叉运用。在债务融资方面,政府仍在信贷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作用(陆正飞等,2015),其在经济和政治利益驱动下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使国有企业容易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更长期限的贷款(方军雄,2007;曹春方等,2015)。迫于政府干预的影响,银行在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方面满足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进行契约的次优化选择,这将致使国有企业产生银行债务软约束的现象大量存在,提高银行的信贷风险;银行将会通过提高贷款利率等措施来补偿由此产生的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国有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会导致信贷规模扩大、信贷期限延长和信贷成本上升。
(二)股权激励、非国有控股股东与信贷契约选择
相对于国有控股股东,非国有控股股东通过控制公司董事会或直接作为高管密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实质掌控着上市公司的财务决策和对高管的激励政策,伴随而来的是其在公司治理中产生监督或侵占效应。而控股股东所发挥的治理效应不同,会导致其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动机不同,进而对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匹配的非国有公司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动机更倾向于弥补控股股东监督的不足;这容易向银行传递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改善和提升的积极信号,以缓解“信贷歧视”,进而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大规模、长期限和低成本)。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匹配使其在公司治理中更倾向于发挥监督的治理效应。利益侵占行为使两权匹配的终极控股股东获取的控制权私利(凭借控制权获得的私利)等于其成本(按照现金流权承担的公司价值损失),从而无利可图,因此也就丧失了利益侵占的动力(LaPorta,2002)。此时,企业价值的提升成为终极控股股东最根本的财富增长点。控股股东对企业的大额投资承担了投资组合不分散的风险,自身利益更多地与企业利益相关,因此会通过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对企业的重要事件进行干预和影响,防止企业高管层的低努力水平、非生产性消费行为、短视行为等损害控股股东利益的自利行为(Cheung等,2006)。控股股东对自身利益的主观追求形成了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客观约束。但是,由于现代企业的代理链条不断延长,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处于代理链条顶端的终极控股股东无法对处于代理链条末端的上市企业的每项财务决策进行干预和控制,而是按照金额和性质分级授权给董事会和高管。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使得控股股东无法对高管层的任何自利行为都可实现监督和约束,企业内部主要的代理问题是在管理层方面。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下控股股东的监督不足,控股股东需要通过对高管层激励机制的设计以缓解管理层的代理问题。此时的股权激励才将真正发挥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的作用,进而缓解了与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信贷风险,降低了债务代理成本。因此,银行会愿意增加对企业的信贷(特别是长期信贷)的额度,并给予比较优惠的贷款利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非国有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会带来宽松的信贷契约(信贷规模扩大、信贷期限延长和信贷成本下降)。
而在终极控股股东因两权分离而具有掏空动力的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容易向银行传递公司控股股东与管理层两类内部人合谋的治理水平不升反降的信号,进而使得银行采用更为严苛的信贷契约(小规模、短期限和高成本)。终极控股股东两权的分离是其掏空的原动力,因为终极控股股东凭借其控制权掏空企业所获取的收益大于其需按照现金流权比例承担的企业价值损失,可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净收益(LaPorta,2002)。此时,控股股东要想通过对底层企业的投资、融资、日常经营、利润分配等决策的操纵来实现掏空净收益的行为,必须由作为企业行为的实际执行者的高级管理层经手才能实现(潘泽清,2004),也就必须给予高管层额外的回报才能收买高管层与之合谋(严也舟,2012)。与货币薪酬相比,股权激励薪酬更容易成为控股股东收买高管与之合谋进行掏空的工具,降低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首先,股权激励使民营企业的高管成为控股股东一样的内部股东,这就实现了两者的利益趋同,加强了两者的利益捆绑。其次,股权激励作为长期激励的机制设计,存在股票期权激励的等待期或限制性股票激励的锁定期的规定。高管要实现股权激励薪酬,首先要达到激励方案中规定的等待期或锁定期的服务期限,这就延长了高管与控股股东利益捆绑的时间。陈仕华和李维安(2012)发现,控股股东在通过转移上市公司资源进行掏空时,会授予高管股权激励而对高管进行收买。两权分离的终极控股股东会通过过度投资将原本作为现金流权共享收益的部分转移,作为控制权私有收益(刘星等,2009;俞红海等,2010)。因此,控股股东基于谋取控制权私利而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会诱发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杨慧辉等,2016),导致高管具有更多的资产替代以侵占债权人利益的动机(Coles等,2006;Panousi等,2012),进而会引起企业对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融资需求的增加,这将增加企业财务危机和债务违约的风险,降低了公司出现违约时的抵押品资产价值,提高了预期破产成本,进而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包括银行在内的外部投资者的利益。非国有控股企业并没有国有企业那样的优势,可将政府作为贷款的政治担保,只能靠抵押物和自身经营的收益等来获得银行长期和规模大的贷款。一旦其控股股东与管理层由于股权激励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而侵占公司利益,那么就会降低企业未来业绩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提高了银行贷款的风险。银行会相机缩减银行信贷规模、缩短信贷期限和提高贷款成本。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b: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非国有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会带来严苛的信贷契约(信贷规模缩减、信贷期限缩短和信贷成本上升)。
三、研究设计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下的样本选择
为了避免单纯从行业归属、资产规模、终极控股股东性质和治理效应方面选择未披露股权激励的公司组成配对样本(对照组)而产生的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因股权激励与信贷契约选择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而可能产生的研究结论偏差,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本文数据来自万德和国泰安数据库。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上下1%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1.股权激励处理组。为剔除我国资本市场和股权激励政策环境在2009年前后存在巨大差异造成的噪音,①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之初的2006−2008年,股权激励的政策处于摸索制定阶段,而且股权分置改革带动了资本市场的疯狂,直至2009年资本市场才回归理性;这些噪音的存在可能会使对该阶段股权激励的研究存在结论偏差。我们选取2009−2015年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企业为初选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了样本筛选:(1)存在重大财务困境的企业(ST/*ST)的信贷契约选择会因财务困境的影响而不能体现股权激励的作用,因此予以剔除;(2)本文旨在考察非金融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其与金融机构订立的信贷契约的影响,因而剔除实施股权激励的金融企业;(3)股票增值权最终以现金结算,并非实质的分享剩余收益的股权激励,因此予以剔除;(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的初选样本为714份股权激励计划对应的上市公司。
我们进一步对股权激励处理组的初始样本进行了筛选和分类。首先,我们设定了股权激励动机的识别标准(见表1)。结合股权激励契约关键要素取值的相关制度规定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窗口期间的市场反应,借鉴Matolcy等(2009)以及吕长江等(2009)对股权激励动机效应的划分方法,我们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前30个交易日的CAR为负)①当前法规明确规定行权(授予)价格的底线应以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企业标的股票的市价为基础来确定。2006年1月1日实施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仅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底线进行了明确,规定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应低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和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较高者。2006年9月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出台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不对股权激励方式进行区分,统一要求股权激励的授予(行权)价格不应低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和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较高者。2008年3月证监会出台的《股权激励备忘录1号》进一步规定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折扣问题:如果标的股票的来源是存量,即从二级市场购入股票,则按照《公司法》关于回购股票的相关规定执行;如果标的股票的来源是增量,即通过定向增发方式取得股票,其实质属于定向发行,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50%。在管理层自利或者控股股东-管理层利益共同体掏空的环境中,作为激励对象的管理层有能力凭借其内部人的信息优势,通过压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披露前的企业股价以便获得较低的行权价格,表现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将会在企业股票持续下跌后首次披露,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杨慧辉,2009;张治理等,2012)。和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或解锁条件的合理性(是否高于公司自身近3或5年的平均业绩;或是否高于公司所在行业的地位加权平均值)来区分股权激励的激励型动机和非激励型动机。对于非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我们再从公司的控制链层级、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股权分散度、管理层长期任职、大股东在董事会席位等因素构建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从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总经理是否为职业经理人、董事长是否在上市公司领薪、企业是否属于基业长青型的家族企业等因素构建控股股东−高管合谋指数,然后将合谋指数高和管理层权力大(超过均值)的非激励型股权激励分别识别为合谋动机和福利动机。其次,依据股权激励动机识别标准,我们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初选样本进行了动机的识别,并将其与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两权分离度进行匹配(见表2)。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福利型股权激励的占比为93.90%,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激励型股权激励的占比为90.78%,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合谋型股权激励的占比为92.99%。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假设相符。

表1股权激励动机识别标准

表2股权激励子样本细分
我们最终以77份国有上市公司的福利型股权激励、276份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激励型股权激励和305份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合谋型股权激励共计658份股权激励计划对应的上市公司为处理组。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观测值,共获得2009−2015年448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2.未实施股权激励对照组。2009−2015年,以从未披露过股权激励计划的A股上市公司为PSM下配对样本(对照组)的初始构成,我们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了处理:(1)与处理组处理方法相同,剔除了存在重大财务困境(ST/*ST)的企业和金融企业。(2)由于实施股权激励的处理组中不存在林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物流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水上运输业以及教育业,为避免匹配过程中受到行业因素的影响,我们剔除了对照组中相关行业的样本。(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我们最终得到2009−2015年潜在配对初选组共1923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我们以股权激励为因变量,并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从公司经营特征、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和高管特征三方面选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基于因变量较自变量滞后一期的Logit模型(模型1)确定样本的倾向得分:

对于公司经营特征,我们选择了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公司成长性、资产负债率、市场竞争力水平;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我们选择了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独立董事比例;对于高管特征,我们选择了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年龄。我们还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依据2012年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对制造业按行业大类划分,其他行业直接按照行业门类划分。变量定义与Logit回归结果见表3。

表3变量定义与 Logit回归结果
一般而言,Logit回归的AUC值大于0.8则表明模型所采用的指标合适(Marco和Sabine,2008)。Logit回归分析得到的Pseudo R2值和AUC值分别为0.1853和0.8259,表明以此结果作为匹配模型来计算倾向得分较合理。根据Logit估计结果,我们计算了每家公司可能实施股权激励的概率值,即倾向得分值(PS),并按照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的方法进行了一对一的样本匹配。
(二)实证模型
我们将以实施股权激励的观察样本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配对样本组成的总样本为研究对象,控制企业特征、治理质量、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模型2)。主要的测试变量为EI×Post,其系数表示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信贷规模、信贷期限和信贷成本的影响。

由于激励机制存在滞后效应,在模型2中,我们设定信贷契约要素变量相对于股权激励变量滞后一年,以避免股权激励与信贷契约选择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企业信贷期限、规模以及成本的选择还受到企业的资产结构、资产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带来的财务风险、短期偿债能力、控制链层级等企业特征的影响(Shaw,2012;Kabir和Li,2013;刘星等,2015)。本文控制了这些影响公司信贷契约的主要因素。此外,本文还引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变量定义见表4。

表4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为检验不同控股股东特征下的股权激励实施与信贷契约选择的关系,我们首先分析了PSM下股权激励处理组与非股权激励对照组的处理效应(见表5)。在三种样本匹配方法下,DM、DS和DC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的ATT值均显著为正,在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的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的ATT值分别显著为负、负和正,在终极控制人两权匹配的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的ATT值则分别显著为正、正和负。这表明在匹配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公司经营特征、内部治理结构特征以及高管特征之后,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使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但银行基于风险控制会要求更高的贷款成本,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股权激励在终极控制人两权匹配的非国有企业中的实施才能帮助其获得更为有利和优惠的信贷契约,这支持了假设2a;股权激励在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的非国有企业中的实施反而会使企业获得更为严苛和不利的信贷契约,这支持了假设2b。
双重差分模型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6。研究对象是按照股权激励动机细分的658份股权激励计划的观察样本和以PSM获得的一对一的未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配对样本。在控制了影响信贷契约的其他因素和信贷契约结构要素的内生性后,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实施变量(EI×Post)与信贷规模、信贷期限和信贷成本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假设1。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实施变量与信贷规模和信贷期限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信贷成本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假设2a。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实施变量与信贷规模和信贷期限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信贷成本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假设2b。

表5基于 PSM 的差异分析

表6股权激励实施与信贷契约选择
五、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对股权激励样本及其对应的非股权激励配对样本进行重新选择,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结论偏差。对于714份已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正式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对应的上市公司,我们直接根据控股股东将其细分为国有企业组、两权匹配的非国有控股股东组和两权分离的非国有控股股东组。对于配对样本,我们遵循以下原则进行一对一配对:(1)与观察样本公司属于同一行业;(2)与观察样本公司的资产规模相近;(3)在实证区间内没有进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披露;(3)与观察样本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性质和治理效应相同。
其次,我们采用两阶段回归的处理效应模型来控制可能存在的股权激励与信贷契约选择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我们以股权激励为因变量,以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因素为解释变量,采用Logit回归(模型1)来分析哪些公司更可能实施股权激励,并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内生选择偏差调整项代入第二阶段的回归中(模型2)。
最后,为减少实证模型中变量的代理指标选择偏差可能带来的研究结论偏误,我们对前文模型中的一些代理指标进行了重新选择。借鉴胡国强等(2014)的方法,采用增量指标计量,即分别用银行借款增长率、长期借款增长率和借款利率增长率作为反映信贷契约要素的信贷规模、信贷期限和信贷成本的代理指标。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以实施股权激励的观察样本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配对样本组成的总样本和实施股权激励的观察样本为研究对象,再次进行模型2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同样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六、结 论
在我国股权相对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中,控股股东有动机也有能力影响股权激励下的公司融资需求,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调节作用。我国当前的股权激励主要是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中推行。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中,控股股东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能够影响包括管理层激励机制设计在内的公司重要决策,进而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而且,控股股东的治理目的和权力差异,可能使其对股权激励效应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另外,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首要的债务融资方式,银行作为企业的主债权人,对不同类型控股股东的企业会有不同的信贷政策。本文将公司的控股股东、高管以及作为公司主债权人的银行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股权激励的信号传递效应,剖析在国有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非国有控股股东和两权匹配的非国有控股股东三类不同的控股股东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股权激励中的控股股东、管理层和银行三方博弈对企业信贷契约选择的影响。在控制了规模、期限和成本这三大信贷契约关键要素的内生影响和影响信贷契约要素选择的其他因素后,基于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研究了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特征的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下的信贷契约选择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容易诱发管理层基于自利而扩大信贷规模和延长信贷期限的行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银行会满足国有企业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期限的需求,但会通过价格因素(即提高信贷成本)弥补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所产生的风险。在控股股权两权匹配的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的实施使得企业容易获得规模更大、期限更长和成本更低的宽松信贷契约。在控股股权两权分离的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的实施使得企业容易获得规模更小、期限更短和成本更高的严苛信贷契约。
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的影响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控股股东的治理效应直接影响股权激励的设计动机,进而影响股权激励发挥的实际作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会加剧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股权激励容易成为管理层自谋福利的工具,加剧了国企的管理层代理问题;而政府干预形成的银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会导致股权激励诱发管理层更多的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偏好。非国有企业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与否会影响控股股东的治理效应,进而导致股权激励动机的不同。控股股东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设计动机倾向为激励,银行会形成债务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提升的预期,这确实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缓解信贷歧视;但非国有控股股东两权高度分离时股权激励设计动机倾向为合谋,银行会形成债务企业内部治理水平降低的预期,进而导致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
[1]白俊,连立帅. 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所有制歧视抑或禀赋差异?[J]. 管理世界,2007,(8):23−34.
[2]白俊,连立帅. 国企过度投资溯因:政府干预抑或管理层自利?[J]. 会计研究,2014,(2):41−48.
[3]曹春方,许楠,逯东,等. 金字塔层级、长期贷款配置与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5,(2):115−165.
[4]陈仕华,李维安. 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大股东的一个合法性“赎买”工具[J]. 经济管理,2012,(3):50−59.
[5]方军雄. 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J]. 经济研究,2007,(12):82−92.
[6]胡国强,盖地. 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信贷决策——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4,(4):58−65.
[7]金宇超,靳庆鲁,宣扬.“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J]. 经济研究,2016,(10):126−139.
[8]李延喜,曾伟强,马壮,等. 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J]. 南开管理评论,2015,(1):25−36.
[9]刘星,付强,郝颖. 终极控制人代理、两权分离模式与控制权私利[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5,(1):75−85.
[10]刘星,窦炜.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J]. 中国管理科学,2009,(5):156−165.
[11]陆正飞,何捷,窦欢. 谁更过度负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J]. 经济研究,2015,(12):54−67.
[12]吕长江,巩娜.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及其经济后果分析——以伊利股份为例[J]. 会计研究,2009,(5):53−61.
[13]潘泽清,张维. 大股东与经营者合谋行为及法律约束措施[J]. 中国管理科学,2004,(6):118−122.
[14]冉茂盛,李文洲. 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债务融资与资金侵占——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样本分析[J]. 管理评论,2015,(6):197−210.
[15]严也舟.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2012,(4):28−35.
[16]杨慧辉,奚玉芹,闫宇坤. 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J]. 软科学,2016,(8):92−96.
[17]俞红海,徐龙炳,陈百助. 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J]. 经济研究,2010,(8):103−114.
[18]肖作平,廖理. 终极控制股东、法律环境与融资结构选择[J]. 管理科学学报,2012,(9):84−96.
[19]钟海燕,冉茂盛,文守逊. 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与公司投资[J]. 管理世界,2010,(7):98−108.
[20]Bae K H,Goyal V K. Creditor rights,enforcement,and bank loans[J]. Journal of Finance,2009,64(2): 823−860.
[21]Bebehuk L,Fried J. How to tie equity compensation to long-term results[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0,22(1): 99−107.
[22]Cheung Y,Rau R,Stouraitis A. Tunneling,propping,and expropriation:Evidence from connec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2(2): 343−386.
[23]Coles J L,Daniel N D,Naveen L.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risk-tak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 ics,2006,79(2): 431−468.
[24]Datta S,Iskandar M,Raman K. Managerial stock ownership and the maturit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deb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5,60(5): 2333−2350.
[25]Garvey G T,Mawani A. Risk-taking incentives of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and the asset substitution problem[J]. Accounting & Finance,2005,45(1): 3−23.
[26]Ge W,Kim J-B,Song B Y. Internal governance,legal institutions and bank loan contracting around the world[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18(3): 413−432.
[27]Gong J J,Li S.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prediction[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3,40(4): 647−674.
[28]Hackbarth D,M iao J,Morellec E. Capital structure,credit risk,and macroeconom ic condi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2(3): 519−550.
[29]Harris M,Raviv A.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e,1991,46(1): 297−355.
[30]Jenso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 ics,1976,3(4): 305−360.
[31]Kabir R,Li H,Vels-Merkoulova Y V.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and the cost of deb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3,37(8): 2893−2907.
[32]Kuang Y E,Qin B. Credit ratings and CEO risk-taking incentiv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3,30(4):1524−1559.
[33]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et al.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1): 1147−1170.
[34]Marco C,Sabine K. Som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8,22(1): 31−72.
[35]Matolcsy Z,Riddell S,W right A. A 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rket values and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expenditure[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9,5(2): 95−107.
[36]Panousi V,Papanikolaou D. Investment,idiosyncratic risk,and ownership[J]. Journal of Finance,2012,67(3): 1113−1148.
[37]Polk C,Sapienza P. The stock marke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1): 187−217.
[38]Shaw K W. CEO incentives and the cost of debt[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2,38(3): 323−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