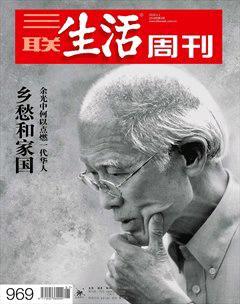减税的潜力在哪里?
邢海洋
4月到2017年底,特朗普的减税计划终于落地,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了21%,个人所得税率也有所下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除此之外,企业承担的社保缴费也远高于国际水平。全球降税的声浪中,我们是否会跟进呢?
其实早在美国之前,中国政府就致力于为企业减负了。“五险一金”中有一种99%的人从未有幸領取过的失业保险金,缴费比例一度高达工资的3%。因为领取率低,该保险金曾年年巨额结余,在2015年开始的企业减负中首当其冲,至今已经降至1%。至于不断发出“入不敷出”警报的养老社保,对尚有余力的如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的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份,单位缴费比例已经由20%降至19%。多次调整后,我国企业缴存的“五险一金”费率中位数从44%降至40%以下,约降低了4.5个百分点。相对于约70%的企业综合税率,相当于降低了6.4%。当然,这和美国大刀阔斧一下子将企业所得税免去了一小半比,显得微不足道。并且,中国的减税,最容易的部分降下去以后,又到了一个瓶颈期。
美国减税之所以“四两拨千斤”对周边国家形成了虹吸效应,在于美国的税负体系中企业所得税只占很少的部分,这就给予它较为灵活的操控能力。虽然美国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公司,但是公司所得税只占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10%左右,而个人所得税占比达到48%。以直接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林林总总的围绕纳税人收入的税种“层层包围,处处设卡”,将个人的各种收入都纳入到税收体系。而相对于个人,企业作为创造价值、追逐利益的现代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对税收体系最为敏感,却不是纳税的主体,而是价值传导的“二传手”。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商品流动的自由度远胜于企业迁移的自由度,企业的自由度又远胜于个人在国家间的迁徙能力,在收入流向的终端,也就是个人处征税,也就有了最稳定的税基。又因为征税于终端,挣得多的多缴,挣得少的少缴,除了“养活”公务人员、为公共服务付费,税收对收入二次调节的“副作用”也发挥了出来。
我们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收体系,一大半的税收“隐藏”在商品之中,最后由消费者买单。而富人消费少,穷人购物却是刚需,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无疑是向穷人征集了重税。扭转这一税负失衡,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这条改革路径,在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中已见端倪。在2006年至2011年的5年间,国家曾连续3次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从800到1600到2500再到3500元。可最近的6年时间,曾经紧锣密鼓的个税调整彻底哑火,于是乎个税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16年突破万亿大关,增速竟达到17.1%。我国的个税税率分为七档,刚过3500元起征点还只有3%的税率,可很快税率阶梯就“陡峭”起来,一旦应纳税部分超过4500元就是20%的税率,超过9000元就是下一个25%的阶梯,对于城市中勉强生存的所谓“中产”,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触碰到四分之一收入来纳税的高收入。也就是说,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国人,已有相当比例与西方国家居民的税负看齐了。
减税的另一个重头戏流转税也在下降,2016年启动的营改增一年共减税7000亿元。但最高档增值税率仍为17%,远高于海外消费税的税率。当然流转税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非企业的真实税负。
最终,企业的真实税负还是高在了“五险一金”等人工费率上,即使下降了,我国企业缴费养老金比例为19%,是美国的3倍,也高于福利国家瑞典的11.9%、老龄化国家日本的7.7%,而企业减负的潜力也正在此。一些省份养老金亏空,是1992年退休金由企业向社会转制的结果,巨量国企收益理应用于弥补这个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