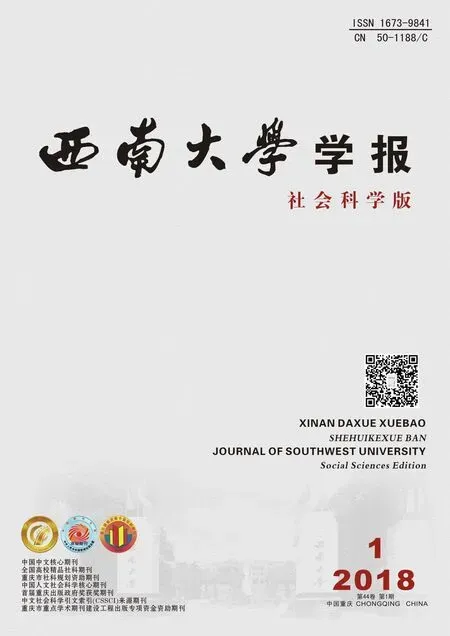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论心理活动的生成机制及其当代意蕴
曹 青 云
(云南大学 哲学系,云南 昆明 650091)
亚里士多德论心理活动的生成机制及其当代意蕴
曹 青 云
(云南大学 哲学系,云南 昆明 650091)
心理活动,例如知觉、想象、思考是如何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心理活动是什么”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理活动既不是单纯地由外在的物理对象引起的生物体的生理运动,也不是单纯地由灵魂实体引起的精神活动,而是由内在的灵魂作为原初的动力因和由外在的物理对象作为辅助的动力因协同作用而引起的生物体的运动。本文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的四种解释模型以及灵魂作为不动的动者对身体的作用,进而指出心理活动的原因机制不是物理线性的,而是外在的物理原因和内在的灵魂原因协同作用的双层结构。而这个双层结构为我们解决当代心灵哲学的“心理因果性”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灵魂;心理因果性;运动
心理活动(mental event),或称心灵活动,如知觉、想象、思考等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像物理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由外部的物理刺激引起的物理生理运动,还是像二元论者认为的那样,是精神实体的运动?一方面,还原论的物理主义取消了心灵活动的实在性和原因效用;另一方面,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无法解释心灵活动和生理活动的交互关系。因此,对心灵活动的生成机制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何为心灵活动”。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当代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或二元论的学说,他认为任何心灵活动都包括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它们是由灵魂引起的、发生在身体中的运动。因此,心灵活动是“复合的”,它既不是单纯地由外部物理对象引起的物理运动,也不是单纯地由精神实体引起的精神活动。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范式称为“质料形式主义的”(Hylomorphic),这是在物理主义和二元论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1]。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心灵活动“如何”发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动是如何发生的*亚里士多德的“心灵活动”概念之所指范围要比当代心灵哲学所谓的“心灵活动”或“心理活动”的所指要广,它不仅包括知觉和思维,还包括生长、繁殖等生命活动。这是因为当代心灵哲学受笛卡尔的影响,像笛卡尔一样将营养灵魂从“心灵”(mens)的概念中分割出去了;笛卡尔只在认识和意思的角度上使用“心灵”概念,而亚里士多德是从生命或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灵魂”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使用“心灵活动”一词的,多数时候我们称之为“灵魂活动”。。亚里士多德对灵魂活动的解释以他的运动理论为基础。运动是自然哲学的核心问题,而灵魂是生命体的本质和自然,因此关于灵魂的研究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并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一、灵魂活动的外部原因机制
亚里士多德对灵魂活动的原因机制的探讨建立在他对运动的解释上,但同时在许多方面运动的基本模型又不能涵盖某些灵魂活动的特殊性(例如,知觉活动和思维活动)——他因此不得不拓展自然哲学中的概念架构使得类比式的研究得以可能。但是,运动的基本模型仍然是我们理解灵魂活动及其原因机制的入口。伯恩耶特(M. F. Burnyeat)说:“在《论灵魂》的开篇,关于灵魂的知识被认为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研究,在这里,自然哲学的理论是被预设了的。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是他的自然哲学的桂冠。”[2]在《论灵魂》中,我们随处可见这顶桂冠生长的土壤,这也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基础。
在总结前人对灵魂的理解时,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者与无灵魂的存在者相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运动和认知”(《论灵魂》403b25- 26)*本文对亚里士多德原文的引用出自笔者的翻译,翻译所依据的版本是J. Barnes,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Two Volum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亚里士多德希腊文引用的注释采用国际通用的Bekker边码,均在原文后加括号表示,如(416a22- 24)。关于《论灵魂》的中文翻译,参看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及其它》,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如果认知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运动,那么有灵魂的存在者的本质特征便是运动。因此,任何类型的灵魂活动——包括生长、繁殖、感知、想象、欲望、思考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用运动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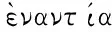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总结前辈哲学家的观点说:运动的发生总是在一对相对者间进行,而不是发生在任意两个存在者之间——除非我们是在偶然的意义上描述运动;“任何能生成或毁灭的事物都是从它的相对者或中间状态而来的,或者毁灭为它的相对者或中间状态”(《物理学》188b22- 23)。“运动是相对者的转化”这个原则稍后在《物理学》第一卷第七章中得到确立,亚里士多德指出运动有三个原则:基体、形式和缺失(191a13- 14)——形式和形式的缺失是相对者,但这三个原则在数目上是两个:即缺失形式的基体和获得形式的基体[3],它们也可以视作相对者(《形而上学》1018a31- 32)。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对营养活动的最初解释中,他将生物体与食物视作相对者,营养活动就是它们之间的转化,或者说生物体从缺少食物到获得食物,即食物被转化为生物体的增量。我们将这个运动的解释模型记为(双箭头表示运动位于两者之间,P和-P表示它们是相对者):
① P(生物体)←——→-P(外部对象)

亚里士多德认为,相对者之间存在一个“相似”与“不相似”的程度问题,这是我们理解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的前辈中,有些人认为相互作用的东西是相似的,而有些人认为相互作用的东西是不相似的。对于营养活动,他指出“有些人认为相似的东西是被相似的营养并得到增量。另一些人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被营养的东西和提供营养的东西是不相似的;他们说相似的不能被相似的作用;但是食物在消化过程中被改变了,而变化总是朝向相反者或中间状态”(《论灵魂》416a30- 34)。亚里士多德指出两方的观点都仅为部分正确,他在《论生灭》第一卷第七章中集中处理了这个问题。面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他说:“他们的观点产生冲突的原因在于每一方都仅仅陈述了一部分,但他们应当考虑这个问题的全部。如果两个事物是相似的——绝对地或在每个方面都相似——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事物不能以任何方式被另一个作用。的确,为什么是其中的一个事物倾向于产生作用而不是另一个呢?此外,如果相似的事物被相似的事物作用,那么每个事物都能够被自身作用,倘若果真如此——即相似的实际上作用于相似的——那么,没有什么是不可毁坏的或不运动的,因为每个事物都能使自身运动。如果两个事物绝对地不相似,即在任何方面都不相同,那么我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白色不能以任何方式被一条线段作用,一条线段亦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白色作用——除非在偶然的意义上,即如果一条线段偶然地是白色的或黑色的;因为除非两个事物是相对者或者由相对者构成,(否则)它们不能使对方改变原来的状态。因为,只有包含相对者的两个事物或相对的事物本身才能作用和受到作用——但并非任意两个事物都能如此,作用者和受作用者必须在属上是相似的,并且在种上是不相似的(或相对的)。”(《论生灭》323b16- 32)
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一对相对者在属上是相似的,但在种上是不相似的,说相似的与相似的东西作用的人只看到了事物在属上的相似,说相似的与不相似的东西作用的人只看到了事物在种上的不相似[2]。从这个方面,运动可以理解为属上的相似者之间的转化,同时亦是种上的不相似者之间的转化。作用者和受作用者是相对者,它们是同一个属之下的不同的种。例如,在营养活动中,生物体和食物是相对者,它们在种上是不相似的,但它们同在一个更高的属概念之下。运动开始时,推动者(agent)和受动者(patient)是相对的——即它们在种上是不相似的,但属于同一个属;当运动结束时,受动者变得与推动者相似了——即运动的过程就是推动者把受动者向自身同化,而受动者朝推动者改变自身。我们将这个从相似和不相似的角度对运动的解释模型记为(S和-S表示二者不相似):
② S(生物体)←——→ -S(外部对象)/S和-S同属G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模型①和模型②与“潜在性”和“现实性”概念连接起来。一对相对者是运动的两端。换言之,运动发生在相对者之间;相对者不仅在种上是相对的和不相似的,而且它们是推动与受动的关系——这个关系亦是现实者和潜在者的关系。缺失代表着潜在的形式,或者说缺失形式的基体潜在地拥有形式,而获得形式的基体现实地拥有形式。因此,推动者现实地拥有形式,而受动者潜在地拥有形式。所以,运动不仅是基体从缺失形式到获得形式的过程,或受动者被推动者作用的过程,亦是潜在者向相应的现实者的转化——即运动是从潜在者到现实者的过程。潜在者在本体论上是由现实者决定的(《形而上学》1050a4),并且它以现实者为变化之目的。所以,潜在者和现实者的关系揭示了一对相对者在本体论上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它为运动的方向提供了解释——即运动是“从潜在者到现实者”的过程。
在《论灵魂》中,这一模式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在对灵魂活动的解释中。在探究知觉活动时,亚里士多德说:“知觉活动是某种运动或受到外部对象的作用,因为它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性质变化。”(416b34- 35)知觉活动并不取决于我们自身,而是被外在的可感对象引起的,因此知觉活动是一种“被动运动”。这个最初的解释与潜在性和现实性概念连接起来了:知觉者潜在地拥有可感对象的性质(417a6),而可感对象现实地拥有可感性质;当知觉活动开始时,知觉者和可感对象是不相似的,但知觉者以潜在的方式与之相似,当知觉活动结束时,知觉者变得实际上与可感对象相似。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拥有知觉能力的东西潜在地与作为现实者的可感对象相似;即,在它被作用的过程开始时,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是不相似的,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被作用的被同化为另一个,并与之在性质上相同。”(418a3- 5)此外,亚里士多德在解释思维活动也采用了这个模式,因为思维活动和知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他说:“灵魂的理智部分尽管是不受影响的,但它必定能够接受一个对象的形式;即,它必须潜在地与它的对象在性质上相同,但并非是这个对象。思想与可思对象的关系犹如知觉与可感对象的关系。”(429a15- 18)我们把从潜在性和现实性角度对运动的解释模型,即运动是从潜在者到现实者的过程记为(虚线箭头表示运动的方向):

为了理解这个模型,我们需要分析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三卷第三章中对推动者和受动者以及运动的原因机制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运动是潜在者作为潜在者的现实性(energeia)(《物理学》201a11),且运动是由推动者作用于受动者而产生的,因此运动既是推动者的能动(即主动)能力的实现,亦是受动者的受动能力的实现,即运动既是推动者的现实性又是受动者的现实性;但是,推动者的“推动”与受动者的“被动”似乎是不同的,这里是否有两个不同的现实性(即运动)呢?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推动”与“被动”并非两个不同的现实性,它们是同一个存在,尽管它们的定义是不同的(202a20)。关于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回答,学者们有诸多争议。
吉尔(M. L. Gill)指出“当一个推动者作用于一个受动者时,运动发生在受动者之中,推动者是不变的”这个传统观点并不正确[4]。她认为推动者和受动者都变化了,推动者在受动者中产生运动并且它自身也运动了,因为运动同时是推动者和受动者的现实性,“推动者和受动者都包含在运动中,如果它们都包含在运动中,那么它们就都在这个运动中变化了”[4]。她说:“例如,‘教’作为运动的定义与‘学’作为运动的定义是不同的:教是属于老师(产生)的运动但它在学生中,学是属于学生的运动但它是被老师产生的,但教与学是同一个运动。”[4]吉尔的论证是令人费解的,亚里士多德确实指出“推动”与“被动”在定义上是不同的,正如“什么是教”与“什么是学”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包含在运动中”,或者说它们都是构成运动的要素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发生了变化——即它们并非都是运动的主体或承载者;“推动者包含在运动中”并不能推出“它自身也运动了”。因为“推动”与“被动”是相对的(200b30- 31),正如教与学是相对的,被动者是运动的主体,而推动者提供了运动的形式——但它自身并不承载运动,这对相对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正是在受动者中,推动者才能够活动。”(202a18)
查尔斯(D. Charles)在他的《亚里士多德的行动哲学》一书中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物理学》第三卷第三章的推动者与受动者的问题。他指出,“教”与“学”,“推动”与“被动”必须是两个数目不同的运动,因为它们的本质和定义是不同的,它们是由不同的能力引起的并且它们拥有不同的目的。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运动,即“被动运动”作为质料构成了“推动运动”;或者说它为后者提供了物质之必然(materially necessitates),即没有“被动”的过程,“推动”是无法发生的[5]。我们无法接受查尔斯的观点,因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推动者的现实性和受动者的现实性是同一个,并非不同的两个运动。正如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从雅典到底比斯和从底比斯到雅典的路是同一条路一样,“推动”和“被动”的所指是同一个存在者,只是它们各自的定义不同*Robert Heinaman拒绝了David Charles对《物理学》第三卷第三章的解释,他指出Charles的“不同的能力引起不同的运动,因此推动和被动是不同的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一个运动的恰当的主体是一回事,实现这个运动的能力又是另一回事”。Heinaman对第三卷第三章的解释更接近传统的观点,但他指出对于任何运动而言,受动者是运动的恰当主体,但是推动者——即一个特定的推动者,并不是必须的。我认为Heinaman并未清晰地解释推动者在一个运动中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它,一个特定的推动者或许是不必要的,但运动的形式是必要的——这恰恰是由推动者来提供或传递的。参看Robert Heinaman, “Aristotle and the Identity of Actions”,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vol. 4, 1987, pp.307- 328, esp. p.315。。另一方面,尽管亚里士多德说推动者和受动者的关系是现实性与潜在性的关系(202b10),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前者是由后者作为质料构成的,而是前者拥有运动的形式,后者尚未拥有但能够获取这种形式,它们反映的关系正是模式③所刻画的。模式③从受动者的角度与模式④从推动者的角度所反映的相对方向不正是上坡路与下坡路的相对方向所比拟的吗?
我们认为吉尔和查尔斯都未能理解“推动者”在一个运动中的真正地位。《物理学》第三卷第三章是从推动者和动力因的角度对第三卷第一章中的运动定义的再阐释。运动的定义(即运动是潜在者作为潜在者的现实性)刻画的是受动者(即潜在者)的现实性,这意味着只有受动者才是运动的恰当主体,亚里士多德在第三章不断重申这一点(202a18,202b7)。然而,倘若只有受动者,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它还需要动力因——即一个推动者。推动者在受动者中产生一个运动,即它使得受动者通过自身的变化获得一个新的形式。亚里士多德说:“推动者将总是传递一个形式,要么是‘这个’,要么是‘这样的’,要么是‘这么多的’,当它推动(活动)时,它就是运动的原则和本原。”(202a9- 11)因此,当推动者活动时,它将自身的形式传递给受动者,但它并不因此获得一个新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推动者自身并不运动。换言之,推动者代表着运动的原则,它作为运动的原则是不动的。所以,“推动”描述的并不是发生在推动者之中的运动,而是推动者相对于受动者产生的效果,同时对这个效果自身的恰当描述就是受动者的“被动”和现实性。“推动”和“被动”是同一个现实性,只是对它们的描述和定义是不同的。
倘若我们把推动者理解为提供了运动的形式和原则并认识到受动者是运动的主体和发生的起点,便能清楚地看到运动总是发生在受动者中,而这个运动的种类、方式和目的是由推动者规定的。因此,一个确定的运动是推动者和受动者协同作用的效果,这个效果是由动力因或推动者引起的,但它总是表达在受动者之中。马尔莫多罗(Anna Marmodoro)最近的研究契合我们的分析,她认为从原因结构的角度能较好地理解《物理学》第三卷第三章的论证,推动者的主动能力的实现取决于与被动能力的接触,即它实现在受动者之中;在原因和效果之间存在着一种本体论的依赖,即原因将自身“延展”到效果之上,或者说推动者将自身“延展”到受动者之上。*参看Anna Marmodoro, “Causation without Glue: Aristotle on Causal Powers”, in Cristina Viano, Carlo Natali, Marco Zingano,eds. Aristotle Traductions Et Etudes, Walpole, MA: Peeters, 2013, p.244。尽管我赞同她对运动的原因结构的分析,但我并不像她那样认为推动者的现实性和受动者的现实性之下有一个奠基的运动(substratum)。因此,运动的解释模型④是关于运动的原因——特别是动力因,与效果之关系的分析。推动者作为动力因将形式或原因表达在受动者之中,而受动者自身的运动就是这一效果。当运动结束时,受动者对原因的表达已经完全实现,这时它获得了一个新的形式——即推动者“传递”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活动解释为外在对象(例如可感性质、可思对象、甚至食物和热量)作为推动者对生物体的作用,因此灵魂活动并不发生在外在对象之中,而是发生在生物体之中,即灵魂活动的承载者和主体是生物体,它接受了外在对象“传递”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生物体是作为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体——即复合实体——来承受外在对象的作用的。换言之,单单灵魂或者单单身体并不是灵魂活动的恰当主体。*不了解这一点便容易误以为灵魂是灵魂活动的主体,Christopher Shields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代表性的,参看Christopher Shields, “Soul as Subject in Aristotle’s De Anima”,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38, 1988, pp. 140- 149。他一直无法放弃灵魂是灵魂活动之主体的观点,直到晚近的文章中都一直为这个观点辩护(见下文),究其原因是他把形式理解为作为主体的实体,因此灵魂作为形式也是某种主体。另外,有学者认为灵魂活动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灵魂,另一个是身体,这种解释属于二元论,它也是站不住脚的。参看Robert Heinaman, “Aristotle and the Mind- Body Problem”, Phronesis, vol. 35, 1990, pp. 83- 102。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多次指出灵魂活动是灵魂和身体“共有的”(403a4- 7,403a25),灵魂不是灵魂活动的主体(408b12- 14),以及承受外在对象的作用而发生变化的是“被赋予灵魂的身体”(ensouled body)(416b21- 22, 424a27- 28)。因此,运动的解释模型④,以及与之相关的模型①②③都将灵魂和身体作为整体来考虑,即它们解释的是生物体与外部对象遭遇时是如何运动的,外部对象如何对生物体产生影响。我们把这些模型称为对灵魂活动的“外部原因”的解释。然而,对“外部原因”机制的分析并不足以解释灵魂活动为什么能够发生,它们的产生必有内部原因的作用——这便是灵魂的缘故。
二、灵魂活动的内部原因机制
灵魂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需要外部对象对生物体的推动,更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存在者”的活动。灵魂活动即便可以用运动的一般模型(即以上四种模型)来解释,它们也是特殊的,即它们是生物体特有的、区别于非生物体的运动。同一个外部对象当它作用于生物体时与当它作用于非生物体时将产生类型完全不同的运动,究其原因乃是前者是拥有灵魂的。例如,当面包作用于动物将使得动物体产生消化的过程,但面包作用于一块石头绝不会产生消化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说坚硬的面包可以推动石头向前运动;声音作用于动物体将使得它产生听觉,但声音作用于墙壁绝不会产生听觉活动,我们或许可以说声音被墙壁反射。灵魂的存在是产生灵魂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是生物体能够进行这类特殊运动的内在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多次谈到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生长”时证明了灵魂存在是产生这种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并反驳了恩培多克勒的观点。恩培多克勒认为植物的生长可以解释为土元素向下运动的倾向造成了植物根系向下生长,而火元素向上运动的倾向造成了植物枝干向上生长。亚里士多德指出,首先恩培多克勒误解了“上”与“下”的意义,植物的根系类似于动物的头部,它应当是“上部”。其次,“是什么力量把倾向于相反运动的土元素和火元素结合在一起?如果不存在这样反向作用的力量,那么它们将会分离;如果存在这样的力量,那么这一定是灵魂以及营养和生长的原因”(《论灵魂》416a4- 10)。因此,生长的原因最终归之于灵魂,而不是构成身体的元素或物质特性。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造成生物体的生长,比如火元素或热量这样的外部对象?亚里士多德说火元素或热量只是协同性的原因(concurrent cause),而非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只要存在燃料的供应,火的生长就会无限持续下去,但是对于自然产生的所有复合体,都有一个界限和比例决定着它们的大小和增长,而界限和比例是灵魂的特征,而非火元素的特征”(416a15- 18)。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灵魂不存在,像生长和营养这样的活动就是无法产生的;灵魂不仅是产生灵魂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且它是根本原因——它规定了这些运动的类型和界限。
更具体地说,灵魂作为根本原因意味着它是活的身体的动力因、目的因以及形式因(415b9- 11)。我们解释灵魂活动的生成机制主要从灵魂作为动力因的角度来看,当然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维度。生物体作为统一体进行着各种灵魂活动,这个统一体有着内在的原因结构,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是原因与包含和展现着原因的物质存在之间的关系。从灵魂作为动力因的角度说,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是推动者与受动者的关系,并且它们构成了统一体——即生物体整体是自我运动的。
然而,灵魂是特殊的推动者,它自身是不运动的。换言之,灵魂是“不动的动者”。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一卷第三章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证明“灵魂是不可能运动的”(406a1- 2),他给出了一组论证,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其中重要的两个。第一个论证说:“有四种类型的运动——位移运动、性质变化、增长和缩减;因此,如果灵魂运动,那么它必须进行这四种运动中的一种或几种或全部。如果灵魂的运动不是偶然的,那么必然有一种属于它自身的运动;如果情况如此,因为这四种运动都包含位置,那么灵魂就必然包含位置。……如果灵魂自身是运动的,那么它就必然处于某个位置。”(406a11- 21)然而,“灵魂处于某个位置”这个结论是亚里士多德无法接受的,他不认为灵魂是一个“物体”或“量”,因此它不可能占据空间。所以,这个论证表明灵魂自身是不动的,而它隐含的前提是:灵魂不是物质存在者。
第二个论证说:“如果灵魂自我运动,那么它必须是自己推动自己;因此,如果运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受动者作为受动者的替换或改变,那么灵魂的运动一定是对它的本质的替换,至少,倘若灵魂不是在偶然的意义上运动的。”(406b11- 15)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证假设灵魂自身是运动的,如果运动意味着替换或改变运动者原有的本质,那么,灵魂的本质被替换或改变了。但这个结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灵魂不可能替换它的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因此灵魂就自身而言是不可能运动的,至多,灵魂能够偶然地运动。这个论证乍看起来是难解的,因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运动是对受动者的替换或改变”;希尔兹(C. Shields)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证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从“运动是对受动者的替换”并不能推出“灵魂运动是对其本质的替换”[6],有许多受动者在运动中并不会改变其本质,例如苏格拉底从市场走到了体育馆,在这里被替换的是位置而不是运动者的本质。因此,希尔兹认为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不动”的证明是有疑问的,甚至他的这个观点是矛盾的。*当然,Shields也提出了与我们类似的、对这个论证的解释,但是他从总体上认为亚里士多德没能成功地证明“灵魂是不动的”,并且在很多地方,特别是讨论知觉和思想的文本中他承认了灵魂是运动(或活动)的主体。参见Christopher Shields, “The Peculiar Motion of Aristotelian Soul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 vol. 81, 2007, pp.139- 161, esp. p. 139, p.160。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运动是受动者对原先的性质或形式的替换,但处于运动两端的、被替换的性质或形式本身并不发生改变——它们作为原则规定了运动的类型和目的,例如,在苏格拉底的例子中,运动发生在苏格拉底替换的位置之间,但市场和体育馆本身并未运动,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灵魂是作为原则和形式来理解的,因此它自身并不运动——即它并不能替换原先的本质。换言之,灵魂并不是运动的承载者,而是运动的形式和目的。
从上述两个论证中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意在表明灵魂是非物质性的原则,并且它作为运动的原则本身是不动的(不变的)。如果灵魂自身是不动的,那么它是如何作为推动者的呢?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都无法设想“不动的灵魂”可以推动身体运动,因此前者把灵魂设想为运动着的球形原子——它们拖着身体运动,后者亦把灵魂设想为自我运动的存在者——它把自身的运动传递给身体*参看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一卷第三章中对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批判(406b20- 31)。。亚里士多德认为推动者本身并非必然是运动的。在《物理学》第八卷第五章中,他解释了运动的原因序列,例如某人用一根木棍拨动一块石头,木棍是石头的推动者——它也是运动(被动)的,人是木棍的推动者——他是自我运动的,即人的运动并不来源于其他对象的推动。但是,一个物体不可能同时是主动的和被动的(或同时是现实的和潜在的),因此在自我运动的物体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引起运动但自身不动的部分,以及被推动的部分;因为,唯有如此,一个物体才可能是自我运动的”(258a1- 3)。因此,人的自我运动的来源是灵魂——这是引起运动但自身不动的部分。所以,任何运动的原因序列的开端是“不动的动者”——一直上溯至神,而灵魂是生命活动之原因序列的开端。
灵魂作为生物体内在的“不动的动者”,它是生物体自我运动的最初原因或第一推动者。灵魂如何推动身体?这个问题可以从推动者与受动者的解释模型(即上述模型④)的类比和扩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灵魂与身体时说:“能够引起运动的存在者之现实性似乎发生在受动者之中”(414a11- 12),即灵魂的活动发生在身体中。灵魂与身体是推动者与受动者的关系,但特殊之处是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此外,灵魂是不动的推动者,尽管就一般而言,推动者可以是运动的(如教师、建筑家),也可以是不动的(如建筑技艺)。然而,这些特殊性并不妨碍我们理解推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原因- 效果”模式。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推动者提供了运动的原则和形式,受动者是运动的承载者,推动者的“推动”效果表达在受动者的运动中,但它自身(在由它引起的运动中)并不被改变;运动是推动者将自身拥有的形式“传递”到受动者之中,或者说推动者作为原因将自身表达在受动者之中。因此,灵魂作为推动者将它产生的效果或它的活动实现在身体运动之中。换言之,灵魂作为原因和形式直接表达在身体运动中,但它自身是不动的。灵魂“推动”身体便意味着灵魂启动了运动序列并将自身所代表的逻各斯或规定性表达为身体运动的类型和界限。
此外,灵魂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特点区别于一般的推动者和受动者——例如建筑师和石材是分离的。因此,尽管灵魂自身是不动的,但它处于一个被推动的身体之中;尽管它引起的运动发生在身体之中,但这个运动也在间接的或偶然的意义上属于灵魂。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尽管灵魂自身是不可能运动的,但它能够在偶然的意义上运动。在这里,身体的运动是由灵魂产生的,并且这个运动在间接的意义上也是灵魂的活动,因此,作为灵魂和身体之统一体的运动是由内部原因结构的支配而产生的自我运动或自我实现。至此,这种“内部原因”的分析是否足以解释灵魂活动是如何发生的呢?
事实上,生物体的灵魂活动总是在与外部对象交互作用的情况下产生的(或许,思维活动例外,因为可思对象并不在理智之外)。例如,知觉活动必须有外在对象的刺激才能产生——就像可燃物必须有火将其点燃,而营养活动也必须依赖于食物的供给,因此“外部原因”对于灵魂活动的发生是必要的。然而,当我们把“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的解释结合起来时,就会发现灵魂和外部对象都是必要的,它们都是作为推动者或动力因出现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它们是同一条原因序列中的动力因吗?
灵魂和外部对象不可能是同一条原因序列中的动力因。因为,如果它们是同一原因序列中的两个动力因,并且外部对象是第一推动者,那么灵魂就是被它推动的,而身体被设想为被运动着的灵魂推动——我们已经指明这个观点被亚里士多德拒绝了*“外部对象是第一推动者”这个观点还会导致对“生物体是自我运动者(self- mover)”这个论点的否定,因为如此一来,生物体的运动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外部对象的刺激和推动,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许多文本中肯定了生物体能够自发地运动。有些学者为“生物体是自我运动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辩护,例如David Furley、C. A. Freeland 和S. Meyer等人,尽管他们的策略不同。Furley认为“外部对象”,例如可欲对象是意向性对象(intentional objects);Freeland指出什么东西能成为“外部对象”是由生物体的生存目的设定的;而Meyer认为“外部对象”作为动力因只是偶然的,但他们的目标都是瓦解“外部对象是第一推动者”这个观点。参看下述文集Mary Louise Gill and James G. Lennox,eds. Self- Motion: From Aristotle to New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然而,如果灵魂是第一推动者,外部对象是被灵魂推动的——即外部对象成为受动者,那么外部对象如何作为推动者作用于灵魂与身体之整体呢?因此,我们认为灵魂活动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并不是线性叠加的,而是双层原因的协同作用。
在灵魂活动的双层原因结构中,灵魂起着主导作用,外部对象起辅助或协同作用,如果说灵魂是灵魂活动的原初动力因(primary efficient cause),那么外部对象就是灵魂活动的辅助动力因(instrumental efficient cause)。灵魂作为原初动力因在身体中产生运动,外部对象作为辅助动力因在生物体中——即在拥有灵魂的身体中产生运动,因而身体运动由来自两个层面的动力因共同产生。灵魂和外部对象都是灵魂活动发生的必要条件,甚至在同一个活动中,它们对身体的推动作用是同时存在的。然而,灵魂与外部对象并不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我们把灵魂称为“原初动力因”是因为灵魂决定了什么事物能够成为对生物体产生作用的外部对象。亚里士多德说:“除了活物没有什么能够被营养,因此,被营养的东西是拥有灵魂的身体,这正是因为它拥有灵魂。因此食物在本质上是与有灵魂者相关的。”(416b10- 11)食物之所以作为食物是相对于有生命的存在者而言的,水是植物的食物,但水无法作为石头的食物;颜色之所以作为视觉对象是相对于拥有感知灵魂(视觉能力)的动物而言的,但颜色无法使植物产生视觉活动。因此,灵魂是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的原因,它决定了何种事物能够作为外在的推动者,它才是灵魂活动的原初启动者。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活动的双层原因结构表达为运动的三个要素,他在分析营养活动时说:“营养过程包含三个要素:被营养的东西,用什么(以进行)营养的东西,以及进行营养活动的东西;在这些要素中,进行营养活动的是第一灵魂,被营养的是身体——它在自身中拥有灵魂,用以进行营养的东西是食物。”(《论灵魂》416b20- 22)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了灵魂是营养活动的主导原因,食物是辅助灵魂进行营养活动的原因,而拥有灵魂的身体是被作用的对象,即营养活动的承载者。这个图景似乎在说:灵魂作为原初推动者利用食物作为它的工具对身体产生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灵魂是内在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图景一再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位移运动的分析中(《论灵魂》第三卷第十章,第十二至十五章),在那里,理智灵魂利用可欲对象和欲望灵魂对身体产生作用*关于《论灵魂》第三卷第十章的解释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的焦点在于可欲对象是否是原初推动者(以及欲望灵魂是否是运动的)。我们认为尽管可欲对象是动物位移运动的动力因,但它不是原初的动力因,它必须首先在理智灵魂或想象中被设计为可欲求的,它才能作为动力因起作用,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分析并不是从动物运动的原初推动者开始的,这里的观点并未与第二卷第四章的论点相矛盾。。因此,外部对象是一种“工具性”的动力因,它们附属于原初动力因即灵魂,并为其产生的活动服务。
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三个要素,即灵魂、外部对象和身体,处于不同层次的原因结构中。外部对象尽管是从属性和辅助性的,但它作为动力因作用于整个生物体,即外部对象与生物体整体构成了“外部原因”结构。灵魂是原初动力因,它从内部推动生物体的运动,即灵魂与身体构成了“内部原因”结构。“外部原因”结构与“内部原因”结构的连接不仅在于拥有灵魂的身体之运动(即灵魂活动)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协同作用的结果,还在于外部推动者是由灵魂设定的。换言之,当我们从外部原因来解释灵魂活动时,我们已经预设了生物体具有内部原因结构并在其支配下能够与外部对象发生相应的反应;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内部原因来解释它们时,我们已经把外部对象的作用整合为双层原因序列中的一部分。我们用下图表示灵魂活动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层结构:

在这个图示中,我们用曲线箭头表示灵魂设定了什么事物能够作为推动生物体的外部对象,用实线箭头表示动力因(即灵魂和外部对象)对受动者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文归纳的关于运动的四种模型是对灵魂活动的外部原因结构的解释,而灵魂作为不动的动者对身体的推动是对灵魂活动的内部原因结构的解释。灵魂活动就是发生在身体中的、由灵魂和辅助动力因引起的运动。这种双层原因结构是产生灵魂活动的普遍机制,它支配着亚里士多德对灵魂活动的理解,即便对于知觉和思维来说,这个结构也是类比理解的基础。
三、“心理因果性”问题与亚里士多德范式
从亚里士多德对灵魂活动的生成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心灵活动的确是一类物理运动(即身体的运动),但心灵活动并不能由单纯的物理运动来解释——即心灵活动无法还原为由物质自身引起的变化或在物质构造的基础上溢出的或附加的结构、功能等。相反,心灵活动最终是由非物质性的原因即灵魂产生的。因为,当我们谈到对心灵活动的物理“还原”时,我们理解的不仅仅是心灵活动的构成,更多的是产生它的原因。当这些“原因”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存在、甚至必须追溯到非物质的灵魂时,将心灵活动等同于或还原到物理运动就是错误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心灵对身体的因果效用是一切心灵活动之存在的前提。因此,心理因果性(mental causation)并不是一个棘手的、需要作出解释的问题,而是我们解释某类物理变化(即心灵活动)的基础。这种“自上而下”的因果效用是亚里士多德心灵哲学的前设。
“自上而下”的心理因果性,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并未面临“过度决定”的疑难(overdetermination problem)——即同一个物理变化既是由物理原因完全决定的亦是由心理原因完全决定的*心灵因果性的“过度决定”的问题是物理主义者(包括强的物理主义者和属性二元论者)在坚持心灵的因果效用时遇到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的成立还需合取一个前提,即“排除命题”:任何一个物理变化(或物理事件)有且仅有一个原因序列。金在权(J. Kim)指出,物理主义的各种版本都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他自己选择放弃心灵的因果效用,拥抱物理主义的还原论。参看Jaegwon Kim, Mind in a Physical World: An Essay on Mind- Body Problem and Mental Caus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reprinted), 2000。此外,当前也有研究者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心灵因果性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条道路,参看William Jaworski,“Mental Causation from the Top- down”, Erkenntnis, vol. 65, 2006, pp. 277- 299, esp. p.278。。因为,灵魂作为原因表达为对物理运动的种类、目的和界限的规定,我们已经指出灵魂并不像物质对象那样推动身体,而是规定了生理运动的“逻各斯”。换言之,灵魂决定了拥有灵魂的物质实体在遭遇其它物体时会“如何”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心理因果性并非与物理因果性相冲突,它们是互补的——即灵魂与外部对象协同作用才能产生某种心理活动,甚至在强的意义上(即肯定灵魂的实在性和优先性)灵魂的存在为物理因果性何以可能奠基——即灵魂设定了何种物体能够作为身体运动的外部推动者,继而使得外部对象对生物体的作用得以可能。例如,我们看见红色,我们的视觉灵魂决定了发生在身体中的变化是一个视觉活动,亚里士多德谓之“接受不带有质料的红色之形式”,而外在的红色对象决定了我们看见的是这片“红色”,即它规定了一个视觉活动的具体内容。因此,在物理世界中,灵魂绝不是无用、多余的、甚至可以消去的存在者,它是物理世界之构成和运动的基础。当然,不承认这样的基础,甚至把灵魂的原因效用划归为物质实在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那么心灵的因果性问题对于物理主义来说就是无解的。“心理因果性”的难题是物理主义自创的,一旦我们取消它的某些本体论前设,这个难题或可消弭。
因此,亚里士多德对灵魂活动的原因机制的分析为心理因果性提供了一种解释范式,它避免了物理主义者在这里遭遇的疑难——即因为无法在物理主义的本体论中解释心灵如何作为原因,以至于取消了心灵的原因效用、甚至心灵的存在地位。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又区别于笛卡尔式的实体二元论,后者尽管可以充分保留心灵对物质的原因效用,但又无法解释作为二元实体的心灵与物质的交互关系[7]。在亚里士多德的范式中,心灵与物质的交互关系是内在的,并且心灵活动的外部的物理原因和内部的心灵原因的协同作用模式既保留了心灵效用的实在性和优先性又确保了物理效用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的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既区别于物理主义又不同于二元论的、解决身心问题以及心理因果性问题的路线。
[1] 曹青云.在二元论与物理主义之间:论亚里士多德的心灵活动观[J].哲学研究,2017(5):78- 84.
[2] BURNYEAT M F. “De Anima” II 5[J]. Phronesis,2002,47(1):28- 90.
[3] 曹青云.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1- 52.
[4] GILL M L. Aristotle’s theory of causal action in “Physics” III 3[J]. Phronesis,1980,25(2): 129- 147.
[5] CHARLES D.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action[M].London:Gerald Duckworth &CO. Ltd.,1984:29.
[6] SHIELDS C. The peculiar motion of Aristotelian souls[J].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2007,81:139- 161.
[7] KIM J. Philosophy of mind[M].3rd ed.Colorado:Westview Press,2011:48- 50.
10.13718/j.cnki.xdsk.2018.01.003
B502.233
A
1673- 9841(2018)01- 0022- 11
2017- 02- 20
曹青云,哲学博士,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亚里士多德心灵哲学研究”(17CZX042),项目负责人:曹青云。
责任编辑 高阿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