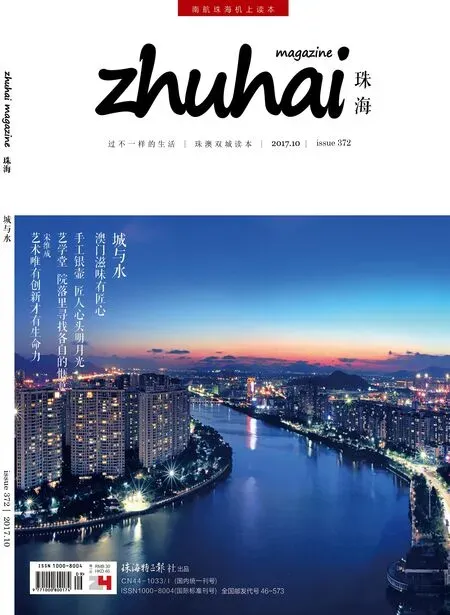手工银壶匠人心头明月光
文|黄丹丽 图|云朵
手工银壶匠人心头明月光
HANDMADE SLIVER TEAPOT
文|黄丹丽 图|云朵
若非窗外飘过一片晚霞,倒真没觉出日暮已斜。轻轻放上才制好的壶盖,工作台上的那把银壶总算是完工了。凌飞扬端详着这件千锤百炼而成的作品,仔细地用手掌摩挲着上头一朵朵起伏的祥云,每一刀的纹路,皆是用心血錾刻而出。此时已是入秋,距离这把祥云壶开料的那一天,整整过去了八个月。他手上被银屑割开的伤口早已经愈合,只留下三两道浅浅的疤。
世人都知晓一寸光阴一寸金,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两百多个日升月落,足以盖起几栋高楼,足以量产出数以万计的器皿,可偏生有人愿意拿寸金不换的光阴来慢慢雕刻一把纯手工制作的银壶,一刀失误便一壶尽毁,没有半点可以修复的余地,也幸而有人这样不计得失地付出心与时,我们才得以在一桌长案与茶席之间,寻得一丝器物的精美与工艺的考究。
拉开工作台上的小灯,四散的工具仿佛都有些疲倦,安静地躺在杂乱的边角料中,而此时,置于凌乱物件之中的那把银壶却显得神采奕奕,莹莹的白色光线从壶身上缓缓地流出,仿佛细细缕缕的白月光,倾洒在匠人心上。
以手传心,随心而活
一个人的出身,很多时候决定了他日后发展的轨迹,凌飞扬出生于广西的一个书画世家。游走于不同的文化与技艺之中的凌飞扬,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美学素养,也正因为有了对比,有了感知,他更深层次地发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之美与传统精髓,那是源于骨子里的根与土,是一种无法取代的眷恋与依赖。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家当然也离不开生活。毕业之后的凌飞扬并没有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到大学里传道授业,后来又与相熟的意大利朋友学习珠宝设计,开设工厂,名利场中多重身份的转换给了他常人难及的生活经验,却也让他渐渐地看清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向往。一如浑浊的泉水,须得经过一番沉淀,才能显出清澈和纯净来。
“有一天我忽然问自己,我在做什么?难道我一辈子都要这样过下去吗?”凌飞扬审问着自己的内心,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不要再做批量的工艺品,我想做一名匠人,一名遵循古法制作的手工艺匠人,制作一些能让人感知生活,享受生活的物件。”
凌飞扬于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匠人生涯应当从何开始,“因为从事过珠宝行业的关系,我接触到很多贵金属、宝石,在我的审美标准里,我认为白银是最素雅的一种材料,同样是贵金属,它却不像黄金那样光芒灼人,而是自有一种柔美的动人,颇具文人风骨。这么美好的贵金属,如果变成一件手工艺的作品,一件平时能用得到的器具,那该有多么地完美啊,我于是想到了制作手工银壶。”
茶事本无雅俗,却也是门一人得幽、二人得趣、三人成品的生活艺术,古人有“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一说,以白银打造茶壶的手艺古已有之,明朝许次纾在他的《茶疏》中写道:“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而茶圣陆羽更是在《茶经》中写道:“鍑,以生铁为之……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银也。”可见,银壶之于茶客,之于懂得生活的人们而言,是考究的上乘之选。
告别城市,拂袖而入深山。在云南边远的山村里,凌飞扬找到了云南当地的老师傅,学习古法制作银壶的方法,从上百件工具到数十道繁复的工序,一板一眼都是遵循老祖宗传下来的工法,古老的民间手工艺,与古来有之的金属相结合,二者产生的年龄感与岁月感让凌飞扬沉醉其中,也渐渐开始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工具的落后,制作的粗糙使得这些老手艺人只能在当地制作一些粗使的日用物件,而我认为,如果将这些技术问题改良一番,可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创作水平。”
以手传心,一个人的审美、美学造诣、价值观都会直接体现在制作出来的手工艺作品上,多年来累积的美学素养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凌飞扬将自己对于东方美学的理解融入到创作之中,摸索打造出了一些自己设计的专用工具,在银壶的制作上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和技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银壶匠人,凭心制器。
岁月不曾负匠心
机器生产一把银壶不过几日时间,纯手工打造所需的时间却是机器的数十倍,而在手工制壶的工法中,还有着“焊接”和“一张打”之分,凌飞扬采用的,便是耗时最长,工艺难度最大的“一张打”工法。他似乎总愿意将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机器无法比拟,旁人无法复制。
器之美,先在形,后有韵。一片银板,打出壶底、壶身与壶嘴,一体化的茶壶上没有一个焊接点,全凭匠人心中的预设,在手上做出器形。而后便是在壶身上一笔笔地画出图案的走向、花形的分布,虽然没有草稿,可每一笔落下时,心中早已有了一幅绘就的画卷。比如那一蓬婉约起伏的莲,花与叶的交相依偎,莲蓬与枝叶的延展,在落笔的那一刹便已经注定了会是一个绽放的夏季;比如那一只灵动的翠鸟,嘴巴还未画上,耳际已能听见那悦耳的鸣叫;比如那层层叠叠的云涌,每一朵单独摘出来,都足以使天空不再寂寥。

机器生产一把银壶不过几日时间,纯手工打造所需的时间却是机器的数十倍,而在手工制壶的工法中,还有着“焊接”和“一张打”之分,凌飞扬采用的,便是耗时最长,工艺难度最大的“一张打”工法。他似乎总愿意将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机器无法比拟,旁人无法复制。

银壶并不只是美则美矣,养心之余亦可养生,以银壶煮水,可使水质柔薄爽滑犹如丝绢,泡茶时除了可扬香性茶之气,亦可醒普洱、铁观音之味觉,令品茶时的口感喉韵更为细腻甘甜。
一切了然于心,跃然壶上,再通过那双凭心而为的匠人之手,一刀一刀地錾刻,呈现出来的样子只会比想象中更美。与机器压模方式制出的呆板纹路相比,纯手工錾刻的花纹自然而富有灵韵,纹路均匀而灵活,带着手工制作时留下的锤纹印痕与轻微瑕疵,那是时间与掌心共同留下的记号,任何机器都复制不了。
“一把壶制作下来大概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每年的产量很低,最多不超过十把,但是每一把都是经久不衰,甚至用来传家的,我始终认为,好的东西绝不是量多制胜。”
世间万物,皆有可以变通的地方,工具可以改良,技术可以革新,可唯有时间是无法商量与妥协的,既然选择了传统的工法,便要耐得住日月流转的等待与寂寞,按得下追名逐利的浮躁与欲望,无数个晨昏之间,凌飞扬就静静地守候在工作室里,或是等待着一把银壶自然的冷却,或是思考着下一个錾花的落刀,或是用小叶紫檀做出一个莲蓬形状的壶钮,再用白银制成细小的银珠当做莲子,一颗颗装饰其中……他说自己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安静而悠远,亦相信好的器具不惧流年,所以才会不计成本地投入时间,仿佛在他的价值观里,标价只是其次,将所有光阴投掷于此间,才是最值得的事情。
而岁月,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用心的匠人。从凌飞扬手中诞生的银壶,壶身摸起来比机器制作的要薄,分量却十分厚重,那是因为每一把都经过千万次精敲细击的捶打、一点点的淬火,纯度最足的银板在千锤百炼中密度大,性质稳定,久用而不变形,不断裂,不漏水,经得住漫长岁月的炙烤。
“当你执着于一件事情之上时,这件事情同样会将你带到不同的人生维度上,比如从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变成了琴棋书画诗酒花,比如从前我会为了推广生意而妥协,接受一些奇怪的定制要求,而如今我只会专注地坚持去做自己认为美的图案与器形,匠人要有自己的坚守,若是连底线都抛却了,当初何苦放下一切名利走上这条路呢?”
几年来的匠人生活中,凌飞扬自有一番感悟与坚持,他常跟与他讲价的客人们打趣道,“平均下来我的日薪还不如一个泥水工呢。”
从一开始难以被大众接受,到如今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他说老手艺一定要有人坚守,有人传承,而时代慢慢对了,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欣赏这种古旧的手工艺,工匠才能活下来,并且活得自在。
温一壶清水,煮净世俗尘埃
多有文人感叹,魏晋之后再无风骨。
自然,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再难见如诸葛亮一般抱膝长啸于山林之中的翩翩少年;宴饮之间不复古时雅致的酒令,唯有推杯换盏的喧嚣;陶渊明般不为谋生只为谋心的躬耕,落到现在只会沦为笑谈;更无人再“扪虱而谈,”早已将五石散弃于历史的疾风中远远吹散。
幸而,国人的诗性未死,于是仍有匠人愿意传袭古旧的工艺,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为今人留守住一些雅致的情愫,实现着一些内心的向往。
一器一物皆能见生活之美,一方茶席之间,一把千锤百炼、精雕细琢而成的手工银壶,可以使人平心境、舒精气,悦目之时亦可养心,何其美哉。
当然,银壶并不只是美则美矣,养心之余亦可养生,以银壶煮水,可使水质柔薄爽滑犹如丝绢,因着传热快而均匀,泡茶时除了可扬香性茶之气,亦可醒普洱、铁观音之味觉,令品茶时的口感喉韵更为细腻甘甜、顺滑饱满,这是其他器皿难以媲美的。此外,银壶煮水时释放出的银离子可将细菌吸附并将细菌赖以生存的酶系统封闭、失活达到杀菌的效果,而银离子不仅能作用于人体外,进入人体后可杀灭肠道中的病菌,同时排毒,从而使人觉得平静舒适,灵敏度提升。
因着这许许多多的好处,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手工制作的银壶,因为喜爱,便不会拿它与廉价的不锈钢水壶相比较,懂得的人自会晓得,银壶的贵重之处,除去白银本身的价值之外,最珍贵的是那巧夺天工的技术和一份对于情怀与岁月的坚守,这种炽热的工匠精神,使得这把银壶更加弥足珍贵。
器物与人一样,需要一个知己。而通过手工制器,凌飞扬亦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闲暇时与友人三两,温一壶黄酒,对一张古琴,一人弹奏古曲,众人唱和宋词,酒毕用自制的银壶煮一壶清水,泡一杯口感柔和温纯的清茗,涩减韵长,岁月悠悠。
这或许便是他从前设想过的匠人生活,生而有去处,苍而有归途,而我们亦可相见,那些从他手中接过银壶的人们,总能品读到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