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的禅意叙事
任媛

数百年来,古老的东方文化引发欧美文人无穷的玄奇想象和浪漫遐思,从而产生了众多文学的奇花异果。而当我们在对他们蕴含着若隐若现的东方元素的作品细细品读之后,体味到的不仅仅是东方智慧对他们的诱惑,还有他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禅宗便以其纯净、空灵、超脱尘世的审美意蕴吸引着美国一些当代作家顾盼、接纳,使之在禅意玄机中捕捉禅的现代意义,赋予自己的创作以独特的韵味。
以《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而一举成名的“文坛隐士”——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2010)成名之后便离开了喧闹的大都市,在新罕布什尔州买下了一些土地并造了一座小屋,过着60年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生活,到2010年去世前一直在发奋写作,只是196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版过作品,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位“遁世”的作家。有人说:“塞林格将生命中前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努力吸引世人的目光,又把余下的光阴用于努力遁世。”作家之所以选择离群索居,《塞林格传》的作者斯拉文斯基认为,部分原因是塞林格在“二战”期间的从军经历加剧了他的疏离感。内华达大学教授约翰·昂鲁说:“塞林格决定不再发表作品,这是受了他的佛教信仰的很大影响。他希望尽可能不被人注意,放下他的自我。”
从1946年起,塞林格便开始研究佛教禅学,还把读过的与禅相关的书籍赠予身边的朋友以验证其是否拥有灵性。之后他一边撰写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边继续探索禅宗。1950年,他与日本著名作家、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相识,后者多年苦苦追求的是将基督教神秘主义融入禅宗思想。这种表述正合塞林格的口味,他一直相信艺术与精神有关,禅宗哲学与此信念结合之后使他深信,写作过程近乎于禅思,写作即精神救赎的源泉。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就已借人物之口向世人传达出对东方文化的向往,而佛教禅宗对他影响的痕迹则可以从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等词语捕捉到。然而纯真的年代毕竟一去不复返,霍尔顿式的愤世嫉俗与苦闷失意,虽然依旧催生同情共感,但无法走出成人世界困境的主人公最终以精神崩溃宣告了自己以及作者的无奈。此后塞林格更加潜心研究禅宗,在其中后期的中短篇小说里,那些逐步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年轻人开始着手营建并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曾经愤世嫉俗,曾经因精神危机的重压而神经脆弱、心怀强烈幻灭感,但在东方智慧的引导下,就像选择遁世、自我囚居的作家本人一样,欲以自我救赎的形式重构生活的根基,在禅宗的诗性智慧中发现生命本體内涵。同时,这些作品越发呈现出多元开放的、颇具实验性的叙事风格,如禅宗公案、话头的穿插及顿悟情节的安排,使作品焕发出盎然的禅意。
阅读塞林格的作品,总会让读者感受到其笔下一个又一个具有“反正统文化倾向”的主人公在孤独的自我世界中踯躅,在现世的痛苦中挣扎,以及在生命困境中执着探寻,随之在对禅宗的迷恋和顿悟中得以心境澄明。而深蕴禅意的叙事风格更赋予作品耐人寻味的意蕴及诗化色彩,让人品味到其诗意表达“哀而不伤”的旋律。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大多语言平实,但句句可悟而不可言说的禅宗语录隐于其间,亲切、简约、朴素的叙述流露着他对自身存在的探究以及对佛学禅理的体悟。
禅宗公案是中国历代禅师判明教义、对修行禅法者进行指示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言行,用以判断是非迷悟、启发禅思。“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即是一段有名的禅宗公案,禅师不说破,其目的是让学人自觉自悟,明心见性,从而领悟到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述的真理。塞林格把这段公案放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的扉页绝非率性而为,其中的玄妙何在?世人皆知二掌相击方能发出声音,“独手击拍之音”本身无逻辑可言,而这正如禅家真谛,意指放弃执着及捆绑自己的理性规范,从世俗生活的牵挂与纠缠中抽身而出,方可获得生命的真实,即海德格尔所指的诗意栖居方式。或许塞林格以这段公案给《九故事》的读者们提供了一把破解迷津的钥匙,小说中自杀的智者西摩(小说里格拉斯兄弟姐妹中的大哥,被塞林格描绘成真正得“道”的禅师形象)、烦躁无奈的德·杜米埃—史密斯,还有预知自己即将死亡的特迪,纷纷通过自己的心灵感悟走出羁绊,体验到刹那永恒的解脱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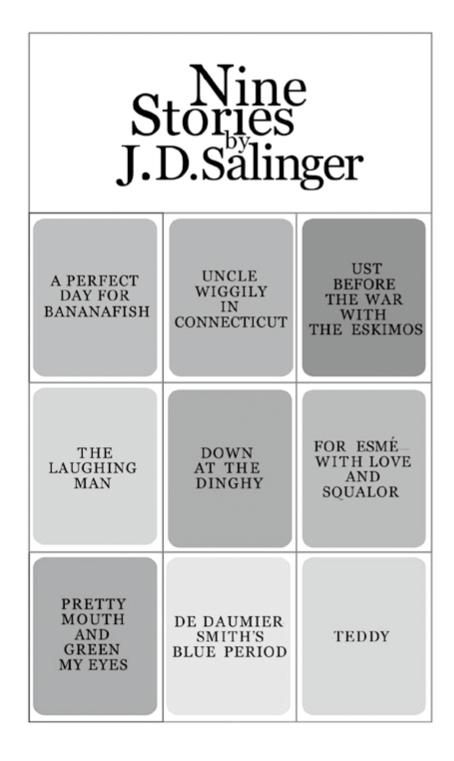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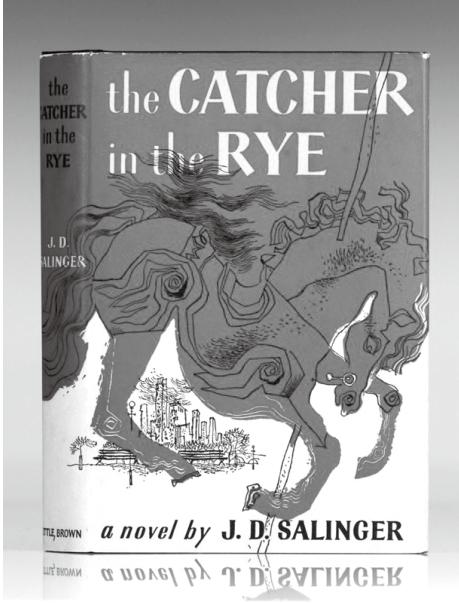
禅宗公案本身是无法用二元逻辑思维去分析的,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是禅师以“即境示人”的方式来开悟弟子。如在塞林格的《西摩:小传》中,10岁的西摩指导弟弟巴蒂打弹子,后者模仿哥哥的技巧却一直在输,西摩便启发他运用“不瞄准的瞄准”方式:“你能不能瞄准的时候别那么使劲?”“如果你瞄准之后打中他,那就只是运气。”说话的同时,智者西摩两脚交叉站在街沿,手插口袋,声音和谐地融入四周的静谧,而此时的巴蒂隐约地感受到哥哥目光中的爱。以上西摩启发弟弟的这段完全就是禅宗公案式的叙事模式,语意模糊,欲言又止,再加上耐人寻味的小动作,便足以直指本心,启迪他人开悟。在此,“打弹子”虽是游戏,却也蕴含着禅的精神。
当塞林格开始创作《 西摩:小传》之时,“垮掉的一代”已经走上舞台中央,诗人金斯伯格等延续着塞林格的追问: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和塞林格一样都痴迷于禅宗,然而塞林格却对他们波西米亚式的疯狂不屑一顾,严厉地斥责他们为“禅宗杀手”,宣告坚决捍卫自己所理解的静寂、幽玄的“纯正的禅”。《西摩:小传》由巴蒂(塞林格的代言人)担当叙述人,在对“垮掉的一代”的谴责中展开对早逝的大哥西摩的回忆,读起来宛若一系列的禅宗公案式的故事,时时绽放出玄妙的感悟之光;通过巴蒂的叙述,西摩幻化成一首转瞬即逝的诗歌,一个空灵清幽的俳句。在巴蒂抑或塞林格来看,西摩的价值仅用生命的长短是衡量不出来的,他的意义在于对他人灵魂的触碰及精神上的导引,西摩的言行及其禅境隽永的诗歌都被当作是“立竿见影的蒸汽疗法”,为精神痛苦的世人带去救赎的希望。
中篇小说《祖伊》也像是一则披着美国外衣的禅宗公案。在创作前,塞林格读完了印度圣人尤迦南达的《一个瑜伽信徒的自传》及《基督再生》。后者认为,通过祈祷和打禅能够唤醒自身内的神圣感,基督的再生可以在任何人身上、任何时间内发生,在明白神无所不在后,人就能在精神上开悟。该小说的情节核心是祖伊按照兄长西摩和巴蒂的教导给陷入精神危机的妹妹弗兰妮以启示,使她最终消除了与世俗的对立而顿悟。这里既没有传统小说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激烈的人物冲突,更没有从开始、高潮到结局的清晰的叙事过程,充斥全篇的是密集而紧迫的话语交锋。
故事的开始,客厅被弗兰妮当成精神的坟墓,那里摆满了物品、家具等,给人造成黑暗、压抑、尘封已久的感觉,上面的划痕甚至每个斑点都会引起一段段的回忆,似乎室内充满了鬼魂,让弗兰妮陷入绝望几近疯狂。母亲为此深感担忧,而祖伊开导弗兰妮未果,无计可施之下假装成巴蒂给弗兰妮打电话,在对西摩的回忆中劝解弗兰妮要超脱、无欲。最后提到多年前巴蒂录制“智慧儿童”节目,上台之前被西摩要求把皮鞋擦干净而极不情愿,因为在他眼中,录音棚里的观众、主持人、赞助商都是白痴,何必为了他们擦皮鞋呢?西摩则劝说,不管怎样擦擦皮鞋吧,为了那个“胖女士”。巴蒂并不清楚西摩在说什么,但还是擦了,并且之后每次上节目前都会为了那个“胖女士”擦皮鞋。当弗兰妮从祖伊口中得知“胖女士”就是耶稣本人的刹那间顿悟了(祖伊认为耶稣因拥有佛禅的慈悲与智慧而伟大,这个故事便成为塞林格作品中一个著名的意象),她释然地轻吸了一口气,突然感觉拥有了世间智慧,知道该干什么了,于是清扫干净床铺,盖上被子含笑睡去,一夜无梦。塞林格在《祖伊》里敞开他的灵魂,把精神与自我之间的矛盾诉说给读者: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总是感到与周围人无法沟通,他们为此而痛苦,这种痛苦塞林格并不陌生,而弗兰妮和祖伊最终的感悟——接纳他人,在凡俗浊世中寻觅美好——更是作家本人心中所愿。
公案中的“无意味语”就是话头,禅宗通过参话头可以使人进入定境从而内心获得宁静。话头看似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如“何谓祖师西来意”“狗子有佛性否”皆为“无解之语”,但究其实,是在强调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和本质的“疑情”。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最令人惊叹的就是精彩的对话,而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是洋溢着浓浓禅意的诗性语言,看似俏皮无厘头,却又让人在似懂非懂中难以释手。如短篇小说《特迪》中的同名主人公在游船上与年轻人鲍勃·尼科尔森便展开了一段极富于哲学意味的、如智者访谈般的问答,由“木头或许并非是木头”谈到“举起的胳膊也并非是胳膊”,实际上是阐释如何摒弃理智和逻辑、以禅之道看待事物本质。禅宗认为万物皆因缘所生,而缘起缘灭之间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性,世间事物本无质的规定性及独立实体。这一讨论尚未结束,特迪马上又提出“伊甸园的苹果是什么”的疑问,从而引发对生与死的拷问。
塞林格小说有着十分独特的悲剧审美韵味,每一篇故事中几乎都少见悲与喜的大波澜,但在表面平和冷静的叙述和禅味十足的诗化语言表达下凝聚着沉重的反思。能够预知未来并参破生死的神童特迪淡然地和他人谈话,淡然地等待终极命运的到来,将含有淡雅清新、空灵澄澈等审美意蕴的禅诗读给尼科尔森听。在禅者眼中,生固未可喜,死亦不必悲,要紧的是超越生死,勘破生死,任运随缘,如预知生死的宋代德普禅师,于雪后焚香盘坐,怡然离世;而特迪同样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即將被妹妹推下游泳池摔死的命运,因为只有超然于生死的概念,才能在其中获得永恒的领悟。
的确,透过塞林格作品的字里行间,读者似乎看到一个个行走在西方的禅宗大师(譬如西摩、特迪),他们一直在以言行启发弟子明辨善恶对错、参悟禅理,而其最忠实的弟子塞林格则将段段习禅语录一一记录。
禅宗的终极目标就是开悟、解脱,就是在自然自在中对终极存在的洞悉。《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通过禅学的领悟达到对人生的理解与超脱,但结尾留下的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又恰恰说明他并未进入彻悟澄明之境;而在塞林格中后期的多部作品中,则清楚地暗示了禅学的“顿悟”让主人公们真正摆脱精神桎梏、彻底实现自我救赎和生命超越。这也可以解释塞林格后半生过着隐居遁世的禅僧的生活方式,即是他参禅悟道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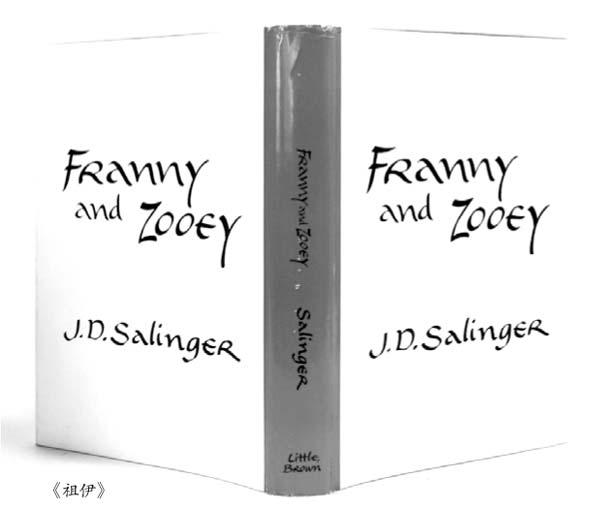
其实,与 《麦田里的守望者》同年完成的短篇小说《陌生人》中的贝比,也仿佛霍尔顿的影子,经历了战乱与战友的死亡,承受着战争的创伤,而后又身处同样混乱的都市,忍受着花粉过敏的痛苦,一次次停下来整理乱糟糟的思绪,不情愿地与陌生人交流,被8月热辣的阳光照射着,倍觉乏味而烦闷地走过街区……然而这一切只因妹妹玛蒂在小说结尾告诉哥哥“我会用筷子”而改变!一如既往,在塞林格的作品中,孩子即本真,而“筷子”则是东方哲学意蕴本真的象征,贝比即刻进入解脱的妙境之中,就连妹妹的随意跳跃都感觉是那样的美好,似乎重获新生。
前面提到的小说《祖伊》开篇不久就一字不漏地展示了巴蒂写给祖伊的一封长信,其中提到自己在超市的肉制品柜台排队时看到一对母女,4岁的小女孩儿天真可人,而母亲的声音则有些刺耳,他联想到在大哥西摩自杀的房间里找到的一首俳句:“飞机上的小女孩儿/她把洋娃娃的头转过来/让她看着我。”就此,巴蒂感觉对真理有了微妙的把握,似乎转瞬之间顿悟,决定立即回家给弟弟祖伊写信,引导他要坚守本真,告诉他不管做什么,只要是美的都会得到爱与支持。或许,这里的小女孩儿、洋娃娃在巴蒂看来就是本真,是美、善及人生终极意义的象征,而“肉制品柜台”、发出刺耳声音的母亲则是世俗烦扰及妄念的象征。巴蒂的顿悟即是来自那一刻对人生本真意义的呼唤与感受。而身处这世俗众生之中,何以进入真正的生命存在?慧能语:一念悟,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破除烦恼业障,解脱生死轮回,了悟之时便顿见真如本性。于是,祖伊替代顿悟的巴蒂启示弗兰妮:百老汇剧场里脑满肠肥的观众就是“胖女士”,即耶稣本人!此刻的弗兰妮顿觉心中的焦虑烦忧顷刻消散。《西摩:小传》的结尾,巴蒂亦领悟到:“房间里所有的女孩儿,包括恐怖的扎贝尔小姐,她们都是我的姐妹,都和波波还有弗兰妮一样;也许她们身上散发着时代的错误信息,但是她们确实在发光。”仿佛“见性成佛”的兄妹几人,与霍尔顿一样自心消解了与世俗的对立。
禅宗美学把妙悟的目的诠释为生命的超越,开悟前后虽同是一人,但在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上却又恍若隔世。开悟前或许只是一条曳尾于途中的青蛇,开悟后却是遨游天宇的巨龙;开悟前或许只是一条摇尾乞怜的小狗,开悟后却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金尾狮。于是,生命突然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得以怀揣着前所未有的凛冽心境重返尘境。同时,禅宗的顿悟也像一首诗,表现了禅者一瞬间的生命体验,顿悟的境界,就是瞬间获得永恒的境界。
塞林格日日打坐的生活是静谧的,不过对于外界的读者及评论家们来说,他的退隐是一种困惑,这种困惑留下了神秘的空白。虽然塞林格一次次请求不要搅乱他的生活,但不少人仍然希望揭开谜底。而塞林格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他的沉默一方面引来四起的传言,同时愈加为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平添了几许神秘而更具传奇色彩,甚至大家对其本人的痴迷程度超过了对其作品的研究。曾经的塞林格因个人的价值观在大众中间显得格格不入,1970年代之后却被美国青年一代奉若神明,在对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的质疑下,人们开始追逐纯朴、适意、洒脱的境界和身心自由的超越,希望在令人焦灼的时代里寻找出路,于是禅宗和五花八门的印度哲学开始大行其道,精神探索方兴未艾。对那些顺应上述潮流的人来说,塞林格近乎先知。而在他的小说文本中,禅家况味浓郁的叙事呈现出来的就是令人回味的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与思”的结合,可以说,塞林格就在这诗性化的表达之中早已寄予着对人类存在的深沉思考。
注: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塞林格后期中短篇小说禅家况味研究”(项目编号:TJWW13-01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