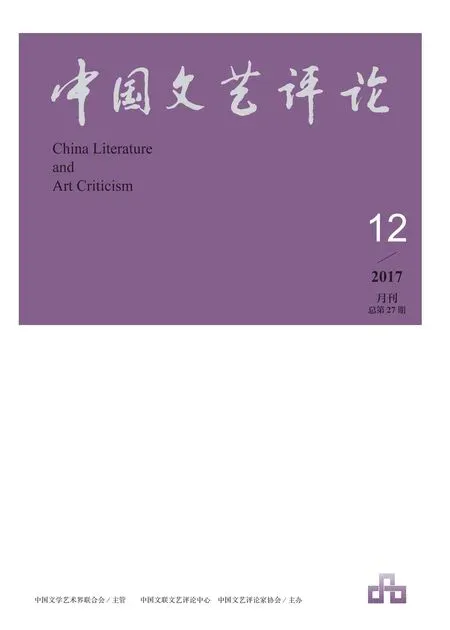探索中国水墨现代“画”之路
——访画家刘国松
采访人:李昌菊
探索中国水墨现代“画”之路——访画家刘国松
采访人:李昌菊

一、面向东西方艺术
李昌菊(以下简称“李”):
刘老师好,您不仅在台湾被称为“现代水墨之父”,还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刮起“刘国松旋风”,作为中国水墨现代化的先驱人物,您开启了观念和技巧上的革命,您是如何走上绘画道路?曾经受教于哪些教师?刘国松(以下简称“刘”):
我14岁开始画中国画,那时候在武昌读中学,上学路上有个裱画店,每天放学的时候我都会到那个裱画店去转一转。店里的裱画师傅看我经常来,就问我是不是很喜欢画画,我说是,他说你想不想学,我说当然想,他说那我给你介绍个老师吧。但因为父亲在抗日时保卫大武汉中阵亡了,家里很穷,找绘画老师也付不起学费,甚至家里连纸笔都没有。于是这个裱画师傅就找了一沓裱画裁剩下的纸,又拿了两支笔、一本画册,让我回去照着画,于是初中二年级那个暑假我整天都在画画。初三下学期我考取了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那时学校要办一个初中毕业展览,老师让我交了一幅国画作品,展完之后,学校把我的画挂在了贵宾室、校长室,这对我鼓励很大,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当画家。后来这个学校迁到台湾,我们被安排在师大附中读书,在高二时我以同等学历考进了师大艺术系。当时的师资主要是国画和西画的,国画方面有黄君璧、溥心畲、林玉山以及金勤伯老师。西画方面有朱德群、赵春翔、廖继春和孙多慈老师。李:
您早年喜欢中国画,但在中国现代画探索之前,比如在1956—1959年间,您的创作曾以西画为主,您为什么会去画西画?这一阶段您的表现主要受什么影响?刘:
大学一年级时,一位老师讲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一切艺术来自于生活。之后我就反省,学国画全是临摹,并不是来自于生活啊。到了二年级,水彩画、油画全部写生,这倒是来自生活,于是我开始全盘西化。当时我在台湾是一个人,没有经济后盾,因为水彩颜料便宜,所以画的水彩画比较多。从那开始,我从印象派起步,一直追随20世纪欧美大师们的脚步,最后画到抽象表现主义,画了七年。李:
您不仅坚持自我探索,也善于团结同仁共同努力开辟新局面。1956年您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后,与同学们一起成立了“五月画会”,那么成立“五月画会”的缘由与初衷是什么?刘: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同窗们都在准备毕业创作,那个时候我们早就不画印象派,已经画野兽派、立体派了。台湾那时候有个全省美展,我们从大一到大三看了三年。毕业之际,我们班四个人约定去拿那个全省美展的奖,结果三个人落选,一个人入选,入选的那位还因为画的是印象派。后来,我们听说最终得奖的都是些评审委员的学生,于是我就提议,干脆我们自己搞一个画会,自己展览,大家很赞同。当时大家对法国的“五月沙龙”非常崇拜,年少幼稚的我们便想着做一个“五月沙龙”的台湾分号,所以便取了“五月画会”这个名字,每年5月展览。就是在这种“全盘西化”的氛围之下,“五月画会”成立了。李:
从1959年起,您开始向民族传统回归,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促使您文化选择的转变?刘:
全盘西化之后,“五月画会”到了第三届,我就发现这样做不对,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画抽象表现派了,跟着西方画家的脚步走,但我发现美国抽象表现派的不少画家却是受中国书法影响。我想,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文化发扬光大,却要等外国人把它发扬光大之后,我们再去学呢?于是,1959年第三届“五月画会”时我提出,我们应该走中西合璧,而不是再全盘西化。李:
1961年起您开始画水墨画,并以抽象的形式去表现,您认为既不能仿古也不能仿洋,甚至也不同于今人,您为什么重新开始画水墨画,又是如何开启自己的中西融合的创作之路?刘:
这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很频繁的时代,不可能完全不受西方的影响,要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应该是中西合璧。那个时候我是把水墨画加到油画里面,让油画既有西方的材料特点,又有中国水墨画的一些感觉。这样画了两年之后,我又觉得不对了。因为我当时在建筑系教书,参加他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建筑材质的问题。有人讲无论用什么材料,都要把那个材料的特性发挥到最高境界,不可以用这种材料去代替另外一种材料的特性。后来我一想,我在这用油画颜色要表现水墨画的趣味,是不是在作假呢?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想,既然想把水墨画的味道发扬光大,为什么不直接用水墨呢?另外,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美术史以及美术理论的书,发现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都是从人物写实到花卉,然后到山水,这个路子是完全一样的。在形式上看先是写实,然后经过写意,达到抽象的表现。但是中国比西方走的快,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第一句话就是“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就有石恪画出了非常写意的《二祖调心图》,随后又有梁楷的《泼墨仙人图》。而西方一直写实,直到19世纪末受了日本浮世绘和版画的影响,20世纪初才开始写意。
西方印象派画家因为看到东方二度空间的绘画比他们三度空间的绘画更有艺术味道,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所以他们就开始变了。东方的画受老庄与禅宗思想影响,不太写实,同时也受儒家中道思想的影响,就是不偏不倚走中间,既不写实,也不抽象,一直停留在写意、半抽象的领域,后来西方追上来。我们那时候全盘西化就是因为一方面对中国画的保守不满,另一方面觉得西方的创意和抽象很有意思。其实,我们真正的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是最能欣赏抽象美的民族,抽象美学从很早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了,例如早期的彩陶上面的抽象花纹,甚至我们戏曲表演中的很多动作都是抽象的。
我想,我们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化里,要有选择的把它保留和发扬光大,对西方现代艺术也是有选择的吸收消化,不能再全盘西化了。1959年,我开始用油画探索中西合璧之路,画了两年。到了1961年,我提出了“中国画的现代化”,从此开始回到水墨画的实验与创造上来。
二、在革命与实验中创造
李:
为了探索水墨画现代化,您不仅挑战自我,更多次颠覆传统,如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革中锋的命”,这无疑是惊世骇俗的,您说:“作为一个艺术的创造者,不但有不用中锋的权利,而且还有不用笔的自由,为了表现的需要,画家有权自由地选择任何其他需要的工具和技法。”您为什么提出这些非常具有叛逆色彩的观点?刘:
我先来讲书画不同源。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原始人在岩石壁上就已经开始画画了,而书法是很久之后才有的,所以我认为书画是不同源的。要勉强讲它同源的话,它同的是用笔。由于文人日常生活离不开毛笔书写,于是把书法性的要求在绘画中拔高,最终发展为一味强调不用中锋就画不出好画来。中国画的技法有那么多种,有各种不同的风格,结果到最后就变成一种技法,一种风格了。所以那时候我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要想继续走就要革中锋的命。不但要革中锋的命,还要把笔的命都革掉。画画是为了表现,怎么表现是画家自己的权利,只要能表现出来就好了。李:
在水墨画艺术创作中,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创造与实验意识,非常注重材料、工具、技法的创新,不仅发明了“国松纸”,自创“抽筋剥皮皴”、拓墨、水拓、渍墨、揉纸、喷洒、拼贴等种种方法,还运用各种刷子、器物作画,制作出变化莫测的画面肌理效果,这些方法完全有别于传统笔墨表现。您可否介绍下这些技法的发展变化过程?刘:
在传统上,中国画跟西洋画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画是用点和线组合而成的,西方的绘画是面和面的关系组织而成的。但是中国画的点和线全是黑点,我想如果能把白线也加进去的话,我们的表现能力就增强了,领域也拓宽了。1961年至1963年,我一直在做拓墨画,后来是利用了10世纪石恪画的《二祖调心图》的狂草笔法来作画。水拓花了很多时间,渍墨画也是,就拿九寨沟系列来说,实验了很多次。1963年至1969年,是狂草抽象画时期,把白线加入到中国画中。1969年到1975年,是太空画时期,1976年后,开始试验水拓画,搞了十几年,接着是渍墨画,又是十几年,到后来画九寨沟、雪山系列,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李:
从1969年起到1975年,您创作了四百多张太空画,拓展了中国传统绘画表现的时空,这是传统水墨画从未表现的题材,您为什么对该题材这么感兴趣?能介绍下相关创作情况吗?刘:
这些画里的方圆,其实是受元宵节花灯的影响。有一年元宵节,台湾的庙会上有花灯展,孩子们非要我带他们去看,然后看到了走马灯。走马灯长长的,底下摆蜡烛,上面有圆的洞,里面有马在转,我将这个构图记了下来。后来又受美国太空发展的启发,看到了阿波罗7号第一次拍回了地球的照片,觉得应该把这个时代的变化记录下来,于是开始了这个主题,结合之前走马灯带来的构图启发,动用了一些剪纸拼贴的呈现方式,太空画就出现了。我第一张太空画是《地球何许》(Which Is Earth),创作于1969年,送到美国参加5月举办的主流国际美展(现收藏于凤凰城美术馆),得了个绘画大奖,这对我的鼓励很大,后来就又画了一大批“太空系列”的作品。
刘国松 《午夜的太阳 III 》 139.7×375 cm 1970年
李:“
太空绘画”之后您又变了,从1977年到1987年,您主要是水拓法时期,而后开始渍墨法实验,这些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刘:“
太空系列”发展到后面,画面感觉逐渐西方化,其中的东方感觉开始弱化,画到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越走越西方了。艺术家在一种风格成熟后难免进入自我复制,而我对于这种已经可以控制自如、没有挑战性的创作感到累了,开始寻找新的创作路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看中国美术史里面介绍,除了文人画之外,传统美术有版画、年画、绣画、缂丝、漆画,还有两个特殊的名词,火画和水画。其他的画我都知道是什么,水画跟火画是怎么回事,又为什么失传了呢?我决定把它找回来!我开始做实验,先拿香去烧、熏那个纸,结果并不成功。后来我就尝试水画。我们在画传统国画时如果笔墨太浓了,想让它淡一点,就把笔在水盂里蘸一下,之后就有墨浮在水面上,我想“水画”一定跟那个有关。刚开始实验时,我拿个洗脸盆装满水,滴一点墨上去,墨迹就浮在水面上,然后我就拿宣纸往上一放,把墨痕吸到宣纸上,产生水纹的痕迹,这就是“拓墨”画中“水拓”的开始。1970年代和80年代的画中的一些线条都是水拓的,颜色是后来加的。渍墨法的创作是把两张干的纸摞在一起,然后把清水用不同的方法泼洒上去,那样两张纸大部分就会粘在一起,彼此的夹层中会有很多形状不规则,充满偶然性的气泡。继而我再把墨和颜色泼洒上并渗透下去,让墨色在两张纸间流动,这样就会沿着气泡的边缘,形成不规则的墨渍和纹路,尤其是狭长的气泡和缝隙就会促使墨色的黑线边上有时会贴着一条空隙形成的白线,如影随形,效果非常特殊,这些都是用笔无法实现的。
一开始我画了一批渍墨画,后来我去了三次九寨沟,那里的山水深深地感动了我。尤其那里的水,由于湖底积存物的反射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风吹过水面时,风的大小对水面的水纹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太美了。

我画九寨沟只画水,因为我对水面波纹变化的感受最强烈。开始时,我用渍墨、用宣纸来画,后来又用棉纸画,结果都画不出那个味道来。结果还是曾经被“挤”到建筑系教学的经历再次启发了我。那时我看到建筑系的学生赶绘建筑设计图,发现他们用的描图纸(大陆叫“硫酸纸”)很有意思。传统的中国纸打湿后都是透过纸背,西洋纸打湿后颜色是不会透过去的。同时描图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打湿之后就会横向里起皱,于是我就把描图纸铺到下面,上面用宣纸盖上,然后打湿,打湿之后就发现下面那个纸皱成一条一条的,就有水纹的效果。进而我尝试把描图纸铺到底下,先在上面喷水,等它起皱后我把颜色再往上滴,滴完了之后就把另外一张描图纸铺上去。因为下面那个纸已经皱了,而且颜色也顺着纹路在走,这样干湿两张纸相叠又起到了类似印染的效果,而且水的多少、纸的厚薄不同,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这都是不断实验做出的效果,所以说画室就是实验室,不停的自我突破,不停的实验,不停的革命,这是我持续至今的创作理念。
李:
1990年代您又综合运用各种手法,并强化了色彩的表现,您为什么又开始重视色彩?刘:
水墨水墨,这个墨是一个色彩的代名词,不是说一定非墨不可。我们中国画在早期的时候颜色是非常重的,叫重彩,到了唐朝以后,水墨才慢慢成为一种绘画形式。把笔墨这两个字用现在的观念来分析它,什么叫做用笔好?因为中国画都用笔画,这个笔画到了纸上或者绢上去之后,留下的痕迹好的话就叫用笔好,但是留下的痕迹不就是点和线吗?对不对?所以说笔者就是点和线,点线画的好就叫用笔好。什么叫做用墨好呢?墨就是用墨或颜色渲染出来的面的效果好就叫用墨好,如果用这个颜色染出来的效果不好,就叫用墨不好,所以墨者就是色和面,所以说笔墨这两个字就是点、线、面、色彩。这些不是中国画独有的,所有的绘画都是点、线、面、色彩。所以笔墨这两个字要把它从狭隘的文人画里解放出来,海阔天空,你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线条好的话都叫用笔好,你用水彩画颜色也好,用别的颜料也好,只要用的好都叫用墨好。李:
您十分热爱自然,去过许多地方,看见喜爱的景色时您会对景写生吗,或者拍照作为创作的素材与参照吗?刘:
我做学生的时候写生,后来就不写生,创作时从来不写生。人们问你有没有照照片,我说我根本没有照相机。我到每个地方就是看,感受那种氛围与气势,中国传统画家都是把感受存在身体里面,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我2010年年底去九寨沟,回来之后就开始做实验,我画九寨沟跟传统的画水完全不一样,不光是我的技法不一样,而且出来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我画水,就只画水,别的通通不画。
李:
范迪安先生曾说,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各地,只要谈及水墨画现代发展这一命题,刘国松的艺术总是一个榜样,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系。为了实现中国现代画的理想,您成立艺术组织,举办展览,还发表文章,四处讲学,并示范自己数十年探索的表现方法,您不断寻求技法与风格上的变化,这中间遇到过什么困难与阻力吗?刘:
当年我在台湾时,所有的美术系不敢请我,因为他们都很保守,怕我把学生教坏了,所以我被挤到建筑系去教素描和水彩画,因为他们是用水彩来画建筑图,水墨画根本不用的。还有,我们曾经搞了一个全省的现代画会的大串联,在台北展出,结果就受到压制,说我们破坏中国传统文化。1966年,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基金会给了我一个两年环球旅行奖,在美国住了一年多,后来又到欧洲去环游。回来之后,台湾马上给了我一个“杰出青年奖”。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外国承认,台湾才承认,我很感慨。还有我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1976年在《台湾联合报》副刊连续登三天,在香港的《星岛日报》的副刊也连续登三天,港台两地的传统画家都一直在骂我。我曾经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受画家徐渭的启发,他上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下联“一个南腔北调人”,我也来一个对联,“几幅乱七八糟画,一个东西南北人”。我是一个北方人,却在南方长大,在台湾受教育。我是一个东方的画家,在西方成名,最早是被西方认同的,在台湾根本没有人认同我,而且被打压。所以我就感慨,就来了一个“东西南北人”的称号。
三、先求异,再求好
李:
您一边创作,一边教学,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东海大学、台南艺术学院、美国爱荷华大学和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等学校任教四十余年,您认为建立中国现代画必须从学生抓起,不仅开展了探索性、实验性、创造性的教学,还提出了著名的“先求异,再求好”的教育理念,怎么理解这一观念?请您介绍一下。
刘国松 《永不融化的屹立》 185×277 cm 2016年
刘:
在台湾都没有美术系请我,所以香港中文大学就请我去,本来请我去做一年访问,结果访问一个学期之后,就希望我留下来做系主任,改革学校的艺术系。1973年,我做了系主任之后,有了开新课的权利,开了一门现代水墨画。我反传统的美术教育,主要的理论是“画室就是实验室”,画室不是传统绘画制造的工厂。因为我觉得以前的画室都是制造传统绘画的工厂,没有什么创意。对于美术教育,我的一个改革思路,就是“先求异再求好”。上课我就跟学生们讲,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很崇拜科学家,但是我们跟科学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创造者。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家,要先有一个新的思想,有了新思想后,要证明这个新思想是对的,就得做实验。实验成功了,刚好是想的那个结果,就算是有所发明,有所发明才是科学家。没有发明是什么科学家,最多在大学里教个物理或者化学。我说画家也一样,也要先有一个新的思想,要把你的新的思想落实在画面上,但是你用传统的技法,用传统的材料,没有办法把你的新思想落实上去怎么办?做实验,实验新的技法,通过新的技法落实新的思想,一旦你新的思想在画面上真的表现出来了,那你就有所创造,有所创造才是画家,你没有创造是什么画家?我说没有创造最多也就做个老师,我跟学生讲画室是实验室,教室也是实验室。传统的美术教育是受了一个教育思想的影响,那个教育思想是什么呢?叫为学如同金字塔,就是从开始画花鸟,然后画山水,然后画人物,一步步去学,把这个地基打的越宽越广,将来金字塔盖的越高,先把传统的各家各派的技法都去临摹,都去学好,学的越多越好,这是传统的教育思想,这是通才教育。
基于这个观点,我曾经画了两张画,就是《荒谬的金字塔》《现代艺术的摩天大楼》,这两张画是我对于传统美术教育的一种批判或者宣示。我把“为学如同金字塔”的理论称为“先求好,再求异”。我从事美术教育超过半个世纪,就提出一个相反的想法:先求异,再求好。摩天大楼的地基是往深里扎,不是求宽广,是求专、求深、求精、不求广的摩天大楼的建筑才是符合专业教育的思路。
现在学画一开始都是学花鸟、人物、山水,到最后画来画去还是古画。“先求好,再求异”的结果是,越“好”越“异”不了,画得越“好”越没办法跳出古人的牢笼。很多画家画了十几二十年,拿起笔来,很自然地就是那一套。传统国画专业出来的,一年有多少毕业生?但现在又有几个出人头地,有几个真正国际知名的大画家?而在国画创作出名的,大都是从西画出身的。因为西画没有那个包袱,吸收一些传统的东西,就可以把它发扬光大。
我的现代水墨画课程是绝对不允许临摹的,完全反对传统的美术教育。我说画室是实验室,延伸之后可以说教室也是实验室,所有的学生都来做试验,不许临摹。我有个学生李君毅,到现在从没有临摹过一张古画,也没有临摹当下画家的画,更没有画过传统国画。但他看过很多古画,他从古画里边吸收了传统绘画的精神,但没有采纳形式。他大学二年级到我的课程班学现代水墨画,画了三年,毕业得了第一名,现在已经国际知名了。
画家是人类文明史的创造者,没有创造就不是画家了,最多是个老师。有一次我在福建福州演讲,有一个年轻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刘教授,按照您这个说法,现在大陆的文人画家都不是画家了吗?他这个问题一问,全场鸦雀无声。我说,对的,没有错,他们都是助手。你看科学家有了新的思想就去做实验,但他可能是在大学教书的,他要上课、改卷子、改论文、演讲、开会,可能还要出国,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来做这个实验,怎么办?他就教给他的助手,你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最后的结果拿给我看。这就好比传统的文人画家,古人怎么画他怎么画,老师怎么教他就怎么画,为什么这么画不知道。画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他要的,也不知道。话音刚落,台下一片掌声,第二天报纸报道称“刘国松丢了一个重磅炸弹”,从此保守派骂我骂得更厉害,说我是玩特技的,画画是制做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
李:
与许多单纯的画家不一样,您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勤奋的作者,您觉得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刘:
通过研究美术史和传统画论,就可以告诉我哪些路不能走,哪些路可以去闯。因为这样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走,我应该走哪一条路。没有理论研究的人,他就只会跟着潮流走,不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李:
您已经走过七十余年的艺术历程,这种执着创造的原动力从哪里来?回顾您70年的艺术创作历程,您有些什么感想与我们分享?刘:
我的创作动力就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爱,创作完全是由爱出发的。我爱中国文化,喜欢艺术,并一心想把它发扬光大。我太太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做“现代水墨画的传教士”,我把艺术当成一种信仰,只要把它当成一种信仰,就绝不会因受他人的攻击而改变。我觉得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作为一个画家,一生里面创作几种个人风格,其做画家的责任已经尽到了,而且还教育和影响了很多的学生。在台湾时受争议,美术系不请我,所以对台湾的美术教育一点贡献也没有。后来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台湾东海大学请我回去教课,我就回去了。二十多年来,我已培养了一批现代水墨画的接班人,对台湾来讲,已没有遗憾了!李:
您对大陆的现代水墨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开启,可以说是最早的引路人,很多人都向您学习过。今天大陆的现代水墨探索也很活跃,您怎么看待这种探索现象,或者有什么建议?刘:
现在有那么多的画家在做水墨实验,从上世纪末一直到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美术馆办了现代水墨画的展览,古根海姆美术馆曾举办五千年中国文化艺术展,里面就有现代水墨画的部分,那个时候他们向芝加哥美术馆和一位香港的收藏家各借了一张我的大画。随后大英博物馆、德国林登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相继举办了现代水墨画的大展。为了推广中国画的现代化,总算是有了成绩,的确是很高兴的事情。李:
谢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谈,祝您节日快乐,健康长寿!访后跋语:
对先生慕名已久,在2017年8月下旬举办的“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上,有幸聆听先生亲讲“中国水墨文艺复兴”。先生谈古论今,跨越中西,视野广阔,虽已85岁,然精神矍铄,声若洪钟,其率真洒脱的气度风范令人印象深刻。承蒙《中国文艺评论》重托,委以专访刘国松先生的美差。先生往返于港台与内地之间,如何拜见尚不能确知,一时间有些茫然。幸得先生之女刘令徽女士大力支持,告知先生的行程,于是,一场北京赴上海的专访,在9月底开启了轻快的节奏。
先生端坐室内,面带微笑,侧对来访的我们,那一幕定格在幽淡不明的光影里,宛若画面,不能忘怀。从少时习画到专业训练,从抗争台湾官方美展机制到成立“五月画会”,从全盘西化到复兴传统,从潜心画史画论到反思批判,直至风格初成再求新意。先生的艺术探索之路,在洪亮的声线中,源源不断地延展开来。先生不仅创“国松纸”,尝试拓墨,制作肌理,试验水拓,汇入色彩,运用渍墨,还激扬文字,著书立说,在深研传统的基础上,力倡“革中锋的命”,反对笔墨中心论,这些无不惊世骇俗。不过,反传统不是不要传统,而是解放既有观念,走向更自由更恢弘的创造。
三个半小时,先生侃侃而谈,以生动、风趣的话语,与我们分享创作的过程、观念与细节,那份大破大立的胆识豪情,那样不畏险阻的执着追求,那种引领水墨走向世界的信念,令闻者时时感佩于心。难以想象,眼前这位平和、达观、睿智的先生,竟是一位勇于挑战的艺术先锋与斗士。是啊,不同凡响,不拘一格,力主创新——先生最鲜明的本色,早已凝结在天地浑茫的画作中,也浓缩在这个晴好静幽的下午时分。
几十年如一日,这位新水墨的开创者,上世纪60年代成名于美国,80年代风靡内地画坛,已誉满海内外,但先生从未就此止步,依然以年轻人的激情,沉浸在宏大的水墨天地,创造着独特的艺术风貌!
刘国松简介
刘国松,1932年生于安徽蚌埠,祖籍山东青州,1949年定居台湾。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美国艾荷华大学与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所长、国内多所重点大学与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现任台湾师范大学讲座教授。曾于1956年创立“五月画会”,发起现代艺术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五年后开始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提出了“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的鲜明主张。1983年初,刘国松应中国美协之邀在中国美术馆办展,三年内在国内十八个主要城市巡回展出,并到处演讲与讲学,促使传统文人画的一元化走向了多元的局面。1985年第六届全国美展曾颁给他特别奖,2007年故宫博物院在中国文化经典的殿堂举办“宇宙心印·刘国松绘画一甲子”特展,他又先后获得了两岸最高的“台湾文艺奖”(2008)、“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2011)和“台湾文化奖”(2017),是第一位华人画家获得美国文理科学院的外籍院士(2016),同时也获选为中国文联的荣誉委员。李昌菊: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王朝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