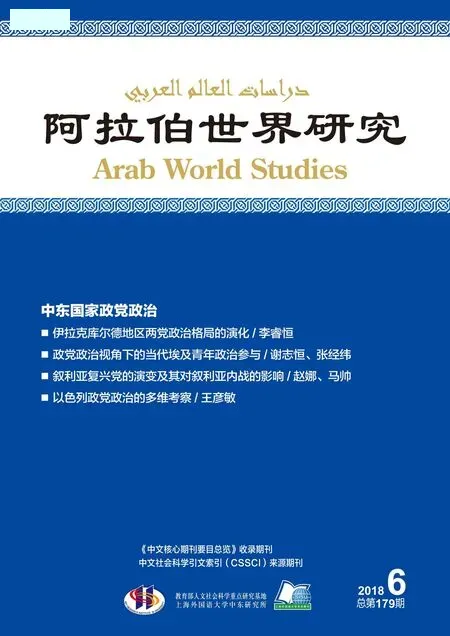政党政治视角下的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
谢志恒 张经纬
自现代政党产生特别是立宪君主制建立以来,埃及青年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该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埃及15至35岁青年[注]当前国际社会对青年年龄范围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联合国将青年人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5~24岁,但考虑到青年人实际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大以及社会对于青年依赖性的增强,世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按照联合国对青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包括埃及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对青年年龄界定的上限超过了28岁。中国对青年的界定是14~35岁。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政治参与问题,青年政治参与的年龄普遍比一般意义上的青年年龄要高,因此本文探讨的埃及青年是指年龄在15岁至45岁的群体。参见邓希泉:《青年法定年龄的国际比较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第40页。人口数量超过3,200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44%[注]Nadine Sika,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Egypt: From Abstention to Uprising,”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9, No. 2, 2012, p. 185.。政党作为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在穆巴拉克时期实现了长足发展,但威权主义的精英统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效果。
2011年“一·二五”革命标志着以青年为主体的抗议群体对埃及长久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各种问题不满的全面爆发。其间,埃及青年利用各种社交媒体抨击政府行为,联合反政府力量进行街头抗议,[注]Shahjahan H. Bhuiyan, “Can Democratic Governance Be Achieved in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8, No.7, 2015, p. 502.高喊“人民要政权倒台”等政治口号,表达革除旧政权与旧体制的决心。[注]Reem Abou-El-Fadl, “Beyond Conventional Transitional Justice: Egypt’s 2011 Revolution and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Wil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 6, No. 2, 2012, pp. 319-320.抗议群体将1月25日称作“愤怒日”,以表达自身对埃及社会“暴力、腐败、贫穷和失业”等现象的不满,主张“要面包、要自由、要尊严”。[注]Ibid., p. 323.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步入政治转型期,政党政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通过选举上台的穆尔西政权仅维持了一年,世俗威权政体便再次回归。当前,青年借助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空间仍然有限,此前埃及社会面临的教育、就业等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进而导致青年对未来感到迷茫。本文试从政党政治的视角考察“一·二五”革命前埃及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制约因素及社会影响。本文探讨的青年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当代埃及威权政治体制下,青年通过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行为,主要包括埃及青年在政党内部的政治地位、政治诉求、政治行为及其效果。
一、 埃及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的传入,埃及教育与媒体迅猛发展,埃及民众对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增强,政党开始登上近代埃及的政治舞台。1879年奥拉比创建的祖国党是埃及首个初具现代政党形态组织,该党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军人、官员及开明地主都加入了该党。面对西方的渗透和控制,祖国党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宣扬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思想,反对陶菲克的专制统治及其与英国的勾结。祖国党要求当局推行政治改革,建立欧式议会,实行宪政。祖国党的上述活动史称“奥拉比运动”。祖国党的建立及其开展的奥拉比运动,在思想层面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埃及政党政治的演变和发展。
1882年,英国以恢复埃及秩序为由出兵镇压奥拉比运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埃及实行全面控制,埃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活动遭到英当局的严厉打压。尽管如此,1907年,埃及诞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民族党。该党坚持民族利益至上,强调以埃及民族认同超越宗教,实现埃及社会统一。该党崇尚自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英国的占领,反对民众暴力运动,主张渐进式改良。同年,穆斯塔法·卡米勒成立了埃及第一个提出明确纲领、组织严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政党——新祖国党。该党要求在埃及建立议会和工会、实行民主,反对英国殖民者,主张用暴力手段实现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卡米勒去世后,新祖国党内部分裂成激进派和保守派,导致该党实力不断弱化。这一时期,埃及还出现了一些小型世俗政党,但它们都因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并受到英国和埃及统治力量的双重打压而逐渐衰微。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受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埃及国内以世俗自由民主思想为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1918年成立的华夫脱党成为埃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议会政治的核心力量。华夫脱党一方面竭力参加巴黎和会和英国直接谈判,另一方面领导和协调民众暴力抗争向英国施压,最终迫使后者于1922年单方面宣布埃及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英国仍控制着埃及的军事和外交大权。
1923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埃及进入了立宪君主制时代。1924年议会选举获胜首次组阁后,华夫脱党成为该时期埃及社会基础最广泛、选举得票最多的政党,但该党主要的社会支持力量是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土著乡绅和城市中产阶级等群体,在党内外推行精英和老人政治,[注]哈全安:《中东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2页。将广大下层民众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其争取民众支持的唯一诉求就是实现民族完全独立,手段是在议会框架内与英国谈判。但在英国和埃及王室的联合夹击下,华夫脱党无力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陷入了长期维护议会政体斗争的尴尬境地。1936年,华夫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与英国签署同盟协议,背离追求民族完全独立的建党宗旨,渐失民心。二战期间,英国对埃及加强控制,战争给埃及带来了经济灾难,战后埃及民众掀起反英反政府运动高潮,华夫脱党等世俗自由民族主义政党主导的议会政治逐渐走向衰落。
此外,议会体制外的政治力量——青年埃及党、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和自由军官运动等政党与组织逐步兴起和壮大,青年埃及党和穆兄会在城市青年、学生、工人和中产阶层等群体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1933年,埃及青年组建了第一个政治组织——青年埃及协会,后改称为青年埃及党。该党倡导法老主义[注]法老主义是埃及近代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学主张,强调埃及的历史和文明,以及由此而来的埃及个性和独立精神。该思潮认为法老文明是埃及文明的本源,埃及的历史和文明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到来后的历史和文明,早在伊斯兰国家出现之前埃及就存在绵亘了数千年的法老文明,法老文明留下了辉煌的文学艺术遗产。这一思想常在非伊斯兰教的科普特思想家的言论中得到公开或曲折的表露,在埃及的穆斯林思想家中也有支持者。、埃及至上、伊斯兰认同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反对华夫脱党的西化思想和议会君主政体。[注]James P. Jankowski, Egypt’s Young Rebels: “Young Egypt”, 1933-1952, Stand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p. 44-107.该党所有成员均因年龄未满宪法规定的30岁而无法参加议会选举。20世纪50年代前,青年埃及党始终未能获得议会席位,[注]谢志恒:《埃及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76页。缺乏直接推行其政治主张的机会。
穆兄会由埃及青年教师哈桑·班纳于1928年创建,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则,主张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倡导实行伊斯兰教法,[注]哈全安:《中东史》,第586页。反对西方文化和世俗教育,反对妇女解放,崇尚“圣战”观念,倡导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统一,[注]哈全安:《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26页。认为伊斯兰教需根据时代变化进行调整,强调早期伊斯兰政治理念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注]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3期,第25页。二战后特别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穆兄会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并对埃及政权构成威胁。1948年,该组织因其成员暗杀埃及首相努克拉什而遭到镇压,班纳亦遭暗杀,穆兄会内部出现分裂,此后激进派与温和派的纷争一直影响着20世纪后半叶该组织的发展进程。
在民众政治力量与旧体制和旧势力激烈碰撞、社会动荡无序之际,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乘势崛起,于1952年发动“七·二三”革命,终结了立宪君主政体,开启了埃及共和国时代。纳赛尔时期,埃及政府为加强集权取缔了包括青年埃及党、华夫脱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穆兄会亦遭打压和解散。纳赛尔政权先后成立了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等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和组织。统治集团需要党内各精英团体的支持,而作为回报,各精英团体也获得了必要的政治利益,但没有进入精英团体的埃及青年则很难有政治话语权。
萨达特执政后推行政治多元的自由化政策,穆兄会重新恢复活动,并在穆巴拉克上台后成为埃及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伊斯兰组织。1976年,萨达特开始实行多党政治,两年后华夫脱党重新组建。此后,埃及的政党数量不断攀升,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多党制实现了较大发展。但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党法》和《选举法》对反对派政党参与议会竞选做出诸多限制,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仍未真正脱离。[注]哈全安:《埃及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不仅如此,埃及共和政体建立以来,强人政治和威权体制色彩浓厚,总统权力强大,议会和司法机构权力弱小。埃及多党政治确立后,议会内执政党一党独大,不公平的政党竞争关系一直存在。埃及政府主导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有权通过政党委员会决定新政党组建与否。表面上埃及新政党不断涌现,民主氛围活跃,但政党的生死和发展并不掌握在自己和支持者的手中,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很多政党在90年代皆因政府压制而停止活动。[注]Joshua Stacher, “Parties Over: The Demise of Egypt’s Opposition Partie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1, No. 2, November 2004, p. 215.民族民主党还通过各种方式强化选举操控,在议会中处于绝对优势。在1990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获得的议会席位数量占比分别高达81%和94%。[注]Eberhard Kienle, A Grand Delusio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gypt,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p. 51.剩余的少数席位大多由依附于民族民主党或在其压力下妥协的独立人士获得,他们大多是高级军官和上层精英,普通人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政党途径表达政治诉求。在政党体制外,埃及政府通过《紧急状态法》压制民众的政治表达权利与言论自由。虽然2000年7月埃及宪法法院裁定将选举程序置于司法机构的全面监督下,但穆巴拉克在其担任总统的最后五年间仍不断强化对反对党、穆兄会以及各类行业协会的控制,使埃及的多党政治始终徒有虚表。
不难看出,埃及的政党政治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表面上自由的反对党实际上受到当权者的明显压制与束缚,政党政治机制不健全,政治精英化严重,包括青年在内的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强人政权和威权政治的传统和社会环境持续存在;二是世俗政党长期主导埃及的政治发展,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大多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而长期以来教俗力量的对抗与冲突阻碍了政党自身和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抑制了民众进行有序和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也阻碍了包容性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 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困境和特点
当代埃及政党政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青年政治参与方面。威权主义虽然给埃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在青年政治参与的问题上,埃及政府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自华夫脱党创立以来,埃及政党大多奉行精英统治,无论是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反对派内部,少数精英贵族长期把持领导权,普通党员与青年的激进主张无法表达,其政治诉求普遍受到压制。[注]谢志恒:《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华夫托党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66页。
从执政党内部来看,青年政治参与受到的制约贯穿各执政党执政时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建立初期,联盟内部青年成员数量庞大,他们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抱有较高期待。纳赛尔满足了青年的部分诉求,吸收大量青年进入国家官僚机构,但要求青年保证不参与对政府的“革命活动”,使他们服务于威权主义政府,这实际上销蚀了青年的政治立场,剥夺了青年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注]Haggai Erlich,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in 20th Century Egyptian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4, 1989, p. 171.
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埃及经历了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开放的过程,但整体上该党代表的仍是军政高官集团和资本大鳄的利益,始终坚持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青年无法参与到党内核心决策,党内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注]哈全安:《中东史》,第568页。党内精英选拔缺乏完善的民主程序,任命权集中在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局手中,党内选举遵循既定的潜规则,多数青年无法有效表达自身诉求。青年曾期待萨达特时期多党政治下的民族民主党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但未能实现。虽然当时党内许多青年参加了高校学生会组织,但学生会缺乏自主权,财政严重依赖政府,学生却不能自由表达观点,其活动受到政府控制。
穆巴拉克时期,民族民主党内部形成了复杂的派系和利益团体,被称为“迷你的埃及政治体系”[注]Virgine Collombier, “The Internal Stakes of the 2005 Elections: The Struggle for Influence in Egypt’s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1, 2007, p. 95.,权力斗争层出不穷。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民主党面临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考验,党内各派特别是新老两代人之间对于党的运行机制和纲领存在巨大分歧。在2000年的埃及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444名候选人中只有175人当选。此次选举中有2,500多名党员的参选申请被拒绝,其中大多数是青年。这次大选也暴露出民族民主党内部的代际矛盾,老党员被称为“老顽固”和“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地位的守旧领导人”,青年党员则经常对旧领导层发起激烈批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注]Mona Makram-Ebeid, “Egypt’s 2000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8, No. 2, 2001, pp. 33-34.
从反对派内部来看,青年的政治参与也遭遇类似瓶颈。穆兄会曾是埃及青年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在相对自由的宪政时代,青年在穆兄会的政治抗争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该组织依靠植根于埃及社会深厚的宗教传统成为青年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平台。但在穆兄会内部,组织权力集中,领导人长期把持权力并将个人思想上升为组织主张,而伊斯兰传统中服从长者的观念,使青年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以服务于穆兄会的政治目标。纳赛尔政权对穆兄会的严厉打压,使青年试图通过宗教动员来参与政治的道路完全被封闭。虽然重建后的穆兄会政治立场和手段渐趋温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成员并获得学生会的支持,但青年在穆兄会内部的参政道路未被彻底打通,领导人权力移交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变,如2004年1月总训导师马蒙·胡代比去世后,穆兄会领导层很快指定由穆罕默德·马赫迪·阿齐夫继任总训导师一职,广大下层青年丝毫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注]Carrie Rosefsky Wick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volution of an Islamist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02.
在穆巴拉克时期,新华夫脱党是埃及世俗主义政党中的活跃力量。但和多数埃及政党相似,老一代领导人长期垄断党的权力和发展方向,萨达特时代出生的青年常常受到党内领导层的排挤。新老华夫脱党甚至在成员组成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新华夫脱党24.7%的领导层成员和33.3%的普通党员来自老华夫脱党。老一代对新华夫脱党领导层的把控,使青年难以涉足党内高层事务。总体上,新华夫脱党领导人多是自由军官组织革命前的精英人物,如老华夫脱党领袖福阿德·萨拉格丁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担任新华夫脱党领导人,直到1998年去世,享年90多岁,被称为“元老中的元老”。[注]Steve Negus, “Egypt: A Come-back for the Wafd?,”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No. 633, 2000, p. 24.新华夫脱党还因政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纲领与埃及政府的主张存在差异,不断受到政府和执政党的压力,处在政党政治的边缘,难以为青年参政提供宽阔的外部舞台。
在上述背景下,在埃及主要政党内,青年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青年的政治参与受到来自政府和政党内部的双重压力。埃及各政党,尤其是反对党内部的青年政治参与面临来自党内组织的阻力,同时威权主义政府对各政党持续施压,进一步削弱了青年参政的权利。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频繁动用《紧急状态法》,直至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虽然此举最初是为应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对政府的威胁,但很快就成为防范反对党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手段。[注]Gregory Starrett, Putting Islam to Work: Educatio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in Egypt Comparative Studies on Muslim Societi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91.埃及政府依据《紧急状态法》限制言论自由,严格管制电视和广播等媒体,使包括青年在内的许多倾向于支持反对党的民众难以全面获得反对党的活动信息和最新状况。[注]Eberhard Kienle, A Grand Delusio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gypt,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p. 55.尽管穆兄会不断加强对高校学生会的渗透,但政府对学生活动的整体限制使青年学生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空间被严重挤压。如新华夫脱党出于选举需要与政府开展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主动调整该党报刊的宣传内容和手段,保持同埃及政府步调一致。[注]Steve Negus, “Egypt: A Come-back for the Wafd?,” p. 24.
第二,各政党中青年成员数量众多,但力量十分有限,无法突破政权和党内守旧势力对其参与政治的阻挠。近数十年来,埃及青年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注]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nd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Denmark: Scanprint, 2014, p. 177.但青年在政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仍十分有限。在萨达特时期,除穆兄会外,“伊斯兰团”、“埃及伊斯兰圣战”、“赎罪与迁徙”等伊斯兰激进组织中吸收了数量众多的青年支持者,尤其是学生占比较高。[注]冯璐璐:《从青年学生“回归”伊斯兰现象透视萨达特时期的伊斯兰运动》,载《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第64页。在萨达特政府的威逼利诱下,青年群体同样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政治抗争力量。穆巴拉克时期,由于反对党弱小且埃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遭遇失败,许多青年发起社会草根运动,呼唤社会改革,但青年的自发运动力量分散、缺乏协调,政治主张大多不成熟、不完善,得不到民众的普遍响应,极易受到政权和党内守旧力量的压制。这种草根运动本身也凸显出青年依靠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效果不彰。[注]Nadine Sika,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Egypt: From Abstention to Uprising,” p. 184.
第三,多数青年处于社会下层,在政治参与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严重。埃及政府拥有庞大的官僚阶层,1986年埃及政府继续扩充行政事业队伍,各行政等级间隔阂明显,上层人员官僚作风十分严重,与下层联系稀少。[注]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少数处于上层的青年能够实现部分参政权利,但1985年埃及政府取消毕业生分配政策后,多数下层青年在政府官僚主义的压制下更加难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各政党内部,上层领导人的后代可以轻易接替老一辈领导的职位,而处于底层的多数成员则很难晋升。2002年民族民主党改革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之子走上了领导地位,而对于多数青年来说,政治参与则遥不可及。
三、 政党政治背景下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从政党角度来看,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与埃及的政治传统、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埃及长期存在的威权体制是青年政治参与受阻的制度性障碍,而威权主义与家族世袭的深厚传统在政党内部组织体制中的延伸,则是阻碍青年政治参与的内在因素。从古埃及的法老专权到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的专制主义,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统治到奥斯曼帝国的自治行省,埃及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不断加强。近代以来,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统治延续了君主专制,即便是立宪君主制时代,埃及人仍希望精英人物带领他们走向民族解放和自由。“七·二三”革命后,埃及确立了新型威权政治。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及其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表现,使其成为了埃及人心中崇高的领袖,[注]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为他建立集权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尽管埃及在后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经历了经济开放和政治民主化,但该国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传统被保留了下来,选举被操控,政府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以随时压制任何反对或质疑政府的势力,成为包括青年在内的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结构性障碍。
穆兄会受制于威权主义政府的压制,无法为青年在合法体制内提供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与穆兄会的关系总体处于“冷和平”状态,但政府对穆兄会时刻保持警惕,并不断加强控制。尽管穆兄会控制着埃及主要高校的学生会团体,但高校同样没有政治自由。在穆兄会影响力较大的其他领域,如金融和各行业协会中,穆兄会的组织形式仍是精英式的,内部缺乏民主,领导任职时间长且权力过大,决策不透明。[注]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2007年埃及宪法修正案则规定“不允许在宗教框架内或以宗教名义、性别和出身为基础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或组建任何政党”[注]Nathan J. Brown, Michele Dunne and Amr Hamzawy, “Egypt’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3, 2007,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07/03/23/egypt-s-constitutional-amendments-pub-19075, 登录时间:2018年1月20日。。宪法在继续将穆兄会定为非法组织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将穆兄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此外,穆兄会内部组织结构纷杂,实行的“家庭制”使阶层等体制固化,青年发表意见的渠道十分不畅,加上部分领导人的阻挠,各阶层青年之间以及青年与领导之间关系阻隔重重。
同样,在执政党的影响下,包括新华夫脱党在内的政党内部都出现了各种利益团体和裙带关系,他们中许多人在地方享有较高声誉和地位,拥有众多地方支持力量。裙带关系使得党内权力中心非常稳固,处于边缘的青年成员无法参与党中央事务,久而久之彼此隔阂,矛盾不断。虽然许多青年加入新华夫脱党的初衷是“以华夫脱党为载体来实现政治理想”[注]Ramond A. Hinnebusch, “Party Activists in Syria and Egyp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uthoritarian Modern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 No. 1, 1983, p. 89.,但实际上真正参与党内事务的青年少之又少,致使其受到领导力量的排斥,对外部青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面对许多领导人雄厚的势力,党内青年既无法融入其中,也无力与之抗衡,造成青年不满加剧。
其次,埃及青年面临教育、就业、健康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政党无法提供必要的参政机会和发展机遇,极大地制约着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程度。埃及青年人口数量大,教育和就业机会等严重不足,青年受教育的权利直接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背景挂钩。埃及学校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公共学校资源不足,教学机构内部人浮于事,缺乏效率,大学行政人员占教职人员半数,[注]刘海军:《冷战后埃及青年问题初探》,载《当代青年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2-123页。严重影响着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同时,青年人口剧增加剧了埃及社会的就业压力,导致失业率高,而青年的就业与家庭出身、城乡差异、教育质量高度相关,家庭出身好的青年往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2011年埃及中央统计局数字显示,18~29岁青年人口约1,900万,占劳动力市场的51.9%,失业率却高达20.4%。城市青年失业率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整个开罗地区15岁以上适龄工作的青年失业率也达到10.78%,开罗老城区更是达到了19.7%。[注]Mohamed Fahmy Menza, Patronage Politics in Egypt: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and Muslim Brotherhood in Cairo,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61.巨大的就业压力使青年无心专注政治,政党内部的参政障碍进一步抑制了青年的热情。
此外,埃及青年还遭受严重的健康危机。面对就业、家庭婚嫁等诸多问题,多数青年无力承担,从而选择放弃自我,吸食毒品特别是大麻、海洛因和麻醉性毒品成为青年常见的恶习。2004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埃及15~25岁的青年中有2.5%~3%有过滥用药物的经历,1%的青年吸食过毒品。[注]Sameh Sh. Zaytoune et al., “Patterns and Distribution of Drug Dependence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among Male Youth in Upper Egypt,”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Vol. 131, No. 2, 2015, pp. 191-192, 194.青年用日益糟糕的身体状况来换取虚幻的精神慰藉,直接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兴趣,进而产生反抗心理,导致更多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在影响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同时更危害了埃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埃及青年深受当代西方思想影响,政治民主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与政党内部老一代之间存在巨大的代沟和观念差异,守旧力量长期存在使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难以畅通。
2005年,人民议会废除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制度,允许多党多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注]王泰:《2011,埃及的政治继承与民主之变——从宪政改革到政治革命》,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5页。在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的领导下,民族民主党的青年改革派有力地推动了总统选举进程,但是保守派很快就强化了其在党内选举和人民议会选举中的力量,最终成功地限制了议会中青年的数量,保住了议会主导者的地位。穆兄会内部的新老团体间矛盾同样突出,老一代领导人阻碍了青年政治抱负的施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观念的更新和时代的发展使得埃及青年更易接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理念。互联网的兴起使得更多青年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政治愿望。穆兄会老一代领导者大多是哈桑·班纳思想的执行者,无法接受青年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诉求,不希望自己的裙带关系被打破,因此总是试图控制总训导师职位和协商议会,组织关系缺乏更新,青年政治参与被阻断。在新华夫脱党内部,青年更注重实用和妥协退让,而老一代领导人则顽固保守。[注]Dina Shehata, Islamists and Secularist in Egypt: Oppos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Routledge, 2010, p. 147.代际差异和思想分歧造成二者在党内沟通上存在问题,青年的激进思想遭到老一代的否定和反对,从而限制了党内青年力量的壮大,造成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持续加剧。同时,新华夫脱党深受旧华夫脱运动的影响,来自旧华夫脱党的领导人不愿让青年参与政治决策,青年党内政治参与举步维艰。
四、 埃及青年政治参与不足的社会影响
青年参与政党政治的困境折射出埃及政党政治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埃及政治稳定以及社会秩序形成了冲击。
首先,反对党内部老一代与青年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党内部分裂与政党实力被削弱,青年群体在与威权主义政权的抗衡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在穆兄会内部,青年努力使该组织成为合法政党,但以老一代领导人为首的守旧派安于现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拥有新思想的穆兄会青年成员与长期在纳赛尔时期被囚禁的守旧派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分歧。[注]Yokoda Takayuki, “Democratization and Islamic Politics: A Study on the Wasat Party in Egypt,” Kyoto Bulletin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No. 1-2, 2007, p. 151.1996年,以马迪为首的青年领导人宣布成立中间党,旨在弥合分歧,[注]Carrie Rosefsky Wickham, “The Path to Moderation: Strategy and Learning in the Formation of Egypt’s Wasat Part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6, No. 2, 2004, p. 208.但因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最终与穆兄会决裂。尽管中间党的政党申请未被穆巴拉克政府接受,但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仍不断发展。2011年1月21日,一批青年脱离穆兄会,建立奉行中间主义的埃及潮流党[注]埃及潮流党在2014年被并入强大埃及党(Strong Egypt Party)。。潮流党持更加自由化的伊斯兰政治立场,将青年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注]Matt Bradley, “Young Brothers Rebel in Egyp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11,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970604576401923397045788, 登录日期:2017年10月14日。倡导政教分离,保护个人自由,宣扬在不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同时接受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注]“In Egypt, Youth Wing Breaks From Muslim Brotherhoo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6/23/world/middleeast/23egypt.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4日。潮流党的出现反映出穆兄会内部青年对守旧派的反感和不满。
新华夫脱党内老少两代斗争也导致许多青年选择脱党,加入或组建新的政党,与母党展开竞争,这进一步削弱了华夫脱党的实力。如2004年由前华夫脱党青年创建的明日党和“受够了”运动,吸引了大量华夫脱党青年的参与。青年党员的流失削弱了华夫脱党的活力和号召力,极大影响了该党为适应时代变化而采取的发展模式。青年尝试结束守旧派控制的政党,终止教俗力量之间的对立,却受到华夫脱党和埃及政权内老一代的阻挠与限制。
其次,各政党内部因精英统治、青年缺乏参与,导致腐败问题严重,民主政治发展滞后。
由于缺乏拥有新思想的青年加盟,民族民主党依旧按照传统方式运作,缺乏活力,腐败丛生。埃及从纳赛尔时期就形成了强大的官僚政治力量,用以控制民众和社会资源。这些官僚唯恐失去地位,其政治精英力求控制政府并拥有长久权力。[注]Auda Gehad, “Egypt’s Uneasy Party 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 No.2, 1991, p. 77.民族民主党在改革中对青年采取打压政策,使保守派和改革派难以达成共识。“尽管民族民主党在2000年着手就埃及未来发展开启内部对话,但新思维并没有在党内各层完全贯通。”[注]Virgine Collombier, “The Internal Stakes of the 2005 Elections: The Struggle for Influence in Egypt’s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1, 2007, p. 98.2005年之后,民族民主党虽然意识到自身问题,但仍缺乏措施来扩大青年的政治参与,直到穆巴拉克政权被颠覆,民族民主党也没有解决好腐败问题。此外,民族民族党僵化的党内运作延续了威权政治,执政党一党独大,反对派政党势单力薄。虽然各反对派极力抗争,但威权主义的政治局面始终没有被打破,民主政治转型困难重重。
在新华夫脱党内部,青年政治参与的缺失造成领导层封闭僵化,盲目自大,独断专行。2005年该党领袖努曼·古玛参加总统竞选败北后,却在随后的议会候选人提名时取消批评他的候选人的提名资格,禁止该党报纸报道选举时出现涉及批评他个人的内容,禁止党内成员在各自地区寻求反对古玛的势力。[注]Dina Shehata, Islamists and Secularist in Egypt: Oppos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p. 76.内部纷争削弱了新华夫脱党的政治影响力,使伊斯兰联盟获得更大优势。在2005年的埃及人民议会选举中,世俗反对派遭到了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联盟的毁灭性打击,仅获得12个席位(不足3%),而穆兄会则获得88个席位(20%)。[注]Ibid., p. 140.新华夫脱党世俗反对派的领导地位大为动摇,开始从一个崇尚自由的政党变成了随波逐流的政党,逐渐接受威权主义的统治和伊斯兰主义的渗透,陷入了为生存而挣扎的境地。[注]Nervana Mahmoud, “The New Old Wafd,” Nervana, May 28, 2015, https://nervana1.org/2015/05/28/the-new-old-wafd/,登录时间:2017年10月5日。
穆兄会青年政治参与的缺乏,助长了政府对它的控制。在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下,穆兄会为延续其政治上的温和策略,尽可能防止新生力量涉足穆兄会政治核心,以免与政权对立,而政权可以随时压制穆兄会,穆巴拉克利用穆兄会的非法地位限制其调动政治资源。[注]Yokoda Takayuki, “Democratization and Islamic Politics: A Study on the Wasat Party in Egypt,” p. 160.因此,穆兄会很难获得底层民众参与和青年的普遍支持;而排斥青年的观念又导致穆兄会进一步被政府压制,形成恶性循环。青年参政不足造成穆兄会在政策与行为上缺乏活力,妨碍其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合作。没有强大的内部改革压力,穆兄会极易恢复“伊斯兰是解决方案”的传统主张。穆兄会领导的伊斯兰联盟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最大反对派组织后,对世俗反对派就形成了压倒性优势,进而强化了对青年改革主张的排斥和传统保守势力对权力中心的控制,增强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主张,忽视与世俗派的合作,加剧了反对派势力间的不和,有利于执政党长期控制政权。
再次,对政党政治的绝望使埃及青年选择加入非政府组织等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和控制的组织,对埃及社会稳定和国内团结造成负面影响。
在穆巴拉克时期,非政府组织成为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参政的一种替代选择。在埃及国内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由1976年的7,500个增长到2005年的20,000个,其中宗教非政府组织增速最快,占所有官方承认组织的40%。[注]Yokoda Takayuki, “Democratization and Islamic Politics: A Study on the Wasat Party in Egypt,” p. 37.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和自由性使其在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作用。1985年,埃及人权组织宣告成立,之后人权非政府组织数量增长迅速,并在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注]Ibid., p. 66.自2005年以来,埃及政府允许国内非政府组织监督议会选举。人权非政府组织培养了数千名选举监督人员,与国际机构及国家人权理事会开展合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埃及选举违规情况的报告。选举监督的实践促进了埃及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巩固了自身地位。非政府组织更是埃及女青年参政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有效途径。[注]Sunny Daly, “Young Women as Activists in Contemporary Egypt: Anxiety, Leadership,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Vol. 6, No. 2, 2010, p. 81.
由于政党不能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参政渠道并维护其利益,青年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放弃加入政党和从事政党活动,[注]Nadine Sika,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Egypt: From Abstention to Uprising,” p. 194.加入非政府组织成为埃及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替代选择。由于许多非政府组织具有国际性,资金多来自西方国家,其中充斥着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思想渗透,西方国家妄图借此加强对埃及的影响,并为自身利益鼓动埃及各种势力的纠纷和斗争,严重影响着埃及社会稳定。因此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通过多种方式遏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导致在内外夹击中发展的埃及非政府组织很难作为青年参政渠道。而受到西方操控的非政府组织日益左右埃及人的思想,加剧了埃及国内社会的不稳定。
最后,青年政治参与受阻而又无力改变现状,青年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使其最终走向以激进方式进行街头抗争,这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直接因素之一。
政治参与不畅及执政党内部的问题加剧了青年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由于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在威权政治体制下,青年的自我认同容易在理想和现实的混乱中迷失,产生对社会的抵抗情绪;教育、医疗及就业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造成青年大量脱离政党组织以及暴力事件的增长,有些青年甚至加入极端组织,对埃及社会经济稳定造成威胁。
威权政治下青年难以参与政治决策,加速了民族民主党固有问题的恶化。总统权力过于集中,执政党不断打压反对党,民主政治几乎被破坏殆尽。在选举方面,民族民主党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规则并以整个国家机器为后盾,利用国家资源与反对派竞争,压制反对派媒体,甚至公开舞弊。[注]陈文、胡胜全:《从金字塔顶溃落:埃及民族民主党垮台的系统因素分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1期,第111页。在2010年的埃及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再次操纵选举,获得97%的选票,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在威权主义弊端成为埃及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时,埃及人民开始放弃穆巴拉克及其民族民主党。埃及是中东地区使用社交软件人数最多的国家,[注]Carrington Malin, “15 Million MENA Facebook Users — Report,” Spot on Public Relations, May 24, 2010, http://www.spotonpr.com/mena-facebook-demographics/,登录时间:2017年3月13日。埃及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动员反对政权的力量。他们的政治诉求从要求穆巴拉克进行政治改革,到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和推动起草新宪法,体现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动员力量。在以青年为主体的民众呼声中,穆巴拉克被迫辞职,埃及议会解散,《紧急状态法》宣布废止,埃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五、 结 语
埃及青年的政治参与是埃及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产生于近代以来埃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社会背景下,其发展状况深受埃及政治环境的影响。在立宪君主制时期,由于埃及社会控制相对宽松,青年单独成立组织或作为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纳赛尔时期,埃及推行威权政治,青年的政治参与受到限制。萨达特开放党禁后,青年的政治活动重新活跃。从萨达特1978年实行政治开放政策、允许建立新的反对党,到穆巴拉克推行议会选举,埃及政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埃及作为执政党一党独大、总统权力不受约束的威权主义国家,总统通过执政党和行政资源操纵选举,打压反对势力,长期把持政权,权力更迭和监督受阻,造成利益分配固化和社会严重分化。同时,从执政党到各反对派,埃及政坛的裙带关系和老人政治问题突出,各政党中的青年成员数量巨大,却不能对政党纲领与政策产生有效影响。面对执政党对反对派的压制和政党内部老一代精英对普通青年的压制,青年在无法解决教育和就业等问题而感到迷茫时,在无法通过现有政党和合法体制争取权利和利益保障而感到绝望时,冲破现有体制的束缚、走上街头抗争成为了他们的最后选择。